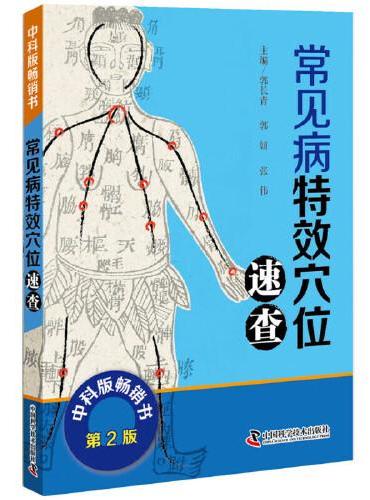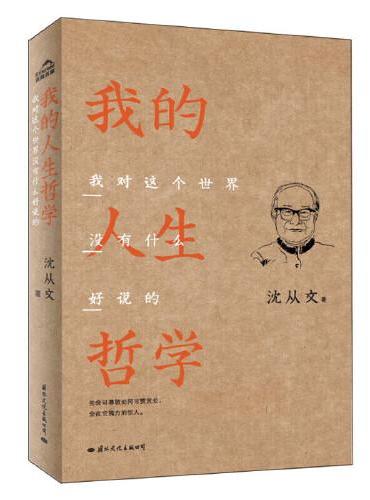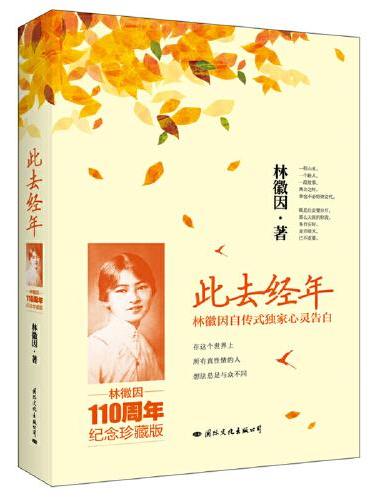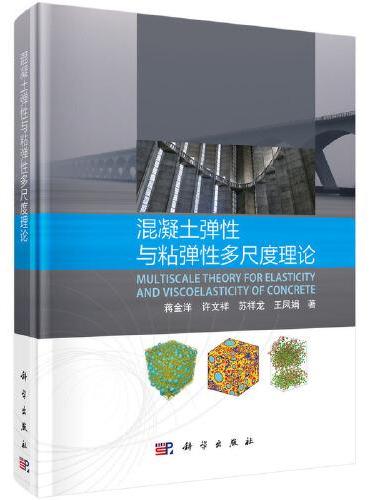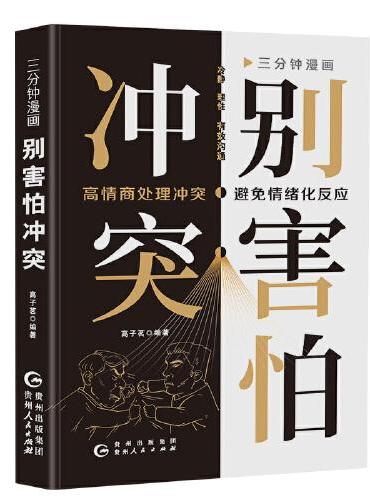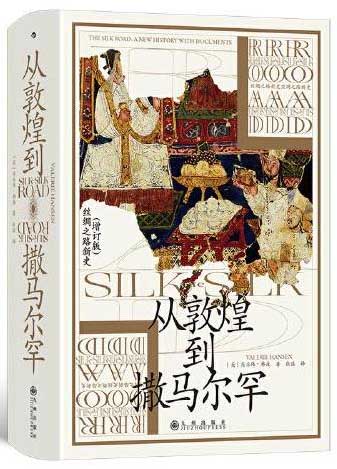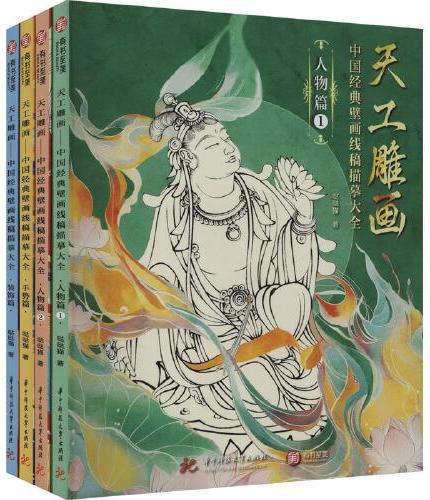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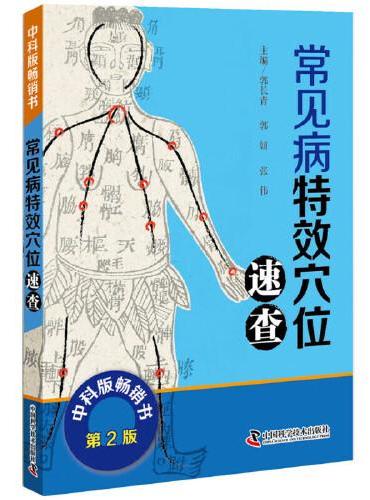
《
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
》
售價:HK$
3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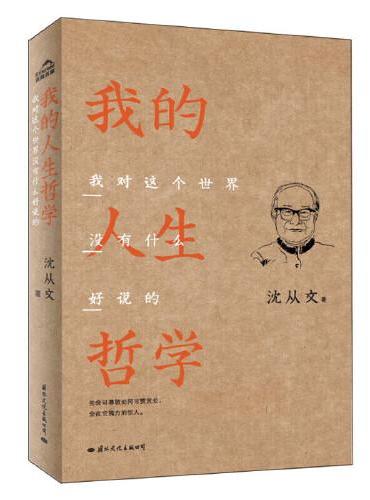
《
我的人生哲学: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
售價:HK$
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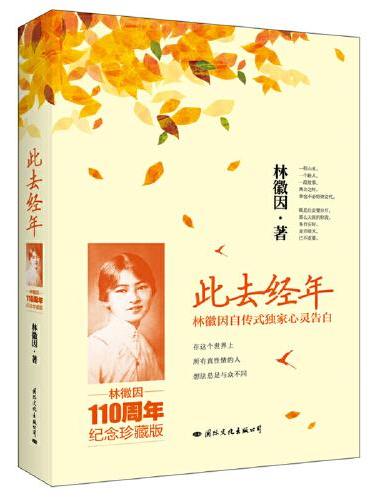
《
此去经年:林徽因自传式独家心灵告白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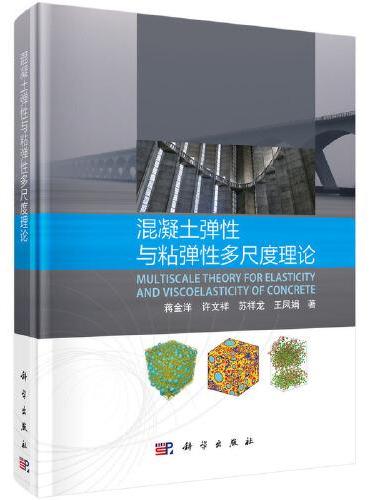
《
混凝土弹性与粘弹性多尺度理论
》
售價:HK$
18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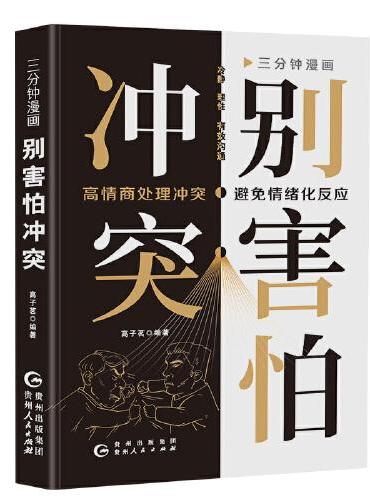
《
别害怕冲突 高情商处理冲突避免情绪化反应 揭秘冲突背后的复杂原因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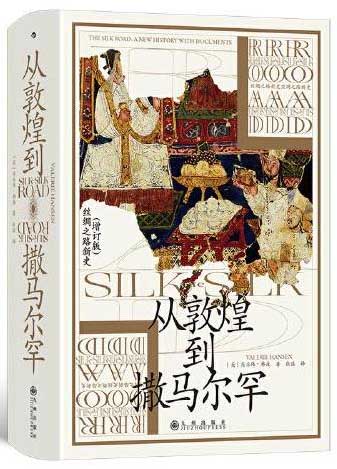
《
从敦煌到撒马尔罕 汗青堂丛书002
》
售價:HK$
118.8

《
梁衡给孩子的365堂作文课(孩子听得懂、学得进、用得上的大师级作文课)
》
售價:HK$
28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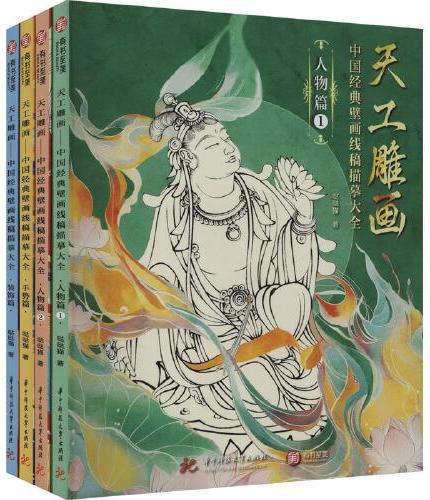
《
天工雕画:中国经典壁画线稿描摹大全(全4册)
》
售價:HK$
217.8
|
| 內容簡介: |
|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结束了一直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封建帝制,让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中国又进入了长时期的军阀混战时期。辛亥革命除了造成清政府的灭亡以外,却还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如何厘清辛亥革命的全貌?本书对辛亥革命做了一个完整梳理。本书编选了著名学者如杨天石、马勇、桑兵等关于辛亥革命的著名阐述24篇文章,从方方面面使读者从一本书即可清楚准确的了解辛亥全貌。本书虽是文章合集,但有自己独特的编排体例,即有对史事的考辨历史的复原,又有思想的阐释,更有人物的评传,并且所选文章均可读性很强,适合一般读者以一书而知历史全貌。
|
| 關於作者: |
|
邓文初,1968年生,湖南宝庆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研究生毕业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思想史专业;2005年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毕业,获史学博士学位。曾在媒体做过编辑、记者与策划。
|
| 目錄:
|
导读 001
邓文初
篇
鼎革之际的角力
1911:中国大变局 017
晚清政治改革:逻辑与困境 029
辛亥革命何以胜利迅速,代价很小 038
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 064
新政困局与辛亥革命 075
王权衰落与地方主义 100
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114
民初国会存废之争与民国政制走向 124
第二篇
新世纪的宣言
近代民权政治的起源 133
民国初年政治结构和文化初探 144
“梁启超之问” 160
民初有关共和制度的争论 181
政治浪漫主义与中国早期议会民主 198
略论中国革命的法兰西风格 215
《新世纪》——“破坏者”的登场 225
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兴起 235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民粹主义 247
清末的民族主义 260
第三篇
不安定的底层
“群众心理”的兴起 271
成都的街头政治 286
秘密会党与辛亥革命 302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运动的新发展 313
论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会党的特征 329
会党与辛亥革命前夜之广东社会政治 344
辛亥革命与游民社会 358
|
| 內容試閱:
|
导读
邓文初
那一年发生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一个旧朝廷的结束,一个新政权的开始。
那一年的历史书写其实也应该很简单,大清结束了,《清史》诞生了。一部官定的史书,本该是盖棺定论的工作了。
然而似乎有些例外。清亡了,民国江山也改易了,却连一部晚清史都难以出产,遑论正史体系中的《清史》了。
究竟遇到了怎样的困境,使得历史学家们如此踟蹰?
其实,经过一百多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文献工作,成千上万的“历史工作者”生产了数千万上亿的史学文字,历史这具木乃伊早已被层层拆开,躯体经过一片一片的CT扫描,检测报告已足以将历史事件本身纤细无遗地呈现,史学文字甚至比历史本身更为浩瀚,足以覆盖历史本身的言说。然而,历史知识越来越丰富的我们,或许对历史的理解越来越迷乱。被过度诠释的历史犹如掺入三聚氰胺的牛奶,不仅因稀释而流于肤浅,更可能因添加而毒化大脑。历史学者自然应该在越来越窄越来越尖的问题上深掘,但这样的一味深掘也可能将我们这些常人带入一个缺乏氧气的地下暗层或者一个陷阱。本来应该将读者带入更为深远的智慧之境,但远离常识的发明很可能使我们失去对历史的真切体会,这就是史学的悖论。
我总觉得,史学家们不免要置身于旋涡、纷乱和陷阱之中,探讨那些被人类遗忘的边角碎料,注视那些令人眩晕的幽暗深渊,挑战自己的眼力、智慧和勇气,但正如那些艺术家一样,在他们因好奇而窒息之前,总该浮出水面,仰头长长地吸一口新鲜空气,将其作品献给我们的普通读者。
选编这本集子的初衷就在这里,从近千万字的各类论文论著中挑选出二十万字的作品,从而避免了史学诠释给人造成理解力麻痹,带我们回到具体可感的历史时空。
一
1911年,岁在辛亥。
先的场景也许应是清廷的退场,一场略显尴尬又不失优雅的谢幕。这是习惯了鼎革之际的那种杀人如麻、血流漂杵之历史故事的国人们难得见到的稀有历史场景,也是尘埃落定后回首前尘时我们才会想起的略带温情的历史画面,或许还是智者们事后总结历史规律时高声提醒我们的要珍惜的政治智慧。可能也正是因为它的特殊,才让诸多的历史学人在百年之后产生依稀牵挂与感伤:随着帝国的消失,数千年的大一统创设的那套文化、制度、价值与生活,真的就该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吗?何况,十年前的大清已经全面启动现代化的历史车轮,一个有勇气将手术刀指向自己的政府难道应该遭受这样的命运不公吗?
是谁之过?
其实,这样的“世纪之问”不仅扰乱了历史学者平静的书桌,还在本来不太安静的学界点燃了神经症式撕打的硝烟,壁垒分明的知识立场因此更加壁垒森严。归罪清廷愚钝的,指责革命捣乱的,在改良派中寻找线索的,在枭雄们的计划中发现阴谋的,将矛头直指那些无知而鲁莽的青年学生的,将激烈而暴躁的科举精英绑上历史审判台的,比比皆是。文化的反思、人性的剖析、制度的梳理、行动的复盘,再加上学者们相互不服气,互相轻视与嘲讽,知识界因为“那一年”历史耗费了大量的脑力,试图在纷乱混杂中找出某种“根本因”说服他人并证明自己。
然而,历史从来就没有根本因,有的只是众缘所凑的一张因陀罗网。
其实,如果放宽视野,不是局限在“那一年”的时空里,如黄仁宇所说,在中华第三帝国的长脉络中,在自朱明王朝以降的连续时空中考量“那一年”的史事,其事故、灾变中的偶然就会呈现出清晰的轮廓和意义。那不是某些表层力量的临时角力,也非当政者的几步棋走错,而是五百年来的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的慢性失败,是系统失败所呈现的免疫力缺失与急性溃疡,因某些偶然因素而走入一局死棋。也因此,为破解这一死局而启动的所有力量、招术、谋略、布局、攻守,既有应对糜烂之局的急就章,又有应对五百年来大势变迁的长期考量。因此辛亥之年既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普通年份中的一个。
在《天下1:明清对外战略史事》一书中,我提出的这条理解中国历史的长程脉络,也是莫里循、芮玛丽、孔飞力、麦金农等欧美学人的观察报告,尽管他们的论题集中在晚清,但一样抓住了帝国政治的一贯逻辑,那就是中央帝国的改革从来没有停止,不仅没有停止,而且以一种强大的加速度向深度与广度扩张。其激进性,从西方人的视角看也足以令人惊叹。权力以改革的名义实施全方位的扩张战略,而且变得越来越具有渗透性,其充满活力的“自改革”,往往进入教育、军事、警察、税收、文化、交通、技术等领域,甚至触及县级以下的财政、税收、教育、文化与管理层,而这些本属于乡绅或底层民众自治范围。
任何改革都需要成本,而这种由中央主导的激进改革,往往是借改革的名义将成本转嫁到底层民众的身上。这种以牺牲民众为代价而追求富国强兵、不顾民众承受力与生态稳定等社会后果而希求“傲立”于世,超英赶美,必然引发底层的激烈反弹与周期性的社会震荡。但是,由于不存在民意机构这样的反馈机制,这些由改革引发的反弹就被儒家官僚解读为底层对权力的挑战,理解为规范的失控,由此产生某种“帝国危机”意识。一旦这种危机意识截获帝国的神经,也就启动了黑格尔式的“理性的狡狯”,历史也就进入了新一轮“恶性循环”的怪圈——权力扩张引发社会震荡,社会震荡又反过来引发更为激烈的权力扩张。这样,陷入“恶性循环”怪圈的改革者们,就将自己逼入一种毫无回旋余地的镜像空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四面楚歌、四面受敌,十面埋伏、十面出击,于是将所有那些被激发的不可控因素当作假想敌对待,而不免手忙脚乱、进退失据。这种方寸大乱的失控又与权力意志的独断相互激荡,结果就点燃了隐藏的火药,政局鱼烂、全盘皆输的局面也就降临了。
这是深藏在帝国权力系统中的痼疾,是其刚性结构带来的基因病根,就算对比有着清醒的认知与精确的诊断,也无法抑制与根除这一病灶的发作。何况,在缺乏自我反思与外部监控的帝国系统中,这种病根本就是无可救药的死症。在没有意识到这种死症存在的情况下,帝国却想通过自改革实施自救术,不仅自救,甚至妄想在万国竞争的时代胜出,那就好比启动了一辆没有刹车的高速列车,其危险可想而知。
这种改革所引发的危机,不仅帝国执政者未能意识到,事后的历史学界也未必明白。故提出这些观察报告的往往不是涵泳在这一文化中的学人,而是那些外来的研究者。像法国史家巴斯蒂就敏锐地发现,对立双方的革命党和立宪派,敌对双方的袁世凯和孙中山,其实共享同一逻辑,那就是帝国中央集权一以贯之的强化;美国史家斯蒂芬·麦金农在对袁世凯的研究中也提及这种“几个世纪以来闻所未闻的”权力扩张。其实,如果我们接受他们这一“假说”,一些历史之谜也就能够做出合理解释。比如,何以清朝皇族在退位诏书中要特别加上一句,“着袁世凯组织新政府……”。这句话一直被史学界认作是袁世凯的“自我加冕”,是其抢占权力合法性的政治阴谋。他们忘记的是,一种权力之所以能够平稳让渡,就是因为权力本身并未断裂,而是借着这一时机顺利交接与转移,袁世凯不仅是晚清政府中这波激进改革的重要推手,也是此后的民国政府继续推行这波权力扩张的实质继承人。历史的演进在此显示了它的一脉相承,从当时“非袁莫属”的内外呼声中也是可以读出这条信息的。
因此,清廷的倒台其实就只是这波改革的意外与暂时性的中断,这一“事件性”的中断,并未改变历史的长程进展——无论是帝国的国策、富强目标的追求,中央对地方制约的权力关系,还是社会结构的长期演变方向,以及帝国内部民族关系的处理,在袁世凯出任总统时期,以及在此后的北洋政府时期,仍旧是在旧的框架和旧的问题意识中展开,在展开中试图获取某种结构性重构与达成某种新的权力平衡。由此,辛亥鼎革、民国开场之际上演的那一系列的议会闹剧、党争笑谈,台上崭新的亮相、台下激烈的折冲,其实既无关共和观念也无关思想冲突,只不过是历史进程尚未根治的并发症的发作罢了。
二
历史研究首先应该面对事实,但绝大部分其实是在面对价值,面对钱穆先生所说的“时代意见”而非“历史意见”。正是因为这种“意见”式的历史书写,才会在历史研究中引发对抗性的思想纷争。
这种对抗,早些年是改革与革命的反复翻牌,近几年进入政治哲学领域,在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问题上“商榷”起来。当然,没有谁会愿意回到君主时代,但君主时代的那种天下一统、“国泰民安”的真实与幻象,多少让一些自称的权威主义者和隐藏的国家主义者心动。何况其中还有“后现代”“后殖民”“中国中心观”之类的范式变迁所带来的新奇与时尚,反文化霸权、反西方中心的思想刺激所引发的流量飙升。
如果说,在以前的革命史观中,中国近代的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等政治、生态灾难该由“帝国主义”承担责任的话,那么这一波的反思就将社会的动荡、政治的激化与传统的崩溃归罪于西方的“文化霸权”。在其强势文化影响之下的中国思想界,被公理、自由、民主、人权、共和、平等、博爱、权利、宪法、政党、革命、军国主义、铁血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外来”词洗脑,导致“黄金时代”的终衰落。罪魁祸首就是那些食洋不化、数典忘祖的洋学生、读书人和那些言必称希腊,道必循罗马的知识分子、观念人。
不错,这些“洋腔洋调”“异端异声”确实始终伴随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且一度被史学书写为推进中国近代化的启蒙力量。为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背书的也正是这些出自西洋文明的“关键词”。然而,“中国故事”上演的真的只是贩自西方的“文明戏”吗?近代中国跌宕起伏的悲喜剧,难道其情节、内容,结构、风格不是“中国”的吗?那出神入化的角色扮演、扑朔迷离的变脸戏法难道不是中国人自己天才的本色出演吗?
几个洋文词汇何能搅乱我伟大之中华?!
历史研究不该将这些抽象的观念想象成历史的推进力量,观念从来就是纸上的符号,而历史必是真刀实枪的比拼。热血头颅的抛洒,哪有一丝半毫的虚头巴脑!在枪杆子与笔杆子的较量中,历史无一例外的都是由实在的东西做主,至少,历史的中国如此,那时的中国如此。
将历史变动归结为观念的发生、引介与冲突,是宣传家们的魔术,也是唯意志论的幻觉,但如果历史学者也重复这样的启蒙论,那就不仅是思想的懒惰,更是历史的无知——双重的失误。
基于这双重失误,那些浪漫主义者相信观念的爆炸足以改变世界,那些经验主义者则坚持历史进程应像植物生长一样自然而然,反对理性的设计。双方看似在相互攻难,事实上却共享着同一的思维困境与认知谬误——忽视观念背后的社会情境。然而历史的真实却正是建立在这种社会真实的基础之上的。晚清中国的凋敝窳败,帝国根基的动摇破裂,早已深埋在人们的意识里,深埋在深层的人格分裂与真实的生存血泪里。新概念的浮现与新思想的冲击乃是出自文化人格的爆裂与自我救赎的呻吟,这是随数百年所积劫数而来的心灵压抑、扭曲,焦虑与渴望而发出的生命悲鸣,是生物本能、生存意志的呐喊。如果说它呈现出海浪一般的掀天动地之力量,那也不是思想启蒙的结果;相反,启蒙正是借助这股洪荒之力而掀起了新时代的浪潮。这股洪荒之力,自元明之际延伸至晚清,其释放出来的能量始终没有得到传统文化的安置,没有得到制度性的安排,才不得不以山崩海啸般的气势爆发,正像火山一样,终挤出一条裂隙喷薄而出。
历史从来不是理性的设计,而是力量的较量,是生存意志与生命能力的释放。它表现为情感的爆发、言语的激荡与身体的狂欢。阁楼密谋、街头暗算、广场宣讲、议会嘶喊、谣言飞驰、群氓暴动、会党掠抢、战场冲杀、血与火的漫卷、生与死的狂啸,新名词也会随同传单一起飘洒,新理念更如子弹一般乱飞,这些都是情绪爆发释放出来的信息,是秩序崩溃引发出来的气浪。喧嚣观念的背后,正是被阻碍的社会转型、被压抑的生命势能。其被导向政治反叛的路径,正说明这股阻碍与压制的力量内存于政治结构之中,内存于政治失败与社会崩溃之中。这是一种生命的直觉,无关乎外来观念或翻译思想。
在这样的群情中,政治行动是情绪性的更是宗教性的,是信仰而不是理性,它不受革命者的设计,革命反倒是其意外的产儿。正因为意外,它才令革命者举额庆贺,以为数千年专制可在一夜间颠覆,民主共和制度可凌空蹈虚新建,于是其“毕其功于一役”的浪漫主义遐想被激活。实际上,作为制度的共和政治,与其说是启蒙者的设计,不如说是在妥协中的展开,是为了避免坏结果而达成的折中。在这样的权衡中,一些没有实质意义,可以自由解释的概念,如民主、共和、主权之类,正好符合“小公约数”这一政治谈判条件,从而被抬举为民国招牌。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共和、民主等这些插入汉语世界的外来语?
与其将它当成某种历史的动力,不如将它当成一场深情的告白,那些绝望中的知识人,在绝望的暗黑中,向着同样绝望的同胞和想象中的未来,向着不可见的历史深处——深情告白。正因为绝望、孤独,他们才会如此决绝;正因为现实没能给他们以希望,他们才需要远寻异声;正因为传统没能给他们以光明,他们才需要仰望星空。这是疏离者的孤独,是被母族文化抛弃后的自我放逐。也因为这种放逐,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影子和想象中,生活在观念的洞穴与激情的焰火中。他们的步履是先知者的行程,属于时间之流中的未来时态。
不过,有了这些外来语,历史当事人的演出就有了外来的观众与全球的传播,我们这些读历史的后来者就有了参照的眼光和对未来的想象,历史当前的形态与此后的演变也就有了另一种可能。
思想的价值或许就在于此。
(节选未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