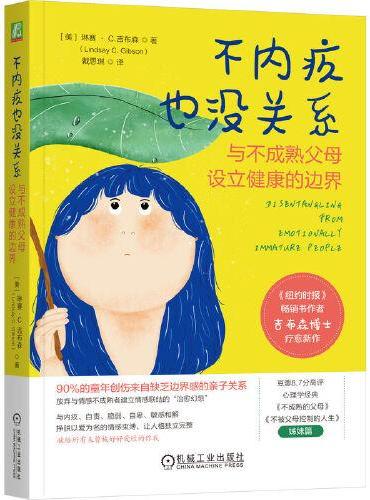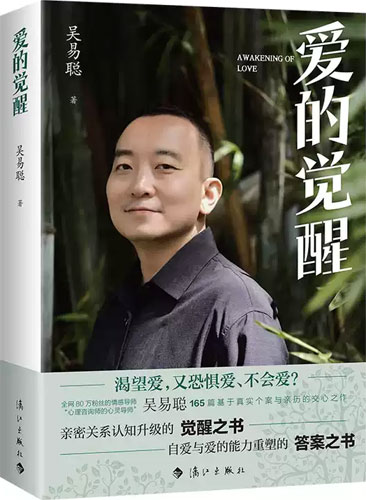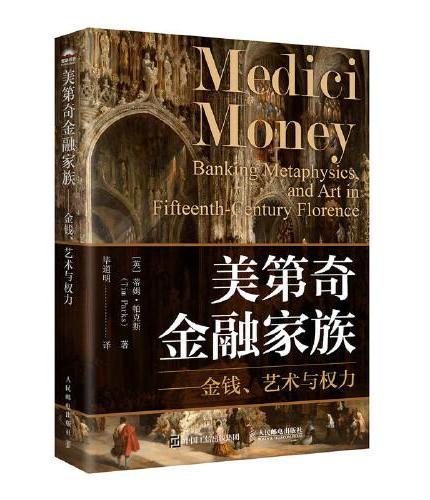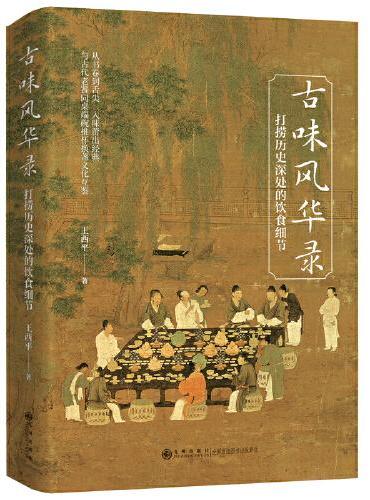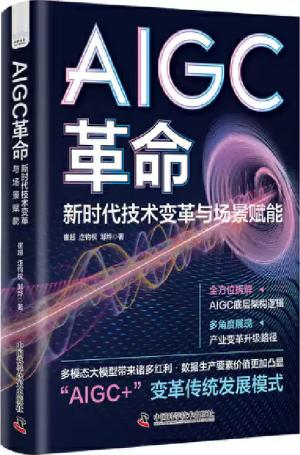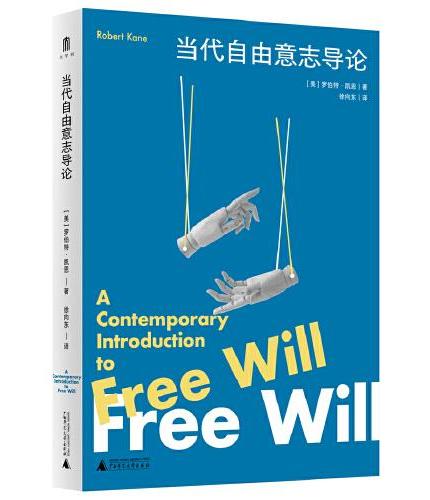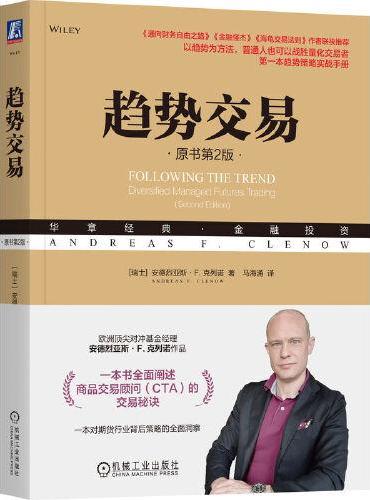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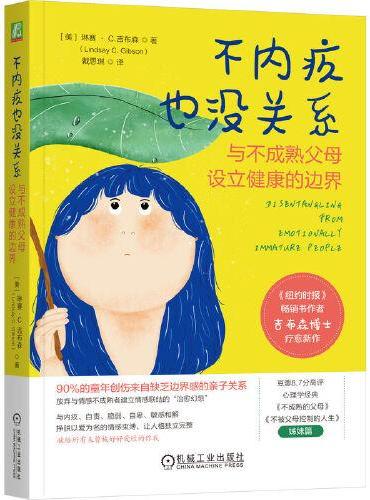
《
不内疚也没关系:与不成熟父母设立健康的边界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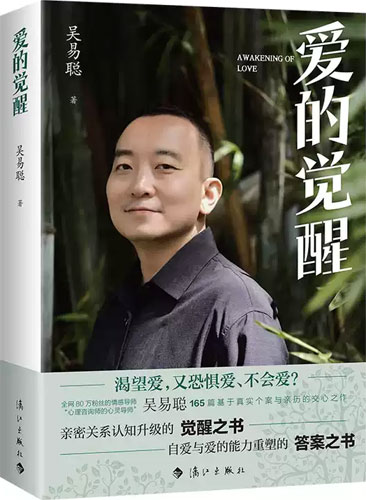
《
爱的觉醒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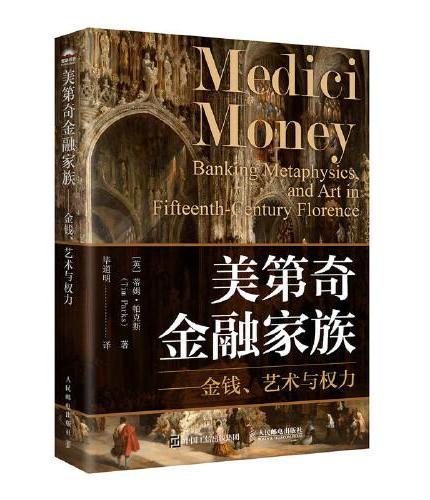
《
美第奇金融家族——金钱、艺术与权力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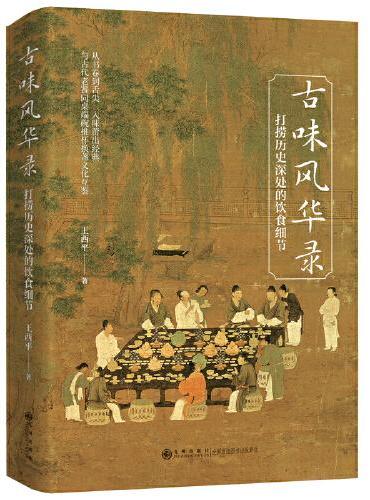
《
古味风华录:打捞历史深处的饮食细节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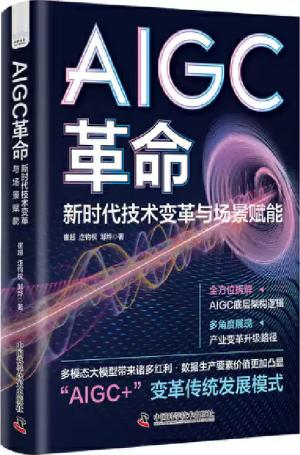
《
AIGC革命 :新时代技术变革与场景赋能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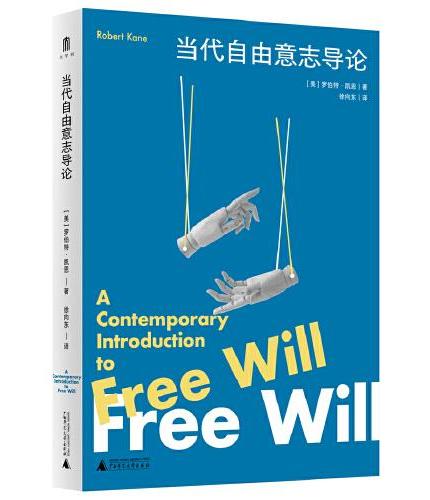
《
大学问·当代自由意志导论(写给大众的通俗导读,一书读懂自由意志争论。知名学者徐向东精心翻译。)
》
售價:HK$
74.8

《
(格式塔治疗丛书)进出垃圾桶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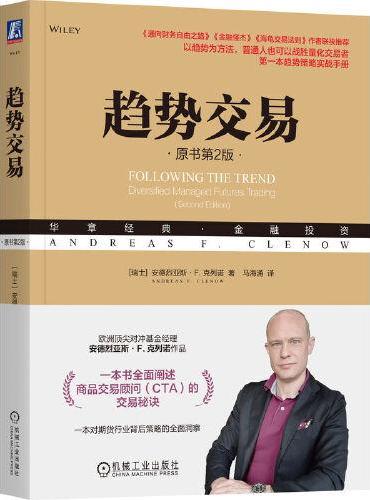
《
趋势交易(原书第2版)
》
售價:HK$
97.9
|
| 編輯推薦: |
“穿上懵懂女孩的旱冰鞋,滑入只有永不相交的危险道路的花园……”
★ 纳博科夫名作《洛丽塔》的雏形
★ 对疯人脑海中幻象的研究
★ 一则优雅而令人毛骨悚然的童话
作为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作品对英文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本系列在已出版的二十余种纳博科夫作品中,精心挑选六种较具代表性的作品,以精装版全新面貌呈现,其中不乏《洛丽塔:电影剧本》等市面上难以寻见、读者翘首以盼的佳作。
《魔法师》是纳博科夫著名作品《洛丽塔》的前身,按作者本人的说法,“魔法师”的书名预示了《洛丽塔》“着魔的猎人”的主旨。在小说中,“魔法师”也是一个中年男子,他向寡妇求爱,为的是要接近她的女儿,终用变戏法式的手段,把欲望变成了童话般的梦,从而创造了和《洛丽塔》截然不同的结局。小说以第三人称叙述,其中的人物没有名字,故事发生的地点也有着异域风情,而《洛丽塔》则以人称详细说明了小说各要素的来龙去脉。即使撇开和《洛丽塔》的关系,《魔法师》仍然是部有趣的作品,值得一读。同书收录纳博科夫之子德米特里?纳博科夫的导读。
欢迎来到纳博科夫的小说世界,在文字魔法师的迷宫
|
| 內容簡介: |
|
《魔法师》是小说大师纳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名作品《洛丽塔》的前身,按作者本人的说法,“魔法师”的书名预示了《洛丽塔》“着魔的猎人”的主旨。在小说中,“魔法师”也是一个中年男子,他向寡妇求爱,为的是要接近她的女儿,终用变戏法式的手段,把欲望变成了童话般的梦,从而创造了和《洛丽塔》截然不同的结局。小说以第三人称叙述,其中的人物没有名字,故事发生的地点也有着异域风情,而《洛丽塔》则以人称详细说明了小说各要素的来龙去脉。即使撇开和《洛丽塔》的关系,《魔法师》仍然是部有趣的作品,值得一读。同书收录纳博科夫之子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导读文章。
|
| 關於作者: |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
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纳博科夫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
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
| 內容試閱:
|
作者按语一
我初感觉到《洛丽塔》的轻微脉动是在一九三九年末,或一九四○年初,1在巴黎,是我急性肋间神经痛发作、不能动弹那个时候。依照我所能记起来的,初灵感的触动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报纸的一条新闻引起的。植物园的一只猴子,经过一名科学家几个月的调教,创作了幅动物的画作:画中涂抹着囚禁这个可怜东西的笼子的铁条。我心中的冲动与后来产生的思绪并没有文字记录相联系。然而,就是这些思绪,产生了我现在这部小说的蓝本,即一个长约三十页的短篇小说。我是用俄语写作的,因为俄语是我自一九二四年以来写小说用的语言(这些小说大部分没有翻译成英语,而且全都由于政治原因在俄国禁止出版)。故事中的男人是中欧人,那个没有起名字的性早熟女孩则是法国人,故事的地点是巴黎和普罗旺斯。[原文以下部分是扼要的故事情节的梗概,而且纳博科夫在梗概里还给故事的主人公起了名:他把他叫做亚瑟,这个名字可能在早就遗失的一个草稿里出现过,但是在现在所知的手稿里始终没有提到。]在一个张贴蓝纸5的战时的夜晚,我把故事读给几个朋友—马克? 阿尔达诺夫,两个社会革命党人,一个女医生;可是,我不喜欢这篇小说,所以一九四○年我们移居美国后的一天把它销毁了。
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在纽约州北方的伊萨卡,一直不曾完全停息的脉动又开始让我不得安宁。关联的情节又带着新的热忱与灵感相伴,要我重新处理这个主题。这一回是用英语写作。英语是我的个女家庭教师,即一个名叫蕾彻尔? 霍姆小姐说的语言。那是在圣彼得堡,大约是一九○三年。性早熟的女孩现在带一点爱尔兰血统,但是,实际上还是同一个女孩,与她的母亲结婚这一基本思想也保留下来了;但是除此之外,这部作品是新的,而且悄悄地一部长篇小说已经成形。
弗拉基米尔? 纳博科夫
一九五六年
作者按语二
正如我在《洛丽塔》后面附的一篇文章里所说明的,一九三九年秋我在巴黎写了一个不妨说是《洛丽塔》前身的中篇。以前我一直认为这个中篇早就已经销毁了,可是,今天我和薇拉在翻找一批书籍资料,准备再送国会图书馆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小说的一个单独本子。我的个反应是把它(与一批索引卡片和《洛丽塔》未使用的材料一起)存放到国会图书馆去,但是接着我又有了别的想法。
这个本子是一个五十五页的俄文打字稿,题名《沃尔谢卜尼克》(Volshebnik,“魔法师”)。由于我现在与《洛丽塔》在创作上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我又重读了一遍《沃尔谢卜尼克》,而且与写作《洛丽塔》的过程中已经把它当作一块废料的时候感觉到的乐趣比较起来,重读时的乐趣要大得多了。这是一个优美的俄文散文作品,行文明白晓畅,稍加注意,就可由纳博科夫家人翻译成英文。
弗拉基米尔? 纳博科夫
一九五九年
她与其他的人一起,哗啦啦地滑过铺沥青的小巷的路面,俯身前进,同时富有节奏地挥动她的放松的双臂,以飞快的速度向前猛冲。她动作敏捷地转身,于是,随着她的裙子下摆轻轻地甩起,大腿暴露了。然后,随着她缓慢地向后滑动,小腿腿肚几乎看不出曲线,但是她的裙子紧贴着身体的后背,显示出一个小小的凹沟。他的一双眼睛贪婪地注视着她,惊讶地看着她红通通的脸蛋,注视着她的每一个简洁与娴熟的动作(尤其是刚一动不动地站定,她又冲出去,膝盖向前突出,一鼓作气地滑行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所经受的这种折磨就叫做好色吗?抑或这是始终伴随着他无法实现的渴望的悲痛?因为他渴望从美好的事物中抽取一点,一动不动地握在手中,让它待上片刻,摆弄一下——不管怎样摆弄,只要能有一个接触,因为这样的接触,不管怎么样总可以让他消除那种渴望。为什么要这样苦苦思索?她还会加快速度,从眼前消失——而明天又会闪过一个不同的人,于是,他的人生就会在目睹一个接一个的人的消失中度过。
真会这样吗?他看见那同一个女人坐在同一张凳子上结着绒线,但是看到她后,他并没有报以具有绅士风度的微笑,而是斜睨了她一眼,一粒尖牙在有一点发青的嘴唇之间露了一下,然后坐下来。他的不安的情绪和两手的哆嗦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们开始谈话,而且光是这谈话就给了他一种奇怪的满足感;压在他胸口的重负放下了,于是他差不多开始感觉快活起来。她出现了,就像前一天一样,在砾石路上啪哒啪哒地走过来。她那淡灰色的眼睛朝他凝视了一会儿,即使此刻说话的并不是他,而是结绒线的女人,而她在认出他之后,也便漫不经心地转过脸去。然后她就在他身边坐着,玫瑰色的、指关节凸出的双手抓着长凳的边沿,而她的手上一忽儿暴出一根很粗的青筋,一忽儿手腕边上现出一个深深的凹陷,但是她的耸起的双肩却一动也没有动,而且两只睁大的眼睛盯着别人的一只皮球在砾石路上滚过。又像昨天一样,他旁边坐着的人隔着他递过一个三明治给女孩,于是女孩一边吃,一边晃动两条腿,用留着几个伤疤的膝盖轻轻地相互敲打。
“……当然这样更有益于健康,要紧的是,我们有一流的学校。”远处传来一个人的说话声,而就在这时他猛地发现在他左边那个长着赤褐色鬈发的脑袋毫无声响地垂着,在看他的手表。
“你的手表针掉了,”女孩说道。
“没有,”他清了清喉咙说道,“它原来就是这样的。这种表很少见。”
她伸过左手(因为右手拿着三明治)抓起他的手腕,仔细观察没有指针、没有中心的表面,而就在表面的下方,在银色的数字当中嵌着指针,只露出指针的末端,像两颗黑色的水珠。一片枯叶在她的头发上抖动,就靠近她的脖子,在一个微微突起的脊椎骨的上方——于是在后来的一个失眠的夜晚,他不住地伸手把那片鬼影似的枯叶拿掉,不住地抓住它,拿掉它,先是伸出两个手指头,然后伸出三个手指头,后五个手指头都伸出来。
第三天,以及后来的几天,他虽然不熟练但是还算不错地模仿一个古怪的喜欢孤独的人,坐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时刻,同样的地方。女孩的到来,她的呼吸,她的双腿,她的头发,她所做的每一件事,不管是在腿肚子上抓痒并且留下几道白色的抓痕,还是把一个黑色的皮球扔向空中,还是在长凳上坐下来时裸露的胳膊肘在他身上擦过——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他看似集中注意愉快地交谈的时候发生的事)激起了难以忍受的感觉,仿佛他与她血液、皮肤、密布的血管都是共有的,仿佛从他身体的深处抽取全部体液的粗大的等分线,像一条搏动的虚线,延伸到她的体内,仿佛这个女孩是从他体内生长出来的,仿佛她每做一个随意的动作,就是拉扯、摇曳长在他体内深处的她的生命之根,因此,当她猛地变动位置,或者突然跑开,他就会觉得被拉了一下,被使劲地拽了一下,会一时失去平衡:你突然之间后背着地被拖走,后脑撞击地面,拖过去,拉出肠子将整个人悬挂起来。可是他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笑着,点着头,拉一拉一条裤腿以便松一松膝盖,拿手杖在砾石地上轻轻地划着,并且说着“是这样么?”或者说“没错,有时候会有这种事,你知道……”不过只有当女孩不在附近地方的时候他才能听明白坐在他旁边的人说话的意思。他从这个事无巨细都要从头说起的饶舌者嘴里得知,她和女孩的母亲即一个四十二岁的寡妇之间,已经有五年的友谊了(她自己的丈夫的名誉是寡妇已故的男人挽救的);她说,这个寡妇长期卧病之后在今年春天肠子动了一个大手术;她说,寡妇的家人早就都不在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寡妇立即并且牢牢抓住这一对善良的夫妻的建议,让女孩跟着他们一起住到乡下去;她说,现在女孩是跟着她来看望母亲的,因为这个饶舌的女人的丈夫有一点棘手的事情要到首都来处理,不过她说过不了多久他们又要回去的——越早回去越好,因为女孩在身边寡妇就觉得心烦,而她原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只是近变得有点任性。
“哎,你不是说她要把家具卖掉几件吗?”
这个问题(以及接下来要说的话)他昨天晚上就已经想好了,而且在静悄悄的房间里低声地说过几遍;在自己觉得这句话听起来还自然之后,第二天他向他新结识的朋友又说了一遍。她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她一点也不含糊地说明,让寡妇发一点小财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她的医药费用昂贵,而且她还要继续这样花下去,她的经济来源很有限,她又坚持要负担女儿的开销可是又常常不能按时给钱——可是我们自己也不富裕——总之,很明显,良心债应该说已经付清了。
“实际上,” 他有条不紊地继续说道,“我本人也可以买一两件。你是否觉得这样既方便又妥当,假如我……”他已经忘记了后半句话,但是他临时想到的话也非常地巧妙,因为他对于现在仍旧不十分理解的、一环扣着一环的梦的做作的风格已经开始熟悉,虽然非常模糊,但也是非常牢固地与这个梦结合在一起,于是,举例来说,他已经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不知道它又是谁的东西:是他自己腿的一部分,还是章鱼的一部分。
她听了显然很高兴,说要马上带他过去,假如他想去的话——寡妇的公寓,也就是她和她的丈夫现在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跨过电气列车铁道上的天桥就到。
他们出发了。女孩在前面走着,一边手抓着帆布包的绳子用力地挥动,而在他眼里看来,与她有关的一切都已经惊人地、难以满足地非常熟悉了—— 她那细小的腰的曲线,腰部以下两块小小的、圆滚滚的肌肉富有弹性,在她举起一个胳膊的时候裙子(另外一条咖啡色的裙子)上的格子花纹匀称地收紧,她的纤弱的脚踝,她的很高的脚跟。她可能有一点内向,活动的时候比说话的时候要活泼一些,但她不能说是胆怯,也不是冒失,她的心灵似乎是浸在水中,但那是光彩照人的湿润。由于表面是乳白的,而在深处却是半透明的,因此她一定喜欢甜食,喜欢小狗,喜欢新闻短片的无害的欺骗。像她这样的皮肤温暖、有黄褐色的光泽、嘴唇微张的女孩初潮来得早,而且对她们来说这与玩游戏也没有什么多大区别,就像清洁玩偶小屋的厨房一样……然而她的童年,半个孤儿的童年,并不很幸福:这个严厉的女人的善良不像牛奶巧克力,而是苦的那一种—— 一个没有爱抚的家,只有严厉的命令,极度疲惫的征兆,对于一个已经成了一个包袱的朋友的特殊照顾……而为了得到所有这一切,为了她两颊的红润,那十二对窄小的肋骨,她背部的汗毛,她这个纤弱的人儿,她那略显得沙哑的喉咙,旱冰鞋和灰蒙蒙的天气,她站在铁路天桥上注视着一个陌生的东西的时候刚从她头脑中闪过的一个陌生的想象……为了要得到所有这一切,他愿意拿出一大袋的红宝石来交换,愿意放出一桶的热血来交换,要他拿什么来交换他都愿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