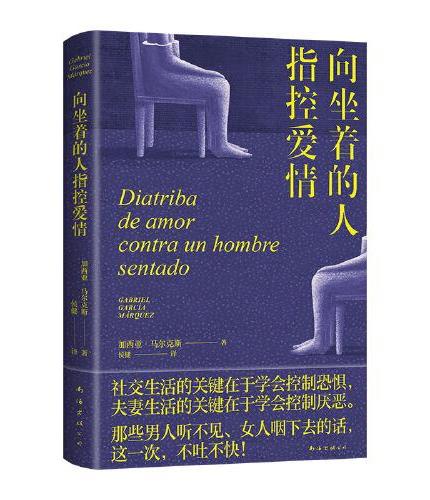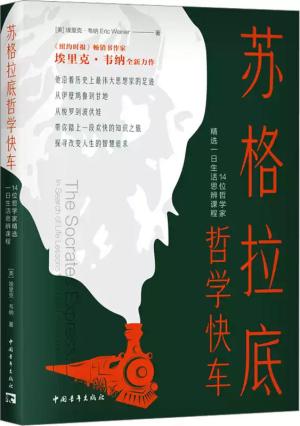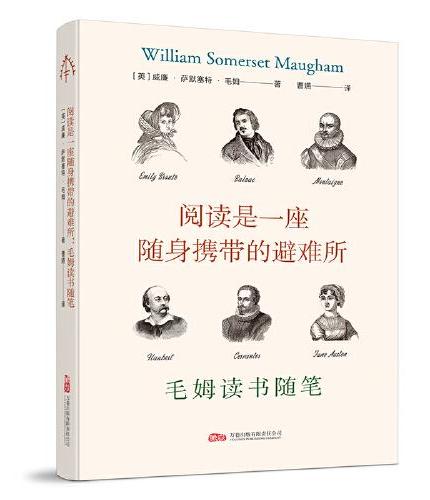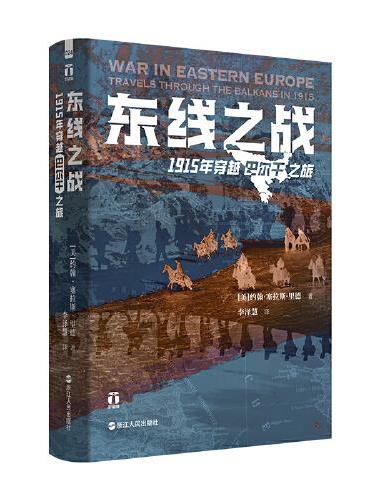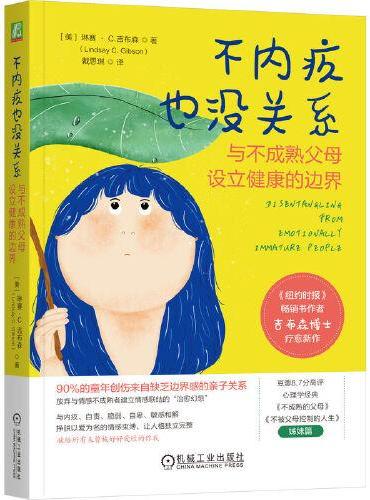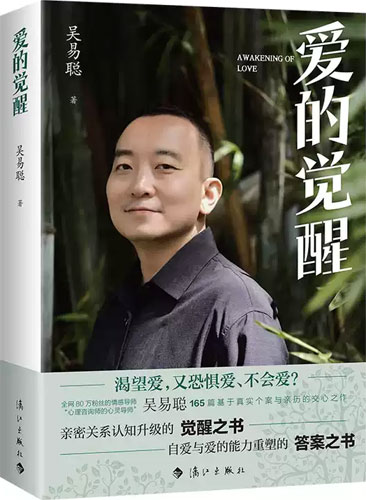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蔡康永2025新作)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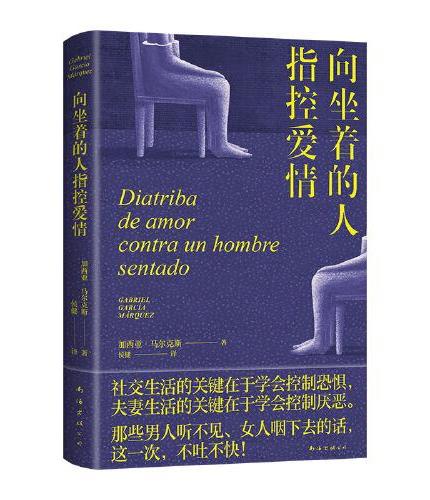
《
向坐着的人指控爱情
》
售價:HK$
4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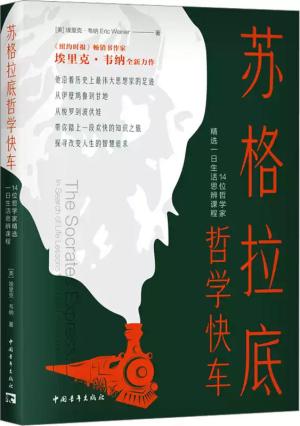
《
苏格拉底哲学快车:14位哲学家精选一日生活思辨课程
》
售價:HK$
65.9

《
放手的练习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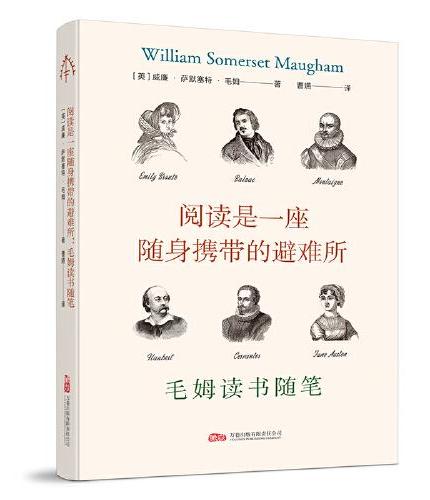
《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毛姆读书随笔
》
售價:HK$
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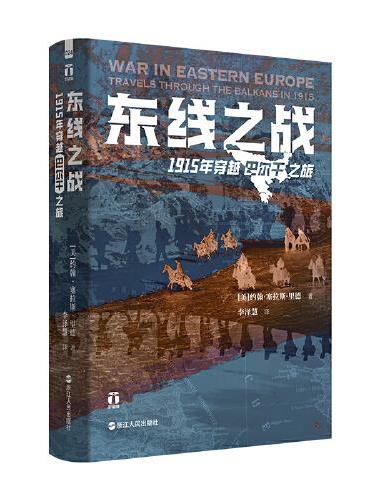
《
好望角系列·东线之战:1915年穿越巴尔干之旅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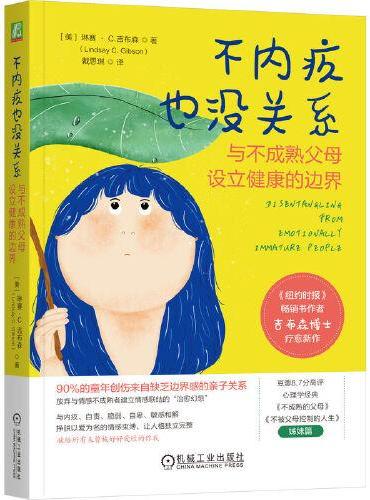
《
不内疚也没关系:与不成熟父母设立健康的边界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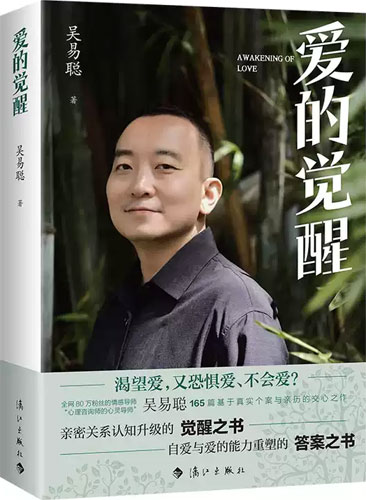
《
爱的觉醒
》
售價:HK$
85.8
|
| 內容簡介: |
|
九篇彝族题材的散文集。以回忆的笔触,大体每篇书写一个代表性的彝族人物,如作为彝族强人的祖辈,深受彝族文化熏染的兄长,害羞的母亲,在新旧时代遭遇完全不同人生的彝族祭师、欧婆婆,等等。通过写人,写出了彝族的文化、风情,也写出了彝族社会几十年间的变迁。作品写人叙事真切自然,转圜自如,笔调看似轻松,淡然云烟下却展现出一列列厚重起伏的历史山峦。
|
| 關於作者: |
|
冯良,1963年生,四川凉山人。198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藏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著有长篇小说《西南边》《西藏物语》《秦娥》、散文集《彝娘汉老子》等。
|
| 目錄:
|
凉山少年 /1
喜德县 /37
沙,沙马拉达的沙 /67
害羞的民族 /97
有名气的人 /123
彝娘汉老子 /145
病故的老阿牛 /167
一个苏尼 /189
欧婆婆传 /215
|
| 內容試閱:
|
我家表姐不用说也是彝族,而且好喝酒。
和一般好酒者一样,喝得晕乎乎时,她的话就多了。她风趣、机智,即使醉了,本性也不改,好像更有长进,真的像俗话形容的那样,舌头像抹了油,滑溜得很,逗得听她酒话的人笑得咯咯的。
有一次我们在成都一个小辈子家喝酒。喝到一定程度,我家表姐不用说话又长了。那一次她主讲的是“我们彝族是个害羞的民族”这样的话题。据她说,这个题目和内容均来自于一位彝族文化人,这个人在她上大学那个时段在中央民族大学当老师。
我表姐声称,她不过是在重复那位老师有关彝族性格的一个演讲。
我和我家这位表姐是校友,她虽然大我六七岁,但年级只比我高三级。原因不用说,她被“文革”耽误了。做了一年的校友后,她留校当了老师,我们接触更多了,或者说我是那种被称作跟屁虫的家伙,反正我挺爱跟她这里去那里去的。什么演讲啊演出啊,1980年代初中期简直多得很,思想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压抑后释放的口子像蜂窝一样密。可有关“我们彝族是害羞的民族”这个题目的演讲我没有听过。我问了很多同时期的彝族校友,他们也没听到过。这就奇怪了,不可能只有她一个人听到过呀?信不信由你,她这样对我说。那就姑且信之吧。
有关这个题目的演讲是这样开头的:
“我们彝族是个害羞的民族,为什么呢?”下面她讲道,公公和儿媳妇坐在锅庄的两边做所谓的对话,两个人要交流的事其实很简单:晚饭吃什么?可凑巧的是,媳妇的婆婆不在,公公的儿子也不在,否则的话,不用费什么周折,只要婆婆去和儿媳或者儿子去和公公直接对话就行了。但真是不凑巧,这两个人当时都不在场,而晚饭到底吃什么是必须定下来的,否则岂不要饿肚皮吗!于是公公问:“锅庄呀,晚上我们吃啥子呢?”媳妇答:“锅庄呀,晚上我们吃洋芋坨坨和荞粑粑。”两个人显然是通过眼前相隔着他们的锅庄在一问一答。
讲到这里,我表姐又来反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她又自己回答说,因为我们彝族是个害羞的民族。作为一个害羞的民族,公公和儿媳是不能直接对话的。我家表姐说。
在讲述的过程中,我家表姐充分发挥了她可能具备的表演才能,语气呀手上的动作呀都多得很,尤其她把“我们彝族是个害羞的民族”和“为什么”挂在嘴上,一咏三叹的重复了又重复,模仿的又是彝族人说汉话时半洋半土的风格,简直笑死人了。
像一般有幽默细胞的人一样,在别人笑得死去活来时,我家表姐不仅不笑,还很端庄,在那里不断重复“我们彝族是个害羞的民族”什么什么的。
彝族翁媳间岂止不能对话,还不能接近,其间的距离以六步为佳,万一哪一方无意中突然过近,另一方会奋起喊道:“请让!”
这是凉山那位叫岭光电的土司在六十年前记录下的彝族社会的实情。自那以后,过去了这么多少年,凉山所发生的变化确实可以用翻天覆地这样的词来形容,可是习俗变起来总是难的,像翁媳回避这类的礼节仍然存在于凉山的彝人社区里,只或者程度有所不同罢,比如城里相对而言会轻弱一些,乡下,尤其是那些更偏僻的地方会严重一些。
原因是什么呢?上面提到的那个土司有论说,他说大概在于很久以前公公,包括大伯子,在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抢婚时用的劲出的力太多,引起被抢者儿媳和弟媳持久的愤怒,进而演变成了后来互相回避的习俗。也说得过去吧?!等到抢婚已然成为一种形式时,翁媳还在互相回避,在我看来就是我表姐宣扬的害羞使然了。而用害羞来涵盖一个民族的特性,或者说一种特性,我不知道同是彝族的其他人怎么看,我是深以为然的。
很多时候,我听人家在评论少数民族时都说少数民族热情大方。具体到彝族,我在小时候就听四周的非彝族人说,啊呀,彝胞啊,胆大得很,田间地头、山坡梯坎上,男男女女,老在嘻嘻哈哈的打闹。这大概和议论者奉行的“男女授受不亲”有直接的关系。另外,也是关键的一点,我觉得说者未必搞清楚了打闹者的身份和年龄。
打闹者实际都是些尚未成婚的年轻男女。以此来反问议论这个场景的人,他一定会干噎住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青年男女都喜欢互相打闹,除非不正常。
排除了这个因素后,我要说的是,彝族有的一个特性确实是害羞。想一想,把全中国,或者限定在凉山,把凉山二百多万彝族人都放到害羞一词里来加以说明,也挺有意思的。
在我的老家,大人们骂小孩常用的一句话是:“你咋不知道害羞啊!”你说错了一句话,做了不合适的一件事,或者仅仅是你的胆子大了点,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表一点见识,他们都这样骂你。这算是很严厉的骂人的话了,剩下的还有骂你疯子傻子的,为了发泄气愤, 至多再威胁你说:“用石头打死你!”如此而已。
我的继母,我们叫孃孃,有一次告诉我,她刚参加工作那一阵,从省会成都来了几个采风的男子。他们来找我家孃孃等几个彝族姑娘收集民歌。
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有人唱,还必须有人给翻译,因为我家孃孃和她的伙伴唱的是彝语歌,因此场面一定很热闹,也因此招徕了很多的看客,这其中有的是彝族长者。他们眼见得自己的几个姑娘在那里又说又唱还笑的和来历不明的异族男子周旋,马上就不高兴了,就骂她们不懂得害羞啊!
这件事,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家孃孃就讲给我听过,她当时大概有同样的话要骂我,但到底懂技巧,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服我。不过也是遗憾,我一点都没听出来她婉转传递给我的意思。像我这样凉山的新一代哪里能够领会有关害羞的深意呢。我反驳她:就唱几支歌,那有什么害羞的!还说,哎呀,你也是不经骂,老人骂你几句,你就不敢唱了。你要还敢唱的话,我保证起码凉山州歌舞团早把你招进去了。
在我小时候社会不提倡读书,主要是读了也没有什么前途,像我这样大小的女孩子妄想的都是到州歌舞团去当个唱歌跳舞的演员,很风光的。
不用说,我把我家孃孃气得哼一声,无话可说了。
要说的话,我们家的几个孩子尤其我哥哥在我们那个小县城的口碑就属于害羞一类的人物,也因此我觉得众人还有点担待我们似的。
大家都说,啊呀,这几个娃娃像极了他们的妈。据众人说,我早逝的母亲就是个害羞的人。
我工作了以后,有一次在贵州参加一个彝学会,碰到我母亲在西南民院上学时的一个同学。他一听我是李国英的女儿,自然免不了要缅怀一番他的同学、我的母亲。他一开口说的 也是,你家妈妈啊,真是个害羞的人!
当时我们是在告别,时间很紧急,其中的一方,我吧,正要离开所住的宾馆,上送站的车去火车站。就在那么一会儿的时间里,他突然知道我是他同学的女儿,当然感慨了,可想不到,他想起的有关我母亲的个事迹竟然是害羞。
在那么紧迫的时间里,他还居然把我母亲如何害羞的往事讲给我听了。
他说,有一次他们开小组会,讨论什么呢,他已经忘了,但要求与会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说不行,人人过关。
那是1950年代初的事。当时凉山的民主改革还没有开始,奴隶娃子还没有翻身,他们的子弟呢,自然都还在山上放着主子家的羊啊牛的。就是说,到西南民院来接受新社会的教育的还多是所谓的统战子弟。他们多半来自凉山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以我母亲而言,她家在彝人社会里完全称得上是有名气的。其时他们家的当家人是她的三叔。她的父亲死于之前旷日持久的冤家械斗。
我的三外公和他二哥、我的外公一样,曾经在成都上过华西大学,思想开明,能顺应时势,是早与解放军联系的当地上层人士之一,而且很快就将家里的大孩子,我母亲和他的大女儿送到位于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去受教育。同时送去的还有当地一家马姓黑彝的子女。
不知道我母亲在西南民院学习的具体时间,我无从判断她当时的年龄。不过以解放军进凉山的时间——1950 年和她生于1935 年来推测,而又没有到1955 年——凉山民主改革开始的年份,可以确定的是,当时我母亲的年龄在 17 岁至 20 岁之间。
我母亲的老家汉源今属四川雅安地区,距成都二百来公里吧,以现在来看的话,一天能倒来回,可在五十多年前却是件困难之极的事,不单纯是交通不方便的问题,主要的是沿途各地方势力林立,寸步内外就有荷枪实弹的牛人让你留下买路钱。如果再碰上个谁知道在祖上什么时候结下梁子的仇人,那你的小命还要不要?如此的情势之下,没有人敢随便出门的,更何况是女子呢。
我母亲去成都西南民院学习时情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中国在前一年——1949 年——的十月成立了,西南的顽垒成都也被攻克了,解放大军扫平了进入凉山的大道和部分小路,前往成都的沿路艰险已不复存在。和她一同去的前面说过人还不少,她呢,童年时已然经历了母丧父亡,算得是见识过世态艰难的女子了。综合以上种种,按理说,她不该那么无措的。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她的适应能力也应该比其他来自纯粹的彝人社区的学生强,她是在彝汉杂居区长大的。在那里,彝话汉话都通行无阻。具备这样先天条件的人在当时的凉山并不多,如果发展得好的话——无非是胆子大一点,成为新社会一个小有名气的妇女干部是极有可能的。此种情况在凉山屡见不鲜。
可她骨子里却害羞得不行。据她的同学告诉我,那一天轮到我母亲发言时,她怎么都开不了口,勾着脑袋,身体绷得紧紧,如果地上有一条缝的话,她肯定就钻下去了,他说。但是,没有。如此的话,我母亲还得把她的言发出来。
几经学习小组的组长和同学里的积极分子劝说,她决定发言了,不过有一个前提,她昂起头,脸红透了,她让小组的成员都出去。他们很是不解,疑惑地都看向她,什么意思嘛,出去? 我们是听众啊,可能针对你的发言还要点评什么的,他们的眼神说。但我母亲坚持请他们出去,她说,你们都到门外去,还要把门关上,我才发言。那怎么听呢?
过了近四十年,她的同学告诉我说,当时他就是这样质问我母亲的。我母亲复又垂下头,小声小声地说,她可以大点声。总之,她的意思是,这些人如果围在她面前的话,她就会紧张得什么都说不出来。
当时大家大概还有很多事要忙着去干,新社会刚开始,到处都在嘿啦啦的为新中国添砖加瓦呢,或者大家忙着去吃饭,不知道了,反正大家都忙着要离开会场,而为了听我母亲的发言,已经浪费了半个小时还多。于是,小组长不得已的宣布说,那就这样吧。
怎样呢?大家都到门外去听李国英同学发言。他说。 那我母亲发言了吧?“发了,”她的同学回答我,事隔几十年,他还是忍不住笑。
后来,我把这事讲给我父亲听,他也笑,说他倒不知道竟有这样滑稽的事。他说,我母亲确是很害羞。具体如何,他说,人一多,你妈说话时脸就要红。他还推测说,这大概是你妈妈不爱说话的原因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