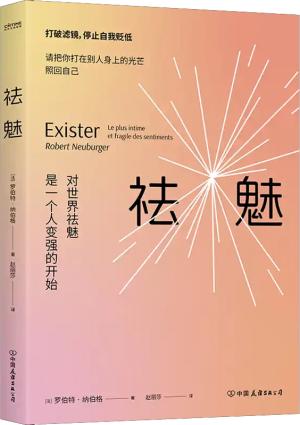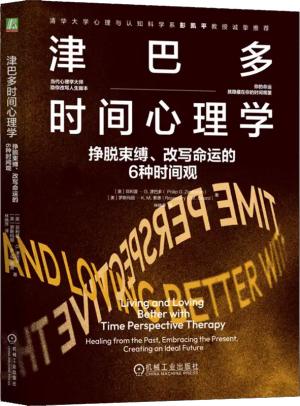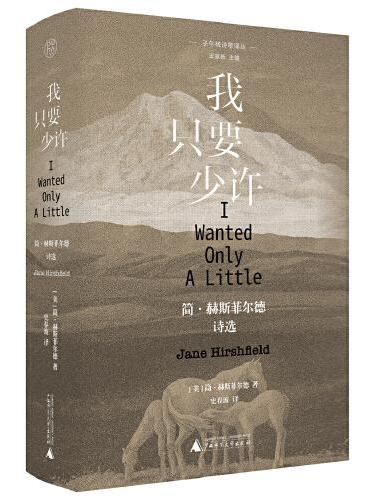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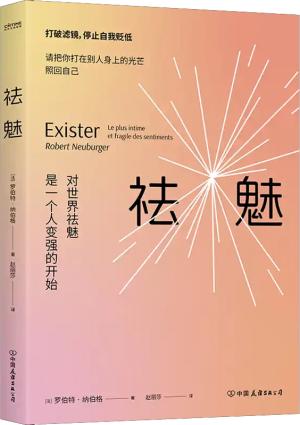
《
祛魅:对世界祛魅是一个人变强的开始
》
售價:HK$
62.7

《
家族财富传承
》
售價:HK$
154.6

《
谁是窃书之人 日本文坛新锐作家深绿野分著 无限流×悬疑×幻想小说
》
售價:HK$
55.8

《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第3版
》
售價:HK$
110.9

《
8秒按压告别疼痛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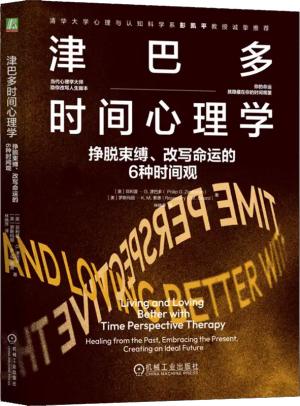
《
津巴多时间心理学:挣脱束缚、改写命运的6种时间观
》
售價:HK$
77.3

《
大英博物馆东南亚简史
》
售價:HK$
1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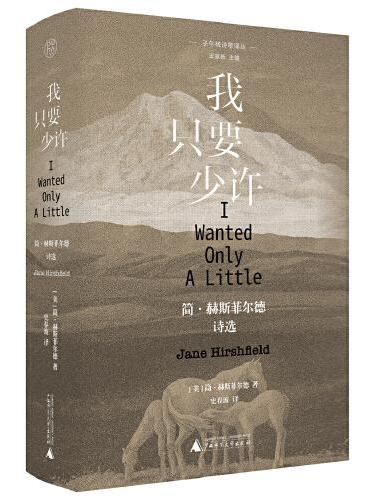
《
纯粹·我只要少许
》
售價:HK$
80.6
|
| 編輯推薦: |
透过《木屋旅馆》,读者可见阿尔巴尼亚社会的现状——渗入政治精英阶层的腐败,以及追求轰动性新闻甚于事实真相的媒体环境。书中对阿尔卑斯山区,即解开谜团之处的描写,引人置身于阿尔巴尼亚高山深谷的乡村景致之中,同在木屋旅馆中遭遇的各色人物共处。一个有分量的主题,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多变、流畅、精致的风格,其间不乏幽默、讽刺和令叙述鲜活生动的种种变故。—— 沙班·西纳尼(阿尔巴尼亚科学院院士、文学批评家)
作家迪安娜·楚里的这部小说想要告知我们,尽管堕落与腐化已渗透到政治、媒体、经济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却依然有追求、捍卫真相的人,依然存在正义的空间。作家想要在文学的范畴里赞颂这些个人,燃起希望之火。—— 普雷茨·佐加伊(阿尔巴尼亚政治家、作家)
在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中,迪安娜·楚里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她的小说创作带有强烈的个人艺术风格,作品丰富,精品甚多。—— 罗兰德·齐西(阿尔巴尼亚发罗拉大学校长、文学批评家)
|
| 內容簡介: |
|
《木屋旅馆》是阿尔巴尼亚当代著名女作家迪安娜·楚里近十年的重要小说之一,也是国内首次关注并译介她的文学作品。小说讲述的是关于调查一个失踪女人的故事。一个小有名气的节目主持人阿图尔?拉多瓦尼,在妻子突然失踪的同时,碰巧他也陷入腐败的丑闻中,为此丢掉了工作和名声,面临着入狱的危险。所有的这些怪事仅在短短的一周之内发生。男人委托年轻的私家侦探莉莉安娜?杜卡寻找自己的妻子,莉莉安娜?杜卡也由此开始了新的冒险。她循着拉多瓦尼的妻子的踪迹,前往阿尔巴尼亚阿尔卑斯山,却被一群奇怪的欧洲旅行者跟踪……在案情大白的过程中逐步揭露浮躁喧嚣的媒体背后历史与当下的种种残酷真相,反映阿尔巴尼亚半个多世纪以来价值体系崩塌、社会黑白颠倒的现实,刻画个人内心的惶惑、迷茫、挣扎与改变,展现他们对人生意义的苦苦寻觅与艰难抉择。
|
| 關於作者: |
译者简介:
迪安娜·楚里
阿尔巴尼亚作家、记者、翻译家。一九五一年出生于地拉那,一九七三年毕业于地拉那大学阿尔巴尼亚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常年在国内知名文学报刊《光明报》和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杂志《阿尔巴尼亚文学》(法语版)工作。她人生阅历丰富,深度接触社会,擅长刻画女性心理,在以男性作家为主流的阿尔巴尼亚文坛脱颖而出,曾获阿尔巴尼亚出版商协会二〇〇七年度图书奖、阿尔巴尼亚出版商协会二〇一七年度翻译奖等奖项、阿尔巴尼亚KULT研究院二〇一九年度艺术图书奖。著有《人行道上的鹿》(1989)、《午夜太阳》(2000)、《武装天使》(2006)、《总理府谋杀案》(2018)等;译有《等待的幸福》等。
译者简介:
陈逢华
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阿尔巴尼亚语教研室及阿尔巴尼亚研究中心主任,译有教材《当代中文》,长篇小说《事故》,短篇小说《沐浴之前》《斯芬克斯之夜》,合译辞书《汉语图解词典》《汉语图解小词典》(阿尔巴尼亚语版),参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阿尔巴尼亚文学部分等,编著教材《阿尔巴尼亚语听力教程》《阿尔巴尼亚语口语教程》等。
|
| 目錄:
|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 / 高兴/1
一场心灵回归之旅(中译本前言) /陈逢华/1
章周日的意外/
第二章阿图尔·拉多瓦尼的讲述/
第三章马克斯/
第四章校长与米兰达·波伊斯卡的故事/
第五章德拉戈比山口的隐秘与泡沫四起的瓦尔
博纳河/
第六章阿丽亚娜/
第七章这本书后的陈述/
第八章莉莉、简·霍尔特及补充说明/
尾声/
|
| 內容試閱:
|
一场心灵回归之旅
陈逢华
《木屋旅馆》是阿尔巴尼亚当代著名女作家迪安娜·楚里近十年的重要小说之一,恐怕也是国内首次关注并译介她的文学作品。楚里继《人行道上的鹿》(1989)、《午夜太阳》(2000)、《武装天使》(2009)等小说代表作问世之后,在二○一一年出版了这部罕见的以电视传媒为书写对象的长篇小说。作品以著名媒体人拉多瓦尼委托私家女侦探杜卡调查并寻找失踪的妻子阿丽亚娜为起因,在案情大白的过程中逐步揭露浮躁喧嚣的媒体背后历史与当下的种种残酷真相,反映阿尔巴尼亚半个多世纪以来价值体系崩塌、社会黑白颠倒的现实,刻画个人内心的惶惑、迷茫、挣扎与改变,展现他们对人生意义的苦苦寻觅与艰难抉择。
迪安娜·楚里一九五一年出生于地拉那,一九七三年毕业于地拉那大学阿尔巴尼亚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常年在国内知名文学报刊《光明报》和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杂志《阿尔巴尼亚文学》(法语版)工作。一九九○年后,楚里开始投身妇女及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活动,领导“女性独立论坛”保护妇女权益,二○○五至二○○九年间被选举为阿尔巴尼亚议会议员。在以男性作家为主流的阿尔巴尼亚文坛,楚里的脱颖而出实属不易。她人生阅历丰富,深度接触社会,擅长刻画女性心理,在小说、戏剧和电影剧本等多种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均有建树。尤其是在小说中,楚里常常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细致入微地展现阿尔巴尼亚当代社会的真实样貌。
《木屋旅馆》由周日一通不识时务的电话铃声开场,将小说的位核心女性——“私人纠纷处理机构”(即侦探社)三十出头的女侦探莉莉安娜·杜卡推至台前,反之,让阿尔巴尼亚北部边境旅游胜地瓦尔博纳的“木屋”隐藏其后,成功地制造了“木屋旅馆”的阅读悬念。杜卡是位活泼浪漫、冷静果敢的独立女性,她不仅是阿尔巴尼亚现实生活中难得一见的女侦探,而且受命暗中调查名人妻子的失踪事件注定充满未知的风险。然而,杜卡毫无畏惧,在大名人拉多瓦尼面前如此,在尚无头绪的案情面前亦如此。她目光敏锐、心思细腻,迅速把追踪的目标锁定在阿尔巴尼亚边境城市瓦尔博纳,同时,作为小说的主要讲述者,她把故事自然而然地引向木屋旅馆,让真实的阿尔巴尼亚社会铺展开来。此时,小说第二位核心女性——拉多瓦尼苦寻的失踪妻子阿丽亚娜已在木屋旅馆向我们招手。在拉多瓦尼精彩传神的描绘中,一位漂亮优雅、衣食无忧、家庭幸福的职业译员跃然纸上,然而很快这一切就被无情地颠覆,富裕的生活和成功的丈夫正在不知不觉间摧毁她内心的宁静与满足,与昔日恋人的意外重逢更成为二人关系的致命转折点。阿丽亚娜后续的讲述再为我们彻底破解了她的失踪之谜,显然,她奔走木屋旅馆的举动并非对婚姻困境的逃避,而是一场自我价值和婚姻理想的救赎,因为在冰天雪地、无所遁形的瓦尔博纳,阿尔巴尼亚社会的善与恶将愈发分明。其间,小说的后两位核心女性——拉多瓦尼在视窗电视台的“忠实”下属白发女魔玛格丽塔和《闪电报》记者谢丽·塞费里,走出她惟妙惟肖的叙述,在木屋旅馆正式登场。她们是真实居住在“木屋”的小说人物,然而这纯净天空下的“木屋”恰恰暴露了她们的丑行。虚伪狡诈的玛格丽塔表面上对拉多瓦尼毕恭毕敬,对他的成功人生艳羡不已,低俗阴险的塞费里打着“正义”的幌子无情摧毁他人的生活。可以说,正是这些与大名鼎鼎的媒体红人拉多瓦尼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阿尔巴尼亚女性,在白雪纷飞的严寒冬季粉墨登场,又带着完全不同的动机在木屋旅馆不期而遇,才让小说一开始制造的神秘、紧张悬念延续升级为刺激、惊悚的对抗。随性而来的阿丽亚娜,乔装而至的杜卡,追踪出现的玛格丽塔和塞费里,打破了木屋旅馆的静谧与纯净,自然、温暖的“木屋旅馆”与屋外凛冽的寒风、纷飞的白雪一夜较量,阿尔巴尼亚延伸到巴尔干乃至欧洲的真实复杂的社会现实激烈涌动,在瓦尔博纳的悬崖峭壁、波涛翻滚间对峙……
围绕着木屋旅馆,小说还为读者勾勒了几位阿尔巴尼亚女性的典型形象,慈祥善良的老妈妈穆巴丽梅、乖巧能干的大儿媳特伦达菲丽娅和孤寂胆怯的女儿赛丽姆。这质朴的一家人热情坦诚地招待着各怀心思来到“木屋旅馆”的各路人马,展现出阿尔巴尼亚女性善良勤劳的传统面貌。老妈妈穆巴丽梅温和包容、睿智超然,她真诚地关爱着孤身前来、不免战战兢兢的女侦探杜卡,忧心人生不幸、性格柔弱的女儿赛丽姆,即便对图谋不轨的三位“不速之客”也并无丝毫敌意。大儿媳特伦达菲丽娅同样坦诚待客,温和友爱。而在拉多瓦尼和马克斯的叙述中,赛丽姆被无辜构陷的过程、丈夫兰迪早逝留下幼年病女的悲惨经历一一呈现,令人不禁哀叹生活原本的艰辛与社会人为的不公。
很快地,木屋旅馆成为失踪案峰回路转的关键一环,阿尔巴尼亚北部山民的热情好客、真诚善良让它化作了一个无须言语而充满力量的场域,故事人物的不安、烦恼、焦虑在这里得到彼此的慰藉,她们的痛苦、愤怒、绝望在这里得以安全地宣泄与释放,平和、希望和力量在这里找到了合适的落脚点。结果,佯装前来调查旅游情况的杜卡有惊无险地解救出善良的阿丽亚娜,带着她和她关照的赛丽姆脱离了可能的危险。一路追踪杜卡而来的白发女魔玛格丽塔、同伙塞费里与三个乔装打扮的“北欧人”起先暗中联手,但后者在木屋旅馆里渐渐识破了前者以制作《魔眼》节目来揭露“社会黑暗”的险恶用心,她们暗中拍摄,妄图无中生有的阴谋终破产。同时,在木屋里,杜卡与阿丽亚娜的友好初识也开启了柳暗花明的后续,阿丽亚娜找到内心暂时的安宁之后勇敢走出木屋自然与人为的困境,反思自身与拉多瓦尼渐行渐远的夫妻关系,积极帮助被丈夫所代表的媒体无辜伤害的赛丽姆找到解决之道。因此,冰天雪地里的木屋开始让阿尔巴尼亚的现实黑白分明,官员贪污、栽赃无辜内幕的曝露隐喻着现实中阿尔巴尼亚勇敢面对真相,找寻现实出路的积极努力。
楚里不仅是知名作家,也是法国文学的阿尔巴尼亚译介者。有评论家提到,在创作《木屋旅馆》之前,她翻译了美国小说家、新闻记者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美食、祈祷和爱》(另译为《一辈子做女孩》),认为其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比如女主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着与信念,场景间电影画面式的安排,利用冥想探寻事件间无形的联系,文笔准确优美,等等。但是,更有意义的是,《木屋旅馆》通过精巧设计的悬疑故事自然而然地呈现阿尔巴尼亚复杂、真实、丑陋、冷酷的社会现实,犹如一块帷幕徐徐拉开,有效地把读者的目光聚焦在黑暗、残酷的阿尔巴尼亚社会真相上来。
与失踪事件的惊险博弈围绕木屋旅馆展开不同,阿尔巴尼亚社会现实的片段则几乎都是在地拉那的玫瑰人生酒吧和普里兹伦的豪宅里交代的,此时阿丽亚娜的离奇失踪不过就是引子而已。在拉多瓦尼与杜卡多次的会面之中,先是为寻找不告而别的妻子,这位昔日风光无限的名牌主持放下了自尊与戒备,向女侦探和盘托出了自己一路成名却即将身败名裂的真相。拉多瓦尼原先简单远离政治的幻想在全社会追名逐利的现实里被悄然扭曲,他囿于金钱所定义的成功,在日渐舒适的众人追捧中逐渐迷失自我。他追回妻子的种种努力更是他极为艰难的自我剖析与反省。同时,依旧在玫瑰人生酒吧,杜卡的好友马克斯坦然追忆了他与阿丽亚娜的昔日男友拉迪的友情决裂,虽然这段令人心伤的过往是揭开阿丽亚娜失踪案的重要线索之一,但更为重要的是,拉迪当年的绝情欺骗、极度自我准确地回溯了阿尔巴尼亚社会转型初期人性挣脱了过度的束缚与重压后报复性的可怕释放。而在脱离危险之后阿丽亚娜与杜卡在普里兹伦的畅谈更是把这位女性在整个转型时期所历经的个人成长逐一呈现,令人无比清晰地意识到,她无法忍受、毅然决然的出走是对以往自我价值和存在的反思与批判。阿丽亚娜在此时此刻完成了肉体的出走后心灵的回归!在《木屋旅馆》中,不难发现作家透过主人公的交谈构成了对小说主题的一次次叩问:阿尔巴尼亚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力量?一旦媒体的力量大到可以操控乃至主宰个人的命运,国家的财富便可以大言不惭地窃取,高官名人便可以习以为常地全身而退,而弱势者只能一次次地沦为替罪羊,昔日的受迫害者将一次次地被新的受迫害者所取代。如果媒体无须区分正义与邪恶,那么媒体究竟在阿尔巴尼亚社会制度转型的剧变出现的人性道德沦丧中,在走向欧洲还是与欧洲背道而驰的两大势力较量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小说在这一主题上的探讨或许太过真实与犀利,楚里表示小说内容“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当然,有关阿尔巴尼亚媒体的善恶探讨仍然是小说的表层主题,制度剧变所带来的人性价值自身的瓦解与崩塌,以及原本隐匿其后,如今凸显而出的犹如深井的幽微人性,恰恰困住了当下社会信奉民主制度通往人性自由的每一个普通阿尔巴尼亚人。在小说世界里,阿丽亚娜出走,带着惊慌失措的赛丽姆躲避于木屋旅馆,犹如走入了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的迷宫,没有杜卡的协助和三位“北欧人”后来的撤离,依旧难逃媒体穷追而来的魔爪;而在现实世界里,阿尔巴尼亚始终徘徊在社会转型过渡期的迷宫之中,融入欧洲、走向复兴的梦想依旧遥不可及。当然,作为社会活动家和小说家的楚里乐意给未来一抹希望的亮色,或者说,那是她所主张的作家与文学应当承担的社会使命,即给予阿尔巴尼亚人走出过渡时期的思想深渊一股精神力量。因此,她为小说的两位受困女性都找到了救赎之路,赛丽姆重新站起来,得以重返社会,自食其力,抚养生病的女儿,阿丽亚娜回归了和谐的婚姻和充实的生活,她们肉体的出走换来了心灵的回归和精神的安顿。然而,不得不说,现实恐怕不可能如此理想与简单,官员引咎辞职,名人坦承过错,心态、冤冤相报的媒体人得以收敛,真的仅凭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侦探或者一群有正义感的“英雄”吗?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普遍认知中,阿尔巴尼亚依然停留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尔巴尼亚老电影里战争与革命定格的激情岁月之中,然而《木屋旅馆》展现了阿尔巴尼亚的进行时,一个正在经历着思想、观念、价值的剧烈动荡与重构的生动的阿尔巴尼亚,一群生活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年,没有了英雄的伟大与崇高的他们,让真实强烈的现场感在小说中扑面而来,体现出阿尔巴尼亚文学与作家的时代担当。同时,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小说里,以木屋旅馆为转折点,离开喧嚣嘈杂的首都地拉那去追踪阿丽亚娜的女侦探杜卡终揭开了白发女魔和塞费里二人的险恶算计;价值迷失、婚姻陷入困境的阿丽亚娜在解救深陷危局的女伴的同时,挽救了自我与婚姻,回归了平淡却不显乏味,诚挚而不做作的生活。一场肉体出走、心灵回归的大戏在女性视角下徐徐展开,娓娓道来,让我们有幸一窥当今阿尔巴尼亚社会如此生动鲜活的,看似普通却又并不平凡的女性群像。
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章 周日的意外
视窗电视台节目负责人阿图尔·拉多瓦尼给我打来电话的时间是周日,下午四点钟。周日,午后,我通常眯上一会儿,把手机调为“静音”,拔掉家里的座机线,放下窗帘,关掉电视,再盖上一条柔软的毛毯,躺在沙发上小憩。大约一个小时而已。
那个周日,正下着绵绵细雨,雨水轻轻敲打着窗子,短暂地打个瞌睡在我看来显得无比甜美。进入梦乡前,我一贯想些愉快的事,或者至少,有趣点的事。那天,我在法国《世界报》的网页上才看了旧时代一位中国演员的口述。这个人现在住在纽约,已经到了显老的年纪,他说险些没逃过一场可怕的惩罚。恐怕一拨演员之中,他是侥幸逃脱的人。因为,在那个时期,剧院里上演的戏,光是手就能当主角。妙。到这里一切都很正常,符合当时的逻辑。但是,接下来,这位中国演员说,所有扮演过这个角色的演员,一个个都死了。要么倒在家门前,要么死在浴缸里,要么淹死在湖里,或者干脆中毒,死在床上。至今没有人能说清楚谁杀了这些演员,原因或者动机又是什么。没有任何证据……什么都没有。
我正遐想着是谁、为什么、在什么地方如此作为,联想到那里的街巷,那里的一切。那平白无故的心绪不宁、胡思乱想仅仅也就过了十分钟,座机就疯狂地响了起来。显然,我忘了拔掉电话线。
闭着眼,我想到——此时此刻绵绵的雨停了,死去的魂魄在黑暗中也黯淡了下去——这位周日下午四点叨扰的不讲礼貌的人,在电话响过五六声后会撤退的。但是,没有。刺耳的电话铃聒噪了十五声方才停下来。我心想,他放弃了,于是把毛毯罩在头上。令人昏昏欲睡的絮语声又回来了。或许,在我的梦里,一个湿漉漉的街角上会出现某个令人恐惧的军人。我再也睡不着了,我想,但是,至少我得略微平复一下电话铃声对我脑子造成的冲击。
说起来,那天下午我有罪受了。戳破我脑壳的电话铃声执拗地聒噪了整整七回,每回都得响上十五声。第八回,我飞身跃起,冲到我的灰色座机兀自杵着的床头柜前,愤怒至极地操起听筒。
“您好啊!”
电话线另一端的人好还是把话筒放下,否则就会再次听到我发出的貌似问候的沙哑咆哮。
“您是杜卡女士吗?”男人用喉音说。
“不,我不是杜卡女士。”我回答。
另一头儿是犹豫的沉默。
“对不起,”低沉的嗓音说,“有人给了我这个电话号码,找杜卡女士。”
“这里没有杜卡女士,”我接着说,“您打错了。”
“是吗?对不起。”声音有些含糊地说,接着挂了电话。
我又回到了沙发上。杜卡女士!
我站起身,走进厨房,打开意利咖啡机。你等我把咖啡煮好,我对自己说,再倒到杯子里。
我才把咖啡倒在杯子里。
电话铃声又响了。响了四声。
“您好!”
“您是杜卡小姐吗?”还是那个低沉的嗓音,竭力显得通情达理。
“是啊?”
“我是在和杜卡小姐说话吗?”
“是啊?”
“您是莉莉安娜·杜卡吗?”
“是啊?”
“我是阿图尔·拉多瓦尼,杜卡小姐。”
“是啊?”
电话线那头的人彻底晕了。他原以为著名的阿图尔·拉多瓦尼给我打电话,我得高兴死了。在周日下午四点钟!这个人不是在做节目吗?在他任职的电视台,周日下午的节目里,他常常喋喋不休。
“请原谅,”他继续说,还是完全如坠云雾之中,“但是我去过您的办公室,他们引我来找您,我一点也不想打扰您……您理解我吗?”
“不理解。”
“莉莉安娜小姐……您的上司让我来找您……”
我醒了。他一共说了四回以“指向”在阿尔巴尼亚文中,drejtohem、drejtoj与drejtues的词根都是“drejtoj”(指向),故有此说。为词根的词。他们引我,我找您来,上司……他言辞太贫乏了。
“我明白了,”我决定放过他,后说,“请讲。”
“我想要马上见到您,我有一件急事。”
这个人竟然如此不明事理,挂电话的时候我想。他在哪里学的说话,电视台那儿吗?
阿图尔·拉多瓦尼希望我们晚上七点在罗格纳酒店的酒吧见面。当然,我不再躺在沙发上了,而是给我的美发师打了电话,问她六点是否有空,给我简单梳个头。然后,我走到卧室里,打开了衣橱。我的衣橱很大,是从一个手艺很好的木匠那里定做的,占了四面墙。在一面墙上有些简单的服装,牛仔裤、T恤衫和运动外套。另一部分挂着时尚西装、丝绸衬衫,下方的抽屉里摆了我很少穿的高跟鞋。窗户两侧的墙上分别是大衣、风衣、棉服、毛衣等等;都是依照我着装的意图摆放的。
次与阿图尔·拉多瓦尼见面,不论他的意图是什么,我都会穿黑色西装去,但配的是短裙,而非西裤,还有乳白色丝绸衬衫。再搭上带跟的黑皮鞋。
从他的语气,我已经感觉到,上司把他“推给”我令他不悦。我必须在外表和气势上压过他,让他态度温和些,不要一开始就张牙舞爪。
我把西服放在床上,走到窗前。雨还在下,现在下得更厉害,并非摇篮曲似的雨了。我应该坐车去,否则必得挨淋,头发一定会乱的。
阿图尔·拉多瓦尼,这个名字对我没有多大意思。我知道他在视窗电视台负责综艺节目《魔眼》——一档类似于《老大哥》全球流行的游戏真人秀,1999年在荷兰首播,后在各国播出了不同版本。节目要求参与者生活在一所一举一动都被摄像机和麦克风记录的房子里,不允许他们与外界接触。的真人秀。近两年来,他的节目成功超越了后者,夺走了一大批观众和赞助。他还常常参加电视上文化和政治问题的谈话节目,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个稳重而专业的人。
我慢慢地穿好衣服,一边思索着究竟为何阿图尔·拉多瓦尼到我们事务所登门拜访,身为上司和老板的我舅舅又为何选了我来摆平他的事。
我们事务所,或许是目前阿尔巴尼亚的调查机构。事务所的门牌上写着“私人纠纷处理机构”,路过的人瞄上一两眼,都搞不太明白我们在解决什么样的私人纠纷。实际上,我们就是实打实的侦探,与电影和书本里的那些人没有任何不同。我们总共三个人,全都忙得要死,而我舅舅埃米尔·阿巴兹却不想增加人手。他的理由是,选人不是件易事,做侦探必须得有兴趣、有本事,目光敏锐、头脑聪明,既有文化知识,又了解情况,具备极其迅速收集信息的渠道,可想而知,这样的人有多难找。
我舅舅说,他以前曾就职于安全机关,在抓窃贼的部门工作,但是没什么人相信他。看他工作时的样子,我也不相信他只是抓一般的窃贼,但是说到底,谁又还在乎他的过去呢。开事务所的时候,他找来了他的前同事穆罕默德·哈吉伊梅尔当合伙人。他又把我找了来,理由是我打小时候就热衷于剖析形形色色的隐秘,这热情人尽皆知。
实际上,我一直失业。二○○○年,我读完法律系,该找的地儿都找了,但就是找不到工作。有一个女律师协会让我干了五个月志愿者,帮助受虐待的妇女,捍卫她们的法律权益,但是由于女律师们根本筹集不到经费生存下去,我就离开了。在一家橙汁生产企业、一家建筑公司里,我又混了大概两年;还是由于缺乏资金,他们也停发了我的工资。
那段时间,我一如既往地啃着探秘和谋杀的书。我就这样把这个世界上我喜欢的一切当成了消遣:我读阿加莎·克里斯蒂、柯南·道尔、约翰·格里森姆、约翰·勒卡雷,还有当代的一些人,想象自己成了现代版的夏洛克·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马普尔小姐让我相当疯狂,虽然我并不像她年纪那么大。实质上,那是一段痛苦的时期,因为我无法谋生,仰仗着父母度日,在我看来,这太无法让人接受了。
此间,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我舅舅埃米尔,他认为自己在布洛克区地拉那市中心的一个区域,东欧剧变前为高干住宅区。的一幢大厦里干保安已经干够年头了,足以让人们忘记他前特工的身份,便决定出去闯一闯。当时,他已经替几位重要人物解决过麻烦,他们对他的工作评价很高,在这些成功的尝试并蛰伏了十年后,他自己下定了决心,是时候干点事了。
一月的一个夜晚,隆冬时节,是没有人到外面去、都往暖烘烘的房间里一待、看电视上放恐怖片的日子,阿斯德里特舅舅即埃米尔·阿巴兹。突然造访我们家。他打断了我们正在欣赏的惊悚情节,把我们推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隐秘气氛之中,让我们在那约莫两个小时里吓得发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