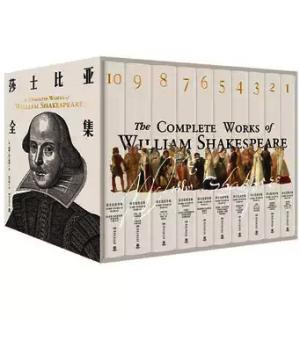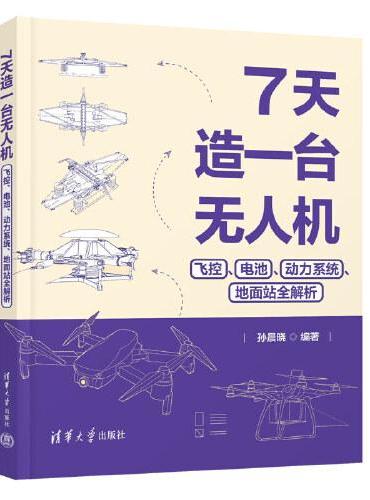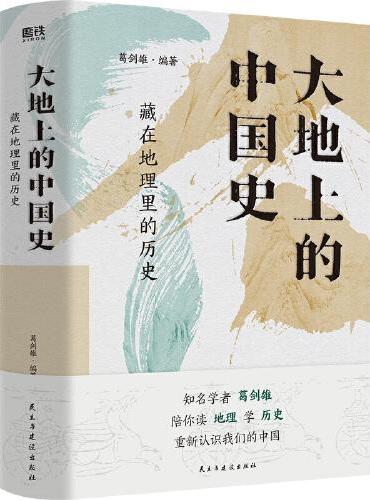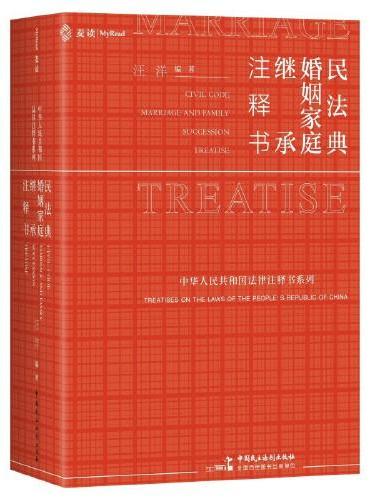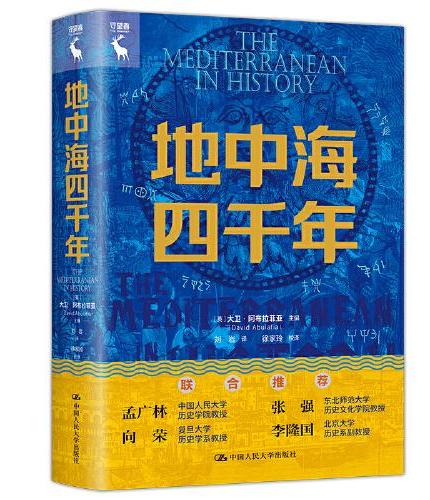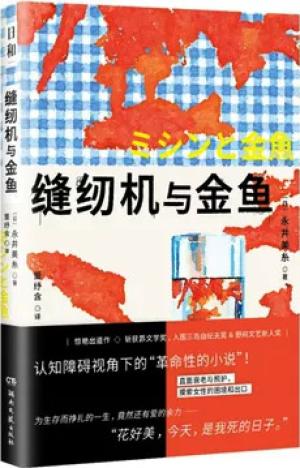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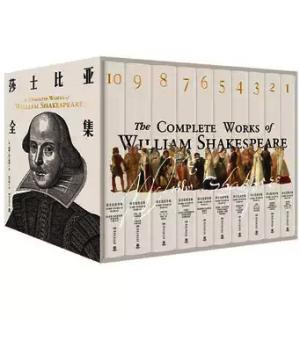
《
莎士比亚全集十卷
》
售價:HK$
5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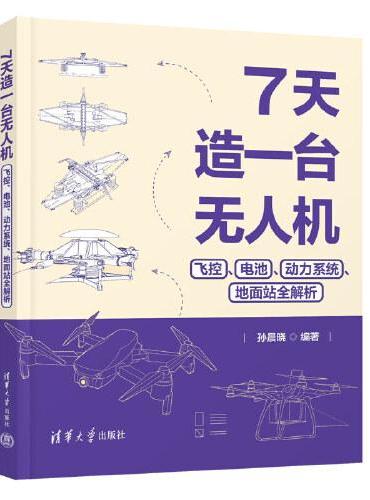
《
7天造一台无人机:飞控、电池、动力系统、地面站全解析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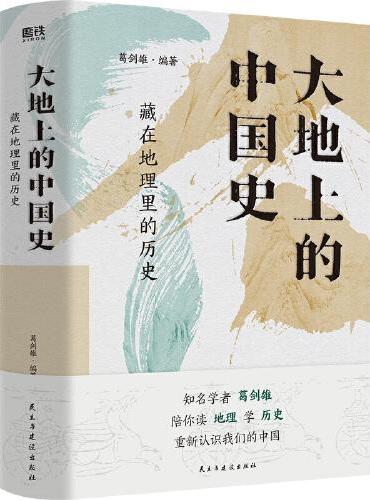
《
大地上的中国史:藏在地理里的历史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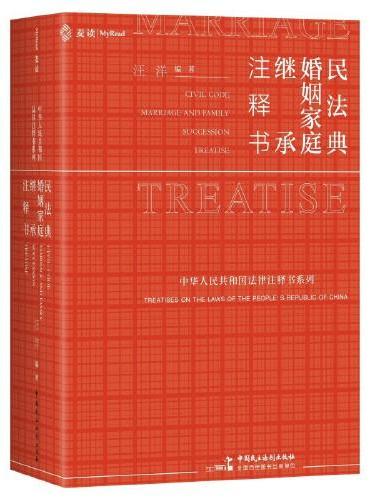
《
《民法典·婚姻家庭继承注释书》(家事法专用小红书,一书尽揽现行有效办案依据:条文释义+相关立法+行政法规+地方立法+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地方法院规范+权威案例,麦读法律54)
》
售價:HK$
1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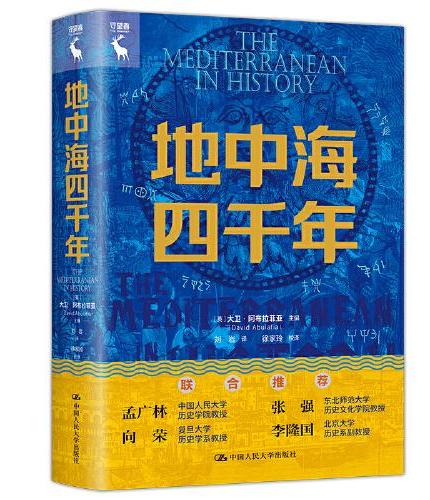
《
地中海四千年
》
售價:HK$
184.8

《
君子至交:丁聪、萧乾、茅盾等与荒芜通信札记
》
售價:HK$
6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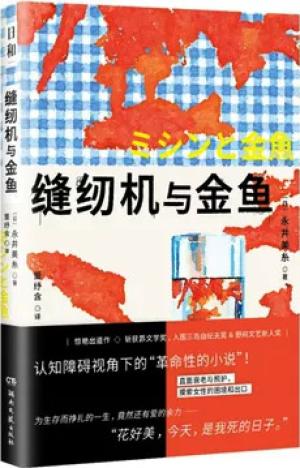
《
日和·缝纫机与金鱼
》
售價:HK$
41.8

《
金手铐(讲述海外留学群体面临的困境与挣扎、收获与失去)
》
售價:HK$
74.8
|
| 編輯推薦: |
|
继早期推出影响力巨大的《革命之路》和《十一种孤独》后,耶茨的创作生涯历经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复活节游行》再次展现了耶茨不凡的创作实力,这部作品包藏了惊人的广度和分量。平淡节制的叙述中流淌出耶茨惯有的文雅与悲剧性视角,将两姐妹的命运与梦想一点点撕碎,“既残忍,又温馨,既令人心碎,又严酷无情”,“这是耶茨好的小说”。
|
| 內容簡介: |
|
孩提时代的萨拉和艾米丽便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女孩。在艾米丽眼中,理智的姐姐总是高高在上,她嫉妒姐姐与爸爸(爸爸因为离婚而离开了她们)的关系,也嫉妒姐姐后来看似美满的婚姻。艾米丽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并不那么安全也异于传统的道路,所有的风流情事都无法真正满足她。虽然联系姐妹的纽带一直存在,但是她们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直到后,一起悲剧事件使得她俩的关系成了风暴中心……
|
| 關於作者: |
|
理查德?耶茨(Richards Yates,1926—1992)是“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作为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主流生活的忠实记录者,批评家们将他与契诃夫、菲茨杰拉德、约翰?契弗相提并论。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革命之路》甫一推出即获成功,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1962年他的部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出版,更被誉为“纽约的《都柏林人》”。耶茨的作品曾获《纽约时报书评》、《君子》、《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好评,有四本小说入选“每月一书俱乐部”。此外他还拥有一大批作家拥趸,其中不乏著名作家,如库尔特?冯古内特、安德烈?杜波依斯,他的作品也影响了许多作家,如雷蒙德?卡佛,他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
|
| 內容試閱:
|
部分
章
格莱姆斯家两姐妹没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回头看的话,问题总像是始于她们父母的离婚。那是一九三〇年的事,那一年,萨拉九岁,艾米丽五岁。她们的妈妈——她总是鼓励两个小女孩喊她“普奇”——带着她们搬出纽约,住到新泽西州特纳弗莱一所租来的房子里,她认为那里的学校更好,而且她希望能在郊区房地产行业开启一番事业。目标并没有实现——她寻求自力更生的计划就几乎没有实现的——于是两年后,她们离开了特纳弗莱,不过对于两个女孩来说,那却是一段值得铭记的时光。
“你爸爸从来不回家吗?”其他小孩子们会问,而萨拉总会抢先解释一番离婚是怎么回事。
“那你们能去看他吗?”
“我们当然啦。”
“他住在哪里?”
“纽约市。”
“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写标题的。他在纽约的《太阳报》写标题。”她这么说的口气清楚地表明,他们应该对此印象深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用词浮夸、不负责任的记者,或者一个闷着头干苦活的改稿编辑;但是那种写标题的人!他每天通读浏览纷繁复杂的新闻,提炼出显著的要点,然后用寥寥几个精挑细选的词语概括出来,并巧妙地加以编排以适合有限的空间——他是一位技艺非凡的新闻工作者,还是一个称职的爸爸。
有一次,两个女孩子去城里看他,他领着她们参观了《太阳报》报社,她们把一切都看了个遍。
“初版准备开印了,”他说,“所以我们先下去到印刷车间看看;然后我再领你们参观楼上。”他护送着她们,沿着一道铁制楼梯往下走,那楼梯散发着油墨和新闻纸的味道,接着便走进一间大大的位于地下的房间,里面排列着一排排高大的轮式印刷机。遍地都是工人在忙碌着,全都戴着挺括的方形小帽,是用报纸巧妙折叠而成的。
“为什么他们戴这种纸帽子,爸爸?”艾米丽问。
“嗯,他们可能会告诉你说这是为了防止油墨沾到头发上,但是我觉得,他们戴这帽子只是为了看起来神气活现。”
“‘神气活现’是什么意思?”
“哦,就跟你裙子上的那只小熊差不多意思,”他说,指着她连衣裙上石榴石镶嵌的泰迪熊形状的别针,她那天把它别在裙子上,就希望他能注意到。“那是一只很神气活现的熊。”
他们看着刚铸好的弧形的金属纸型在传送带上一路滑行,直到被扣紧在圆形转筒上;接着,一阵铃响之后,他们看到印刷机转动起来。脚下的钢制地板也颤动起来,让人感觉痒痒的,而那噪声铺天盖地,令他们无法交谈:他们只能彼此看着,微笑着,而艾米丽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耳朵。四面八方,连绵不绝的白色新闻纸通过机器,于是印好的报纸则源源不断地淌出来,一张压一张整齐地摞成一大堆。
“你们觉得怎么样?”在他们爬楼梯时,沃尔特?格莱姆斯问他的两个女儿。“现在让我们去看一下城市部办公室。”
那一大片地方摆满了办公桌,工人们坐在桌前噼噼啪啪地打字。“前面那地方,几张桌子挤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城市部的办公桌,”他说。“那个在打电话的光头男士就是城市版的编辑。他旁边那个人则更重要。他是执行编辑。”
“你的办公桌在哪儿呢,爸爸?”萨拉问。
“哦,我在稿件部。就在边边上。看见那儿了吗?”他指着一张黄色木头制成的半圆形大桌子。一个男士坐在桌子的圆心位置,另外有六个人围坐在外边,有的在阅读,有的在用铅笔匆匆地写东西。
“那就是你写标题的地方吗?”
“嗯,写标题是部门工作的一部分,是的。通常情况是,当记者和改稿的人完成他们的工作之后将报道交给送稿员——那边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就是送稿员——他就把稿子拿给我们。我们检查文稿中的语法、拼写和标点,接着我们写好标题,然后就可以送去了。你好,查理,”他对一个去冰水机那里,正好路过他们身边的人说。“查理,我想您认识一下我的姑娘们。这是萨拉,这是艾米丽。”
“好啊,”那个人说,腰弯成了九十度。“多么可爱的一对甜心啊。你们好?”
接下来,他带她们去了电传打字室,在那儿她们看到电报新闻从世界各地传来,之后她们进了排版室,一切都在那里被转换成铅字,排成报纸版面的形状。“你们想要吃午饭了吗?”他问道。“想先去下卫生间?”
他们走出去,在春日的阳光下穿过市政厅公园的时候,他一直牵着她们俩的手。她们俩都在自己漂亮的裙装外面穿了件薄大衣,脚上是白色的袜子、黑色的漆皮皮鞋,她们都是甜美漂亮的小姑娘。萨拉肤色要黑一点,一脸容易信赖别人的天真,而这将自始自终都伴随着她;艾米丽要矮一个头,长着金黄色的头发,瘦瘦的,神情非常严肃。
“市政厅看起来并不怎么样,是不是?”沃尔特?格莱姆斯说。“但是看见树林背后的那座高大建筑了吗?暗红色的那座?那是《世界报》——过去是,我应该这样说;它去年关门了。美国了不起的日报。”
“嗯,那现在《太阳报》是好的,对吗?”萨拉说。
“哦,不,亲爱的;作为报纸,《太阳报》真的并不怎么样。”
“它不是的?为什么呢?”萨拉看起来挺担心的。
“哦,因为它有点反动。”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非常、非常保守;非常亲共和党。”
“难道我们不是共和党吗?”
“我想你妈妈是的,宝贝儿。我不是。”
“噢。”
午饭之前他喝了两杯酒,给他的女儿们要了姜汁无酒精饮料;然后,等到他们狼吞虎咽皇家奶油鸡和土豆泥的时候,艾米丽张口说话了,这还是他们离开办公室后她头一次开口。“爸爸?如果你不喜欢《太阳报》,那你为什么还要在那里工作呢?”
他那哭丧的脸,在两个小女孩看来很英俊,露出了疲惫的神色。“因为我需要一份工作,小兔子,”他说。“工作越来越难找了。哦,我想要是我很有天分的话,我或许会换工作的,但我只是——你们知道的——我只是一个负责处理稿件的人。”
没有很多东西可以带回特纳弗莱,但至少她们还可以说他是写标题的人。
“……而如果你认为写标题很容易,你就错了!”一天放学后,萨拉在操场上对一个粗野的男孩说。
不过,艾米丽是一个非常讲究精确的人,于是一等那个男孩走出听力的范围,她便提醒姐姐要注意事实。“他只是一个处理稿件的人,”她说。
埃斯特?格莱姆斯,也就是普奇,是一个活跃的小个子女人,她的生活,似乎发誓要实现并保持一种难以把握的品质,她把它叫做“范儿”。她钻研时尚杂志,着装讲究品位,尝试各种各样的方式打理自己的头发,但是她的眼神依然是迷惘的,而且她永远学不会画口红,总是要超出唇线,而这导致她整个人染上一种恍惚的、容易受伤的踌躇感。她发现,有钱人比中产阶级更有范儿,所以她在培养两个女儿时,渴望她们能养成富人的那些神态举止。她总是寻求住在“好的”社区,也不管她能否负担得起,而且她还在礼仪得体方面要求苛刻。
“亲爱的,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做,”一天早晨吃早饭时她对萨拉说。
“做什么?”
“把吐司的硬壳浸在牛奶里。”
“哦,”萨拉把一片长长的、浸泡过的黄油吐司硬壳从自己的牛奶杯子里拖出来,一边在滴着奶汁,一边送进伸出来的嘴巴。“为什么呢?”她在嚼完咽下去之后问道。
“仅仅因为。看上去不好看。艾米丽比你整整小四岁,可她都不会做这么小孩子气的事。”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她总是暗示,百般暗示,艾米丽比萨拉更有范儿。
她在特纳弗莱的房地产行业不会成功的前景渐趋明朗之时,开始频繁地去别的小镇或者城市,一去就是一整天,把两姐妹丢给其他人家照顾。萨拉似乎并不在意她不在家,但是艾米丽做不到:她不喜欢别人家里的气味;她吃不下饭;她整天提心吊胆的,脑子里想着妈妈会出各种可怖的交通事故,而如果普奇来接她们晚了一两个小时,她就会像个婴儿似的嚎啕大哭。
那是秋天的某一天,她们到一个姓克拉克的人家里去待着。她们带了自己的纸娃娃,以防被孤零零地晾在一边无事可做,这似乎很有可能的——克拉克家三个孩子都是男孩子——但是克拉克夫人已经告诫她的大儿子迈伦要做一个好东道主,而他也认真对待自己的责任。迈伦十一岁,当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向她们炫酷。
“嘿,看呐,”他不断地说。“瞧这个。”
克拉克家后院的尽头有一根与地面平行的钢管,用钢的支架支撑着,而迈伦很擅长翻单杠。他会向钢管冲过去,毛衣里面的衬衣下摆在风中摆动,然后双手紧握钢管荡起来,脚跟由下面穿过管子再翻上去,用膝盖窝吊住身体;接着伸直整个身子从里面翻下来,跳到地面,溅起一阵尘土。
后来,他还带着弟弟们和格莱姆斯姐妹玩了一场复杂的打仗游戏,那之后,他们进到屋子里去看他收藏的邮票,而等到他们又一次来到门外时,已经再没有什么可玩的了。
“嘿,你们看,”他说。“萨拉的身高正好可以从单杠下面走过去,碰不到它。”确实如此:萨拉的头顶比单杠大约矮半英寸。“我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了,”迈伦说。“我们叫萨拉以快的速度朝着单杠跑,而她会刚好擦着单杠下面过去,那肯定非常刺激。”
他们确定好离单杠大概三十码远的一个地点,其他人站在两旁观看,萨拉则开始奔跑,她的长发在空中飘舞。没有一个人想到的是,萨拉跑起来的时候会比站着的时候要高一些——艾米丽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几分之一秒,她甚至来不及叫出声来。钢管正好撞在萨拉的眼睛上方,发出一声艾米丽永远不会忘记的声响——“咚!”——随之,萨拉倒在地上翻滚尖叫,满脸是血。
艾米丽和克拉克家的男孩子冲进房屋,一边尿湿了裤子。克拉克夫人看到萨拉也尖叫了一声;然后她用小毯子将萨拉包起来——她听说过事故受伤者有时会休克——立马开车送萨拉去医院,艾米丽和迈伦坐在车座的后排。萨拉这时已经不哭了——她从来不多哭——但是艾米丽的哭却刚刚开始。在去医院的途中她哭了一路,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她还在哭个不停。克拉克夫人从急诊室出来了三次,说了三句话:“没有骨折”,“没有脑震荡”,“缝了七针”。
后来他们全都回到克拉克家——“我从来没看见过有谁能这么忍住痛。”克拉克夫人一直说——萨拉躺在光线已经暗淡下来的客厅里的沙发上,大半个脸都肿了起来,青一块紫一块,一条厚厚的绷带蒙住一只眼睛,绷带外面覆着一条包着冰块的毛巾。克拉克兄弟又到外面院子里去了,但艾米丽却不愿意再离开客厅。
“你必须让你姐姐休息一下,”克拉克夫人告诉她。“去外面玩,好吧,亲爱的。”
“没事的,”萨拉用一种奇怪而渺远的声音说。“她呆在这儿可以的。”
因此艾米丽被允许留下来,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她正站在克拉克家难看的地毯上,咬着自己湿漉漉的拳头,而如果有谁非要想着拉她走的话,她一定会拳打脚踢的。此时她已经不哭了;她只是注视着躺在阴影处的姐姐,失去姐姐的可怕感受在心里一浪一浪地翻腾。
“没事的,艾美 ,”萨拉用那种渺远的声音说。“没事了。不要难过。普奇马上就来了。”
萨拉的眼睛并无大碍——她深邃的棕色大眼睛依旧是她那张将会变得很漂亮的脸上突出的特征——但是在她嗣后的人生中,一条细细的泛着蓝的白色伤疤永远地留在了脸上,从眉毛或隐或现延伸到眼睑,像被铅笔犹犹豫豫地划了一记似的,而艾米丽只要一看到它,就会想起她姐姐当时是多么地能够忍受痛苦。它也时不时地提醒艾米丽,自己面对恐慌是多么脆弱,自己孤身一人时是多么难以理解地感到恐惧。
?
第二章
是萨拉传授了艾米丽初的性知识。她们一边在房子后院里吃橙味雪糕,一边胡乱摆弄一只破破烂烂的吊床,那时她们住在纽约的拉奇蒙特——那是她们离开特纳弗莱之后住过的其他郊区城镇中的一个——而艾米丽听着听着,脑子里充满了各式各样混乱不堪、困惑不解的画面。
“你是说他们会把它塞进你里面吗?”
“是呀。一直往里塞。还会疼的。”
“那如果不般配呢?”
“哦,会般配的。他们总是般配的。”
“那然后呢?”
“然后你会有一个小宝宝。正因为如此要一直到你结了婚之后才可以做。你还不知道八年级的伊莲娜?辛科吧?她和一个男生做了,然后就有了小孩,所以她不得不退学了。甚至谁都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啦。”
“你确定吗?伊莲娜?辛科?”
“的。”
“好吧,但是她为什么想要做那样的事情呢?”
“那个男生引诱了她。”
“什么意思?”
萨拉慢慢地、长长地舔了一口雪糕。“你还太小了,你不懂。”
“我是不懂。但你不是说会疼吗,萨拉。如果疼的话,那为什么她——”
“嗯,是会疼的,但是也会觉得舒服。你知道有时候你洗澡的时候,或者可能你把手放到那里摸一摸,那种感觉——”
“噢,”艾米丽有些尴尬地垂下眼睛。“我明白了。”
对于不是完全理解的事情,她常常会说“我明白了”——而在这件事情上,萨拉也会如此。比如,她们俩都不理解妈妈为什么总是如此频繁地变换住所——她们刚开始在某个地方交了朋友,就要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但是她们谁也没有问过。
在很多事情上,普奇都令人难以捉摸。“我所有事情都和孩子们讲,”她会向其他成人夸耀;“在我们这个家里没有任何秘密。”——可是转过身,她就会放低声音,讲一些孩子们不宜听到的事情。
为了遵照离婚协议的规定,沃尔特?格莱姆斯每年都会来看望姐妹俩两三次,无论她们租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而有时候他会在客厅的沙发上过夜。艾米丽十岁那一年的圣诞夜,她躺在床上很久都没有睡着,一直能听到楼下父母亲发出不同寻常的说话声——他们一直在聊啊聊啊——而因为她必须要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她就装作一个小婴孩那样:她大声喊叫妈妈。
“怎么了,亲爱的?”普奇开了灯,弯下腰来问她,身上一股杜松子酒的味道。
“我的肚子难受。”
“你要么喝点小苏打?”
“不要。”
“那你想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
“你真是个傻孩子。我帮你把被子压好,你呢,就只想那些圣诞节会拿到的各种好东西,然后就睡着了。你不许再叫我啦;答应不?”
“好的。”
“因为爸爸和我正在进行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我们讨论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很久很久之前就应该谈了,而现在我们就要达成一个新的——一个新的谅解。”
她给了艾米丽一个湿吻,熄了灯,然后匆忙下楼去了,那场谈话进行得没完没了,而艾米丽躺在那儿,带着一股温暖的甜蜜等待着入睡。达成一份新的谅解!这就像电影里的离婚妈妈会讲的那样,就在画面渐渐淡出,气势磅礴的音乐响起的时候。
但是第二天早上,一切看起来都和之前他来看她们时的后一个早上一样:吃早饭时,他安安静静,彬彬有礼,就像一个陌生人,而普奇也避而不看他的眼睛;之后,他叫来一辆出租车把他送去火车站。起初艾米丽在想,也许他只是返回城里去拿他的物品,但是这个希望在几天后、几周后渐渐烟消云散了。她从未能找到合适的话去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她也没有向萨拉提起过。
两个小姑娘都有牙医所称的“覆咬合”问题,小孩子们把那叫做“龅牙”,但萨拉的情况要更严重一些:到十四岁时,她几乎嘴巴都合不拢了。沃尔特?格莱姆斯同意支付矫正牙齿的费用,而这意味着萨拉要每周坐火车到纽约去一次,跟他待一整个下午,去调整她的牙套。艾米丽有些嫉妒,既包括牙齿矫正又包括去市里见爸爸,可普奇解释说,他们无法承受两个女孩子同时矫正牙齿;艾米丽的矫正后面再弄,要等她再长大一些。
与此同时,萨拉的牙套有点糟糕:牙套里会不雅观地嵌些白色食物碎屑,而且学校里还有人喊她行走的五金店。谁会愿意亲吻那样一张嘴巴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又忍得了挨着她的身体待上哪怕是一小会儿的时间呢?萨拉非常认真洗她的毛衣,并且努力不让腋下的部分褪色,但是没有什么用:一件海军蓝毛衣的腋下部位会逐渐褪成知更鸟蛋的蓝白色,而一件红色的会变成泛黄的粉红色。出汗多似乎是她的一个诅咒,带给她的痛苦一点也不亚于她的牙套。
又一重魔咒降临了,降临至两个小姑娘身上。普奇宣布说,她在一个叫布拉德利的呱呱叫的小镇找到一座呱呱叫的房子,她们将在秋天的时候搬过去。她们几乎都记不清她们搬过多少次家了。
“嗯,这个地方并不差,是吧?”在她们搬到布拉德利的天放学后,普奇问她们。“跟我说说看。”
艾米丽已经忍受了一整天无人搭理的敌意——她是整个六年级仅有的两个新生中的一个——于是说,她想一切都挺好。但萨拉,一名高中新生,则兴奋不已地说着那天在学校里过得有多开心。
“他们为所有新来的女孩子召开了一个特别的晨会,”她说,“有人弹钢琴,原先学校的所有女生都站起来一起唱这首歌,你们听:
你好,新来的女孩,你好吗?
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
我们很高兴你加进来
因为你总带来开心欢乐
你好,新来的女孩,你好吗?”
“哇!”普奇开心地说,“确实挺不错呢。”
艾米丽心里一阵厌恶,只好把她的脸别转过去。这也许的确“挺不错”,可它是虚情假意的;她知道那样一首歌里隐含着虚情假意。
小学部和高中部是在同一栋大楼里,这意味着白天如果碰巧的话,艾米丽能看见她姐姐一两眼;这也意味着每天下午放学后她们可以一起走回家。她们约好的是放学后在艾米丽的教室碰头。
但是橄榄球赛季中的一个星期五,艾米丽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等啊等啊,等得她的胃都开始发紧了,也没见萨拉的影子。当萨拉终于到来时,她看着很滑稽——她很滑稽地笑着——在她身后笨手笨脚地跟着一个皱着眉头的男生。
“艾美,这是哈罗德?施耐德,”她说。
“嗨。”
“嗨。”他身材高大,肌肉健硕,粉刺疙瘩脸。
“我们要去阿蒙克看比赛,”萨拉解释说。“就告诉普奇我会回家吃晚饭的,好吗?你不介意一个人走回家吧,对不?”
但是问题是普奇那天上午去纽约了,她在吃早饭时就说了:“嗯,我想我会在你们放学前回来,但是我也不敢打包票。”那就意味着艾米丽不仅要一个人走回家,而且还要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家里,盯着光秃秃的家具看上好几个小时,听着时钟的滴答声,默默地等候。而即使她妈妈真的已经到家了——“萨拉呢?”——她可怎么告诉妈妈说萨拉跟一个叫哈罗德的男生一起去阿蒙克镇看比赛了?这是不可能的。
“你们怎么过去呢?”她问道。
“坐哈罗德的车,他十七岁了。”
“我觉得普奇不会喜欢你这么做的,萨拉。而我想你知道她不会喜欢的。你好跟我一起回家吧。”
萨拉绝望地转过头看着哈罗德,他那张大脸盘抽搐着,一副半笑不笑、难以置信的样子,仿佛在说他长这么大还没遇见过这么烦人的小屁孩。
“艾美,不要这样嘛,”萨拉恳求道,她颤抖的声音说明她正在输掉这场争论。
“不要哪样?我在说的你都知道。”
后艾米丽赢了。哈罗德?施耐德没精打采地沿着走廊走了,一路在摇着头(他很可能在比赛开始之前就能找到别的女孩子),格莱姆斯姐妹一起走回家去——或者更应该说是排成一列,艾米丽走在前面。
“你该死,你该死,你该死,”人行道上,萨拉跟在艾米丽身后说,“我要为这杀掉你——”说着她往前连跑三步,在她小妹的屁股上狠踹一脚,踢得艾米丽扑倒在地,双手趴在地上,课本全都飞出去,活页夹摔开了,纸张撒了一地。“——我要杀掉你,你把一切都搞砸了。”
讽刺的是,当她们到家时,普奇已经回来了。“什么情况?”她问道,萨拉于是哭着把整个情况讲了一遍——这是少而又少的艾米丽看到她哭的次数之一——很明确,那天下午的所有错误都是艾米丽的。
“有很多人去看那个比赛吗,萨拉?”普奇问道。
“哦,是的。所有的毕业班的,每个人……”
普奇看起来不如平常那么困惑。“好啦,艾米丽,”她严厉地说。“这的确一点都不对,你这样做。你明白吗?这的确一点都不对。”
在布拉德利有过一些幸福的时光。那年冬天,艾米丽交了几个朋友,放学后她就和她们一起玩,这样就使她不再很为普奇在不在家担忧。而同样是在那个冬天,哈罗德?施耐德开始带着萨拉去看电影。
“他吻过你吗?”在他们约会了三四次之后艾米丽问。
“不关你的事。”
“得了吧,萨拉。”
“哦,好吧。是的。他吻过我。”
“感觉怎么样?”
“和你想象的差不多。”
“哦,”其实艾米丽想说的是他不介意你的牙套吗?但是她又想了想,转而说:“你究竟看上哈罗德哪儿了?”
“哦,他——非常不错。”萨拉说,然后继续洗她的毛衣。
布拉德利之后是另一个小镇,之后是又一个小镇;终于在后一个小镇时,萨拉高中毕业了,没有上大学的具体打算,再说了,她的父母本来也负担不起。现在她的牙齿已经矫正好了,牙套已经取掉了;她似乎再也不爱出汗了,她胸部高耸,身段可爱,走在大街上,男人们都会回过头看,令艾米丽自惭形秽。艾米丽的牙齿依然有点龅牙,并且将永远无法矫正(她妈妈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承诺);她长得又高又瘦,胸部很小。“你有种小马驹一样的优雅风度,亲爱的,”她妈妈安慰她说。“你将会非常有魅力。”
一九四零年,她们搬回了纽约市,普奇为她们找了一处非同寻常的住所:华盛顿广场南边一座曾经气派不凡、如今已经破败陈旧的“大平层公寓”,有大窗户面朝着广场公园。租金远远超过普奇的负担能力,但是她就在别的开支上节省;她们再也不买新衣服,很多时候只吃意大利面。厨房和浴室里的装置都是锈迹斑斑的老古董,但是天花板却异乎寻常地高,参观者们都毫无例外地称赞这地方很有“特点”。这套房子在一楼,这意味着第五大道双层巴士上的乘客们在绕公园一圈向上城方向去的时候,可以看到房子的里面,而这在普奇看来似乎相当有范儿。
那一年,温德尔?L.?威尔基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于是普奇把姑娘们送到上城一个叫美国威尔基联合俱乐部的全国总部去做志愿者。她认为这对艾米丽是有益的,艾米丽需要有些事情做;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这会给萨拉一个“认识人”的机会,她这样说的意思是指合适的年轻男士。萨拉十九岁了,自哈罗德?施耐德以来,她看上过的男孩子当中,还没有一个能叫普奇觉得合适的。
萨拉也确实在威尔基俱乐部认识了一些人;没几周之后,她就带回家一个叫做唐纳德?克莱伦的年轻人。他面色苍白,彬彬有礼,着装非常细致,以至于你看到他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的衣装:一套白色细条纹西装,一件带天鹅绒领子的切斯特菲尔德大衣 ,还有一顶黑色的圆顶窄边礼帽。这礼帽有点古怪——已经不流行很多年了——但是他戴着给人一种威风凛凛的架势,让人觉得这个时尚可能会回归。他说话同样谨小慎微,像极了他过分讲究的穿着:他不说“像那种事”,而总是说“具有那种性质的事情”。
“你究竟看上唐纳德哪儿了?”艾米丽问。
“他非常成熟,非常善解人意,”萨拉说。“而且他非常——我不知道,我就是喜欢他。”她顿了顿,垂下了眼睛,仿佛特写镜头中的电影明星那样。“我想我可能爱上了他。”
普奇也挺喜欢他的,起初的时候——萨拉有这样一位贴心的追求者是再好不过了——而当他们正式请求她同意他们订婚时,她哭了几声,但没有做出任何反对。
提出反对意见的是沃尔特?格莱姆斯,是在订婚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之后才给他消息的,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疑问。这个唐纳德?克莱伦究竟是何许人也?如果他真像他说的那样是二十七岁,那么在他加入威尔基的竞选阵营之前,他是做的哪一行哪一业?如果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就像他的日常举止中显示的那样,那他上的是哪所大学?还有了,他是哪里人?
“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他呢,沃尔特?”
“我不想在午餐的饭桌上拷问这个孩子,还当着萨拉的面;我想你可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哦。”
“你是说你从来根本就没问过他这些事情?”
“嗯,他总是像很——没;我没问过。”
接下来就是几次气氛紧张的面谈,通常都是夜里很晚了,普奇熬夜等到他们回来之后,而艾米丽也会躲在客厅门外偷听。
“……唐纳德,有些事情,我还从没有很清楚。你到底是哪里人呢?”
“我告诉过您的,格莱姆斯太太。我出生在本地的嘉登城,但是我父母搬过很多次家。我主要是在中西部长大的。中西部许多不同的地方。后来我爸爸去世后,我妈妈搬到了堪萨斯州的托皮卡;现在她在那儿安家了。”
“那你在哪儿上的大学?”
“我想我也告诉过您了,在我们次见面的时候。其实我没有上过大学;因为我们付不起学费。但是我很幸运在托皮卡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工作;再后来威尔基先生获得提名,我就为威尔基俱乐部工作了,直到我现在被调到这里。”
“哦,我明白了。”
似乎那一夜就只能想到这些问题了,但还有别的问题。
“……唐纳德,倘若你只在那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三年,并且倘若你高中毕业后就一直在那儿,那你怎么能——”
“哦,不是高中一毕业就去那儿的,格莱姆斯太太。我起初还做过一些别的工作。建筑工作,繁重的体力活儿,类似那种性质的。能找到的活儿都干。我还要养活我妈妈,您明白的。”
“我明白。”
终,威尔基选举失败之后,唐纳德在下城的一家经纪公司做一份微不足道的工作,而他也反复多次自相矛盾,暴露出他并不是二十七岁;他是二十一岁。一段时间来,他一直在虚报自己的年龄,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比同龄人要大一些;威尔基俱乐部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二十七岁,因而当他遇到萨拉时,他就很自然地说自己是“二十七岁”。难道格莱姆斯太太还不能理解这样的言辞草率?难道萨拉还不能理解?
“那好吧,可是唐纳德,”普奇说,艾米丽也在竭力想听到谈话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你不能在这事情上告诉我们实情,那我们还怎么相信你说的其他事情呢?”
“要怎么做您才能相信我呢?好吧,您知道我爱萨拉;并且您也知道我在经纪事业上有着美好的未来——”
“可我们怎么能知道?不,唐纳德,这样还不够的。这完全不行的……”
等他们声音歇下来之后,艾米丽冒险朝客厅里偷偷瞄了一眼。普奇看起来浑身正气,萨拉倍受打击;唐纳德?克莱伦则独坐一旁,双手捧着脑袋。他那搽过发油、精心梳理过的头发位于头顶处有一道微微的隆起,显现出他圆顶窄边礼帽压出来的痕迹。
萨拉再没有把他带回家里来,但是一周中她还会去见他几次,跟他一起出去。她看过的所有电影中的女主人公都清楚地表明,她无法采取其他行动;再说了,她已经向很多人介绍说他是“我的未婚夫”,他们会怎么想呢?
“……他是个骗子,”普奇会大声吼她。“他是个小孩子!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我不在乎,”萨拉会大声反驳。“我爱唐纳德,我要嫁给他!”
这让普奇无计可施,只能拍着手大哭起来。这些吵架通常会以她们二人在这散发霉味的气派公寓的不同地方嚎啕大哭而终结,而艾米丽则会一边听,一边吸吮她的指关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