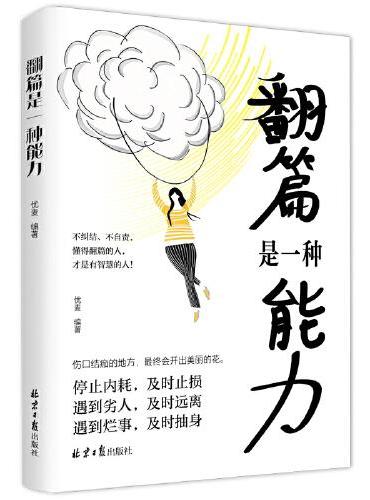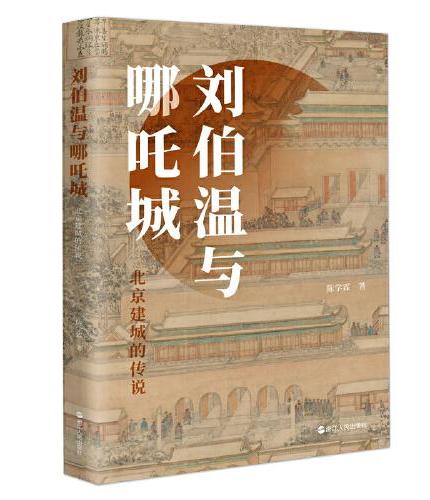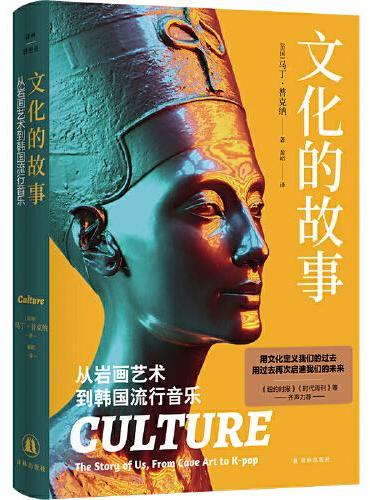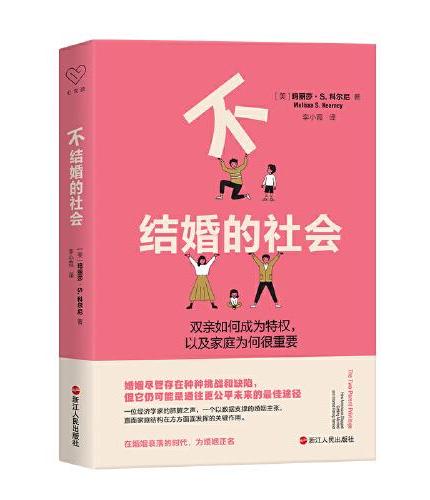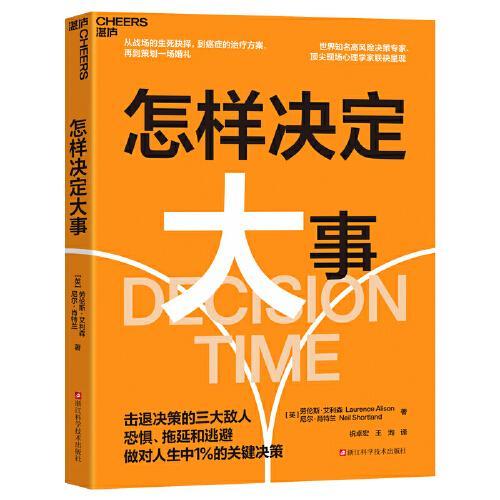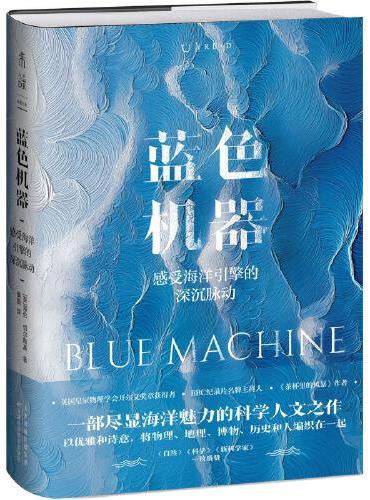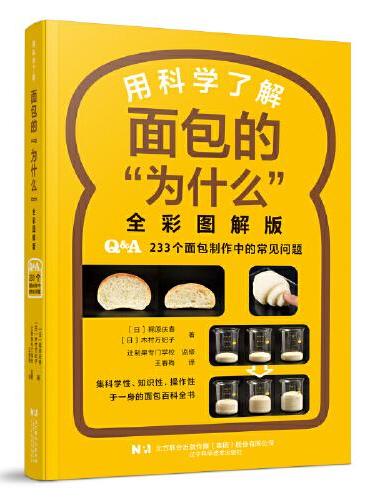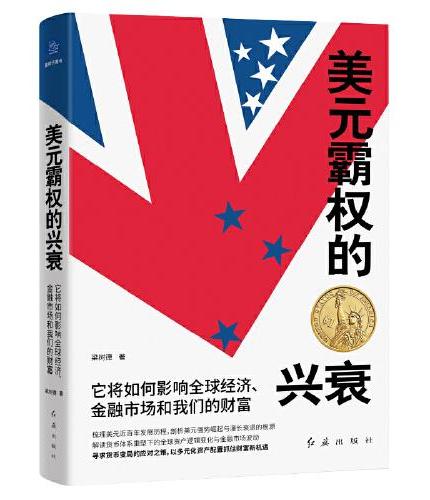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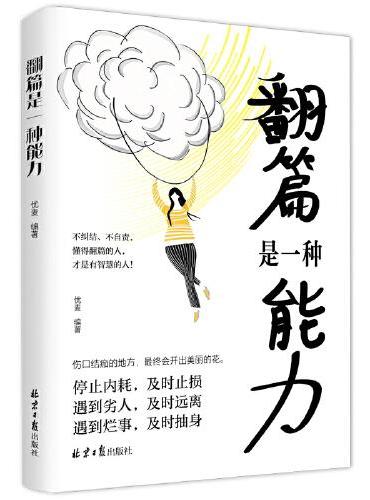
《
翻篇是一种能力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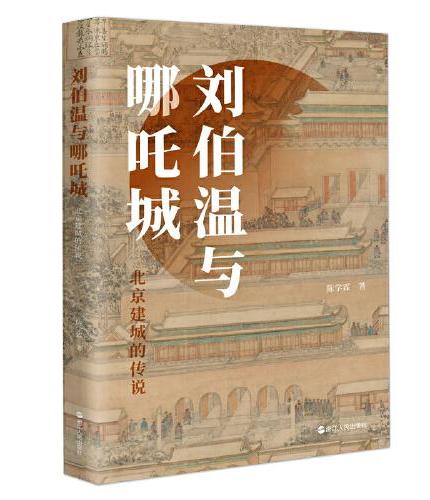
《
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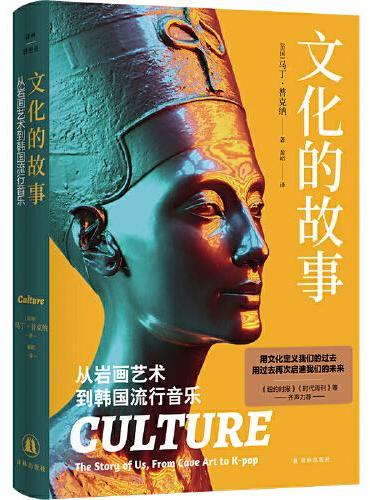
《
文化的故事:从岩画艺术到韩国流行音乐(译林思想史)哈佛大学教授沉淀之作 获奖不断 全球热销 亲历文化史上的15个关键点 从史前艺术到当代韩流的人类文化全景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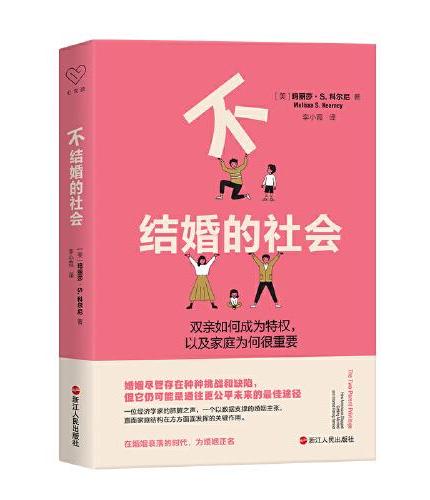
《
不结婚的社会:双亲如何成为特权,以及家庭为何很重要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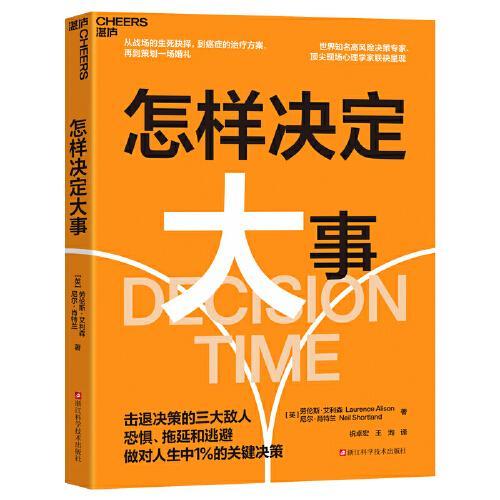
《
怎样决定大事
》
售價:HK$
10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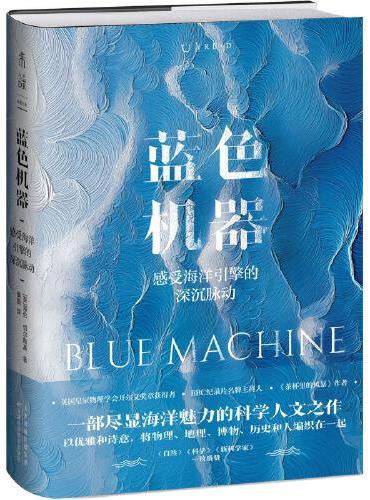
《
蓝色机器:感受海洋引擎的深沉脉动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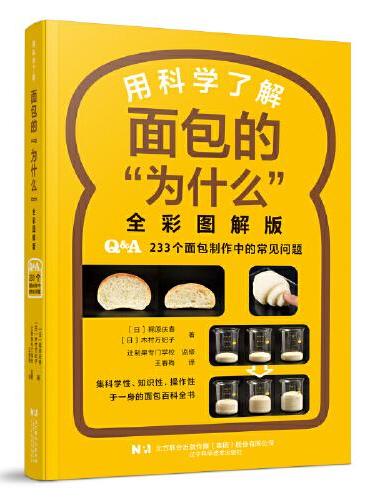
《
用科学了解面包的“为什么” (全彩图解版)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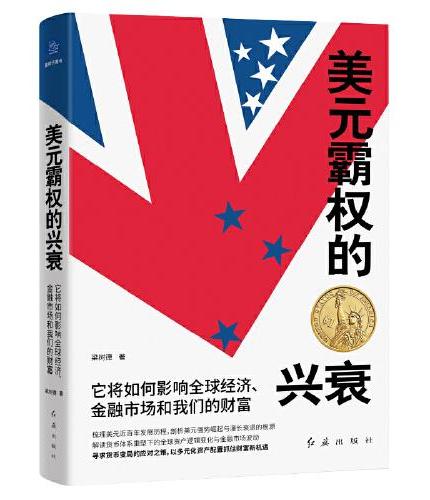
《
美元霸权的兴衰:它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和我们的财富(梳理美元发展历程,剖析崛起与衰退的根源)
》
售價:HK$
63.8
|
| 編輯推薦: |
兼具敏锐的艺术感觉、独特的思想追求、清醒的社会意识的文学批评。
以谦虚审慎的态度回应文艺创作,用朴素自然的文风进行理论探索。
《不如忘破绽》是来自著名文学评论家郜元宝多年来优秀文学批评文章的“自选集”,并非“旧作”的“选萃”,而是一部崭新的力作。
批评范围更开阔,力求呈现当代文学的全貌。
时间跨度更扩大,力求把握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探究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内在关联。
批评态度更审慎,基于对文学史本身的尊重,对当代文学更多一份耐心和虔敬。
批评语言更务实,力避架空的理论或多余的文辞,力求朴素自然的风格。
|
| 內容簡介: |
《不如忘破绽:郜元宝文学批评自选集》,是作者近六七年当代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新作的首次结集。名为“自选集”,却并非“旧作”的“选萃”,而完全是一部新书。
对作者本人来说,本书论述范围有所扩大,有作者过去熟悉的王蒙、张炜、贾平凹等,也有作者以往论述较少的汪曾祺、路遥、莫言、夏商等,还有作者先前未曾讨论过的柳青、赵本夫、李约热等。范围扩大的主要目的,乃是力求呈现当代文学的全貌。
本书所论作家作品,在时间跨度上也有所拓展。作者过去主要关注当下文学现象,本书则从“新世纪”延伸至九十年代、“新时期”“文革”和“十七年”,既关注新作的破土,也考释旧作的复活,既有作家论式较全面的评述,也有某些重要作品的细读与再解读。多半还是以点带面的个案研究,但力求辐射整个当代文学,力求把握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也努力探究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内在关联。
在批评态度上,作者比以往更为审慎,对当代文学更多了一份耐心和虔敬。但这是对文学史本身的尊重,并非刻意追求当代文学的“经典化”。
在批评语言上,继续探索一种求真务实、朴素自然的风格,架空的理论或多余的文辞能免则免。这是作者想矫正自己过去华而不实的文风的努力,或许对批评界同行也不失为一种提醒。
|
| 關於作者: |
郜元宝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现代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鲁迅研究、现代汉语与中国新文学互动关系四个具体学科领域,先后著有《遗珠偶拾——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时文琐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鲁迅六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汉语别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等。另有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集多部。
|
| 目錄:
|
目录
自?序 1
上编
作家与作品
上海令高邮疯狂
??——汪曾祺“故里小说”别解 2
与“恶食者”游
??——汪曾祺小说怎样写“吃” 27
天漏,人可以不漏
??——评赵本夫《天漏邑》 45
擦亮“过去”这面镜子
??——读冯骥才《艺术家们》 53
写出“万难忍受的”“骇人的卑污”
??——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读后 64
“旧作”复活的理由
??——《这边风景》的一种读法 75
审视或体贴
??——重读王蒙《活动变人形》 102
千古一哭有素芳
??——读《创业史》札记之一 118
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一)
??——重读《白鹿原》 142
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二)
??——重读《古船》 159
中国初期改革前后的编年史与全景图
??——细读《平凡的世界》 184
羿光庄之蝶,海若陆菊人
??——贾平凹《暂坐》《废都》《山本》对读记 214
作家张炜的古典三书 225
先锋作家的童年记忆
??——重读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230
空间·时代·主体·语言
??——论《东岸纪事》对“上海文学”的改写 237
难懂的袁凌 249
下编
文学史与文学批评
“民国文学”,还是“‘民国的敌人’的文学”? 254
“创作”与“议论”
——反思“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的一个角度 261
论“权威”
??——关于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一个设想 280
“重大题材”再议 287
二十年后的回顾
??——“人文精神讨论”再反思 296
身份转换与概念变迁
??——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观 302
近二十年“文学沪军”一瞥 312
“作家论”的转变与重建 317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 321
文学是借助文字来发挥语言奥妙的艺术 351
何必以“代”论文学 360
中国当代文学和批评八题议 362
我怎么做起“批评”来(代跋) 424
|
| 內容試閱:
|
自?序
近十年,我没有再出版新的评论集,因为精力更多消耗在其他方面了。比如,这三四年陆续出版的四本书,《时文琐谈》关注当下中国某些语言现象,《小说说小》不拘古今中外,侧重谈“小说理论”,《鲁迅六讲二集》收录《鲁迅六讲》之后十多年鲁迅研究的文章,此外还出版了《汉语别史》的修订本。
但我毕竟没有丢开评论,十年里也写了六十余篇。只是忙东忙西,从未想到要按老办法每隔几年编一本集子,就任其全部胡乱堆积在电脑文件夹里,以至于承蒙作家出版社不弃,约我编文学评论自选集时,面对这六十余篇文章,真不知如何来“选”。踌躇再三,姑且就从中拣出二十八篇:一半是作家作品的重读细读,一半是文学史概观与批评理论的漫谈。
过去出评论集,喜欢用其中谈论某作家作品的某篇文章之标题做书名,如《拯救大地》《另一种权利》《说话的精神》《不够破碎》《岂敢折断你想象力的翅膀》等。这次打破惯例,截取鲁迅杂文《怎么写〈夜记之一〉》的结语“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之下半句来做书名。这倒并非玩什么禅机,而是觉得差不多能借以说明当下的心境。
过了“知天命”之年,心思识见好像不进反退。许多想法一经反省,便破绽百出。就说为何要从六十余篇文章中选出这二十八篇,自己想到的理由总觉得有许多破绽。不从以往七八本评论集中选取“代表作”,而只取近十年的“新作”,是想避免炒冷饭,将来也好理直气壮送人“新书”。名为“自选集”,实乃裒辑近十年批评方面的“新作”。但这些文章都曾发表,也并非时鲜货。何况就内容而言,我之所谓“新”,安知不正是他人之所谓“旧”?又安知“新作”一定比“旧作”更高明呢?
上编“作家与作品”聚焦于重要作家作品,强调“重读”与“细读”,但方法不尽相同,而且限于篇幅,许多谈青年作家作品的文章都不能选入,结果似乎主要围着几个老作家和“乡土文学”兜圈子。下编“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关注文学史宏观问题和理论批评的某些症结,但是跟流行的文学史宏观与批评理论的研究往往并不合拍。
这当然都是“破绽”,也都无可奈何。人无完人,书无完书,文无完文。许多破绽,与其徒劳无功地去“防”,倒不如一开始就叫它无所容于胸臆之间,这样至少可以免掉无谓的纠结。“不如忘破绽”,因此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书名。
但真正“忘破绽”又谈何容易!此处“忘”了,彼处又会“防”起来。几十年埋头写文学评论,自以为算是在小事情上有忠心了,但这会不会正是将来经不起试炼的草木禾秸的工程,也就是、难弥补的破绽呢?
总有一些破绽,“忘”不了,也“防”不住,只能面对。
2021年1月15日编讫,记于沪上
我怎么做起“批评”来(代跋)
我于1982年秋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大一、大二的中国文学史必修课,章培恒先生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王水照先生讲唐宋,李平先生讲元明清,如果说我还有一点古代文学的底子,完全是拜这几位可敬的先生之赐。
章先生据说本来不修边幅,但那时新从日本讲学归来,衣裳光鲜、皮鞋锃亮,头发理得一丝不苟,金丝边眼镜后面,双目炯炯有神,“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每次走进教室,没有任何过门,立刻就以浑厚深沉的男中音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低头看讲台,不说闲话废话,也不看学生。课后我们整理出笔记来,就是一篇思路缜密、材料翔实、观点新颖的论文。水照先生一贯乐呵呵的样子,十分谦和。他在完成文学史规定动作之余,喜欢讲古代作家和健在的古典文学研究名家(比如他在“文研所”时期的“领导”何其芳、余冠英、钱钟书等)的趣闻轶事,课堂气氛活跃,大家兴致很高。李平先生讲元明清,重点在戏曲,“唱念做打”,都要“表演”一番,据说是深得他的老师赵景深先生的真传。三十多年过去了,元杂剧和昆曲的一些段落记忆犹新,想忘都忘不了,这不能不感谢李平先生。
选修课有刘季高先生的清诗研究、王运熙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陈允吉先生的佛教与文学研究、黄霖先生的明清小说专题,都很叫座。这是复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继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蒋天枢诸老之后力量强的组合。我们一进复旦,就受到浓厚的古典文学的熏陶,许多同学很快“自动”打消了来中文系当作家的梦想,迷上了古典文学。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并且有幸在同学们中间博得了“老夫子”的称号,至今无法卸去。
但到了大三大四,也就是1985年前后,我竟突然冒冒失失地写起文学评论来了。
不用说,这是“新时期文学”潮流裹挟所致。和中国绝大多数高校一样,复旦中文系的“强势学科”也是古典文学。但“现当代”在八十年代势头陡起,“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作品选”都是同学们喜欢的课程。贾植芳先生、潘旭澜先生不常上课,陈思和先生本科毕业留校,做班主任工作,课也不多,但在线授课的王继权、鄂基瑞、邓逸群、唐金海等先生们都专心致志、意气风发,虽然不像古代文学那样名师荟萃,但在爱好现当代文学的学生们眼里,也未遑多让。更何况整个社会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受大环境影响,我的兴趣很自然地也就从过去爱读的历代文学名篇和相关研究论著慢慢转到“现当代”了。
走进中文系阅览室或学校图书馆报刊厅,让我流连忘返的不仅有现当代名家名作,还有全国各地一口气冒出来的专登文学评论的报刊,如甘肃《当代文艺思潮》、陕西《小说评论》、山西《批评家》、黑龙江《文艺评论》、辽宁《当代作家评论》、山东《文学世界》(后改名为《文学评论家》)、四川《当代文坛》、福建《当代文艺探索》、天津《文学自由谈》和北京的《文艺报》、山东的《作家报》、河北的《文论报》以及上海本地的《文学报》《文汇报·文艺百家》。后来我在这些刊物上都发过不少文章。其他如《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福建文学》《当代》《花城》《钟山》等文学杂志也有评论专栏,我几乎每期都看。那时对现代文学兴趣不太大,只是惊喜地发现在古典文学研究之外,原来还有当代文学评论这片神奇的天地!文思喷涌、神采飞扬的评论文章和正襟危坐严谨求实不尚辞华的古典文学研究,味道毕竟不同,但对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文学评论的崛起是“新时期”文学复苏的必然现象,也是“思想解放”的副产品。文学评论——那时大家更爱讲“批评”——充当思想探索乃至社会运动的急先锋,这在世界范围屡见不鲜,但八十年代中国的“批评热”又有其特殊性。“文革”结束,环境宽松,上上下下精神面貌昂扬舒畅,长期积压的地火与暗流纷纷冲出地表,而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尚未全面展开,人文社会科学也百废待兴,青黄不接的关口,历史选择了读书人比较熟悉、容易上手也更能吸引读者大众的文学批评这一表达方式,于是在“批评”的名义下就迅速集结了大批“精英”,他们借谈论文学来纵论社会历史文化的一切问题,诚可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有不可一世之慨。
那时候,老中青三代批评家齐聚一堂,挥笔竞写文学评论,盛况空前,但跟我们距离近的还是上海各高校中文系、社科院、作家协会的“青年批评家”,班主任陈思和先生邀请他们中的吴亮、许子东、程德培、李劼、夏中义、毛时安、蔡翔等多次来复旦讲课,或者与我们面对面座谈,极大地煽动了我们对评论的热情。1985年10月浙江文艺出版社“新人文论”丛书中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吴亮《文学的选择》在我们中间不胫而走。斯文清秀言辞犀利的程德培,敦实健壮、长发披肩、口若悬河的吴亮,简直就是两颗耀眼的明星。
高校文学评论一开始有点落在作协系统后面,所以思和先生经常带我们几个喜爱当代文学的同学一起去上海市作协参加各种文学活动,结识李子云、周介人等作协的评论前辈,同时指导我们选修本系“中年批评家”潘旭澜、徐俊西先生的当代文学以及陈鸣树先生的文艺学方法论课程。潘先生的研究生称他们的导师为“潘公”,我的篇关于梁晓声的评论文章就是他课上的作业,得到他的首肯,再由思和先生推荐给《当代作家评论》发表。“潘公”在我文章后面写了一大段鼓励的话,正文部分也有不少批注修改。他的字刚劲方正,很有个性。我也是次从他那里学到如何使用准确而醒目的修改符号。原稿誊抄过后没有保留,近看李辉先生纪念潘公的文章,附有潘公当时给他的修改记录。他对老师墨宝的敬惜令我惭愧。周介人先生不久主政《上海文学》,本来就颇有影响的《上海文学》评论栏到他手里办得更加有声有色。徐俊西先生后来借调至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做所长,旋又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期间他一手创办的《上海文论》很快就继《上海文学》评论栏之后,产生了全国性影响,这使我们颇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感觉。《上海文论》似乎没有正式的编委会,徐先生和他的助手,社科院文学所毛时安先生,以及新从《当代作家评论》转来的顾卓宇先生,不定期在复旦大学教师第十宿舍他自己家里商量办刊事宜,每次总会邀请思和先生和我们几个在评论界刚刚冒头的复旦同学参加。
身处这种环境,没有理由不走上批评的道路。但我大学时代主要兴趣是古典文学,尤其是复旦特色之一的古代文论。虽然发表了几篇评论,但临近毕业,还是想考文学批评史专业的研究生。碰巧那年王运熙先生轮空停招,就准备报考华东师大古代文论专业研究生,听说王元化先生刚开始在华师大担任这一专业的导师,但思和先生劝我还是留在复旦,于是就改考据说与古代文论相通(后来才知道其实区别很大)的文艺学专业。幸亏硕士导师应必诚和博士导师蒋孔阳两位先生都很宽松,他们知道我不喜欢纯理论,总是跟在陈思和先生后面搞评论,心里都有些不以为然,但口头上从不明确反对,所以六年“读研”,我一边应付学业,一边就用大把时间做批评。至于古典文学,只能偶尔读一点,维持业余爱好的水平。如今碰到某些和古典文学、古代文化关系密切的当代文学问题,很想一探究竟,但储备不足,只能知难而退。这算是我当初选择以批评为主业的遗憾之一吧。
转眼三十多年,自己并不觉得特别懒惰和愚笨,也确实写过不少文章,出过不少批评文集,但到底几斤几两,自己清楚。
我首先不能和前辈(亦即当时那些“中青年批评家”们)相比。就拿中文系我的老师们来说吧,他们从事批评之前已经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潘旭澜先生评杜鹏程,徐俊西先生评王蒙,陈思和先生评巴金,都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发人所未发,而我以及跟我年龄相仿的“青年批评家”们则是“纸上得来终觉浅”。比如我也研究王蒙,还很快得到王蒙先生的称赞,但徐俊西先生论王蒙,更加关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王蒙复出之后的小说塑造的那些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形象,对此我是直到不久前才若有所悟。又比如我很长一段时间对巴金《随想录》的“讲真话”并不太当回事,对思和先生一再谈论晚年巴金的贡献认识不足,也是直到近,才彻底扭转了一直以来对巴金《随想录》的模糊认识。
从事文学批评,需要多方面修养。首先必须保持大量而快速的吞噬性阅读,否则你就无法对当下创作动态作出及时回应。其次,需要有包括文学史在内的社会文化历史的广博知识,否则你就无法将批评对象放在恰当的框架内予以准确把握。复次,需要敏锐的艺术感觉,不仅知道作家“写什么”“怎么写”,还要知道“写得怎样”,否则即使讲了许多关于“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貌似聪明的话,却很可能根本分不清你所面对的是杰作,还是平庸乃至失败之作。后,明达顺畅的文字表达无疑也非常重要,好还要有个性鲜明的文体追求,否则文字干巴巴,无法贴近作者,也不能拨动读者的心弦。
但在这一切之上,重要的还是批评家对背负着自己时代特殊社会历史问题的时代精神的理解,否则你不仅看不清批评对象与时代的联系,也无法以你的批评准确而有力地击中时代和文学的要害。恰恰在这点上,我们这一代“学院批评家”先天不足。这除了因为我们太早太顺利地被批评界接纳,囿于书本知识,生活阅历跟不上,也因为在我们登上文坛的1985年前后,“文学回归自身”“文学向内转”“文学自律”的呼声正高,提倡者们自然有他们的考虑,但不谙世事的年轻批评家们就有可能因此而过分看重“文学本身”,多少疏忽了文学和社会人生一刻不能分离的血肉关系。批评应该从这种“关系”中汲取激情和灵感,不能仅仅面对生活,不能仅仅念叨历史,更不能仅仅抓住作品。
但有一得必有一失,反之亦然。前辈批评家们固然不乏清醒的社会意识,相应也都具有开宗立派、舍我其谁、喜欢扯旗帜呼口号的气概,而我们六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一代批评家们在成长过程中虽然并没有被社会运动的洪流抛在局外,但毕竟也没有一开始就被推抵旋涡中心,因此逐渐也就习惯于软弱迷惘的状态,偶尔也呼两句口号,下几点大判断,事后总感到心虚,只想单单夸耀自己的软弱,正视自己的迷惘,只想在作品和历史的细部寻寻觅觅了。因为积习难改,表面上我写文章似乎颇重气势,其实非常荏弱。不相识的朋友往往误以为我必定人高马大,见面总是愕然。
我的许多评论集往往以某篇作家论或作品论的标题为书名。1994年本《拯救大地》的书名是张炜论的标题,此后《说话的精神》是王蒙论的标题,《不够破碎》是评阿来论的标题,《岂敢折断你想象力的翅膀》是苏童论的标题。作家论和作品论是我的主要批评模式。
我偶尔也会写一点“概观”模样的文章,但始终提醒自己要少写。并非不想写,更非不懂得欣赏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勃兰兑斯那种高屋建瓴纵横捭阖的大块文章,而是自觉力量不足以扛鼎,所以还是藏拙为妙。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2期
上海令高邮疯狂
——汪曾祺“故里小说”别解
一、“作品的产生与写作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汪曾祺一生足迹遍天下,“按照居留次序”,先后有高邮、“第二故乡”昆明①、上海、武汉、江西进贤、张家口、北京。武汉除外,上述各处汪氏小说或多或少都写到过。《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1992)小说部分就是“把以这几个地方为背景的归在一起”②。1995年编《矮纸集》,如法炮制,但交代得更清楚:
以作品所写到的地方背景,也就是我生活过的地方分组。编完了,发现我写的多的还是我的故乡高邮,其次是北京,其次是昆明和张家口。我在上海住过近两年,只留下一篇《星期天》。在武汉住过一年,一篇也没有留下。作品的产生与写作的环境是分不开的。③
短篇《迷路》与散文《静融法师》都写在进贤参加土改之事,可能数量有限,忽略不计了。上海仅《星期天》一篇,却特别提及,显然比较看重。
“作品的产生与写作的环境是分不开的”,汪氏这一点颇有古风,不同于许多当代作家有意无意模糊作品的时、地线索,一味以虚构为圭臬,或一转而趋之影射。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家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陆游,他们的诗文,鲁迅杂文和《故事新编》“今典”部分,时代有别,文体各异,精神却一脉相承,皆始于写实而终于普遍意味之寻求。
汪曾祺小说包含虚构,又无不依托真实生活经历,绝非“纯属虚构”,此点已为“汪迷”所熟知。他说,“我写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沙上建塔,我没有这个本事。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有些是有原型的”。①不仅创作依据原型,有时甚至连人物姓名都不加改动。但汪氏家乡人并不“对号入座”,跟他打官司。他们知道作者以自己为原型,终创造的人物却有质的区别。②这也就是鲁迅谈到《故事新编·出关》时所说的:“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③当我们将汪曾祺归入“中国当代作家”时,应特别留意此点。读汪氏小说,首须注意他在时地背景清晰的写实基础上增添了哪些社会人生的普遍寄托,如此方可获更深之解悟。
汪氏和高邮、昆明、张家口、北京的关系,论者甚夥。近年来,分地域重新编辑出版汪曾祺文集的举措不止一例。①汪氏将上述各处社会历史文化和他本人在这些地方的经历反复写入作品,不劳研究者特别放出眼光,也能看得分明。相比之下,汪氏与上海极深之因缘至今尚无全面梳理。②笔者近作《汪曾祺结缘上海小史》略述文本之外汪氏与上海关系始末。③但汪氏结缘上海并不限于文本之外。1970年代末“复出”之后,除了《星期天》,他再无作品直接叙写上海,然而八九十年代故里小说“藏”了不少上海元素。汪氏笔下三四十年代高邮古城并非世外桃源,乃是与外界交通频繁的颇为开放之区,而汪氏故里小说所涉之外界主要即为上海,昆明、北京、张家口、武汉、进贤等地则绝少有深刻关联彼时之高邮者。
这点从未有人留意,遑论研究。今特撰此文,一探汪氏故里小说内部上海叙事之深意,及上海与汪氏故里小说特殊魅力之关系,希望借此打开“汪曾祺研究”另一扇窗户。
二、高邮的远方是上海
1983年7月,以四十年代末在上海致远中学教书经历为素材,汪曾祺顶着北京骄阳挥汗创作了短篇《星期天》。这是他正面描写上海的小说,笔者曾有评析①,其中和本文相关而尤可注意者,是上海人形象在这篇长久被忽略的杰作中大多不佳,或荒谬可笑,或无聊空虚,或平庸鄙俗,或阴冷恶毒。《星期天》之外,1980年代和1990年代汪氏小说很少正面涉及上海,但侧面描写并不少。比如,1986年夏创作、被老友黄裳誉为“晚的力作”的《安乐居》②,写作者本人在北京住家附近经常光顾的小饭馆,中间就冒出一个“久住北京,但是口音未改”的“上海老头”。在另外一些和上海并无直接关系的小说中,汪曾祺也会提到上海,甚至突然用到几句上海话。
但“复出”之后,上海叙事更多乃见于以儿时生活记忆为素材的故里小说——并非像《星期天》那样正面描写上海众生相,而主要描写那些身份特别的高邮人,他们都与上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高邮人怎么会和千里之外的上海发生关联?1947年创作的小说《落魄》早透出此中消息。该篇写一个斯文的“扬州人”在昆明的凄凉光景,身为“同乡”的叙述者“我”为之痛心疾首。汪氏写这篇小说时人在上海,颇多自况,说的是扬州人在昆明的“落魄”,暗含的则是高邮人汪曾祺在上海的灰暗与愤激,跟同时正面描写“我”漂泊上海的短篇《牙痛》互为表里,一个暗讽,一个明说。
《落魄》开头一段议论颇能解释高邮人缘何要去外地:“我们那一带,就是像我这样的年纪也多还是安土重迁的。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小时候我们听老人戒说行旅的艰险绝不少于‘万恶的社会’的时候”,但一则有“那么股子冲动,年纪轻,总希望向远处跑”,一则“大势所趋,顺着潮流一带,就把我带过了千山万水”。这里提到“高邮人”去外地的两个原因具有普遍性,我们不妨就以此为入口,一窥1980年代和1990年代汪氏故里小说描写的“故乡人”结缘上海的各种具体方式。
就从好像与上海无关的《异秉》《受戒》说起吧。
《异秉》(1981)中受人欺凌的“保全堂”学徒“陈相公”比《孔乙己》中咸亨酒店学徒“我”处境更糟,但他也有小秘密,就是每天爬上保全堂屋顶翻晒药材,“登高四望”,“心旷神怡”,“其余的时候,就很刻板枯燥了”。陈相公“登高四望”,除了周围屋顶、远处田畴、街道和人家,还有他看不见却可能想到或听过的远方吧。比如《受戒》中《卖眼镜的宝应人》(1994)列述的高邮周围运河沿线,“南自仪征、仙女庙、邵伯、高邮,他的家乡宝应,淮安,北至清江浦。有时候也岔到兴化、泰州、东台”。汪氏其他故里小说还提到更远的徐州、扬州、镇江、南京、苏州、杭州、武汉、天津、北平,甚至南洋,美国。
“远方”闪亮处是上海。陈相公自然不能洞悉,上海在近代的崛起既给苏北带来现代生活气息,也直接导致整个扬州地区繁华不再。加上1910年、1920年、1930年三次水灾,1937年日军占据高邮,1947年苏北成为内战逐鹿之区,大量苏北难民(包括部分富庶移民)一路南迁,终目的地几乎都锁定上海。只有上海才能容纳庞大的“苏北人”族群。上海也赋予高邮人以备受歧视的新身份“苏北人”“江北人”,深刻影响他们的生活与命运。上海渗透、笼罩、深刻关联着包括高邮在内的整个苏北。
汪曾祺目睹过1930年高邮大水,平时水旱两灾不断,他也印象深刻,“我的童年的记忆里,抹不掉水灾、旱灾的怕人景象。在外多年,见到家乡人,首先问起的也是这方面的情况”①。1939年和1947年他在上海,又亲历了两次苏北难民和移民潮。汪家虽非高邮望族,但较为富庶,直系亲属较少移民上海,有也不属难民,因此汪氏“复出”之后大量故里小说主要背景是高邮而非上海,他也没有正面描写在上海的高邮人。但自从苏北人大量移民上海,许多高邮家庭都有人在上海,或往来上海与高邮之间。耳闻目睹,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汪曾祺记忆中应极分明,流露笔端,也很自然。汪氏故里小说主题之一就是描写在上海阴影下高邮古城社会凋敝、旧家没落与风俗改移。
《异秉》可说者,除了每日“登高四望”的陈相公,还有走南闯北、懂得极多的张汉轩(人称张汉)。正是他提出“异秉”之说,成为一篇之“文眼”。这两个思想或行动上的活跃分子是连接高邮和远方的桥梁。《受戒》(1980)提到上海,一笔带过,对整篇小说的成立却至关重要:原来高邮男子去外地做和尚,首先就“有去上海静安寺的”。多亏明子舅舅没把明子送去“上海静安寺”,否则这篇小说就无从写起了。但作者描写留在故乡当和尚的明子,逻辑上也就隐括了去“上海静安寺”的另一群明子的同类。①
陈相公,可谓“年纪轻,总希望向远处跑”;张汉轩和“明子”,当属“大势所趋,顺着潮流一带”,被“带过了千山万水”。他们都未曾去过上海,却有结缘上海的两种潜在可能,是高邮内部去向远方的种子,条件成熟,即可开花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