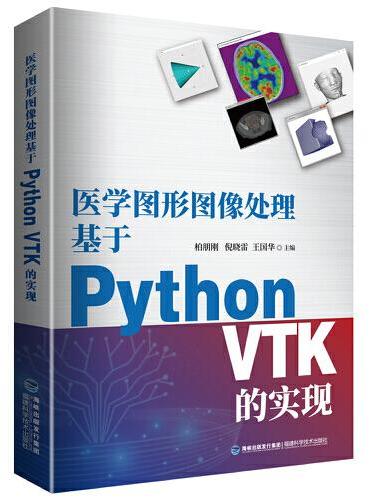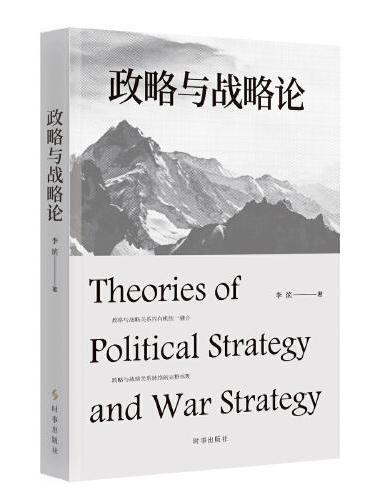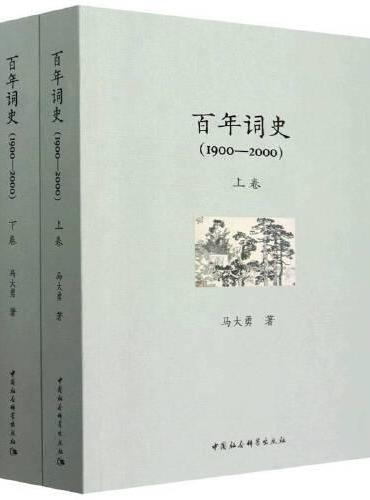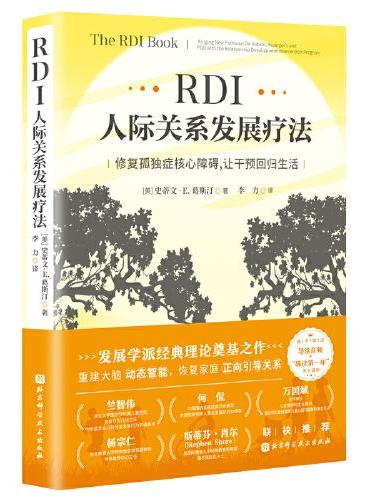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
》
售價:HK$
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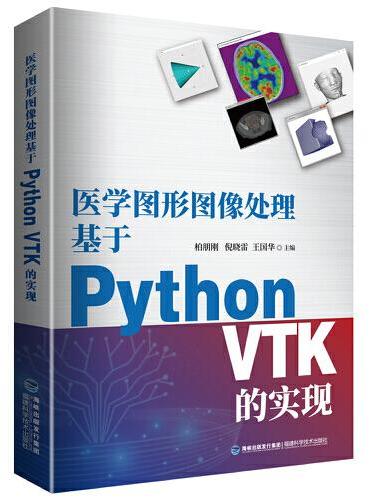
《
医学图形图像处理基于Python VTK的实现
》
售價:HK$
166.9

《
山家清供:小楷插图珍藏本 谦德国学文库系列
》
售價:HK$
1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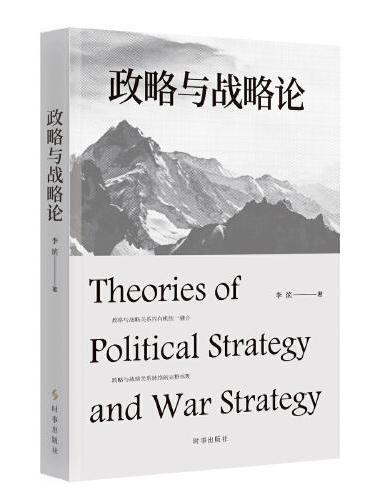
《
政略与战略论
》
售價:HK$
1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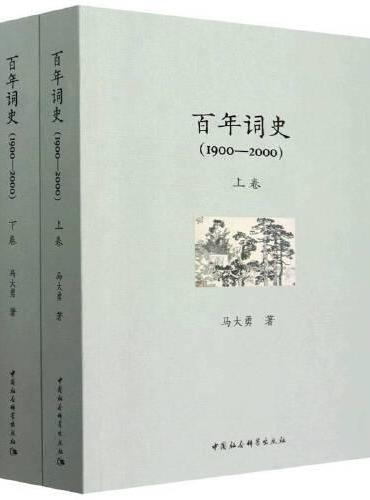
《
百年词史-(1900-2000(全二册))
》
售價:HK$
3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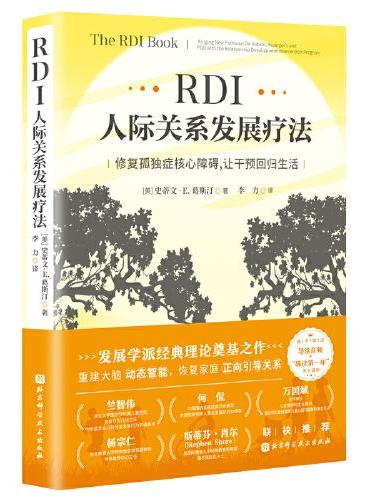
《
RDI人际关系发展疗法:修复孤独症核心障碍,让干预回归生活
》
售價:HK$
99.7

《
金融科技监管的目标、原则和实践:全球视野下加密货币的监管
》
售價:HK$
110.9

《
城市轨道交通绿色低碳规划设计研究——深圳地铁6号线工程创新与实践
》
售價:HK$
221.8
|
| 編輯推薦: |
|
本书创刊于1979 年,一年四辑,面向国内外鲁迅研究者,以“新发现、新观点、新方法”的编辑方针,侧重刊载以资料整理、梳理和考证为主的学术论文,兼顾理论研究型论文。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主要包括“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文物研究”“鲁迅作品研究”“鲁迅生平研究”“鲁迅同时代人研究”“史料·辩证”“读书杂谈”“纪念”“鲁海漫谈”等主题。在这些主题下,计有近30篇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国内外前沿的鲁迅研究状况。
|
| 關於作者: |
|
上海鲁迅纪念馆坐落于上海市虹口区,是1949年后个人物性纪念馆,也是1949年成立后个名人纪念馆,同时管理鲁迅墓,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
| 目錄:
|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文物研究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文物提要
重温《秘书处消息》期及其他 李浩
每当迁徙,大加擘画——鲁迅居上海时期的书橱 高方英
鲁迅作品研究
鲁迅小说中“我”的两种隐身术 郜元宝
从《题辞》至《墓碣文》的幽深之路 沈之韵
单四嫂子的迷信、守节及其他——关于《明天》 李恒顺
以序观文——《阿Q正传》序的副文本性解读 于翠梅
何为“大团圆”——《阿Q正传》结局再考 袁宇宁
鲁迅生平研究
鲁迅对未名社的影响 乐融
袁文薮其人其文——再议鲁迅筹办《新生》的班底 乔丽华
略论鲁迅对目连戏和京戏的两极态度 施晓燕
鲁迅对建崇寺造像碑的著录与研究 刘雁翔
鲁迅同时代人研究
章运水的悲苦人生及“后运水时代”其子孙的悲惨遭遇——为鲁迅《故乡》发表100周年而作 裘士雄
章太炎与徐梵澄在“孔学”上的隔代传承 贾泉林
史料·辨证
20世纪80年代鲁园中的一株小草:《鲁迅学刊》(上)——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鲁迅学刊》创刊40周年 李春林
电影《爱之牺牲》考:兼论鲁迅的《伤逝》——以电影放映广告为路径 石珠林
日记所见章太炎事迹钩述 陈宇
许杰集外文两篇及演讲稿《中国新文艺的道路》钩沉 刘锐 涂惠玲
纪念
一位值得纪念的鲁迅研究专家——追忆刘家鸣先生 张铁荣
散忆吴福辉先生:素昧平生但对我有知遇之恩 北塔
忆纪维周先生 吴作桥
读书杂谈
美术家眼中的鲁迅——读《上海鲁迅纪念馆藏美术品选》 林金壹
廖久明《〈藤野先生〉探疑》序 王锡荣
我的“犟”学姐姚锡佩——读《风定落花》随想 陈漱渝
光影烛照下的文学生活——读《参照,比照和映照——从文学到影视的转换研究》黄临池
鲁海漫谈
“我愿以高尚的党员品质悬为目标”——许广平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 北海
重读鲁迅的《文艺与革命》(1928)——以冬芬的“来信”与鲁迅的“回信”为引发 周晓平
“左联”成立大会的情景要有一幅画邵黎阳
简讯
“中国人物类博物馆70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海文
第四届鲁迅研究青年工作坊——暨第五届浙江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分论坛综述杨成前
编后
|
| 內容試閱:
|
编后
近年来,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馆藏文物研究逐渐深入,为充分发掘馆藏文物的文化内涵,使之更便利地为社会文化建设服务,上海鲁迅纪念馆以馆藏文物保管基础性工作为前提,探索编撰馆藏文物提要,本辑之《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文物提要》便是初步成果,如编者按所识,敬请专业人士提供建议。《秘书处消息》是“左联”时期一份幸存的内部刊物,由鲁迅保管,许广平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本辑所刊《重温〈秘书处消息〉期及其他》重新阅读了这份刊物,发现了之前未为人所重视和关注的问题,认为从当年“左联”工作部署来考察鲁迅的文艺活动,可以进一步阐释鲁迅与“左联”相关问题。本篇也是之前刊载的《〈前哨〉再识》的姐妹篇。鲁迅不是藏书家,但他的藏书不少,其中相当部分的藏书又跟随着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到广州后到达上海,为便于运输和保护藏书,鲁迅在书橱方面也动了不少心思,《每当迁徙,大加擘画——鲁迅居上海时期的书橱》一文向读者叙述了鲁迅的书橱。
《鲁迅小说中“我”的两种隐身术》一文直截了当地对鲁迅小说中的“我”展开探讨,不长的文章从“‘我’藏在第三人称叙述者背后”“第二人称叙述:‘我’的另一种隐身术”“鲁迅小说中的‘鲁迅’”三个方面展开讨论,言简意赅,直击要点,读来让人畅快:“研究鉴赏鲁迅小说,若仅仅抓住人物,不顾及‘我’,那就只能看到鲁迅小说的一半——甚至连这一半也无法看清”。《从〈题辞〉至〈墓碣文〉的幽深之路》认为:“《题辞》与《墓碣文》在可怖的梦境中以料峭的语言裹挟着鲁迅自我分裂、自我认知、自我解剖的过程,正是基于鲁迅黑暗与虚无矛盾思想的复杂性和独异性”。正如《单四嫂子的迷信、守节及其他——关于〈明天〉》题目所示,文章讨论了单四嫂子的迷信和守节问题,不过,文章更重要的是关于“主体性的遮蔽”方面的讨论:“鲁迅对单四嫂子的心理描写,看似超出了她的表现能力,然而那未尝不是单四嫂子内心的真实的一面”。关于《阿Q正传》的序文的解读是研究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以序观文——〈阿Q正传〉序的副文本性解读》别有独到之处。同样,大团圆结局也是如此:《何为“大团圆”——〈阿Q正传〉结局再考》中云:“在黑暗中清醒地死去,从轮回里微笑着再生,阿Q的‘大团圆’成为一出超脱单纯‘反讽’意味的真正的喜剧,是鲁迅亲自策划的一次启蒙实践”。
《鲁迅对未名社的影响》重估了两者之间的文化意义,认为:“丰富了中国编辑出版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中国的文学发展和转型作出可贵的贡献”。《袁文薮其人其文——再议鲁迅筹办〈新生〉的班底》是一篇难得的考据文,该文基于翔实的文献资料对于重新考察留日时期的鲁迅的思想和生活状况有着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作用。《略论鲁迅对目连戏和京戏的两极态度》从鲁迅的儿童时期的生活状态切入研究,是一篇具有民俗研究价值的文章。《鲁迅对建崇寺造像碑的著录与研究》作者认为“文学家的鲁迅过于有名,金石学家的鲁迅其成就往往被忽视。兹以鲁迅对建崇寺造像碑的著录与研究为例,作相关考述,展示其高超的学术水准”。
《章运水的悲苦人生及“后运水时代”其子孙的悲惨遭遇——为鲁迅〈故乡〉发表100周年而作》用翔实的资料和丰富的情感,对章运水及其后代的生存际遇进行了梳理和论述,是一篇难得的佳文:“‘后运水时代’其子女在新中国成立前,尝遍了人间各种苦难,这种似人非人的生活直到1949年5月解放,换了人间,才实现鲁迅当年所希望的他们‘应该有新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章太炎与徐梵澄在“孔学”上的隔代传承》通过对章、徐的“孔学”的探讨,认为:“鲁迅一面痛诋‘礼教吃人’的社会现实,一面自己却又恪守以‘孝’为根本的孔学道德,看似矛盾观点的背后亦是源于对儒学‘精神性’的把握。可以说,‘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这句话,即为章太炎、鲁迅、徐梵澄三人孔学传承之‘心法’。”
《鲁迅学刊》是改革开放后的一种重要的鲁迅研究刊物,承蒙当事人李春林先生赐稿,《20世纪80年代鲁园中的一株小草:〈鲁迅学刊〉(上)——纪念鲁迅先生诞辰40周年、《鲁迅学刊》创刊40周年》得以在本辑刊载。文章对《鲁迅学刊》的发生与发展进行了详尽的记述与梳理,让我们得以完整地了解当时历史的一面,对中国鲁迅研究的历程也有了更好的了解,文章将分两次刊发。《电影〈爱之牺牲〉考:兼论鲁迅的〈伤逝〉——以电影放映广告为路径》是一篇有价值的资料考证文章,尽管作者尽所能而未见电影《爱之牺牲》全片,却基于广泛的资料汇集,大致勾勒出这部电影与《伤逝》之间的关联,对于鲁迅的创作活动的再探索具有一定的揭示意义。《日记所见章太炎事迹钩述》《许杰集外文两篇及演讲稿〈中国新文艺的道路〉钩沉》在资料汇集与整理方面各有所长,对于相关研究皆有一定的补益。
刘家鸣、吴福辉、纪维周等三位先生在鲁迅研究方面各有不同的贡献,本辑分别刊载三文,以资纪念。
2020年在继《上海鲁迅纪念馆藏品选》出版后,《上海鲁迅纪念馆美术品选》也得以面世,该书是为上海鲁迅纪念馆馆藏文物文献研究项目的一种,具有鲜明的特色,《美术家眼中的鲁迅——读〈上海鲁迅纪念馆藏美术作品选〉》从美术家这个角度对该书进行介绍,可视作特别的介绍文。廖久明对鲁迅《藤野先生》的探究及其观点令人印象深刻,在读了王锡荣的文章后,很期待能目睹该书。陈漱渝记述姚锡佩的文章生动感人,值得再三品读。《参照,比照和映照——从文学到影视的转换研究》是陈力君的文集,《光影烛照下的文学生活——读〈参照,比照和映照——从文学到影视的转换研究〉》所云:“作者在书中的‘看’更像是一种学术的‘漫游’。用本雅明的话说,如果传统社会人们的观看模式依赖于‘静观’,那看似漫不经心但实则带有目的性的‘漫游’便是现代人更热衷的观看行为”是比较切中的。《“左联”成立大会的情景要有一幅画》是版画家邵黎阳对创作《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战士!》的回顾,文章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鲁迅倡导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在今天的承续及其展现。
今年5月21日—23日,由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联合举办的“中国人物类博物馆70年”学术研讨会在钱学森图书馆召开,近40位来自全国各大人物类博物馆的馆长及相关研究专家等出席研讨会。会议收到了具有相当价值的论文,但限于种种因素无法将之全部发表,在此仅录文章篇目和作者以为记录。
编者
2021年8月
鲁迅小说中“我”的两种隐身术
郜元宝
一、“我”藏在第三人称叙述者背后
人称之外,《呐喊》《彷徨》还有12篇采取第三人称叙事,即《呐喊》之《药》《明天》《风波》《端午节》《白光》,《彷徨》之《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弟兄》《离婚》。
除作者自我投射之外,一部小说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叙述主体。“第三人称叙事”并无“他(们)/她(她们)说”的叙述话语结构,只是人称叙事的变形。但如果作者不将自己作为叙述人的身份落实为“我”“我们”,假装超然于一切人事之外,作为无处不在的叙述人拥有上帝般的全知视角,那这种故意隐蔽“我”“我们”的人称叙述,至少在形式上就变成了匿名的第三人称叙事。
所以第三人称叙事,可以理解为特殊的人称叙事:人称叙述者故意隐藏起来,故意不挂出“我”“我们”之类的招牌,由此获得更大的自由:赋予通常总是不可靠的人称叙述者所没有的可靠叙述者的全知视角。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三人称叙述中,尽管叙述者不以“我”“我们”的身份口吻来讲述故事,但读者心目中仍然有个无处不在的代表作者“我”的匿名讲述者。
何况许多小说并不始终严格遵循第三人称叙事。在第三人称叙事框架中,叙述者偶尔也会以“我”“我们”的身份跳出来说话,只是不那么引人注目而已。比如坚持第三人称叙述的《明天》就忽然跳出一句“我早就说过:他是粗笨女人”——仅此一句而已。这或许是作者的某种疏忽,但也因此说明第三人称叙事不过是人称叙事的变形。
第三人称叙事,或者说被赋予全知视角、刻意隐藏“我”“我们”之类代词的人称叙事,因为叙述者不受拘束,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理论上就更加灵活多变,也更容易取信于读者,获得可靠叙述的权威性。即便明确宣告人称叙述的小说,也会在不知不觉间转变为第三人称叙述,如《阿Q正传》。
鲁迅小说区别于传统话本小说和近代通俗小说显著的一点,就是作者不再拘泥于千篇一律、固定不变的“说话人”身份,而通过人称叙述者“我”,在作品中实现了强烈的自我投射。写杂文的鲁迅不惮于挺身而出,“放笔直干”,写小说的鲁迅也偏爱带有浓郁主观性和抒情性色彩的人称叙述,即使第三人称匿名叙述,也感染了这种强烈的主观性,那藏在第三人称匿名叙述背后的叙述主体似乎随时都会跃然而出。
这是现代人“发现自我”的狂喜冲动在叙述艺术上必然的表现。鲁迅次读到《天演论》,对并未现身该书之中的作者赫胥黎就产生过强烈的惊奇与崇拜: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
“五四”时期的中国读者读鲁迅小说,不也像鲁迅读《天演论》一样,无论对采取人称还是采取第三人称的作者鲁迅都感到极大的新奇和激动吗?“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鲁迅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狂人’‘孔乙己’也出来了,单四嫂子、阿Q也出来了,闰土、祥林嫂也出来了!”
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杂文中,鲁迅都急切地宣示自我的存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这种冲动一度曾经被压抑,甚至“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因此一旦“开口”,就更容易“一发而不可收”。
但《呐喊》共收小说14篇,其中9篇采用人称叙述,而到了更加用心写小说的《彷徨》11篇,只有4篇是人称叙述。鲁迅在小说中以“我”的身份跳出来说话的冲动似乎有些减弱了,这大概就是鲁迅本人所谓“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吧?
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他不会甘心从小说中隐退。《彷徨》虽然更多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但“我”并未完全退出,而是以退为进——作者自己隐藏得更深,希望读者也能看得更深。在《呐喊》《彷徨》问世2年多之后,鲁迅曾在一次演说中,从作者介入文艺作品的深浅出发,区分新旧两种不同的文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现社会,也可以发现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取消人称而退隐为匿名的第三人称,“隐含作者”/“叙述主体”在客观上会冒险“退化”为传统话本小说或近代通俗小说毫无表现力的“说书人”“说话的”,从而放弃启蒙者“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职责与使命,因此如何以退为进,既采用匿名的第三人称叙事,又能投射叙述主体形象,并且毫不逊色于人称,这便是鲁迅在采用第三人称匿名叙述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必须接受的挑战。
人称叙述,好处是作者“也烧在这里面”,富于感染力,更容易打动读者。但需要防止像《一件小事》《兔和猫》那样过于直露。鲁迅小说的人称叙述有得有失,但总体上得大于失。
第三人称叙述,好处是以退为进。作者巧妙地隐藏起来,让人物和场面自动呈现,读者因此可以不受来自作者的“干扰”,更客观地打量人物世界。作者不再以“我”的口吻站出来说话,而是在不动声色的白描和叙述中精心做出一些暗示,给细心的读者以意外的发现。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经特别提到,“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其实这样的“曲笔”和暗示在鲁迅小说中十分普遍,尤其在第三人称的小说中,几乎就构成叙述的主要内容。
但倘若作者过于退隐,客观化叙述中的微言大义倘若过于暗晦,读者也会迷失,难以把握真实的命意。据冯雪峰回忆,鲁迅曾多次对他谈起,“他在文字上以后将尽可能避免用‘曲笔’”,鲁迅“常常痛惜他的小说和他的文章中的曲笔常被一般读者误解”,可见鲁迅本人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⑨。
鲁迅小说第三人称匿名叙述有得有失,总体上也是得大于失。
二、 第二人称叙述:“我”的另一种隐身术
向某一固定对象倾诉的诗歌(如《圣经·诗篇》向耶和华倾诉),或某些诗体与诗化散文与小说采用向第二人称“你”说话的形式,作品始终围绕“你”这个中心展开。具体在小说中,作为受话者的“你”可以是某个小说人物,可以是拟想中的读者,也可以是说话人自己(叙述者或叙述者兼人物)。只要作者愿意,他可以将任何一个人物设定为受话者(类似某个收信者)。“书信体小说”正是典型的第二人称叙述。小说中长短不一的书信也属此范畴,如《孤独者》中魏连殳给人称叙述者“我”的那封长信。
在采取第二人称叙述的小说中,除了被刻意突出的“你”,自然也还有向“你”诉说的“我”,以及在“我”向“你”诉说过程中必然涉及的“他”与“他们”。有些“书信体小说”开头结尾还有“收到”“发现”“公布”书信的人称叙述者“我”(如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或者把“我”隐蔽起来的第三人称叙述者。所谓“第二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一样,也可以视为人称叙事的一个变体。
有些的第二人称叙述,不仅刻意隐藏和第三人称叙述者,也不仅仅只是形式上有个隐藏的说话者向“你”说话,更要在说话过程中将主要叙述信息都指向“你”,从而达到迎面歌颂“你”、控告“你”、认识“你”、塑造“你”的目的。这种更的第二人称叙事可以法国新小说家布托的长篇小说《变》为代表。
在中外古今小说史上,“第二人称叙述”并不多见。鲁迅只是在《孤独者》中有局部的采用,本来可以忽略不计,但鲁迅小说某些地方还是可以看出近乎“第二人称叙述”的手法。
鲁迅小说都不曾特别指明是写给某个具体的受话者,而都是叙述者向“你”(拟想中的广大“读者”)在说话,故鲁迅小说的叙述者从来不曾明确称呼某个具体读者为其受话人“你”——《伤逝》也并非写给子君一个人。然而“你”的泛化并不减弱鲁迅小说强烈的读者意识。读者作为隐藏的“你”始终能感到隐含作者的真诚邀请——邀请并非单个的“你”而是所有的“你”加入小说整体的叙述结构。
《狂人日记》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人称叙述者“狂人”这些话并非说给“大哥”或任何一个小说人物,乃是说给狂人所悬想的有可能看到日记的每一位读者“你”。这个悬想中的读者“你”才是狂人说话(写日记)时的受话者。不仅如此,从节到后第十三节,狂人所说每一句话(包括他对“大哥”等小说人物所说的)不也都是向着隐含的读者“你”(或“你们”)诉说的吗?
这样的隐含读者“你”在鲁迅小说中无处不在。“你”所指向的是认真阅读其小说的每一个读者。读者如果不认真阅读,当然也可以认为这些隐含的“你”与他无关,然而对于严肃的读者而言,跳进鲁迅的小说,站在叙述者所悬想的“你”的地位,和各种形态的叙述者“我”展开对话,乃是一种积极的阅读艺术。鲁迅不仅在小说中塑造人物以及不同的叙述者,也始终召唤着“你”——愿意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其作品的读者。
一旦读者意识到,在作者悬想中始终有受话人“你”,读者就会站在“你”的位置,跟向“你”说话的或隐或显的“我”产生互动。
有“我”必有“你”,反之,有“你”亦必有“我”,尽管在许多场合,“你”和“我”都可能被作者刻意隐藏了。
三、 鲁迅小说中的“鲁迅”
不同身份的叙述者始终横亘于读者和人物(以及人物活动构成的小说世界)之间,不仅掌控着人物的一颦一笑,也左右着、控制着、影响着读者对小说人物和小说世界的阅读理解。
乍一看,无处不在的叙述者都被作者鲁迅所操控,都是鲁迅本人的传声筒。尤其人称叙述者“我”,不就是作者鲁迅本人吗?但事实并非如此,或并非全部如此。
鲁迅大部分小说发表之初,一般读者并不知道“鲁迅”(以及发表《阿Q正传》时署名“巴人”)乃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的笔名,许多人后来甚至只知笔名鲁迅而忽略了本名周树人,并且直接将鲁迅小说人称叙述者“我”等同于以笔名行世的作者鲁迅。
其实这都是想当然。《故乡》的“我”把“母亲”和“宏儿”搬家到“二千余里”之外“我在谋食的异地去”,小伙伴闰土先前称“我”为“迅哥儿”,隔壁杨二嫂至今还这个叫。《社戏》小伙伴也称“我”为“迅哥儿”。《鸭的喜剧》中“我”提到同住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和“仲密夫人”(仲密是周作人笔名)。在上述3篇小说中,鲁迅确实不想隐瞒自己的身份,甚至鲁迅自己也承认《在酒楼上》《孤独者》两篇都是“描写自己”⑩,但这也只不过显露了其身份与“行状”的某一角度、某一片段,并非“整个的进了小说”。
鲁迅小说人称叙述者“我”更多只是假托之名,是“我”亦非“我”。即使鲁迅明确招认“我”就是他本人,也只是他本人的某个部分而非全体,何况更多的小说并无任何明确招认。因此,不能说鲁迅小说中的“我”就是鲁迅本人,充其量只是鲁迅全人的某个部分在小说中的化妆演出。
但鲁迅小说中的“我”并不因此就减少了对读者的吸引力。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与真实生活中的作者鲁迅没有太多直接关系,反而获得了(或者说被作者赋予了)更多蕴含,对读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当“狂人”发出声呐喊,当“孔乙己”现身于“凉薄”的人群,当古怪的阿Q横空出世,当可怜的寡妇单四嫂子希望在梦中遇见刚死去的宝儿,当同样可怜的寡妇祥林嫂不知如何跟死去的亲人相见,后在“鲁镇”新年祝福大典中孤独地“老了”,当赵太爷、假洋鬼子、吕韦甫、魏连殳、高老夫子、鲁四老爷、四铭、涓生和子君们陆续登场,活跃于“未庄”“鲁镇”“咸亨酒店”或“首善之区”的某个地方时,就有不少读者注意到鲁迅小说富于主观性和抒情性,其引人入胜的原因固然来自众多形象鲜明、姿态各异、意蕴丰富的人物,但也来自既有相对统一的身份语调而又各不相同的“我”的形象。
不管普通读者如何想当然地以为这些“我”就是文本之外真实的作者,不管专业的研究者如何将这些“我”理解为文本之内不断被生成、被建构、被创造的“隐含作者”,不管这些“我”是还是第三人称叙述者是否是小说人物之一,“我”都是鲁迅小说世界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进入鲁迅小说,读者首先碰到的并非那些人物,而是把人物“介绍”给读者的作为中介人的叙述者“我”。即使在读者认识了那些人物之后,“我”也并未马上退场,乃是一直参与读者对小说人物从不熟悉到熟悉的全过程。甚至小说结束,人物退场,“我”还继续占据小说画面中心,继续跟读者交流。读者不能直接认识鲁迅小说的人物,总是先认识“我”,再跟在“我”后面进入小说世界,听“我”慢慢讲述这个世界各色人等的故事,琢磨“我”对人物以及人物的世界的某些暗示与评说。
总之阅读鲁迅小说,总是离不开小说中的“我”,总是笼罩在“我”的强大气场中。读者眼前始终晃动着“我”的面影,耳中始终听着“我”在说话,心中也始终思索着“我”是谁?“我”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
研究鉴赏鲁迅小说,若仅仅抓住人物,不顾及“我”,那就只能看到鲁迅小说的一半,——甚至连这一半也无法看清。
2021年4月21日
(复旦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