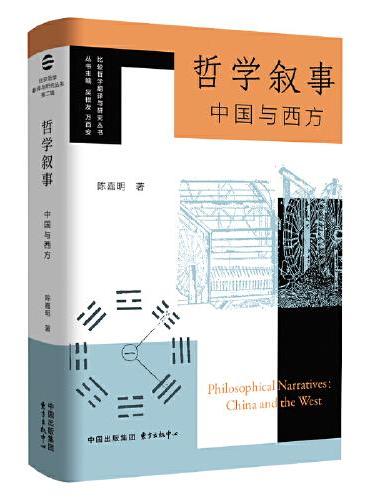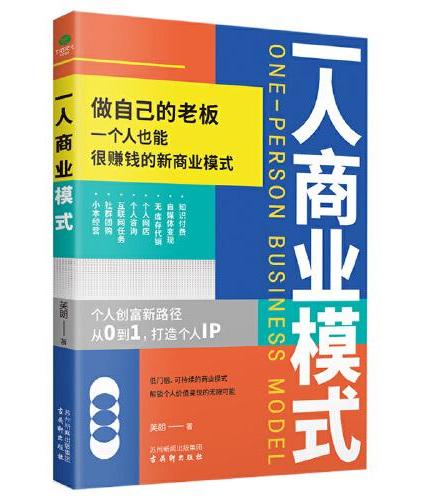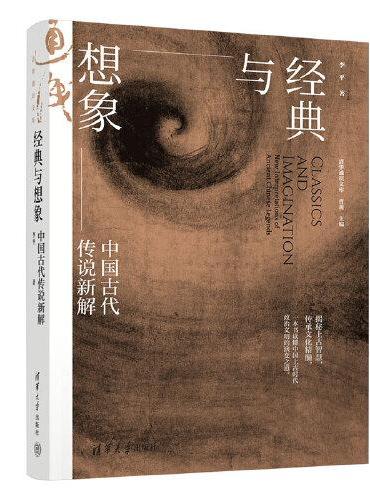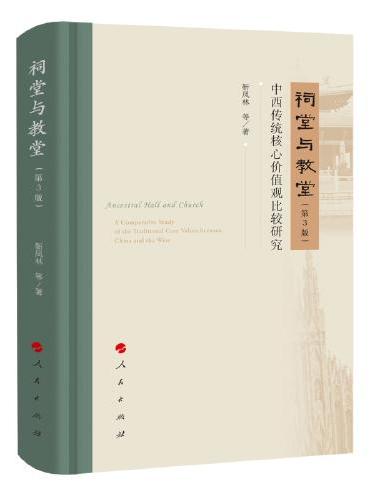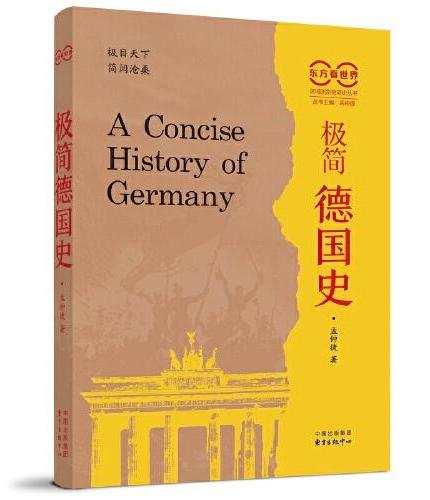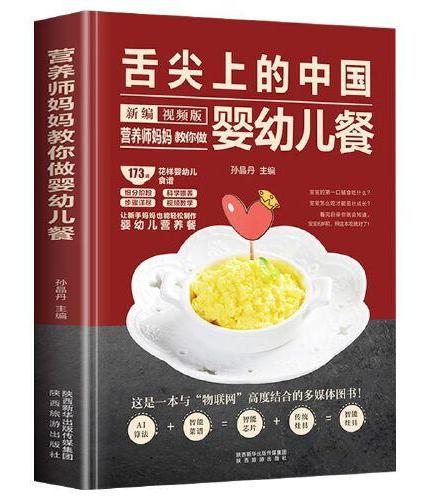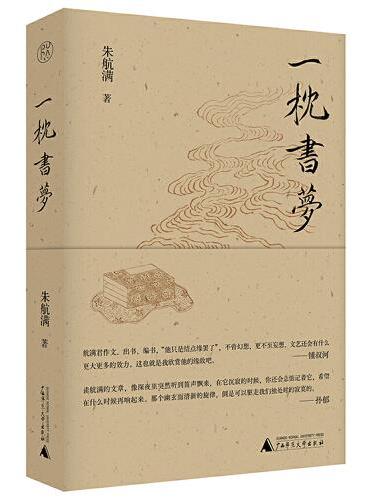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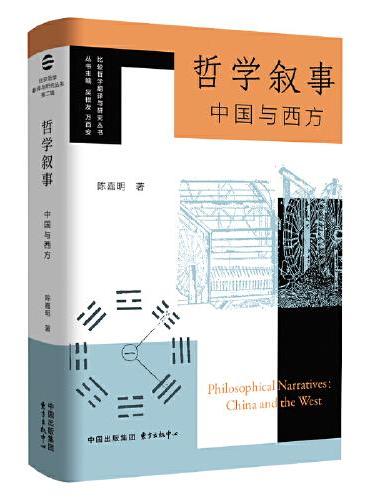
《
哲学叙事:中国与西方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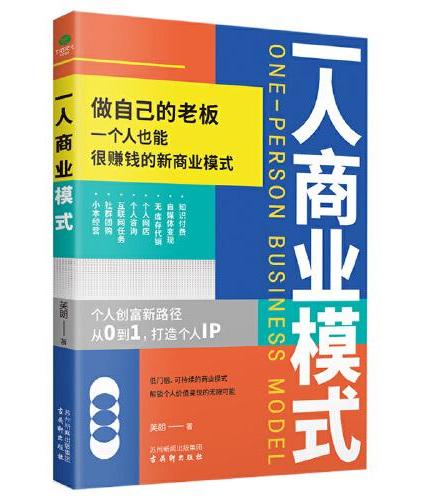
《
一人商业模式 创富新路径个人经济自由创业变现方法书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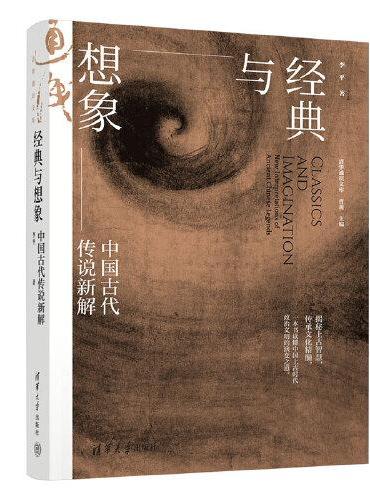
《
经典与想象:中国古代传说新解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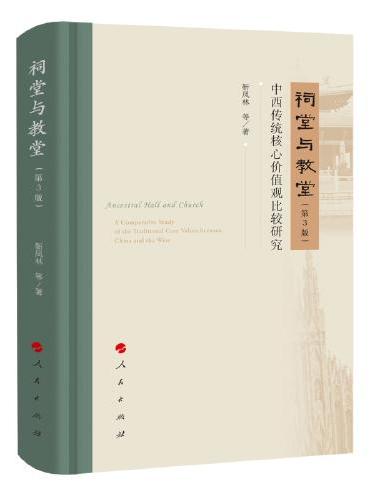
《
祠堂与教堂:中西传统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第3版)
》
售價:HK$
1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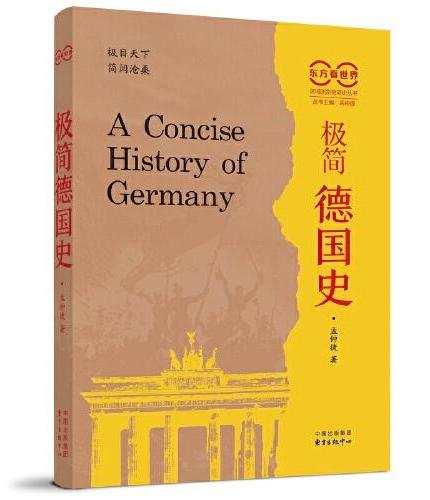
《
极简德国东方看世界·极简德国史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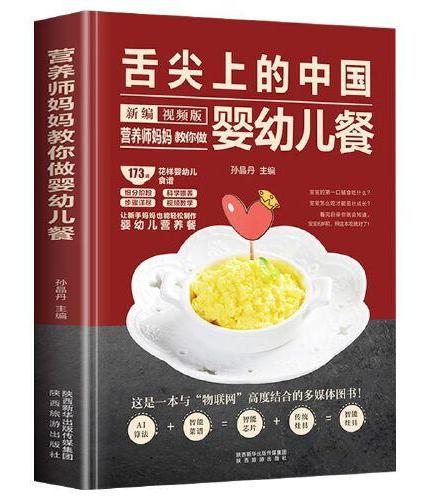
《
舌尖上的中国新编视频版营养师妈妈教你做婴幼儿餐
》
售價:HK$
63.8

《
Scratch创意编程进阶:多学科融合编程100例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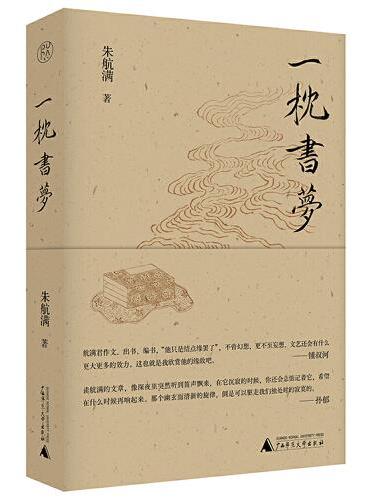
《
纯粹·一枕书梦
》
售價:HK$
79.2
|
| 編輯推薦: |
|
《刀锋》出版于1944年,是“故事圣手”毛姆漫长的创作生涯中的集大成之作、晚年的之作,毛姆也将《刀锋》视为自己的“后一部长篇小说”。《刀锋》与《面纱》《人生的枷锁》并称“毛姆解析人性三大作品”。《刀锋》叙事技巧高超,情节跌宕起伏,故事环环相扣,带有毛姆作品中特有的嘲讽腔调和怜悯意味,探索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文学青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刀锋》讲述了美国青年拉里探求人生意义的历程,拉里的故事浸润了毛姆对人生的思考——金钱不是人生成败与否的衡量标准,物质的满足是暂时和肤浅的,只有在自我完善的精神追求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拉里独自探索,追求精神世界的自我完善,后返回现实生活,“抱无我无求之态度、走尽善尽美之路”的生活态度仿佛浑浊世界的一股清流,鼓舞了许多内心荒芜的年轻人摆脱浮躁与迷茫,找寻灵魂的栖息之所。在这部小说中,每个人都在表达着对人生的理解。艾略特认为是名望声誉和社会地位,伊莎贝尔认为是丰厚的物质享受,格雷则认为是发展家族生意。人生的意义何在?毛姆没有给出答案,或许,这是每个人用一辈子去思考、去实践的问题。
|
| 內容簡介: |
长篇小说《刀锋》出版于1944年,美国青年拉里曾参加一战,目睹了战争的无情和残酷, 因此对人生心存迷惘。战争结束后,拉里渴望寻求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他与未婚妻解除婚约,在巴黎游荡,并从巴黎出发遍游全世界。后,他在印度宗教的神秘中顿悟,对人生有大彻大悟之感,后返回美国,过上了“大隐隐于市”的生活。
毛姆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拉里探求人生意义的历程,揭示了精神追求与实利主义之间的矛盾。他通过拉里的故事表达着其哲学思考——物质的满足是暂时和肤浅的,只有在自我完善的精神追求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
|
| 關於作者: |
毛姆(1874—1965),英国著名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20世纪上半叶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毛姆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剖析人心,文笔质朴,结构严谨,人物鲜明,故事叙述引人入胜,是“二十世纪用英语写作的为流行的作家之一”。
他创作力旺盛,尤以《人生的枷锁》(1915)、《月亮和六便士》(1919)、《寻欢作乐》(1930)、《刀锋》(1944)等为脍炙人口,在各个阶层都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
|
| 內容試閱:
|
一
我下笔写小说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疑虑。我之所以称它为小说,只是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叫它什么。我有微不足道的故事要讲,我既没有死亡的收场也没有婚姻的结尾。死亡是一切的终结,也是一个故事的总定论。当然婚姻作为结局也很合适,那些见过世面的人用不着去嘲笑世俗认为的快乐大结局。百姓有一种本能,总认为该交代的都说了这才合乎情理。无论男女,在经历怎样的悲欢离合之后,终走到一起时,他们就已经履行了传宗接代的使命,兴趣也自然地移到未来下一代人的身上。可我使读者如堕云里雾里。这本书回顾了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我和他关系密切,不过要间隔很长一段时间才见一次面,所以几乎不知道这中间他发生了什么。我想使用杜撰的手法填补缺漏,这完全行得通,还可以使故事情节更连贯;但我不希望这样做。我只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
许多年前,我写了一本小说,名叫《月亮和六便士》。在那本书里,我写的是一位著名画家保罗·高更;他是法国的艺术家,关于他的事,我知之甚少,但我使用小说家的特权,凭借得到的些许提示,炮制了若干情节来述说我创造出来的人物。在这本书里,我打算不再这样做了。我在书中没有一点杜撰。为了避免还活着的人尴尬,我把书中角色的名字都更换了,并努力用别的办法使人认不出来他们是谁。我要写的这个人没有名气。也许他永远不会出名,也许他一生终结也不会在这个世上留下什么,甚至不及一枚石子投入水中留下的涟漪。至于我的书,如果有人读,那就是它固有的兴趣所在。不过,或许他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和他特殊的过人之处及受人的爱戴在同类中的影响会与日俱增,这样或许在他死后很长时间人们才会认识到在我们的年代曾有一位非凡的人物。那时你就会清楚我在这本书里写的是谁了,至少那些想了解一点他早期生活的人会在书里看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本书虽然涉猎有限,但对于写传记的朋友来说不失一部可用来征引的书。
我不敢说我记下来的谈话都是逐字逐句一字不差的。在这类或其他场合,我不能记下谈话的全部内容,但与我有关的事却记得很清楚,虽然这些谈话出自我的笔,但我认为内容忠实地呈现了他们的谈话。我说过,我一点没有杜撰;现在想要改口。如希罗多德以来的历史学家们,我已经擅自把我没有亲自听到、也不可能听到的事情放在了我故事人物的口中。我这样做的理由和历史学家一样,是增添场景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如果只有叙述没有对话就会显得没有生气。我想要有人读我的书,所以我觉得为了这个做什么都说得过去。聪明的读者自然会明白我在什么地方使用了增添手法,他完全可以自由地摒弃它。
使我对写这部小说有忧虑的另一个理由是书中要描述的主要人物都是美国人。了解人是件很难的事,我觉得一个人除了本国人以外说他真正地了解了谁,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男人女人不仅仅是他们自身因素决定的;还有他们的出生地、学会走路的农场或城市的公寓、儿时玩的游戏、不经意间听到的愚蠢迷信、吃的食物、去的学校、从事的体育、朗读的诗句和信奉的上帝。所有这一切造就了现在的他们,而这些事情绝非道听途说可为,你只有和他们共同生活才能知晓。你只有是他们才能知晓他们。除了观察之外,你不可能了解你陌生的民族的人,所以把他们真切地呈现在书中不是容易的事。就连亨利·詹姆斯那样细致的观察家,在英国住了四十年,也没有创造出一位地道英国味的英国人物来。至于我,除几部短篇小说外,从未打算去写本国以外的人。即便在短篇小说中斗胆染笔,也是因为在这些书中你可以更为粗略地交代人物,让读者大概地了解,让他们填补细节。人们或许要问,既然你把保罗·高更编成了英国人,为什么不能把这本书里的人如法炮制呢?答复很简单:我不能。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是他们自己了。我不要把他们装扮成美国人眼里的美国人,他们是英国人眼里的美国人。我不想仿效他们说话的特点。英国作家试图做到这一点闹出的乱子如同美国作家模仿英格兰人说英语也是弄得一团糟。俚语是大陷阱。亨利·詹姆斯在他的英语小说中经常用,但从来都不像英国人用的那样,所以不但没有达到他想要的地道效果,还常常使英国读者感到有一种颠簸的不舒服。
二
一九一九年,我到远东的途中恰好路过芝加哥;我在那里待了两三个星期,理由与这本书情节毫无关联。之前不久,我成功地出版了一本小说,当时也算是成了新闻人物,所以一到芝加哥,就有记者来访。第二天早晨,我的电话响了,我接了。
“我是艾略特·坦普尔顿。”
“艾略特?我还以为你在巴黎呢。”
“不,我在和姐姐聊天,我要你今天过来与我们一起吃午饭。”
“那好。”
他说了时间,也告诉了地址。
我认识艾略特·坦普尔顿有十五年。现在他快六十了,高高的个头,眉清目秀,一表人才。满头乌黑的鬈发,但其中冒出了一些花白的银发,明显衬托了他的仪表。他总是衣冠楚楚;一般用品在夏尔凡商店购买,但西装、皮鞋和帽子要到伦敦去购买。他在巴黎有一所公寓,坐落在圣纪尧姆时尚街左岸。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是掮客,那是对他的非议,他愤恨至极。他有品位和学识,也不否认以往做过的事情。他初落脚巴黎时,曾经给那些想买画的有钱收藏家出过点子;而且通过社会关系打听到破落的贵族,不论法国人还是英国人,要卖掉一幅精品画,正好他还知道美国博物馆的理事们正在寻找某类大师时,他很乐于把两者联系起来。在法国,有许多年久的家族,在英国也有一些。他们的境遇迫使他们不得不把镶嵌布尔名字的橱柜或者齐彭代尔亲手制造的书桌悄悄地卖掉,所以他们愿意认识一位有文化素养和懂规则的人,谨慎地安排此事。人们自然会想艾略特在这些交易中得到好处,但人们都很有教养地谁也不提这事。不厚道的人硬说他公寓里的东西都是要卖的,还说他用佳酿宴请美国阔佬一顿美餐,他值钱的那些画作中的一两幅就不见了,要不然就是一个镶嵌精美的梳妆台换成了一个上漆的。有人问他怎么那件东西不见了时,他振振有词地说那件东西他没看上眼,换了一件品质更高的。接着又说总看同样的东西腻味了。
他张口说了句法语,“我们美国人喜欢变化。这既是我们的弱点,有时是我们的长处。”一些在巴黎的美国太太声称了解他的底细,说他的家境很穷,他能这样地起居生活只是因为他非常的精明。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但他的公爵房东着实让他支付了一笔房租,而且公寓里的摆设都很名贵。墙上挂有华多、弗拉戈纳尔、克洛德·洛兰等法国大师的画作;镶木地板上铺的是萨伏纳里和奥比松的地毯,彰显美感;客厅里摆了一套路易十五时代的家具,雕琢精美高雅,如他所说,完全有可能是蓬帕杜夫人的闺中物。总之,他能过着他认为的绅士派头的生活,而不用设法去挣钱,至于他过去怎么做才能达到这样,明智的话好别提,除非你要和他断交。由于在物质上不需要费心,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一生的爱好—社交中去。他与英国和法国那些一贫如洗的艺术大家们的商业关系使他站稳了脚跟,有了立足之地。不再是个刚到欧洲拿着介绍信去见要人的毛头小子。他的老家在弗吉尼亚,从他母亲的血缘可以追溯到一位在《独立宣言》上签过名的人,他的这一背景使他得以拿着信件见到那些有头有脸的美国太太们。他英俊、聪明、善舞、枪法好,还是个不错的网球运动员。他是任何聚会里少不了的人物。他慷慨大方,手捧鲜花和成盒昂贵的巧克力送人,虽然次数不多,但每当这样做时,总是别出心裁令人愉悦。那些被带到苏活区波希米亚人的餐馆或拉丁区酒吧的富婆们开怀大笑。他时刻准备替人效力,你要请他为你做点什么,不管多无聊,没有不甘心情愿的时候。他费尽心思地去取悦上了年龄的老妇人,所以没多久他就成了许多显赫人家的座上宾,特别讨人喜欢;他从不介意被人找去顶包,甚至你可以让他坐在一位非常烦人的老太太身旁,一定替你把她照料得高高兴兴,流连忘返。
两年多以后,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伦敦,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能够认识的人他都认识了。他常住巴黎,而伦敦,则在每年的旅游季节的尾端前往,再有就是在初秋时节光临一圈乡间别墅。早把他引入社交圈里的那些太太们惊奇地发现他的熟人圈竟发展得有那么广。她们的感情是喜忧参半。一方面,令她们高兴的是她们抬爱的年轻人居然取得了偌大的成功;另一方面,叫她们感到有点懊恼的是他竟然能和那些一直和她们保持着非常拘谨关系的人处得很亲密。尽管他对她们依旧彬彬有礼愿意效劳,可她们还是心神不安,总觉得他把她们当作垫脚石爬上社交的高层。她们担心他是势利眼。是的,猜着了,他是势利眼。他是一个非常势利的人,是个不知廉耻的势利眼。为了受邀置身于他想去的晚会或攀上某位大名鼎鼎而脾气暴躁的老妇,他可以忍受侮辱,不怕碰钉子,粗言秽语全吃,可谓是不屈不挠。他一旦盯上自己的猎物,就会像植物学家那样执着,不怕洪水、地震、患病发烧和怀有敌意的当地人所构成的危险,为的是找到独特稀世的一种兰花。一九一四年的战争给了他后的机会:战争爆发,他就参加了一个救护队,先在佛兰德,后在阿尔艮战区服役;一年后回来,胸前佩戴一枚红勋章,并在巴黎的红十字会得到了一个职位。那时候,他经济状况很宽裕,对于需要人赞助的善举,他都慷慨解囊。他时刻准备着用其高雅的品位和组织才能去协办任何一场广泛宣传的慈善大会。他是巴黎两家贵俱乐部的会员。他是法兰西耀眼的太太们脱口而出的“那个好艾略特”。他终于发迹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