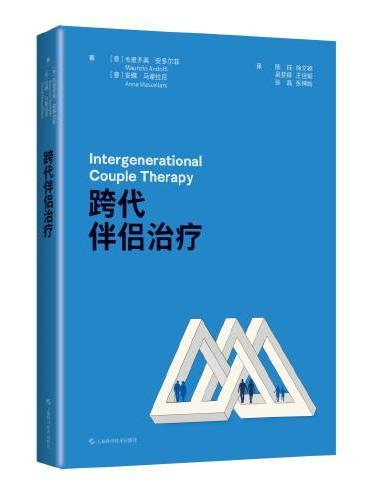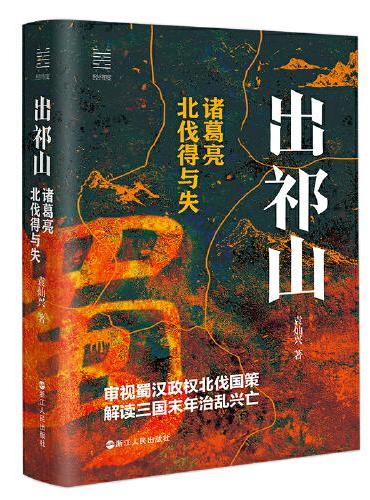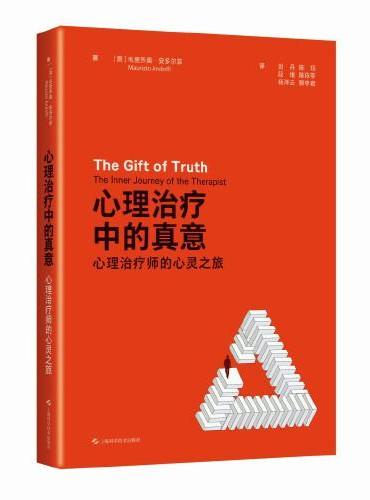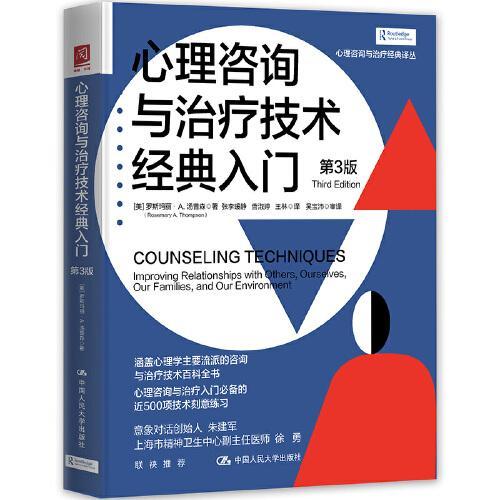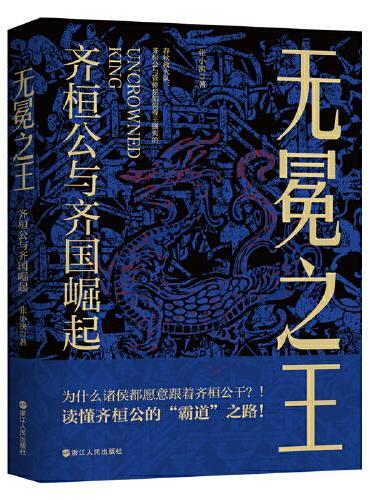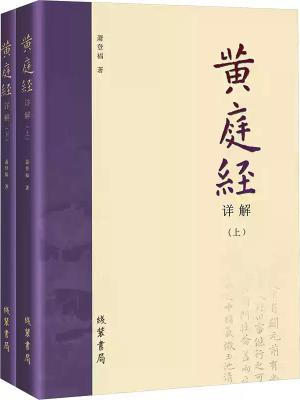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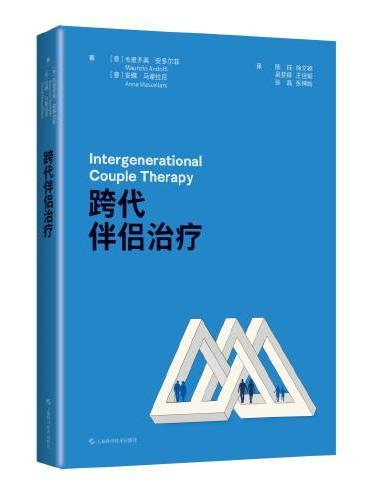
《
跨代伴侣治疗
》
售價:HK$
96.8

《
精华类化妆品配方与制备手册
》
售價:HK$
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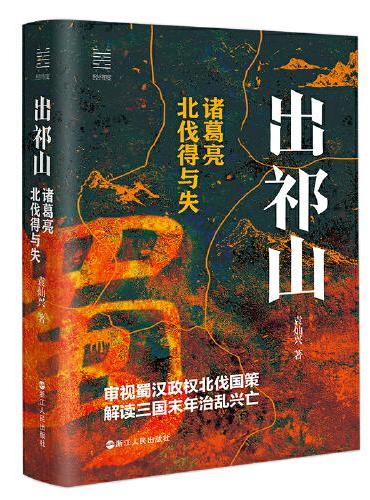
《
经纬度丛书:出祁山:诸葛亮北伐得与失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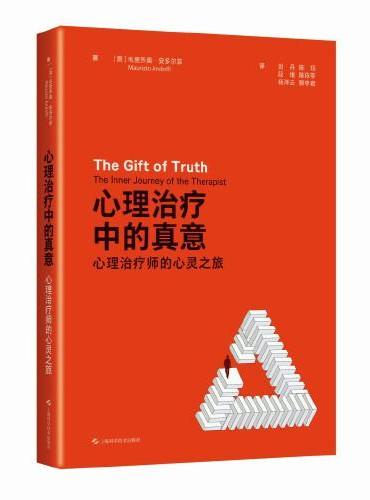
《
心理治疗中的真意:心理治疗师的心灵之旅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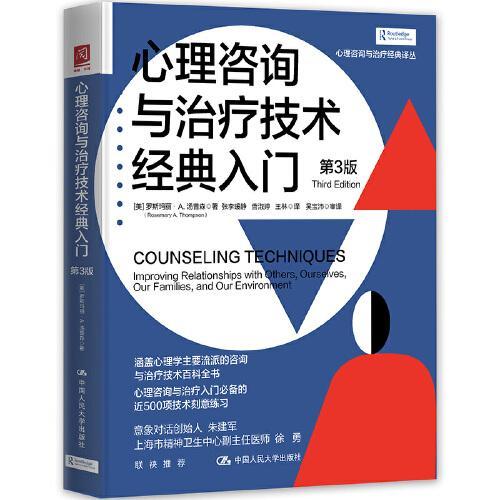
《
心理咨询与治疗技术经典入门(第3版)
》
售價:HK$
14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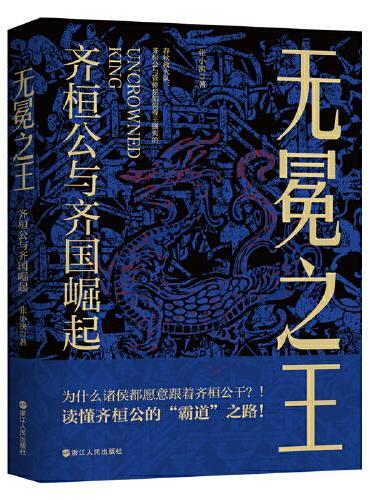
《
无冕之王:齐桓公与齐国崛起
》
售價:HK$
63.8

《
中国涉外法治蓝皮书(2024)
》
售價:HK$
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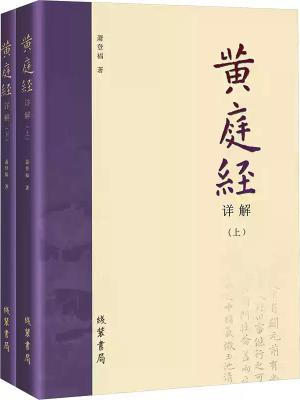
《
黄庭经详解(全2册)
》
售價:HK$
141.6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冉正万的中短篇小说集,共收录《唤醒》《一只阔嘴鸟》《诗人与香菇》《高脚女人》《十字弩》《慢生活》六篇作品。从“自我坚守”的主旨出发,结撰了六个不同的个人世界,背景跨越历史和未来,探索个人对于信念的坚守、良知的坚守、美好人性的坚守……以细腻温和兼具空灵想象力的叙述,直面生活现实,着力表现人生百态、世间悲喜的“原生态”,传达在混沌的世界里,每个个体自身既是潜伏者也是掩护者,保持清醒、有所坚守才是根本之道的理念,让大众在他人的故事中反刍自己的生存际遇。
|
| 關於作者: |
|
冉正万,1967年生,贵州遵义人,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文学黔军”的重要力量。获贵州省首届政府文艺奖、花城文学奖新锐作家奖,短篇小说《树上的眼睛》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其作品多取材于贵州本土民间文化,野性、神秘、传奇、质朴。代表作有《苍老的指甲和宵遁的猫》《银鱼来》《洗骨记》《纸房》等。
|
| 目錄:
|
目 录
唤 醒 1
一只阔嘴鸟 57
诗人与香菇 77
高脚女人 131
十字弩 151
慢生活 205
|
| 內容試閱:
|
不敢马虎(代序)
不敢马虎,是我写作的态度。
我的写作来源于我对故乡的眷念和鄙视。即使梦见皇帝登基,也是在我老家的土地上举行,而不是在皇帝的都城。当然,我从没梦见过皇帝,也没梦见过皇帝登基。
那是一片忧郁的土地,一种与生俱来的情绪暗藏在每个故乡人的心头。他们很少高声喧哗,很少嬉闹,很少唱歌,这是过于理性、缺乏活力的乡村。我鄙视故乡的落后与孤独,我眷念她的宁静和与世无争。你留在这里,你的灵魂要去哪里随你的便;你把灵魂留在这里,你的身体要去哪里随你的便。这是我故乡对每个出生在那里的人的忠告。
他们中有文盲,也有多少认识几个字的人,但很少读书,对我的写作从不关心,也没有必要关心。我是因为感激他们才写作,感激他们的纯朴、低调、聪明、虚伪、自私、傻头傻脑、自以为是,并因此吃亏上当。
这真是我写作的根源吗?不是,我是因为自视过高,因为心虚才写作。他们怎么样,其实我并不清楚,就像有时候我不清楚自己的想法一样。
几十年来,我努力写作,讨好卖乖,努力把自己放进现代社会,接受嘲笑和屈辱,同时去埋怨这样埋怨那样。回头一想,如果加入家乡的文盲队伍,受到的打击将会更加严重。于是继续努力。
我是为寻找自己而写作:我为什么是我,而我就是我。
这诡异的命题才是我写作的根源。别样的思维让我倍感沉重,有时忍不住耍耍赖皮,玩下小聪明,以为如此可以从自己的困境中解脱。但得不偿失,自己依然在困境中。
我老实下来,安静下来,继续追问:我为什么是我,而我就是我。读着《喧哗与骚动》,我特别理解昆汀、凯蒂、杰生和班吉明。但有时也想,去你的《喧哗与骚动》,叫昆汀和凯蒂见鬼去吧,伟大的作品不可能只有这一部。
毛姆说契诃夫的为人好像性情开朗和讲求实际,但作为一个作家却是抑郁和消沉的。我觉得这仿佛也是在说我,一条从冉的泉眼里流出来的、叫正万的河流。
很多人以为我一直在写我的故乡,其实不是。如果你读过我所有作品的话,你会发现,我是把整个人类社会当成我的故乡,而不是某块邮票那么大的土地。
我在黔西南看到黄金开采的盛况,于是把老家的人放进一片矿区,然后演绎他们的悲欢离合。这是我写的部长篇小说《纸房》,至今已逾十年。
在遵义毛石乡,我看见小孩装在玻璃瓶里的透明鱼,这鱼是从溶洞里流出来的。溶洞的水量非常大,雾气蒸腾,天气越热,水雾越浓。我老家一个嘴巴似的岩洞,让人充满遐想。我把这些要素放在一起,经过四年马拉松似的胡思乱想,写出了长篇小说《银鱼来》。
十多年前,我在黔东南听说过一个小故事。黔东南是贵州民风纯朴的地方,土改时期,当地人不明白什么是地主,什么是贫下中农。他们一直自给自足,都有土地,贫富差距并不大。但土改工作队不允许,要求他们必须像别处一样,也要有地主,也要有贫农。当地人不知道何为地主,以为是个社会职务,通过推选,村里一个为人好、大家都尊重的人当选。这人谦虚一番,也就答应了。几年后,他才知道地主不好当,但已经没办法了,一当就是三十年。一直觉得这个故事有意思,但我知道,仅仅靠这一个故事,写个短篇都很难。几年后,我在凤冈县采风,到一个叫梯子岩的地方,悬崖峭壁之上有个村庄,村里有块石碑,说这些人是明王朝一位带刀侍卫的后人。他被人追杀,躲到这个四面环山的地方。现在修了一条公路上去,邀我采风的人想要我们对悬崖上这条公路发出感叹。我觉得凡是人力能做到的事情,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公路修通后,有人在半山一个溶洞里养娃娃鱼。婴儿期的娃娃鱼特别怕吵闹,要在水无比干净,没有其他动物(特别是人)气息的地方才能生长发育。长大后对环境要求却又极其简单,比其他任何一种鱼都好养。村民用木盆、水缸都能养,可以养在床前,养在厨房。当时觉得挺有意思,想写一部关于养殖与商战的小说。写了几千字,发现这根本不是我应该触碰的东西,明白后立即删掉。两年后,把选地主和悬崖上的村庄结合在一起,写了长篇小说《天眼》。写完章,我就知道这比写养娃娃鱼容易。
迄今为止,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小说是没有人提及的一部小长篇。有一次乘车经过正在修建的环城公路,看见有人提着一个人形何首乌叫卖,宣称这是施工员刚刚挖出来的,长成人样,肯定有益寿延年的功效。我不禁大为惊奇。但车上有好事者悄悄告诉我,这是人工培植的,并且是从别处拿来的,和修路的工人没有关系。没想到骗子这么厉害,为了发财,竟想出这么绝妙的办法。经过五年的构思和一支秃笔的经营,我写了长篇小说《什么是你的》,把人性的贪婪和聪明写得风生水起。这部长篇虽然发表了,我估计读者不会超过十个人,这么多年,我只听到三个人向我提起过。
原本打算写三部,把已经发表的这部取名《什么是你的·人书》,再写《什么是你的·兽书》和《什么是你的·神书》,这种写法没人看好,写作的勇气大受打击。
写作的意义何在,其实很少有人问我。倒是自己从没停止过追问,尤其是长篇小说写作。这是我必须思考的基本的问题。不过从没找到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随着思考的深入,似乎越来越接近写作的终目标。但同时也清楚,你只能努力接近这个目标,不可能真正抵达,这也许正是写作的魅力和动力。
“盖闻二仪有像,显覆载以含生;四时无形,潜寒暑以化物。”这是《圣教序》里面的句子:听说天地有形状,所以显露在外,覆盖并且承载着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因为四季没有形状,所以深藏着严寒酷热来化育万物。文学不可与天地四时相提并论,但其运行规律是可以类比的。沃尔夫在他的处女作《天使,望故乡》里说,现世每一分钟都是四万年历史的结晶。日复一日,人们苍蝇般地飞向死亡,寻找归宿,其间的每一片刻都是窥视整个历史的一扇窗户。学者孔飞力则指出: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都存在于我们周围。每次读到这些句子,我都会放下书本沉思。如何看清此在,又如何向后人标记出管线走向,似乎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小说不是统计学,不讲任何科学依据,它只能靠隐喻和暗示把一个观察者的思想储存在字里行间。
我们都是未来的祖先,未来的读者在等着我们。我们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不可能一死了之。那么,谨慎写作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此时写下的句子,有可能成为善知识,也有可能成为恶知识。麻烦的是,善恶不能靠此时此地来判断,而是要通过从此以后永远的检阅。
我懂卡夫卡为什么要在临终时叮嘱布罗德烧掉他所有手稿。他不愿自己的文字在世间生根发芽,因为他无法确定这些文字的善恶。以前,有自以为是的评论者说:作为一个在文学上失意的人,烧掉手稿完全合情合理。这是多么简单和粗暴的结论。希望死后烧掉手稿的作家远远不止卡夫卡一人。有谁敢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的文字必须传世并且是可供后人借鉴的善道?
真正的写作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个体的体验虽然丰富,但不敢说这就是直义和见解。写作不是大彻大悟者所为,破除迷妄者不需要留文字,因为文字的局限已经不能准确传达其真味。所以写作是小思小悟,并且是容易兴奋容易激动藏不住知见的人,恨不得立即把自己的知见公之于世。如萨拉马戈所说,我们都是充满欲望的可怜巴巴的魔鬼。对我而言,恰似我小说中所写的山魈。
我一直在写,不过是希望广种薄收,让后人有所认同,有所欣悦。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生根,能够给人一点点希望,不要因为世事的无常就茫然无计。事实上,这也是托词,还活着,就得有所作为。不可马虎,也不敢马虎。
唤醒
(节选)
点水雀在飞,蚱蜢在跳,燕子在穿梭,一切都生机勃勃,但一切都将过去。秋天已经到下半场,远山越来越远,溪水越来越清凉。
明月把野棉球铺在晒席上,让太阳暴晒。这张晒席与其他晒席不同,从没晒过粮食。晒粮食的晒席用慈竹编织,八尺宽一丈长,卷起来像炮筒,粗糙的篾片常分裂出细篾丝,折断后极其锋利,扎进肉里又痛又痒却又看不见,让人恨不得把手剁掉。明月的晒席小得多软得多,用芦苇的青篾蒸煮后编织,可以折叠。这是大户人家给幼儿当席子用的,光洁玉滑,不但清爽,还能兜住尿,不会弄脏席子下面的被褥。明月的东西不多,但都很精致。野棉球暴晒三天后炸裂翻转,像一个个小棉帽。摘掉干缩的黑色种子,把储藏着太阳光的小棉帽装进枕套,枕在头下一年四季都会充满阳光。
野棉花在偏刀水常见也滥贱,人们除了觉得它没用和滥贱,不再有别的看法,任它在田坎上堡坎上小路旁水沟边坟堂里自生自灭。粉红色的花瓣有肉质感,丰满而圆润,女子们把花朵的模样绣在背带上、衣服上、鞋面上,喜庆而朴实。金色的花蕊被绣成鱼眼似的圆球,一百个圆球就是一百个金色的太阳。偏刀水只有明月用野棉花做枕芯,一到秋天就去采摘。棉球比蜘蛛肚子大,比麻雀蛋小,球上布满了斜向交叉的麻点。棉球炸裂后麻点变小,小得几乎看不见,棉花团看上去有点黑,正是因为这些小麻点的存在。仿佛这是它小小的自尊,提醒人们我不是别的,我是你们看不起的野棉花。
明月来偏刀水已有几十年,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世,没人知道她为什么来偏刀水,也没人见她去过别处。她不和当地人来往,她不讨厌他们,也不喜欢他们。她就像一棵栽错位置的树,周边没有一棵树和她相像。她更像飘浮在山顶上的白云,看上去很近,其实很远。
有人说她来自云南边陲深处的红河,一个当地人没去过的地方。说她是一个地主的小老婆,地主有十几亩水田,地主死后,她不愿改嫁又不敢在原来的地方生活,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偏刀水。偏刀水人自豪地感叹,幸好偏刀水人心地慈善,一点都没有为难她。他们推断她是地主小老婆的理由很充分,一是她长得漂亮,二是她不会干农活,三是她特别爱干净。
大家确切记得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明月有一支手枪。枪被派出所没收后她去要过几次,没有还给她。
她连钉锤都没有,居然有一支手枪。有一次她换枕芯,换完后坐在屋门口,旁若无人地把玩一支精致小巧的手枪,看她拿枪的样子就不像会打枪。她颠来倒去地看,像小女孩拿到一个从没玩过的复杂玩具,爱不释手又不知道怎么玩。这枪平时十有八九放在枕头下面,要不然怎么会在换枕芯的时候翻出来?她喜欢握住枪管,而不是枪柄,就像拿着一把锤子。她抚摸着每个部件,有时还把枪口朝向自己,想看看枪膛到底有多深,深处是否有什么机关。谁都看得出来,这支枪是她的心爱之物。
这个禁物在偏刀水镇并没引起轩然大波,只是进一步加深了大家的印象。一定是地主留给她的,让她用来防身,地主还没来得及教她怎么用就死了,她拿着它不中用又舍不得丢。
有个自以为是的小青年,想法与众不同,说这个女人有可能是特务,新政权稳住江山后,她和她的上级不是失去联系,就是不敢再联系。这话立即招来众人的鄙视:特务?偏刀水有什么呀,难道握锄头把修地球,追着牛屁股犁田打耙的全是大人物?难道打田栽秧需要派一个特务来破坏?嚼你的舌根,嚼烂了都没有人信。
这个头脑简单的年轻人不明白大家对明月的感情,虽然她和他们没有亲密的交往,但他们全都信赖她,就像信赖山坡上那棵孤零零的白杨,他们于她无求,只要她在那里就好,正是这样才不允许有衅隙,有裂痕。她与世无争,像白杨树一样端庄慈祥,他们享受着这份宁静、这份吉祥如意就心满意足。
没有人报告派出所,是派出所的民警无意中听说,听说后又不得不行使职责。当时枪支管理还没那么严,没有人觉得她保存这支枪有什么不妥。生产队队长柴启物带着民警来拿走时,她只弱弱地说了一句:这是我的。
连老实巴交的农民都看得出来,明月的枪不是用来朝某个地方射击的,是一个秘密纪念品。当民警问她,子弹呢,没有子弹吗?她弱弱地回答:这是我的。看热闹的人忍不住想提醒民警:不要再逼她喽,用不着嘛。他们的每个愿望都向着明月,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看着民警像取走她的魂一样,把手枪装进公文包,骑上自行车扬长而去。他们知道总有很多事情让人无可奈何,想到自己身为农民,更觉得万般无奈。
他们记得的第二件事情,是明月来到偏刀水时到处打听剿匪指挥部在哪里,似在寻找一个他们都不认识的人。
剿匪是在一九六一年春天进行的。土匪大鼻子老烟,新政权成立之前就是威震一方的悍匪。大鼻子老烟的人马不多,喜欢单打独斗,以寒婆岭为中心,活动在方圆百余公里的大山丛中。很少有人见到他的真身,只知道他是个大鼻子。他抢劫从不留活口,把被劫者全部杀光。实施抢劫后从不逗留,连夜奔逃几百里,在深山老林里一躲就是几个月。没有固定住处,对密林里几百个山洞就像对自己的耳朵嘴巴一样熟悉,不用照亮也能摸进去。大鼻子老烟是个神枪手,看见他的人和动物都得死,全都一枪爆头,不浪费一颗子弹。打死的动物皮剥下来,是他山洞行宫里的被褥。被他打死的人往往不明就里,到了阎王那里也结结巴巴交代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就来到了这里。大家对悍匪大鼻子老烟无不谈虎色变,为了不看见他,走路时尽量低头看路,不东张西望,以免引火烧身,以免长了眼睛的子弹朝自己飞来。大鼻子老烟被剿灭后,他的枪法被人津津乐道,讲述者情不自禁地竖起拇指食指,“叭”的一声,仿佛自己就是大鼻子老烟。除了枪法,大鼻子老烟还会一种特别的奔跑步法,叫鬼步,一步滑出去足有四五米远,相当于腿长的人走七八步。这或许仅仅是传说,但他确实做到了来无影去无踪。有人天真地向往:用这种步法去参加体育比赛,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一九五三年,大鼻子老烟抢过一辆运送救灾物资的汽车。救灾物资有棉絮和粮食,押运的民兵只有三个人,这对神出鬼没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不简单的是他竟然把那么多物资和粮食搬走。这次抢劫激恼了政府,派驻军中队百余人,加上三千民兵,对全县进行地毯式搜索。没找到粮食,也没抓到大鼻子老烟,他像烟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天再次露面。
再次露面是因为饿。这几年,所有人都在想方设法寻找食物。粮食和蔬菜远远填不饱肚子。令人们意外的是大鼻子老烟也在挨饿,这天他在都溪林场边的玉米地里抠红薯,边抠边吃。一个九岁的小孩看见他,小孩不知道他是大鼻子老烟,开始以为那是一头野猪,继而觉得那是野鬼。小孩逃跑时被大鼻子老烟一枪打在屁股上,临死前说他看见鬼,一丈二高红毛的野鬼。或许是因为饥饿,大鼻子老烟次失准,没能一枪爆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