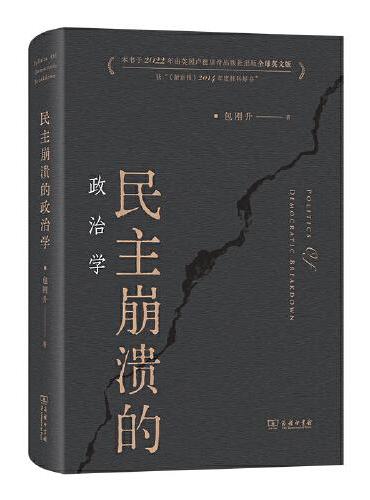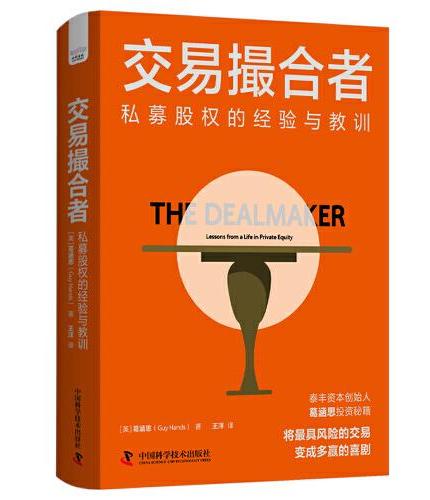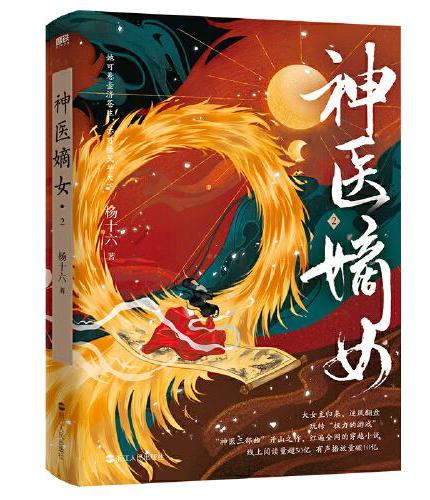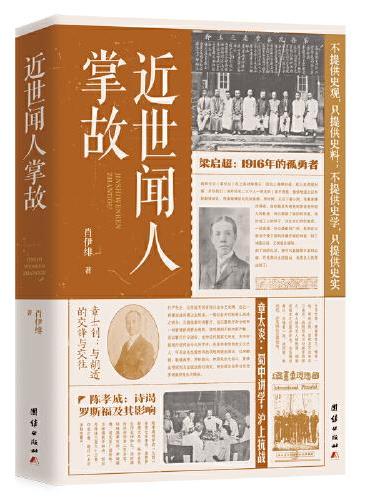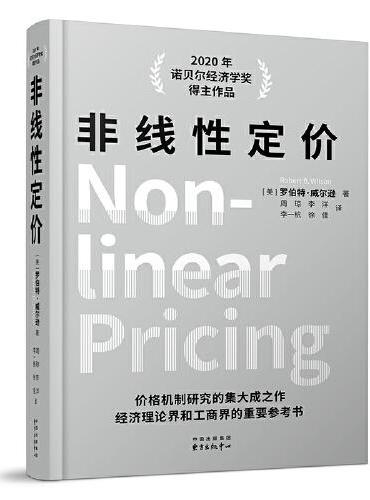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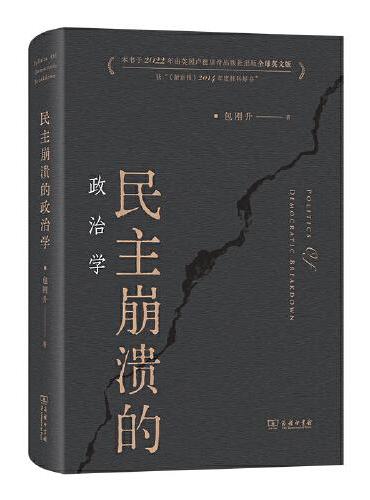
《
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精装版)
》
售價:HK$
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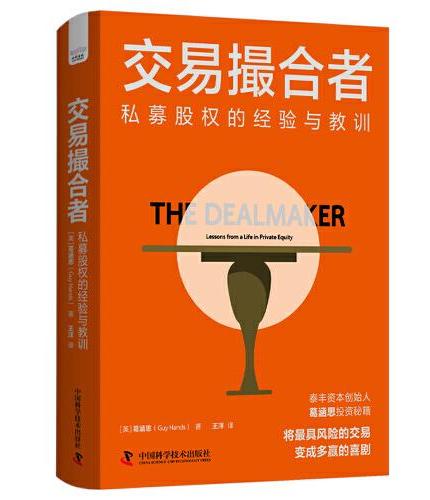
《
交易撮合者:私募股权的经验与教训(泰丰资本创始人葛涵思投资秘籍!)
》
售價:HK$
86.9

《
最美世界名画(顾爷十三年匠心之作。超大开本;精美刷边;4米长海报;藏书票)
》
售價:HK$
734.8

《
侧耳倾听
》
售價:HK$
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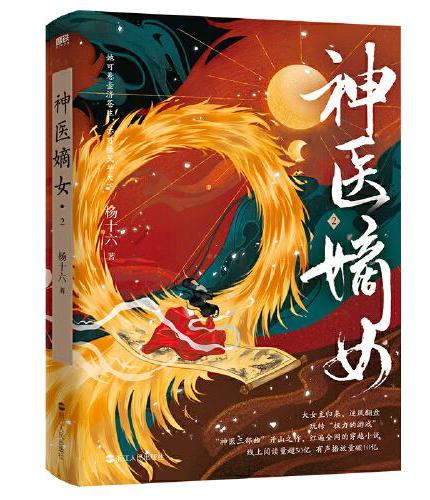
《
神医嫡女·2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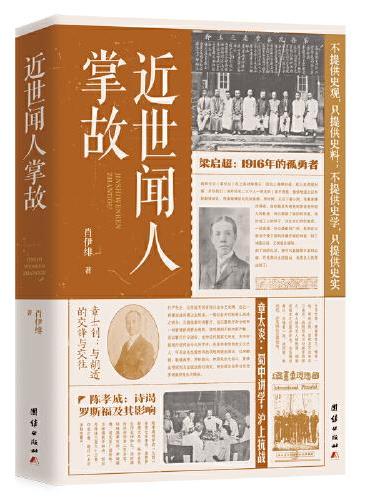
《
近世闻人掌故
》
售價:HK$
74.8

《
余华长篇小说全集(共6册)
》
售價:HK$
3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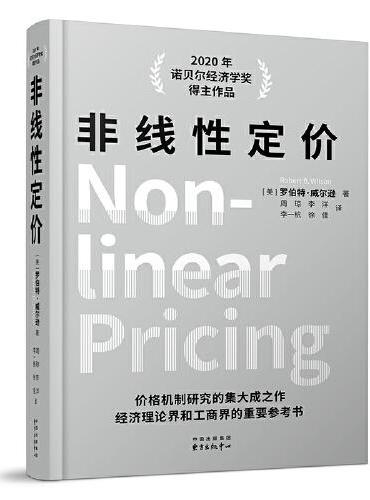
《
非线性定价
》
售價:HK$
162.8
|
| 編輯推薦: |
1. 互怼生情的都市爱情。
这是一本都市言情故事。整个故事爽快,直白,所有的喜欢和讨厌都是直来直往。
作者整个文风也非常爽辣,会让读者看的很爽。
而作者也出了几本书,拥有了一定的读者基础。
2. 荷尔蒙爆棚的防沙队队长VS才华横溢性格“小作”的摄影师,性格天南地北的两人碰撞的火辣爱情!
男主是在西北沙漠的防沙护林队的队长,长期生活在沙漠里,很野很MAN荷尔蒙爆棚,他的工作非常具有正能量。
而女主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独立摄影师,但是性格是那种不拘小节,却又事很多的。
一个是城市里的精致的精英,一个是西北地里素面朝天的队长,生活习性完全不同,性格也完全不同。
但是却在这篇沙漠里上演了非常有趣火辣的爱情故事。
整个故事很爽辣,都是很直来直去的喜欢,非常适合当下的爱情观,也是现在读者喜欢的一种爱情。
|
| 內容簡介: |
何遇这女人邪性得很,看着一副冷冷淡淡的样儿,却眉梢眼角都是钩子,顺毛捋下去着了她的道,逆毛薅上来又被她钳得死死地。
“川昱,有了你,见不见或者睡不睡的都挺好,对别的男人,身材再好似乎也没什么耐心看了,你觉得呢?”
“一样。”
“不然,咱俩就登记了吧?怎么样?”
川昱眉头一皱,完了,这事儿让她抢先了。
|
| 關於作者: |
三川:
喜欢呼啸的风喜欢滂沱的雨,
喜欢将现实的事故变成笔下的故事。
已出版:《余生爱你如初》《风吻过他的侧颜》等作品
|
| 目錄:
|
目录:
章 冤家路窄
第二章 嘿,闷骚型,真有意思
第三章 你是讨厌我吗?
第四章 我抓住你了,你放心
第五章 她吻在了他唇上
第六章 你喜欢我
第七章 你受伤,我不愿意
第八章 我的人,我会照顾好的
第九章 我不会让自己想念你的
第十章 我会来找你,不管在哪儿
番外一——求婚
番外二——川息
|
| 內容試閱:
|
章 你摸了我的腰
(一)
透过红酒杯看过去的银框带着秘金色,像一种什么东西,何遇的脑袋里一时没有确切的答案。
展会现场是不允许喝酒的,但经纪人还是给她倒了一小杯,不然,怕留不住她。
离何遇七八米的正前方有一张黑白色的照片,半身像,是一个刚从夜宵摊上喝得烂醉下来的街头辣妹,额角有几处伤,冲镜头比了一个中指,带着目空一切的笑。
临近的一个观赏者看了许久发出一声叹息,自以为优越者的可怜与鄙夷参杂,何遇一向不喜欢关注旁人,但她很喜欢这个反应,觉得滑稽。
《野蛮生长》摄影展选用的照片只有十七张,比任何一个见报的展会都少,可取景的地域跨度却几乎纵贯了整个中国的东西向,南方多雨,她不喜欢。
何遇记得照片里那些人物的所有细节,比如眼前这个姑娘,她的眉毛里有一颗痣,照片上看不出来,藏在眉色浓的眉峰位置。
何遇抓拍下这张照片后问:“我可以存下吗?或许会用于展览。”
女孩翻了一个白眼:“随便,你有钱吗?搞点来花花。”
她还说:“蠢货,人家想敲诈你你还把钱夹子给人看?脑袋有毛病吧!算了,收你50,唉,刚才那张照片要是真有用,记得搞成黑白的,反正老娘死了也没人收尸,当灵位了。”
想到这儿,何遇端着酒杯勾起一抹淡漠的笑,欣赏、艳羡,打心眼儿里觉得她是个好姑娘,至少,用力,鲜活。
“每天1000张的网络预约票一上架就全月售空,今天的500张窗口票更是差点儿没让那些人打起来,遇,你是好的,为什么不肯给更多的人见识完美的机会呢?我们的场馆,完全可以容纳数倍的参观人次。”
助理kevin熟稔地搭上她的肩,眼睛却顺着她的视线牢牢地锁定在那张竖中指的照片上。
他们相识于一个名利场,2013年,当天kevin背了一只Chanel的呼啦圈包,走秀款,名如其物,包体硕大。何遇站在一个角落里抽烟,说细枝末节的事情太麻烦,想找个经纪人,好婊气一点的。圈内的一个熟人随手一指,kevin的视线正好与她对上,他闻到了无上限的人民币味道。
“遇,你知道那些期刊怎么评价你的作品吗?”
何遇穿了一双细高跟,比他略微高一点儿,从他的角度,她的颧骨看起来比平常格外高一些,很冷,很古典,也很美。
“所有作品都会收入影集,现场一张票都别加,我累了,先走了。”她侧了一点儿身子,很巧妙地让他的手从自己肩上溜下,酒杯顺势传到了他手里,kevin托着杯体摇了一下,一点儿没少。
一个小助理轻声跑过来,看了一眼何遇的背影有些讶异,依旧对kevin说:“kevin哥,专访会场准备好了,问题过滤过,这是提问清单,记者正等着何老师呢。”
“记者正等着何老师呢”kevin学着小助理的语气复述了一遍,腰一插白眼一翻,“好几百万还正等着老娘呢,有用吗?我问你,酒杯里的吸管跑哪儿去了?”
“忘……忘了放。”
“你这么棒怎么不干脆忘了细胞分裂永远做个受精卵。”
Kevin气得够呛,声音却压得极轻,落在一旁的观赏者眼里更像一对亲密兄弟耳鬓厮磨地品评摄像作品。
小助理接不住这句吐槽,尴尬地站在那里。
眼看何遇就要走出大门了才皱眉喃喃了一句:“kevin哥,怎么办啊?”
Kevin撇了他一眼,视线在那双慌张但足够圆亮的眼睛上停留了两秒:“碰运气吧。”
何遇疾步走向大门,未得到访问允准的记者将展会入口团团围住,隔着一道茶色玻璃,城市的霓虹、观展的引路牌、摄影机的补光灯……像无数双眼睛。
“有后门吗?”她没回头,但她知道身后跟着Kevin。
“有,展览期间临时封闭了。”
“打开,带我过去。”
“遇,越是曲高和寡的艺术越需要流量和曝光度。”
“当然。”
“那你——”
“我追求的不是艺术。”
“什么都好,你讨厌热闹和嘈杂我替你安排了专访,只有几个问题,你看看,不想回答的可以划掉。”
Kevin适时将清单递给她,何遇一边朝后门走一边扫览。
“《野蛮生长》定名的出发点与立意?没有。单幅作品拍卖的预估价?的那个。个人成长经历对摄影作品的影响……”
她的目光停留在第三个问题,WPP、达盖尔奖、哈苏国际摄影奖……这个问题总在不同的场合被乍然问起。
“抱歉,遇,人们需要这个。”
“从绝境中苟延残喘下来的少女凭借热爱与勇气铸就辉煌?”
“差不多,可以更煽情一点。”
“狗屁。”
“是,狗屁,但是遇,你先跟我回去接受采访好吗?”
高跟鞋停在后门的大挂锁前,何遇向 Kevin伸出手。
“钥匙存在大厦保卫科,我让他们送过来,遇,接下来的一个月会是展会受瞩目的时间,你用镜头换来的成功,应该在镜头前享受,我会把专访调到明天下午,你今天好好休息,好吗?”
何遇背手,玉琢似的一段手臂伸过脖颈将发髻拆散,盘发的是一柄刻刀造型的铬锻簪,银白色,坚硬的金属,很衬她。
细端伸入锁眼儿挑了几下,“咔”一声,何遇认真地回答:“有些不得空,还有一个拍摄计划没完成,今晚就得动身。”
Kevin明知故问:“动身去哪儿?”
掏出手机,指腹随意划了两下,她误点进了电子邮箱,看到了一则半年前的未读邮件,发行人Unknown,主题栏写个一句与垃圾广告异曲同工的话——浑善达克沙地欢迎您。
她一指:“这儿。”
“浑善达克沙地?这是哪儿?”
“内蒙古吧。”
“……”
(二)
十月,入夜后阿巴嘎旗的气温降到了零下,没下雪,但那辆后漆涂成迷彩色的越野停在宝拉格旅馆前时,何遇还是清楚地听到了轮胎碾压冻化小砂砾的“咯咯”声。
手机移动电源电量耗尽,爆胎一次、陷沙一次,这次求安宁的入蒙之旅本身一点儿也不安宁。
出发前给尤金回复了一封邮件要具体地点,他立马打了电话说来接,她说不必,他说,从机场到驻地的路不好找,她说不必,这边信号不好,喂喂。
何遇靠在车座上点了根烟抽了两口,捻熄后锁了车锁从后备箱拖出一只背包和一只行李箱往那道半开的门里走。
宝格拉旅馆的老板娘正坐在门后用一枚磨得锃亮的钢针穿牛羊肉干,七块肉干一摞,专卖给徒步旅行的背包客。
何遇从门口跨进来,厚实的冲锋衣添上那个包将门缝顶开了一些,撞到了穿肉者的屁股。
老板娘大声朝柜台吆喝:“阿拉格,有客!”
她没回头,柜台上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抬起了脑袋,指了指正上方一排系着褪色黄绸的木片。
单间七十,标间一百一十七,很随意的标价。
“一个标间。”
男孩趴在柜台上朝何遇身后看,老板娘已经将门推回了原来的位置。
何遇:“就我一个人。”
“标间两个床哦。”
“知道。”
男孩看着她觉得奇怪,但这份好奇没有停留太久就被灯罩上的一只小飞虫引过去了,他盯着看,何遇也不催,直到再一次响起了推门声男孩才“咯咯”地笑了一声,迅速问何遇要了身份证登记。
“额吉,有客!”他以同样大的声音向老板娘吆喝,得胜般从柜台后的高凳上跳下引着何遇上楼。
他在前她在后。
走到楼梯口何遇闻到了一股奇怪的香味,很幽微,不是这个店里原有的。
“小伙子,等一下啊,就穿完了。”
是新进的那个人,何遇上了楼。
小旅馆标价随意是有道理的,木制的旧楼梯每走一步都“吱吱”响,房间分布也密而乱。
“柜子里有毛揪揪哦。”
“什么?”
“房间柜子里有毛揪揪哦,有两个,左耳朵塞一个右耳朵也塞一个,运气好就不用,你别丢哦。”
男孩停在一个房间门口,用钥匙戳下一块门锁边翘起的漆皮,冲她笑了一下,开了门。
何遇没明白他刚才的话,也不想问。
乍然看过去房间里收拾得倒算干净,正壁上还挂着空调,条件已经很好了。
“啊!你要洗澡吧?”
“是。”
“用热水吗?”
“今天零度。”
阿拉格笑了一下,小拇指小心地戳了何遇的外套,似乎在通过衣服厚度检测她的抗冻能力:“我给你换一间吧。”
“随便。”
“嘿,我好了。”
“……”
他将她领到了隔壁,差不多大小,少了一张床。
“单间?”何遇问。
“热水没坏哦。”
“我需要一个软一点儿的地方摆我的相机。”
他笑:“我好了。”
转身逃开,将楼道跑得“蹬蹬”响,冷风从尽头半开的窗户里灌进来,何遇打了个哆嗦,正要关门,“蹬蹬”又回来了。
“给,单间,我好了。”他手里攥了一个花布缝的座垫和找得四十七块零钱。
何遇接过,道了谢,进了屋。
放倒行李箱,她打开绒布袋取出那些镜头,RF15-35mm、RF24-70mm……一一检查,这一路太颠簸了。
后抚过手的是RF70-200mm,她摸了一圈,套上机身开门迅速拍下了那条被寒风侵袭的廊子。
狭窄逼轧,灯光昏沉,尽头朝夜的窗口像一个横向的深井,盛着化不开的浓黑色。
“在阿巴嘎旗,我也说不清具体是哪儿,那……你在家想我没有?”
不知道哪个房间漏了娇滴滴的一声,何遇删了照片装好镜头,从背包里取出雾化喷头和洗漱用品,熄灯去了浴室。
门口有摊水,她落脚时往旁边挪了一点儿,三两下换上自带的喷头,连浴室的灯也熄了。
高耸流畅的锁骨,纤长细腻的脖颈……她喜欢在暗色中触碰自己的皮肤,雾化的细水珠轻柔地像某种透薄的丝绢,得配合一遍遍的悉心擦拭方能完成清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