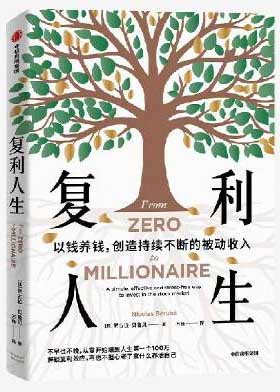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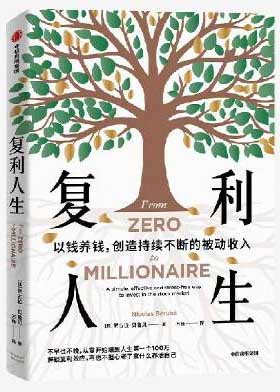
《
复利人生
》
售價:HK$
75.9

《
想通了:清醒的人先享受自由
》
售價:HK$
60.5

《
功能训练处方:肌骨损伤与疼痛的全周期管理
》
售價:HK$
140.8

《
软体机器人技术
》
售價:HK$
97.9

《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
售價:HK$
74.8

《
奴隶船:海上奴隶贸易400年
》
售價:HK$
75.9

《
纸上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破译古老文明的密码,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150+资料图片)
》
售價:HK$
85.8

《
米塞斯的经济学课:讲座与演讲精选集
》
售價:HK$
74.8
|
| 編輯推薦: |
法国知名诗人、学者、文学批评家米歇尔·高罗全面剖析身体在西方现当代诗歌中的形象。
20世纪是身体出场的世纪,它备受现代艺术青睐。高罗通过剖析兰波、马拉美、瓦莱里、克洛代尔、安德烈·杜·布歇、罗朗·加斯帕等现当代著名诗人的典范作品,阐明身体在当代诗学与哲学中的中心地位。其中有些诗人的作品首度被译成中文。
明确区分现代身体诗学内部两种竞争的趋势,全新审视身体与宇宙的关系。
高罗从现代身体诗学的内部区分了两种相互竞争的趋势:一种将身体与精神对立,一种则把身体视为精神与世界的中介。本书仿佛让读者与文本有了体肤之亲,那些嵌入主题、文字和世界的肉身就是我们自己身体的延伸和铺展。现代诗歌通过身体为我们揭示的,正是这种万物俯仰生息的亲缘关系。可以说,通过身体这个微观的宇宙,我们能更好地感受我们所归属的宏观的宇宙。
|
| 內容簡介: |
|
身体是现代性重要的表现对象之一。不论在大众文化中还是在先锋文化中,对身体的崇拜早已成为共识。法国知名教授、诗人米歇尔·高罗从现代身体诗学的内部区分了两种相互竞争的趋势:一种将身体与精神对立,一种则把身体视为精神与世界的中介。作者通过剖析建立身体·宇宙形象的典范作品,以及自己的写作实践,结合现象学“肉身”概念,提取出一种“肉身化诗学”的特质与艺术倾向,阐明身体在当代诗学与哲学中的中心地位,从而将身体与灵魂、自我与世界、文字与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为我们进入现代诗歌的深邃之处指出了一条明路。
|
| 關於作者: |
米歇尔·高罗(1971— )
法国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巴黎第三大学法国文学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第三大学“现代性书写”研究中心主任。2019年,法兰西学院授予其学院奖,以表彰他的诗歌和文学评论作品。著有《绝妙的地平线》《现代诗歌与地平线结构》《物质-情感》《风景与诗歌》等。
【译者介绍】
朱江月
巴黎索邦大学法国文学博士。本科与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法语系,曾赴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交流学习。研究方向涉及克洛岱尔诗学、法国二十世纪诗歌、法国文学与东方关系等领域。2014—2018年任教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现为法国教育部中文教员。
|
| 目錄:
|
中文版序言
引言
部分 身体·宇宙
诠释身体的两种方式
论身体—精神
世界之肉
肉身化的语言
第二部分 诗歌的身体性
能指与所指
诗歌与感觉
跨越地平线
厄帕福斯的启示
结语
|
| 內容試閱:
|
引 言
诗歌于我,总与某种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相依存:在或优雅或粗俗的状态之中,身体已不再是完成语言与行动的听话而隐蔽的工具,我的身体突然间把我吸引。它没有把我支离破碎地引向外部世界,而是邀请我重归心源,那些由此心源而散发开来的离心运动实则构成了我们存在的常态。
但是向原点的回归绝不意味着倒退。对自我身体的重新觉醒,并未使我回溯到一颗静止而封闭的星球。我不仅重新在我的肉身中找回了我曾经在世界与思想的空间中探索的每一条道路、每一丝痕迹,而且还感受到了一股股邀我进入全新境域的紧张与冲动。这个生机勃勃的、震颤的微宇宙(microcosme)绝没有把我封闭起来,却向我启示了我对宏宇宙(macrocosme)的皈依。在亲密的体感内核,我突然抓住了记忆,捕捉到了那些指引我结识他者、认知天地万物的情感源泉。
从这个万籁俱寂的世界升起了对话语的迫切呼唤,我寻找词语,为了表达那些寄居在话语中的无声无言的感觉。然而,这种小心翼翼的摸索首先在我的肉身隐晦处开始,在它那精巧微妙的质料的千条褶皱间百转行进。那里,信息在循环流动,并在我的思想中开辟出一条条意料之外的道路;这种对感觉的探索还发生在我喉咙的空洞中,音弦的震颤引起神秘的搅动;它还发生在我的颚下,那里已然回响起了歌声。我兴奋的身体成了内部与外部、思想与感觉、文字与情感之间强烈而永无止境的交换之域。
身体是自我、世界和文字的交汇之处,因此,它成了诗歌的源泉、思想的锦囊。所以,我在此书中汇集了不同性质的文本,然而它们全部都阐明了身体在当代诗学与哲学中的中心地位。
身体是现代艺术备受青睐的对象。不论是在我们的大众文化还是先锋派文化中,对身体的崇拜早已成为共识。然而,在这种表面的认同背后,身体以迥异的方式启发着它的崇拜者们;这些方式所揭示的观点存在分歧,甚至大相径庭,因而导致了当代艺术创作和当代思潮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种倾向将身体与精神对立,没有任何传统装饰的肉身不再同宇宙之间发生任何象征性的交换。另一种倾向则将身体视为精神与世界的中间人。我重读了一些建立“身体 · 宇宙”形象的重要作品,并尝试从中提取出一种“肉身化诗学”(poétique de l’incarnation)的特质与艺术倾向。这一诗学从现象学哲学所阐述的“肉身”(Chair)概念中,得到了宝贵的理论支撑,从而将身体与灵魂、自我与世界、文字与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尽管当今众多诗歌创作与艺术实践倾向于将它们分离。
有一种诗歌的体质(physique du poème),它不排斥抒情,甚至也不拒绝形而上的叩问,而是将此二者嵌入主体的、世界的和词语的肉身。我希望追溯自己的若干首诗歌创作,以便去描述其中的活力。这不是作者的虚荣心或自恋主义作祟,而是为了把理论与实践对照观之。既然关乎诗歌创作既隐秘又独特的过程,那么避而不谈个人经验的教诲实在令人感到遗憾,即使终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些更为普遍的可与世人共享的结论。
身体如同语言,是我们每一个人为亲密的归属,同时也是为公共的领域。我将以对“赤裸”的短篇颂词为此书作结。赤裸是一种典型的身体状态,既面向他者又面向世界开放;它并不像裸体者通常给人们的印象那样任由视觉侵犯,更不像许多当代影像那样热衷于表现施虐的暴力,而是在厄帕福斯的启示之下,传达出抚摸的温存和触感的微妙。
诗歌与触觉息息相关,在一个崇拜身体却又经常压迫它、折磨它、践踏它的社会里,肉身化的诗学所具有的不仅仅是审美的特质,更兼备道德和政治的意义。应该在结论部分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总结出身体所历经的诗学的、历史的、批评的、理论的和自传式的探索道路,这些路径揭示了身体的全部状态:被感觉与被重新感觉;书写与被书写;阅读与被阅读,抑或被重读。
诠释身体的两种方式
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匹配的材料,那么,它就与我们的意识共同延展,领悟着我们所感知到的一切,直至通向遥远的星辰。
——亨利 · 柏格森
长期以来,西方传统将身体与灵魂分离甚至对立起来,让肉体屈从于精神。然而,精神唯有摆脱基督教言成肉身的桎梏和奴役,才能够在艺术、文学或宗教领域得到充分发展。这样的二分法和等级观念从现代以降便经常遭受质疑,直至19世纪末,身体在西方世界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报复,针对身体的这次反击,查拉图斯特拉向那些“轻蔑者”这样总结道:“身体是完整的一切,而不是任何其他事物:灵魂只不过是一个字眼,用来指称身体中的某种东西。”
为身体平反的行动深刻而持续地标志着艺术与文学的创作历程:20世纪的文学先锋派们为身体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主动性,无论是从未来主义到达达主义,还是从当代的身体写作到被称为身体艺术(Body Art)的行为艺术,都体现了这样的特点。行为艺术和身体写作试图挑唆身体去对抗精神,让身体独立地成为实践的原则和根据,这种实践坚定地打着物质主义的旗号,并且时常带有反叛意义。其中为狂热的实践甚至偏离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或是走向了令人不安的;这些自称具有革命性的实践只不过照鉴了堕落粗鄙的现实,我们的社会时常让身体陷入此等境地,此时的身体可能是一个纯粹为了工作或满足享乐的工具,可能是一种应用于科学技术中的被实验甚至被操控的对象,可能是进行性交易或毒品交易的商品,还可能是人肉炸弹或人体导弹。
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种“身体采取的立场”(parti pris du corps)是否真正摆脱了它宣称要推翻的唯心主义,还是只不过对唯心主义的从属关系进行了倒置而已;更富有成效的做法难道不是应该努力将被唯物主义与唯灵论分离的东西重新聚合,不再将肉体看作精神的对立面,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创造和酝酿思想的场所?需要指出的是,对尼采来说,“身体是一种重要的理性”。a现象学所要努力阐释的,以及许多现代作家试图探索和挖掘的,正是这个潜藏在我们的身体印象和身体表达中的逻各斯。比如对普鲁斯特来说,“一些观念,比如光影、声音、立体感或肉欲的观念……是装点着我们内心世界的财富,我们的内在因此而丰富多彩”。或者蓬热(Ponge)也曾说过,他始终在寻找“一种不会将感性中途抛弃的理性”。
身体地位的提升明显地呈现出文学现代性和艺术现代性的一个普遍特征;但是模糊之处依然存在,就像现代性本身也远非一个同质体一样,对身体的表达亦涵盖了种类繁多的实践,这些实践对应着许多相异的有时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哲学观点。如今存在着不止一种思考身体、表达身体的方式。
考察身体在现代诗歌中的表现时,我们似乎可以在两种主要倾向之间识别出一道相当清晰的分水岭。种倾向自称将“现代性”表现得为彻底,它把身体当作一种与诗歌传统预设的唯心主义彻底决裂的工具,因而让身体对抗灵魂,让文字对抗精神,并且把主体消解在一个匿名的不洁之躯中,以单个物体或者一组器官的形式浮夸地展现这个不洁净的身体。这种倾向通过对美、对自然和/或社会的拒斥,心甘情愿地与癫狂和淫秽同流合污。
我们可以在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和雅里(Jarry)的作品中发现这种倾向的早期征兆;20世纪中叶,这种倾向在阿尔托(Artaud)和巴塔耶(Bataille)那里得到了强化,此后历经《如是》杂志的诗人们如德尼(Denis)或莫里斯 · 罗什(Maurice Roche)的传承,直至今日又在克里斯汀· 让(Christian Prigent)等人的作品中得到了延续。皮让主办的刊物TXT在1988年第23期以“身体上的工程”为题介绍了一部让人大开眼界的诗集,以下的变移字母位置构词法(anagramme)彰显了这本诗集的主题及其全部内涵:“猪 = 身体”(PORCS = CORPS)。与此同时,一些强调音响效果的诗人,如亨利 · 肖邦(Henri Chopin),还通过一系列语言行为把自己的身体诗学搬上舞台,不假思索地让舌头、喉咙和所有与发音相关或不相关的括约肌如音素一般释放声响。一个逃脱了意识控制的身体虽然得到了解放,但是语言也被免除了产生意义的义务,缩减为一种更似吼叫而非话语的纯粹身体性的表达。
这些实践经常伴随着身体形象的四分五裂,那些供给局部冲动的身体碎块既独立自主,又相互交流,在这场肉体的狂欢中,身体贱的部位占据了贵的地位。尽管这种碎裂的身体形象看似完全延续了以狂欢或讽刺方式颠覆古典礼仪的传统,我却认为它是一种与社会规约更深刻、更彻底的断裂,这些规约在不久以前曾是社会、世界和主体三者统一性的保障。碎裂的身体形象还与“社会机构的隐喻”a对立,后者曾经长期为人们提供范式,用来思索和表达那种凝聚社会机构成员的团结性;然而,由于失去了“领袖”,失去了那个曾经在众人之上扫除一切离心势力的领头人,社会机构中的成员们从此分崩离析。这种身体的形象还更进一步地破坏了富于象征意义的通感,损害了通感在人体与被视为有序整体的宇宙之间建立的联结。它对曾经统治世界的社会秩序和神性秩序表现出彻底的决绝,并抛弃了人们曾经一致树立的那些美的典范。被肢解的身体再无宇宙性可言,亦不再具有审美性:它完全沦为污秽之物。
这样的身体形象当然也很可能就此成为一种新的审美象征,它否定古典时期所推崇的统一与和谐,转而对多样化、异质性和碎片性进行赞美。但是,此番探索在产生了某种现代审美形式的同时,时至今日被越来越多地与对丑的崇拜、对堕落和颓废的持续追捧混为一谈。身体的支离破碎由于直接冲击了身份认同的根基,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精神焦虑。此外,它还会导致个体倒退到心理生命原始的阶段,那时的自我不具有完整性,四分五裂的个体因而顶着陷入精神错乱的风险,只有用腐化堕落,用当代舞台恣意纵容的这些行为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才能够逃脱可能发生的精神劫难。
如今,一切艺术家和作家都应当正视这种预示着文明危机的身体分裂,但是也不排除其中一些人情愿逃避自我,一味缅怀那不复存在的统一性。然而,与其在身体的肢解中自鸣得意,或者将这种困境推向,作家和艺术家们可以实施反抗,并且尝试进行补救的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身体审美倾向,它不满足于仅仅将唯心主义传统中的从属对象颠倒位置,而是尽可能地去超越建立了这种传统的二元对立,努力让身体成为沟通物质与精神、主体与世界的纽带。
作为对20世纪遗留下来的悲剧性创伤的回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弗朗西斯·蓬热的倡导下,一些艺术家感到自己有可能并且有义务对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和四分五裂的身体“进行修复”;现如今,似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正在尝试重新恢复那些散落的肢体和器官之间的联系,重新编织将它们与世界之肉相结合的纽带。风景就是其中一个重建了身体与宇宙统一体的典型场所。尤其对于那些参与了地景艺术(Land Art)或者从中受到启发的艺术家来说更是如此,比如汉密斯·伏尔顿(Hamish Fulton)和理查德·朗(Richard Long)选择徒步行走,吉塞普·佩诺内(Giuseppe Penone)和查理·西蒙斯(Charles Simonds)选择用某种行动来拥抱风景的空间。
吉塞普·佩诺内初的行动是将自己的身体痕迹印刻在故乡的森林里。照片上的他紧紧地抱住一棵树的树干,之后他“用一张勾勒出他的身体轮廓的铁丝网勒紧”树干。于是“这棵树将会记住接触的感觉”:“它(将)贴合着人体的形状”而生长,从此,人便融入了风景中。另一张照片为我们展示了“正抓住一棵幼年树的艺术家之手”。“为了定格这个紧握的瞬间”,佩诺内“以自己的手的形状制作了一件青铜模具,并把它固定在树干中”。这只与源身体切断联系的手在若干年之后已经嵌入了树木的肉体之中,这棵树“在手以外的地方持续地生长”。
在1973年的一部名为《风景身体居所》(Landscape Body Dwelling)的影片中,雕塑家查理 · 西蒙斯“赤身裸体地平躺在地面上,把全身盖满泥土和沙子,让自己变成风景,而他在这个风景之上建起了一幢幢贴合身体 — 土地轮廓的住宅模型”。批评家约翰 · 比尔兹利(John Beardsley)对这个充满象征意义的行为评论道:“尽管不可能真正地与土地结合,但是,这个私密性的仪式中体现的融合身体、风景和建筑的尝试始终奠定着西蒙斯作品的根基。”
在身体和宇宙之间建立新的联姻,这样的探索还涉及许多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绘画、雕塑、影视或家居艺术。近期的一场名为“人 — 风景”的展览因而能够将一系列当代艺术作品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形风景进行比照。比如,此次展览的画册封面就印制了一张中国艺术家黄岩的摄影作品,他让人直接在自己的皮肤上绘制了一幅带有中国山水画风格的传统风景画。当代诗歌中的这种倾向本身也提出了一个身体·宇宙的形象,在这个形象中,精神被嵌入一个既是主体的也是世界的和文字的肉身中。这一肉身化的诗学尽管与先锋派那些招摇炫目的主张相距甚远,但是在今日同它的对手一样充满活力:例如,1996年《研讨会》(Conférences)杂志便将其中一期献给了“身体之美”的主题,并且刊登了多张克洛德·格朗什(Claude Garache)创作的精美绝伦的裸体画。肉身化的诗学体现了另一种现代性,它较少地考虑与传统决裂的问题,而更加关注如何让传统重拾活力:它尤其与现象学立志将身体与精神融合而对肉身化理论进行的革新不谋而合。我将在此提出一个假说:有一种同源的运动,它不仅主宰了肉身(Chair)b思想的诞生,尤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说为佐证,而且诱发了一种新的身体诗学的出现,后者的蓬勃发展始于兰波,历经马拉美、克洛岱尔、瓦莱里、阿尔托和超现实主义,时至今日则体现在罗朗·加斯帕和贝尔纳·诺埃尔的诗作中。在本书中我将着重以这后两位诗人的作品为例来阐明我的论点。
毋庸置疑,这道分割了当代诗歌图景的分水岭不仅提供了两种诠释身体的方式,而且穿越了某些作品的内部空间。正如我们即将在兰波、阿尔托或贝尔纳·诺埃尔的诗歌中看到的那样,他们的作品蕴藏着一种内在的张力,一面着迷于支离破碎的快感,一面又对统一性心向往之。我将依次探讨三个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正处于这场哲学和诗学辩论的核心:它们涉及肉体与精神、身体与世界、词语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我将努力呈现出肉身化的思想和诗学如何弥补了这三组关系之间的断裂,而先锋派艺术家们则在颠覆等级秩序的同时让这种断裂局面恶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