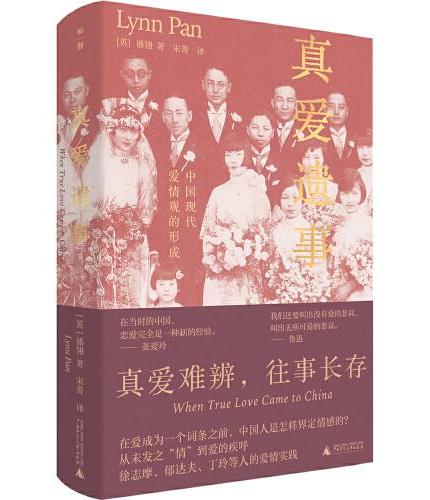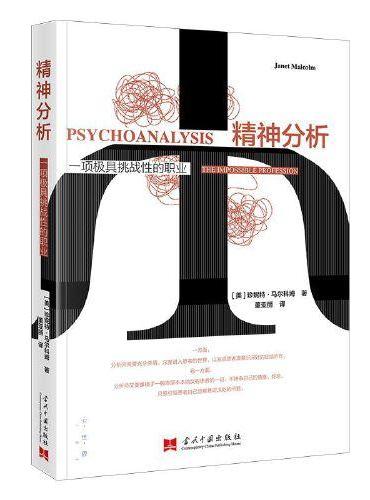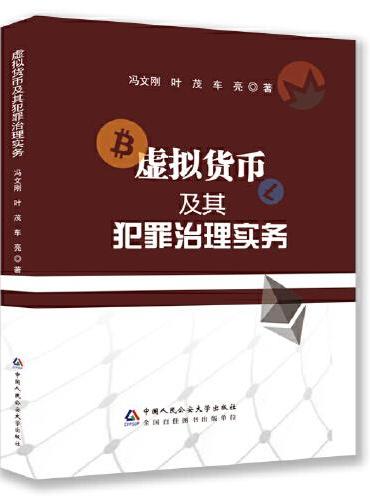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DK园艺的科学(100+个与园艺有关的真相,让你读懂你的植物,打造理想花园。)
》
售價:HK$
107.8

《
牛津呼吸护理指南(原书第2版) 国际经典护理学译著
》
售價:HK$
206.8

《
窥夜:全二册
》
售價:HK$
87.8

《
有底气(冯唐半生成事精华,写给所有人的底气心法,一个人内核越强,越有底气!)
》
售價:HK$
74.8

《
广州贸易:近代中国沿海贸易与对外交流(1700-1845)(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经典著作!国际知名史学家深度解读鸦片战争的起源!)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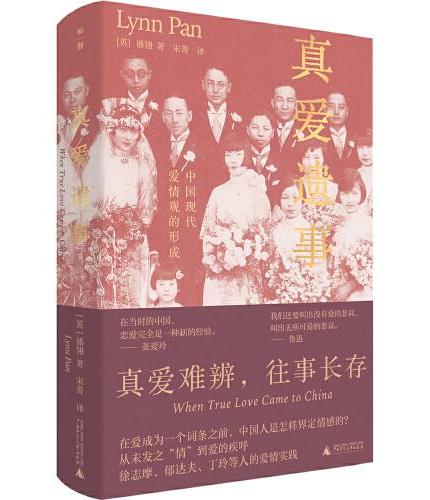
《
真爱遗事:中国现代爱情观的形成
》
售價:HK$
1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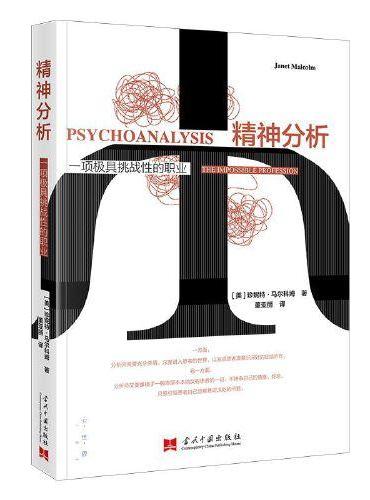
《
精神分析: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职业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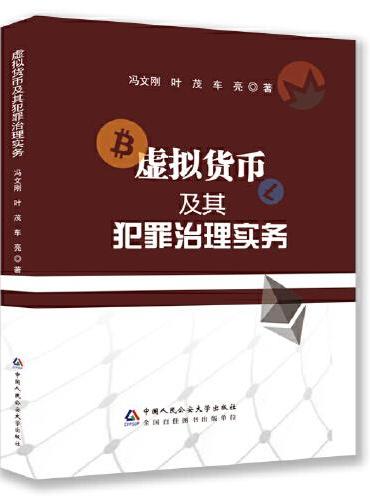
《
虚拟货币及其犯罪治理实务
》
售價:HK$
63.8
|
| 編輯推薦: |
|
《莎士比亚、乌托邦与革命》是对英国现代早期人文思想的多维时空的精妙呈现,代表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沛近十年来对英国现代(1516—1690)人文历史的观察和思考。
|
| 內容簡介: |
“历史”的观念意味着“历史性”的自觉。由于时间-运动,人类得以进入四维存在;由于记忆-想象,我们得以思想五维时空。对历史的解读或者说意义的制作穿越和连接了“异代不同时”的四维时空。
《莎士比亚、乌托邦与革命》按照古典戏剧的形式编组,其中“序曲”讲述彼特拉克的历史意识和身份觉醒,“进场”展示英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和文艺复兴诗学精神的自觉,、二、三歌分别探讨爱欲、城邦、自由、王权、帝国等议题,以散点透视加重点聚焦的方式讲述了现代乌托邦神话“道成肉身”的文学历程。
|
| 關於作者: |
|
张沛,北京大学中文系暨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委员。著有《隐喻的生命》《中说校注》《哈姆雷特:注释与解读》等,编著有《英国人文经典读本》《比较文学基础读本》等,译著有《常识中的理性》《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文学与美国的大学》等。
|
| 目錄:
|
序曲
彼特拉克的焦虑3
进场
英国“现代文学”的发生17
锡德尼的敌人39
歌
爱欲与城邦59
城邦与诗人81
凯撒的事业103
第二歌
莎士比亚的意图131
王者的漫游153
莎士比亚的乌托邦175
第三歌
乌托邦的秘密211
培根的寓言228
霍布斯的革命249
终曲
洛克的“白板”275
索引301
后记310
|
| 內容試閱:
|
彼特拉克的焦虑
文艺复兴精神通过远交近攻、厚古薄今的斗争策略,从更久远的时代(在文艺复兴中人看来,这是一个失落的美丽新世界)——古代希腊罗马异教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通过模仿古人而战胜了前人,终从古人-前人手中夺回了自身存在的权利和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彼特拉克本人以其生命话语实践(其中不无“影响的焦虑”)见证和开启了这一精神:通过这一精神,彼特拉克成为了“文艺复兴之父”和人文主义“位伟大代表”;也正是通过这一精神,欧洲文艺复兴成就了自身的辉煌。
中国读者大都听说过彼特拉克(FrancescoPetrarca,1304—1374)的名字,甚至知道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欧洲文艺复兴之父和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先驱。但是熟知不等于真知:在很多方面,他对于我们(包括笔者在内)仍不过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首先,彼特拉克的作品在国内译介无多:就中国大陆而言,目前仅见《歌集》(李国庆、王行人译,花城出版社,2000年;王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和《秘密》(方匡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两种以及一些零星译介,此外几乎无书可读。其次,即便我们对他有所了解,也仅仅是将他作为抒情诗人或文学作者,而对他作为一个整全个体的自我认知——这一认知构成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自觉和自我意识——仍不甚了了;读其书而不知其人,更谈不上“知人论世”,尽管今天我们事实上仍然生活在彼特拉克及其后来者即所谓“文艺复兴人”开启的那个时代。
不过,这个时代似乎正在成为自身的遗蜕或者废墟。在后现代状况下(这一状况因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量子传输、虚拟增强现实技术而证取自身),“人文主义”被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已陈之刍狗,甚至是本身需要祛魅的神话。然而,没有神话的现实是可悲的,而废墟也许是新生的根基。在此方面,彼特拉克本人的知识生活(同时也是他的精神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见证。作为从“黑暗世纪”中走出的人,彼特拉克——顺便说一句,他正是“黑暗(中)世纪”这一深入人心的说法的始作俑者——通过回望古典而发现了未来世界的入口。
1336年4月26日,彼特拉克成功登顶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旺图山。这是彼特拉克个人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西方世界历史的一个包孕绽出时刻:正是在此并以此为标志,近世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的缕曙光。站立高山之巅,俯瞰下界人间,彼特拉克不禁心神激荡,同时也倍感孤独,如其事后所说:“我突然产生一种极其强烈的欲望,想重新见到我的朋友和家乡。”这时他想到了奥古斯丁,于是信手打开随身携带的《忏悔录》,正好看到第十卷第八章中的一段话:“人们赞赏高山大海、浩淼的波涛、日月星辰的运行,却遗弃了他们自己。”仿佛醍醐灌顶,彼特拉克顿时醒悟:原来,真正的高山,或者说真正需要认识和征服的对象,不是任何外界的有形存在,而是“我”的内心!
那么,彼特拉克在他的内心中看到了一个怎样的自己呢?一言难尽。在他晚年致教廷派驻阿维农特使布鲁尼的一封信(1362年)中,彼特拉克自称“热爱知识远远超过拥有知识”,“是一个从未放弃学习的人”,甚至是一名怀疑主义者:
我并不十分渴望归属某个特定的思想派别;我是在追求真理。真理不易发现,而且作为一切努力发现真理者中卑下、孱弱的一个,我时常对自己失去信心。我唯恐身陷谬误,于是将身投向怀疑而不是真理的怀抱。我因此逐渐成为学园的皈依者,作为这个庞大人群中的一员,作为此间芸芸众生的末一人。
这是他在五十八岁时的自我认识。而他早年的自我认识承载和透显了更多自我批判(同时也是自我期许)的沉重和紧张:
在我身上还有很多可疑的和令人不安的东西……我在爱,但不是爱我应该爱的,并且恨我应该希求的。我爱它,但这违背了我的意愿,身不由己,同时心里充满了悲伤……自从那种反常和邪恶的意愿——它一度全部攫取了我,并且牢牢统治了我的心灵——开始遇到抵抗以来,尚未满三个年头。为了争夺对我自身内二人之一的领导权,一场顽强的、胜负未决的战斗在我内心深处长期肆虐而未有停歇。(1336年4月26日致弗朗西斯科信)
这种沉重和紧张源于并且表达了中世纪人(以奥古斯丁为其原型)特有的一种生存焦虑,而这种焦虑——从历史的后见之明看——正预示了后来蒙田和笛卡尔表征指认的现代意识与精神症候。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彼特拉克身上看到另一种“在世的心情”:不同于方才所说的自我怀疑,它更多是一种源于他者——确切说是作为他者的古人和前人——知识的“影响的焦虑”。事实上,正是后者使彼特拉克成为“一个早的真正现代人”(而不是一名单纯的中世纪西塞罗主义基督教道德哲学家)并率先开启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化转型。
彼特拉克本人曾在他的灵修日记——《秘密》(Secretum,1342—1343)一书中借奥古斯丁之口批判自己对世俗“荣耀”即文名的迷恋和追求,其中他特别提到“年轻一代的成长本身依靠的就是对老一辈的贬低,更别说对成功者的嫉妒”以及“普通人对天才生命的不满”。他这样说当是有感而发——二十五年后,他被四名来自威尼斯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嘲讽为“无知之人”而愤然写下《论自己和大众的无知》一文,公开声称“我从来不是一个真正有学识的人”,“就让那些否定我学识的人拥有学识吧”,但是随后又说“在我年轻的时候,人们经常说我是一个学者。现在我老了,人们通过更加深刻的判断力发现我原来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白丁”,到底意难平,此时他一定感触更深——不过他似乎没有想到(或是想到却不愿承认)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员。“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这大概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宿命或“人类境况”吧。
例如他对但丁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但丁是彼特拉克的父执长辈和同乡(尽管流亡在外),也是横亘在后代作家(彼特拉克即是他们的领袖)面前的一座文学高峰。彼特拉克从不吝惜对古人——从柏拉图、西塞罗到奥古斯丁——的礼敬和赞美,但对年长他一辈的但丁却始终保持意味深长的沉默。后来他向挚友薄伽丘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时坦陈心曲:
我当时极其渴望获取我几乎无望得到的书籍,但对这位诗人的作品却表现出异常的冷淡,尽管它们很容易取得。我承认这一事实,但是我否认敌人强加给我的动机。我当时亦致力于俗语写作;我那时认为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而且还没有学会向更高处眺望。不过当时我担心,由于青年人敏感多变而易于赞赏一切事物,自己如果沉浸在他或其他任何作家的诗歌作品中,也许会不自觉地、不由自主地成为一个模仿者。出于青年人的热情,这一想法令我心生反感。我那时十分自信,也充满了热情,自认为在本人试笔的领域足以无需仰仗他人而自成一家。我的想法是否正确留待他人评判。但我要补充一句:如果人们能在我的意大利语作品中找到任何与他或别人作品的相似甚至雷同,这也不能归结为秘密或有意的模仿。我总是尽量躲开这一暗礁,特别是在我的俗语写作中,尽管有可能出于偶然或(如西塞罗所说)因为人同此心的缘故,我不自觉地穿行了同一条道路。(1359年6月自米兰致薄伽丘信)
如其所说,他对但丁选择视而不见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袭蹈前人(“不自觉地、不由自主地成为一个模仿者”),事实上是出于要强和自信(“自认为在本人试笔的领域足以无需仰仗他人而自成一家”)而非嫉妒。为了强调这一点,他甚至反问老友:“你难道认为我会对杰出之人受到赞扬和拥有光荣而感到不快吗?”并向对方保证:“相信我,没有什么事物比嫉妒离我更远”;“请接受我的庄严证词:我们的诗人的思想和文笔都让我感到欣喜,我每当提到他都怀着的敬意。”
当然,这只是彼特拉克(尽管他是重要的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其然乎,岂其然乎?作为后来旁观的读者,我们本能地感到他的话不尽不实。例如,他在五年后同是写给薄伽丘的一封信中再次谈到自己早年的文学道路,但是这次他的说法有所不同:
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拉丁文无疑都是比俗语更加高贵的语言;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在前代作家手中已经登峰造极,现在无论是我们还是其他人都难以有大的作为了。另一方面,俗语直到近才被发现,因此尽管已被很多人所蹂躏,它仍然处于未开发的状态(虽说有少数人在此认真耕耘),未来大有提升发展的空间。受此想法鼓舞,同时出于青年的进取精神,我开始广泛创作俗语作品。(1364年8月28日自威尼斯致薄伽丘信)
彼特拉克所说的在俗语文学领域“认真耕耘”的“少数人”自然包括但丁在内,甚至首先指的是但丁,但他强调“它仍然处于未开发的状态”,换言之但丁的“耕耘”成果几可忽略不计。看来,年届花甲的彼特拉克仍未真正解开心结:面对据说“思想和文笔都让我感到欣喜”——尽管“他的风格并不统一,因为他在俗语文学而非诗歌和散文方面取得了更高成就”——的但丁,他内心深处仍是当年那个满怀超越野心并深感“影响焦虑”的青涩少年。
但是少年总会长大成熟并成为新一代的前辈。彼特拉克本人亲身见证了这一人类境况,并预示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精神和历史命运。面对自己的直接前辈——“黑暗的”中世纪文化,一如彼特拉克之于但丁,文艺复兴精神通过远交近攻、厚古薄今的策略,从更久远的时代(在文艺复兴中人看来,这是一个失落的美丽新世界)——古代希腊罗马异教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通过模仿古人而战胜了前人,终从古人前人手中夺回了自身存在的权利和现代人的自我意识。
这是人类精神——确切说是文艺复兴精神——从“影响的焦虑”走向自信的胜利传奇,也是古典人文理想的伟大再生。“人文主义的普遍原则”,克罗齐向我们指出,“无论是古代人文主义(西塞罗是其伟大范例),还是14—16世纪间在意大利繁荣的新人文主义,或是其后所有产生或人为地尝试的人文主义,都在于提及过去,以便从过去中为自己的事业和行动汲取智慧”,即“采用模仿观念并把过去(它所钟爱的特殊过去)提高到模式高度”,然而“人文主义含义上的模仿,不是简单的复制或重复,而是一种在改变、竞争和超越时的模仿”,也就是从无到有而后来居上的创造。事实上,这正是维达、杜贝莱、明图尔诺、锡德尼、瓜里尼等文艺复兴人理解认同的模仿精神,而他们的主张又与古人和前人——从但丁到朗吉努斯、贺拉斯——的观点不谋而合并遥相呼应。我们甚至在西方人文曙光初现的时刻即看到了这一精神的自我表达:
这种不和女神有益于人类:陶工厌恶陶工,工匠厌恶工匠;乞丐妒忌乞丐,诗人妒忌诗人。(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第24—26行)
赫西俄德所说的同行间的厌恶和妒忌,即古希腊西方文明的核心精神——竞争的又一表述。与同类“竞争”的目的,用荷马的话说是“追求卓越”,今人所谓“做好的自己”,而用德尔菲神谕作者的话说则是“认识你自己”,即寻求自我实现。彼特拉克的焦虑——历史证明这一焦虑提供了自我超越的动力并终转化为审己知人的自信——正是这一古典精神的再现和新生。通过这一精神,彼特拉克成为了“文艺复兴之父”和人文主义“位伟大代表”;也正是通过这一精神,文艺复兴成就了自身的辉煌。
尽管这一辉煌在今天已经暗淡消退——从现代科技应许的伟大前程和光明之境回望,这一辉煌甚至成为人类未来世界的一道阴影。然而,正是这一挥之不去的阴影赋予其历史的纵深而印证了此在的真实。所谓“潜虽伏矣,亦孔之昭”,人类之“奥伏赫变”在是:不知此者不足以言人文,更不足与论人类的未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