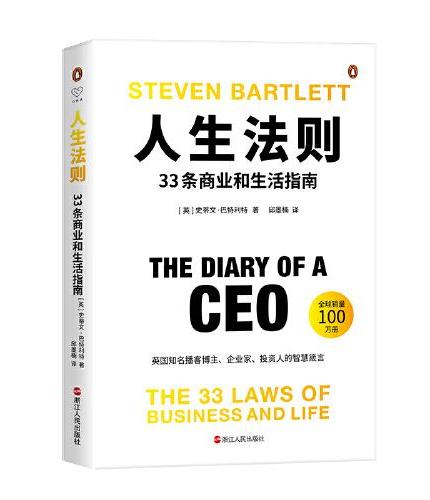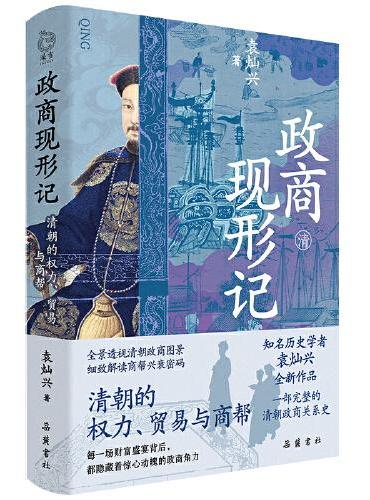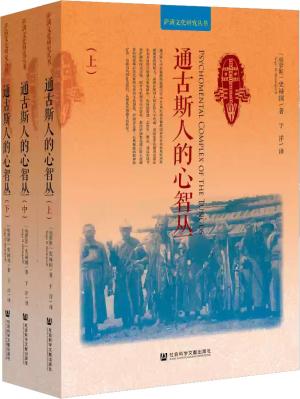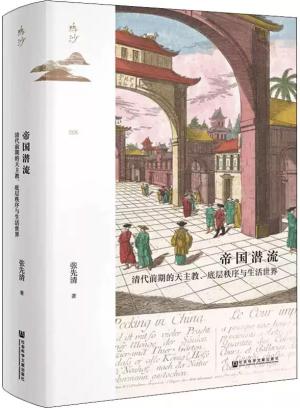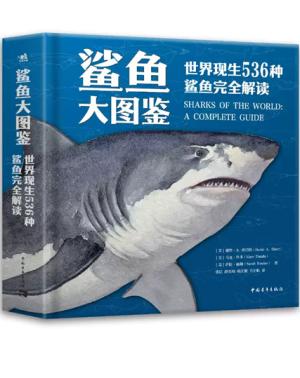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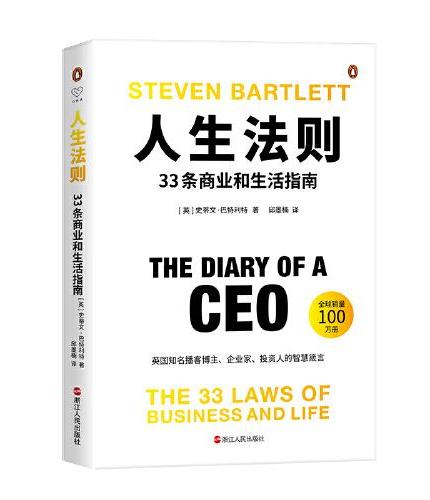
《
人生法则:33条商业和生活指南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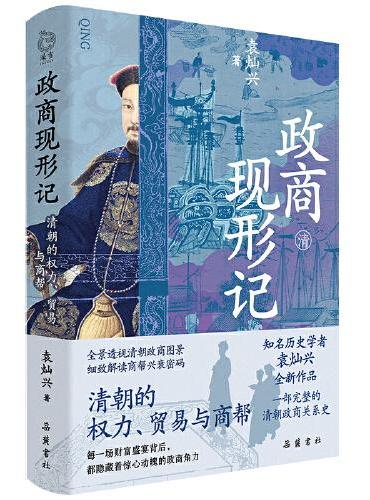
《
政商现形记: 清朝的权力、贸易与商帮
》
售價:HK$
85.8

《
早期干预丹佛模式辅导与培训家长用书
》
售價:HK$
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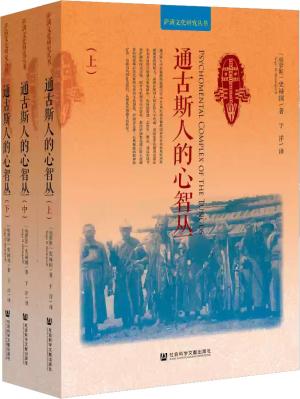
《
萨满文化研究丛书——通古斯人的心智丛(全三册)
》
售價:HK$
3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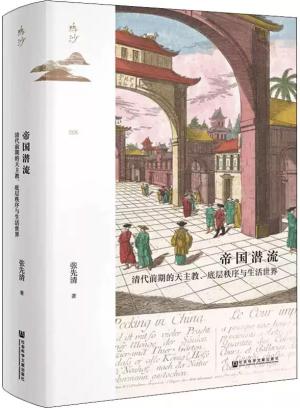
《
帝国潜流:清代前期的天主教、底层秩序与生活世界
》
售價:HK$
1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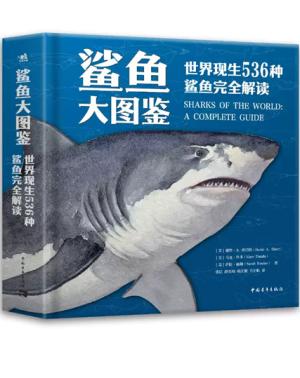
《
鲨鱼大图鉴:世界现生536种鲨鱼完全解读
》
售價:HK$
469.6

《
佛教与晚唐诗(修订本)
》
售價:HK$
55.0

《
大模型智能推荐系统:技术解析与开发实践
》
售價:HK$
141.9
|
| 內容簡介: |
“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持久、*著名的特色栏目。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三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且并非为配合作家某本新书的出版而作,因此毫无商业宣传的气息。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之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即成为传奇,足可谓“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
经《巴黎评论》授权,我们从“作家访谈”栏目中挑选了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六十余位受访作家的访谈,分四卷陆续出版。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收录的受访作家包括如下十六位:卡波蒂、海明威、亨利?米勒、纳博科夫、凯鲁亚克、厄普代克、马尔克斯、雷蒙德?卡佛、米兰?昆德拉、罗伯-格里耶、君特?格拉斯、保罗?奥斯特、村上春树、奥尔罕?帕慕克、斯蒂芬?金、翁贝托?埃科。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收录的受访作家包括如下十六位:E.M.福斯特、弗朗索瓦丝?萨冈、奥尔德斯?赫胥黎、哈罗德?品特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E.B.怀特、巴勃罗?聂鲁达、约翰?斯坦贝克、库尔特?冯内古特、胡里奥?科塔萨尔、唐?德里罗、苏珊?桑塔格、伊恩?麦克尤恩、诺曼?梅勒、大江健三郎。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收录的受访作家包括如下十五位:威廉?斯泰伦、T.S.艾略特、埃兹拉?庞德、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约瑟夫?海勒、卡洛斯?富恩特斯、菲利普?罗斯、约翰?欧文、多丽丝?莱辛、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托妮?莫里森、阿摩司?奥兹、V.S.奈保尔、石黑一雄。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4》是该系列的*一辑,共收录以下十四位作家的长篇访谈:格雷厄姆?格林、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W.H.奥登、乔伊斯?卡罗尔?欧茨、E.L.多克托罗、威廉?特雷弗、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艾丽丝?门罗、若泽?萨拉马戈、萨尔曼?鲁西迪、哈维尔?马里亚斯、大卫?格罗斯曼、大卫?米切尔、米歇尔?维勒贝克。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5》是该系列的*一辑,共收录以下十六位作家的长篇访谈: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威廉?福克纳、伊夫林?沃、让?科克托、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伯纳德?马拉默德、詹姆斯?M. 凯恩、田纳西?威廉斯、纳丁?戈迪默、詹姆斯?鲍德温、V.S. 普里切特、普里莫?莱维、理查德?福特、伊斯梅尔?卡达莱、莉迪亚?戴维斯、达尼?拉费里埃。
|
| 關於作者: |
“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持久、著名的特色栏目。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三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且并非为配合作家某本新书的出版而作,因此毫无商业宣传的气息。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之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即成为传奇,足可谓“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
|
| 目錄:
|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4》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5》
|
| 內容試閱:
|
|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巴黎评论》:在某个地方你曾谈到小说作为一种完美的文学形式非常伟大,它是各门艺术之王。莫里亚克:我当时是在赞美我的商品,但是没有任何一种艺术比其他种类艺术更加高贵。只有艺术家才称得上伟大。托尔斯泰、狄更斯和巴尔扎克是伟大的,而不是他们所展示的文学形式。 威廉?福克纳:《巴黎评论》:有人认为你作品中太喜欢写暴力。福克纳:那就等于说木匠太喜欢用榔头。其实暴力也不过等于是木匠手里的一件家伙。光凭一件家伙,木匠做不成活儿,作家也写不出作品来。 伊夫林?沃:《巴黎评论》:这是不是说明您经常润色、经常实验?沃:实验?天呐,怎么可以!看看像乔伊斯这样的作家,就明白实验会有什么结果了。他一开始写得还不错的,然后你就看着他带着满心虚荣,写疯掉了。写到后来他就是个神经病。 让?科克托:《巴黎评论》:当你写作时,你会想到一个抽象的潜在读者或者评论者吗?科克托:你得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到内在的东西上。一个人一旦意识到受众,为了受众而履行职责,这是悲惨的,这是丑陋的。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巴黎评论》:我还有一两个问题。你认为你的医学课程以及科学学科对你的诗歌有何影响?威廉斯:科学家对诗人非常重要,因为他的语言对他很重要……当然,对诗人也很重要。我不想偏离主题太远,不过人们总是让我说话要准确些。 伯纳德?马拉默德:《巴黎评论》:真的有人能教……写作?马拉默德:你教的是写作者——多少表现出一点才华的那些。一开始,年轻的写作者只是倾倒出自己的才华,但并不太清楚那才华的本质。你要做的,就是拿起一面镜子,举到他们的作品前面,然后,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能看清自己展示或表露的东西。 詹姆斯?M. 凯恩:《巴黎评论》:阿尔贝?加缪对您写作的赞誉,您有何回应?凯恩:他写了些关于我的文字——其中多少也承认他的一本书是模仿我的书写的,他还尊称我为伟大的美国作家。可是我从没读过加缪……对于小说我并不无知,但读得很少。我不敢读小说,因为可能会太喜欢某个人的书! 田纳西?威廉斯:文化现状文学的重要地位已经被电视取代了,你觉得是不是?真是这样。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拥戴作家创作,或者给予他们很好支持的那种文化。我指的是严肃的艺术家。如今在百老汇他们只想要廉价的喜剧、音乐剧和重排剧。严肃作品想要制作出来都几乎毫无可能,即便出来,能演一个星期就算是幸运了。 纳丁?戈迪默:《巴黎评论》:所以你觉得你的写作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而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戈迪默:我不认为任何作家能说出他为什么选择这个或那个,或者怎么表现某个主题。它可能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你的生活到达了某一个阶段,你的想象力已经成熟,你就可以自然地写出来。 詹姆斯?鲍德温:《巴黎评论》: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白人的世界,那么是什么让你觉得写作还有任何意义?以及为什么写作是一个白人的世界?鲍德温:因为他们拥有这个生意。嗯,回想起来,归根结底是我不允许自己被其他人定义,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我鄙视那种把发生自己身上的事怪到别人头上的行为。这是我自己的责任。我不想要任何怜悯。 V.S. 普里切特《巴黎评论》:你有没有觉得生活和写作相互影响?普里切特:我一直认为生活和文学是相互纠缠的,而且这些纠缠正是我探索的。 普里莫?莱维:《巴黎评论》:人们曾经引用过海因里希?伯尔的一句话,关于德国人为什么能允许大屠杀的存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太守法了,他们听从法律。您也曾经说过,意大利人的一个特征是他们不遵守法律。莱维:是的。那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的主要区别。我们过去常说,法西斯的暴政因为我们对法律整体性的无视而得到缓和。当时就是这样。许许多多犹太人都因此得到拯救。当法律本身是恶时,不遵守法律是对的。 理查德?福特:《巴黎评论》:有些评论家说他们认为你是一个特别男性的作家。你这样看你自己吗?福特:我认为那是胡扯。虽然我的叙事者到目前为止都是男人,但主人公并不总是男人。我写女性人物的句子和写男性的一样好,更重要的是,在故事中给了她们平等的机会控制自己的命运,在现实生活中,也就是做强大的人。 伊斯梅尔?卡达莱:《巴黎评论》:这部小说被禁了。那你靠什么生活呢?因为,一旦没有了官方作家、作协会员的身份,你就什么都不能做。卡达莱:他们给我出书,接着又禁掉,轮番进行,不过一旦你有书出版,并且被承认是一个作家,那你就是作家协会的会员了,每个月会有薪水可拿,每个人都一样,不管是有天赋的还是冒牌货。那份薪水是我所售书籍得到的版税的千分之一。 莉迪亚?戴维斯:《巴黎评论》:你会有意识地计划去写一种故事而不是另外一种吗?还是说每个故事都是从直觉当中来的?戴维斯:我对提前计划好怎么写小说很警惕。几乎从无意外,它们都是从一个想法或一个句子开始的,然后我会立刻一头扎进去开始探索。如果我停下来去想,这个应该是人称复数,或者,这个应该是一个不分段的段落,或者诸如此类的,我觉得我会写不下去。它们都是直觉式的。 达尼?拉费里埃:《巴黎评论》:你所有书的主题都是希望边界消失。这也适用于种族吗?拉费里埃:在海地,根据我们的宪法,每个住在那里的人都是黑人(Negro)。所以没有问题。即使你是金发碧眼的日本人,如果你是海地国籍,你就是黑人。就是那样。我的一些读者可能把我看成黑人作家,但我在生命的头二十三年里并不是黑人。在独裁者的统治下,我们都是平等的……根据肤色来读我,就是不正确地读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