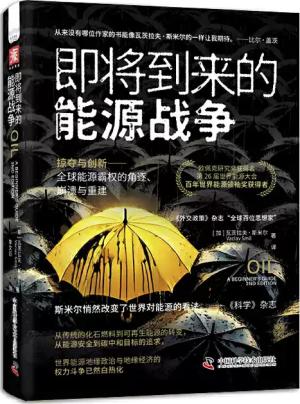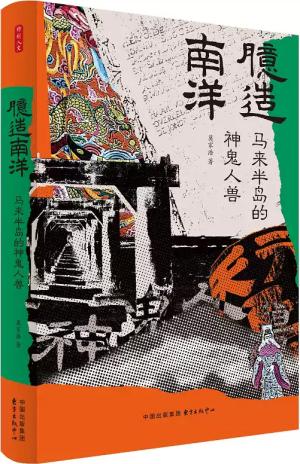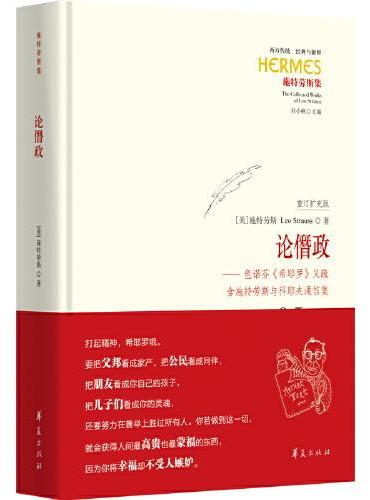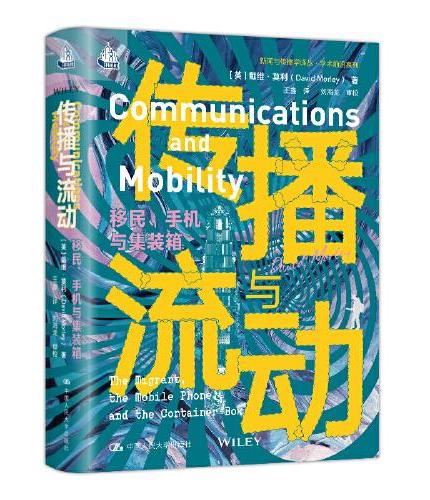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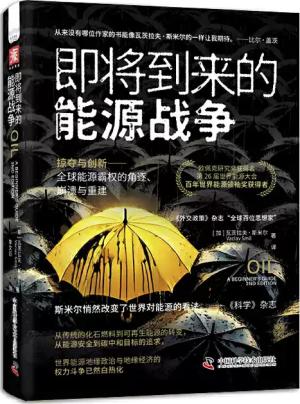
《
即将到来的能源战争
》
售價:HK$
8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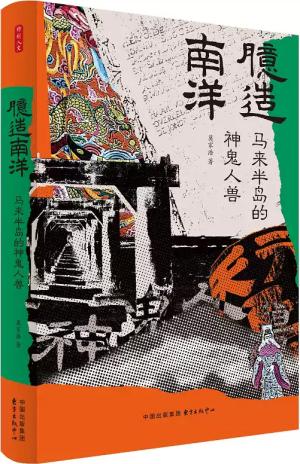
《
时刻人文·臆造南洋:马来半岛的神鬼人兽
》
售價:HK$
65.0

《
心智、现代性与疯癫:文化对人类经验的影响
》
售價:HK$
188.2

《
时刻人文·信用的承诺与风险:一个被遗忘的犹太金融传说与欧洲商业社会的形成
》
售價:HK$
103.0

《
同与不同:50个中国孤独症孩子的故事
》
售價:HK$
66.1

《
开宝九年
》
售價:HK$
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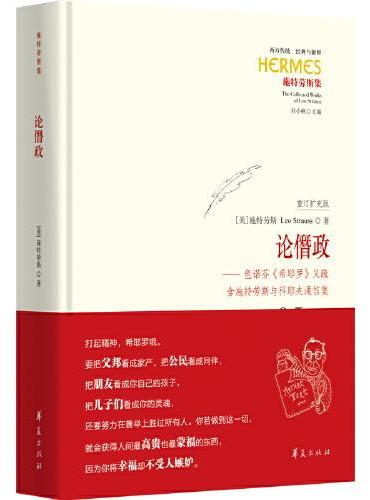
《
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含施特劳斯与科耶夫通信集)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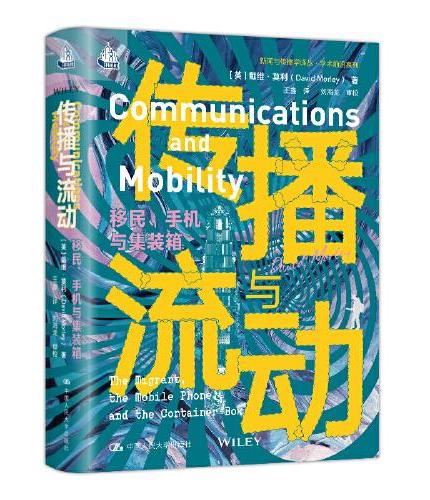
《
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学术前沿系列)
》
售價:HK$
109.8
|
| 編輯推薦: |
|
1959年《铁皮鼓》面世,标志着战后德语文学的崛起,鼓手奥斯卡从此在世界文学画廊中占有一席之地。
|
| 內容簡介: |
《铁皮鼓》是君特·格拉斯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奥斯卡生于1924年,三岁时目睹了成人世界的荒诞无聊,决定停止长高。他经历了“二战”带给波兰和德国的苦难,见证了纳粹的罪行。三十岁时,这个将现实敲入鼓声,将玻璃唱碎的人,在精神病院写下自己的生平和家族故事,他试图在其魔幻现实自传中证明,自己是充满假象、谎言和罪恶的世界中的特立独行者。
1979年,由施隆多夫执导的同名电影上映。该片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奥斯卡外语故事片奖。
|
| 關於作者: |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2015),德国作家、画家。生于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父亲是德国人,母亲为波兰人。1944年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后被关入美军战俘营。战后做过钾矿工、石匠学徒等,曾在杜塞尔多夫和柏林学习造型艺术,参加过爵士乐队。
1955年开始参加“四七社”活动,1956年出版诗集《风信鸡的优点》,1957年剧作《洪水》首演。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其代表作还有《猫与鼠》《狗年月》《比目鱼》《母鼠》《辽阔的原野》《我的世纪》等。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译者: 胡其鼎(1939—2013),德语文学翻译家,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审。译有黑塞的《彼得·卡门青德》《格特露德》《骏马山庄》,格拉斯的《铁皮鼓》等。
|
| 目錄:
|
目录
译本序
篇
肥大的裙子
木筏底下
飞蛾与灯泡
照相簿
玻璃,玻璃,小酒杯
课程表
拉斯普京与字母
塔楼歌声的远程效果
演讲台
橱窗
没有出现奇迹
耶稣受难日的菜谱
棺材一头小
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背脊
尼俄柏
有信有望有爱
第二篇
废铁
波兰邮局
纸牌屋
他躺在萨斯佩
玛丽亚
汽水粉
特别新闻
把昏厥带给格雷夫太太
七十五公斤
贝布拉的前线剧团
参观水泥——或神秘,野蛮,无聊
接替基督
撒灰者
耶稣诞生戏
蚂蚁大道
我该不该呢
消毒剂
在货运车皮里长个儿
第三篇
打火石与墓碑
北方幸运女神
四九年圣母
刺猬
衣柜里
克勒普
在椰棕地毯上
在洋葱地窖里
在大西洋壁垒或地堡不能同水泥分家
无名指
末班有轨电车或朝拜密封大口玻璃瓶
三十岁
|
| 內容試閱:
|
译本序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作家群中,非常重要的有三位。海因里希·伯尔,他的名字同“废墟文学”紧密相连,人们称他为“小人物的兄弟”。一九七一年,他的长篇小说《女士及众生相》(又译《莱尼和他们》)问世,次年,他成为第六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人。伯尔的许多作品已经有了中译本,他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阿尔诺·施密特,这个名字在我国是比较陌生的,他被认为是德国的詹姆斯·乔伊斯,他的作品几乎是无法翻译的,然而,由于他的文学素养很高,很多德语作家都要读他的著作。这两位作家都已经去世,现在仍在从事创作活动的,就是君特·格拉斯了。《铁皮鼓》是他的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发表至今已近四十年了,在世界文坛已有定评。一九八七年年初,当译者终于完稿搁笔之时,建设出版社也预告这部小说即将与民主德国的读者见面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四七”社在阿尔高伊的阿德勒饭店聚会。“四七”社是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既无纲领,也不发会员证,在作家汉斯·韦尔纳·里希特的主持下,每年聚会一次,作家们在会上朗读各自的新作,当场听取评论,该社就以这种方式来推动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发展。从一九五○年至此,“四七”社共评过五次奖,获奖者是君特·艾希、海因里希·伯尔、伊尔泽·艾兴格尔、英格博格·巴赫曼和马丁·瓦尔泽。这一次聚会时,来了一位年轻人。他来了,朗读了,胜利了。君特·格拉斯,他从巴黎到此地,来时囊中无几,他朗读了长篇小说《铁皮鼓》的章《肥大的裙子》,与会者一致认为,这部作品生动、感人、清新,并同意授予他“四七”社奖(三千马克)。次年秋季,格拉斯同他的《铁皮鼓》一起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露面。这部小说的七种外文译本的版权已被买去。就在这一年,联邦德国的图书市场上还出现了一批长篇小说:乌韦·约翰逊的《雅各布的揣测》、海因里希·伯尔的《九点半打台球》、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面包和运动》、鲁道夫·哈格尔施坦格的《众神的玩物》、奥托·弗里德里希·瓦尔特的《哑巴》、格哈德·茨韦伦茨的《死去的男人们的爱》等。在此之前,文坛的中心议题是长篇小说的危机,而此时,连外国通讯社也报道说,联邦德国的“文学也进入了繁荣时期”。
君特·格拉斯,一九二七年生于但泽。这是一个海港城市,有着多灾多难的历史。但泽曾属汉萨同盟,后归波兰。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时,又划归普鲁士。次大战后,改为自由邦,由国际联盟代管。纳粹德国又以“但泽走廊”问题为借口入侵波兰,点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战后,但泽划归波兰,今名格但斯克。格拉斯的父母,一方是德意志人,一方是波兰人。一九四四年,他被征入伍,当空军辅助人员,同年受伤。一九四六年,当他从马利恩巴德的美军战俘营获释时,他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因为被划给苏联和波兰等的德国东部土地上的德国人都被驱赶了。格拉斯先在希尔德斯海姆的钾盐矿当矿工,接着到哥廷根打算通过中学毕业考试,但一上历史课他就反感,终于放弃。一九四七年他到杜塞尔多夫学习石匠手艺。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在当地艺术学院学习,兼当模特儿并在一个爵士乐队演奏。一九五三年他迁到西柏林,继续学习雕塑与版画。一九五五年,他的《幽睡的百合》获斯图加特电台诗歌比赛头奖。次年,他的部诗集《风信鸡的优点》出版,他举家迁居巴黎。这是一段艰辛的岁月:
我的房间无风
虔诚,一支香烟
如此神秘,谁还敢
提高房租
或者打听我的老婆。(《信经》)
他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幢后排楼房里。卢赫特汉德出版社给他每月三百马克的津贴,让他维持起码的生活并写作剧本。长篇小说《铁皮鼓》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格拉斯说,他当时连德语的正字法都还没有完全掌握。
一九五九年底,不来梅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决定授予格拉斯奖金,但不来梅市政府不予承认,表面的理由是《铁皮鼓》亵渎上帝、有伤风化,真正的原因是认为这个小胡子作家是个“有头脑的无政府主义者”,亦即对当时的阿登纳政府持有不同政见。市行政当局干涉独立评奖委员会事务被公众舆论目为一件丑闻,这自然也未能阻止这部小说赢得更多的读者并被译成更多的语言。一九六○年德意志评论家协会授予格拉斯文学奖,一九六二年他又获得法国的文学奖。《铁皮鼓》初版后的四年间,给格拉斯带来了四十万马克的收益,使这位“经济奇迹”时期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成了“经济奇迹”的受益者。
一九六○年,格拉斯定居西柏林。他的一些剧本,如《恶厨师》(1961)等先后上演,第二部诗集《三角轨道》(1960)出版,接着,他的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长篇小说《狗年月》(1963)相继问世,尤其是后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卢赫特汉德出版社把这两部作品同《铁皮鼓》一起改版重印时,经作者同意后加上了“但泽三部曲”的副标题。因此,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三部曲”。这三部小说各自独立,故事与人物均无连续性,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部分情节发生的地点都在但泽。格拉斯说,它们有四个共同点:一是从纳粹时期德国人的过错问题着眼写的;二是地点(但泽)和时间(1920至1955年)一致;三是真实与虚构交替;四是作者私人的原因:“试图为自己保留一块终失去的乡土,一块由于政治、历史原因而失去的乡土”(1970年11月28日在西柏林同亨里·普拉尔德的谈话)。所以,这三部小说是格拉斯怀着一个有着德、波两种血统却又失去家乡的难民的心情写的。这种心情同战后德波间领土问题一样复杂。民主德国在一九五○年即已承认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为德波边界,联邦德国则直至一九七○年十二月同波兰签订《华沙条约》时才予以承认并确认德波两国间无领土争端。当时,格拉斯是勃兰特总理的“东方政策”的拥护者。
一九四七年初,在一片废墟的汉诺威的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上,格拉斯听了社会民主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的讲演。格拉斯说,舒马赫的“狂热和他的生硬一方面使我感到抵触,另一方面,他的论证的正确又使我信服”(同普拉尔德的谈话)。他从次参加选举起,就投社会民主党的票。一九六○年,格拉斯回到西柏林时,正值威廉·勃兰特首次作为候选人竞选总理。一九六一年,阿登纳在雷根斯堡讲演,影射勃兰特是非婚所生。格拉斯被这种人身攻击所激怒而全力支持勃兰特。他就此成为勃兰特的好友,并从一九六五年起的几次大选中作旅行讲演,为社会民主党竞选。在阿登纳任总理的时期内,社会风气是不问政治而只关注福利与消费。作家和知识分子只要安分守己,就可能得到各种奖金。“四七”社和后来的“六一”社(以提倡劳工界文学为宗旨)的作家们则关注着一个问题:民主(Demokratie)的本义是人民的统治(Volksherrschaft)。公民难道可以放弃责任,放弃监督的权利,而把国家的祸福交给少数决定政策的职业政治家去掌握吗?当这些作家或其他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社会联盟和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的政策发表歧见的时候,当他们对德国的重新武装、单方面同西方结盟、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的分裂以及后来的紧急状态法公开提出指摘的时候,他们会立即遭到当政者的鄙视和辱骂。格拉斯就是一例。阿登纳的后任、“经济奇迹”总理艾哈德公开把格拉斯、霍赫胡特等作家骂作“”(一种小犬),说他们只晓得“朝荆棘上蹦”(“螳臂当车”之意)。艾哈德的后继者基辛格总理也扬言,在魏玛共和国还有左中右文学,在联邦德国却只有左翼文学,这种文学“不能代表”德国。这就是当时政界与文学界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格拉斯开始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他不仅同勃兰特建立了友谊,而且也明确了他本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他把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观点——相信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改革来争取所有公民限度的平等——同启蒙运动的精神——呼吁公民的理智,使之树立社会责任感——结合起来。他对一系列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都发表意见。他的意见表明,他“站在了几条板凳中间”,左右不讨好。他反对国内的“紧急状态法”(1968)、“教权主义”“反动的同盟政策”,也反对民主德国建立柏林墙;他批评美国(如印度支那战争、支持希腊军人独裁政府),他抨击右派施普林格报系的《图片报》,也抨击左派的杂志《重音》;尤其因为他对大学生运动的态度,他被蓄长发的青年目为头号敌人。格拉斯理解青年一代的愤怒与抗议,但认为他们想通过一次性的革命造反来一劳永逸地改变一切的看法是乌托邦。鉴于当时的社会动乱,联邦议院通过了紧急状态法。对此持反对态度者联想到了魏玛共和国的危机。那时,刚上台任总理的希特勒便是利用紧急状态法取缔了纳粹党之外的一切政党,建立了独裁政权。这些人因此也担心大学生过激的行动会导致当局采取更严格的警察控制措施而有害民主制。这也是格拉斯的考虑。他的诗集《追问》(又译《盘问》)(1967)、言论集《论不言而喻》(1968)和长篇小说《局部麻醉》(1969)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观点。格拉斯认为,谁要承担责任和过错,谁就得有理智。他呼吁青年人的理智,使社会保持“正常状态”而不是“非常状态”,只有在“正常状态”下才有可能实现渐进的改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修正”。他在写给自己的子女们的散文《蜗牛日记》(1972)里进而申述了他的这种观点。一九七一年,格拉斯在纽伦堡讲话中说:“唯有看到和重视进步中的静止的人、已经有一次或多次停步不前的人、曾经在蜗牛壳上坐过并在乌托邦阴影一侧居住过的人,才能衡量出进步。”他的不要革命只要“修正”的观点,在激进的青年一代看来,自然是十分“保守”的。
.......
肥大的裙子
供词: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我的护理员在观察我,他几乎每时每刻都不让我离开他的眼睛;因为门上有个窥视孔,我的护理员的眼睛是那种棕色的,它不可能看透蓝眼睛的我。
因此,我的护理员根本不可能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喜欢上他了。这位门后窥视者一跨进我的房间,我就向他讲述我一生中的事件。这样一来,尽管有窥视孔的阻隔,他仍然可以了解我。看来,这个好人欣赏我所讲述的故事,因为每当我给他讲了点编造的故事时,他就给我看他编结的形象,以表示感激。他是不是一个艺术家,可以暂且不去讨论。可是,如果用他的创作办一个展览的话,新闻界定会给予好评,也会吸引来一些买主。他用普通的包扎用的线绳编结,线绳是在探望时间过后在他所护理的病人房间里收集来的,经过整理,编结出多层次的软骨鬼怪,随后把它们浸在石膏里,使之僵化,再插上针,固定在木头底座上。
他经常转念头,想创造出五颜六色的作品来。我劝阻他,指着我的白漆金属床,请他想象一下,这张完善的床如果涂成五颜六色,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呀。他一听这话,惊恐地把护理员的双手伸到脑袋上方猛地击掌,力图在他那张过于呆板的脸上同时露出各种恐惧的表情来,并且放弃了他的涂彩色计划。
因此,我那张白漆金属架病床乃是一种准则。对于我来说,它甚至还不只如此:我的床是我终达到的目的地。它是我的安慰,还可能成为我的信仰,如果疗养院管理处允许我做一些改变,让人把床栏杆升高,使任何人都不得过于接近我的话。
每周一次的探望日,打断了我在白漆金属床栏杆之间编织起来的寂静。到了那一天,他们全都来了,那些要救我的人。他们以爱我来自娱,想通过我来珍视、尊重和认识他们自己。他们是多么盲目,多么神经质,又多么没有教养。他们用手指甲刮我的白漆床栏杆,用圆珠笔和铅笔在白漆上乱涂不正派的长线条小人。我的律师每次“哈啰”一声闯进病房来后,就把他的尼龙帽挂在我左脚跟的床柱子上。在他来访的时间里——当律师的话又特别多——他就用这种强暴行为剥夺了我精神上的平衡和欢畅。
来探望我的人们,把礼物放在那幅银莲花水彩画下铺蜡布的小白桌上,把他们正在实行的或者已经盘算好的搭救计划告诉我,并且说服我,说服他们不倦地设法搭救的这个人,高度相信他们的博爱精神。在这之后,他们又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生存的乐趣,便离我而去。他们一走,我的护理员便来开窗通风,同时收集捆扎礼物的线绳。通完风以后,他经常还能找到时间,坐在我的床边,解开线绳的结,整理好,让寂静扩展开去,直到我把寂静叫做布鲁诺,把布鲁诺叫做寂静。
布鲁诺·明斯特贝格(我现在讲的是我的护理员的姓名,而不是在做文字游戏),籍贯绍尔兰,未婚,无子女。他给我买过五百张打字纸,钱挂在我的账上。我储存的纸张还不够,便又让布鲁诺再到兼卖儿童玩具的小文具店去一趟,替我买没有横格的纸,给我提供必要的场地,以便施展我的记忆力。啊,但愿我的记忆力准确无误!这件事我从来不托那些来探望我的人去办,不论是律师还是克勒普。仁爱之心使朋友们为我担忧,给我定下种种规定,仁爱之心也肯定禁止他们干这类危险的事情,例如带给我空白纸张,好让我用以录下我头脑里分泌出来的不连贯的音节。
“喂,布鲁诺!”我对他说,“你能替我买五百张清白的纸吗?”布鲁诺抬头望着天花板,要找出一个譬喻来,他的食指也指着同一个方向,然后回答说:“您的意思是白纸,奥斯卡先生。”
我坚持用“清白”这个字眼,还要求布鲁诺到了店里也这么讲。傍晚时,他买了一包纸回来,还想要我觉得他真像个若有所思的布鲁诺。他几次三番抬起头来,久久地凝视天花板,从那里汲取了他所需要的全部灵感,稍后才说出这么几句话来:“您向我推荐了那个恰当的字眼。我向女售货员要清白的纸,她给我去取之前,就羞得满脸通红了。”
我害怕没完没了地谈论文具店里的女售货员们,后悔自己不该把纸称为“清白”,因此保持沉默,一直等到布鲁诺离开病房,这才打开五百张打字纸的纸包。
我把这种柔韧的纸拿在手上,掂量的时间并不太长。我取出十页,把其余的保存在床头柜里,又在抽屉里的照相簿旁边找到了钢笔,钢笔是灌满了的,墨水也不缺少,那么,我从何写起呢?
一则故事,可以从中间讲起,正叙或者倒叙,大胆地制造悬念。也可以来点时髦,完全撇开时间与空间,到末了再宣布,或者让人宣布,在后一刻,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可以开宗明义地声称,当今之日,写长篇小说已无可能,然后,譬如说,在自己背后添上一个声嘶力竭的呐喊者,把他当作后一个有可能写出长篇小说的作者。我也听人讲过,若要给人好印象,谦虚的印象,便可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不再有长篇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了,因为有个性的人已不复存在,因为个性已经丧失,因为人是孤独的,人人都同样孤独,无权要求个人的孤独,因此组成了无名的、无英雄的、孤独的群体。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可能有它正确可信的地方。可是,就我,奥斯卡,和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而言,我敢说,我们两人都是英雄,完全不同的英雄。他在窥视孔后面,我在窥视孔前面;如果他打开房门,我们两个,由于既有友谊又很孤独,因此仍然构不成无名的、无英雄的群体。我将从自己出世以前很远的时候写起;因为一个人倘若没有耐心,在写下自己存在的日期之前,连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想去回忆的话,他就不配写自传。所以,我要向不得不在我所居留的疗养与护理院外面过着混乱不堪的生活的诸君,向每周来探望我一次的、根本想不到我会储存纸张的诸位朋友,介绍一下我奥斯卡的外祖母。
我的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在十月某一天傍晚的时候,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坐在一块土豆地的地边上。如果在上午,你就能看到我的外祖母如何熟练地把枯萎的土豆秧整整齐齐地归成堆。到了中午,她便吃涂糖汁的猪油面包,接着,掘后一遍地,末了,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坐在两只差不多装满土豆的篮子中间。她的靴底同地面构成一个直角,靴尖差一点碰到一起,靴底前闷烧着一堆土豆秧,它间或像哮喘似的冒出一阵阵火苗,送出的浓烟,与几乎没有倾斜度的地壳平行,局促不安地飘去。那是一八九九年。她坐在卡舒贝地区的心脏,离比绍不远,更靠近拉姆考与菲尔埃克之间的砖窑,面对着迪尔绍与卡特豪斯中间通往布伦陶的公路,背朝着戈尔德克鲁格的黑森林。她坐着,用一根烧焦了的榛木棍的一端,把土豆捅到热灰下面去。
我在上文特别提到了我的外祖母的裙子,说她穿着几条裙子坐在那里,我希望这已经点得够清楚的了。我甚至把这一章冠以“肥大的裙子”的标题,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应当如何感激这种衣裳。我的外祖母不仅穿一条裙子,她套穿着四条裙子。你不要以为她穿了一条裙子和三条衬裙;她穿着四条裙子,一条套一条,并且按照一定的顺序,每天里外倒换一次。昨天穿在外面的,今天变成第二层,昨天在第二层的,今天到了第三层。昨天的第三层,今天贴身穿着。昨天贴着皮肤的那一条,今天可以让别人看到它的式样,或者说,看到它根本没有式样。我的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的裙子都偏爱土豆色。这种颜色必定同她相称。
除去这种颜色以外,我外祖母的裙子的特点是尺寸宽大,过分地浪费衣料。它们圆墩墩的,风来时,似波浪翻滚;风吹到时,倒向一边,风过时,噼啪作响;风从背后吹来时,四条裙子一齐飘扬在我外祖母的前头。她坐下来时,四条裙子便聚拢在她的周围。
除去这四条经常蓬松一团、下垂着、起皱褶,或者硬撅撅、空荡荡地挂在她床头的裙子而外,我的外祖母还有第五条裙子。这一条同另外四条土豆色裙子毫无区别。这第五条裙子并非永远排行老五。同它的弟兄们一样(因为裙子是阳性名词),它也得服从轮换的需要,并且同它们一样,如果轮到它的话,那便是在第五天星期五,它就被扔进洗衣桶里,星期六晚上被挂到厨房窗前晾衣服的亚麻绳子上,晾干了以后,又被放到熨衣服的木板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