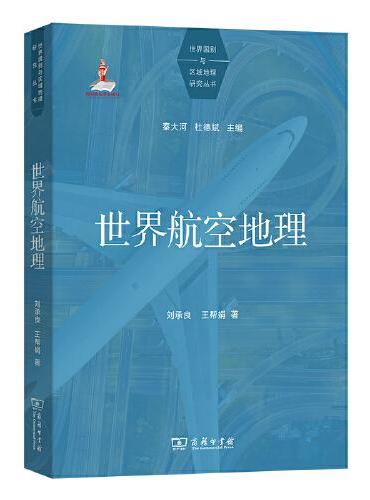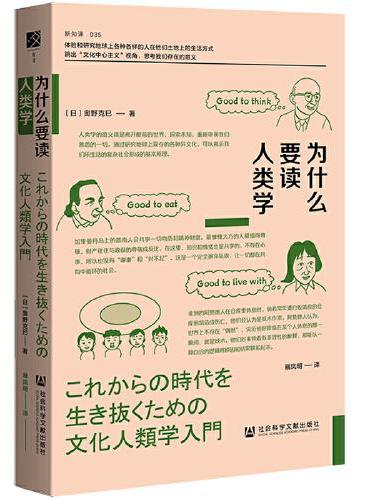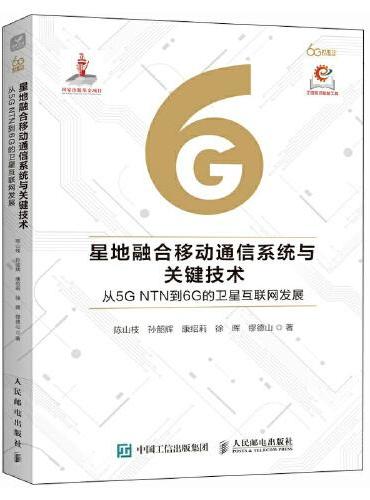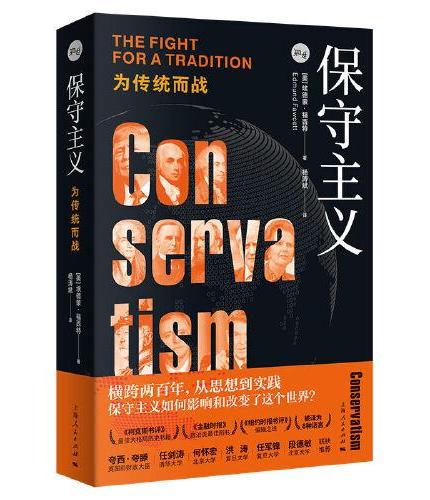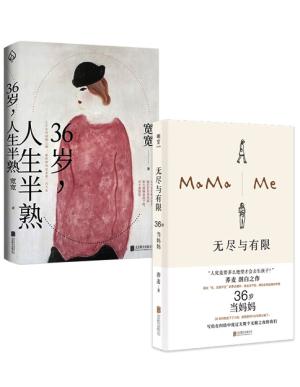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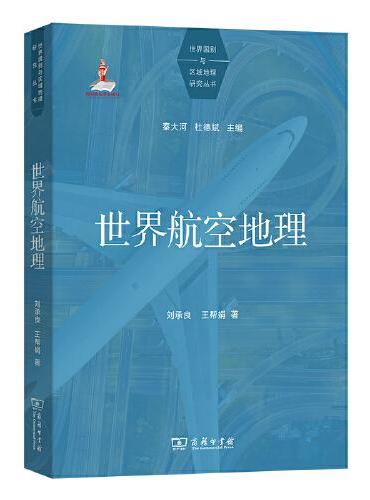
《
世界航空地理(世界国别与区域地理研究丛书)
》
售價:HK$
244.2

《
学术的中心:英法德美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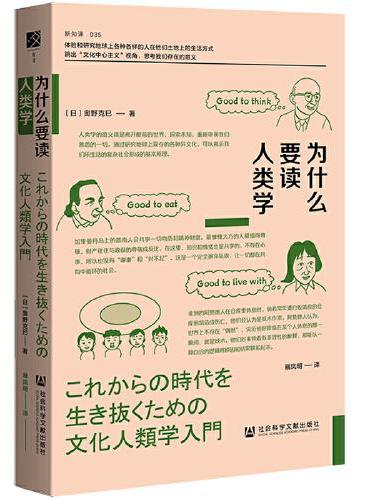
《
为什么要读人类学
》
售價:HK$
77.3

《
井邑无衣冠 : 地方视野下的唐代精英与社会
》
售價:HK$
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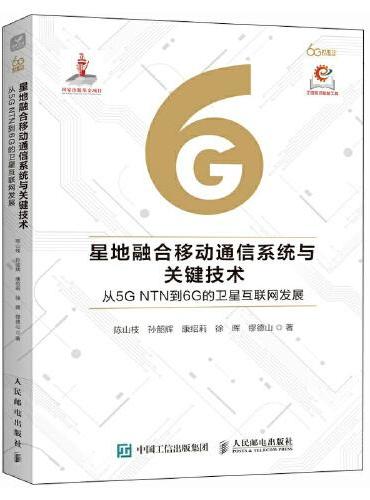
《
星地融合移动通信系统与关键技术从5G NTN到6G的卫星互联网发展
》
售價:HK$
212.6

《
妈妈,你好吗?(一封写给妈妈的“控诉”信,日本绘本奖作品)
》
售價:HK$
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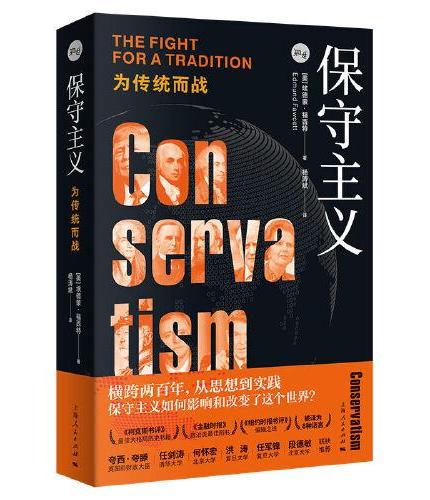
《
保守主义:为传统而战
》
售價:HK$
15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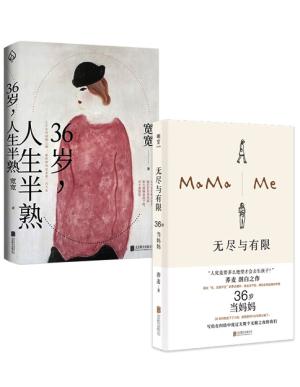
《
不同境遇的36岁:无尽与有限+人生半熟
》
售價:HK$
112.0
|
| 編輯推薦: |
陈年喜新作,现实版《活着》,易中天感动推荐。--卑微如尘,也要热烈地活着;
作者入选《南方人物周刊》2021魅力人物”100张中国脸”
堪称中国文坛”六边形”作家,经历、情绪、思想、表达、结构、张力,丝丝入扣,宛如神作;
收录故事21篇,刻画50余位人物画像:爆破工、运石工、乡村木匠、农夫、农妇、小作坊老板、民谣歌手……从地下5000米到地上3000米,从北疆大漠到秦岭山川,从一地霜白到内心波澜,芸芸众生之于时代,仿佛一粒粒微尘散落。
粗粝之中饱含深情,白描式简洁却极具电影画面感,一个个鲜明的形象,一幕幕棱角分明的人间悲喜剧,一个时代的生存见证。
《人民日报》《南方周末》《GQ报道》《澎湃新闻》《腾讯新闻》《吴晓波频道》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
| 內容簡介: |
我见过的不幸太多了,从来没有沮丧过。
--陈年喜
这本书收录了陈年喜21篇非虚构故事。
书中写了一群平凡而朴素的劳动者。
他们是爆破工、运石工、乡村木匠、农夫、农妇、小作坊老板……
而作家自己的故事,贯穿始终:在地下五千米开山炸石,在烟尘和轰鸣中养家糊口,在工棚和山野中写下诗篇,记录命运的爆裂和寂静。
他们虽历经生活的磨砺,却淳朴而硬扎,沉静地诉说关于亲情、爱情、死亡、欲望的生活主题……
这是一本生命的书,也是死亡的书,归根到底,是一本生活的书。
世界是什么样子?生活是什么样子?我的感觉里,除了绵长、无处不在的风,其余都是尘埃,我们在其中奔突,努力站稳,但更多的时候是东倒西歪,身不由己。
|
| 關於作者: |
陈年喜:
生于1970年,陕西省丹凤县人。
曾从事矿山爆破工作十六年;
数百首诗歌及散文、评论文章散见《诗刊》《天涯》《散文》等刊;
2016年冬应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赴美诗歌交流;
获2016年届桂冠工人诗人奖;
2019年,出版诗集《炸裂志》;
2020年,受邀做客央视节目《朗读者》。
陈年喜高中毕业之后便外出打工,爆破工是他至今做过时间长的职业。
成长在秦岭脚下,从小浸酝于老家的秦腔、鼓书等传统文化,陈年喜将其视为自己的文学启蒙。
在矿山工作期间,陈年喜开始不间断写作,他灵感如泉涌,在炸药箱上、在岩石上、在床铺上,他笔下的诗篇和故事如泉水般源源不断地流淌而出。
2015年离开矿山后,陈年喜在贵州、北京等地辗转。
2020年,陈年喜确诊尘肺病。现在,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仍在继续写作。
|
| 目錄:
|
我的朋友周大明
那一年,在秦岭黑山
那场旷日持久的矿事
不曾远游的母亲
父亲这辈子
手术
陪读的日子
割漆的人
葫芦记
野猪凶猛
一九八七年的老腔
表弟余海
吃相凶猛的人
在苦盏
南地十年
用平板电脑写诗的人
北京的秋天
一位青年的球状生活
一路有你
小城里的文人们
一个人的炸药史
后记
|
| 內容試閱:
|
偶尔停电的时候,或者材料跟不上的时候,我就邀约大明翻过山头到那边打电话,给朋友,给家人,给见过和没见过面的人。从电话里,我们知道了有人走了,有人还在,有些人富了,有些人还在挣扎中,知道了不管人在不在,富了还是穷着,生活都在往前走。而它下一步走向哪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山下那遥远的灰蒙蒙的人烟集中地,就是陈耳镇,那里离我家乡不远了。我把我家的方向指给大明看,看得他唏噓不已。我知道,这唏嘘里也有他自己命运的悲愁。矿石选炼的结果非常有成效,老板三天两头下山卖金子,也三天两头给他加工资。大明也好久没有回家了。
这里是秦岭向东北的后余响,在离这里不到二十里远的苍珠峰群岭,余响戛然而止。这-段秦岭拔地而起,把陕豫分隔开来。向更远的地方看,苍山如涛,驼形的山影直铺到天际。眼前野草无涯,开着只有高海拔地方独有的小花,颜色纷杂,粉白、艳红,经久不败。向下的山路上骡队行走着,骡蹄得嚕,赶骡人的吆喝声像一支长长的歌调。
时间如奔马,不停蹄地跑着,跑过春,又跑过冬。一切,都落在它的后面,只有突然的不幸,比它更快。
二0O八年八月,再见到大明时,他整个人已经不行了,这时他已离开了矿洞,重新经营起家里的碾房。他瘦得皮包骨头,身材显得又高又弯。长期的浸化冶炼提金,氰化物与汞的毒性浸入他的身体,像一棵再也拔不出来的芦苇,根须扎满塘底。这是大多数炼金人无可逃避的一天,只是没有料到它来得如此凶猛,来得这么有力。我曾亲眼见过一头从山上下来渴极了的牛误饮了浸化池的水,一瞬间直挺挺地倒下,死不瞑目。
过度的虚弱,让他走路已十分困难,呼吸受阻,脸色发紫。家里十几年的积蓄已经花光,两个孩子辍学在家,所有的生活重担压向了他的妻子。这个善良的女人有一股单纯的坚强。对于无数女人来说,坚强不过是一种掩饰,只有大明的妻子不是。我去过她的老家,那是一段黄泛区的岸边,黄土无边,出产酸枣和流沙。
这期间,我辗转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喀什的叶尔羌河源头,一事无成。不得已,重新回到出发的地方,在一个叫大青沟的地方,再次找了一份活儿。此时,整个秦岭金矿发展形势早成明日黄花,有实力的老板们强强联手,开始了深部开采。坑口直接选择在村庄或公路边。高处的坑口十有八九枯竭停掉。我工作的工作面已经掘进到万米,上下班有专用三轮车接送。接近四十度的地热逼得工人们走马灯似的更换。我们每天在工作中,要喝下一塑料壶冷水才不致虚脱。
这个时候,大明家早已无矿加工,整个村子也难见转动的机器了。三台碾子的铁轮锈迹斑驳,碾池里的水一层红锈, 像铺上了一片破旧不堪的红绸。浓重的药料味依旧在,苍蝇也很少光顾。
挨到十月,大明终于撒手走了。那天我从矿上下来,从床上抱起他,像抱起一个婴儿。我闻到他身体里散发出一股苦杏仁的香味,淡淡的,刺鼻、沁心。在盖上棺盖之后依然不散,似乎是透过了厚厚木板渗漏了出来。
那天,村干部送来了五千元安抚费,用以安葬。可这么多年,大明他们上交了多少钱,只有天知道。
家里已经请不起像样的乐队,那天,纸钱零落,喇叭声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