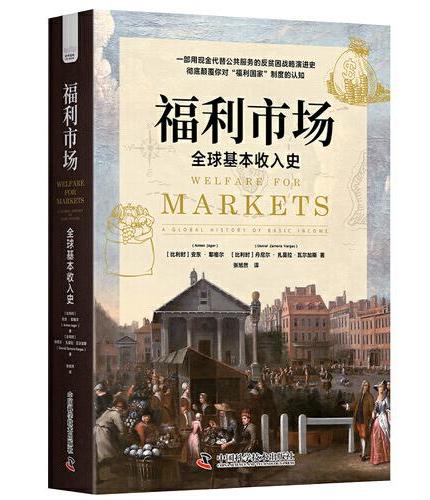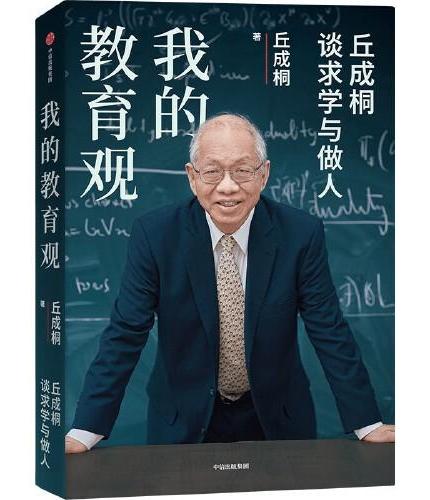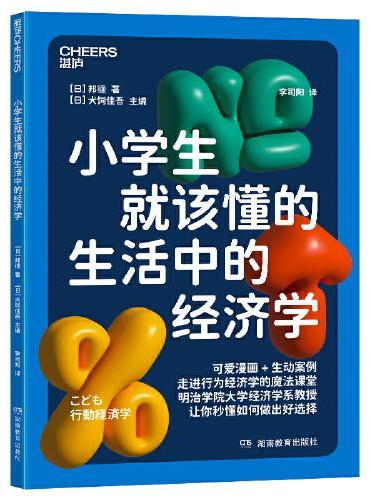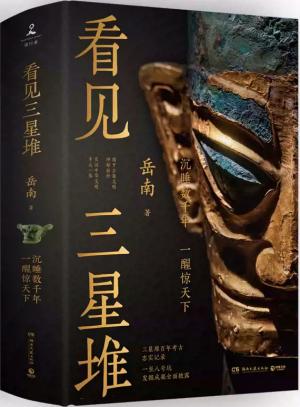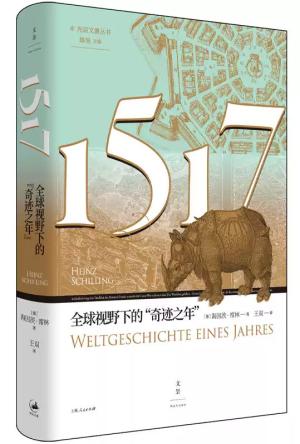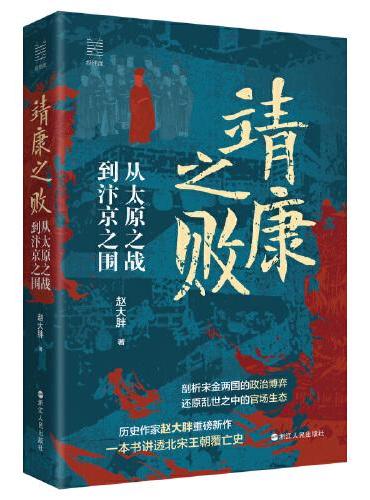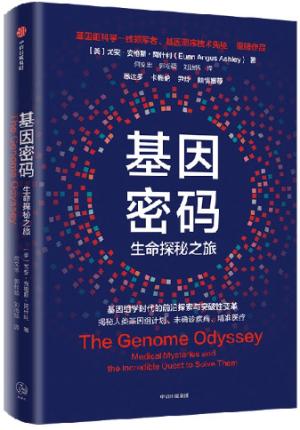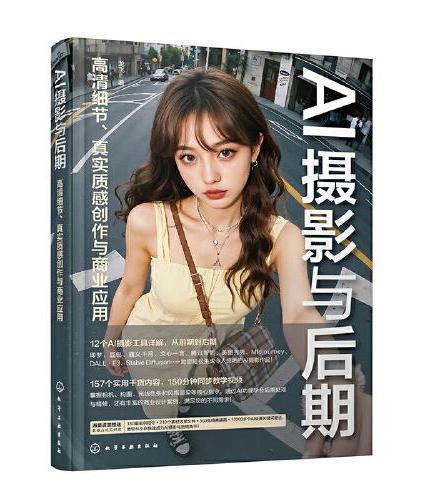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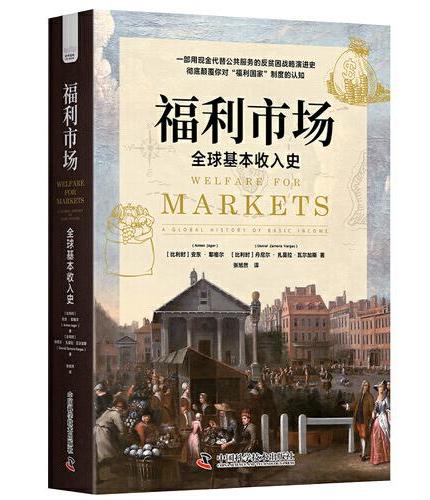
《
福利市场 : 全球基本收入史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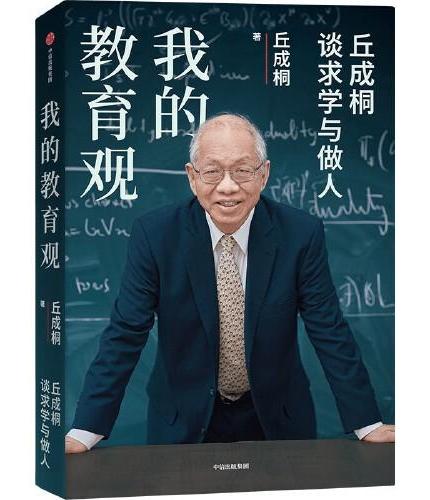
《
我的教育观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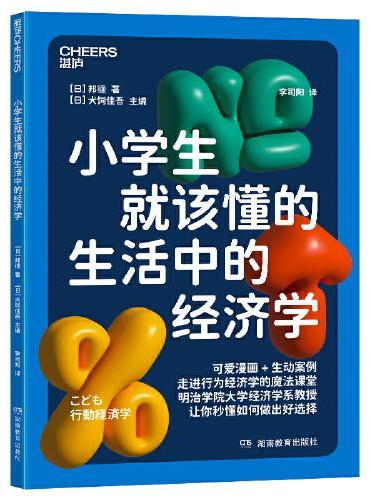
《
小学生就该懂的生活中的经济学
》
售價:HK$
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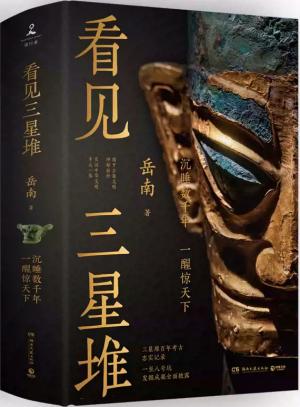
《
看见三星堆
》
售價:HK$
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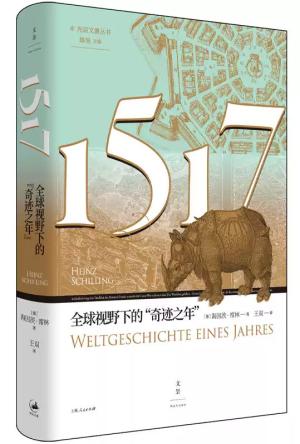
《
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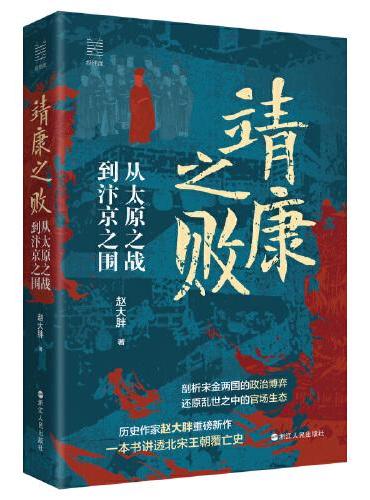
《
经纬度丛书·靖康之败:从太原之战到汴京之围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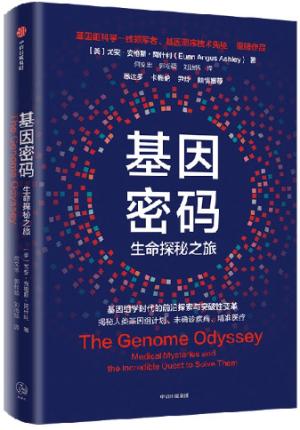
《
基因密码:生命探秘之旅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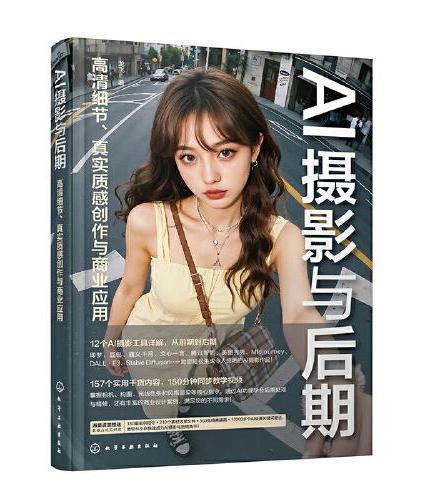
《
AI摄影与后期:高清细节、真实质感创作与商业应用
》
售價:HK$
107.8
|
| 編輯推薦: |
|
想要了解莫里亚克就要读《爱的荒漠》。全新译者,法语直译版,很好地保留了文中原有的意味,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法国文学的魅力。书中搭配精美插图,图文并茂,整体提升了阅读体验感。本书作为诺奖获得者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写作手法。小说通篇运用追叙、内心独白以及意识流的写作手法,把往事和现实巧妙地结合起来,写得哀婉动人,别开生面。在小说的后,莫里亚克还留下了光明的尾巴——家庭是一切的终归宿。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本探讨婚姻、爱情、家庭以及人性的小说。故事由主人公雷蒙·古雷热的回忆展开。他与父亲生活在优渥的中产阶级家庭里,被满屋子的人与事挤压出了厌倦感。他们一眼望见寸草不生的荒漠顺着生活的涸泽渐渐地浸蚀而来,于是踏着各自的节奏转身奔逃。不巧的是,他们爱上了同一个叫做玛丽亚·克罗丝的女人。然而,玛丽亚却没有选择他们俩中的任何一个。
镇上的人都传玛丽亚是个放荡的女人,却不知道她只是想找个可以依靠的港湾。至始至终她都在纯洁与罪恶之间、善与恶之间、幻想与现实之间踯躅徘徊。她曾在遇到雷蒙·古雷热时认为自己遇到了爱情,但是雷蒙对她的轻视让她逐渐认清了现实,再也无法让任何人走进她的内心。她虽然倍感孤独,但她仍认为温情的家庭也无法使她解脱孤独。
|
| 關於作者: |
【著】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ois Mauriac,1885年10月11日-1970年9月1日),法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32年任法国文学家协会主席;1933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1952年,其凭借《爱的荒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58年荣获法国国家荣誉勋章。
1970年莫里亚克去世时,戴高乐将军称其“代表了法国文学的精粹,是嵌在法国王冠上美丽的一颗珍珠”。
主要作品有诗集《握手》,小说《爱的荒漠》《给麻风病人的吻》《蛇结》等。
【译】尹永达
男,生于1979年,山东沂南人。法国波城大学文学博士、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天津市译协成员、曾任天津外国语大学法语系系主任。著有Idéographicité et plasticité、《法语描述辞典》等,并在中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地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
| 內容試閱:
|
死亡不会夺走我们爱的人,
相反,它替我们保留着,
将他们永远定格在可爱的青年时代:
死亡是盐,可以储存爱情,生命才会将爱情稀释。
章
多少年来,雷蒙 ? 古雷热一直希望能在路上再次见到那个叫玛丽亚 ? 克罗丝的女人,他热切地渴望着可以对她进行报复。有许多次,他在街上尾随某个女人,以为那正是他要寻找的女人。后来,岁月麻痹了他的怨恨。因此,当命运让他再次面对这个女人时,他一下子难以体味这次邂逅理应带给他的夹杂了愤怒的喜悦。
这天晚上,他走进杜佛路的一间酒吧时,刚到十点钟,里面只有领班一人在聚精会神地倾听混血爵士乐手的轻声哼唱。将近半夜时,情侣们开始在这狭仄的环境里顿足舞动,一台风扇跟只大苍蝇似的嗡嗡作响。门童惊讶地说:“先生,很少见您来这么早。”雷蒙也不说话,只摆手示意门童关掉这聒噪的风扇。神秘兮兮的门童想说服雷蒙“这套新设施,没风,却也能抽走烟”,但他终归是白费口舌。古雷热以一种异样的神情打量着他,门童只好往更衣间退去。于是,吊在天花板上的风扇沉默了,如同停落的黄蜂一般。
雷蒙 ? 古雷热,这位年轻人一时撞乱了酒吧里排列整齐、铺着洁白桌布的桌台。镜子里,他仿佛又看到自己狼狈时的模样,于是自问:“我到底是怎么了?”这显然是因为他向来讨厌虚度夜晚时光,而眼下这个晚上又要因为埃迪 ? H 这个畜生而虚度了。古雷热几乎使用了暴力,好不容易才把埃迪从家里揪到酒馆 儿去。
吃饭时,埃迪浑身都显得焦躁不安,屁股刚沾椅子沿儿,就已经心猿意马,寻思着接下来要找些什么乐子才好。他解释说自己由于偏头痛才会心不在焉。咖啡一喝完他就溜了,离开时的他带着一股子轻盈劲儿,涨红着耳朵,偾张着鼻孔,眼睛里充满了精气神。古雷热可是这一整天都在幻想如何与埃迪共度美好的夜晚,但是埃迪可能已经想到了比在酒馆儿互诉衷肠更加令人畅快的乐趣。
古雷热惊讶地发现,自己不仅感到失望和受了羞辱,还有些忧伤。他很诧异,自己竟然开始珍惜哪怕普通的朋友,这在他的人生中是件相当新鲜的事:沉迷于女色的他,直到三十岁时还无法做到对朋友应有的慷慨大方。古雷热一贯讨厌不该他占有的东西。如果是个馋嘴的孩子,他大概会说:“我只喜欢我能吃的东西。”那段时间里,他不过是拿哥们儿当成见证者和倾诉对象而已,朋友于他而言首先是一双倾听的耳朵。他也爱向自己证明他可以掌控他们、可以领导他们。他执迷于自己的影响力,为自己能有步骤地带坏别人而沾沾自喜。
如果他能把自己的欲望用在哪项事业上,如果不是他的个性使他放弃了眼下的快慰而另有追求,雷蒙 ? 古雷热会跟他的外科医生祖父、他的耶稣会士叔祖和他的医生父亲一样,拥有相当一批追随者。但是到了他这个年纪,只有触动人家的心灵才能奠定掌控者的地位,可是古雷热只能保证给信徒们限度的愉悦。而这些人中,年纪轻的又期待在同龄人里寻找默契。所以他的追随者越来越少。
其实在爱情方面,猎物历来都俯拾皆是,但是和我们同步开启人生的人群却逾年渐稀。经历了战争的砍旧伐陈,有的幸存者陷入婚姻的泥淖,有的则被职业生涯摧残得走了样儿。古雷热看到他们须发花白、腹凸顶颓,不由得恨他们竟与自己同龄。他埋怨他们葬送了青春,指责他们不等青春将他们遗弃便早早背叛了它。而他,则骄傲地把自己归入战后男孩儿那一代。
这天晚上,在尚嫌冷清的酒吧里,只有一架深沉的曼陀林在呜咽低吟(旋律的火苗时而熄灭、时而重燃,颤抖不已),他激动地望着镜子里自己这张顶着一头茂发的脸庞——这张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依然年轻的脸庞。他想到的是,衰老虽然没有侵蚀自己的身体,却已侵蚀了他的人生。听到女人们打听“这个大男孩儿是谁”时,他自然感到骄傲,可他也知道二十岁的小伙子们比女人们更敏锐,他们并不把雷蒙划入他们这个转瞬即逝的年轻人群体。
比起在嘈杂的萨克斯声里聊自己的事儿聊到天亮,这个埃迪或许有更有趣的事儿能做吧。不过,他也有可能只是在另一个酒吧里跟一个1904年出生的男孩儿倾吐心声呢,而这个1904年出生的男孩儿也会不停地附和他“我也是呢”或者“就跟我一样”。
年轻人开始涌入,他们特意为穿过大堂做出一副自负、傲慢的神态,却发现酒吧里寂寥无人,不免有些尴尬。他们聚拢在调酒师那里。古雷热向来无法容忍自己因为他人而痛苦,无论对方是情人还是哥们儿。他用自己的方式给自己做心理工作,说服自己埃迪 ?H 根本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他的抛弃让他心中泛起波 澜,这事压根儿就很滑稽。他从心里拔掉这根情绪的苗草时,很庆幸没有遇到任何根须的阻力。他甚至大胆地设想明天就把这个家伙清理出门户,并且毫不含糊地永不再见他。他决意“要将他扫地出门”时觉得轻松畅快。他长舒一口气,随后却发现胸中还是积着块垒,当然不是因为埃迪的缘故。对,是了,是因为他在
西装口袋里摸到了那封信……不用读第二遍,古雷热医生对儿子使用的言语一贯简洁、易记:
已入住巴黎大饭店,直至医学大会结束。早九点前、晚十一点后可见。
父
保罗 ? 古雷热
“决不……”雷蒙喃喃着,不自觉地做出一副挑衅的姿态。他怪父亲让人厌恶不起来,不像其他家人那么容易令人生厌。三十岁那年,雷蒙曾向父母索要和已婚姐姐的嫁妆一样多的财产,却遭到拒绝,由此就和父母断绝了往来。这是因为家里的财权在古雷热太太手上。雷蒙知道,要是父亲说了算的话,自然不会吝啬,古雷热先生不是个把钱当回事儿的人。他喃喃着“绝无可能……”却不禁从这干巴巴的语句里嗅到了父亲的主动。雷蒙才不会像母亲那样迟钝,古雷热太太对丈夫的冷漠和粗鲁感到恼火,经常抱怨说:“他人品好对我有什么用呢?我又感受不到。他要是人品不好的话,那得成什么样子了?您说呢?”
这个实在叫人恨不起来的父亲,他的主动邀请让雷蒙一阵局促。不了,他当然不会赴约。但是,不管怎么说……后来再想及当晚的情形时,雷蒙只记得自己进入空荡荡的小酒吧时曾心生一丝苦楚,而个中缘由早已忘却,他不记得那是因为有个叫埃迪的哥们儿中途溜了,还有就是父亲来到巴黎了。他以为这苦涩的情绪由某种预感而起,认定在当晚的心境和那会儿正在潜近他生活的变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就从这天起,他再也不觉得仅凭一个埃迪还有古雷热医生就能让他陷入不安之中;反而他坚信,那晚他才点好鸡尾酒时,他的身心就本能地感受到有个女人在靠近他。那会儿,这个女人正乘着出租车到了杜佛路的转弯处,边翻包儿,边对朋友说:“讨厌,忘记带腮红霜了。”
男人回答说:“洗手台那里应该会有。”
“真是糟糕!万一染上……”
“格拉迪斯会借给你的。”
这个女人走进了酒吧。一顶软钟帽遮住了整个上半边脸,只露着供岁月雕刻女人年龄的下巴。四十年的时间总会这儿、那儿地在这下半边脸上留下痕迹,拉松她的皮肤,在她的脖颈上微微堆出皱褶。皮草下应该是一副短小的身形。酒吧里灯光闪烁,她被晃得像刚从斗牛场的牛栏里走出来一样,一阵头晕目眩,不得不在在门口停了下来。她的朋友因为和出租车司机吵了一架刚刚赶来,古雷热起初并没有认出他,只是心里纳闷儿:“我在哪儿见过这个人……这是个波尔多人。”他再次仔细打量这副五十来岁、似是因自命不凡而膨胀的脸庞时,忽然脱口而出一个名字:维克多 ? 拉鲁塞尔。
心跳不已的雷蒙又仔细端详女人:她发现酒吧里只有她一人戴着帽子,于是赶紧摘下来,对着镜子抖了抖新剪的头发,露出一双沉静的大眼睛,然后是宽阔的额头,但是被七绺年轻人样式的深色头发一丝不苟地戛然拦住。这个女人的上半边脸浓缩了她所有残存的青春。尽管头发剪短了,身体臃肿了,从脖子到嘴巴和脸颊都经历了漫长时光的摧残,雷蒙还是认出了她。他认出她,就像认出童年走过的小径,即使荫蔽小径的橡树已被砍伐。古雷热计算着到底多少年过去了,片刻之后,感叹道:“她今年四十四岁了。当年我十八,她二十七。”就像所有把幸福和青春混为一谈的人一样,流逝的时光在他的意识里沉寂却伺机而动。
他的眼珠不停地蠡测逝去的岁月这潭深渊。凡是在他生命里扮演过角色的人,早已被他安放到属于他们的位置,只要看到某个人的面容,他就能忆起他出现的年代。
“她还认得出我吗?”
可是,假如不是认出了他,她会这么突然地避过身去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