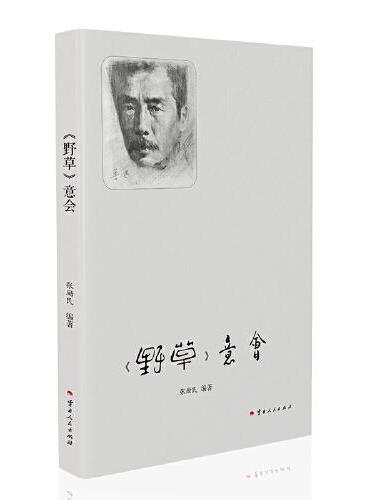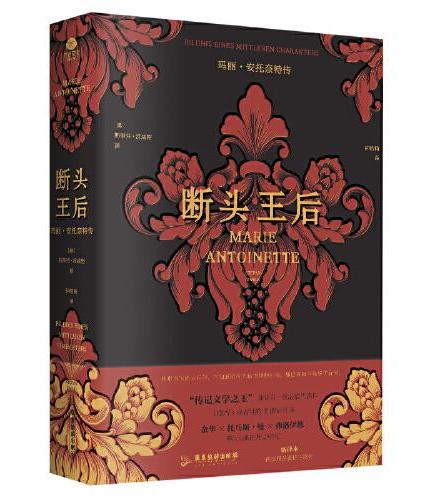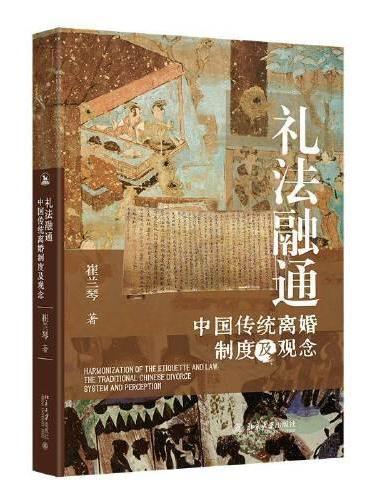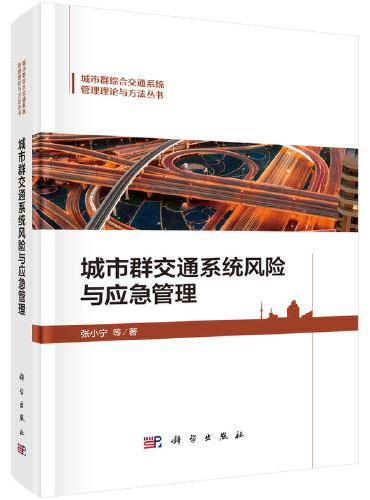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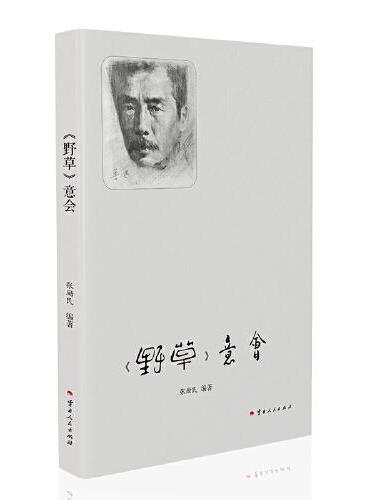
《
《野草》意会
》
售價:HK$
107.8

《
格外的活法
》
售價:HK$
86.9

《
大陆银行(全两册)(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续编(机构卷))
》
售價:HK$
6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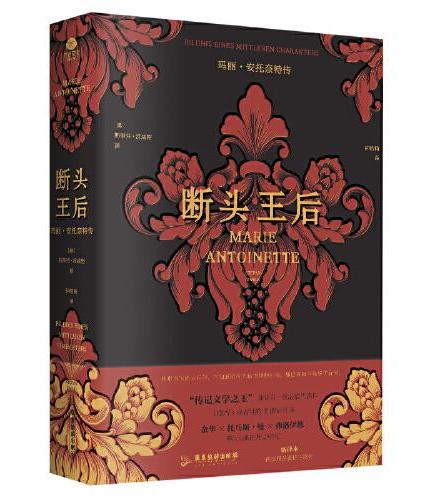
《
断头王后:玛丽·安托奈特传(裸脊锁线版,德语直译新译本,内文附多张传主彩插)
》
售價:HK$
61.6

《
东南亚华人宗祠建筑艺术研究
》
售價:HK$
97.9

《
甲骨文字综理表
》
售價:HK$
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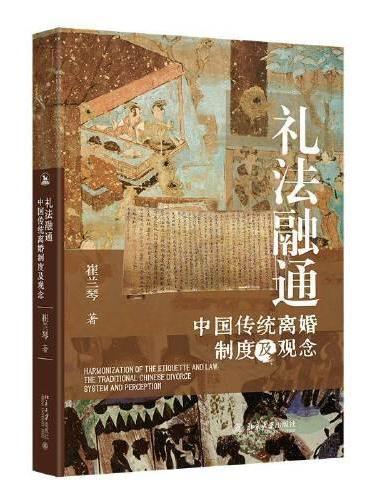
《
礼法融通:中国传统离婚制度及观念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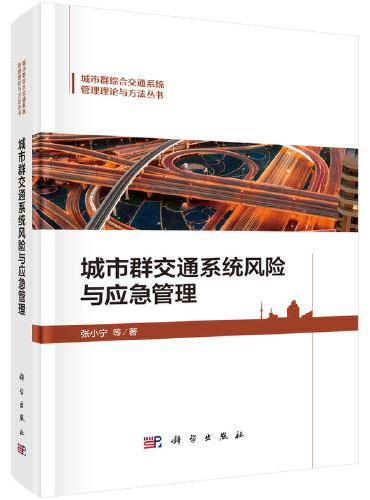
《
城市群交通系统风险与应急管理
》
售價:HK$
204.6
|
| 編輯推薦: |
人与狐,罪与罚
大地道德,京西村歌。
旷野虽广阔,人们却往窄里活。
读懂京西,便是读懂了乡土中国。
|
| 內容簡介: |
为什么山场上偏偏就有雪狐?
雪狐机智,且逗弄人类,有灵异样相,疑是百年修炼而成,便诱发了人与之较量的本能冲动。终虽然人居上风,但也留下狐疑——男女失和,婴儿畸形,神经错乱,种种舛运,找不到根由,便归于迷信,觉得狐是“仙儿”,是神灵化身,不该招惹。不敬之下,必遭“报应”,禁忌的力量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所以,旷野虽然广阔,但是人们却往窄里活。
|
| 關於作者: |
凸凹,本名史长义,著名散文家、小说家、评论家。1963年4月17日生,北京房山佛子庄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文联理事、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房山区文联主席。
创作以小说、散文、文学评论为主,已出版著作四十余部。其中,著有长篇小说“京西三部曲”之《京西逸民》《京西之南》《京西文脉》,《慢慢呻吟》《大猫》《玉碎》《玄武》等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集三部,评论集一部,散文集《风声在耳》《无言的爱情》《夜之细声》《故乡永在》等三十余部,出版有凸凹文集系列《西典新读》等八卷本,总计发表作品八百余万字,被评论界誉为继浩然、刘绍棠、刘恒之后,北京乡土题材创作的代表性作家。
近六十篇作品被收入各种文学年鉴、选本和大中学教材,作品获省级以上文学奖三十余项,其中,长篇小说《玄武》获北京市建国六十周年文艺评选长篇小说头奖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散文获冰心散文奖、第二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老舍散文奖、全国青年文学奖和十月文学奖。2010年被评为北京市“德艺双馨”文艺家,2013年被授予全国文联先进工作者称号。
|
| 目錄:
|
1 两只柿子,一条人命
2 一个女的,两记耳光
3 相亲
4 我自己找上门来了
5 对不起了,大米你必须留下
6 成婚
7 折磨
8 既然这样,你就没必要哭了
9 捕獾
10 雄雉
11 别有用心的关怀
12 不一样的产儿
13 儿子,咱们娘儿俩没缘分
14 破罐子破摔
15 疯狂的捕猎
16 摽上狐狸
17 与狐狸较量
18 把她咽进肚里
19 她的优雅是装出来的
20 男人都出工了,正是女人找女人的时候
21 爱与不爱,不会写在脸上
22 温柔的夜色
23 在不满足中满足
24 你没必要惯着他
25 原来我拿着老鼠当大象了
26 原来还可以这样快活啊
27 别一种生活
28 新时代开始了
29 镜像之爱
30 与羊群一起成长
31 微妙的感受
32 隐隐的不安
33 就走远些吧
34 瑞云寺
35 显光寺
36 家谱
37 居然还有惦念
38 为家族的兴旺而战
39 保健品推销
40 红色粮仓
41 一定要往正经里活
42 出乎意料
43 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44 一刀两断
45 决绝的自尊
46 惊悚
47 驱鬼
48 再也不能安生了
49 回娘家
50 回来就不回去了
51 我也要跟着改变
52 怦然心动
53 好日子过得昏天黑地
54 突遭变故
55 大日子来了
56 各得其所
跋 呈现环境规定下的人类生活
|
| 內容試閱:
|
17 与狐狸较量
这年的冬天,大白天就阴得极昏沉,老人们说,要下雪了。但雪却迟迟不下,弄得猫冬的人心里很烦闷,便坐在热炕上喝闲酒。天双也想喝,但一想到,酒一旦喝,又是在热炕上,还不弄出燥热,还不动与郑秋兰什么一下子的心思?而郑秋兰是绝不会答应的,等待他的不过是吵闹与无趣。他心里咯噔了一下:“既然是这样,待也待不踏实,就出去找一找那只狐吧。”
在山上转了大半天,翻了不少山的皱褶,勘了不少座或斜或陡的梁坡,狐的蹄迹,竟没找到一处。就在一小块平地上,燃了一堆篝火,扔上去半干不干的柴枝,任其噼啪得繁密,闷闷地烧烤着带来的食物,慢慢地嚼着,心里空。
慢慢地吃饱了,肩背也被烤得很温暖,便有一丝惬意的慵懒从骨缝间滋出来。
“睡上一会儿吧。”他对自己说。
向火堆上扔了一批新柴,便把麂皮帽的护耳扎紧了,把羊皮大衣的阔领子也竖了起来,两只手抄到衣袖里去,就团在离火稍远的地方,听木柴的噼啪声入眠。
木柴已烧塌了架,送出温暖的,便是被微风吹得忽红忽暗的炭火。他睡得很沉。
这时,从远处的一片矮树林中,闪出一团雪白的身影,若一团流动的雪,缓缓地滑向篝火。是那只雪狐。她踅到天双的身边,轻轻地嗅一嗅,便走到炭火旁,坐定了,她抖一抖头上的露水,便低下头,一点儿一点儿地舔舐身上的绒毛。从前肢到胸腹,依次舔下去;舔到两条后腿时,就舔得更慢更仔细。那两条后腿极腴美,那浑圆的轮廓,辐射出一团勾人心魄的温柔。这种美,只有人类可以媲比;而这种感觉,也唯人类所独有。
狐一遍又一遍舔舐着这两条美丽的腿,那片紧凑而小巧的脸上,氤氲着一团妩媚的笑。她或许也在为自己的美所深深地陶醉。
这时的天双,其实是醒着的。雪狐在他身边嗅的时候,他鼻子的灵敏,使他闻到了一种独异的味道,似香还臊,像涂脂抹粉的女人。他不能不睁开眼睛偷觑。
这是他次见到狐。
他当然要暗暗一惊,但他很快便被狐那醉人的美所攫慑,便静静地看狐为自己梳妆。狐原来竟恁美,父亲甫银可从来没有对他描述过。
不知怎的,天双竟想到了郑秋兰。郑秋兰虽然是个女的,但她却从来没用心梳过自己的头发,整日里乱蓬蓬的,竟还长出了几只饱满的虱子。其实郑秋兰的肉皮子很白,但她从来没用心把自己洗一洗,白净的脸下,那截脖子总是黑一块白一块,斑驳而油腻,给人的感觉便极不清爽。而这狐竟比郑秋兰有出息,她知道珍爱自己那美丽的容颜。这也不能怨郑秋兰,因为她知道自己不美,没有好好捯饬一下自己的心情。他突然想到,这只狐狸即便是美,但也是有缺陷的,因为她被地夹夹过,为了逃生她咬断了自己的腿。于是他又重新偷觑,从后腿往前腿回溯。他终于看见,狐狸断在左侧的前腿,由于蹲坐,也由于绒毛雪白而长,把残缺遮蔽了。这让他幸灾乐祸,因为他可以像轻视郑秋兰一样轻视她,既然不完美,就是不美。
他忍不住生出一种恶毒的快意,呵呵地笑出声来。
狐被惊动了,也适时地抬起头来,她温柔恬适的目光正同天双的目光撞在一起。而天双的目光是敌视而凶厉的,是要把她吞下去的目光。但狐却未因此而受惊,只是目光有些迷惑,脸上的妩媚也收敛了一些,便露出更惹人爱怜的柔媚。
“妈的,这该死的狐媚!”天双闷闷地骂一声,手就去摸索身边的猎枪。
就见狐轻轻地摇了摇头,目光里弥散着雾一般的怅惘,慢慢地转过身去,朝来时的矮树林走了。她的步态是那么的从容,是那么的停匀,一点也看不出是用三条半腿走出来的——这大自然总是让人吃惊,能给旧的残缺修补出新的平衡,让她残而不瘸。而且,她那身雪白的毛,因加舔舐又被炭火烘干,就愈加洁白愈加蓬松,疑似是一团不可侵犯的圣洁。如果是一般人,感动之下,肯定想送上深情的抚摸,然而天双是猎人,而且还抱着捕猎的意图,那么她的从容与停匀便被他看作是戏弄,冷厉的仇恨就油然而生。
他手中的枪在她身后响了。
矮树林娇嫩的树枝被铁砂拦腰击断了,纷纷落下,如一阵繁急的骤雨。
天双几乎是随着枪响跑出去的。跑到林畔,除了吱咯吱咯踩响断枝的碎尸以外,却并不见狐的一丝踪影。
天双茫然地站在那里,把自己站成一柱冰冷的失望。
过了几天,山里的雪就来了。雪纷纷地下,不日,便没膝了,山里就显得更小、更逼仄。然而,雪后的山垭,终究是有些个温柔而爽洁的气氛了。好喝酒的汉子,就纵情地喝下去了。
天双却依然喝不下去,整日里擦他那杆猎枪。擦枪的声音像把仇恨锉在仇人的骨头上,让郑秋兰什么话都不敢说。
甫银见状,问道:“你见到她了?”
“见到了。”
“有什么感觉?”
“比他妈的人都美。”
“既然比人都美,你就应该放过她。”
“放过她,那么,把人放在哪儿?”
“你的意思是说,她的美就是罪过?”
“对,正如郑秋兰,她的丑就是罪过。”
待雪停了,天双就毫不犹豫地上山去了。尾在他身后的,竟然是怎么拦也拦不住的甫银。既然好心的规劝不被善待,那么,他就冷眼相看,去见证罪恶。
天双是很有他的道理的。雪后,松鸡和灰鸽们就生活得极艰难了,疲惫地逡巡在林间的空地上,费力地用趾爪把积雪拂开,啄食雪下草窠里那几颗零落的松子。而雪后的山间回暖,使狐喜欢出来活动,狐便很容易就捉到味美的松鸡和灰鸽。
在山间,父子俩很快便遇到了几只普通的狐。那些狐的皮色灰暗若土,脸颊亦窄小,透着鄙俗的狡黠。天双便没有好兴致,只是出于猎人的本能,把枪砰砰地打响了。然而竟也打了三四只。他也不捡拾猎物,依然脸色阴沉地朝前走。
甫银理解天双的心思:一般的猎物已不在他话下了,即便是这些也算是出类拔萃的狐类;他之渴望,只是那只美丽的雪狐。甫银摇摇头,把那些猎物捡了起来,他不忍心让它们遗尸荒野,况且它们的皮也是上好的宝物。
临近傍晚的时候,在一片原始的冷杉林畔,终于见到了那团雪白的身影。但那身影飘然一闪之后,就又杳了踪影,父子俩便循着狐的蹄印,追下去。
那狐的蹄印精巧若花瓣,由于她走得轻盈,“花瓣”的边缘便极完整,没有跳开的裂痕;也因了步态的停匀,“花瓣”散落得亦均匀,印在白白的雪底子上,便如灿星丽天。甫银深深迷恋着这些蹄印,拼命地跑在天双的前面。他舍不得这些白雪中的美丽,在未经欣赏之前,就被天双那丑陋的大脚无情地践踏。甫银拒绝杀生之后,居然多了一点儿童心,内心有了与年龄不匹配的柔软。
甫银便跑得气息喘喘。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光景:一个老人,为了一排美丽的雪狐的蹄印——一桩自然中的神奇,竟然恣意地迸发着激情。天双觉得他真的是老了,因为都把老人叫作“老小孩儿”,所以才有了孩子一样的举动。他心里说,你来得真是多余,再怎么弄天真,也不会打动我,我的心里已经长茧子了。
当暮色四合的时候,他们已追到了一个极陌生的境地。空前的疲惫使他们仰翻在雪地上,吮着从树挂上零落而下的雪末,感受着人在极度疲惫之下,把自己躺倒以后,那种透骨的惬意。而那串美丽的蹄印依然朝前延伸着,天双的惬意便极短暂,而甫银的惬意却极绵长。当天双咒骂着去折树枝点篝火的时候,甫银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决绝地沉浸在这童话般的雪白世界。
父子被饿醒的时候,天竟蒙蒙亮了。
坐起来,父子就呀地叫到一块儿了—— 那未熄尽的炭火的周遭,竟环列着两排极清晰的蹄印;在炭火的另一端,有被坐压的凹痕,且蹄印繁沓;那凹痕的边上,有两只未被啃啮的松鸡的腿骨,而两扇松鸡的灰色的翅膀,也平覆在白雪之上,泛着诱人的幽光。
“那狐夜里来过了!”
“嗯,来过了。”
父子便都感到了雪狐的诡秘。
接下来,父子便有了不同的感觉——甫银感到了这狐有不一般的善良,因为恶狐也有被迫的恨意,遇到穷追不舍的猎人,会抽冷子咬断他的喉咙,然而面对两个躺倒了的猎人,她却没有下嘴。而天双却不这样看,他感到了狐对他的戏弄,使他感到了做人的惭愧,尤其是作为一个猎人。
——在大自然中,人类普遍地容不下畜类的机智。这是一条生存法则,是有切身体验的前人总结出来的。天双上过学,从课本上学到过,所以到了具体情景,自然会生出相应的情绪,所以,他恨恨地对甫银说:“操,回家。”
甫银也学天双的样子:“操,回家。”说完,竟乐出声来。
天双便瞪他:“笑什么笑!”
甫银依旧是笑,且笑得咯咯的了。
天双很恼火,在甫银的屁股上重重地踹了一脚。甫银打了个趔趄:“你敢踹老子,真是个孽障。”天双说:“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你之所以跟我来,其实就是给那个狐狸通风报信的。”甫银说:“你真是扯淡,我又不会说狐狸的话,我怎么给她通风报信?”天双说:“因为你追过她,她记住了你的气味,闻着味道就知道我们的行踪,知道怎么躲。”甫银先是一愣,后来竟放声大笑:“你他妈的一点儿也不傻!”
……
回家以后,天双就借来了村里所有的火夹,又新做了几十副套索。火夹,是地夹中的,有两排硕大的铁牙,连接处是两只能敲出脆响的钢簧,钢簧因为有极强的弹性,当夹板被踏翻之后,叭的一声,两排铁牙便被钢簧匝在一起,且匝出璀璨的火花,故得名。要打开这火夹的牙,得有过人的力气。于是,只有意志决绝的猎人,才想起来使用这钢性的火夹,一般的猎人,从不轻举妄动。
这些火夹和套索,自然就下到了雪狐出没的地方。
这时,雪花又下得很轻曼了,山里的世界就更小、更温馨了。
天双终日窝在炕上,既无聊又充实,因为他那套猎法是需要时间的,他需要忍耐。
至于甫银,则终日忐忑着,像孩子一样,把雪簇成堆,然后狠狠地将尿柱射上去,看白雪在嘶嘶的弱声中,无奈地化去。他次感到了雪花的不够可爱。因为雪花把山里世界弄得过于美丽,而美丽之下,却藏着一团团阴谋。那只雪狐,虽机智,却不会机智到分辨人间的真假。在她眼里,洁白便是洁白,洁白的世界正可自由地走一走的。
雪终于停下来,天双便突然兴奋起来,冲着甫银喊:“爹,快跟我上山哩!”甫银懒洋洋地说:“我不跟你上山,因为你说过,我身上有雪狐熟悉的气味,会给她通风报信。”天双说:“我已布下了天罗地网,还怕你通风报信?再说,有你的出现,会增加我捕猎的难度,这才刺激呢。”
爬上山里的主梁,天双问甫银:“下火夹的地方知道吗?”甫银点点头。“下套子的地方知道吗?”“也知道。”甫银的回答,透着老大的不耐烦。
“那好,这山场忒大,咱就分头踩一踩吧。”(山里管收取火夹和套索上的猎物叫“踩”。)
在甫银踩的路线上,雪狐果然被夹住了。
那是一座矮崖的根际。狐从上边跳下来时,踏翻了雪层下的地夹,火夹那冷冷的铁牙,自然就紧紧地夹住了她的一条后腿。
狐腿中的骨头已被铁牙猛烈的瞬间撞击击碎了,相连的,是腿上坚韧的内筋和柔韧的外皮。血仍不停地从伤处渗出,但雪却只被洇红了小小的一块;热血滴在上面,便嘶地被吸收了(雪厚啊!)。那一小片被洇湿的雪,便黏稠成一团红泥。
狐浑身颤抖着,泪水和口涎混在一起,凝成黏浊的绝望。
甫银的喉间痒痒的,蹲下身去,欲将铁牙打开。但他究竟是上了几岁年纪,力气显得微弱,铁牙便一动不动。他看到了不远处的一株小树,就走过去,折一段枝杈,以期借树枝的力量,把铁牙撬开。
狐误会了,她因此而惊惧;她闷闷地叫一声,决然地俯下头去,拼命地撕咬那伤处的筋皮。
甫银再一次被惊呆了。
狐又一次把铁牙中的腿咬断了。
甫银很悲伤,因为他本意是想救她的,以为他曾给过她生存的机会,她应该明白他的用意,但还是不信任,选择了自残式的自救。他心里很懊丧。
雪狐跑走的路上,留下了细细的一线血痕。
火夹的牙缝中,狐那条美丽的断腿被静静地衔着,丰沛的血已将雪白染成殷红;远远望去,便似一束火焰,灼灼地往地下烧着。
灼灼烧着的,其实是一炷极强烈的生的意志!
甫银迟暮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久久地立在那里,对周遭的一切,已毫无感觉。
但天双却不理解老人的感觉,他在附近的一个高处看到了这边的情景,骂了一句:“老东西,你以为你是观音菩萨啊,嘁。”他撒开腿追下去,嘴里还故意弄出啸叫,既是对狐狸,也是对甫银。对狐狸,是扬眉剑出鞘,是立斩立得;对甫银,是钝刀子割肉,是对衰老的嘲讽。
雪狐便难逃被捉住的命运。
在庭院中,天双霍霍地磨着刀,他要炫技,活扒皮。
甫银哀求道:“你既然捉住她了,就证明你比你爹强,你既然是强了,就没必要再斗狠了,要么放生,要么给她留下一个完整的尸首,你尊重了她,她的在天之灵也会尊重你。”
天双说:“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狐,而是一只狐仙;既伤了她,就再别迁就了,放了她,她会回来加倍地伤害你!”
天双的话,也是山里早有的一个说法,甫银自然也是知道的,便拿不出更有力的规劝。他颓然地蹲在地上:“天地之间有因果,你既然不信,就走着瞧吧。”
那美丽而哀怜的雪狐被吊在树上,她不作任何的乞求;她平静极了,绵绵地垂着那颗精美的头,定定地看天双把刀磨得亮亮。
在一边上,就坐着无可奈何的,善良的,且是无奈的,那个仁厚的老人。
天双狞笑着,走近了狐。
狐积攒着她终生的力量。
当刀锋刺进她那条美丽绝伦的前腿时,她终于使出所有的力气,仰天长啸。
那嘶声凄惨而嘹戾,枝头的积雪,簌然颤落着。
雪狐的叫声,好像给了天双一种意外的刺激,虽然他有一套比甫银更娴熟的技艺,但是,他不想一下子就把活儿做完,他玩味。他的手在雪狐身上滑动,一边触摸她的骨缝和筋脉,一边念念有词:“嗯,这里,要往左偏半指;嗯,这里要往下错两分;呃,这处的骨节有三块碎骨,切不可直行……”他是在
给刀刃寻找路径、计算参数,让刀法稳准狠。他已经剥过那么多小兽的皮,刀子已能够随着直觉走,所以他这样算计其实是很没必要。他之所以还弄得这么煞有介事,是做给甫银看的。
也是做给郑秋兰看。因为好奇,郑秋兰也出现在庭院,这就让天双暗自窃喜。
由于玩味,刀子走得很慢,疼痛就持久而深刻,雪狐的叫声就有了嘹戾之上的嘹戾,分外刺耳。郑秋兰忍不住捂上了耳朵,满脸抽搐。甫银则冷笑,不停地嘟囔:“你拿一个畜生斗狠,不就是做给我看吗?你是比我强,但你少了厚道,已经跟畜生没什么两样了。”
天双听到了,说:“你不要干扰我,我要把手下的活儿做好。”
他把雪狐身上难剥离的部分剥离之后,把刀子往地上一扔,对甫银说:“你别在我跟前碍手碍脚的,站远点儿,我要扒皮了。”他攥紧了已到手的部分,贴着雪狐那柔滑的肉身,低沉地喊了一声“走”,便在一瞬间将狐皮整个地撕了下来。
于是,赤裸的雪狐便一下变成了一个粉色的婴儿,在寒风中无助地抽搐,那尖厉的嘶叫,就更无遮无拦,直抵人心。
在恍惚中,甫银竟觉得这叫声是那么的熟悉。民国那一年,东头那一个美丽的女儿被蛮野的地主强暴时,也是叫得这么凄哀。但后来地主到底是被处置了,而这只雪狐的呼嚎又有什么结果呢?!
甫银泪流满面。他已弄不清,这雪狐的后的绝唱,是用来呼唤恶,还是呼唤善!他只知道,山里的天地是极广阔的,既容得下不屈的猎人,也容得下柔媚的狐狸……
郑秋兰被吓得钻进了屋子,双手攥拳,用力地捶打着自己厚实的胸脯。她心跳得厉害,好像马上就要蹦出来。“这个挨千刀的,他竟然能下得去手!”一声惊叹脱口而出,居然像一刃刀尖儿,刺向她的心坎儿,她的心一剜一剜地疼。
一如再麻木的树木被刀斧砍过,也会流下黏着的泪水,再木讷的内心一旦被伤害,也是无法被安抚的。从这天起,甫银不再同天双讲话,虽然没有公然宣布断绝父子关系,但亲情已被冷冻,再也化不开了。他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养了这样的一个儿子。但是他有了一个坚定的确信:杀生,的确是有报应的。而且,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他得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