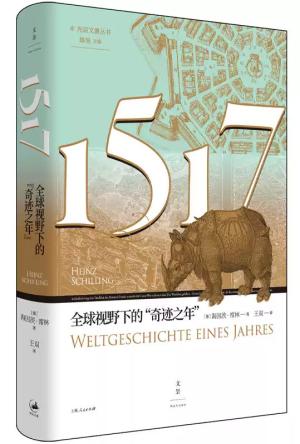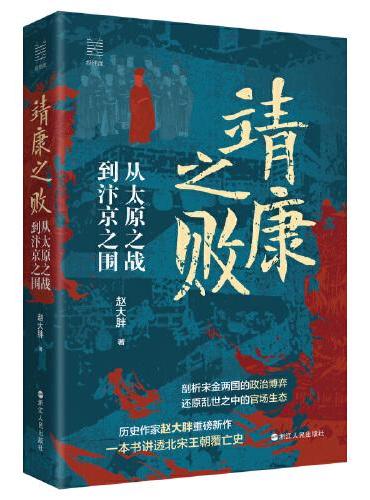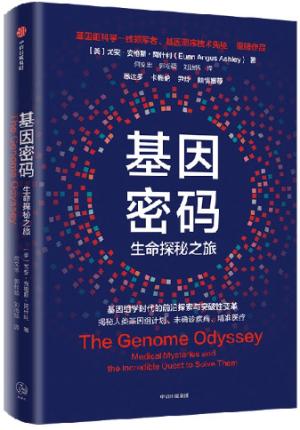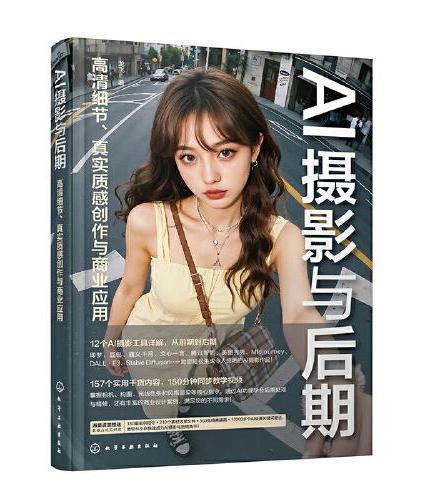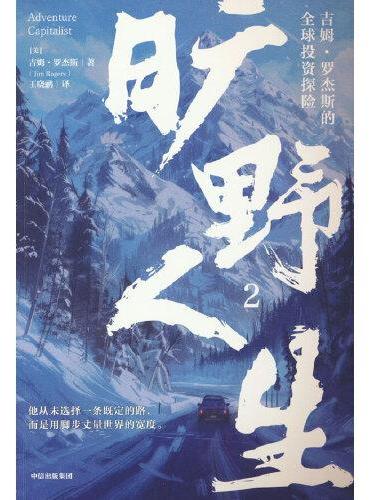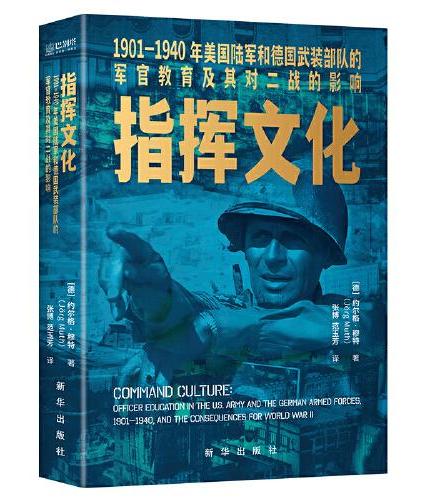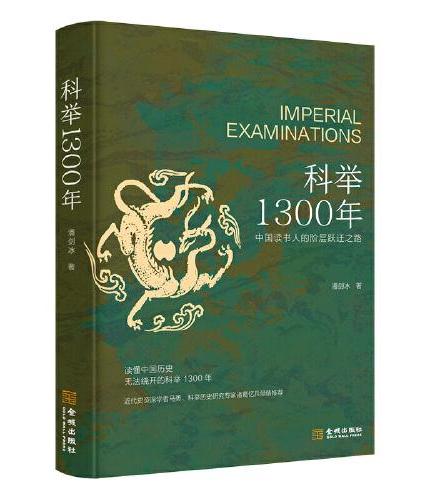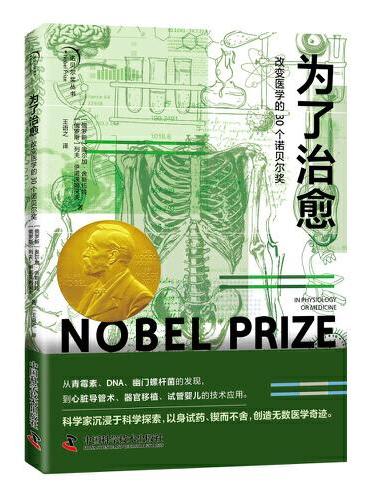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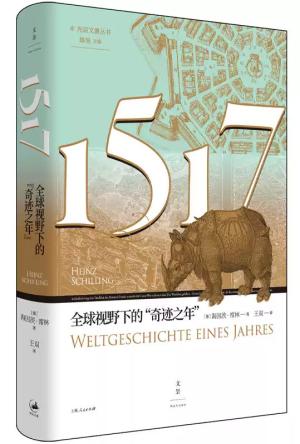
《
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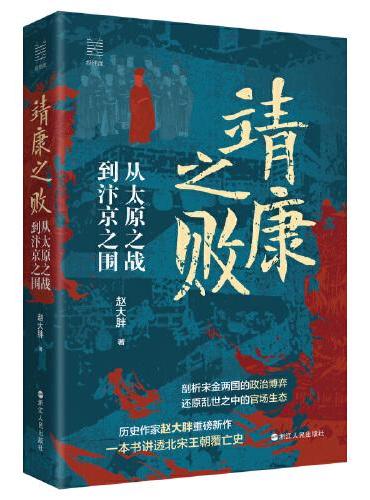
《
经纬度丛书·靖康之败:从太原之战到汴京之围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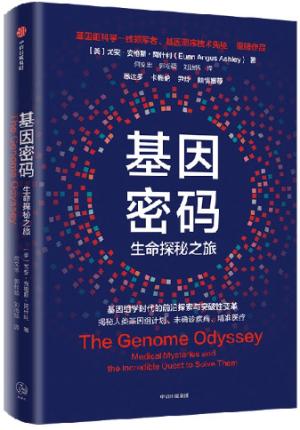
《
基因密码:生命探秘之旅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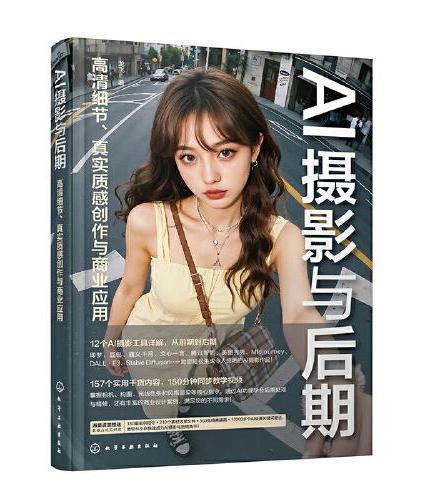
《
AI摄影与后期:高清细节、真实质感创作与商业应用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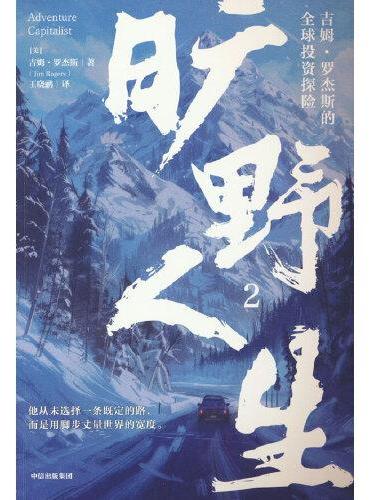
《
旷野人生2:吉姆·罗杰斯的全球投资探险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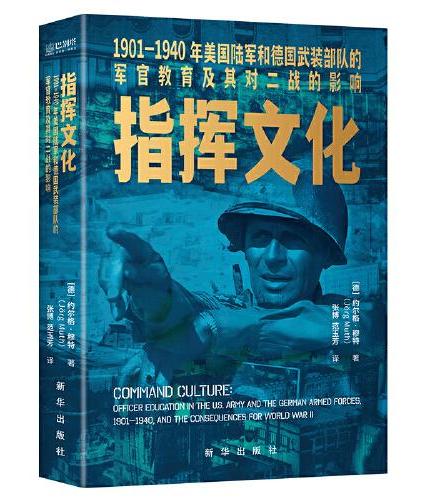
《
指挥文化: 1901—1940 年美国陆军和德国武装部队的军官教育及其对二战的影响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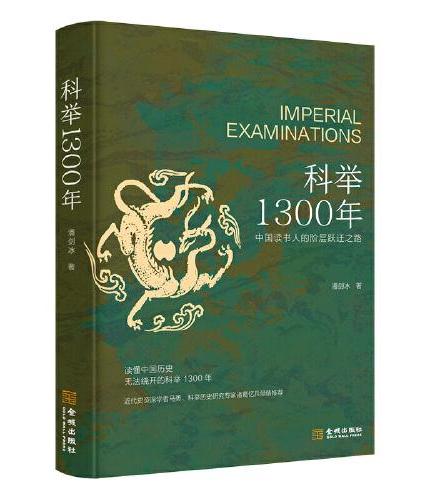
《
科举1300年(中国读书人的阶层跃迁之路,读懂中国历史,无法绕开的科举1300年)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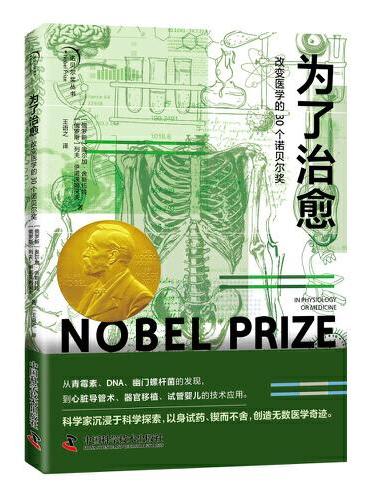
《
为了治愈:改变医学的 30 个诺贝尔奖
》
售價:HK$
64.9
|
| 編輯推薦: |
|
一个身处不自由社会的自由女人是一个怪物?身为女人就要有女性气质?身为男人就要有男性气质?女人的生理结构决定了她必要作为男性性欲的承受者,必要生育、为人母?金发、丰满却不幸的玛丽莲·梦露是坚守贞洁却惨遭横死的茱斯蒂娜的后继者?1740年出生、生来即显贵的萨德侯爵在狱中写下了《索多玛120天》《闺房哲学》等惊世骇俗的色情文学。1940年出生,一生致力于摆脱性别枷锁、追寻平等两性关系的安吉拉·卡特,在性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70年代,写下了冒犯之作(既冒犯了男人也冒犯了女人)——《萨德式女人》,奉在其作品中凌虐女性的萨德为“道德色情文学作家”。在《萨德式女人》中,卡特并没有推崇或认同萨德作品中惊人的暴力、性虐和厌女症。她认为,萨德是在以色情写作的方式对人类进行极具杀伤性的讽刺,以穷凶极恶的色情批判病态的两性关系以及背后那个压抑的权力社会。他将一个不自由的社会背景下的性关系描绘为纯粹暴政的表现。在他笔下野兽般的纵欲狂欢中,施暴者永远是握有政治权力的人,受害者则是几乎没有权力的人。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迷人怪物》中写道:“如果无论小红帽怎么做,终都会躺在狼的床上,她仍有两个办法逃脱。一是适应
|
| 內容簡介: |
《萨德式女人》是英国独树一帜的重要女作家安吉拉·卡特独绝的文化史批评。在本书中,卡特从女性主义视角重新评估备受争议的法国哲学家、色情文学作家萨德侯爵的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女性主义者,卡特认为萨德开创性地不把女性视作单纯的生育工具来书写,他看到了女性在生理特征之外的存在,因而在此意义上解放了女性。在本书中,卡特将性视作一种权力政治进行剖析,解构了关于性别的神话,并且极具独创性和先锋性地将萨德令人发指地虚构的女性形象转化为我们所属时代的女性象征进行批判。好莱坞的性感女神、母女关系、色情作品,甚至性爱与婚姻的圣殿都被卡特的雄辩妙语毁灭性地暴露在我们面前。卡特深入扭曲性欲的内核,提出建立一种既不承认征服者也不承认被征服者的爱之关系。
《萨德式女人》既非对萨德的批评研究,亦非对他的历史分析,而是20世纪晚期对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阐释。这些问题关系到受文化决定的女性本质和由此生发的两性之间的关系,这一对抗关系残酷地分裂了我们了解世界的共同斗争,而且本身就是对此斗争的深刻揭示。
|
|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英国女作家,凭借《染血之室》《马戏团之夜》《焚舟纪》《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明智的孩子》等新颖无畏、独树一帜的作品,成为一代人的偶像,被萨尔曼·鲁西迪、伊恩·麦克尤恩、石黑一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大作家拥戴为一代文学教母。2008年,《泰晤士报》将她列为“1945年以来50位伟大英国作家”第10位。时至今日,她仍是女性主义的象征。
【译者简介】
曹雷雨,女,四川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教授。近年致力于文学作品和艺术图书翻译,已出版译著十余部。译有安吉拉?卡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影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姜丽,女,山东人,兰州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硕士,瑞士伯尔尼大学语言学博士。长期在高校从事英语教学工作,有二十多年的翻译经验。
|
| 目錄:
|
小 引
一 辩论性序言
造福女性的色情
二 神殿的亵渎
茱斯蒂娜的一生
三 作为恐怖主义的性
茱莉爱特的一生
四 爱的学校
女俄狄浦斯的教育
五 思索的尾声
肉体的功能
后 记
雷德·埃玛答沙朗东夫人
参考文献
|
| 內容試閱:
|
摘自 辩论性序言
色情文学作家是女性的敌人,只因我们当代的色情观念并不包括变化的可能性,似乎我们是历史的奴隶而非缔造者,似乎性关系未必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似乎性本身乃如同天气一般不可变的外在事实,创造着人类实践却绝非它的一部分。
在程式化的涂鸦中,阴茎始终坚挺,保持着探究、好奇或肯定的警觉姿态,它仰天翘首、坚定不移。那个洞口则敞开着,一个怠惰的空间,犹如一张等着被填充的嘴。或许可以从这一基本图像衍生出性别差异的整个形而上学:男人渴望,女人除了存在并等待,无所作为。男人积极阳刚,是一个惊叹号。女人消极阴柔,双腿之间空无一物,只有零,一个代表虚空的符号,只有当男性原则填入意义才能成就它。
生理即命运,弗洛伊德如是说,诚如斯言,可惜模棱两可。我的身体不过是极其复杂的组织,即自我的组成部分。涂鸦的解剖学简化法,即男女之间身体差异的反证法,从我身上抽走了“我”的所有证据,只留下我作为哺乳动物的生命的一个方面。它扩大并简化了这个方面,然后将其作为我整个人最重要的部分展现出来。所有关于性行为的神话大抵如此,只不过涂鸦让人们眼见为实。由于纯属天然,它成为表现男女不同性本质观念最直截了当的版本。面对这一象征,我所自命的任何社会存在皆一无是处。涂鸦把我引回我作为一个女人的神话同类,而作为一个女人,我的象征价值主要是一种忍耐与接受的神话的价值,即一张被拔除牙齿的哑口。
如果女人任由自己借假想的伟大女神来宽慰自己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对智识辩论方法的缺乏,她们只是在哄骗自己屈服(男人常用在她们身上的伎俩)。所有关于女人的神话版本,从关于处女贞洁的救赎之力的神话到治愈调解之母的神话,皆是宽慰人的无稽之谈,而在我看来,宽慰人的无稽之谈似乎是对神话的公正定义。母神是跟父神一样愚蠢的观念。如果说女神崇拜的神话复兴给予女人情感上的满足,那么这种满足是以掩盖真实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这也就是神话最初被编造出来的原因。
神话以虚假的共性来减轻特定情况下的痛苦。没有什么领域比两性关系对此体现得更充分了。涂鸦从神话的这些虚假共性中获得了所有的效果,这一性图像最公开的形式在操作中不需要任何训练或艺术技巧,却总会有观众。涂鸦对人际关系复杂性的野蛮否定也是一种宽慰人的无稽之谈。
如同在所有男女关系的神话图式中一样,在涂鸦图式中,由男人来处置而女人则被处置,正如她在强奸中被处置一样。强奸是一种身体上的涂鸦,对爱的极度消减,在此所有的人性皆背离了具有性征的众生。因此害怕强奸不仅仅是身体上对伤害和屈辱的恐惧(害怕心灵崩溃和支离破碎,害怕不仅限于受害者本人的自我丧失或分裂)。由于所有色情直接源于神话,从最粗陋到最复杂的色情男女主人公皆为神话抽象物,是具有维度和容积的人物。这些对原型男女的再现根本无法表现现实男女。
个体本质不仅没有融入这些原型反而遭到忽视,因为原型的功能便是削弱独一无二的“我”,转而弘扬一个共同的具有性征的生命,而后者因其本质实际上并不存在。原型不过是一个高大全的形象,充其量也就是对现实的幻想。
所有原型都是虚假的,但有些原型比其他原型更具欺骗性。性别差异是不争的事实,但阳刚之气和阴柔之气的行为模式与之无关,且仅部分源于这一差异,这两种行为模式皆是受文化制约的变量,共同语把它们转化为共相。这些原型只会混淆主要问题,即两性关系是由历史决定的,是由女人在经济上依附于男人的史实决定的。这一史实而今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过去,即使在过去也只在某些时期适用于某些社会群体。如今,大多数女人婚前婚后及离婚后都在工作。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对女人经济不独立的虚构信以为真,而且据此想当然地认为女人情感不独立乃万物自然秩序所固有,从而以此安抚女人接受低工资。她们在工作,却眼看着收入微薄,因此她们断定自己根本不能真正工作。
然而,这一对现实经验的混淆(我从自我经验中获知为真者却非如此)在原型的虚幻爱抚中最明显。世世代代的艺术家想方设法使之显得如此诱人,不少女人受幻想哄骗,心甘情愿地忽略自身反应这样的明证。
在这些美丽的邂逅中,任何一个男人都可能偶遇任何一个女人,对他们的交媾来说,他们的个性远不及他们的性别事实本身来得重要。在第一次触摸或叹息中,他(她)立马被归入大同。(当然,她几乎不靠近他;那可不是完满幻想的一部分。)当她躺在一个男人身下的时候,她当即戏剧性地成了一个女人,她的顺从便是他男子气概的顶峰。在勃起之前,为了显示自己的谦卑,一个男人定会跪着接近一个女人,正如他接近神灵一样。正是这种美妙的思想一直困扰着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中的性史,几乎引起了与性爱即罪的观念不相上下的困惑。
将男人和女人表现为男性和女性,他们特殊的个体存在也就没有了。这些歪曲的场面把我们的性生活从这个世界移开,从触觉经验本身移开。情侣们迷失在否认而非超越现实的隐私空间之中。这一行为绝不会让他们满足,因为它对他们的生活毫无影响。它出现在宗教仪式的神话梦幻时分。
然而,我们的肉体如世间一切事物一般,离开历史,抵达我们自身。我们可能以为自己性交时剥去了社会欺诈。在床上,我们甚至觉得自己触摸到了人性自身的基岩。可是我们上当受骗了。肉体并非无法简化的人类共性。尽管爱欲关系似乎独善其身地自由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扭曲的社会关系中,实际上,它却在所有人类关系中最具自我意识。两个人正面交锋,他们床上的动作完全由他们床外的行为所决定。如果一个性伴侣在经济上依附于对方,那么性胁迫和合同义务的问题就会在爱巢露出其丑恶的嘴脸,而且必然会影响爱意的性表达本质。婚床作为躲避世界的庇护所尤其具有欺骗性,因为所有的妻子必须按合同性交。妓女至少还会像模像样地当场拿到交易款,几乎不会对没有社会认可做伪饰的受雇身份抱有幻想并自吹自擂。可是对她们服务的需求在下降,原因在于其他女人侵入她们的领土来寻找一种新近得到认可的性快感。这一时期,淫乱滥交似乎是自由交换的唯一类型。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无论多么明显地无厘头,没有一张床能免于现实生活非普遍化的事实。我们并非单单成双成对地上床,我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我们父母的生活、我们的银行存款、我们的性期待和情感期望、我们的全部履历(我们独一无二的存在中的所有鸡零狗碎)所合成的文化辎重还会拖累着我们,即使我们对此缄口不言。在我们把伴侣弄进卧室之前,这些考量因素早就限制了我们对伴侣的选择。在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中,伯爵夫人不可能考虑跟她丈夫的仆从上床,即使他显然是现成的最佳人选。在苗头出现之前,对社会阶层的考量就审查了伯爵夫人和费加罗之间性吸引的可能性。如果这一习俗限制了伯爵夫人的活动,那么它并不影响她丈夫的行动,他欣欣然在密谋诱奸自己仆从的妻子。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中,如果中产阶级出身的凯瑟琳·恩肖想跟希斯克利夫同床共枕(后者身为弃儿身世可疑),凯瑟琳不但必须压抑这种欲望,而且还要为此念头付出被社会认可的脑膜炎和早逝的代价。我们的文学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不乏各色男女,尤其是女人,出于对阶级、宗教、种族和性别本身等因素的考量,她们否认了性吸引和爱情的现实。
阶级决定了我们对伴侣的选择和对体位的选择。害怕、羞耻和拘谨迫使穷人和无知者黑灯瞎火地交媾。显而易见,性行为的复杂成熟度是教育的副产品。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情侣原始的赤身裸体是中产阶级的现象。在北方的冬天,赤裸裸的情侣必须付得起卧室的取暖费才行。控制裸体曝光的禁忌进一步由更宽泛的文化考量所决定。日本人裸体混浴了好几个世纪,世世代代的日本情侣穿着和服性交,即便在湿热的夏天也不例外,甚至连发髻上的发梳也不摘除。还有一个复杂之处,他们并不欣赏裸体的情色,而是以令西方人忐忑不安的温和坦然相互观看裸露的生殖器。
生育控制是性教育和官方法规的副产品,这类法规与廉价或免费避孕法的普及有关。即便如此,一个穷女人会发现自己被做了绝育手术,而她当时想要做的不过是一次人工流产。她无法掌控自己的生育,她的能力被社会管理者永久拿走了,他们早就认定贫穷即愚蠢,而一个穷女人根本不会有自己的想法。
五芒星这张床上神奇的隐私本身可以仅用金钱买下。隐私的缺乏会限制性行为的复杂成熟度,而在满是孩子的房子里,隐私是奢求不到的。
给这些社会经济的考量平添一份羞耻、憎恶与德行的犹太基督教遗产,居于原初的冲动和对自我最基本的首肯之间;这种文化中的人竟然能学会性交可真是一个奇迹。
肉体走出历史,来到我们身边,掌控我们肉体经验的压抑和禁忌亦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