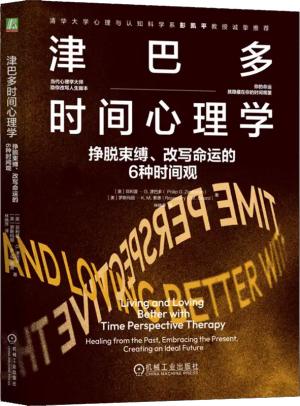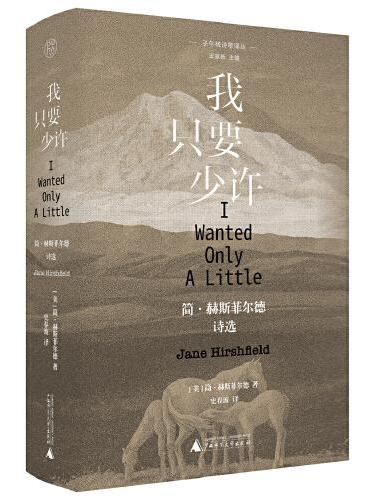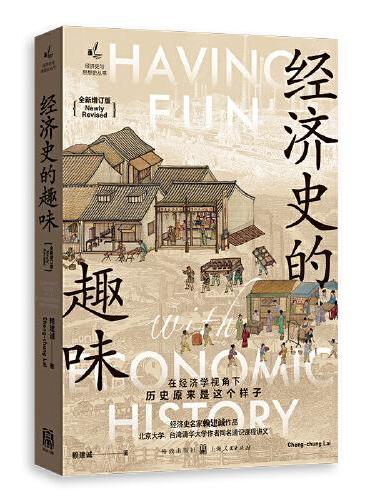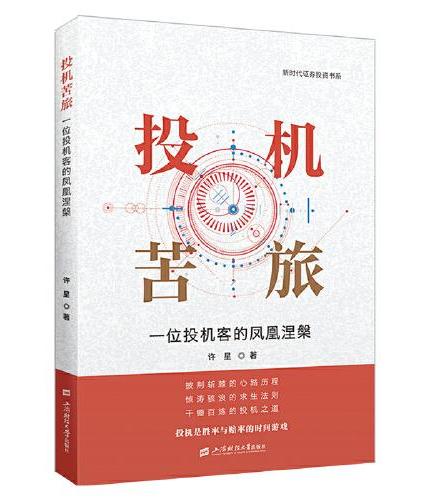新書推薦:

《
8秒按压告别疼痛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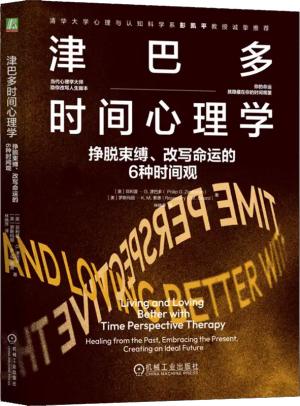
《
津巴多时间心理学:挣脱束缚、改写命运的6种时间观
》
售價:HK$
77.3

《
大英博物馆东南亚简史
》
售價:HK$
1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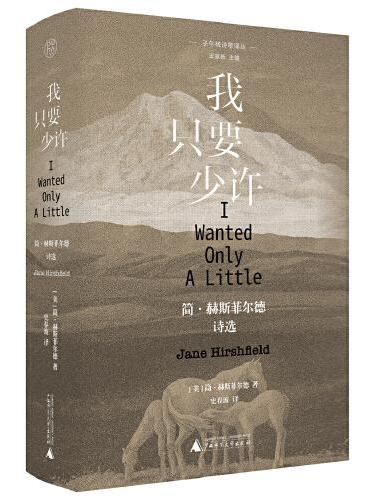
《
纯粹·我只要少许
》
售價:HK$
8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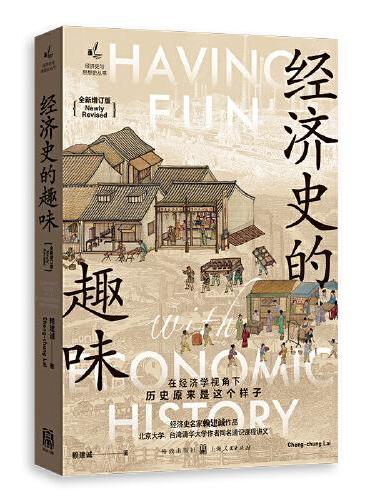
《
经济史的趣味(全新增订版)(经济史与思想史丛书)
》
售價:HK$
84.0

《
中国古代鬼神录
》
售價:HK$
19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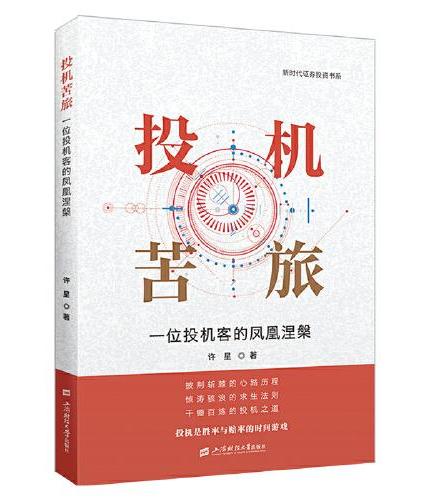
《
投机苦旅:一位投机客的凤凰涅槃
》
售價:HK$
88.5

《
重返马赛渔场:社会规范与私人治理的局限
》
售價:HK$
69.4
|
| 編輯推薦: |
《喜剧》
一出包容载重内涵丰富的人间喜剧
一幅世态人情众生万象的恢弘画卷
一场思接千载寓意深远的人世省思
一段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万千的生命故事
《喜剧》为陈彦“舞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与《装台》《主角》一般,仍属戏曲舞台内外中心人物动人心魄的生命故事,也不外是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诸般际遇所致之起落成败、出入进退、离合往还,然以之为自我砥砺之地,也便蕴含着对人之在世经验透辟、深入的理解和绝妙的艺术处理。不同于《主角》中忆秦娥虽面临外部世界是非毁誉之磋磨,却一味精进自我成就的向上一路,《喜剧》的主角贺加贝、贺火炬兄弟分属两种类型,由之生成两种人生状态:前者因心里有所郁结而对女主角万大莲不能或忘,也在“喜剧”之邪路上愈行愈远,终至于误入歧途难以自拔,其“喜剧人生”终转为“悲剧”收场;贺火炬虽也偶入歧途,但却因偶然机缘幡然悔悟,悬崖勒马,于世态人情之演变中顿悟其父火烧天所论之喜剧技艺,以及戏与生活世界之关系的精到,从而开出喜剧人生贞下起元、峰回路转之新的可能。二者精神取径虽有不同,却有同一志向奇正相生之参互意义。《喜剧》因此既关涉到戏与人生与生活世界之相互影响、互相成就之复杂关
|
| 內容簡介: |
《喜剧》:
《喜剧》是以喜剧笔法写就之喜剧演员(丑角)悲喜交织、跌宕起伏、动人心魄的生命故事。作者以贺氏一门父子两代人的生活和命运为主线,在戏与人生的交相互动中牵连出广阔的人间世各色人等的生命情状——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诸般际遇所致之起落、成败、得失、荣辱等等不一而足,并于此间表达了对戏曲与历史、时代和现实关系的透辟理解。贺加贝一度背离乃父火烧天所持守之价值观念,而在喜剧之“邪”路上愈行愈远,终至于喜剧人生转为悲剧收场。贺火炬却因偶然机缘幡然悔悟,于世态人情之常与变中顿悟喜剧艺术持守“正道”之重要意义,从而开出喜剧人生贞下起元、峰回路转之新的可能。其间世情之转换与个人命运之复杂交错,艺术创造与生活和人民血肉相关之内在联系等等,皆有艺术化的独特处理。就中人事代谢、往来古今,悲中有喜,喜中含悲。戏谑与反讽笔法的背后,乃是愍念众生、长劫沉沦的大悲悯情怀;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热闹之中,实隐藏着广大的寂寥和冷清。人事悲喜无常、起落无定,教人感慨系之,浩叹不已。人物命运之转换一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四时更迭、阴阳消长之天地节律,包含是非毁誉、进退荣辱、奇正相生之复杂隐喻。然无论境遇如何,即便偶入歧途,正大人物终究可以意会到作为历史的中间物的个人之于艺术、文化因革损益的时代责任,并朝向精神和技艺的“上出”一路。故此《喜剧》虽悲喜参互、否泰交织,底色亦堪称悲凉,却仍有不可遏止的振拔力量,蕴含包容载重、化成天下之复杂寓意。
《主角》:
《主角》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作者以扎实细腻的笔触,尽态极妍地叙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起废沉浮,及其与秦腔及大历史的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联。其间各色人等于转型时代的命运遭际无不穷形尽相、跃然纸上,既发人深省,亦教人叹惋。丰富复杂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方言口语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熟稔和叙事的精准与老道。在诗与戏、虚与实、事与情、喧扰与寂寞、欢乐与痛苦、尖锐与幽默、世俗与崇高的参差错落中,熔铸照亮吾土吾民文化精神和生命境界的“大说”。作者上承中国古典文学及思想流脉,于人世的大热闹之中,写出了千秋万岁的大静。而经由对一个人的遭遇的悉心书写,让更多人的命运涌现在他的笔下。忆秦娥五十余年的人生经历及其心灵史,也成为古典思想应世之道的现代可能的重要参照:即便内忧外患、身心俱疲,偶或有出尘之思,但对人世的责任担当仍使她不曾选择佛禅的意趣或道门的任性逍遥,而是在儒家式的奋进中觅得精神的终极依托。作者笔下的世界,不乏人世的苍凉及悲苦之音,却在其间升腾出永在的希望和精进的力量。小说遂成浩浩乎生命气象的人间大音。
《装台》:
该书以装台人刁顺子的生活遭遇为线索,写出了西京城各色人等的生活情状。既有对以靳导为代表的艺术家群体的形象刻画,也有对与刁顺子一同装台的大吊、墩子、三皮等“底层”人的艰难生活的详细铺陈。可谓呈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一个“盛大人间”。作品展现百色人生,紧接地气,却又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知所未知,既扎实,又奇异,既合情理,又绝顶新鲜古怪的当代中国故事。读来令人不忍放下,击掌称快!虽然身处“底层”,刁顺子仍然有他的责任,有他的担当,有他对家庭,对社会的一份责任心和爱心,有他的价值坚守和生命的尊严。是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义所在。
《西京故事》:
《西京故事》讲述了一位乡村干部、前民办教师罗天福率领一家四口来到西京城,靠打饼度日,为考入西京城名牌大学的一双儿女提供支持,全家人在城市生活中所遇到各种始料未及的情况,一次次感受到生活的不易和人间的爱,并最终融入城市生活,重新确立了生活目标,其生活面貌及思想境界得到提升的过程。小说真正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里在都市的沼泽之中苦苦挣扎着的小人物们的命运。以强烈的忧患意识、鲜明的时代气息和饱满的人文情怀直面当下精神问题,呈现出独特的思想与艺术品格。
|
| 關於作者: |
|
陈彦,当代著名作家、剧作家。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三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五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创作长篇电视剧《大树小树》,获“飞天奖”。著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主角》。《装台》获2015“中国好书”、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主角》获2018“中国好书”、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
| 內容試閱:
|
《喜剧》
一
谁在恋爱,谁就会以喜剧夸张的手法进入角色而不自知。有时可能会像鸵鸟,以为头钻在隐蔽的地方,身子和屁股别人也看不见了,往往就留下一堆笑料,让人间喜剧有了取之不尽的素材。贺加贝就是这样出场的。天快黑时,他看见廖俊卿溜进了万大莲的房里,还随手关了房门。那咯噔一声,就像心被针扎一般,让他很不是滋味。尤其是该开灯的时候,房里始终没有开灯。关键是几小时过去,里面依然漆黑一片,他就知道问题大了:廖俊卿可能得手了。
长到十九岁,这是贺加贝人生受到的致命一击。犹如谁用八磅锤,砸了他的脑袋,并且是砸了一整夜。脑袋底下还垫了铁砧,锤是在上面硬对硬地猛烈敲击着。整整一个晚上,他都蹴在万大莲门前的一蓬冬青灌木丛里,努力想象着房里发生的一切。那个难受,难忍,难耐……他只感到这辈子,是连活下去的意思都没有了。他多么想房里的灯能突然亮起来,甚至万大莲能操着扫帚什么的,把廖俊卿赶在门外呀!可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发生。房里风平浪静,静得甚至连在窗户上交配的壁虎,都没有任何不安的异动。他还凑到窗户下听了听,里面也没有任何动静,像是房里根本就没人。可他明明看见,万大莲下班后就回房了。廖俊卿在天快黑时也溜进去了。难道一切进行得这么快,牛困马乏到已人事不省了?几次他都想破门而入。甚至想喊起一院子人,逮了这对狗男女。可他没有。万大莲毕竟不是自己什么人,他也没公开向人家表示过什么意思,就是暗恋而已。并且没有人把他跟万大莲能联系起来。多少人喜欢万大莲哪!都说这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美人坯子。想下手的多得很,咋能轮到自己呢?自己就是个唱丑角的。万大莲看他,每每都是一种小丑好好玩、好好笑、好可乐的眼光。这阵儿,他只要点一炮,让一院子人起来抓个现行,也是够好玩好笑可乐的事了。两人肯定毁得一干二净。廖俊卿毁了活该,长一副小白脸,还以为自己就真是白马王子了。可万大莲,他有些不忍,毕竟是太爱了。爱得谁把这件瓷器哪怕是轻轻磕碰一下他都受不了。只是这夜太黑,风太利,他觉得心头肉,是被刀风剑霜的黑夜,削刮、磔诛得所剩无几了。“磔诛”这个词,是戏里残酷的一种刑罚,也叫凌迟处死。用在此时,竟然是那么贴切。他今晚真的是快被凌迟处死了。
贺加贝也知道万大莲是喜欢着廖俊卿的。他们一起排秦腔《游龟山》,万大莲扮的小旦胡凤莲,廖俊卿扮的小生田玉川。天天在一起磨戏,导演还嫌他们下班后练习不够。说尤其是爱情戏没味儿,相互抚摸、拥抱得不自然。还说他们眼睛也不来电。只有贺加贝知道,他们已经练得快走火入魔了。两人拥抱得耳鬓厮磨的,万大莲的酥胸都被挤压沦陷了。那身体间距,是针扎不透、水泼不进的。而两人眼里的电流,更是像火狱一样,能把他活活烧死。有时他们恨不得晚上在排练场,把戏走到十一二点还难舍难分。果然是走出麻烦了吧!俗话说:学坊戏坊,瞎娃的地方。你想想,嘴里说唱着哥呀妹呀恩呀爱呀的,再加眉来眼去,撩拨放电;外带手脚乱动,肌肤相亲;导演还反复要求“戏要入脑走心”。他们是理直气壮、合情合法、明目张胆地以排戏、工作和加班加点的名义,在相互勾搭且旷日持久啊!就是柳下惠,恐怕也要勾搭出毛病来了。
狗日小生小旦戏,真是太迷人了!
贺加贝打小就恨他爹不该让他唱丑。啥戏都在里面跟主角胡搅和、瞎捣乱。尤其是老跟人家相爱的痴情男女过不去。不是偷窥、抢亲、掉包、强奸,就是杀人、放火、使坏、告密。反正多数角色坏得只剩下入地狱了。他明明那么爱万大莲,《游龟山》里却偏偏扮的是花花公子卢世宽。带几个歪瓜裂枣的家郎,拉一条“赛虎犬”,咬死了渔民胡凤莲勤劳的爹不说,还老要胡搅蛮缠,企图把人家女儿也“办”了。面对万大莲,真让他有些不好做戏。就说今晚这蹲点夜守,又何尝不是小丑的勾当呢?可他死爱着万大莲,又有啥办法?想想,他是越来越痛恨那个演老丑的爹了。
他爹姓贺,名少天。小名羊蛋儿。七岁时顺汉江一路讨饭到陕南,遇见一个戏班子,死缠着撵不走,就跟着捡场、看台、学戏了。“捡场”是帮着前台撤换布景道具。“看台”是守夜,怕贼半夜偷了帐幕、戏箱。九岁时,羊蛋儿学演了一折小丑戏《顶油灯》,一下爆红,就被师父叫了艺名“火烧天”。戏班子在大秦岭的天南地北来回跑着讨生活,一时被“国军”征为慰劳队,一时又被“共军”编成文工团了。戏词攒来改去,他也捋不清里边的渠渠道道。有一回当着“共军”面,他昏头黑脑地大赞“国军”:“青天白日是蓝天,保家卫国斩匪顽。”被一个“儿童团长”,美美给了几红缨枪,差点把他两个小睾丸都戳散黄了。又一次当着“国军”面,他打快板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人民爱戴又喜欢。”竟被“国军”连长啪啪啪啪连扇十几耳光,从此半边耳朵都成了摆设货。那时他还不满十三岁。后来他们戏班子一股去了山西,完全从了解放军的宣传队。他师父眼皮子浅,觉得跟着队伍溜,没啥前程,而留在八百里秦川“戏窝子”里,有台口,见天还三顿燃面,是吃香喝辣的日子。关键是师父还有两个相好的女人,得靠他唱戏挣钱糊口。火烧天自然是得跟师父一条心走到黑了。可没想到,很快西京就解放了。那一股从了解放军宣传队的,回来成立了专业剧团,并且还到处打听他师父这一股的下落。听说替国民党唱戏的,已五花大绑了好几个,有一个编戏的还挨了枪子儿。吓得他师父撤身就躲进秦岭南边的镇安县塔云山上,做了老穿着诸葛亮戏服“七星锦绣云鹤氅”、摇着“太极八卦鹅毛扇”的道士。师父没让他去,说他年龄小,唱丑有前途。还说谅他们也不会要了一个娃娃的小命。后来火烧天果然就被剧团找了去。团里要排一个儿童团的戏,里边有个角色叫“驴打滚”,属“不良少年”,得按“娃娃丑”扮。他一演,竟然把剧场的大门都让观众挤破了。团长一拍桌子:“好娃!”火烧天这就算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了。后来多次被拉出来“运动”,那是后话。可他生下大儿子贺加贝、二儿子贺火炬后,还都让唱了丑,非要弄出个唱丑的世家来,这让贺加贝实在有些想不通。尤其是在遇见美人万大莲后,更让他觉得唱丑,是倒了八辈子血霉的事。
直到天亮时分,廖俊卿还没从万大莲房里出来,但他已在冬青丛里快藏不住了。露水湿透了衣裳不说,腿脚也麻木得像是别人硬安上去的。关键是有人已经起床在吊嗓子了。可他又特别想看到廖俊卿出房来的贼相,他坚信现在是他“逃闺”的时机。他只能在冬青丛里蜷缩得更小些,圪蹴得更矮些。
《主角》
一
她叫忆秦娥。开始叫易招弟。是出名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忆秦娥的。
易招弟为了进县剧团,她舅给改了次名字,叫易青娥。
很多年后,忆秦娥还记得,改变她命运的时刻,是在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她正在家对面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她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叫,让她麻利回来,说她舅回来了。
她舅叫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她娘老骂她舅,说是不成器的东西,到剧团学瞎了,作风有了问题。她也不知道啥叫个作风问题,反正娘老叨叨。
她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她舅可神气了。他把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鼓,摆在戏台子一侧。他的整个身子,刚好露出来,能跟演员一样,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戏要开演前,他先端一大缸子茶出来。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他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出来的。他朝靠背椅子上一坐,二郎腿一跷,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鼓槌来。说鼓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细细的,长长的。“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都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得溜直。几个敲锣、打铙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她舅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立马就热闹非凡了。四处八下的人,循着热闹,急急呼呼就凑到了台前。招弟是后来才知道,这叫“打闹台”。其实就是给观众打招呼:戏要开始了,都麻利来看!看的人越多,她舅手上的小鼓槌就抡得越欢实,敲得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将爆裂的一迭声脆响。以至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她舅,而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她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下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舅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他一辈子就知道在女人窝里鬼混。三十岁的人了,还娶不下个正经媳妇。骚气倒是惹得几个县的人都能闻见。后来招弟去了县剧团,才知道她舅有多糟糕,把人丢得,让她几次都想跑了算了。这是后话。
她从坡上回来,她舅已经在吃她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她爹在一旁劝酒。舅说不喝了,再喝把大事就误了。
舅对娘说:“麻利把招弟收拾打扮一下,我赶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下,明天一早好坐班车上县。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了,当牛使唤哩,才十一岁个娃娃么。这哪像个女儿家,简直就是个小花子,头蓬乱得跟鬼一样。”
要是放在过去,娘肯定要唠叨她舅大半天。可今天,任舅怎么说,娘连一句话都没回,就赶紧张罗着要给她洗澡、梳头。她舅还补了一句说:“一定要把头上的虱子、虮子篦尽,要不然进城人笑话呢。”她娘说:“知道知道。”娘就死劲地在她头上梳着篦着,眼看把好些头发都硬是从头皮上薅掉了,痛得她眼泪水都快出来了。娘还在不停地梳,不停地篦,她就把头躲来躲去的。娘照她后脑勺美美磕了几下说:“还磨蹭。你舅给你把天大的好事都寻下了,县剧团招演员,让你去哩。头上这白花花的虮子乱翻着,人家还让你上台唱戏?做梦吧你。”说着,又磕了她一下。
招弟也不知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她可是连做梦都没想过,要到县剧团去唱戏的。这事,她舅过去喝酒时也提说过,说啥时要是剧团招人了,干脆让姊妹俩去一个,也好让家里减轻一些负担。她想,那咋都是她姐来弟的事。来弟比她漂亮,能干。她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主儿。娘老说,招弟一辈子恐怕也就是放羊的命了。可没想到,这事竟然是要让她去了。
洗完头,娘给她扎辫子的时候,她问:
“这好的事,为啥不让姐去?”
娘说:“你姐毕竟大些,屋里好多事离不开。我跟你爹商量来商量去,你舅也同意,还是让你去。”
“我去,要是人家不要咋办?”她问。
娘说:“你舅在县剧团里,能得一根指头都能剥葱。谁敢不要。”
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戴。
“姐不让戴,你就敢给我戴?”她说。
“看你说得皮薄的,你出这远的门,戴她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
娘说完,咋看,又觉得她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肩上、袖子上、屁股上,还都是补丁摞补丁的。就这,还是拿娘的旧衣裳改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她姐来弟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来弟姐前年过年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加上六月六晒霉,拿出来晒过两回,再没面过世的。不过两年过年,来弟姐都让她试穿过,也仅仅是试一下,就赶紧让她脱了。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钥匙连娘都是找不到的。
她咋都不敢穿,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了她身上。褂子明显大了些,但她已经感到很派派、很美观、很满足了。
姐那天得亏不在,要是在,这衣服不定还穿不成呢。
出门时,舅看了看她说:“你看你们把娃打扮的,像个懒散婆娘一样。再没件合身衣服了?”
娘说:“真没有了。就身上这件,还是她姐的。”
舅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唉,看看你们这日子。不说了,到城里我给娃买一件。走!”
刚走了几步,娘就放声大哭起来。
娘突然跑上去一把抱住她,咋都不让走。娘说娃太小,送去唱戏,太苦了。就是在家放羊,也总有个照应,这大老远的,去了县上,孤孤单单的,娃还没满十一岁呢。娘越想越舍不得。
舅就说:“放你一百二十个心,娃去了,比你们的日子受活。一踏进剧团门槛,就算是吃上公家饭了。你扳指头算算,咱九岩沟,出了几个吃公家饭的?”
算来算去,这么些年,沟里还真就出了舅一个吃公家饭的。
爹就劝娘,说还是放娃走,不定还有个好前程呢。
招弟就眼泪汪汪地跟着舅走了。
刚出村子,她舅说:“得把名字改一下,以后不要叫招弟了。来弟、招弟、引弟这些封建迷信思想,城里人笑话呢。就叫易青娥吧。省城有个名演员叫李青娥,你叫易青娥,不定哪天就成大名演了呢。”舅说完,还很是得意地笑了笑。
突然变成易青娥的易招弟没有笑。她觉得舅是在说天书呢。
易青娥舍不得娘,也舍不得那几只羊,它们还在坡上朝她咩咩叫着。
十几年后,易青娥又变成了忆秦娥。
在她的记忆深处,那天从山里走出来参加工作,除了姐的两个花卡子和一件绿褂子外,娘还硬着头皮,觍着脸,从邻居家借了一双白回力鞋,两只鞋的大拇指处都有点烂。不过人家很细心,竟然用白线补出了两朵菊花瓣。鞋才洗过,上过大白粉,特别的白。虽然大了几码,娘还给鞋里塞了苞谷叶子,但穿上好看极了。她一路走,还一路不停地朝脚上看着。惹得舅骂了她好几回,说眼睛老盯在脚背上,跟她娘一样,都是些山里没出息的货。
多少年后,剧作家秦八娃给秦腔名伶忆秦娥写文章时,是这样记述的:
那是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一代秦腔名伶忆秦娥,跟着她舅——一个著名的秦腔鼓师,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走了出来。
那天,离她十一岁生日,还差十九天。
忆秦娥是穿着乡亲们送的一双白回力鞋上路的……
二
易青娥跟着舅,在公社客房歇了一晚上。
公社好几个人跟她舅都熟,晚上来房里谝,还弄了半坛子甘蔗酒,就一碗腌萝卜,七七八八地干喝了半夜。易青娥睡在里间房,盖着被子,装睡着了,就听他们谝了些特别没名堂的话。有的易青娥能听懂,有的一点都听不懂。他们问她舅:剧团人,是不是都花得很?几年后,易青娥才知道“花”是啥意思。她舅说,都是胡说哩。有人说:“哎,都说剧团里的男女,干那事,可随便了。”舅说:“照你们这样说,好像剧团人的东西,都长在手心了,手一挨,麻达就来了。那是单位,跟你们这公社一样,要求严着哩。你胡朝女的身上挨,一胡挨,搞不好就开除球了。你们这公社好几任书记,不都招这祸了?”后来,喝着喝着,就开始审问她舅:“听说你胡三元,就是个花和尚啊!”都问他在剧团到底有几个相好的。舅死不承认,几个人就要扒舅的裤子。舅说:“有娃在呢,有娃在呢。”有人就把中间的格子门拉上了。她听见,几个人好像到底还是把舅的裤子扒了。舅好像也给人家承认,是有一个的。再后来的事,她就不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她跟舅就坐班车去了县城。车在路上还坏了几起,到县城已是杀黑时分。易青娥东张西望着,就被她舅领进了一个窄得只能骑自行车的土巷子。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好久,终于有一个门洞,大得有两人高,五六个人横排起来那么宽,歪歪斜斜地敞开着。
舅说:“到了。”
里面有个院子,院子中间有根木杆,上面挑着一个灯泡。灯泡上粘满了细小的蚊虫。还有一蓬一蓬的虫子,在跃跃欲试着,一次次朝灯泡上飞撞。
有人跟舅搭腔说:“三元回来了。”
舅只哼了一声,就领着她进了前边院子。
所谓前后院子,其实就是一排平房隔开的。
整个院子很大很大,是由几长溜房子合围起来的。
易青娥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院子。
前院也是中间竖了根木杆,杆子上吊个灯泡。灯泡被一个烂洋瓷盘样的罩子扣着。无数的蚊虫也在拼命朝光亮处飞扑着。有的粘到灯泡上,有的就跌落在地下了。
地上是厚厚一层飞虫尸体。
前后院的灯杆下,都有一个水池子,有人在那里冲洗得哗啦啦一片响。
她舅刚走进前院,就有人招呼:“三元,你跑呢,今天咱们在院子里逮了一条菜花蛇,刚吃完,你就回来了。”
“吃死你。”她舅说着,就领她走进一个拐角房里去了。
舅的房不大,摆了一张床,还有一个条桌,一把老木椅,一个洗脸盆架子。房的正中间支着他的鼓。一个灯泡,把用报纸糊的墙和顶棚,照得昏黄昏黄的。
舅的床干干净净的。被子和枕头,都用白布苫着。易青娥累得刚想把屁股端上床,就被舅一下拉了下来,说:“屁股那么脏,也不打一下灰,就朝床上赖。”说着,舅把枕头旁边一个很讲究的刷子拿过来,在她身上、屁股上,细细扫了一遍。舅说:“剧团可都是讲究人,千万别把放羊娃那一套给人家带来了。脏得跟猪一样,咋跟人在一起排戏、唱戏呢?”
易青娥刚在床拐角坐下,就见一个女的闪了进来。易青娥一下认出来了,这不就是上次在公社看戏,那个演女赤脚医生的吗?她吓得急忙从床边溜了下来。
那女的倒是和善,先开口了:“这就是你姐的娃?”
舅噢了一声。
那女的突然扑哧笑了:“不会吧,这娃咋……”
不知她想说啥,舅急忙给她挤眼睛,她就把话咽回去了。
舅说:“这就是剧团的大名演,胡彩香。叫胡老师。你看过胡老师戏的。”
易青娥怯生生地点点头。
舅对胡彩香说:“这回就靠你了噢。下个礼拜就考试,你无论如何得把娃带一带。先把唱腔音阶教一下,再给娃把胳膊腿顺一顺,能看过去就行。”
胡彩香说:“哎,这回报名的可不少,据说是五选一呢。”
舅说:“哪怕十选一呢,剧团人的亲戚还能不照顾?”
胡彩香说:“你看你才回去两天,就啥都不知道了。今早才开的会,黄主任说了,这回要坚决杜绝走后门的风气,团内团外一个样。”
舅把牙一咬:“嚼他娘的牙帮骨。不收我姐的娃,你叫他试试。”
胡彩香急忙掩嘴说:“你悄声点。小心人家听见,又开你的会哩。”
“开他妈的个瘪葫芦子!”舅骂开了。
胡彩香急得直摇头:“你就是个挨了打,不记棍子的货!”
“记他妈的瘪葫芦子,记!”
“好了好了,我都不敢跟你多说话了,一搭腔,躁脾气就来了。明晚又演《向阳红》呢,你知道不?”
“给谁演?”
“说是上边来了领导,专门检查啥子赤脚医生工作的。”
“重要演出,那肯定是你上么。”
胡彩香把嘴一撇:“哼,看把你能的。我上,我给人家黄主任的老婆,还没织下背心呢。”
“啥事嘛?把人说得稀里糊涂的。”舅问。
“你不知道了吧。那骚货前一阵,在县水泥厂弄了十几双线手套,拆呀缠呀的,不是老在用钩针,钩一件菊花背心吗?你猜近穿在谁身上了?”
“黄主任的老婆?”
“算你娃聪明!昨天晚上下了场雨,那女人就穿着出来纳凉了。你说这么热的天气,好不容易下点雨,都不怕捂出痱子来。嘿,人家就穿出来了,你有啥办法。哼,穿么,哪一天把那个米妖精,勾引到她老汉的床上,她就不穿了。”胡彩香说得既眉飞色舞,又有些酸不溜溜的。
舅说:“都定了,让米兰上?”
“人家今天把戏都练上了。”
“让她上么。明明不行,领导还要硬朝上促呢。看我明晚不把这戏,敲得烂包在舞台上才怪呢。”
胡彩香又撇撇嘴说:“吹,吹,可吹。小心明晚上给人家献媚,把糖都喂到人家嘴里了。”
“我给她献媚?呸!”
胡彩香说:“我就看你明晚能拉出一橛啥硬货来。”
“放心,那些给哈领导献媚的,我都有办法收拾。”舅把话题一转,说,“你可得把这娃的事当事。”
胡彩香说:“放心。你这窄的床,又是个女娃,睡着多不方便,就到我那儿睡几天吧。刚好,我也能给娃说说戏。”
舅说:“那就太麻烦你了。”
“看你那死样子,还说这客气话。”胡彩香说着,就把懵懵懂懂的易青娥拉到她房里去了。
胡彩香的宿舍跟她舅中间只隔了一个厨房。房子一样大,里面摆设也几乎差不多。不过胡彩香毕竟是女的,房里就多了许多梳子、发卡、雪花膏之类的东西。走进去,先是一股香味扑鼻而来,甚至有些刺人眼睛。胡彩香到院子里端了一盆凉水回来,又把暖瓶里的热水兑了兑,让易青娥洗了麻利睡。她就出去到院子里,跟水池子附近坐着的人谝闲传去了。易青娥听见,那些话里,有一句没一句的,都与那件菊花背心有关。
易青娥洗完后,就上床缩成一团,胆怯地睡在胡彩香的床拐角了。
外面有水声,有说话声,还有笛子声、胡琴声、唱戏声。再有夜蚊子的嗡嗡轰炸声。
易青娥突然有些害怕,把身子再往紧里缩了缩,几乎缩成了蚕蛹状。
在山里放羊,即使走得再远,她都没害怕过。但在这里,她害怕了。她觉得唱戏好像没有放羊那么简单。她想回去,却又不敢对舅讲。她用毛巾被把头捂起来,偷着唤了一声“娘”,眼泪就唰唰地下来了。
《装台》
一
这几天给话剧团装台,忙得两头儿不见天,但顺子还是叼空,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
顺子也实在不想娶这个老婆,可神使鬼差的,好像不娶都不行了,他也就自己从风水书上,翻看了日子,没带一个人,打辆出租车,就去把人接回来了。
接回老婆那天,大女儿菊花指桑骂槐地在楼上骂了半天,还把一盆黄澄澄的秋菊盆景,故意从楼口踢翻,一个倒栽葱下来,连盆带花,四分五裂地解体在小小的天井院中,吓得正发眯瞪的断腿狗,一骨碌爬起来,汪汪叫着,跑回房里,去寻找自己的保护伞顺子去了。
那阵儿,顺子的第三任老婆蔡素芬,正蹲在院子角落的厕所里小解,一个迸碎的陶片,噌地穿过半截布帘飞进来,擦过她的小腿,差点没击中要害处,吓得她急忙撸起裤子,拔腿跑出来,顺着墙根儿溜回了房里。
断腿狗正颤巍巍地把屁股塞在顺子腿弯下,头向外汪汪叫着,那条断腿,轻轻踮在地上,还惶悚得一抽一抽的,蔡素芬就失脚慌忙跑回来,看看顺子,想他能有个硬扎态度。谁知顺子嘴里只叨咕了一句:“惯得实在没样子了,狗东西!”就再没下话了。
菊花已经骂半天了,蔡素芬一直希望顺子能管管,可顺子就是生闷气,多也就嘟哝一句:“啥东西!”连门都没敢出,还别说上楼管人了。蔡素芬也不好明说,毕竟这婚姻,是自己找上门来的,顺子一直都在来回着,终能把自己接回来,也算是顺子硬了头皮,下了狠心的,太不容易。可没想到,刁菊花有这么厉害,她才回来天,就觉得这日子,是没法往下过了。
蔡素芬用被子捂住头哭了起来,顺子就偎到床边哄,手里剥了根香蕉,硬要朝蔡素芬嘴里塞,还被蔡素芬抬手打掉了半截,他急忙从枕头上捡起来,塞在了自己嘴里。
顺子嘴笨,过来过去就那几句话:“女儿迟早是要嫁的,你跟我过,又不跟她过,怕啥?家家经都难念,忍忍就过去了。”
这话还算管用,蔡素芬渐渐不哭了,只用枕巾,盖着哭红的眼睛和大半个脸,留着嘴和鼻子,在外面呼呼地出气。顺子就又把香蕉剥了一根,在蔡素芬嘴边慢慢揉磨着,蔡素芬突然张大嘴,美美地咬了一口,连香蕉带顺子的大拇指,一起咬了进去,顺子哎哟一声,蔡素芬就顺势把他腕拢到了床上。
虽然才是晚上九点多,顺子就灭了灯。
断腿狗看到顺子和那个女人在床上翻动,又早早没了灯,就有些着急,对着床汪汪叫个不停,顺子骂:“没良心的东西,见不得别人锅里米汤起皮,难道也见不得我米汤锅里沁点油花花。”把蔡素芬惹笑了,扑哧扑哧的,如放了气一般的绵软无力。
正在他们享乐着人的那点要命的快活时,菊花已经下楼来了,她先是上了趟厕所,然后又在水龙头接水,故意把水开得很大,冲得满池子噼啪噼啪地响,像是老天在行风暴走。顺子和蔡素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就那样定格在一个姿势上,静静等待着。谁知菊花就在快要上楼的一刹那间,又撂出一句狠话来,像是一支毒箭,直接穿过窗户,射在了他们的心窝里:
“尾巴一揭,只要是母的,都能领上床,哼,贱种!骚货!”
顺子这回是真的忍无可忍了,他猛地翻起来,就要发飙。
蔡素芬却一把搂住他的腰,把脸紧紧贴在他的后背上说:“忍忍吧,忍忍就过去了。”
顺子觉得这回是严重伤害了自己做父亲的自尊,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是咋样把你拉扯大的,你就敢说亲生父亲这样的坏话,今天无论如何,是得给她点颜色看看了。
可蔡素芬咋都没让他下床。蔡素芬就那样死死把他腰搂着,直到他唉声叹气的,又慢慢把身子溜了下去。
可这晚上,顺子也再耍不起做男人的威风了。
断腿狗看床上再没啥动静,也就舔了舔那条断腿,早早安寝了。
大概是睡到半夜时分,素芬突然说浑身痒痒,问:“是不是家里有虱子?”
顺子迷迷糊糊地说:“瞎说,早都没见过那玩意儿了,先前有。”
“哎哎哎,都爬到我身上了,还说没有。”
顺子就开了灯,一看,是蚂蚁,还不是一个两个,越找越多,个头都一般大小,是跟猪鬃差不多粗细的那种小黑蚁。这些家伙,单个行走,几乎不容易发现,一旦集体行动起来,就是一种牵连不断线的浩荡大军。
顺子顺着蚂蚁行走的方向一看,说:“是蚂蚁搬家。咱这村子,蚂蚁多,不稀奇,小时我们经常看见蚂蚁搬家哩。”他看蚂蚁都是从房门底下钻进来的,就打开门一看,果然,月光下,一支黑色大军,正以五寸宽的条形队列,从他家院墙东头翻进来,经过七弯八折,后消失在了西墙脚的一个窄洞里。这些小家伙,多数都用两个前螯,托举着比自己身体笨重得多的东西,往前跑着。而跑进卧房的这些,估计都是出来找东西,或者是开小差跑散了的。素芬问咋办,顺子说:“它搬它的家,咱睡咱的觉,估计天亮就搬完了。”顺子说着,把床上的被子拿起来抖了抖,素芬就用脚,把跌在地上的蚂蚁朝死里踩。顺子急忙制止说:“别踩!”他用扫帚把那些蚂蚁都扫进灰斗里,然后拿到蚂蚁队伍前,轻轻倒了进去。
素芬就笑了,说:“你是吃斋念佛的呀?”
“唉!都可怜,还不都是为一口吃的,在世上奔命哩。”
早上起来,那浩浩荡荡的队伍,果然不见了踪影,只有它们行进过的路线上,丢下了不少米粒、虫卵和其他小动物的尸首。当然,也还有些散兵游勇,在四处奔走着,形不成阵仗的小东西们,就免不了,要被人有意无意地踩在脚下了。连顺子自己一脚下去,也踩死了好几只。
素芬就在后边说:“你也把蚂蚁踩死了。”
顺子说:“唉,那就是它们的命了。我不是故意的。”
《西京故事》
一
天哪,山外原来是这个样子。客车从山隘豁口七弯八拐,一钻出来,罗甲成的眼睛就直了,他想象过多种山外的景致,也听说西京城的所在地,是八百里平川一望无际,但想象毕竟是想象,真的面对这样一个所在,他还是惊呆了。这完全是一个做梦都梦不出来的广阔世界。他分明闻到了来自西京城的一种气味,这种气味带着浓浓的芳香,甜腻、油润,瞬间就把山间的那种淡淡的青草味儿弥漫得无影无踪了。
父亲罗天福看了儿子甲成一眼,又看了比儿子目光更呆滞的妻子淑惠一眼,脸上掠过了一丝小得意。这地方他是来过几次的,次还是十几年前的事,那时他当民办教师,县上为了表彰先进,把他和一群受嘉奖的人一起拉到西京城,美美逛了一趟。也就是那个时候,他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让两个孩子将来都来这里念大学,也让他们都好好活一回人。
女儿甲秀争气,前年考上了,分数之高,在县上都摇了铃了。怪他保守,只选了西京城的头牌高校,没敢再往高处想,结果分数出来,才感觉志愿报得有点亏欠。好在女儿很满足,反复说这是她满意的选择,做父亲的才感到些许安慰。女儿是他亲自送到西京城的。
有了女儿的成功蹚路,他和儿子甲成的信心也就大增,两年时间,起早贪黑,终于把儿子也盘成器了。
罗天福看着嘴巴微微张大、目光朝着四野搜寻不已的儿子,感到一阵惬意。儿子咋看都是那号有出息的种,要个头有个头,要模样有模样,看上去结结实实的,又考上了这样的名牌学校,一生的大样儿就算出来了。
这狗日的,脑子比他姐活套,才上高中时有点贪玩,学习不在前边,结果看到姐姐考了那么好的成绩,一下有了压力,后两年一年比一年学得好。填写高考志愿时,他甚至还想过北大、清华。罗天福一再提醒,让他还是稳当些,他有点不太相信儿子的估分。后,甲成还是选择了姐姐选择的学校。分数一出来,比姐姐还高两分,罗天福又觉得有些亏欠。好在这次他只是提醒,没像对女儿那样,简直是大包大揽地直接定事,志愿没报准但是学校已经很好了。女儿乖,大小事从没抱怨过父母,儿子就不一样了,他甚至感到这狗日的越来越有了牛脾气,啥事都还得顺着毛摸。幸好甲成对这个结果也算满意,他也就更感到心满意足了。说实话,他特别希望的就是姐弟俩都在一所大学读书,相互也好有个照应。这个大学的牌子也就够亮了,还想咋呀?咋想都已是一件给祖宗几代出尽风头的事了。
罗家一凤一龙都考上重点大学的事,在县上可是出了大彩了,领导在大会小会上讲,说罗家是山沟垴垴上的人,家里也不富裕,却教出了一双好儿女,是全县人民的楷模。县电视台采访,乡长还专门到家里看望、发红包,总之,自甲成拿到通知书后,家里的红火事就没断过。但红火是红火,毕竟是两个人读大学,钱也是个硬通货。大家的关心,说到底是一阵子的事,而四年的日子,却是要他罗天福拿肩膀去硬扛的。守在山里,守在他的塔云山,这个钱是咋都凑不够的。因此,他在儿子考上大学的那一刻,就毅然决然地决定:进城打工!
这个想法他已经产生两年了,在女儿甲秀进西京上学时,他就有这种打算,当时还特别去几个工地看了看,也跟塔云山出来的人见了面,想摸摸路数。但那时不行,因为甲成正上高中。在甲成上高三时,他借着看望女儿,又来了一次西京城。那次他去女儿打工的饭店,无意中接触了一个打饼的师傅,两人闲聊了几句。得知这活儿能干,就有意跟女儿流露了他的意图,说:“等甲成考上大学,如果也能来这座城市,我就跟你娘一起来打工挣钱,供你们上学,一家人也好在一起有个照应。你注意一下,有合适的地方了,给我说一声。”甲成按他的意思考进了这个城市,女儿也刚好给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他就率领一家人来了。
淑惠既激动又害怕别人听见似的悄声说:“还有这好的地方,一走几十里一脚平的路哇!”
罗天福不无得意地:“你当是,八百里都是这样一脚平哩。”
罗甲成说:“要把咱那塔云山放在这里就值钱了。”
罗天福:“那倒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