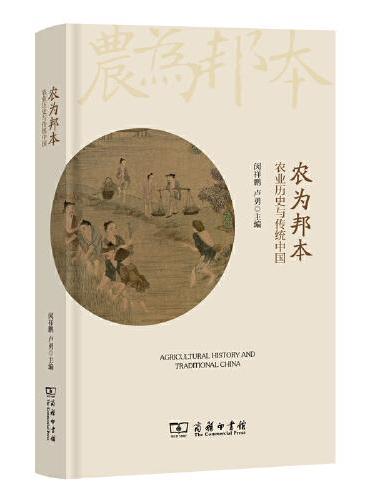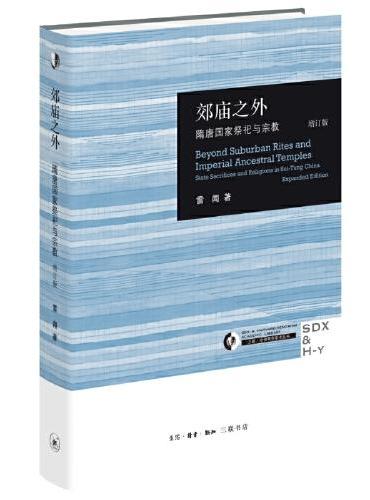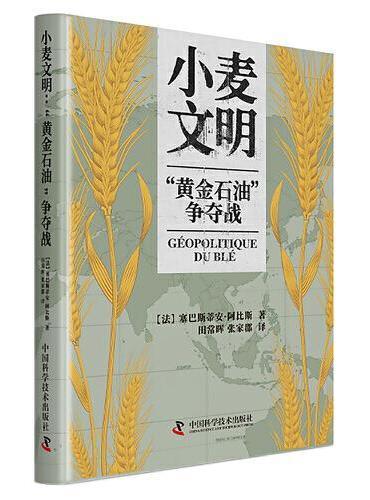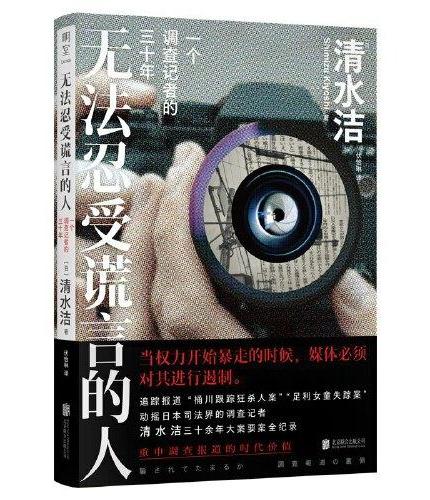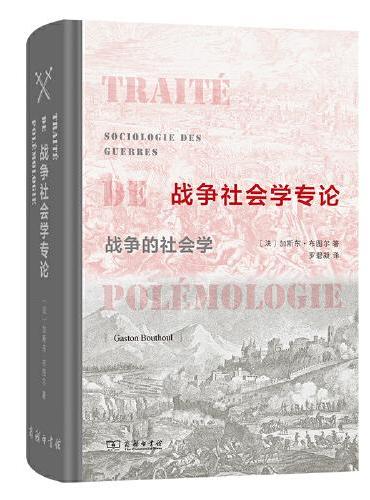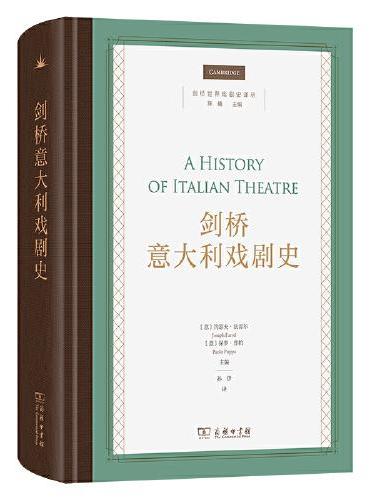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掌故家的心事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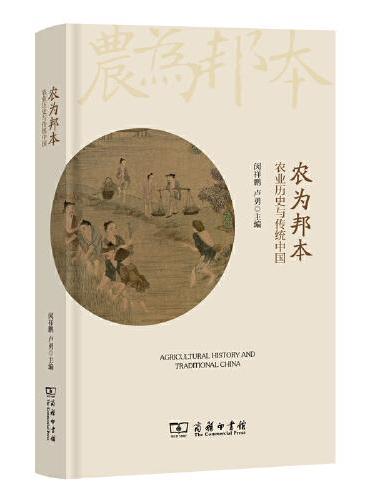
《
农为邦本——农业历史与传统中国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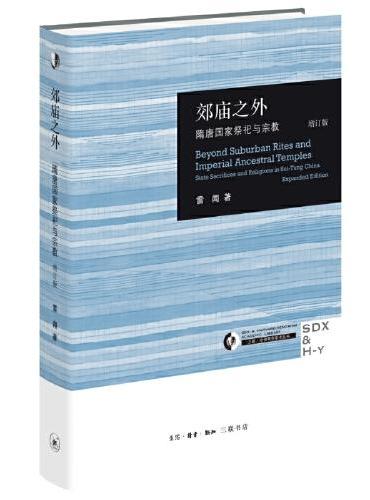
《
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 增订版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
售價:HK$
1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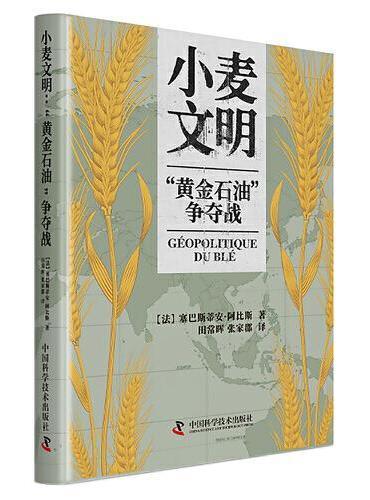
《
小麦文明:“黄金石油”争夺战
》
售價:HK$
97.9

《
悬壶杂记全集:老中医多年临证经验总结(套装3册) 中医医案诊疗思路和处方药应用
》
售價:HK$
13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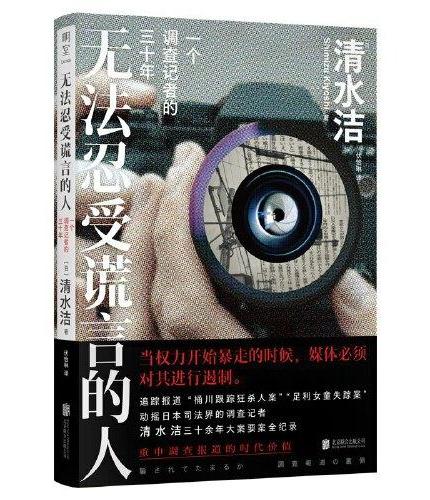
《
无法忍受谎言的人:一个调查记者的三十年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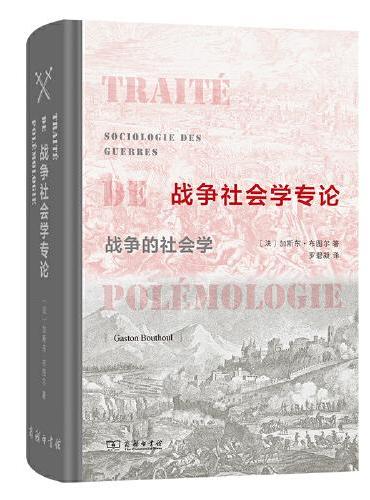
《
战争社会学专论
》
售價:HK$
1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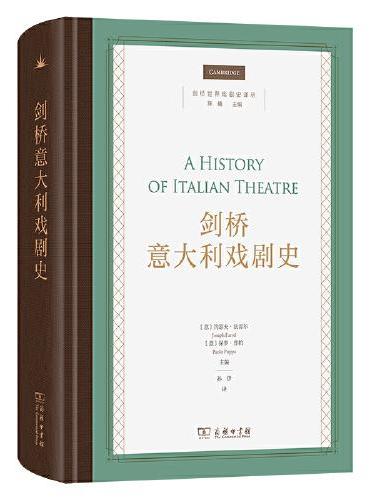
《
剑桥意大利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HK$
162.8
|
| 編輯推薦: |
|
台湾文学家朱西甯短篇小说经典大陆首次出版,彰显人之存在,人之欲念,人之性灵。——从《铁浆》中的北地乡野传奇延展至台湾市镇风情,古希腊式悲剧演变为普通人琐细日常与内心战场,呈现更为现代的深邃风景。破晓时分,天地不仁,欲与悔、罪与孽,纠结消长,彰显人之存在、人之欲念、人之性灵。“人如何靠着某些古老的信仰,不致使那世界整个虚无垮掉? ”张大春、唐诺、王德威、虹影 致敬:“朱西甯以他一人默默完成了台湾现代主义书写的实验。” ——朱西甯被称为“现代小说艺术的冶金者”“台湾*位新小说家”。作为台湾现代主义书写的开拓者,他在《破晓时分》中首次展露多向度的现代书写探索,穷究语言而乐之不疲的兴味,以及高度成熟的现代意识。“堕落的过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如何开始的?这是所有文学作品所能承受的*沉重的主题。”同名短篇《破晓时分》改写自宋代话本小说《错斩崔宁》,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破晓时分,天地幽冥,一场误判生死的官非重演了*原始的代罪仪式。朱西甯以现代手法重写经典悲剧,直指人与荒谬命运之间的纠葛,震慑人心。
|
| 內容簡介: |
听这索链,多少罪!多少孽!和多少冤苦,在一片黑森里摸索而来,在冰霜上滑来。
《破晓时分》是台湾文学家朱西甯先生的短篇小说集,收录十三部短篇经典,首次在大陆出版。人物从《铁浆》中的血气英雄扩展至普通市民,北地乡野传奇与台湾市镇风情相映照,古希腊式悲剧演变为普通人琐细日常与内心战场,呈现更为现代的深邃风景。《春去也》写春日里剿丝师傅的绵绵情思,《白坟》缅怀英雄的陨落,《偷谷贼》悼念正直的衰亡,《也是滋味》写已婚男子的意识流遐想。《福成白铁号》分别以一家四口人的视角,述说牢笼般滞闷的都市日常与生之疲倦。同名短篇《破晓时分》改写自宋代话本小说《错斩崔宁》,直指人与荒谬命运之间的纠葛,一幕震慑人心的悲剧,追问“堕落的过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如何开始的?”
破晓时分,天地不仁,欲与悔、罪与孽,纠结消长,彰显人之存在、人之欲念、人之性灵。在《破晓时分》中,健朗悲壮的北地文风仍存,同时进行丰富面向的现代主义叙事探索,开启台湾现代主义书写的实验。
|
| 關於作者: |
朱西甯(1926—1998),台湾小说家,作家朱天文、朱天心之父。
生于江苏宿迁,祖籍山东临朐。本名朱青海,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肄业。一九四九年随军赴台,曾任《新文艺》月刊主编、黎明文化公司总编辑、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兼任教授。一生专注写作,以小说创作为主,兼及散文、评论。著有短篇小说集《狼》《铁浆》《破晓时分》《冶金者》《现在几点钟》《蛇》等;长篇小说《猫》《旱魃》《画梦记》《八二三注》《猎狐记》《华太平家传》;散文集《微言篇》《曲理篇》《日月长新花长生》等。
【理想国·朱西甯作品】
铁浆
旱魃
破晓时分
狼
华太平家传(即将推出)
|
| 目錄:
|
春去也
冷雨
屠狗记
白坟
偷谷贼
牧歌
也是滋味
黑狼
失车记
本日阴雨
鬼母
福成白铁号
破晓时分
落叶落影——怀念朱西甯先生/虹影
朱西甯文学年表
|
| 內容試閱:
|
黑八说我:“这是你走运,老三!头天站堂就碰上大案子,让你见识见识。”
“好说,八爷,初来乍到的,全仗您啦多指点。”
“说不上;吃衙门饭也就那么回事儿,一回生,两回熟。”黑八从胡子嘴里摘下烟袋,磕磕我怀里的刑棍。“多早晚哪——轻重琢磨使唤熟了这副家伙,就是一辈子的铁饭碗儿。”
黑八那副神情,真像天生的就是个老长辈。
“您啦多指点,八爷!”这样的恭维也不知重三叠四多少次了。我拉拉号衣襟儿,手脚没甚么地方好安放,仿佛老这么恭维人,倒把自己弄得很不如人了。
大堂上灯烛一片明,这情势挺像上甚么庙会香堂。两廊里我们这一号的衙役大约都上齐了罢。天可真寒,一个个号衣底下衬着皮的皮、棉的棉,全都胀得滚圆,也还是冻得不住脚地跳着跺着,真使人以为一个一个操甚么古怪的兵操。这样子溜廊风,纵是裹上三床被窝,怕也抗不住,真不是滋味。还说这是一辈子的铁饭碗儿!
爹花五石麦子给我打点了这份差事。刚打三更,他老人家就把一家大小都给嘈喝醒了。热被窝可难丢。头一天当差不能马虎。天寒地冻的,娘也嘱咐,老婆也叮咛,多穿点儿呀。
新号衣,没想周全,该裁肥敞些儿;光衬小棉袄可架不住,没出房门就哆嗦了。要是单衬皮袄,空心壳儿更加不兜暖。怎样计算也不行,由着娘和老婆撕扯,穿上又换下,若想皮的棉的一总衬进号衣里头,算是没辙儿了,抖得我一个跟一个打不完的喷嚏,人倒是真真地清醒过来。大嫂子把鸡蛋鳖子下好了,爷儿俩,一人三个,吃着的工夫,娘又不甘心地翻箱倒笼,算是找出爹一件没吊面子的胎羊皮筒子,凑合着这才上道儿。
爹不知是把我当作多大的孩子,打着灯笼硬要领我上黑八家。到处是零星的寒鸡早啼,灯笼照不出地上怎么样,脚底下倒是有数,喀嗤喀喳,不是冰碴子,就是霜屑。
“这天哪,一劲儿干冷!”
爹嘴巴埋在风帽兜儿里嗡嗡地说不清。我真懒得从帽兜儿里露出光嘴巴来回应他老人家。爷儿俩埋着头走在不见人影儿的街巷里,黑沉沉的偌大一个深夜,单由咱们父子俩力顶在身上,心也压紧了。
有黑八领着上衙门总该放心了,爹仍然一直跟到衙门口,袖手立在那儿不肯回去。灯笼杆儿袖在装粮食口袋一样肥的袖笼里,灯笼从下面照上去,爹那张富富泰泰生意人的胖脸上,黄是黄一块,黑是黑一块,活像贴金的泥菩萨日久剥落了。他老人家傻傻地望着甚么,背后衬一些灯火和烟雾,专做衙门生意的胡辣汤、煎包子、打炉饼、油条热粥,生起一街的火烟,把衙门两旁站笼的大黑影子投到两侧的粉壁上,一条一条横来竖去的条纹,深的和浅的,罗织出格子洋布一样的花色。
“八爷,早班哪!”
扛洋枪的守卫子一张口就是一团白气,顶面跟黑八打招呼。脸上和身上落满那些条纹,仿佛人正关在站笼里上刑。
“辛苦了,老弟,该换班儿了罢?”黑八冲着那站笼噘噘嘴,“老没生意了!”
“快上生意了。”黑八侧过脸告诉我爹说。
可他老人家傻傻地望着甚么,似乎他得牢牢地盯紧,提防那已经看在他眼里的,一不经心又从眼角溜走了。他若是也能进衙门,怕也少不得陪着儿子捱冷受冻地待在这儿伺候了。
而冬夜长无尽头,离天亮不知还有多久。
“你过来一下,老三。”黑八领我跟一个挺面熟的老家伙打照面。“我给你引荐引荐,这位章老大——立早章,西廊的老伙计,侍候过七任大老爷,你多跟他讨教讨教没错。”
赶上一步去,我打了个千儿:“章大爷,您老前辈多指点!”都是同廊吃饭,原犯不上;只怪初来三天生,不能不攀一攀,多买一点账,又是黑八引荐的。不过若论那把年纪,跟他打个千儿,小不了我,也大不了他。
“火神庙背后陆陈行的少老三。”黑八拍拍我说,“我这就托付你就近多关照了。”
“得,老八,咱哥儿俩还有说的!”
这位章老大总也有六十开外了,瞧那副精神真不输给年轻小伙子,两廊下数他穿着单。
“交冬数九,我就是这一身。要不,三十来年的太极拳一天没拉过,白摸啦?”
“你行,老大,千年王八万年龟,都给你占全了。”
“说你不服,哪天咱哥俩儿找个时间较量较量,单来弹腿,你弹几路,我照加你一番!”
他俩大约就是这么逗惯了的。
“小老弟别见笑,咱俩老家伙碰到一起,连荤加素啥都来的!”
有这么两个又风趣又不见外的老前辈关照,这份差事倒真干得,爹就是再花上五石小麦也划得来,横直咱们家开的是粮食行。
“我说小老弟,把那个吃饭家伙先靠墙上罢,”章大爷指的是我怀里这一副像支船桨的刑棍。“别死掯,大老爷升堂还早着!”
听他们说,县大老爷有一口老瘾,一睁开眼,来不及烧泡子,先得调半盅膏子灌下去,然后才得躺下来,平心静气烧上半个时辰,要不就上不了堂;上了堂也撑不到时候。
“今儿有个大案子,定要多耽搁。大老爷这口瘾只怕十个泡子才过得足。”
“那可不!”
黑八打勒腰带里抽出一串子烟袋荷包,左近几个一人请了一窝子烟丝。
“八爷这是几品来着?”
“人是十八品外不沾边儿,抽的是一品香——就这点儿还值几文!”
有的就溜沟子,品品味儿说:“我尝这是凤台庄出的,八爷你还客气!”
我这个烟酒不沾嘴儿的,夹在里面好像不知多出多少手脚,多得没处可放。就想轻轻地退后些儿。黑八倒像存心当着众人抬举我,把他抽了一口的烟袋捽在手心里擦了擦碧玉嘴儿,横过来敬我一袋。
“我……我……”我摆着双手推拒,不懂该怎么应付才算不失礼数。这就怨不得爹仍把我当作个孩子看待了。
“在理儿?”
“我……我欠学!”我这一急,居然急出词儿来了,趁势儿赶快往后蹭蹬两步,手放在嘴巴上呵暖。溜廊子风吹得两条腿好似没穿裤子。
堂上有人在那儿走动,想是大老爷快升堂。灯火把三两个人影摔到廊前青条石的台阶上,脑袋朝下,仿佛人是截成一段一段儿地倒悬在那边来去晃动。
有两个内衙听差样子的,抬一架大火盆送到当堂的高案子背后。一股子木炭香,浓浓的年意,高案子搭着金黄缎子桌围,上面绣着四爪蟠蟒。
这几个凤台老家伙,聊的是今儿这案子。那黑八好像甚么他都比别人知道的多,净听他拉咕。
“有奸必有杀,你就记住这个道理,没错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