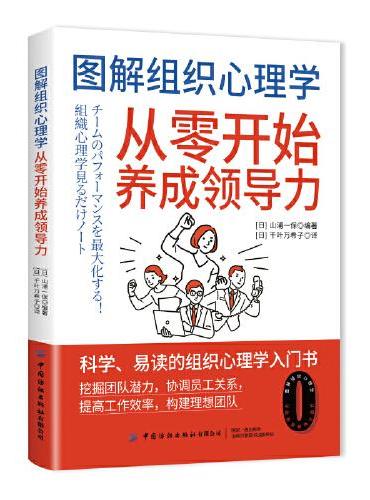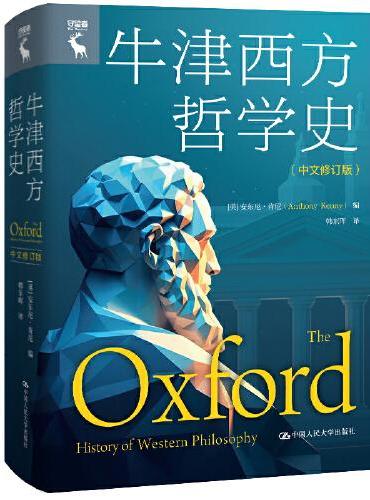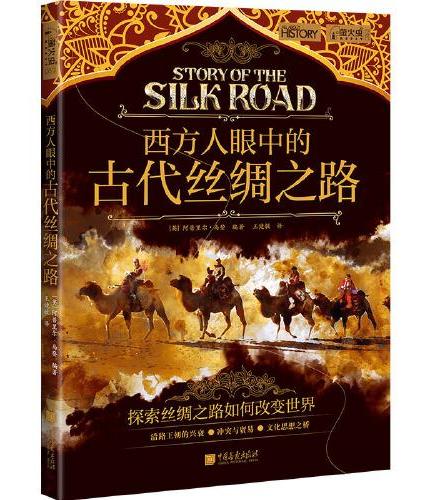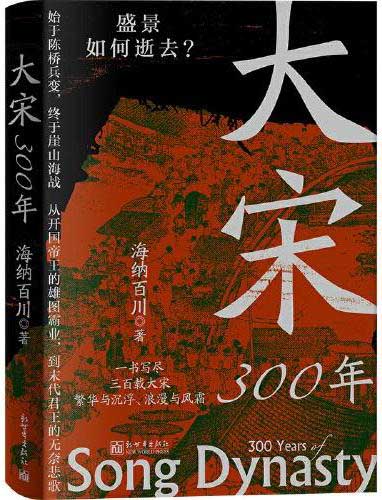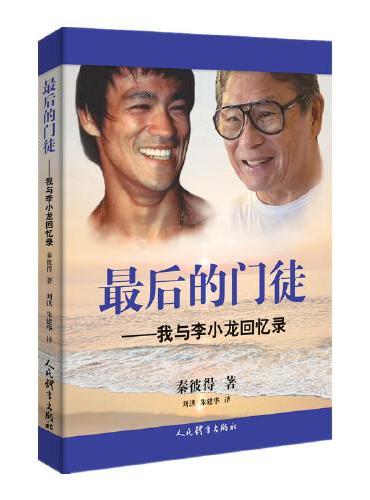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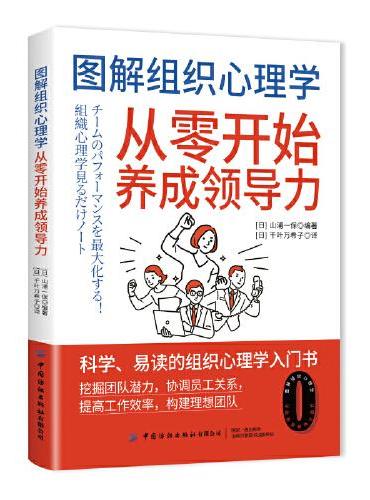
《
图解组织心理学:从零开始养成领导力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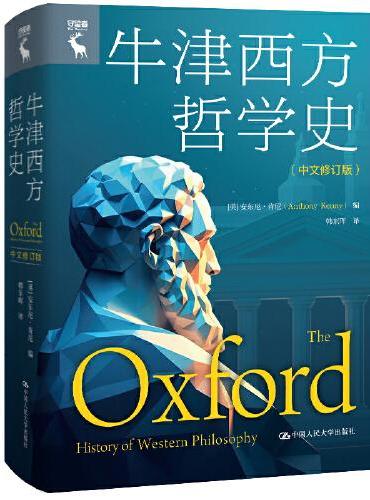
《
牛津西方哲学史(中文修订版)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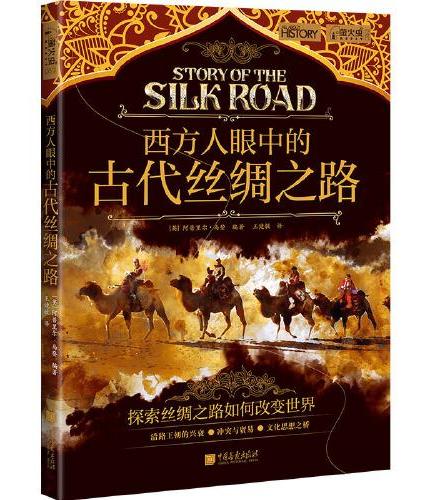
《
萤火虫全球史:西方人眼中的古代丝绸之路
》
售價:HK$
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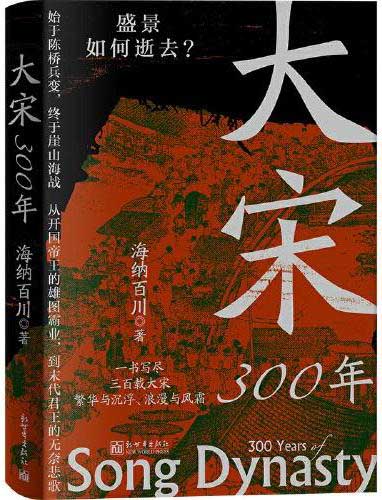
《
大宋300年(写尽三百载大宋繁华与沉浮、浪漫与风霜)
》
售價:HK$
75.9

《
害马之群:失控的群体如何助长个体的不当行为
》
售價:HK$
96.8

《
性别:女(随机图书馆01)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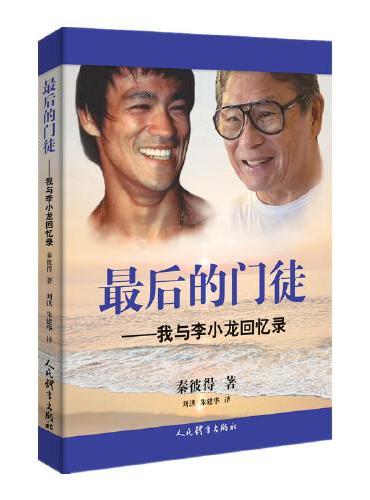
《
最后的门徒——我与李小龙回忆录
》
售價:HK$
74.8

《
没有明天的我们,在昨天相恋
》
售價:HK$
47.1
|
| 編輯推薦: |
|
在《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一书中,叶拉·莱普曼以朴实无华却又不乏幽默的笔触描写了她生命中的一项伟业:创建和发展国际青少年图书馆。本书创作于德国,并于1964年在德国首次出版。本书开篇讲述了1945年秋,叶拉·莱普曼结束了在英国的流亡生活重返德国时的情形,一直写到1957年莱普曼从图书馆工作岗位上退休作为全书的结束。如果回顾一下过去十二年的经历,七十岁的叶拉·莱普曼肯定想象不到她这个“特殊的孩子”——国际青少年图书馆会变得如此成功和经久不衰。
|
| 內容簡介: |
|
本书讲述了叶拉?莱普曼不平凡的故事。为了躲避纳粹政权的统治,她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离开德国,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毅然选择了以“妇女儿童文化与社会需求顾问”的身份返回祖国。她很快就断定,饱受战争蹂躏的德国儿童需要看到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而非到处是被炮弹炸得满目疮痍的建筑物和军用车辆。她与官僚主义进行顽强斗争,并极力争取各界人士的支持,终于在慕尼黑创立了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用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图书填补了德国少年儿童生活中的巨大空白。国际青少年图书馆包括一个艺术工作室、各种写作班、读书会、外语学习班,以及一个叫做“青少年联合国”的组织。这座图书馆目前位于慕尼黑的布鲁腾堡内,拥有130个语种的50万册藏书。
|
| 關於作者: |
|
叶拉?莱普曼于1949年创立了国际青少年图书馆(IYL),后来又于1953年创立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1891年,她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父亲是犹太人,开有一家工厂,莱普曼在三姐妹中排行第二。十七岁时,她就建立了一间国际儿童阅览室。莱普曼的丈夫是一位德裔美国人。在她年仅三十一岁时,丈夫就抛下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撒手人寰。莱普曼后来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并于1928年出版了她的部儿童著作。希特勒上台后,莱普曼失去了在德国民主党内的职位。在朋友的建议下,她去往伦敦避难。本书以九年后她被说服重返战后德国开始为写作背景。
|
| 目錄:
|
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附录一 英文版序言之一
附录二 英文版序言之二
附录三 图书城堡
|
| 內容試閱:
|
章
什么样的儿童读物都没能保留下来,比起其他所有种类的图书,我们更需要它们。
“如果有来生,您想做男人还是女人?”
向我发问的是美军的一名空军上校。那慢吞吞的口音表明他来自美国南部。当时我正坐在他旁边那个叫作“单人座椅”的蹩脚装置中。那天是1945年10月29日,我们乘坐的军用飞机正从伦敦飞往法兰克福。
上校此前一直没有开口,就在他试图通过发问打破沉默时,我正在用一个很不淑女的比喻来形容那把单人座椅。我猜得出他正在想些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一个女人在这儿做什么?女人穿军装已经够荒唐的了。我宁可看到她们像巴黎的女人一样,穿着雪纺绸的裙子漫步在帕斯大道上——看,我们现在正从它的上空飞过!有时候,司令部真是愚蠢透顶。”
我当时对如何与因公务出差(或者也可以说是因公务乘飞机)的美国空军上校进行谈话一无所知,只好说:“如果这纯粹是个假设性的问题,我想我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回答。我哪种人也不想做,我宁可做一只小老鼠或一株向日葵,抑或……”
上校险些从他的位子上跌落下去。带有如此浪漫情怀的答案甚至比他想象中的回答更为可怕。他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然后生硬地问道:“那您为什么要穿军装?司令部想让您做什么?您能告诉我吗?”
“再教育,上校,”我答道,“或者说,这是他们的说法。他们希望我跟妇女和儿童打交道。目前,我只知道这么多,巴特洪堡的司令部大概也只知道这么多。也许有人认为这种工作需要带点儿女性特色。”
这时,飞机突然开始翻筋斗,我们的谈话进行不下去了。我感到难受得要死。早上飞机起飞时,我省掉了那顿著名的英式早餐,可没想到那竟是我一天当中一次用餐机会。上校注意到我的脸色煞白,便默默地把一包口香糖塞到了我手中。这种解药的确很管用——我把那块又软又黏的东西填进嘴里,颇有几分战后军人的感觉——在接下来几个小时的飞行中,我的双眼便再没睁开过。
当你这样闭上双眼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突然间,你陷入了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无边无垠、深不可测的地方,如同爱丽丝置身仙境之中。此时,你开始体验到一种真真切切的终极自由,在这个世界中,牢狱变得畅通无阻,而原来那把令人难受的单人座椅则变成一把舒舒服服的安乐椅。
在另外的那个世界中,我不再感受到军装和安全带的束缚,眼中的色彩也不再只有草黄色和灰色,我对即将到来的崭新的冒险经历感到万分激动。就在一周前,我还和一群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坐在办公室里——我们的办公室位于伦敦格罗斯维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内。当时,我们正在策划《女性与世界》杂志的期,它即将以十种语言在全欧洲发行。然而,在工作中,我们总是感到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
我看到自己与朋友——《哈珀时尚芭莎》杂志社的弗朗西斯?麦克法登——坐在桌旁一筹莫展,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内容才会吸引那些在地狱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免于难的人们。
“肯定不会是《哈珀时尚芭莎》的时尚照片。”弗朗西斯皱着她那智慧的额头说道。
“你怎么知道呢?”我说道,“没准儿他们会感兴趣的。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向他们展示怎样将麻布做成各式时装,只是为了证明这些东西依然存在。”
“也许有这种可能,”弗朗西斯说道,“当初希特勒发动闪电战时,我们正在伦敦。哦,那简直糟糕透了。但那是战争‘本身’,而不是这些人经历过的一切残酷。”
“‘拿扫帚的女人’怎么样?”我说道,“这种话题应该是无可挑剔的。”
纽约的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曾写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后来在全球被转载,内容讲述的是欧洲女性如何拿起扫帚清理战后废墟的故事。我们曾为那篇文章配上了照片。至于照片是如何得来的,还真值得在此交代一番。
当时我们收到纽约《生活》杂志的编辑发来的一封电报,说他们杂志社一位秀的摄影师将于第二天上午抵达伦敦来拍摄“拿扫帚的女人”。
“我们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女人呢?”弗朗西斯问道,这让她伤透了脑筋,“她必须是某种特定的类型——我能想象出她的样子,可就是不知在哪儿才能找到她。不过,从《哈珀时尚芭莎》旗下的模特里肯定找不到。”
忽然,一个念头从我脑中一闪而过——为什么不找我认识的那位格拉布尔太太呢?如果没有她,我很可能经受不住战争的磨难。
“为什么不找格拉布尔太太呢?”我提议,想助弗朗西斯一臂之力。她认为这个主意不错。“我会开车回家告诉她这件事,等明天上午我再把她带过来。”我说。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家时,格拉布尔太太正在给前门上锁。像往常一样,她那顶深棕色帽子上装饰着一丛一直垂到脖子的蜡菊花。
“拜托!”我大声说道,“明天和我一起去伦敦,好吗?我请客。”我知道不能对她说出自己真正的意图。伦敦的女佣是很奇怪的一类人,她们是永远也不会让自己成为“拿扫帚的女人”的。
“哦,夫人,您真是太好了,”她说道,“但是我不能接受您的好意。不管怎么说,我还从没去过伦敦呢。”
她口中的“不管怎么说”很不合逻辑,因为她的整个反应相当激动。她的住处距离伦敦西区和伦敦市区只有几英里远——乘地铁只需一刻钟就可到达市中心。
可是,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她的话——她也许理解力不够高,但她从不说谎。
“那样说来,你可真该去一趟伦敦了。”我说道。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她准时出现了,可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恐怕她动用了一笔巨额开支,连头发都烫过了——她原来梳的是“鸟窝头”,现在却煞费苦心地烫成了满头小卷。她那件带有彩色口袋的蓝色棉布围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估计是她的结婚礼服。
我哭笑不得,却又不敢流露出来,便对她说我们的伦敦之行不得不延期了。她是个忍受力很强的女人,同时还具有非同一般的善良品质,反倒马上开始安慰我。
幸运的是,《生活》杂志社的摄影师迟到了七个小时——在那些日子里,日程表太容易被打乱了。我答应杂志社第二天会竭尽全力争取让她恢复原貌。你猜怎么样——一切进行得异常顺利!格拉布尔太太烫的小卷都散开了——真不愧是战争年代烫的头发。棉布衣服和围裙、饰有蜡菊的帽子和鸟窝头——一切都恢复了原样。
我对格拉布尔太太说,我们得马上动身去伦敦。哦,一想到她那身寒碜的衣服会令我难堪,她的表情是多么绝望啊!我赶忙披上外套,一下子抓过厨房里的扫帚——一把稻草做成的真正的女巫用的扫帚,拉着她急匆匆地向地铁站奔去。等我们落座之后,她才惊呼道:“天哪,夫人!您拿着那把扫帚干什么?刚才我们在街上时,您该不会一直拿着它吧?”
“哦,亲爱的,”我说道,“我肯定是匆忙中把它当成雨伞了。”我们俩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们在邦德街出了地铁口,结束了“暗无天日”的旅行。我一直牵着格拉布尔太太的手,因为她已经被这个新奇的世界搞得晕头转向了。我们穿过梅菲尔酒店,来到了位于格罗斯维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
弗朗西斯接待了我们,并请格拉布尔太太喝了一杯“好茶”。《生活》杂志社的摄影师也来了,而且来得正好,不早不晚。过了一会儿,我们便下楼,坐上了使馆的一辆黑色宾利车——我手里还紧紧地握着那把扫帚。
我们一行驱车驶过伦敦西区。一方面,西敏寺的庄严令格拉布尔太太心中充满了敬畏之情,而另一方面,炮弹的破坏力又令她感到惊骇万分。然后,我们来到了圣保罗大教堂。虽然周围的一切已被毁坏得惨不忍睹,但这座大教堂依然雄伟地矗立在废墟之上。格拉布尔太太误把圣保罗大教堂当成了一家豪华影院,她激动地握紧了双手,我们颇费一番周折才向她解释清楚是怎么回事。
“格拉布尔太太,这位美国摄影师想在这儿拍一些关于圣保罗大教堂的照片,”我说道,“现在,我的扫帚可派上用场了。”
格拉布尔太太麻利地拿起她那值得信赖的老朋友——手中的扫帚,不一会儿工夫,就在四周掀起了一片尘土。她起劲地扫着,好像扫地就是她的职业似的,而那位摄影师则趁机一张接一张地拍个不停。后来,我们请格拉布尔太太摆个姿势照张相。她颤抖着双手,捋了捋头发,拽了拽围裙,像小孩子照证件照一样站得笔直。后,那位《生活》杂志社的摄影师冲格拉布尔太太深深鞠了一躬,仿佛她是一位女王。
时至今日,这幅照片仍挂在格拉布尔太太的房间里,成为她一生中难忘经历的永久的纪念。“拿扫帚的女人”传遍了全世界,而格拉布尔太太至今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十分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这份工作,直到有一天,一位美国陆军上校(他的平民身份是一位大学教授)叩响了我的大门,并直言不讳地问我,一旦一切安排就绪,我是否愿意飞往设在巴特洪堡的美军司令部,去担任美军占领区内妇女儿童文化和教育需求问题的顾问。
我后来才发现,那位上校兼教授是位好心人,但当时我却被他吓坏了。我在希特勒执政期间逃离了德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用语言是无法说清楚的,其后发生的一切只有上帝才知晓——我忽然用双手掩住了脸。
一般来说,男人对哭泣的女人缺乏耐性,美军上校当然也不例外。眼泪是他们压根儿就不习惯对付的武器。终于,我让自己镇定下来,直视着他,说道:“上校,请让我仔细考虑考虑。这可不是个轻易就能做出的决定。”
接下来的两周里,我为了这个问题经历了痛苦的煎熬,但是没有谁能帮得了我。这将不得不是一个纯粹个人化的决定,尽管我不想理会,但我已经感受到了命中注定的结局。
“我真羡慕你,”弗朗西斯对我说道,“你受过教育,又懂得多种语言,还与那些人共同生活过。瞧,我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这样一个职位,因为我一点都不适合。”
另一位朋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女儿劝我:“不要去。你已经遭受过太多痛苦,好不容易才开始在这儿扎下根来,再说,无论如何,人是不可能被重新教育好的。”
“不要去,”其他人也这样说,“难道你相信纳粹的阴魂真正消亡了吗?不,它还会延续给几代人,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倾力相助也无济于事。在过去的六年中,德军的炸弹随时都有可能让你丧命,难道你还没有受够这些吗?”
但是我的处境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果只涉及成年人,我会毫不犹豫地说“不”。就成年人而言,“再教育”这个字眼在我听来没有丝毫意义。但如果涉及孩子——这种做法难道不会使事情有所改善吗?
不难相信,如果外界不伸出援手,那些孩子们会很快落入坏人之手。德国的少年儿童难道不是跟全世界的少年儿童一样无辜吗?在那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中,他们不也是无可奈何的受害者吗?
与此同时,铭刻在记忆深处的一幅画面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战争爆发前不久,在英国一个救援组织的帮助下,我成功地使一位好友的孩子得以离开德国。后来,我得到消息:小姑娘乘坐的那列火车大概在那天中午到达,来自利兹的一家人会来接她并收留她。
于是,我胸前紧紧裹着一条暖和的披肩,抱着一盒糖果前去等候。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车站的中央大厅。虽然才是中午,大厅里却黑暗而闷热。我站在那儿陷入了沉思——我自己也是个无家可归者,因而无法给那个孩子提供庇护。后来,孩子们出现了——大概五十个,既有男孩,也有女孩,年龄大多在八岁到十岁之间。他们都很懂礼貌,但个个神色疲惫。他们穿着保暖外套,戴着厚厚的帽子,我能想象出他们的母亲是怎样用颤抖的双手为他们穿戴整齐的。
孩子们严肃的脸庞令人动容,因为在我目前居住的国家,孩子们的生活充满了欢笑和快乐,而这些孩子——他们的眼睛曾有过怎样的所见?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痛苦的离别啊!
我把小姑娘拥入怀中,她没有说一个字。她顺从(其中的原因我不得而知)地跟着我来到桌子旁,接过了一碗汤。尽管对于像她那样的德国儿童而言,橙子早已从他们的世界中消失了,然而面对放在她面前的一个橙子,她却丝毫未动。
有人大声喊出了孩子们的名字,于是那些前来领养的人轻轻地牵着这些小难民的手,一个接一个地走开了。到处都可以看到女人们满怀同情地去亲吻和拥抱孩子,这些场面显示了人与人之间那种非同寻常的同胞之爱,而这感人的一幕就发生在一座伟大城市的火车站候车室内。这对那些造成这些孩子不幸命运的刽子手是何等强烈的控诉啊!
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千万不能回头,必须向前看,而且必须首先从儿童抓起。这一想法的正确性几乎不容置疑。我有什么权利对上校说“不”呢?于是,我答应了这件事——也许只是暂时答应下来,通向过去生活的大门依然为我敞开。
我摇了摇头,不再回忆往事,而是重新回到了飞往法兰克福的现实旅途中。如今,我戎装在身,肩负着一名军人的职责,只有穿军装的人才被允许进入美军司令部;平民穿的是一种特别的服装。不过,我宁可穿着雪纺绸做的裙子漫步在帕斯大道上……
下午四点左右,我们降落在法兰克福的军用机场。我们出了飞机,默默不语地走下陡峭的舷梯。我又一次踏上了德国的土地。
我和一位年轻的加拿大秘书是飞往巴特洪堡司令部仅有的两名乘客。司令部本来应该派军用吉普车来接我们,可我们连一辆车的影子也没有看到。于是,我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沐浴着十月的后几缕阳光。我们一边等,一边看着临时接待大楼的圆形大厅中一位年轻的姑娘正忙得不亦乐乎——她一会儿发布信息,一会儿打电话,其实我们想看的是她在那里竭尽所能地卖弄风情。我感觉这一切有点像是在看电影。
那位年轻的姑娘是我们遇到的个德国人。她长得很漂亮,烫了头发,还穿着尼龙丝袜。她流利地说着一口带有美式口音的英语。很显然,我们原先头脑中那幅忏悔的画面看来是大错特错了,可我们哪知道这个姑娘是经过特意挑选才被派来协助美军工作的——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尽管美军严禁自己的部队“亲敌”,但美国军人总是能想方设法将尼龙丝袜偷偷送到姑娘手中。我们已经意识到,初来乍到,肯定还会遇到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
那位姑娘打了几个电话之后,一辆大轿车——不是吉普车——终于停在了我们面前。“你们好,姑娘们!”司机向我们打着招呼,随后我们就一屁股陷入了软软的坐垫中,毫无疑问,这种坐垫是为三星上将准备的。
即使是坐在车里,我们还是注意到整座城市已沦为一大片废墟,这令我们感到非常震惊,难过得禁不住浑身战栗。
“这就是法兰克福的样子,”那位加拿大人说道,“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说完,她拉下帽檐遮住了眼帘,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她就这样一动未动地呆坐着。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而我尽管已经目睹过伦敦的惨状,可还是与她一样深有同感。
我印象中的法兰克福曾是一座美丽的商业之都。孩提时代,我就曾沿着梅恩河的码头散步,还曾到过歌德的故居,对这位伟大的德国人的生活有过匆匆一瞥,而现在这座城市剩下的只有废墟、瓦砾和笼罩在城市上空乌云般的一团尘雾。
人们都去哪儿了呢?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他们悄无声息地从街上走过时,神情都显得非常机警。他们与机场圆形大厅内的那位年轻姑娘没有丝毫相似之处。经常看到从街角处闪过一个人影,令人分辨不出是男是女,只看到他(她)先是惊恐地环视一下四周,然后从废墟中捡起一捆木柴。这些人对我们丝毫不予理会,只有一次例外——一个孩子向我们挥了挥手。她坐在一段被炮弹炸掉一半的楼梯上,手中拿着一朵秋天的花——这真是奇迹中的奇迹。此后,我常常想起那个孩子。
夜幕降临之后,我们终于到达巴特洪堡,这是当时的美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大门周围都是带刺的铁丝网,门口哨兵林立,在仔细检查过我们的证件之后,他们才把我们放行。接下来,我们看到所有的建筑物内都是一片灯光的海洋,音乐声随风飘入耳中,身着军装的人们在住宿区的街道上有说有笑地散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