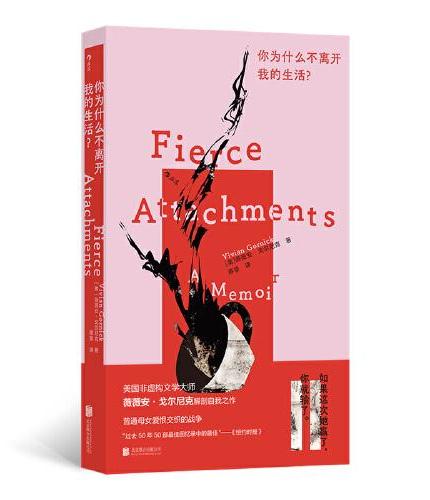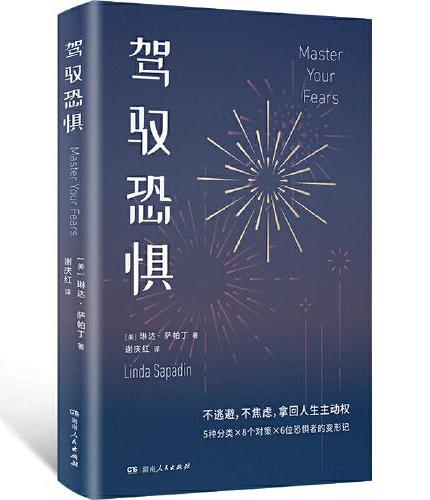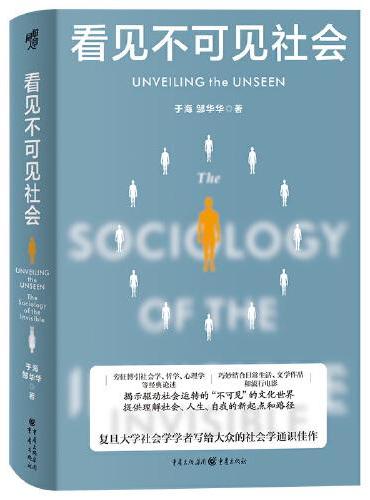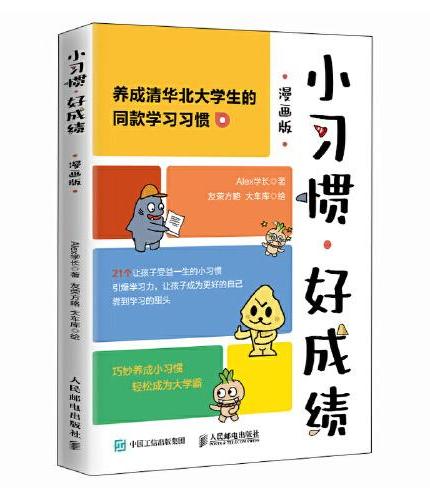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的一种新经济结构
》
售價:HK$
15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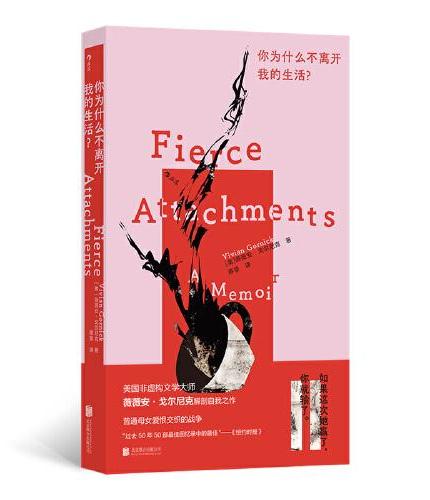
《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
》
售價:HK$
54.8

《
揉碎温柔
》
售價:HK$
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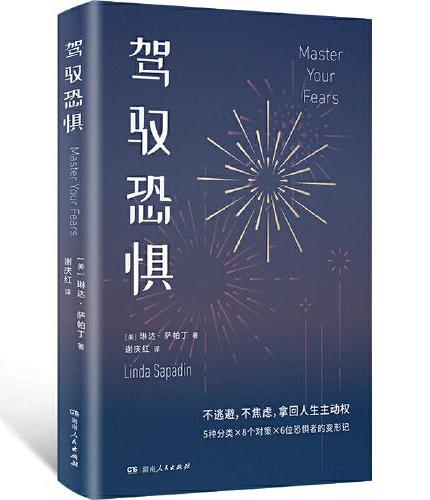
《
驾驭恐惧(菲利普·津巴多力荐的时代读本!减少焦虑、控制情绪、一键重启人生!)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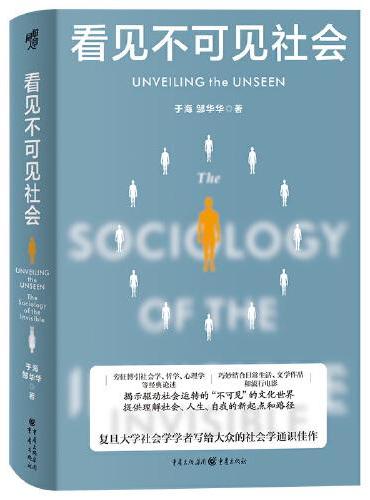
《
看见不可见社会
》
售價:HK$
79.2

《
先懂孩子,再教孩子:7堂亲子沟通课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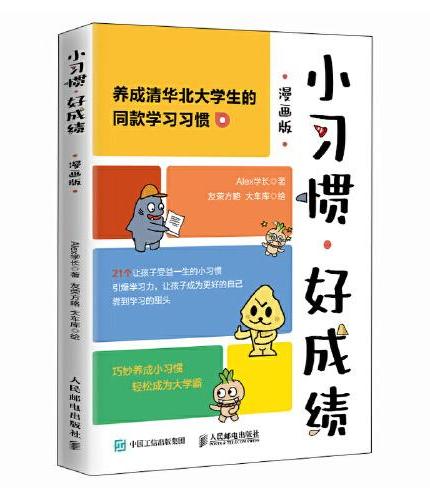
《
小习惯,好成绩(漫画版)
》
售價:HK$
58.1

《
盛夏光年
》
售價:HK$
54.8
|
| 編輯推薦: |
▲ 波伏瓦,世界女权运动先驱,20世纪*有影响力的伟大女性之一。
▲ 《清算已毕》为波伏瓦四卷本回忆录的最终卷,中文版首次正式授权出版!
▲ 她是对世界女性主义运动影响深远的思想家,是亲历重要国际事件和民间运动的社会活动家,也是获得法国至高文学奖的作家,多重身份使她的回忆录具备了难以比肩的广度、高度和深度。
▲ 关于自我认知的分析、女性意识的辩证思考,鞭辟入里,可谓当下广大独立女性寻求自我觉醒的精神典范。
▲ 听波伏瓦说波伏瓦:关于生存、死亡、亲情、爱恋、友谊的梳理和反思。在大众熟悉的强硬外壳之下,波伏瓦在回忆录中坦率表露自己柔软长情的一面:我是个特别不愿意失去过去的人,找回青年时代的这段友谊对我来说弥足珍贵。
▲ 关于她的阅读和写作,看波伏瓦如何正面回怼偏见舆论对其作品的谬评和攻击。
▲ 与萨特游历世界各国:意大利夏日风情,日本社会见闻、禅与艺术,在法国乡间重新发现旅行的意义
▲ 亲历20世纪国际风云:会见苏联领导人,与意共、法共的领导人的交往,与萨特一起参与
罗素法庭对越战暴行的审判工作,1968年法国历史上著名的五月风暴学潮始末及其影响,还有埃及、布拉格、巴勒斯坦
|
| 內容簡介: |
《清算已毕》为波伏瓦四卷本回忆录的*后一卷。
作者在本卷中回顾了其性格的成因,与重要女性友人的交往,与萨特游历世界各国的见闻,她的阅读与写作,她对文学、艺术和国际政治的看法,等等,并对于《第二性》中提及的一些女性主义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补充阐述,可以说是对前三卷的总结,对研究波伏瓦的著作与生平具有重要意义。
|
| 關於作者: |
西蒙娜德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法国哲学家、作家,女性主义重要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被认为是启迪了全世界女性以及改变了许多人思考方式的伟大女性。
1945年与萨特共同创办《现代》杂志,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1954年,她凭小说《名士风流》获得龚古尔奖。晚年出版了自传体回忆录四卷,《清算已毕》为终卷。
|
| 目錄:
|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102
第三章............................................................. 123
第四章............................................................. 191
第五章............................................................. 229
第六章............................................................. 256
第七章............................................................. 306
第八章............................................................. 382
媒体评论这是波伏瓦时期*的编年史。
法国《世界报》
在波伏瓦的笔下,那些知识分子的面孔都复活了。
《法国文化》
作者逝世32年之后,她的回忆录终于被收入了著名的七星文库。
《费加罗报》
在线试读关于萨特
假如没有认识萨特,我会如何发展?我会更早还是更晚摆脱个人主义、理想主义和唯灵论的困扰呢?我不知道。事实是我遇见了他,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
我很难确定那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遇到他不完全是个意外。由于决心要上大学,我已经给自己创造了最大的机会,来促成这样一场相遇:十五岁时,我就梦想自己的理想伴侣一定要是个知识分子,与我一样渴望了解世界。另外,自从进了索邦大学,我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留意在我的同学中找到那个我与之最契合的人。我的开朗待人为我赢得了很多友情,先是赫尔博,通过他我又认识了萨特。
不过,如果他早一年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如果我晚一年参加考试,我们会彼此错过吗?也不一定。赫尔博会为我们牵线搭桥。我们甚至常常设想,就算1929年没有相遇,我们相识也是迟早的事,因为我们后来都加入的年轻左翼教师联盟是个小圈子。我肯定会写作,与一些作家交往,会看到萨特的书,进而希望结识他。由于反纳粹知识分子团结一致,我的愿望在1943年到1945年之间肯定会实现。我们之间必定会建立某种联系,也许与现在不同,但必定非常密切。
如果说我们的相遇部分是出于偶然,后来把两人生命连在一起的那个契约则是我们主动选择的:这种选择不是简单的决定,而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我的选择首先体现在:我决定留在巴黎两年,先不去担任教职。我接受了萨特的朋友们,走进了他的世界,并非像某些人说的因为我是个女人,而是因为那是我向往已久的世界。他也接受了我的朋友圈子,与扎扎很合得来,但不久之后,我的旧友里就只剩下我妹妹、斯黛芬和费尔南德了。萨特的朋友比我多,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是出于情感,有些是由于观点一致。
我警觉地经营着我们的关系,避免让它褪色。我掂量着,我和他身上哪些东西可以接受,哪些应该杜绝,免得损害我们的关系。我本该同意让他去日本,虽然不情愿,也不至于感到绝望,两年之后我们肯定会像彼此承诺的那样重新在一起。那期间我做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去马赛,而不是跟他结婚。在其他所有问题上,我的决定都符合自己内心的愿望,除了这件事。我很不想离开萨特,然而考虑到未来,我选择了当时对我来说最难的那条路。那也是唯一一次我感到自己的决定使我避开了某种危险,给我的生活来了一记有益的当头棒喝。
如果我接受了,又会发生什么?这个假设毫无意义。我一向懂得尊重别人的选择,我知道萨特不想缔结婚姻,我不能一厢情愿。我曾经在一些小事上强迫过他(他也对我做过同样的事),但永远不能想象自己在重大问题上逼他就范。如果万一出于我想象不出来的原因我们不得不缔结婚姻,我知道我们也一定能想出办法,维护两人的自由。
关于美国关于萨特
假如没有认识萨特,我会如何发展?我会更早还是更晚摆脱个人主义、理想主义和唯灵论的困扰呢?我不知道。事实是我遇见了他,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
我很难确定那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遇到他不完全是个意外。由于决心要上大学,我已经给自己创造了最大的机会,来促成这样一场相遇:十五岁时,我就梦想自己的理想伴侣一定要是个知识分子,与我一样渴望了解世界。另外,自从进了索邦大学,我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留意在我的同学中找到那个我与之最契合的人。我的开朗待人为我赢得了很多友情,先是赫尔博,通过他我又认识了萨特。
不过,如果他早一年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如果我晚一年参加考试,我们会彼此错过吗?也不一定。赫尔博会为我们牵线搭桥。我们甚至常常设想,就算1929年没有相遇,我们相识也是迟早的事,因为我们后来都加入的年轻左翼教师联盟是个小圈子。我肯定会写作,与一些作家交往,会看到萨特的书,进而希望结识他。由于反纳粹知识分子团结一致,我的愿望在1943年到1945年之间肯定会实现。我们之间必定会建立某种联系,也许与现在不同,但必定非常密切。
如果说我们的相遇部分是出于偶然,后来把两人生命连在一起的那个契约则是我们主动选择的:这种选择不是简单的决定,而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我的选择首先体现在:我决定留在巴黎两年,先不去担任教职。我接受了萨特的朋友们,走进了他的世界,并非像某些人说的因为我是个女人,而是因为那是我向往已久的世界。他也接受了我的朋友圈子,与扎扎很合得来,但不久之后,我的旧友里就只剩下我妹妹、斯黛芬和费尔南德了。萨特的朋友比我多,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是出于情感,有些是由于观点一致。
我警觉地经营着我们的关系,避免让它褪色。我掂量着,我和他身上哪些东西可以接受,哪些应该杜绝,免得损害我们的关系。我本该同意让他去日本,虽然不情愿,也不至于感到绝望,两年之后我们肯定会像彼此承诺的那样重新在一起。那期间我做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去马赛,而不是跟他结婚。在其他所有问题上,我的决定都符合自己内心的愿望,除了这件事。我很不想离开萨特,然而考虑到未来,我选择了当时对我来说最难的那条路。那也是唯一一次我感到自己的决定使我避开了某种危险,给我的生活来了一记有益的当头棒喝。
如果我接受了,又会发生什么?这个假设毫无意义。我一向懂得尊重别人的选择,我知道萨特不想缔结婚姻,我不能一厢情愿。我曾经在一些小事上强迫过他(他也对我做过同样的事),但永远不能想象自己在重大问题上逼他就范。如果万一出于我想象不出来的原因我们不得不缔结婚姻,我知道我们也一定能想出办法,维护两人的自由。
关于美国
美国一旦觉得某个民族或人民运动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就要出手镇压。为了能让自己舒舒服服地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美国人让数百万人过着非人的生活。然而,荒谬之极而又令人气愤的是,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这掠夺来的数十亿美元并没有让美国人民过得好一些:大多数的美国人尤其是黑人生活贫困,有的甚至极度贫困。政府把巨额收益投入到了战争工业中,结果,美国在疯狂开发地球中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让自己具备毁灭地球的能力。
在美国国内,在我第一次赴美时就让我对黑人的状况感到愤怒,近几年越发令人发指,这导致非裔美国人之间的暴力事件增多,随之而来的是政府进一步的强压。黑豹党成员们纷纷被抓捕、收监、暗杀。警方似乎成功地瓦解、削弱了大批民间运动组织,其中包括推崇恐怖手段的白人革命组织气象人。然而,我与之交谈过的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政权已摇摇欲坠:国内暴力事件频发,失业严重,大批人口靠救济金生活,经济即将崩溃;在技术层面上也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崩溃是一定的,因为无法持续下去了。许多朋友这样说。这场崩溃会引发全球革命吗?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看到那一天,不过这种前景使我感到欣慰。
赫鲁晓夫的招待
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赫鲁晓夫的私人属地。那是一片很大的树林,种的是全苏联最美丽、最稀有的树。赫鲁晓夫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他穿着浅色西装、乌克兰式高领衬衫,带我们参观了他让人在海边修建的游泳池。泳池一望无际,四周围着玻璃墙,按下一个按钮,玻璃墙就会收起,他开心地重复展示了好几遍这个操作。
接着我们进了会议室,在一张张小桌子旁就座,赫鲁晓夫开始讲话,我们越听越吃惊。既然他邀请我们来做客,我们以为他会表现得热情亲切。完全不是。他把我们痛骂一通,仿佛我们都是资本主义的走狗。他讴歌了社会主义之美,声称对苏联出兵布达佩斯负责。完事之后,他挤出了几句客套话:再说了,你们也是反对战争的,我们还是能一起喝酒吃饭的。过后苏科夫私下里对他说:您讲得太棒了。赫鲁晓夫干巴巴地回答道:得让他们明白状况。
我们沿着海边一条开满鲜花的小径,走向他的住宅。泳衣为我们准备好了。维格莱利和苏科夫游了一会儿,其他人都在聊天。接着我们上了一栋漂亮的格鲁吉亚风格老房子的二楼,一顿丰盛的大餐等着我们。赫鲁晓夫脸色仍很阴沉,他大概还没消气。
关于马尔罗
莱利斯在《原纤维》结尾部分列举了他写作时始终努力遵循却不是总能做到的几个原则:不撒谎,不自夸,拒绝任何言过其实的说法,不出言轻率,不哗众取宠,不把文学当万金油,像一个懂得说话的人那样写作,以最大的严格和诚意对待文字。马尔罗的做法与这些训诫恰恰相反。今天,宣称兄弟亲善不是虚伪的粉饰,这是可耻的谎言,如果马尔罗还知道谎言和真相这两个词的含义。可他显然把二者混为一谈,词语对他来说只是些无意义的空话,可这不妨碍他使用它们表达思想。当他想出某个说法时,他自认为创造了一种思想。观察某个物件,然后老老实实说出他看到了什么,这对他来说过于简陋了:他不是去面对,而是逃避。这套把戏太显而易见了,很快就让人无法忍受,他永远得想到点其他的什么。他想得到什么呢?他从来不明说,其他东西又让他想到另外其他东西,对这东西他也没什么想法。这是一层层叠加的空洞:什么都没说明白,所有问题都不停地被回避了。在开罗时,他想到了墨西哥、危地马拉还有安提瓜;在安提瓜的时候他想到了美丽的巴洛克城市诺特。站在毛泽东面前他想到了托洛茨基、中国皇帝和军队将领们生锈的铁甲;看见长城他想到了弗泽莱;在德里他想到巴比伦花园、科尔特兹的士兵以及杭州的荷花;出席让穆兰葬礼后,他写道:我想起了米什莱写的雅尔纳克男爵与剑客拉夏特尼埃决斗的故事。类似的联想我还能继续列出满满几页纸来。
博朗告诫人们,不要手捧鲜花进入文学的花园。马尔罗却披挂着花环与花冠走了进去,还把他号称要表现的东西藏在华丽繁复的辞藻下面。写他与尼赫鲁和毛泽东的会面,他也没有向我们描述任何一个人物。我们都知道,这种官方的会谈,即便是精心安排,又能有什么价值。而且马尔罗还没有倾听的能力,他只会说。如果是提问,他那份固执会让对方不得不按照他既定的框架回答。结果我们根本听不到对方真实的声音,听到的全是马尔罗强加给他的腔调。马尔罗也无意向读者提供什么信息,只是想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让他们知道作者的知识多么渊博,见过多少世面,结识了多少名流。他夸张造作的风格只是为了掩盖内容的贫乏。在谈话时,这种把戏或许会给人留下卓越不凡的印象;但如果是阅读,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些眼花缭乱的套路实际有多空洞,它们掩盖的是些无聊的套话。在《反回忆录》里,马尔罗从头到尾炒冷饭,写的都是他已经写滥的主题,比如现实主义艺术,还有些右派的老调调:赞成剥削,把特权阶层的价值观和信念当作普遍的人类状况。用这种论调满怀激情地谈论法国,可从来不提法国人。
关于女权主义
女性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生物学上说的先天注定,没有一个美国女权主义者质疑这个观点。她们与我书中观点的分歧主要在实践层面:她们拒绝寄希望于未来,宁愿今天就把自己的命运抓在手里。而我的思想变化也在这点上:现在我认为她们是对的。
《第二性》或许对女权战士有用,但这并不是一本号召斗争的书。我本来认为,女性的地位会随着社会变革而变化。我在书里写道:总的来说,我们赢了一局。如今对我们来说,许多问题比那些只涉及我们的问题更为重要。在《事物的力量》中,谈及女性地位时,我写道:女性的地位取决于劳动在未来世界里的状况。只有生产发生重大的变化,女性地位才能真正改变。所以,我不愿把自己局限于女权运动的视角。之后不久,在一次接受让松的采访时,我说,要准确阐述我的思想,就要以最彻底的方式把它与女权主义联系起来。但这些观点当时仅限于理论:我坚决否认女人天性的存在。现在,我认为女权主义就是要为实现女性特有的诉求而斗争,这种斗争与阶级斗争并行,我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不,我们并没有赢得这一局:实际上,自1950年以来,我们一次也没有赢。仅靠社会革命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一半以上的人类:如今我认为这些是关键问题。我惊讶于人们竟如此轻易接受对女性的剥削。如果回顾深深根植于平等思想的旧式民主,我们很难意识到,奴隶总是以为自己理所当然是奴隶,因为我们以为奴隶能轻而易举地看到其中的矛盾。或许有一天,后世会同样惊愕,不理解资产阶级民主或人民民主制度,怎么会如此厚颜无耻地维持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尽管我清楚地看到背后的原因,也不免时常感到惊异。简言之,从前我以为阶级斗争优先于性别斗争,如今我认为这两项斗争应并行不悖。
女权主义者之间也有很多分歧。比如关于家庭的未来,她们意见不一。一部分人,包括舒拉米斯费尔斯通,认为家庭必须解体,否则女性、孩子和青少年就没有自由。虽然那些试图取代家长角色的机构都失败了,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那就像社会边缘的垃圾场,而整个社会都需要彻底重新构建。这种观点是对的,我觉得费尔斯通对家庭的批判也是对的。女性通过孩子以及在孩子身上滥施威权,被置于受奴役的境地,这使我哀叹。父母把孩子带入施虐受虐的游戏当中,把自己的意淫、执念和神经症投射在孩子身上,这种状况极其不健康。父母本应平衡分担父母的任务,尽可能避免把孩子一味地扔给家长,限制家长的权力,并严格监督家长行使权威。如果能做到这些,家庭是否还有用呢?在某些团体中,孩子由全体成人抚养,而且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但这样的事例太少了,不足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
对男性的仇恨使某些女性否认一切男性认同的价值观,反对所有她们称之为男性模式的东西。这我不赞同,因为我不认为这世上有什么品质、价值观或生活方式是纯属女性的:那等于承认女人是天性,而这是男人发明出来的说法,目的是让女性永远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女性追求的不是成为女人,而是成为完整的人。拒绝所谓的男性模式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文化、科学、艺术和技术都是由男人发明的,因为从前他们代表着一切。正如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方式继承过去的遗产,女性也要夺过男性锻造的工具,用它们争取自己的利益。确实,男性创造并发扬的文化反映出他们的大男子主义,他们使用的词语也透着同样的倾向。我们从他们手上得到财富的同时,要保持警惕,分辨哪些是普世适用的,哪些带着男性的偏见。黑白这种字眼我们同样可以接受,但男子气这个词则不行。我觉得女性可以放心地学习数学和化学,生物学就比较可疑,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对这些知识重新修订是必要的,但不能全盘否定。
关于衰老
另一个衰老的信号更加显而易见,也是我一直在抵抗的,那就是我与未来的关系。老年人接受采访的时候,即便表现出一定的乐观,也总会提到衰老的坏处。让我吃惊的是,他们从不谈未来的萎缩,莱利斯在《原纤维》中对此有精辟的表述。有些人确实感受不到这一点,我的女友奥尔迦就说过:我永远生活在当下,而当下即永恒。我从来不相信未来。所以无论是二十岁还是五十岁,对我来说几乎是一回事。还有一些人,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个重担,未来越短暂,生活就越轻松。我的情况则不同:我始终面向未来,兴高采烈地去迎接明天的我。我急切而贪婪,预感到自己每一次开疆拓土都会给将来留下永不磨灭的回忆。现在,我还有勇气制定一些短期计划旅行,阅读,会面但曾经推我前行的强大激情停止了。用夏多布里昂的话说,就是我的人生接近尾声了,我不能再用太大的步伐行动了。我如今把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挂在嘴上,再也不提三十年以后了。这短暂的未来已有定论。我感到自己人生的作品已到了完结篇,即便再多写上两三卷,也不会改变整体的样貌了。
然而时至今日,我的世界仍然在不停地扩大。在谈到战后经历时,我注意过这个现象,而今它愈加显著。外界事件对我个人生活的影响降低了,我的生活按既定轨道运行,偶然的成分几乎为零。新认识的人大多都是因为喜爱我的作品而给我写信:我与他们之间建立的关系,是由我的回应所产生的反作用力而产生的。随着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我的生活成了许多不同轨迹的交汇之处:这就是为什么一段时间以来,我生活中的巧合越来越多。J-B.彭塔利斯说过,小说的无聊之处在于,总是同一群人在故事里不停地相遇。此言甚是。我发现现实生活几乎也一样。我交好的一位四十岁的女子,嫁给了我从前在勒梅尔夫人那里认识的一位先生,当年他十六岁。薇奥莱塔勒杜克偶尔跟丽莎以前交往的两个男同性恋朋友之一约会。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以各种方式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也因为我所属的那个知识分子圈子很小。
我的生活日复一日循着同样的节奏,我做着同样性质的事情,与同样的人来往,然而我完全没有停滞的感觉,重复只是我生活的底色,新的内容层出不穷。我每天都在阅读,但读的书是新的;我每天都在写作,但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是无法预料的。我怀着迫切的心情关注着时事的发展,这些事从未重复,如今已成了我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变老的好处之一,是我可以完整地观察到一些人的人生轨迹,见证他们出人意料的发展道路。我怎么也想不到,花神咖啡馆那个勾魂的姑娘,美丽而又一脸迷茫,时间会把她变成一个出色的女企业家;还有另一个姑娘,懒散而又有点野性,日后居然会成为法国最好的卡夫卡专家;还有英俊的尼克,长大后会拍出那么美的电影。我想象不出,那么不拘一格,看上去又对荣誉满不在乎的波朗,日后会披上法兰西学术院院士的礼服。我也万万想不到,写出《希望》的人愿意在技术官僚统治并与弗朗哥交好的法国政府里当个部长。这些人的人生轨迹让我吃惊,显然是因为我只看到了他们的外表,而不了解他们人生的底色。我对他们的童年一无所知,而童年是了解一切的钥匙。
关于自我认知
事实上,虽然嘴上不承认,其实任何人都不愿变成自己之外的样子。毕竟对所有生命来说,生存就意味着让自己存在。人有时会批评自己的行为,但不见得就会改弦更张。阿米艾尔在《他的日记》中不停地感叹自己懒惰,宣称自己要克服懒惰,然而行为却一如既往。其实他是选择了要做一个躺在自己的懒惰上呻吟的懒汉。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爱自己。我说过,一个人在童年时没有得到应有的爱,学会用父母的眼光看待自己,那么他会在内心整合出一个令人厌恶的自我形象,终生无法摆脱。但这种自我厌恶来自他的主体,于是他一边痛苦,一边认同。在这种本体认同下,某些人骄傲地承认自己有一些在我看来难以承认的性格缺点:我看重钱,我不会浪费它看到认识的人有烦心事我感到好玩我可不像那些歇斯底里的人一样,非得要知道真相。我立即会认为:这是个吝啬鬼;这人真坏;这女人自欺欺人。但他们会否认这些定义。几乎不可能说服别人承认那些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缺点,如果他们认为那不是缺点,那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与我们不同,所以把我们的批评只当耳旁风。费尔南德毕加索说:如果街上的人不冲我起哄,我就会觉得自己的帽子不够帅。别人以为冲他起哄是侮辱他,他只觉得那是在夸他优雅。
我也有这种对自己的认可。有个精通笔迹学的朋友在研究了我的字后,给我描述的人格肖像相当让我自鸣得意。她说:您觉得满意,是因为您自己选择了成为现在的您。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负面理解。确实,我专注工作、善始善终的特点可以被描述为自觉、有毅力或坚韧不拔,但其中也有一意孤行、固执己见的成分。我的求知欲来自开放的心态还是肤浅的好奇心?至于我,我是毫不犹豫地接受自己的。如果我觉得别人评论说的像我,我只觉得有趣。我一度用研究普罗旺斯风景一样的方法研究音乐,我自己心里意识到了这一点,可这并不妨碍我的狂热。我对别人的评价也适用于我自己:我是很难被伤害的。假如别人的批评和指责说得不对,我会置若罔闻;假如说得对,我甘之如饴。随便他们把我当成女知识分子或女权主义者,我都不在乎:我就是我,我对自己负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