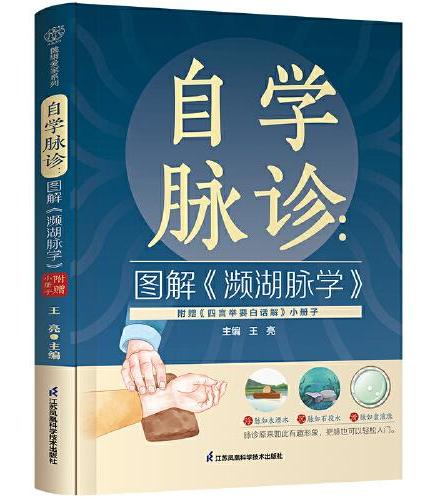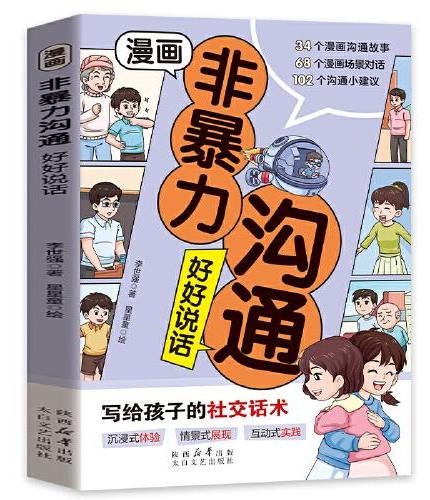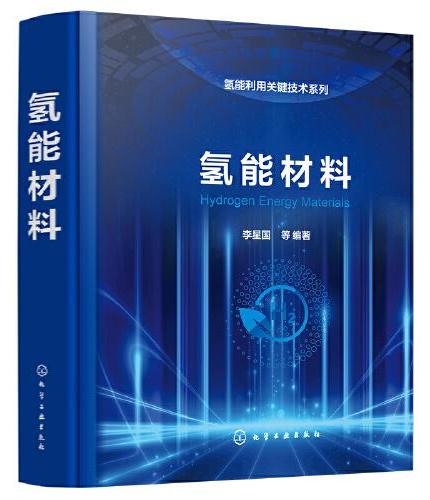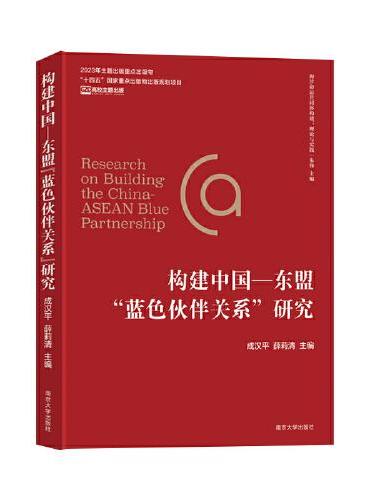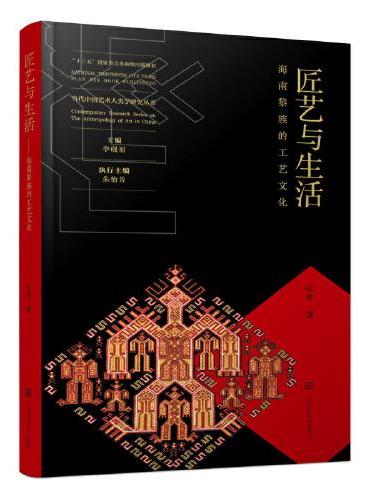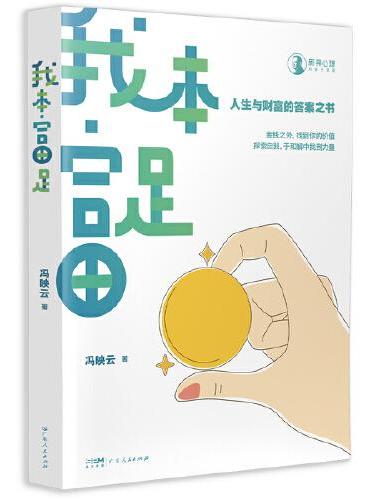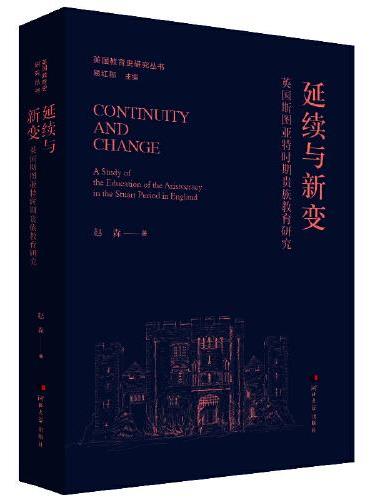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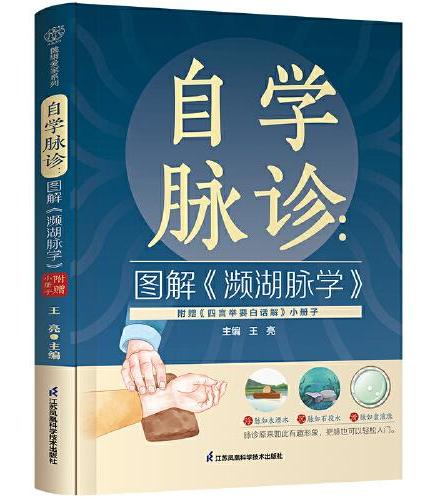
《
自学脉诊:图解《濒湖脉学》
》
售價:HK$
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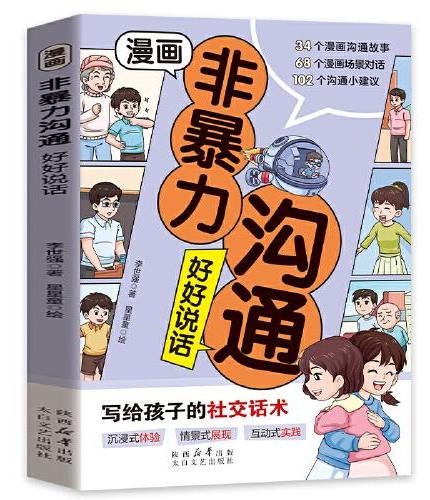
《
漫画非暴力沟通 好好说话写给孩子的社交话术让你的学习和生活会更加快乐正面管教的方式方法 教会父母如何正确教育叛逆期孩子 用引导性语言教育青少年男孩女孩 帮助孩子拥有健康心理的沟通方法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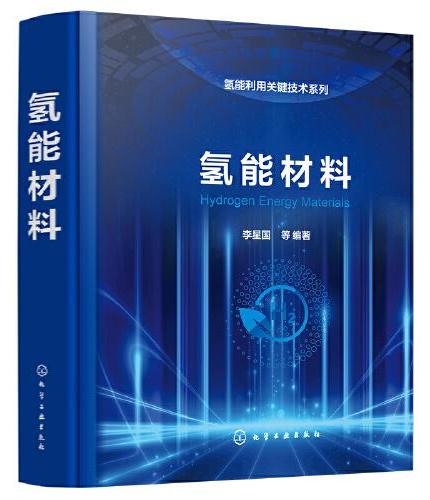
《
氢能利用关键技术系列--氢能材料
》
售價:HK$
39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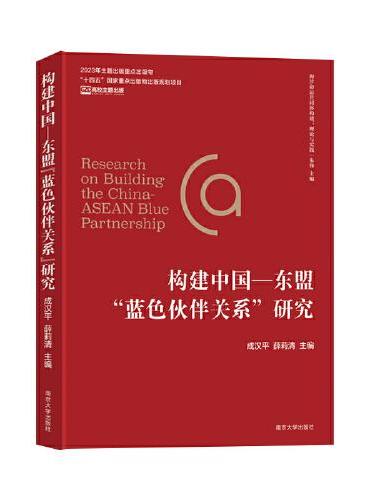
《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 理论与实践)构建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研究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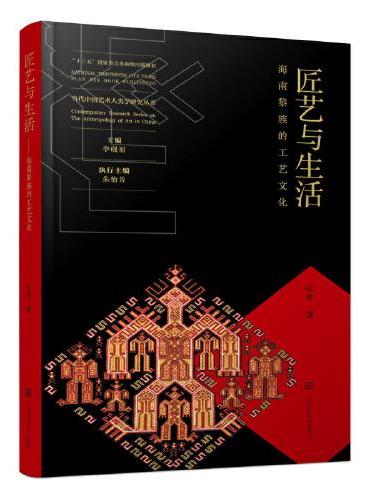
《
匠艺与生活:海南黎族的工艺文化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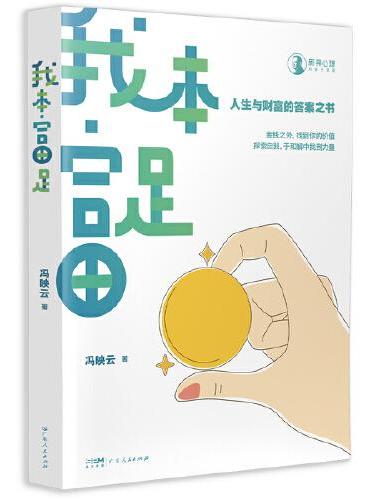
《
我本富足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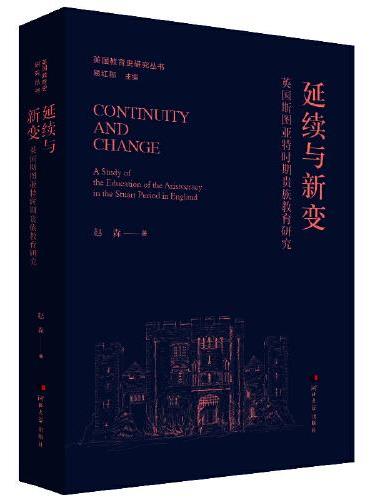
《
英国教育史研究丛书——延续与新变:英国斯图亚特时期贵族教育研究
》
售價:HK$
108.9

《
更易上手!钢琴弹唱经典老歌(五线谱版)
》
售價:HK$
54.8
|
| 編輯推薦: |
茅盾文学奖得主金宇澄继《繁花》之后的又一力作,一纸家族回忆录,以数万言父母笔记、数百幅老照片及历史档案,回望上个世纪父母亲在那不平凡的年代里,各自的人生际遇。金宇澄的文字一贯冷静克制,于浮华散尽处,透出一股不凡的厚重。《回望》舍弃心理层面的幽冥,直展当时的书札原件,一切拨云见日,去除建构,悉数交予读者去感受。
从苏州吴江走出来的父亲,带着激情与豪迈,投身到血与革命中;身为老上海银楼富家小姐的母亲,复旦大学毕业,勇敢大方,目光坚定。在豪情退却后的老迈岁月,众多无言的沉默时刻,子对父的理解与了悟,成为回望之中温暖的、永恒的印象。
|
| 內容簡介: |
他,家道中落的江南子弟,地下情报工作者,蹲过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监狱;
她,老上海银楼的千金小姐,复旦大学毕业,进步青年;
我的父亲母亲,相逢在那个热血澎湃的峥嵘岁月
后来,就有了《繁花》中阿宝爸爸阿宝娘
《回望》是著名作家金宇澄的传记文学作品,采用三种不同的叙事角度,讲述了作者父母辈的故事,成为金宇澄继《繁花》之后的第二部重要作品。这正是金宇澄父母的故事,也是他们那个时代人们的故事。
本次修订版采用法式软精装,封面大红麻织纸手感上品,内文书信草絮纸,年代感扑面而来,更有新增数万字父亲笔记 、折页大事年表,并附录长篇对话集透析金宇澄的写作观。
|
| 關於作者: |
|
金宇澄,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黎里,《上海文学》执行主编。中国好书鲁迅文化奖施耐庵文学奖华语文学小说家奖茅盾文学奖得主。
|
| 目錄:
|
一 我父母
二一 黎里维德黎里
一七七 上海云上海
三五九 我们回望
三六九 附录对话
媒体评论风云儿女的前世与今生;千万人家的欢乐与哀愁。金宇澄《回望》,看见半世纪上海市民生活惊心动魄的底色。盛世还是乱世,天长地久还是云淡风轻,蓦然回首,谁不说此身虽在堪惊!──王德威(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
《回望》在某种意义上可看成《繁花》的前传,从大体的时间线来看,《繁花》开始的部分是《回望》即将结束的地方,两本书合起来几乎跨越了整个二十世纪。一些被历史长河所裹挟的细节,如涓涓细流般重新被找了回来,站在河岸的人,无法忽略水面闪烁的岁月光影。──毛尖(作家)
《回望》(和《繁花》一样)也有一个上海地图。假如金宇澄继续这样写下去,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完整密集的上海地图,每一个点都有自己精彩的、能够被读者记住的故事。自然主义的描写对我们来说,是*本性的,你敢直视的。因为看一个作品的时候,你敢直视它,实际上就是敢直视自己。阿城
《回望》呈现了历史事件中的另外一面,常被人忽略的、隐秘的、因而读来会让人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的一面。小白。
在线试读一切已归于平静
母亲说,我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和四脚透雕梅花的旧圆桌、一个旧柚木小圆台,请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纹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圆台一直在家,现放着我的笔记本电脑。
一九九〇年,父亲在卢湾区一旧家具店橱窗里看到有三张日式矮桌,样式相同,三张叠在一起。他走进店堂,穿过旧家具的夹弄,看这三张暗褐色的桌子。店老板一般很识相,注重来客年龄、打扮、神色,不讲话。父亲想打听什么,但是没作声,最后怏怏出来,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东西。他对母亲说。
他的两颊早有了老年斑,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锐谈锋,即使面对他熟悉的地下党电视剧,也一般在沙发里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记得有一次,他转过脸对我母亲说: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白皮鞋?
母亲耳聋,不习惯助听器,膝上堆着报纸和一本《中国老年》杂志,看一眼屏幕,没明白他的疑问。这是我听到父亲唯一的不满,他的话越来越少了。他曾是上海沦陷期的中共情报人员,常年西装革履,也经常身无分文,为失业苦恼。
穿不起西装,总要有七八套不过时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过去就叫洋装瘪三。
他不许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恶痛绝,日本饭是最坏的东西。或许,那是我母亲讲的,五十年前,他误将盘子里的生猪血当作番茄酱的原因。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近北四川路桥堍,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
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 位于大桥公寓, 据说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关押于此),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近况,本埠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翌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质,堂兄已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
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一切已归于平静
母亲说,我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和四脚透雕梅花的旧圆桌、一个旧柚木小圆台,请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纹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圆台一直在家,现放着我的笔记本电脑。
一九九〇年,父亲在卢湾区一旧家具店橱窗里看到有三张日式矮桌,样式相同,三张叠在一起。他走进店堂,穿过旧家具的夹弄,看这三张暗褐色的桌子。店老板一般很识相,注重来客年龄、打扮、神色,不讲话。父亲想打听什么,但是没作声,最后怏怏出来,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东西。他对母亲说。
他的两颊早有了老年斑,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锐谈锋,即使面对他熟悉的地下党电视剧,也一般在沙发里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记得有一次,他转过脸对我母亲说: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白皮鞋?
母亲耳聋,不习惯助听器,膝上堆着报纸和一本《中国老年》杂志,看一眼屏幕,没明白他的疑问。这是我听到父亲唯一的不满,他的话越来越少了。他曾是上海沦陷期的中共情报人员,常年西装革履,也经常身无分文,为失业苦恼。
穿不起西装,总要有七八套不过时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过去就叫洋装瘪三。
他不许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恶痛绝,日本饭是最坏的东西。或许,那是我母亲讲的,五十年前,他误将盘子里的生猪血当作番茄酱的原因。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近北四川路桥堍,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
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 位于大桥公寓, 据说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关押于此),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近况,本埠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翌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质,堂兄已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
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日占时期,这座远东第一大狱仍以设计精良著称,整幢建筑通风通声,稍有异常响动,几层楼都听得清。新犯进门循照英制,三九寒天一样脱尽衣服,兜头一桶臭药水消毒。糙米饭改成日式分量,每餐一小碗。囚徒必做一种日式体操,平时在监室里跏趺一样静坐,不可活动。四周极为静寂,只有狱警在走廊里反复来回的脚步声,钟摆一样的规则。
有天傍晚,听到一日本看守低声哼唱,踱步经过他面前铁栅,歌词为俄文:
Эй Ухнем! Эй ухнем! Ещё разик ещё раз!
(哎哟嗬!哎哟嗬!齐心合力把纤拉!)
Разовьём мы берёзу, Разовьём мы кудряву!
(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
Эx ты, волга мать-река,Широка и глубока
(伏尔加,可爱的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
静坐狱中,歌声出自一敌方士兵之口,联想到词句的全部含义,他深感惊异。断断续续的《伏尔加船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苏敏感时期,这位年轻日本兵,战前是干什么的?是学生?现实的隔阂,在熟知的歌声中搅动,产生难言的感受。
次年,他被解至上海南市监狱(即南车站路看守所)。一年后,解至杭州监狱。
两地都属汪伪管辖,等于嘈杂的菜市场,杭州监狱更甚,克扣口粮,犯人已到食不果腹的境地,必须依靠亲友接济度日。监室走廊里,每天摆有外来的馄饨担,也卖小笼、春卷、蛋炒饭、大肉面以及包饭作摊档,收受各类钞票或细软,付了账,或一个银假牙,小贩递进铁窗一碗三鲜面、片儿川或几个菜肉包,狱卒听之任之。一人在牢里吃,四面是饥肠辘辘的饿眼,几乎每天都有饿尸被附近的庙祝抬出去。
记得一个身披獭皮大衣的北方人,趾高气扬进监,出手阔绰,常常拿出钞票和首饰,从外面大馆子里叫菜,叫热毛巾揩面,终因缺少社会资助,懂得讨价还价,然后锱铢必较,数零钱吃馄饨面,吃廉价盖浇饭,最后无钱可拿,一件一件剥下衣衫以得充饥,没有接济,坐吃山空,最终饥寒而亡,死时蓬头垢面,仅穿了一套底衫裤,如缩毙街头的乞丐。
附近监室,囚禁不少身份复杂的英、美籍男女,基本失去西人风度,洋装和绒线衣每个缝隙里,蠕动着密密麻麻的虱子,除了被押走几个之外,不久都饿死了,没人管。
这期间,他得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
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 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 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 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地地斯咖啡馆(DDS),以及三官堂桥的棚户里等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