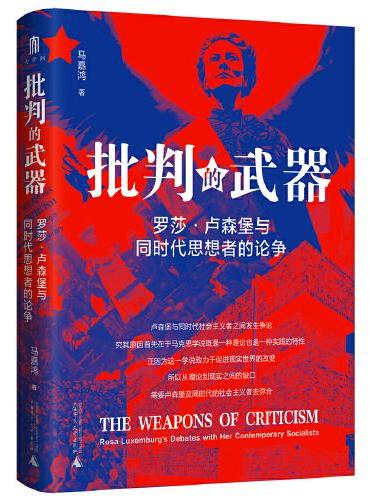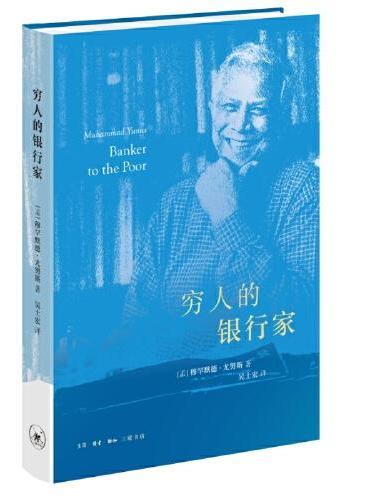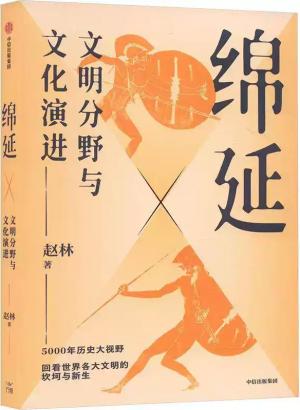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迟缓的巨人:“大而不能倒”的反思与人性化转向
》
售價:HK$
77.3

《
我们去往何方:身体、身份和个人价值
》
售價:HK$
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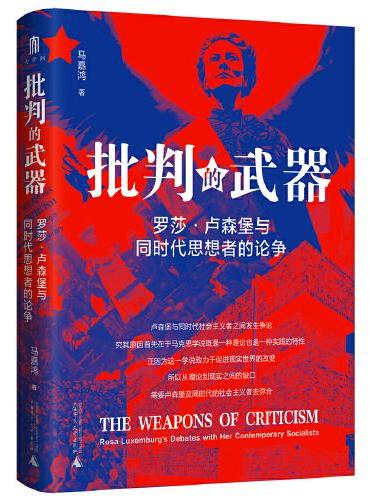
《
大学问·批判的武器:罗莎·卢森堡与同时代思想者的论争
》
售價:HK$
98.6

《
低薪困境:剖析日本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
》
售價:HK$
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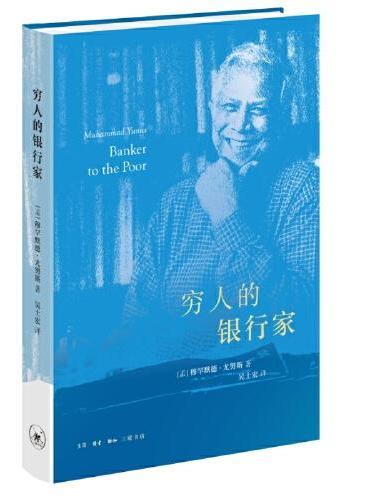
《
穷人的银行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自传)
》
售價:HK$
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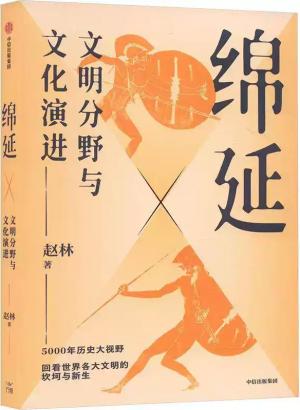
《
绵延:文明分野与文化演进
》
售價:HK$
66.1

《
三神之战:罗马,波斯与阿拉伯帝国的崛起
》
售價:HK$
80.6

《
法国通史(全六卷)
》
售價:HK$
985.6
|
| 編輯推薦: |
★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俄罗斯的萨福阿赫玛托娃诗歌代表作
★ 收入译者俄罗斯-新世纪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中文翻译奖获奖作品《安魂曲》。
★ 她表达的内容自始至终明晰易懂。她是她那一代作家中的简奥斯汀。她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纽带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
★ 阿赫玛托娃为俄罗斯的抒情诗带来俄国19世纪长篇小说所有的错综复杂性和丰富的心理描写。她参照心理小说,发展了自己诗歌的形式,尖锐而独特的形式。诗人曼杰施塔姆
★ 我的脚步仍然轻盈可心儿在绝望中变得冰凉我竟把左手的手套戴在右手上。一本描写女人心灵之书!
|
| 內容簡介: |
|
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中以爱情诗的成就*,她善于描写受挫的爱情爱情带给女性的孤独与忧伤、委屈与折磨、反叛与徘徊,甚至激愤与复仇,还有爱情不可思议的魔力。有别于普希金明朗的忧郁,她用新颖清丽的语句道出心底的深蕴。描绘孤独的生活和抒发相思之情时,表达了对情人的依恋。字句不多,但宛转曲折,清俊疏朗。
|
| 關於作者: |
作者:
阿赫玛托娃18891966
20世纪俄罗斯著名女诗人,阿克梅派的主要代表。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又享有俄罗斯的萨福之称。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译者:
高莽(19262017),笔名乌兰汗,生于哈尔滨,长期在各级中苏友好协会及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从事翻译、编辑、俄苏文学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与对外友好活动;同时从事文学与美术创作。2013年11月,高莽凭借译作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安魂曲》,获得了俄罗斯-新世纪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最佳中文翻译奖。
|
| 目錄:
|
目次
简略的自述
我会爱
《黄昏集》选译
爱
在皇村
一林荫路上牵走了一匹匹马驹
二那儿是我的大理石替身
三黝黑的少年在林荫路上徘徊
无论是那个吹风笛的男孩
深色披肩下紧抱着双臂
门扉儿半开
你可想知道全部过程
吟唱最后一次会晤
心儿没有锁在心上
白夜里
风儿,你,你来把我埋葬
灰色眼睛的国王
他爱过
我的生活恰似挂钟里的布谷
葬
诗两首
一枕头上下都已
二还是那个声音,还是那道视线
我对着窗前的光亮祈祷
《念珠集》选译
心慌意乱
我们在这儿是些游手好闲之辈
眼睛不由自主地乞求宽饶
真正的体贴不声不响
我有一个浅笑
你好!你可曾听见
记忆的呼声
你知道,我正为不自由所苦
1913年11月8日
别把我的信,亲爱的,揉搓
我来到诗人家里做客
我送友人到门口
这十一月的日子,可会把我原谅
我不乞求你的爱
《群飞的白鸟》选译
你好重呀,爱情的记忆
用经验代替智慧,如同
缪斯走了,踏着
别离
滨海公园里小路黑黝黝
万物都让我想起他
总会有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吧
她来了。我没有流露心中的不安
皇村雕像
微睡又把我带进了
你为什么要佯装成
我们俩不会道别
祷告
狂妄使你的灵魂蒙上阴影
记1914年7月19日
梦
傍晚的天色茫茫昏黄
我不知道你活着,还是已经死去
我的影子留在那里了
我觉得这儿永远
《车前草》选译
家中立刻静了下来,最后一朵
你背信弃义:为了绿色的岛屿
天一亮我就醒来
我和一个高个人私交
你当时看了一眼我的脸
我问过布谷鸟
尘世的荣誉如过眼烟云
这件事很简单,很清楚
身躯变得何等可怕
我没有遮掩小窗
如今再没有人听唱歌曲
颈上挂着几串小念珠
短歌
我听到一个声音。他宽慰地把我召唤
《ANNO DOMINI》选译
抛弃国土,任敌人蹂躏
他悄悄地说:我甚至不惜
这儿真好:簌簌,飒飒
黑戒指的故事
铁铸的栏杆
你不可能活下来
站在天堂的白色门口
我的话咒得情人们死去
写给很多人
《芦苇集》选译
缪斯
二行诗
但丁
柳树
活人一旦死去
离异
一我们经常分离不是几周
二正像平素分离时一样
三最后一杯酒
安魂曲
代序
献词
前奏
一拂晓时他们把你带走
二静静的顿河静静地流
三不,这不是我
四爱嘲笑人的女人
五我呼喊了十七个月
六淡淡的日子,一周又一周飞逝
七判决
八致死神
九疯狂张开了翅膀
十钉死在十字架上
尾声
马雅可夫斯基在1913年
《第七本诗集》选译
我们的神圣行业
宣誓
英雄气概
胜利
一炮声轰鸣,大雪漫天
二防波堤上第一座灯塔亮了
三胜利站在我们的门外
四1944年1月27日
五解放了的土地
悼念友人
从飞机上外望
一几百俄里,几百英里
二我要竖起一块雪白的石头
三春天的机场上,青草
三个秋天
亲人的心儿都高悬在星际
在少先队夏令营
CINQUE
一我仿佛俯在天边的云端
二声音在太空中消逝
三很久以来我就不喜欢
四你自己何尝不知道,我不会
五我们不像沉睡的罂粟花那样呼吸
那颗心再也不会回答我的呼唤
这就是它,果实累累的秋季
长诗未投寄时有感
莫斯科的红三叶
一近似题词
二无题
三再敬一杯
代献词
十三行
召唤
夜访
音乐
片断
夏花园
我仿佛听见了远方的呼唤
不必用严酷的命运恐吓我
献给普希金城
一啊,我心疼呀!他们曾把你烧掉
二这棵柳树的绿叶早在十九世纪已经
枯萎
短歌四首
一旅人的歌,或从黑暗中传来的声音
二多余的歌
三告别的歌
四最后的一支歌
诗集上的画像
回声
诗三首
一是时候了,应该把骆驼的嘶鸣遗忘
二翻一翻黑色的记忆
三他说得对又是街灯,药房
永志不忘的日子又临头
如果天下所有向我乞求过
悼念诗人
一人间的绝唱昨天哑然
二缪斯像盲人俄狄浦斯的女儿
皇村礼赞
故乡的土
科马罗沃村速写
最后一朵玫瑰
什么诺言都不顾了
虽然不是我的故土
《集外篇》
那轮狡猾的明月
我用昂贵的、意外的代价
会被人忘记?这可真让我惊奇
就在今天给我挂个电话吧
书上题词
一年四季
我早已不相信电话了
严酷的时代改变了我
回忆有三个时代
一九一三年的彼得堡
两人的目光就这么下望
阿赫玛托娃乌兰汗
|
| 內容試閱:
|
简略的自述
1889年6月11日(公历23日),我在敖德萨近郊(大喷泉)出世。那时家父是退伍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当我还是个周岁的婴儿时,被带往北方的皇村皇村原为俄国历代沙皇的行宫,位于彼得堡市以南35公里处。19世纪时,沙皇政府在该处设立了贵族子弟学校。普希金是该校第一期学生。十月革命后,皇村更名为普希金城。。我在皇村住到十六岁。
我早年的回忆都与皇村有关:苍翠碧绿而又未经人工布置的花园,保姆携我玩耍的牧场,毛色斑驳的小马跑来跑去的跑马场,旧的火车站以及其他,这一切后来都写入《皇村礼赞》中。
我每年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箭湾之滨度夏,在那儿我与大海结缘。那几年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古城赫尔松涅斯建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城,15世纪被毁。19世纪开始对它进行挖掘,发现城墙、城门、塔楼等遗迹。,我家就住在它附近。我按列夫托尔斯泰编的识字课本学会识字。五岁时,听女教师给年长的孩子们上课,我也学会用法语讲话。
我十一岁写成第一首诗。我不是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那里开始接触诗,而是从杰尔查文(《贺皇族少年生日诗》)和涅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这些诗,我母亲都能背诵。
我在皇村女子学校上学,最初学习成绩甚劣,后来大有改进,但始终不太愿意学习。
1905年,我的双亲分居,妈妈携儿带女迁往南方。我们在叶夫帕托里亚住了一年整,我在家中自修学校倒数第二年级课程。我怀念皇村,写了不计其数不成样子的诗。1905年革命的余音隐隐约约传到与世隔绝的叶夫帕托里亚。最后的一个学年是在基辅市丰杜克列耶夫学校读完的,1907年于该校毕业。
我在基辅进了女子高等学校法律系。最初学习法律史,尤其是学习拉丁文时,我尚觉满意,但一开始教授纯法律科目时,我便对课程失掉了兴趣。
1910年(俄历4月25日)我与尼斯古米廖夫尼斯古米廖夫(18861921),俄罗斯诗人,阿克梅派代表人物之一。十月革命后因所谓参加反革命阴谋组织被处死,1986年平反。结婚,我们去巴黎度蜜月。
那时,巴黎市区铺设新的拉斯帕伊林荫大道的工程尚未最后竣工(左拉对此有所描述)。爱迪生的朋友韦尔纳在伟人祠餐厅指给我两张桌子,说:这就是你们的社会民主党,这张是布尔什维克,那张是孟什维克。妇女们的衣着兴趣经常变换,忽而穿裙裤,忽而又几乎都穿包住大腿的窄裙。诗无人问津,诗集只因印有大小不等的美术名家们的装饰画,才有人购买。我那时已明白:巴黎的美术把法国的诗歌给吞掉了。
迁居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等文史讲习所学习。当时我写的诗后来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别人给我看英诺肯季安年斯基英诺肯季安年斯基(18561909),俄国诗人兼评论家。的《柏木匣》的校样,我为之惊叹不已。阅读时,忘掉世上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明显陷入窘境,新起诗人不再追随这一流派。有人走向未来派,有人走向阿克梅派。我和一号诗人会当时诗人的一个派别。的友人曼德尔施塔姆奥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诗人。他死后,阿赫玛托娃为他写过悼念诗。、金凯维奇米金凯维奇(18911973),俄罗斯诗人,文学翻译家。及纳尔布特弗纳尔布特(18881944),俄罗斯诗人。一起,成为阿克梅主义者。
1911年春我在巴黎亲眼看到俄罗斯芭蕾舞获得的最早的辉煌胜利。1912年我遍游意大利北部(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波伦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美术与建筑给我的印象极深,它像那终生难忘的梦。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集》出版。只印三百册。批评界对它的评价尚好。
1912年10月1日我的独生子列夫出生。
1914年3月第二本书《念珠集》问世。它的生存时间只有六周左右。彼得堡从5月初开始转入消沉。人们分批疏散。这次与彼得堡的告别成为永久的告别。我们回来时它已不叫彼得堡,而叫彼得格勒了,从十九世纪一下就跨入二十世纪。从城市面貌开始,一切都变了样。看来,初学写作者的一本小小的爱情抒情诗集应当淹没于世界性的大事之中。时间却做出另外的安排。
我年年在特维尔省距离别热茨克十五俄里的地方消夏。那儿并非风景优美之地:丘陵地带上耕耘的是四四方方的田地,零落的磨坊、泥塘,排干的沼泽、辘轳,除了庄稼还是庄稼《念珠集》和《群飞的白鸟》诗集中的许多诗都是在那儿写的。
《群飞的白鸟》于1917年9月出版。读者与批评界对此书不公正。不知何故这本诗集被认为不如《念珠集》成功。这本诗集是在更为严峻的形势下出版的。交通运输奄奄一息书甚至不能寄往莫斯科,全部在彼得格勒售掉了。杂志一种接着一种停刊,报纸也是如此。因此,与《念珠集》不同之处在于《群飞的白鸟》不可能在报刊上得到热烈讨论。饥荒与经济崩溃日甚一日,奇怪的是,所有这些情况都不在考虑之内了。
十月革命后,我在农业学院图书馆工作。1921年我的诗集《车前草》问世,1922年出版了诗集《ANNODOMINI》拉丁文,意为《耶稣纪元》。。
大约于二十年代中期,我兴致勃勃地着手钻研古老的彼得堡建筑和普希金的生平与创作。研究普希金,其成果是关于《金鸡》、关于贡斯当德堤雷贝克的《阿道尔夫》和关于《石客》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当时都发表了。
近二十年来我写的《亚历山德林娜普希金的妻妹。》《普希金与涅瓦海滩》《普希金在1828年》可能收入《普希金之死》一书中。
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我的新诗几乎不再发表,而旧作不予再版。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时我正在列宁格勒。9月底,已是围困时期,我搭飞机去了莫斯科。
我在塔什干住到1944年5月,贪婪地打听有关列宁格勒和前线的消息。和其他诗人一样,我经常到军医院去为伤病员们朗诵诗作。我在塔什干初次理解什么是炎热中的树荫凉和流水声。我还理解了什么是人的善良:我在塔什干经常患病,而且病势很重。
1944年5月我飞到满城春色的莫斯科,那时莫斯科洋溢着欢乐的希望,并正在等待着即将来临的胜利。6月我重返列宁格勒。
我的城市仿佛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幻影,它使我如此震惊,以至于我把这次与它的相会写成散文。与此同时,写成了两篇特写《三株丁香树》和《走访死神》,后一篇记述我在铁里欧吉前线朗诵诗一事。我一向觉得散文既神秘莫测又诱人试探。我从小熟悉的全部是诗,而对散文从来是一无所知。我这次试笔得到众人的大力赞扬,我当然并不信以为真。我把左琴科请来,他让我删掉几处,并说,其他部分他认为可以。我很高兴。后来,我的儿子被捕,我把他的存稿和我的一起全部付之一炬。
我早就对文学翻译问题感兴趣。战后时期我译的作品很多。现在仍然从事翻译工作。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英雄人物的事诗》。为写作这部作品我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
去年冬天,但丁纪念年1965年为但丁诞辰七百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这一年为但丁纪念年。的前夕,我重又听见了意大利语言的声音我访问了罗马和西西里岛。1965年春,我前往莎士比亚的故乡,望见了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故友重逢,结识新朋,并再次访问巴黎。
我从未停止写诗。诗中有我与时代的联系,与我国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我写诗时,是以我国英雄的历史中的旋律为节奏的。我能生活在这些岁月中,并阅历了这些年代无与伦比的事件,我感到幸福。
阿赫玛托娃(18891966)乌兰汗
安娜阿赫玛托娃是二十世纪初俄国诗坛一颗璀璨的明星。家庭环境和生活地点对她的成长都有过重大影响。她是虔诚的教徒,接受了人生在世即受苦受难的宗教思想,又长期生活在诗意浓浓的皇村。
阿赫玛托娃的第一首诗发表于1907年,当时她只有十八岁。第一本诗集《黄昏集》出版于1912年,立刻引起文艺界的重视与争论。这本诗集抒发的是爱情,从自我表现出发,倾诉少女爱情的不幸。这个主题在她以后的几本诗集中仍然占主要地位。诗中还常常涉及对死亡的联想。这与她家庭的悲剧以及疾病缠身不无关系。1905年,她父母离异,从而使她失掉了父母共同的爱,饱尝了家庭拆散后的辛酸。她兄弟姐妹六人,阿赫玛托娃排行第四。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一妹一弟。他们几乎都染有肺结核病。大姐伊琳娜在阿赫玛托娃未出世前就夭折,二姐伊娜死于二十二岁妙龄。大哥和小妹也都在二十年代初相继去世。阿赫玛托娃本人也患肺结核,所以常常感到死的威胁。她早年诗中的悲凉感,正说明她囿于自我的小圈子里,没有看到整个大社会的残酷现实。她个人家庭生活也很悲惨,第一个丈夫古米廖夫被处决以后,几次再婚都不美满,增加了她诗歌中的哀怨调子。
阿赫玛托娃在白银时代的创作,以对爱情的渴求、恋爱中的陶醉、失恋的迷惘为主调。她用新颖清丽的语句道出了心底的深蕴。描绘孤独的生活和抒发相思之情时,表达了对情人的依恋,字句不多,但婉转曲折,清俊疏朗,特别是诗的结尾,常常出现意想不到的转化。她的很多诗句已经成了俄罗斯诗中的经典,如:我竟把左手的手套
戴在右手上去。又如:世界上不流泪的人中间
没人比我们更高傲、更纯粹。当时,俄国象征派诗歌从高峰转向下坡,新崛起的一代人自命不凡,成立了各种文艺团体。阿赫玛托娃和尼古米廖夫、米库兹明、谢戈罗杰茨基、奥曼德尔施塔姆、弗纳尔布特、米金凯维奇等人便在艺术至上的阿克梅派的旗帜下登上文坛。
在风雷激荡的十月革命时,阿赫玛托娃不是革命的喉咙,也没有企图把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古典作家推下时代的轮船。她我行我素,仍然表现自己内心的感受。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半叶,苏联文艺界对阿赫玛托娃的创作有两种截然相悖的看法。一种是以岗位派文艺评论家列列维奇(19011945)为代表。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批评家一口咬定阿赫玛托娃是反对新生活的敌人,说培养出阿赫玛托娃创作的社会环境是地主之家,是老爷的公馆,说她的作品是地主庄园种植的暖房花草,说她的天地极其狭小,说她的诗歌不外是贵放文化的一块小小美丽残片,说她诗歌中对于社会过程只有极其微弱的反响,而且还是敌意的(见《在岗位上》一书,1924年)。列列维奇的观点在当时占据上风,奠定了对阿赫玛托娃反复批判的理论基础。但,同一时期,或更早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瓦奥辛斯基(18871938)却对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持另一种看法。1922年7月4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阿赫玛托娃是一流的抒情诗人,他写道:每一位杰出的诗人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他善于为同时代的某一群体的心灵活动提出浓缩的、突出的、响亮的表达方式,以它来概括重大的或有特色的事件。另一位女革命家亚柯伦泰(18721952)于1923年第2期《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发表《写给劳动青年的一封信》,认为阿赫玛托娃的诗集是描写妇女心灵的书,是用诗表现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奴役的妇女为争取自身人格而进行的斗争。她认为阿赫玛托娃完全不像我们冷眼初看时所感觉的那么陌生,在她的诗中有过渡时代我们所熟悉的、活生生的、亲近的妇女的心,它在颤抖,它在搏斗。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的心理在分化,在这个时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安娜阿赫玛托娃正是站在欣欣向荣的,而不是奄奄一息的意识形态的一方。
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沉淀,证明这些老革命家看得远,他们透过诗人个人感情的表层发现了丰富的心灵矿藏,他们对阿赫玛托娃以后的发展寄予希望,对她的诗艺技巧表示赞许。而列列维奇的革命大批判,只不过是庸俗社会学的一种表现,可是这种大批判却长时间对阿赫玛托娃起着扼杀的作用。
从二十年代中期起。大约有十个年头,阿赫玛托娃没有发表作品。她在认识新的社会、新的现实,同时也在勇敢地承受自己多灾多难的命运的考验。
从三十年代后期起,她完成了许多新的抒情诗,爱情的主题退让到社会问题和民众命运问题之后,《安魂曲》(19351940)、《列宁格勒诗抄》(19411944)以及诗剧《没有英雄人物的事诗》(19401962)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她本人也承认:我的文风变了,声音也变了,再不可能退回到最初的写法上去。是好,是坏,不能由我来判断。1940年达到了极点。诗作喷涌而出,源源不断,它们来得急,使我喘不过气:什么样的诗都有,大概也有坏的作品。转引自弗日尔蒙斯基著《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创作》一书。
苏联人民进行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时,阿赫玛托娃已年过半百。宣战当天,她即写成一首短诗,说明她的决心:要活,就活得自由,要死,就死在家园作为列宁格勒市的一个居民,她和所有没有上前线的人一样,积极参加保卫战的斗争。她缝沙袋、建路障、在楼前值班防空、挖坑掩埋城市的有历史价值的雕像纪念碑。女诗人奥别尔戈利茨(19101975)为老诗人的行动所感动,曾写下一组诗献给她:在喷泉街旁边,在喷泉街旁边,
在紧紧掩闭着的入口处前面,
在雕花的大铁门旁,
公民安娜阿赫玛托娃
夜里在站岗。阿赫玛托娃虽然不是出生在列宁格勒,但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里度过大半生,把列宁格勒视为自己的故乡。保家卫国的战争加深了她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她目睹德寇炮击市区时造成的破坏,看到应征入伍的青年们与情人、与母亲怎样情深意切地吻别,她忘不了无辜儿童们被法西斯炮弹炸死的惨象。她知道,敌人无论多么疯狂残忍,战争不管会带来何等灾难,祖国一定会胜利,人民一定会胜利。这种信念,这种感情浸透了她四十年代写的诗篇。阿赫玛托娃是乘最后一班飞机撤离列宁格勒的,然后从莫斯科辗转到中央亚细亚的塔什干市。她在那里经常到医院慰问伤病员,为他们朗诵诗歌。
战争胜利后,1946年联共(布)中央以决议的形式,对她对左琴科和其他一些作家、艺术家进行了极不公允的批判,特别是党中央政治局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日丹诺夫的有关报告,对阿赫玛托娃破口大骂,实际上是在精神上判处了她死刑,说她是奔跑在闺房和礼拜堂之间的发狂的贵妇人,是混合着淫声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等等。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她的作品不予发表。这时她从事了大量的诗歌翻译,包括翻译我国屈原的《离骚》、李商隐等诗人的作品。
五十年代后期,她的名誉得到恢复,她的诗作重新出现于报刊之上。人们发现,她的缪斯仍然富有独特的魅力。她对历史的过去进行反思,对诗的使命进行再探讨,更重要的是她捧出一批富有哲理的、感人的新作,如《野蔷薇开花了》《子夜诗抄》和以极深沉的语调悼念亡友的诗篇。
阿赫玛托娃的诗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她还吸收了俄罗斯小说的表现手法。这一点奥曼德尔施塔姆早有评论。他在1922年写的《关于俄罗斯诗歌的通信》中,有这么一段颇有见地的话:阿赫玛托娃把十九世纪俄罗斯长篇小说的全部规模宏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引进了俄罗斯的抒情诗中。没有托尔斯泰和他的《安娜卡列宁娜》、没有屠格涅夫和他的《贵族之家》、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和列斯科夫的部分著作,也就不会有阿赫玛托娃的诗。阿赫玛托娃起源于俄罗斯小说而不是起源于诗歌。她是在注目于心理小说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那尖锐而又独特的诗歌形式的。在阿赫玛托娃的诗中,妇女不再是被任意描绘的对象,而是表达自己意志的主角。阿赫玛托娃的出现,在俄罗斯招来一大批模仿者,她们都企图用阿赫玛托娃的语言表述自己的心境。这事颇使诗人不安,以至使她写出下列的诗句:我教会了妇女们说话可是,
天哪,我怎么才能让她们住口?!除了祖国的文学遗产,阿赫玛托娃还广泛地吸收了世界文学宝藏的营养。她通晓法语与法国文学;通晓德语,早年还译过里尔克的诗;她懂英语,热爱莎士比亚;又可以阅读意大利文,并能大段地背诵但丁的《神曲》。她常常引用外国诗人的原句作为题词,说明她的学识渊博,也表明她与其他作者有一脉相通的思想感受。
诗人喜欢把自己零散的作品加以组合。几首不同的诗,写于不同的年代,甚至年月相距甚久,诗人却把它们排列在一起。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往往对某一现象如何长期苦思冥想,直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体。短的组诗如《在皇村》《离异》《莫斯科的红三叶》等,每组由三首诗形成。
阿赫玛托娃十分讲究诗学。对每首诗,长期推敲,反复修改,不到满意不罢休。正因为如此,有的诗有数种版本。
人民和历史是最后的审判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检验,证明安娜阿赫玛托娃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诗人。国外首先把她推到俄罗斯诗人首席的地位。
1964年意大利宣布那一年的国际诗歌埃特纳陶尔明纳大奖授予阿赫玛托娃。
1965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阿赫玛托娃文学博士荣誉学位。她不顾年迈体弱,应邀前往伦敦。亲临庆祝仪式,她戏称:这是在为我举行葬礼。难道能为一个诗人操办如此的活动?的确,俄国自普希金以来,哪位真正的诗人不是在悲惨中走向永恒的?
1966年历尽沧桑的阿赫玛托娃与世长辞,安葬在她晚年居住的科马罗沃镇的公墓里。
1988年,阿赫玛托娃一百周年诞辰时,苏联为她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当年她在圣彼得堡住过的喷泉楼里的几个房间改建成故居纪念馆。
历史从此洗掉了泼在她身上的污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