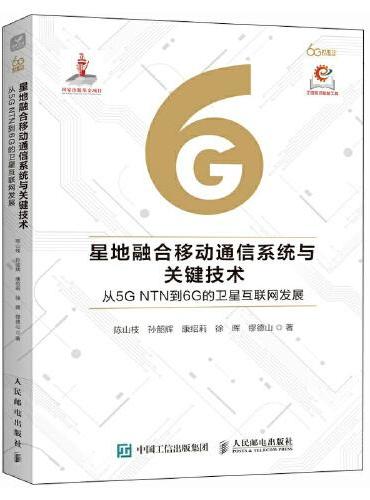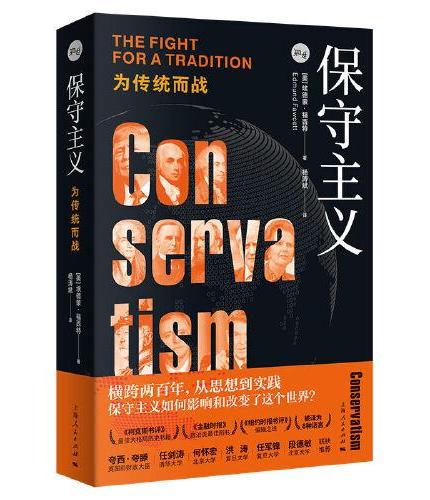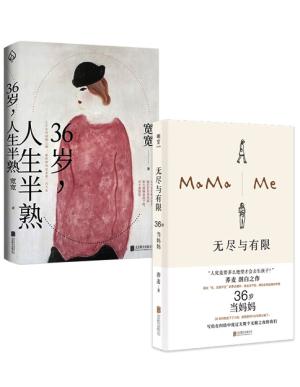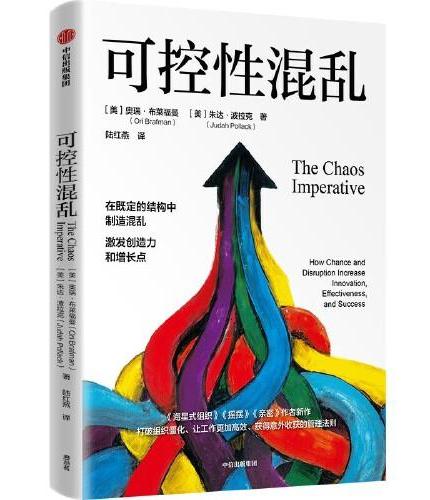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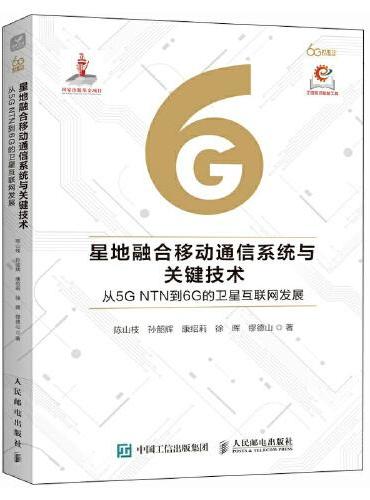
《
星地融合移动通信系统与关键技术从5G NTN到6G的卫星互联网发展
》
售價:HK$
212.6

《
妈妈,你好吗?(一封写给妈妈的“控诉”信,日本绘本奖作品)
》
售價:HK$
4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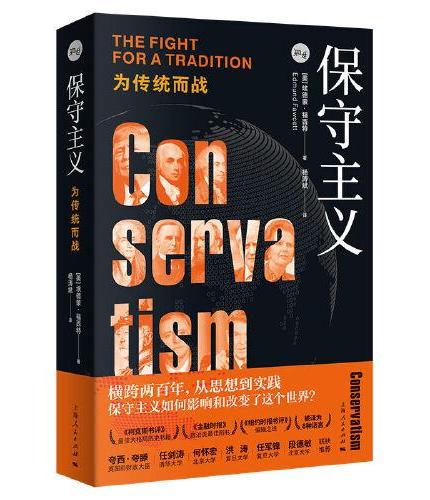
《
保守主义:为传统而战
》
售價:HK$
15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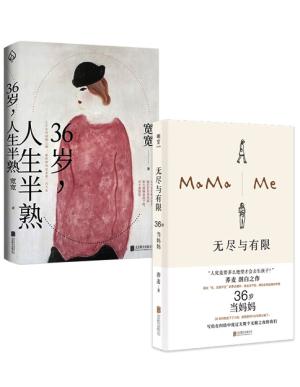
《
不同境遇的36岁:无尽与有限+人生半熟
》
售價:HK$
112.0

《
小时光 油画棒慢绘零基础教程
》
售價:HK$
8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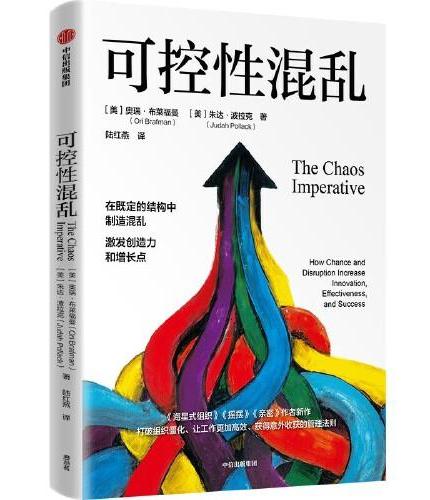
《
可控性混乱
》
售價:HK$
66.1

《
篡魏:司马懿和他的夺权同盟
》
售價:HK$
65.0

《
狂飙年代:18世纪俄国的新文化和旧文化(第三卷)
》
售價:HK$
177.0
|
| 編輯推薦: |
俄国文学专家刘文飞对白银时代精神遗产的全面描绘
三大诗歌流派: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诗派;
五位诗人: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
四位作家:阿尔志跋绥夫、扎米亚金、普里什文、巴别尔;
两位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
这就是白银时代
☆他们是现代艺术的开拓者
从康定斯基起,绘画的三要素被否定了。
从斯特拉文斯基起,音乐的单阶被彻底重建了。
从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起,诗歌艺术被重新定义了。
☆他们是世界文化的捍卫者
他们在偏僻的北疆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做温暖的思考。
他们关注古希腊神话,德国哲学,法国象征理论,第三罗马东正教思想。
☆他们是赤子情怀的文明的孩子
他们普遍显现出心灵的真诚。
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他们端坐在书房潜心写作。
在欲望膨胀、价值重估的年代,他们始终保持对艺术和自身价值的坚定信念。
在充满彷徨和疑虑的世纪之交,他们认真整理文化遗产,并为文化走向确定了新框架。
20世纪是一个文化艺术上的现代主义世纪,而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每个艺术门类的现代化都起源于世纪之初的俄国,这不能不让人感叹白
|
| 內容簡介: |
|
《白银时代的星空》是俄国文学研究专家刘文飞关于白银时代诗歌、文学和文化的学术随笔集。全书分为四个篇章,*部分是对白银时代三个主要诗歌流派:俄国象征诗派、阿克梅诗派和俄国未来诗派的整体介绍;第二部分重点讲述了白银时代几位主要诗人: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第三部分是关于白银时代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和别尔嘉耶夫的评述;*后是对白银时代小说家、散文家及其作品的评介,如阿尔志跋绥夫的《萨宁》、扎米亚金的《我们》、普里什文的散文和巴别尔的小说等。它们是作者力图接近白银时代文学和文化时留下的足迹,有着对白银时代的精神遗产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
| 關於作者: |
|
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美国耶鲁大学富布赖特学者,俄联邦友谊勋章获得者。主要译著有《俄国文学史》《时代的喧嚣》《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悲伤与理智》《三诗人书简》《萨宁》等。著作有《布罗茨基传》《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俄国文学演讲录》《白银时代的星空》等。
|
| 目錄:
|
也谈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代序)
俄国象征派诗歌
阿克梅派诗歌
俄国未来派诗歌
复归的古米廖夫
曼德尔施塔姆:生平与创作
再遇马雅可夫斯基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
茨维塔耶娃和她的诗歌
茨维塔耶娃的孤独
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
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之恋与《终结之诗》
你是我最好的诗: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女儿
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史意义
别尔嘉耶夫:俄国的命运和思想
阿尔志跋绥夫和他的《萨宁》
《我们》的其他读法
普里什文的思想史意义
巴别尔:谜团、瑰丽和惊世骇俗
后记
|
| 內容試閱:
|
也谈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代序)
语言中总有一些用不俗的名词,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等都是这样的词汇,每个民族的文学史中似乎都有被这样命名的时期,而此类名称所指的繁荣或珍贵又绝不仅限于文学范畴。
如今,被冠以白银时代之称谓的一段俄国文学和文化,又突然成了我们一个热门的话题和热门的出版选题,报刊上以此为题的文章不断亮相,光是以白银时代为题的丛书就接踵出了四套(作家版《白银时代丛书》六种,学林版《白银时代俄国文丛》五种,云南人民版《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七种,文联版《俄罗斯白银时代精品文库》四种),真可谓热闹非凡。
这样一种热闹的场面,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从阅读客体的角度看,20世纪之初的俄罗斯文化的确是五彩缤纷、硕果累累的。在白银时代,帕斯捷尔纳克所言的天才成群地诞生的罕见现象又一次在俄国出现。使人难以想象的是,在那短短的20余年时间里,在革命和战争此起彼伏的社会背景中,俄罗斯这一无论就文化传统还是就经济实力而言在欧洲都并不十分强大的民族,却向20世纪、向全世界贡献出了一大批的大师与杰作,并为诸多文化门类在20世纪的走向开了先河,如哲学中的宗教存在主义,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义,诗歌中的阿克梅主义,美术中的康定斯基,音乐中的斯特拉文斯基,等等。那的确是一座文化的富矿,我们在近期同时推出几套丛书,其中却很少有相同作家或作品的撞车,这也能使我们强烈地意识到那一时期文化积淀的深厚。然而,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这一时期的文化不仅未能在十月革命之后得到持续发展,反而受到了有意的冷淡,甚至是有意的遗忘,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阅读和研究。可以说,在当今的俄国,白银时代也同样是一个新的阅读热点。另一方面,从我们主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读者对俄罗斯的文学和文化一直有着一种较强的阅读期待,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传统的苏联文学似乎突然贬值了,与此同时,新的俄罗斯联邦却始终未能提供出足够多的、具有征服力量的新阅读文本。于是,我们将期待、选择的目光投向绚丽却又陌生的白银时代,乃是十分自然的。当然,促使我们关注白银时代文化的,也许还有在20世纪之末梳理20世纪文化遗产的某种潜在愿望,还有对世纪末情结有可能在白银时代文化中得到抚慰、赢得共鸣的某种希冀,还有学术圈中欲描绘出一幅20世纪俄语文学完整画面的刻意努力,等等。客观的、主观的原因,必然的、偶然的因素,共同制造出了目前这个白银时代文化热。
我国学者关于白银时代的讨论也很热烈,单就白银时代这一称谓的来历,就有了诸多意见。起先有人说,是俄国学者马科夫斯基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于慕尼黑的一本俄语诗歌专著中首次用白银时代界定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现代主义诗歌思潮;后来,有人在俄国学者的论述中发现,马科夫斯基本人称,是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最早提出了这一名称;最近,又有人从俄国的相关资料中发掘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俄国诗人奥楚普,他于1933年在巴黎的俄国侨民杂志《数目》上刊出了一篇题为《白银时代》的文章。其实,白银时代这个名称是谁最早提出的并不重要,因为这个名词毕竟不像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或昆德拉的媚俗等词那样是由作者独创出来的概念,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而是一个人人都可以用,并且也一直被沿用的词,就像文学等词一样,其内涵和指向已十分确定。我们不知道文学一词是谁最早提出来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作为整体的文学持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理解。
在是否使用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至今仍有一些学者(主要是一些老辈或老派学者)很反感白银时代的提法,认为它并不构成一个时代,他们很留恋苏联时期学者那个明确却累赘的概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似乎一用白银时代的概念,就是抬举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就是让它与其前辉煌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其后繁荣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平起平坐了。其实,将苏联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如索科洛夫等)的研究成果与当今有关白银时代的著作做一个比较,发现它们在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上并无太大的差异;再者,白银时代文化的总体倾向与其前、其后文化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不能因为其持续的时间短而忽视其独具的内涵和外延。因此,白银时代不构成一个时代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再看一看实际情况:在欧美斯拉夫学术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启用了白银时代的概念,大学里一直开设有以此为题的课程。以其为内容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俄国,这一概念也已经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了,就是以前那些用惯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之概念的学者也转而采用更简洁、更顺口的白银时代了;而在我们这里,白银时代的说法即便不能说深入人心,至少也已让圈内人士耳熟能详了。所以,现在来谈论是否该使用白银时代的提法,似乎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但是,在目前关于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上,有两种倾向是值得关注的:一种倾向是将白银时代的内涵宽泛化,另一种倾向是将白银时代的性质意识形态化。
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通常是指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后和苏维埃文化之前这一时间段中的文化,它横亘在两个世纪的交接处,时间跨度为20余年。关于白银时代的分期,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它大致的起止点还是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界定,即托尔斯泰之后和十月革命之前。当然,你可以说与托尔斯泰的后期创作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安德列耶夫等人的创作就已经显现出了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所不同的一些特征;当然,你还可以说,十月革命并未能截然阻断白银时代的文化惯性。任何一个时代都与其前后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个时期的划分因而也都是相对的。相比较而言,白银时代的划分倒还有着更为牢靠的依据,因为,作为其开端的俄国象征主义诗歌运动,有着与传统俄国文学迥然不同的美学风格和艺术趣味,而注重个人价值和艺术创新的白银时代文化必然会在倡导集体和集权的十月政治革命后不久迅速地中止。面对这样一个相对清晰的文学史分期,我们的一些学者却仍想做某种扩大化的工作,在尽量拉长、抻宽白银时代。有人欲加大白银时代的规模,认为其上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下限为斯大林时期的开始;有人则欲增加白银时代的内容,认为它不仅应该包括当时已近尾声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新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而且还应该包括进普列汉诺夫等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说。在已经出版的一套关于白银时代的丛书中,绝大部分作品都写于20世纪20年代末或30年代,无疑已是苏维埃时期的作品,丛书中的另一部小说属于批判现实主义晚期,真正意义上的白银时代作品也许只有一部。我们认为,应该赋予白银时代文化以一个相对稳定、相对明确的界定,否则,失去了其内在规定性的白银时代概念,便会面临外延泛化的危险,乃至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再一种倾向,便是在对白银时代的理解上添加了很多的意识形态意味。上述一些人士对白银时代概念的反感,其中就包含这方面的原因。他们认为,白银时代的一些作家后来大多不接受十月革命,在革命后流亡国外,与后来的苏联文学一直处于对立状态,因而是不应大加宣传的。令人奇怪的是,有些鼓吹白银时代文化的学者却也持有与此相同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白银时代文化的意义,就在于革命时与现实的距离和革命后与专制的对峙。这里,在低估或高估白银时代的人士身上都出现了一个时代倒错现象,即忽略了白银时代是出现在十月革命之前,完全依赖其与之后时代的联系或其在之后时代中的命运去看待它,是难以对它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的。于是,我们听到了关于白银时代文化为颓废文化的指责,我们听到了关于那一时期的作家世界观落后脱离人民的说法。于是,我们更常在关于白银时代的文字中读到某些作家的悲剧命运以及关于这些命运的感慨。有意无意之间,人们在将白银时代的文学等同于苏维埃时期的境外流亡文学非官方文学乃至持不同政见者文学。例如,人们最近在谈论白银时代文学时,就时常提及包括肖斯塔科维奇和叶夫图申科作品在内的花城版的《流亡者文丛》,有人还将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也归入了白银时代作家的行列。这一切都在强化白银时代文化与苏维埃文化的对立,并欲在这种对立中分出一个高低来。文化与专制,知识分子在集权统治下的命运,这只是白银时代文化的一个内容,不是其全部,而且还只是一个后来附加上去的内容。再者,对于文化与专制,也可以有多种理解。比如在谈到曼德尔施塔姆的遭遇时,似乎是阿赫马托娃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换一种社会制度,曼德尔施塔姆的命运也不一定就会好到哪里去。最近出版的一本索尔仁尼琴传记写道,流亡到美国之后的索尔仁尼琴,与金钱专制下的美国社会同样是格格不入的,该传记的作者因而称索尔仁尼琴为永恒的持不同政见者。可见,纠缠在文化与专制之冲突这一点上,并将这一点视为白银时代文化之重点,是不恰当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总之,给白银时代的文化添加过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既妨碍我们客观、冷静地评判其价值和意义,也不利于我们养成历史地接受文化遗产的良好习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