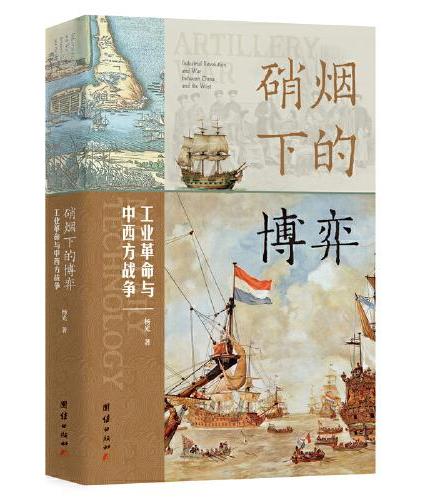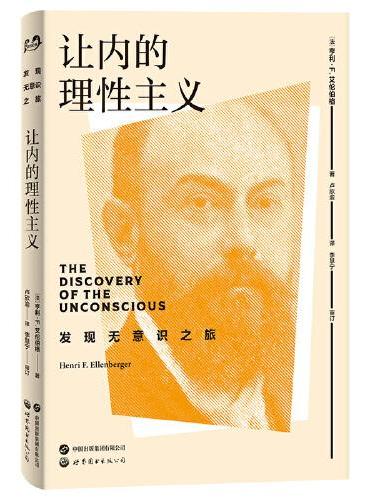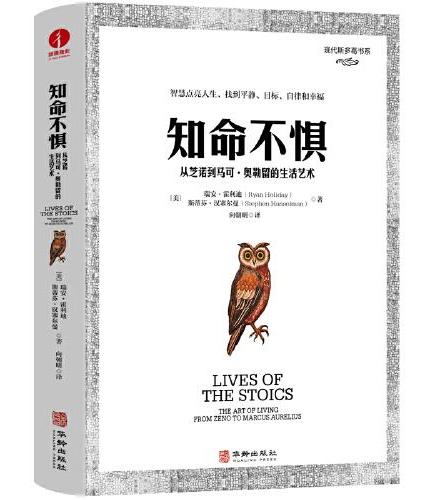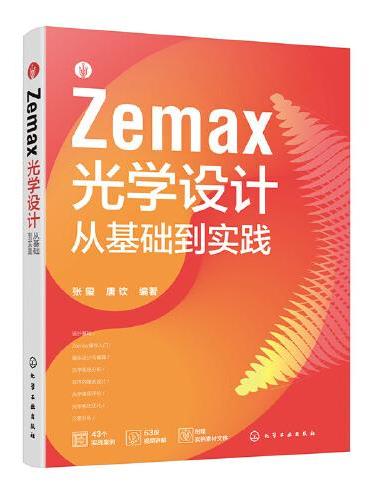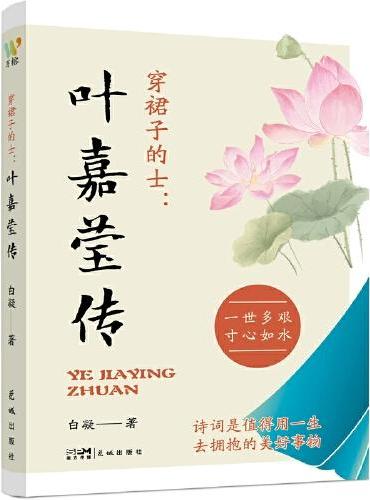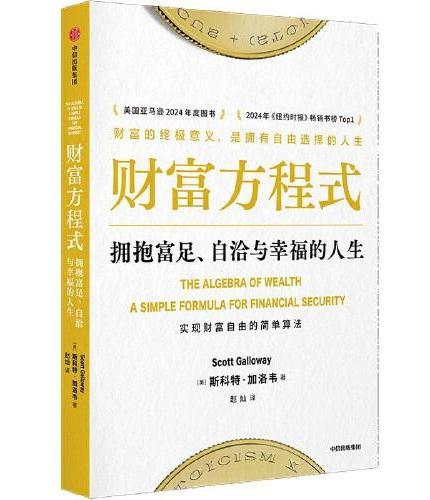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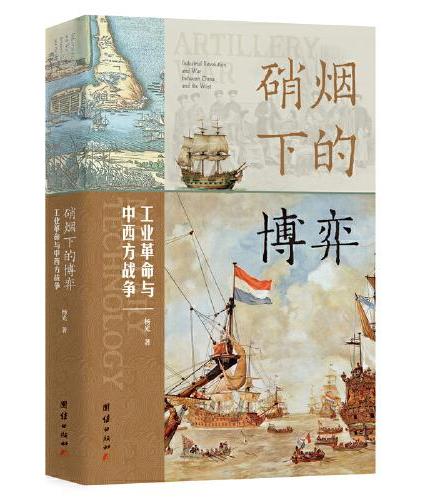
《
硝烟下的博弈:工业革命与中西方战争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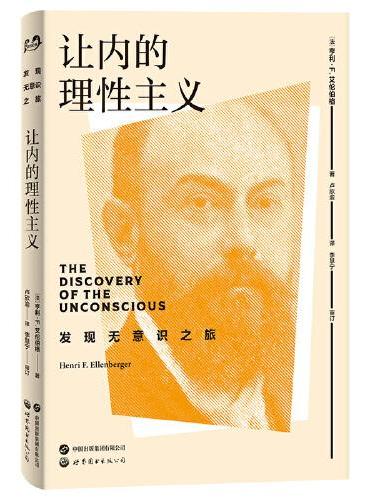
《
让内的理性主义 发现无意识之旅
》
售價:HK$
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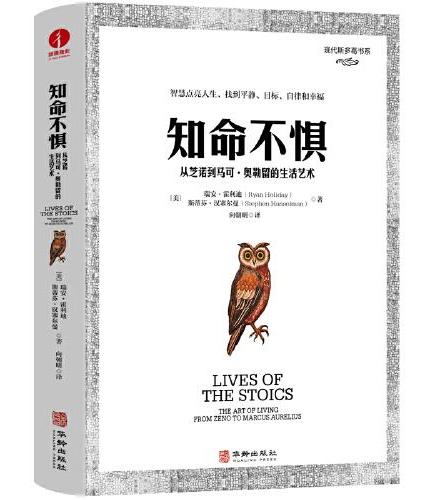
《
知命不惧:从芝诺到马可·奥勒留的生活艺术
》
售價:HK$
1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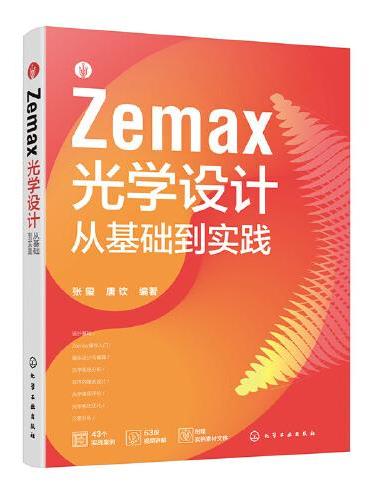
《
Zemax光学设计从基础到实践
》
售價:HK$
132.2

《
全球化的黎明:亚洲大航海时代
》
售價:HK$
109.8

《
危局
》
售價:HK$
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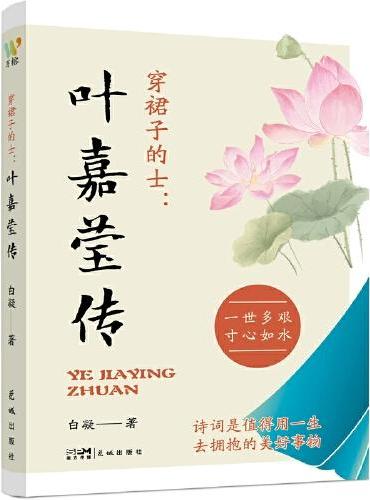
《
穿裙子的士:叶嘉莹传
》
售價:HK$
5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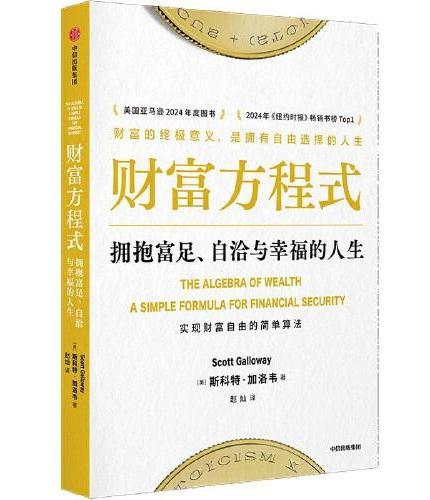
《
财富方程式
》
售價:HK$
77.3
|
| 編輯推薦: |
是枝裕和电影《幻之光》小说原作者宫本辉
收录的《浮月》《烧船》《胸之香》均为作者经久不衰的短篇小说力作
用精湛巧妙的叙事,探索失落的人生片段
|
| 內容簡介: |
宫本辉是日本当代文学大家,日本芥川龙之介奖、太宰治奖等文学大奖的得主。在这个日趋浮躁的社会,宫本辉难能可贵地坚持着古典美学,用正统的小说创作抵制商业对文学的侵袭。他曾说:读小说,那是忘我,是感动,是陶醉。理性探究,或执著于观念,在艺术的创造上是第二位的东西。那*位的东西和第二位的东西颠倒的结果,便成了所谓现代这段历史所携带的毒。他在写作中力求带给读者*纯粹的感动和忘我,在看似平凡的故事中勾起读者难以释怀的回忆或感慨。因此,宫本辉成为了日本当代文坛的中流砥柱,至今仍笔耕不辍,持续地影响着这个浮躁年代中仍然静心阅读的读者。
《烧船》是宫本辉的代表性短篇小说集。作家在本书《后记》中表示,正因为要把故事凝缩在几页之内,所以写一篇短篇小说就像把一滴血硬挤出来那么辛苦。但是,优秀的作品又不能显露这些辛苦。他认为,水随器物而有形,最好的短篇小说要像水一样,失去自己的状态,只会根据喝下它的人,显得或浓或淡。于是,宫本辉用这样的标准约束自己,写下了《烧船》中的七篇:《浮月》《烧船》《涟漪》《胸之香》《时雨屋的历史》《钓深海鱼》《在路上起舞》。它们篇幅相当,质量也很平均。在这些故事里,宫本辉借助诗化的意象,比如海上的明月、沙滩上的覆舟、丈夫胸口的气息等,把生老病死之中的失去意味具象化,变得可感而可悲,余韵悠长。
|
| 關於作者: |
宫本辉(1947 )是日本当代作家,生于兵库县,毕业于追手门学院大学文学系,1977年以《泥河》获第13届太宰治奖,翌年以《萤川》获第78届芥川龙之介奖,1987年凭《优骏》获第21届吉川英治文学奖,2004年以《有约的冬天》获第54届艺术选奖文部科学大臣奖,2010年以《骸骨楼的庭院》获第13届司马辽太郎奖,同年获秋季紫绶褒章,2020年获旭日小绶章。
宫本辉主要作品另有:小说《星星的伤心事》《道顿堀川》《烧船》《锦绣》《流转之海》《多瑙河旅人》《天之夜曲》《热闹的天地》等,随笔《二十岁的火影》《命器》《堆着书的小船》《生物们的房间》,对谈集《与过路行人》《主题》等。
|
| 目錄:
|
浮月
烧船
涟漪
胸之香
时雨屋的历史
钓深海鱼
在路上起舞
媒体评论男女、母子,人形形色色的悲喜爱憎,都在这七则由三十页手稿浓缩成的短篇小说中了。这是一部描写人生阴暗处的动人心弦的短篇集。
池内纪(日本文学批评家、翻译家)
有句话叫作水随器物而有形,所以如果把短篇小说比作水的话,*好的状态就是让它失去本来的状态,根据喝下它的人的感觉,有时显得浓,有时又显得淡吧。
我觉得那才是*好的短篇小说,于是按照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写下了《烧船》中的七篇。
宫本辉
免费在线读《后记》:
这期间写下的短篇小说,算上这本《烧船》中收入的几篇,总共有三十六篇了。
这些小说,除了两三篇之外,基本上都是三十张四百字稿纸左右的篇幅。
过去教导我写小说的先生讲,不能把三十张稿纸篇幅的短篇小说写好的话,说到底也就是个二流作家。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规则。
虽说只有三十页纸。但正是因为要把故事凝缩在三十页之内,所以夸张地说,对我而言,写一篇短篇小说就像把一滴血硬挤出来那么辛苦。每每刚写完一行,我就立刻会感觉到绝望的痛楚。
但是,倘若在作品的某个地方不小心显露出作家的辛苦来,我就会马上面临究竟是为什么要把它凝缩在三十页的问题,眼前的作品也就变成那种应该立刻弃如敝履的替代品了。
因此,哪一行是没必要的,哪句话是多余的,哪里有存在不足,我的神经极力地对它进行琢磨推敲,有时反而让作品的世界变得狭小了,会使故事变得不再从容,还会让形式变得过于讨巧。很难避免陷入这样的陷阱。
有句话叫作水随器物而有形,所以如果把短篇小说比作水的话,最好的状态就是让它失去本来的状态,根据喝下它的人的感觉,有时显得浓,有时又显得淡吧。
我觉得那才是最好的短篇小说,于是按照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写下了《烧船》中的七篇。
《胸之香》:
和他不一样,我从小就喜欢吃面包。
我出生一个月后,母亲就死了。不久父亲就和一个年轻的女人私奔了,一直下落不明。我被亲戚们轮流抚养。留在我心中最早的记忆,就是烤面包的时候,酵母的气味。
四岁的时候,我寄居在一对和我没有血缘关系的远亲夫妇家中。那对夫妇家的隔壁就是一家面包店。每天早上五点,烤面包那香喷喷的气味就会飘过来。《后记》:
这期间写下的短篇小说,算上这本《烧船》中收入的几篇,总共有三十六篇了。
这些小说,除了两三篇之外,基本上都是三十张四百字稿纸左右的篇幅。
过去教导我写小说的先生讲,不能把三十张稿纸篇幅的短篇小说写好的话,说到底也就是个二流作家。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规则。
虽说只有三十页纸。但正是因为要把故事凝缩在三十页之内,所以夸张地说,对我而言,写一篇短篇小说就像把一滴血硬挤出来那么辛苦。每每刚写完一行,我就立刻会感觉到绝望的痛楚。
但是,倘若在作品的某个地方不小心显露出作家的辛苦来,我就会马上面临究竟是为什么要把它凝缩在三十页的问题,眼前的作品也就变成那种应该立刻弃如敝履的替代品了。
因此,哪一行是没必要的,哪句话是多余的,哪里有存在不足,我的神经极力地对它进行琢磨推敲,有时反而让作品的世界变得狭小了,会使故事变得不再从容,还会让形式变得过于讨巧。很难避免陷入这样的陷阱。
有句话叫作水随器物而有形,所以如果把短篇小说比作水的话,最好的状态就是让它失去本来的状态,根据喝下它的人的感觉,有时显得浓,有时又显得淡吧。
我觉得那才是最好的短篇小说,于是按照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写下了《烧船》中的七篇。
《胸之香》:
和他不一样,我从小就喜欢吃面包。
我出生一个月后,母亲就死了。不久父亲就和一个年轻的女人私奔了,一直下落不明。我被亲戚们轮流抚养。留在我心中最早的记忆,就是烤面包的时候,酵母的气味。
四岁的时候,我寄居在一对和我没有血缘关系的远亲夫妇家中。那对夫妇家的隔壁就是一家面包店。每天早上五点,烤面包那香喷喷的气味就会飘过来。
这个家也很穷,很难有机会吃到刚烤好的面包。在面包店前面玩的时候,有时候店主人会心血来潮送给我面包吃。那面包的味道,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几年前去检查心脏的时候,住院的第二天,我见邻床病友的丈夫给她带去了面包店里刚刚烤好的面包,再看看自己盘里的吐司,不由得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那个面包店店主对我说,不介意的话就尝一个吧。看年纪,他应该比你小三四岁。剃得干干净净的脖颈,细而深的双眼皮,其中似乎潜藏着手艺人常有的那种顽固和孤僻。
我说,这么早就给生病的妻子送面包来,这是个多么温柔的丈夫啊。女人告诉我,她的丈夫是面包店店主,自家的店离这家医院特别近。
我看了看床头贴着的患者名牌。上面写着铃本贵美江。
那天上午和下午都在做检查,傍晚四点钟,我才坐着轮椅回到了病房。连吃晚饭的力气都没有,就睡过去了。
你和孙儿们来看我。你们说明天再来,就回去了。你们离开后,我好不容易打起精神去厕所,在走廊里挪着无力的双腿往前走的时候,就看到早上见过一面的面包店店主正从男厕所里出来。他和我打招呼说,晚上好。
我见他之前都没陪在妻子身边,就问他去做什么了。他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是去用医院的洗衣机洗衣服了。说,从出生起,都是母亲替他洗衣服,不过母亲在前一年的秋天过世了。他们夫妻有一对五岁的双胞胎儿子。有了孩子之后,每天都会有大量的脏衣服要洗。这家医院有给住院患者使用的洗衣机和干燥机,所以自从妻子住院之后,每天等店里打烊了,他就到这里来洗衣服。
厕所旁边的洗衣房的门上,贴着住院患者以外人员禁止使用的标示。
年轻的面包店店主为了不让护士和值班医生听见,压低声音,凑近了和我说话。
这时候,我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味。那明明是一种沁透心脾的、令人眷恋的香气,而且也绝不是我的嗅觉或意识出了问题,但,我却不知道那种香气是从哪里传来的。
解了手,我回到床上,思索着那股让人怀念的香气到底是什么的味道。
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是洗衣液的味道吗?或者是我以前到医院看望病人的时候闻到的医院特有的味道?还是探望病人时送来的水果或花的香味?
不,都不是。不是那种随处都可能闻到的香气。是我在更早以前闻到的、特殊而又让我难以忘怀的香气。那,到底是什么呢
快到熄灯的时间了。我在睡觉之前又去了一次厕所。
啊,是了。那种味道是在年轻的面包店店主凑近我说话的时候闻到的。所以,那一定是酵母的味道。
我暂且找到了解释,就闭上眼睛准备睡觉。护士来关病房的灯,和我打了声招呼,说明天下午还有检查,鼓励我加油。
我嗯、嗯地点头答应着。又对躺在邻床的店主妻子道了晚安。
半夜醒来、又一次去厕所的时候,我终于想起了那到底是什么的味道。我明白了,那种令我怀念的味道,是我丈夫的体味。如同遭到雷击一样,深夜里,我在没有人的医院的厕所里,站了很久很久。
是我丈夫的香味。而且,是他胸部和脖颈一带的气味
我和那个年轻的面包店店主是在洗衣房门前聊天的。我朝那边走去。厕所里除臭剂的味道很重,我也知道,在洗衣房附近再次闻到那种香气是不可能的。我的心里就像条件反射一样,丈夫、面包店、在邮局工作的女人、她怀孕的肚子,全都一下子串在了一起,宛如针刺一般,向我的身体袭来。
我脑海里的那种香气,除了从自己丈夫身上闻到过,别处是再也没有的了。那,和狐臭的那种气味是不同的,或者说,那并不是由于某种具体的理由而产生的单纯的气味。那是一种由某个确定的肉体所散发出来的、复杂又朦胧的、极其特殊的香气。
仅仅是微弱的空气流动就能让它瞬间消散。它很微妙,而且仅此一种
这天晚上,我时隔十几年再次沉浸在对丈夫的回忆之中。而在电车中见到的那个女人的神情和她鼓起的肚子、回忆起来的丈夫的种种笑脸和怒容、他意气风发走路的样子还有疲倦的背影,却在我眼前逐一远去了。
我也很熟悉你的气味。毕竟你是我生的,是我养大的,我当然很熟悉你的气味。
但,你的那种香气,毕竟和我丈夫的不一样。那是你独有的香气。
那为什么,那个年轻的面包店店主,会和我的丈夫有着相同的气味呢。
陪着她穿过染开罗城南和她的家。他们
|
| 內容試閱:
|
《后记》:
这期间写下的短篇小说,算上这本《烧船》中收入的几篇,总共有三十六篇了。
这些小说,除了两三篇之外,基本上都是三十张四百字稿纸左右的篇幅。
过去教导我写小说的先生讲,不能把三十张稿纸篇幅的短篇小说写好的话,说到底也就是个二流作家。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规则。
虽说只有三十页纸。但正是因为要把故事凝缩在三十页之内,所以夸张地说,对我而言,写一篇短篇小说就像把一滴血硬挤出来那么辛苦。每每刚写完一行,我就立刻会感觉到绝望的痛楚。
但是,倘若在作品的某个地方不小心显露出作家的辛苦来,我就会马上面临“究竟是为什么要把它凝缩在三十页”的问题,眼前的作品也就变成那种应该立刻弃如敝履的替代品了。
因此,哪一行是没必要的,哪句话是多余的,哪里有存在不足,我的神经极力地对它进行琢磨推敲,有时反而让作品的世界变得狭小了,会使故事变得不再从容,还会让形式变得过于讨巧。很难避免陷入这样的陷阱。
有句话叫作“水随器物而有形”,所以如果把短篇小说比作水的话,好的状态就是让它失去本来的状态,根据喝下它的人的感觉,有时显得浓,有时又显得淡吧。
我觉得那才是好的短篇小说,于是按照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写下了《烧船》中的七篇。
……
《胸之香》:
……
和他不一样,我从小就喜欢吃面包。
我出生一个月后,母亲就死了。不久父亲就和一个年轻的女人私奔了,一直下落不明。我被亲戚们轮流抚养。留在我心中早的记忆,就是烤面包的时候,酵母的气味。
四岁的时候,我寄居在一对和我没有血缘关系的远亲夫妇家中。那对夫妇家的隔壁就是一家面包店。每天早上五点,烤面包那香喷喷的气味就会飘过来。
这个家也很穷,很难有机会吃到刚烤好的面包。在面包店前面玩的时候,有时候店主人会心血来潮送给我面包吃。那面包的味道,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几年前去检查心脏的时候,住院的第二天,我见邻床病友的丈夫给她带去了面包店里刚刚烤好的面包,再看看自己盘里的吐司,不由得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那个面包店店主对我说,不介意的话就尝一个吧。看年纪,他应该比你小三四岁。剃得干干净净的脖颈,细而深的双眼皮,其中似乎潜藏着手艺人常有的那种顽固和孤僻。
我说,这么早就给生病的妻子送面包来,这是个多么温柔的丈夫啊。女人告诉我,她的丈夫是面包店店主,自家的店离这家医院特别近。
我看了看床头贴着的患者名牌。上面写着铃本贵美江。
那天上午和下午都在做检查,傍晚四点钟,我才坐着轮椅回到了病房。连吃晚饭的力气都没有,就睡过去了。
你和孙儿们来看我。你们说明天再来,就回去了。你们离开后,我好不容易打起精神去厕所,在走廊里挪着无力的双腿往前走的时候,就看到早上见过一面的面包店店主正从男厕所里出来。他和我打招呼说,晚上好。
我见他之前都没陪在妻子身边,就问他去做什么了。他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是去用医院的洗衣机洗衣服了。说,从出生起,都是母亲替他洗衣服,不过母亲在前一年的秋天过世了。他们夫妻有一对五岁的双胞胎儿子。有了孩子之后,每天都会有大量的脏衣服要洗。这家医院有给住院患者使用的洗衣机和干燥机,所以自从妻子住院之后,每天等店里打烊了,他就到这里来洗衣服。
厕所旁边的洗衣房的门上,贴着“住院患者以外人员禁止使用”的标示。
年轻的面包店店主为了不让护士和值班医生听见,压低声音,凑近了和我说话。
这时候,我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味。那明明是一种沁透心脾的、令人眷恋的香气,而且也绝不是我的嗅觉或意识出了问题,但,我却不知道那种香气是从哪里传来的。
解了手,我回到床上,思索着那股让人怀念的香气到底是什么的味道。
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是洗衣液的味道吗?或者是我以前到医院看望病人的时候闻到的医院特有的味道?还是探望病人时送来的水果或花的香味?……
不,都不是。不是那种随处都可能闻到的香气。是我在更早以前闻到的、特殊而又让我难以忘怀的香气。那,到底是什么呢……
快到熄灯的时间了。我在睡觉之前又去了一次厕所。
啊,是了。那种味道是在年轻的面包店店主凑近我说话的时候闻到的。所以,那一定是酵母的味道。
我暂且找到了解释,就闭上眼睛准备睡觉。护士来关病房的灯,和我打了声招呼,说明天下午还有检查,鼓励我加油。
我“嗯、嗯”地点头答应着。又对躺在邻床的店主妻子道了晚安。
半夜醒来、又一次去厕所的时候,我终于想起了那到底是什么的味道。我明白了,那种令我怀念的味道,是我丈夫的体味。如同遭到雷击一样,深夜里,我在没有人的医院的厕所里,站了很久很久。
是我丈夫的香味。而且,是他胸部和脖颈一带的气味……
我和那个年轻的面包店店主是在洗衣房门前聊天的。我朝那边走去。厕所里除臭剂的味道很重,我也知道,在洗衣房附近再次闻到那种香气是不可能的。我的心里就像条件反射一样,丈夫、面包店、在邮局工作的女人、她怀孕的肚子,全都一下子串在了一起,宛如针刺一般,向我的身体袭来。
我脑海里的那种香气,除了从自己丈夫身上闻到过,别处是再也没有的了。那,和狐臭的那种气味是不同的,或者说,那并不是由于某种具体的理由而产生的单纯的气味。那是一种由某个确定的肉体所散发出来的、复杂又朦胧的、极其特殊的香气。
仅仅是微弱的空气流动就能让它瞬间消散。它很微妙,而且仅此一种……
这天晚上,我时隔十几年再次沉浸在对丈夫的回忆之中。而在电车中见到的那个女人的神情和她鼓起的肚子、回忆起来的丈夫的种种笑脸和怒容、他意气风发走路的样子还有疲倦的背影,却在我眼前逐一远去了。
我也很熟悉你的气味。毕竟你是我生的,是我养大的,我当然很熟悉你的气味。
但,你的那种香气,毕竟和我丈夫的不一样。那是你独有的香气。
那为什么,那个年轻的面包店店主,会和我的丈夫有着相同的气味呢。
……陪着她穿过染开罗城南和她的家。他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