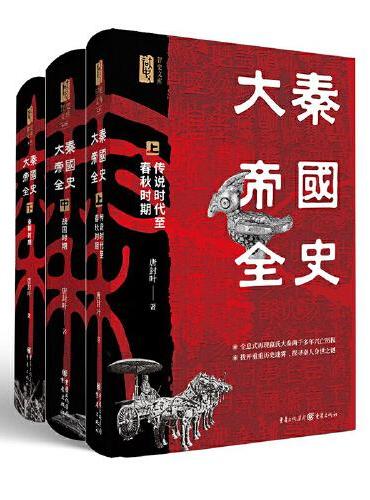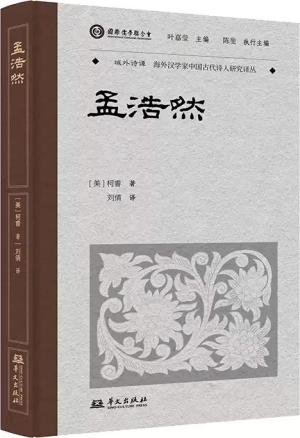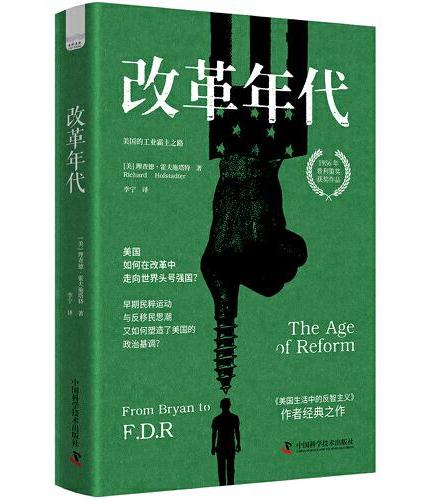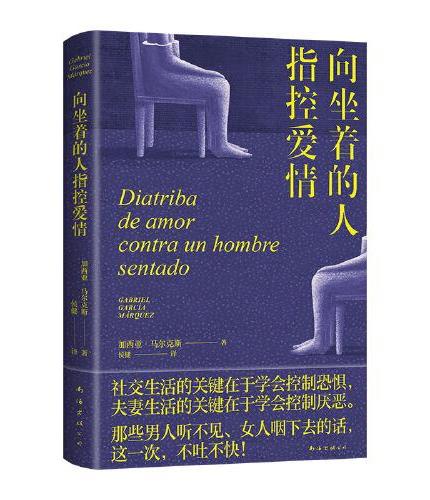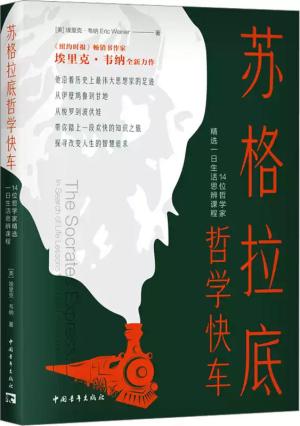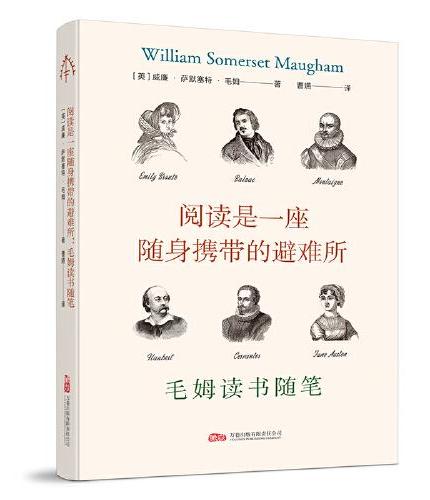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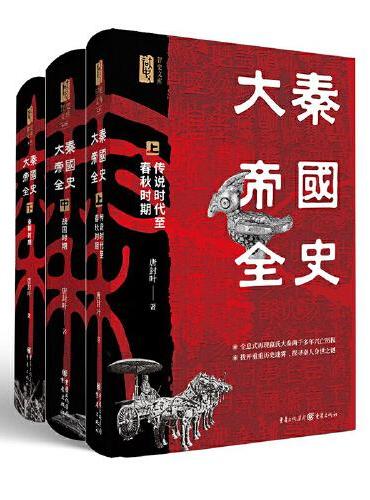
《
大秦帝国全史
》
售價:HK$
2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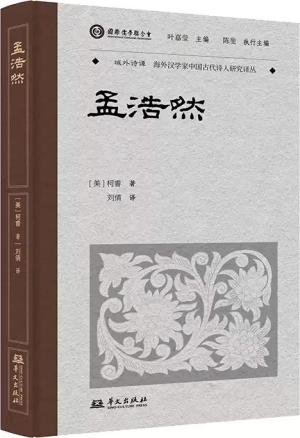
《
孟浩然(英语世界中的*一本孟浩然传记)
》
售價:HK$
7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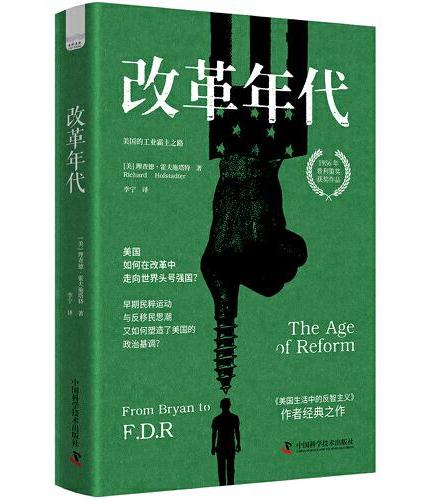
《
改革年代:美国的工业霸主之路
》
售價:HK$
74.8

《
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蔡康永2025新作)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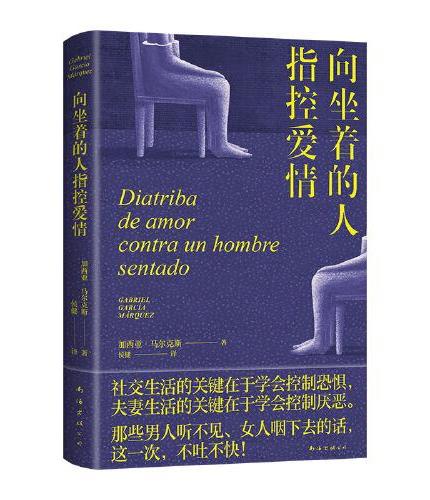
《
向坐着的人指控爱情
》
售價:HK$
4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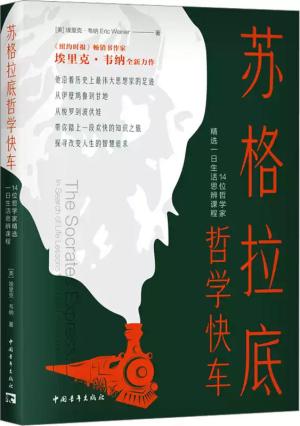
《
苏格拉底哲学快车:14位哲学家精选一日生活思辨课程
》
售價:HK$
65.9

《
放手的练习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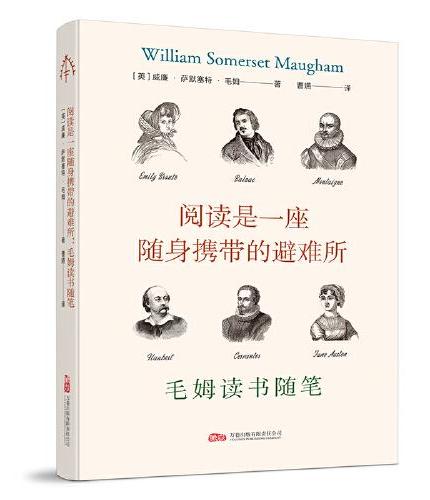
《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毛姆读书随笔
》
售價:HK$
49.5
|
| 編輯推薦: |
|
陈应松中篇小说代表作《夜深沉》《太平狗》《马嘶岭血案》《松鸦为什么鸣叫》等,像锋利的刀刃,直逼人类生存的困境,追问生命的意义,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良知和同情。
|
| 內容簡介: |
|
本书精选陈应松中篇小说代表作《夜深沉》《太平狗》《马嘶岭血案》及“神农架系列”《松鸦为什么鸣叫》等。远离城市生活的浮华,神农架的高山和密林深处,背负生与死的农民,在道路与行走中持久地守望明天;滚钩上的命,江上捞尸人的无奈与痛楚你不会懂……真实的底层书写,像锋利的刀刃,直逼人类生存的困境,追问生命的意义,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良知和同情。作者用全部的心灵去感知大地的深度与炎凉,用笔写下自身对命运的发现,记录人类生存的理由,体现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家国情怀。
|
| 關於作者: |
|
陈应松,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1996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有长篇小说《森林沉默》《还魂记》《猎人峰》《到天边收割》《魂不守舍》《失语的村庄》,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等100余部,《陈应松文集》40卷,《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选》3卷。小说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大奖、《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小说奖、全国环境文学奖、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梁斌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华文成就奖(加拿大)、钟山文学奖、湖北文学奖等。2015年被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文化名家”称号。作品翻译成英、法、俄、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日、韩等文字到国外。中篇小说曾7年进入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小说排行榜”。原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长,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
|
| 目錄:
|
自序 / 001
夜深沉 /
母亲 /
独摇草 /
滚钩 /
马嘶岭血案 /
太平狗 /
松鸦为什么鸣叫 /
|
| 內容試閱:
|
自序
编这本集子的时候,我正在神农架享受没有酷暑和病毒的生活。回过头看这些小说,心想,怎么在这么多小说中没有写美味的木姜子、豆瓣菜(瓜子金)、岩板菜和凉拌花椒叶土豆叶呢?还有箭竹米,还有竹叶茶。好在,我还在继续写神农架。二十年了,我没有仔细倾听过香溪河的水,没有观察野马河、潮水河和阴峪河在多雨的夏季时,一天水位涨跌的变化。还有一个朋友说,你坐在香溪河边就能钓到娃娃鱼。很久的时候,一个朋友一天钓了二十多斤。莫非我没有在神农架生活过?这证明我对神农架知之甚少,神农架太庞大,而我太渺小。
想起我在前两年的元月去神农架时,碰到了十年一遇的暴雪。在皇界垭的地方,雪风呼呼大作,在山上拍照时,手机因为气温极低而自动关机。我从垭子上下来,手已经冻肿了,双脚失去了知觉。这是我此生遭遇过为寒冷的一次,但也是我为开心的一次。我的身体在暴雪中,心中却温暖旷畅。而在这之前的十二月,我去大九湖的途中,在凉风垭,看到了雪后的群山之间,出现的瀑布云海,云海像飞漱的瀑布奔腾直下,气势磅礴不可言状。司机说,他跑这条路二十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云海。我站在悬崖边,明朗的阳光在高山尖上拖着我欢呼的影子,悬崖像一只箭插在云海中,但我在云海之上,有超拔万物的高大和脱颖而出之感。我是幸运的,我可能与这个山有一点小缘分吧。
为写新的小说,我几年前在红花坪村黄运国家里住了些时间,看到了家家不上锁的古代景观,也知道了神农架的众多鸟类,弄清了一些鸟名,听来此养蜂的扬州老刘讲蜜蜂的故事,一下子把我迷住了。也吃了不少的野菜,鸭脚板、马兰头、川芎叶之类。
我喜欢的围炉夜话是坐在火塘边,头顶是一排排腊肉。但现在的火塘变成了两用的大铁炉桌子,虽然茶杯可以放在桌子上,却不能双手绞在膝前,也不能在围炉后,与大伙互拍肩上和头上的白灰,或者有一点点熏人和呛喉的柴烟,这些在许多人家都没有了。正月十五夜,一个男人手捧烧红的火炭(两手来回捣腾),投向山里,驱赶毛狗(狐狸和豺狼),这样的英雄壮举也消失了。
只是星空依然,山水更绿了,山变得肥硕臃肿,没有骨感,风雪也没有久远时候的迅猛残暴,横扫千里。
生活越来越近,伸手可触,生活也似乎柔软多了,有了些许的温度。但生活也面目全非。譬如那个我心目中的狂野的神农架,那个群山,突然醒来了,由一个野地精灵变成了一个与世界靠近的俗人。
还有荆州,我挂职的第二个地方,同样的感觉也让我有恍如隔世之感。
我庆幸赶在那个时候,在封闭远离的环境中,我先所有人置身其中,在别人都没有发现那块地方的时候抢先一步,完成了我文学的积累,这真是有福的事。作为个到来者,我得到了山神给我的回报。
没有好完美的写作,只有个的写作。“我写作不是在你们中间出名,而是离你们更远。”卡夫卡的这句话我想改一个字:我写作不是在你们中间出现,而是离你们更远。
因为离你们远,我有发言权。
我喜欢把一马平川走成千沟万壑。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让我在这里说了几句我想说的话,也有了这本精美的小说集。
2020年6月22日于神农架
夜深沉
一
一个人没有故乡,就等于死后没有棺材。隗三户一路这么想。他在网上看过“虎渡河人论坛”,一帮在外的老乡对家乡的豆皮子、锅盔(类似烧饼)、鲊胡椒大力推崇,仿佛在家乡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其实不过是对家乡的一种意淫罢了。
隗三户开着他的二手广州本田从广东回来,已是凌晨一点。他的车在路上坏了三四次,本来十个小时的路程,跑出了十八个小时,人差不多散架了,身上是机油,手上也是机油。在湖南境内,一次爆胎,差点冲进汨罗江中;还有一次发动机不明原因地着火,要不是车上有个灭火器,车肯定烧成了一副骨架子;还有,一路开来,因为减震器坏掉的原因,车一路摇头晃脑,蹦蹦跳跳,发出哄哄的猪叫声。若不是换了个减震器,人肯定会疯。一个曾经的农民,现被虚名蛊惑,企图抓回来一把乡人的艳羡和夸赞甚而是嫉妒。让人嫉妒是很开心的事。在村里老是受人欺负的隗结巴的儿子,冬天没裤子穿的隗三户,在外混得不错啊,竟开着小汽车回来了,这还不牛吗?其实,两万多块钱的旧家伙,打肿脸充胖子,自欺欺人,自作自受,这样的破车,没把人害死,还能指望一路跑出奔驰宝马的感觉来?!
自欺欺人的隗三户终于回来了,回来却如走在异乡,没有一点儿回家的感觉,家乡已没有了亲人,房子早已卖掉,已被拆了,承包地早就退了。心茫然而虚空,没有坝岸,不知车往哪儿开,人往哪儿走。一阵汹涌的伤感向他袭来,车就慢了,在路上迟迟疑疑。好在路上空旷,半夜三更,鬼都没一个。这个清明才真叫人断魂哩。路上似有游荡的鬼魂,孤魂。是不是自己?自己就是一个孤魂野鬼。车子是热的,自己肯定活着。是鬼魂一阵风就飘回来了,不会一路这么折腾。
不过,让他兴奋的是一浪一浪的油菜花的清香,开着车窗,那香味儿就一阵一阵扑来,活像个妖冶调皮的女子,填满了他周围的每一片空间。过去也未曾觉得它的香味儿,只是离开时间长了,对故乡的气味敏感起来。满田里都是油菜,都是那黄色的花。这闹闹嚷嚷的气氛,过去没有过。过去好像没栽种过这么多的油菜,油菜也没这么好、这么高、这么茂盛。听说油菜籽今年价格不行,忧心的是种油菜的人,对于回乡祭祖的诸多游子来说,这满原野的油菜花和香味儿,就是他们的乡愁,任何惶然不安的心绪都将被打下去,取而代之的是高兴和激动。住在这油菜花海中会是什么感觉?……于是回乡建房的念头灼灼地燃了起来,更加强烈了。
早的念头缘于他去年一场大病。是在去年底,他死里逃生。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书。也不是什么绝症,脑膜炎,来得陡急,人送进医院就昏迷不醒了,身上出现大块紫斑(民间叫尸斑!),血压一度下降为零。他自己反正不知道了。更有甚者,脚指头一个一个坏死。还能活过来,这只能证明隗家人没做过什么恶事,前世都是好人。当然也可以说是生命力顽强,视死如归。遭了这一劫,就不迷信了,人已在地狱门口兜了一圈,花去了五六万,七八个脚指头烂光了,走路九晃十荡。三周后出院,不出院这些年在外挣的几个辛苦银子,将要全部贡献给广州医院。
还是说那场病,隗三户昏迷,接着下病危通知书,老婆除了哭,束手无策。平常老婆只是个家庭妇女,一切听他的。没有亲戚六眷在身边,打电话后有一两个老乡来看过,丢几百块钱安慰两下就走了,人家不可能陪在这里,各有各的事。若是隗三户死了,那就像广州的一只苍蝇死了,说不定骨灰还弄不到老家去。等他病好后,他就决定再怎么着也要回老家去养老,在外太孤单。老婆也同意,有个什么事,离家几千里,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回家一定要起个房子,现在有钱人都这样,古代在外做官的,官做得多大也是这样,咱家乡的杨尚书,官做到三品了,死了还是葬回来,老房子做得跟宫殿似的。但问题是看能不能把地要回来,特别是要块宅基地回来。
想回来踏青扫墓也是因为这场病,想是不是父母的在天之灵在抱怨我,这么多年都不回去看看,我没有给他们培个坟,烧个香,磕个头,如此不孝,他们就不保佑我了。说到此事,特别在这清明之前,几个广东的生意朋友都急急地准备打道回府扫墓。广东人说每年不管怎样,清明都得回乡扫墓。亲自回去,这个是基本要求。隗三户知道广东人迷信,做生意的特别迷信。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怀念祖先的一种情感。每年自己虽说没回乡,也会买一堆数亿元的冥钞烧了,念几句父母的名字要他们来取钱。鬼是随叫随到的,比坐火箭还快。但今年这么糊弄肯定不行了,隗三户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暗示,必须亲自回去一趟。他这就筹备了买个二手车,假模假样、人模狗样地“衣锦还乡”。病后他问过老婆,两个孩子在自己昏迷后来看过他没有。老婆说伢读书,哪来时间看他。隗三户闻此感觉天就黑了,比死还难受。假如我没醒过来,两个孩子不就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就走了,寒心呀寒心呀。如今的孩子与父母感情淡漠,以后老了找什么依靠,又不是国家的人靠国家。决定,再怎么也要回老家养老。虽说没了至亲,还有一些隔代的亲戚吧,还有一些乡亲,一些儿时的玩伴,一些小学中学的同学吧。有个小灾小病不缺人来探望,嘘寒问暖,走走串串。就是死了,还能埋在故土上,与父母在一起。人就是这么不争气,不是你不想这个,是那会儿迫使你想这个。人总是要死的,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非洲难民,怎么阻挡都没用啊。
眼看就快要到镇上了,突然间发现路中间有一头牛!七想八想的,差一点没撞上。以为是看走了眼,定眼一看是真的,还有一个牵牛人。深更半夜的,不让牛归家?牵牛人牵着牛,车灯扫着了那人那牛。他猛踩刹车,吓出一身汗,却突然见那个人甩开牛绳就跑,像兔子一样快,是横着往路边跑的,一下子就钻进了高高的茂密的油菜地里。
怪事呀,怕我?
一忽儿就明白了,牛是偷的,偷牛贼!像训练过百米冲刺。
那牛直挺挺地站在路上,一动不动,像个傻。隗三户停下车,打开车门,去看个究竟。牛是头水牛,当地也称白牛,红皮黑点,毛色金黄,蹄壳双角锃亮如乌金,四五岁的牙口,眼珠饱满浑圆,亮如宝石,特别是头呈黄色,这可是牛中之王啊。可也这么老实,像咱这儿的农民一样。
怎么办呢,这牛?不能走了把牛丢在这儿,偷牛贼肯定藏在田里,只等你走,他还会牵去。牛定是偷的无疑了,牛不跟那人走,就说明不是那人的牛。心想丢牛的人家还在睡梦里,醒来可要急死了。如今牛可是庄稼人的宝贝,又到了犁耙水响的时候。等在这儿,等天亮寻牛人来?不行,才凌晨一点多钟,且饥肠辘辘,又困又乏。这儿也应是咱武家渊的地界了,离镇上也就两里地的样子,必须到镇上寻个旅店过夜,还要弄点吃的填饱肚子,洗个热水澡。这牛咋办呢?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车带着牛走。牛是认生的东西,不能在前头走,若是主人可以。拖着牛走?试试。一只手开车,一只手在外牵绳。头伸出对着后头的牛大喊:“嘘——”,牛就走了;“喔——”,牛就站住了。不愧为本地牛,还听得懂我用荆州的方言指挥。当农民的感觉就回来了,人也兴奋了,睡意全消。慢慢开,慢慢吆喝,就像条虫在公路上爬动。又不能大踩油门,牛总会犯迷糊,不听话,鼻桊儿都快拉翻了,牛桊是黑色的。这么一手牛一手车,要功夫啊,一身汗又下来了。就下车去劝说:“你总得回家吧,老牛啊,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话是网上的一句笑语,很流行的,就这么喊了,“嘘——”,牛又走了。又大步流星走到了前头,把车拽得一哽一哽的。“喔——喔”!这样拉拉扯扯,走走停停,走到镇上,已是三点多钟。累虚脱啦!
敲开一家临街的宾馆,将车和牛开拉进院子,长着一张搓板脸的老板娘眼瞪得像两颗鳖蛋,说:“这、这是怎么回事?”隗三户叫她天亮后报警。问她要吃的,结果吃了“来一桶”,就是来一盅,台湾人很夸张。汤汤水水唤醒了饥饿的肚子,肚子喊声更大,轰轰隆隆的,只好就寝。
梦中混乱不堪,还在路上厮杀。突然被一阵广播声惊醒,是镇广播站的人在喊话:“哪个村民家昨晚丢失了一头水牛,黑色的鼻环,请到镇幸福宾馆来认领……哪个村民家昨晚丢失了一头水牛,黑色的鼻环,请到镇幸福宾馆来认领……”反反复复。老广播啊,还在啊!播音的也还是那个王站长,声音一点都没变。可隗三户太困,又睡了过去。梦里又是激流险滩,天上地下。后来一阵惊天动地的拍门声,差点儿心肌梗塞,一个骨碌滚下床来,搓板女人已将房门捅开,一个驴脸男人就进来了。
“大……大雨书记兄!”差点没破口而出喊成诨名大驴。就是本村的村主任武大雨,还是他小学的同学哩。大驴的脸很有特色,脸长,小时总是受人欺负,都叫他大驴,人还很犟,后来贩猪娃。犟的程度可用“”二字来形容。还是小孩时,与父亲犟了,站在冰坑里,整整一天,冻得硬邦邦的,用牛都拖不上来,后来十几个人用锹才把他挖出来。他爹准备用开水把他烫死的,嗬,竟把他烫活了。
“三户啊隗老板,怎么感谢你呀!”
“感谢我?”
“咱村的牛啊,又回来了!牛跟你有缘,雷锋啊!你咋晓得是咱村的牛呢?”
我知道个鸡鸡,撞上的。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跟大驴打了照面,得赶快抓住机会,出手。正当大驴要退出去的时候,隗三户先把在广州买的两条硬中华塞给了他,后续还有的,只因人没醒过神来。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清明回来啦。独独我们村没丢过牛,全镇丢得厉害,咱们村一直保持治安先进,综合治理社会治安也是一票否决制,你可帮了我啊,隗总。”
不是应付,好像是真的,真心话。了解他的人才知道,大驴有虚荣心,也是。万事都想争个。听老乡说村委会的会议室挂满了各种奖励,从中央,到省市县镇,一堆一堆的。要不咋叫省劳模、市人大代表呢?不容易,一个猪贩子。
到了楼下,牵着牛爱不释手的老农鸡啄米一样地谢恩。大驴说:“谢隗老板。”又给隗三户说,“武爱秀的爹哩。”
是同学的爹,这就不用谢了。我哪是来要谢的呀,我撞着了,瞎猫碰死老鼠,人家扔下的。
“哦,想起来了,三三,三三呀,小时候调皮,又聪明,咱们家的黄瓜掉进塘子里去过……”揭短啦。可是隗三户的心一震,老人叫上我的乳名儿了!
我是三三,我就是三三。这乳名儿有多少年没人喊啦,我都忘记了,忘干净了,我还有乳名儿?心里想哭。一个乳名儿,把自己和家乡紧紧联系起来了。
“武伯,武伯,不用谢,没什么。”人一激动就想流泪,话就没了。只想着自己的。在外谋生,红尘暴土,凶险莫测,你来我往,就跟斗兽似的,甭说乳名儿,就是大名也忘了,只是条在滚滚车流中寻路走的狗而已。给武伯、大驴递烟,亲切,家乡,家乡人,故土上。那两条烟在大驴腋下,用黑塑料袋卷好了的,隗三户就说中午请大伙吃饭。
“早都没过。”大驴说。(过早:吃早餐)
“我请你们喝早酒去。”武伯拉着书记和隗三户就走,膀子都要拉脱臼了。这老人的一把劲!
荆州人有喝早酒的习惯,早晨眼睛一睁,一碗面、二两酒就下了肚。或是一块锅盔、一瓶啤酒,对着瓶子就吹了。打个嗝,吐着酒气,干活儿去。
这一碗面是要吃的,这二两酒是得喝的。牛肉面,辣兮兮,二两“监利荞酒”,绿莹莹的,苦中带甜,好喝。大驴不喝,说有糖尿病。他脸皮浮肿,神情黯然,嘴唇青乌,是有病在身。前两年大驴去广州时隗三户就知道,但不知多严重。其实隗三户也是不能喝酒的,大病后就戒了,但今天在老家他得喝点。在老家,生命就不重要了,感情重要。
“我呢,三高,血糖、血脂、血压,全高了,”大驴拿出一个很细的针管来,“每天自己打一针。有一次在市里开会,在洗手间打针,被抓起来了,还以为我在注射毒品哩,嘿嘿嘿。喝坏了嘛,作死地喝,不喝如今你能办事?上面全是大老爷们,咱们乡下小官有个什么本事?什么资源?就是个拼酒量的事。这几天,搞我的猪场沼气大项目天天喝得半死,不喝人家凭什么把钱给你?跟你无亲无故的。”
“是呀是呀,你的猪场发展得蛮大了吗?”
“马虎相,万把头的存栏。母猪加大猪加仔猪加保育猪一起。哪能跟你们在外头比?你们是做大生意的,咱是小农经济咧。”
大驴话中有话。或者只是他多心吧。话中就是两年前去广州,我小气了呗,捐村里少了呗。可当着武伯的面又不好拿出来——他是准备了的,再补捐一点。这肯定要给见面礼,再说有大事要求他。是捐给村里还是给他本人?模糊奉上,但这要一对一,当着别的人就不好“捐”了。
“我有事要找你大雨书记兄,什么时候去看看嫂子。”隗三户说。
“不看了不用看,这些天全家都在猪场忙。今年春天荆州大猪瘟咧,别的猪场死了不少猪,我们要严防死守。去年我就死了一千多头……”大驴轻松地说。在炫耀哩。
二
“三三咧……三三哦……三三回了!……”
进了村里,一路走去,一路亲切的乳名。小伢儿们是不认识了,小伢们可以忽略不计。村里的老人,老人是村庄的历史,是村庄的记忆。泪流满面。大难不死,人就爱流泪了。多美的村庄,武家渊,我是三三,对对,我就是三三,一个在这里有小时记忆的人,隗结巴的儿子,喜欢钓鱼,言语不多,高考不中,有许多烂事儿,老辈子的人还记得。看啊,渊里的路也修好了,田野圹埌无垠,所有的植物都像潮水一样暴涨。在这个季节,阳光正艳,天空很蓝,油菜花是金黄色的浮金,铺在广大的天空之下,仿佛大地就是一场香喷喷、金灿灿的盛筵。而小麦已经有一尺多高了,大麦开始秀穗。细看油菜也开始自下结荚。田野纤尘绝无,烟岚如缕,黄的耀眼,绿的葱茏,整个田野色彩饱满润泽,青春逼人。鹧鸪一声一声,叫声含着水雾。路边的野芹菜蓊蓊翠翠,半夏、天门冬、麦门冬、绿蒿也同开满红花、紫花的野苜蓿一起茂盛着。水中的蒲草绿芒初现。榆树从疙瘩里抽出枝条,在阳光下抖擞着透明的叶片。高压铁塔牵着雄壮的手,跃向大地的尽头。坟地里,亲人的祭奠五彩缤纷,生生死死多热闹啊!在家乡,真是热闹非凡生机盎然哩。
自己没家了,去了表哥家。表哥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因为年龄和椎间盘突出总算待在家里了。家里就是两老。女儿在城里跟女婿一起做事。表哥也姓隗,单家独户的,从来不引人注意,住在一个角落里。武在这里才是大姓。表哥要他一定住在他们家里。那是个陈旧的楼房。表哥说他女儿女婿要他们去城里住的,但家里还有一点田,想种几年再说。表哥说逢年过节都给小爷、小婶、娘上了坟的,是指隗三户的父母。隗三户谢了表哥,要了把锹就要去父母坟上。表哥坚持要陪他去,他谢绝了,表示他是去给父母赔罪去的,只能一个人去,也是尽个孝道。
从镇上买回香烛、冥币、清明吊子和一些随祭的物品,一大包,拿好就出门了。空气中传来一股隐隐的畜便的臭味,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家乡的气味,让他有些走神。气味来自“大雨生态农庄”,就是书记颇有规模的养猪场。这个养猪场非常有名了,至少在荆州地界名声响亮。猪场够大了,少说有两三百亩,囊括了隗三户曾经的责任田和宅基地共十亩五分地。在荆州这地儿上,一亩基本是按一千平方米计算的,少八百平方米。这也是的算法。过去的荒洲苇滩钉螺窝,一望无际,了无人烟,祖先们开垦肯定以大计算了。算个整数,不搞小眉小眼鸡肠尺寸,敢来这儿开荒住下的,必心怀阔朗,大气磅礴,舍得一身剐,把命赌上算事。往上溯,这地界紧靠湖南,从湖南来“杀青皮”(就是开荒械斗争场子)的老多了,虽去了七八代,还是一口湖南腔,有时候假模假样讲点荆州话,但回了家必吃重辣椒、唱花鼓戏。话又说回来,湖南湖北是一家,都吃辣,打架都能下狠手。你骂他,他骂你。一样地不讲道理,一样地义气为重,一样地说“一炮个”(十个)。两年前,在广东就听大驴说他的猪场存栏就有三四千头了。村里修路他带头捐了二十万。现在这个阵势,这么大的地盘,一排排的猪舍,存栏数肯定一万头不止。还把我隗三户的胞衣屋场给弄成了猪圈!胞衣屋场就是咱埋胞衣的门口,哪儿生,哪儿埋,以便让魂儿锁在这里,不要丢了,记得这里。这是咱荆州的风俗。
父母的坟也不远。父母呀,你们在地下可没保佑我,差一点让我把命丢了,丢在广东了。丢下锹就使劲磕头,恶狠狠地磕,有点怪罪。你们的儿子这么辛苦是为谁呢?还不是想让隗家爬起来,让人称羡,给隗家挣个面子!……爹呀娘呀,你们以后可留只眼照拂咱一家了,宝琴、隗龙和隗凤,一家四口!给你们带东西来了,带钱来了,带烟带酒来了,带吃的喝的来了……一股脑儿地烧,烧得大火冲天,烧得纸灰乱飞。又培坟。坟是表哥培了,十多年来没有坍塌,坟前还有破碗破盘破杯子,这表明表哥是上了饭的。这儿给死人敬了饭菜,是得敲碎碗盘于坟前的,表示亡者受用了。
又是火烤又是挖土,身上就热了,头上有了汗,就坐下来吹风。风是小南风,懒洋洋的,猪粪的味道吹走了,青草泥土的气息来了。父母双亲的坟在一个高岗上,视野开阔,颇有气象。野芹菜长得茂翠可人,娇柔万端,无人采摘。若是弄到城里,那可就不得了,就是金价。一株野樱桃斜长在土坎边,开着粉色的花,异常打眼,仿佛是被遗弃的美人。一些蒲公英的黄花开得明媚动人,坦荡恣肆,两只蜜蜂突然从那里飞走了,像受到了惊吓。高岗下,一片荠菜花开的田野,白白的,有如小雪。它们在风中一浪一浪地被卷走,又一浪一浪地回来。鬼打伞(漆泽)是墓地的景色,它们为亡魂撑着郁郁葱葱的小绿伞。蓝色的婆婆丁也在这儿凑着热闹。草下的小泥堆是蚯蚓拱出的,神秘有趣。
唔,确实好,这儿,这个地方。儿时的地方,死在这里,活在这里实在好。当初出去是因为太穷,种田负担太重,现在想回是外面太冷。这个清明的热力,这个田野,真好。如果死了,就陪伴在父母身边。城里想想都可怕,一点点骨灰,挤在密密麻麻的公墓里,死了都不得安逸,腿脚都伸展不开。死就是休息嘛,长久的、永远的休息,可不能怠慢自己,委屈自己。好的位置是家乡,就是这里。这个地方,实实在在的,就是这儿,野樱桃、野芹菜、荠菜、婆婆丁、风、蓝天白云。大口舒气的地方,魂在这里,离胞衣屋场一步之遥的地方。人还能到哪儿去?人只能到这里,在这个地方,在这里生生死死打转儿。生是这儿的人,死是这儿的鬼,谁又不是这样呢?谁又能逃得过这样的结局?
“三三哩,三三喔……”一个老者,来走走的。手上抓着一把草,来找草药的,或是什么也不找,揪草玩儿。他还说:“前天还梦见你爹跟我钓鱼,只怕是他喊我去给他打伴儿哩……”“呵呵,伯伯不会的,您啷嘎这么精扎(精神),活一百岁。”“那成精啦,儿孙们讨厌死的……三三回来踏青好孝顺,难得哩……”声音和人魂一样飘走了。他死了以后,我们都死了以后,他这么喊我,该多好,该多暖和。这个地方我定下了,我不会反悔的!
心里有些急切,就是怎么向大驴讲了,要回田,要个宅基地。事情还扯得很远,怎么向他赔罪,怎么补些上次的捐款……两年前,人没有病的时候可能有些冷酷,大驴为村里修路到广东去找老乡化缘。一是,隗三户当时确是资金周转不灵,再者也没赚到钱,有时候跟人瞎吹的,喝了二两臊尿,就是百万千万富翁了,老子马上去买宝马的,家里三套房子。那是瞎说的,反正吹牛不上税,要人跟你一介农民做生意的,“广广”(广东人)有钱的人又多,当然在家乡人面前也不应输了形象。重要的是,自己认为这辈子也不想回去了,又没房子又没了田,那是个什么家乡呢?过去你爹当大队书记的时候还不是把我爹整得半死,诬陷我爹投了你家的毒?那时候你这大姓是怎么欺负我们小姓的,我们隗姓几户人家在武家渊过的是人的日子?把我们不当人看哩。心里一想就不舒服,就只捐了两千。也有捐五千的,那是武姓人,多数是捐一万两万,三五万也有。可人家说你隗三户做建材、做防水工程做得大呀,你拿得出手?大驴肯定有想法,当时是怎么想的?由他去,老子又不受你管了,就一个身份证在你那儿,是派出所管的,再说你大驴书记搞得一辈子?总要下的。可现在,你要来求他了,那不正撞在他枪口上?唉!
地是咋没的呢?自己弄没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