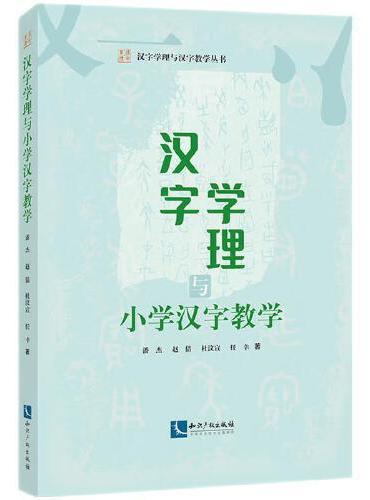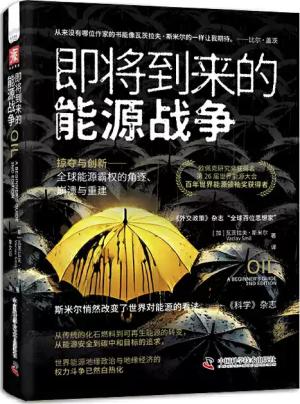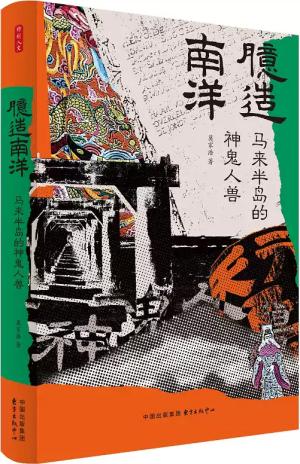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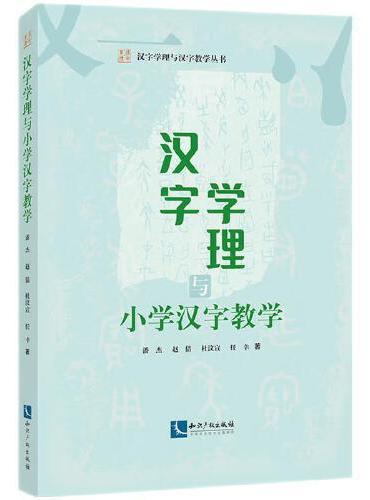
《
汉字学理与小学汉字教学
》
售價:HK$
8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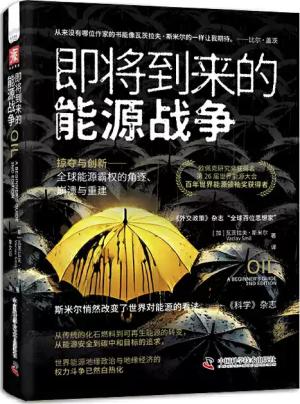
《
即将到来的能源战争
》
售價:HK$
8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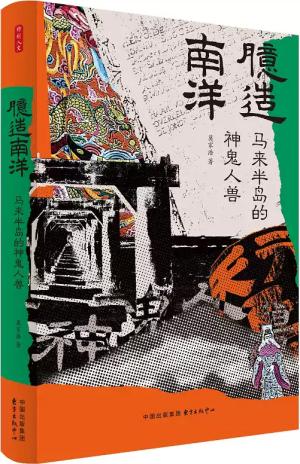
《
时刻人文·臆造南洋:马来半岛的神鬼人兽
》
售價:HK$
65.0

《
心智、现代性与疯癫:文化对人类经验的影响
》
售價:HK$
188.2

《
周秦之变的社会政治起源:从天子诸侯制国家到君主官僚制国家(历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论丛)
》
售價:HK$
188.2

《
时刻人文·信用的承诺与风险:一个被遗忘的犹太金融传说与欧洲商业社会的形成
》
售價:HK$
103.0

《
同与不同:50个中国孤独症孩子的故事
》
售價:HK$
66.1

《
开宝九年
》
售價:HK$
54.9
|
| 內容簡介: |
《作品》
代表林文月后期散文的重大转变,很多非常著名的散文皆出于此 ,包括《从温州街到温州街》《父亲》《我的舅舅》《风之花》《红大衣》《礼拜五会》等,这些篇章回味了过往人生的各个阶段,通过与无限的人交往沟通,共享世事人生的欢乐与伤悲。
从林文月的作品中,感受到文字魅力的深刻,文学启示的辽阔。跟随她的作品,感受精神生活的高贵和充沛。实实在在的没有文学,人生多寂寞。
|
| 關於作者: |
林文月
中国台湾人。
林文月精通中、日两国语言文字,身兼文学创作者、学者、译者三种身份。
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捷克查尔斯大学客座教授,现为台湾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专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教学之余,从事文学创作及翻译。主要著作有《交谈》《作品》《拟古》《遥远》等,译注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伊势物语》等。
曾获时报文学奖、台湾文艺奖、台北文学奖、中兴文艺奖等文学奖项。
|
| 目錄:
|
[目录]
上 卷
人生不乐复何如
礼拜五会
风之花
尼可与罗杰
作 品
白 夜
我译《枕草子》
你的心情
红大衣
迷 园
父 亲
我的舅舅
台先生写字
台先生的肖像
温州街到温州街
坦荡宽厚的心
寂寞的背影
爱台湾的方法
不见瑠公圳
没有文学,人生多寂寞
下 卷
关于《十六岁的日记》
十六岁的日记
重读《水月》旧译
水 月
曾野绫子印象
一张坏了的椅子
至 福
|
| 內容試閱:
|
[内文试读]
重读的心情
灯下展读十五年前的《作品》,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这些文字既熟悉,又有些陌生。有些段落,甚至完全在记忆之外;然而读着读着,又仿佛连贯起来了。于是,那些遥远的许多事情,便又都回到眼前来。
读自己的旧文章,好像是翻看昔日相簿,心中明明是有一点感伤,却也不自禁地产生一丝温暖的感觉。
十五年之前出版这本书时,正是我从多年教学生涯退休之时。文章内容颇涉及我丧失长辈的悲恸;而今再次校阅新版之际,竟连当时与我一同深浸悲恸的亲人友侪,又有几人先后走了。人生的变化,何其重大无奈!
不过,于无奈的大变化中,有些事情似乎是历久不变的。书中有一篇《爱台湾的方法》,是我给平素来往并不十分密切、却衷心敬佩的朋友殷允芃的一封公开信,祝贺她创办的《天下杂志》十年有成。写那篇文章时,“爱台湾”一词,尚未如今天流行响亮。我所以选定那样的题目,是对于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关怀和爱护这一片土地的朋友,表达真诚的敬意。文中有一段文字:
许多年过去了,我的想法仍未改变。这个社会有如一个庞大的错综复杂的机器,要有马达、帮浦、螺丝钉等等大大小小的机件,缺一不可,而且每一部门都得保持正常运作,片刻松动脱落不得。我佩服敬业的人,尤其是默默敬业不懈怠的人。
赶巧,昨天我在南部的一所大学演讲。讲完后,有些听众拿书要求我签名。其中一位,于我签完名后,递一张便条给我。在旅邸的灯下,我读了那一张或许是临时匆匆写给我的便条:
一九八五年下半年,或一九八六年上半年的一个周六午后,当年高三的我,到台中图书馆听您演讲。题目已不复记忆,提问题时间,我举手问:“对于一个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您有何期许?”您说:“很难直接回答。”在台大,您教过许多优秀的学生,然而,对他们,或对我,您想说:“若你是一颗螺丝钉,就努力做好螺丝钉的本分。”说完,怕我不懂,您还问我:“了解吗?”
当年的我,确实无法完全体会。
二十年过去,我念书、工作、教书。生活中总是有语文、翻译与教学。我逐渐比较了解您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心情。
人近中年,一直还在努力的不就是“做好一颗螺丝钉吗?”您二十年前的话,我懂了!
这里是我的母校,很高兴能在此见您。也记下一段二十年的缘分。
读完那张便条,我心头一紧,眼眶发热,虽然我已不记得二十年前在台中所讲的题目和内容,仓促间竟也没有看清楚递纸条的人。
二十年前,我曾对一位青年说过那样的话吗?二十年之后人近中年的他,自己体会了那些话,而且逐渐了解我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心情。容我把他的话记下来,或许再过二十年,他也将不复记忆自己在一张便条上写过这样的文字。
而我曾经在一个场合写过几句话:
我用文字记下生活,
事过境迁,重读那些文字,
惊觉如果没有文字,我的生活几乎是空白的。
二〇〇八年春暮
人生不乐复何如
抗战胜利翌年,我随着家人乘船回到完全陌生的故乡。船在大海中摇荡,我的心波也荡漾。脑中不断设想、揣测着,究竟台湾是怎样的地方?台湾的风俗民情又如何?而船在基隆港靠岸时,眼前所展现的,竟是一副“异国”情调。在上海码头候船时,二月的江南,冷风飒飒;但二月底的基隆港口,蓝天碧海、阳光艳丽,码头上还有人在叫卖着“枝仔冰”。码头上面的人所讲的台湾话,也是我们听不懂的乡音。
我出生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启蒙教育是在日本学校接受的,所以我的母语是日本话,居家外出时则讲上海话。这样的生活方式维持到小学五年级。不过,事实上,五年级只读了一个学期即因战争结束,日本人遣散返归日本,学校停课,我也因而失学半年多。回到台北居住停妥,已是春末。那一年的初中招生仍沿日本学制,在春季举行,台北市的小学仍保有六年级的,就近只余老松国小一所学校。于是,我每天要走四十分钟的路程,从东门到万华上学。路遥并非困难,困难的是语言问题。当时政府为了尽速推行国语运动,禁止说日语,也禁止日文书籍。我们的老师用台语讲解生硬的国语,而这两种语言对我都是完全陌生的。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如何克服两种陌生的语言而逐渐习得国语了,只记得下课后和同学们交谈总是偷偷用日本话。
经过一年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如何使用国语,但写文章难免还是要先用日文思考,再转译成中文。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当时的台湾知识界。对于像我一般年少的人而言,阻碍表达的因素也许尚浅,但是对于中年以上的人,则其困难可想而知。不过,勤勉努力总是可以解决问题。在中学的六年中,我的中文表达能力逐渐赶上水准。我开始代表校际编制壁报,也参与若干次作文比赛而获奖,一方面也偶尔在报刊的青少年作品版上投稿。对于文学与美术的兴趣,大概是与生俱来的性向,语文的中途转换,一度令我对于文学感到沮丧,不过,在相当自在的六年中学生活中,我似乎又稍稍恢复了兴趣与信心。
然而,徘徊在文学与美术的双样兴趣之间,却使我在投考大学时倍添困扰。我们那个时代尚未建立联考制度,我同时考取了台大中文系与师范学院艺术系。长辈与师长都力劝我选择中文系,而我的个性也一向比较顺和,遂舍美术而就文学。这也许就决定了我这一生的命运:搁置绘画彩笔而捡取文学素笔。
在我读中文系及其后又顺利考入中文研究所的一九四十年代时期,正是台湾政府大力查禁中国一九三〇年代文艺书籍以及俄国若干作家作品之时,而系所课程也未敢开设现代文学的课程(此与授课取材有关,也与当时大学教育较保守之风气有关),故而我们终日所接触的科目都是古籍的经史子集。但我个人在上海失学的半年期间,曾经于无聊之余大量阅读日译本的世界名著;而在中学六年之中,虽然已有“反共抗俄”的口号,学校图书馆中倒是还可以借到高尔基的书,以及鲁迅、周作人的一部分著作;在大学研究所的书柜底层,也被我发现一整套的《小说月报》。于古典研读之余,这些现代文学作品及世界文学名著译本的阅读,一方面调剂了我比较单调的学生时代生活,同时也引发了我个人的写作兴趣。
于今回想起来,在学校时代对我写作影响的恐怕是高中时的导师蔡梦周先生,和大学时的系主任台静农先生。蔡老师是一位只身在台的退役军人。他的宿舍就在我们的教室旁边一间小屋内。蔡老师的生活十分单纯,除了教几班高中国文外,便是接受我们随时不定期的课后访问。我至今无法知悉蔡老师的教育背景,只知道他有很好的国学基础,以及极大的爱心与包容的器度。他当时的年纪大约已在六十岁以上,对待我们有如父亲之于女儿,甚或祖父之于孙女儿。他要求我们背诵古文,同时也仔细批改我们的作文,要求我们写作纯正的中文,而痛恨西化的文句。我至今犹记得蔡老师告诉我们的话:“中国人不说‘人们’。‘人’就是‘人’,包括个人,也包括许多人。什么‘我们’‘他们’‘人们’的,狗屁!”从此“狗屁”竟成了蔡老师的绰号。我们背地里那么喊他,其实是充满了爱与敬意的。
知道教授我们中国文学史与《楚辞》的台先生青年时期曾经是热血澎湃的小说家,是经由《小说月报》的阅读。有时我也在课外把自己写作的散文和小说请他过目。台先生认为我的生活环境太过单纯,比较适宜于散文写作,而我年少时候喜欢炫耀华藻丽词的文风,也颇受到台先生的规劝: “文章还是要涩一点的好。”什么是涩的美呢?直到我读唐宋古文、明代竟陵之文,始知其理。而台先生晚年的散文,则更是苍劲之作的典范。台先生又鼓励我善加运用我的日文根基,总是勉励我多从事翻译方面的写作。
大学时期,我的同班同学郑清茂来自贫困的嘉义农家,当时东方出版社的社长游弥坚先生正计划出版两大系列的少年读物——世界名人传记,及世界名著。那些书都是由日本的专家改写成为适合少年阅读的笔调。游先生嘱清茂逐本翻译,以稿费补贴他的学杂费用。由于内容十分庞大,清茂便邀我参与其工作。我利用课余之暇,翻译了其中一部分作品。放置多年的日文,遂与我所读的中文结合。而由浅入深的那些经验,实在是我日后译注日本古典文学巨著《源氏物语》 《枕草子》等的重要奠基训练。
在台湾大学中文系读书的七年,大概是我过去生活中愉快的一段时光。当时的台湾,虽然有许多政治上的禁忌,个人所能享有的自由也较有限,但整个的社会习尚朴实真诚。校园里的人口少,人际关系则比较单纯;尤其中文系的师生之间,有一种大家庭似的温馨气氛。我们的师长皓首穷经,就是给我们的身教典范。由于我逐渐看清自己将步入学术研究之途,所以在我二十岁到三十岁那一段求学与初执教鞭的日子里,几乎无暇他顾,虽偶尔也写散文及若干篇尝试性质的小说,刊载于校刊或其他报刊上,但是都已散佚无踪,因而早期留下的作品,全部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当时外文系夏济安先生主持的《文学杂志》,是一本严肃有活力而朴素的刊物。当今卓然成家的小说作者,许多是当年外文系的学生,《文学杂志》提供了他们创作发表的佳园;至于我们中文系的师生,则亦以古典文学的赏析论著参与其间,使那一本杂志成为兼容中外、并蓄古今的充实的读物。由于我也陆续在《文学杂志》发表过不少篇论文,后来合编成中国古典文学论著二册时,其中一册竟在封面上挂着我的名字。当时我年纪尚未及三十岁,却因此而被人误以为是一个年长的学者。
踏出学生生涯,又步上教坛,我的生活始终没有离开过校园。然而教书、阅卷、写论文,复又结婚、生育子女,使我远离创作几达十年之久。直到我三十岁的后期,获得“国科会”资助,只身赴日本京都研修中日比较文学一年,才在陡然失去家人环绕的寂寞之下,于研究的正业之外,重拾起创作之笔。我非常认真用心地记下日本的古都——京都的风物人文,以及独处异乡游学的心情。那些文章逐月在《纯文学杂志》发表,其后结辑成为游记《京都一年》。
在京都游学的那一年,或许对于我日后的写作生活具有颇重要的意义的吧。我不仅重新拾回放置多年的创作之笔,同时也因为那一整年中,似又回到年少时以日语为母语的生活,乃重温并且自修更高深的日文;而且,由于撰写中日比较文学论文之需要,我开始认真阅读平安时代的巨著《源氏物语》,虽然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机缘会让我在两年以后持续投注六年时间去译注那大部头的书,但冥冥之中,仿佛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牵引推动着,促令事情完成。人生真不可思议。我常常回想:倘若那一年没有接受赴日进修的机会,现在的我会是怎样呢?譬如说:我若将过去二十年来的时间精力专注投入在学术研究中,是否可能会因而有更丰硕的研究成果呢?
然而,我知道这样的设想是无意义的。如今的我,已经无法将论著、创作与翻译从生活中抽除了。身为大学中的教师,自不可怠慢授业解惑之责任,但授课之余,我自有使自己在三种不同的写作领域调适心情的方法;而且三种写作可以互相激荡,彼此刺激、鼓励执笔的我。
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需要深思及谨慎搜集资料。我每年大约只能写一两篇。间亦偶尔写一些与翻译相关的心得,却另成一范畴,未能收入论文集内。创作方面,我以散文为主,已出过五本单行本,另有两本传记。我虽然持续地写着,但因生活忙碌,写作方向又分散,故产量不能称为丰多。在写作的态度上,自问是比较保守而严肃的,我坚决不愿随波逐流而迷失自己。近年来,我从六朝文学的教学及研究中获得灵感,想出“拟古”的散文写作方式,即将自己的感思配合古人的模式表达出来,希望造成拟古而不泥于古的效果。这是半带着游戏性质(文学的发源,本来即有游戏说),又半带着自我挑战性质的。不过,我不否认,这样的文章写起来十分困难。所以目前分两途进行:“拟古”是一系列,有适当的题材内容及对象则写之;另外一系列仍依我个人的自由创作,但我总是慢慢在要求自我超越,而不愿意一再重复故我。
至于翻译,是我化过去的痛苦代价为今日资源的结果。大学时代,相当轻易地改写翻译过一些少年丛书,但其后已不再草率执笔。《源氏物语》的译注,花费了六年的时间;其后隔了六年,我才从事《枕草子》的译事,前后共计三年;又隔五年,自去年开始,我如今正译第三种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和泉式部日记》。此书在分量上远不及《源氏物语》,甚至亦不及《枕草子》,但全书以和歌的情书为中心,展现平安时代一段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我逐首用心翻译,大量加注,所用的精力并不减于前二书。有时我深夜苦思,译完一段古文或一首和歌,不免想到:如此辛勤地工作,究竟会有多少人来阅读这种古典的文学作品呢?然而,随即又想回来,只要有一位认真的读者,一切都是值得的了。
提笔写作,无论是学术论著、散文创作,或文学翻译,本来就是相当寂寞之事,但我乐此不疲已有年。近则又于《联合文学》逐月刊载《和泉式部日记》译文之际,每月自己绘制插图以为内容说明之需要。我在延续了这许多年以后,又拿起画笔尝试自习,仿佛年轻时代的另一个兴趣又于此捡回,绘画时候的执着与喜悦,有时更超过文字斟酌的成就感,遂不自觉地欣欣然自陶。人生不乐复何如!
原载一九九二·八月《幼狮文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