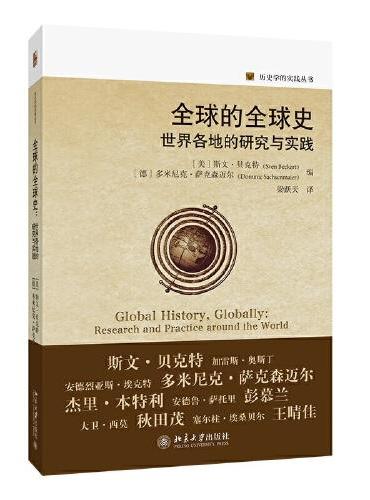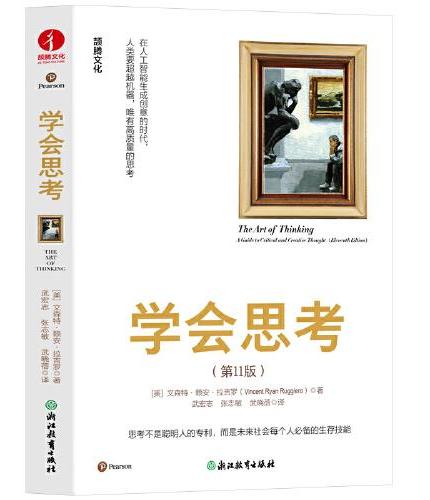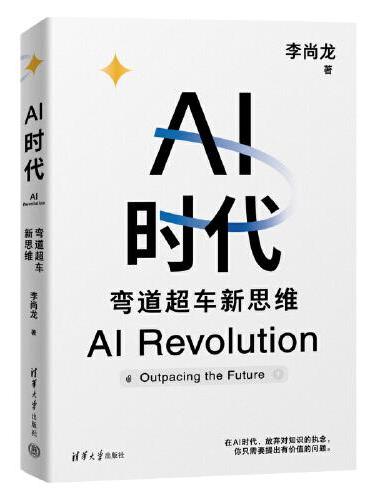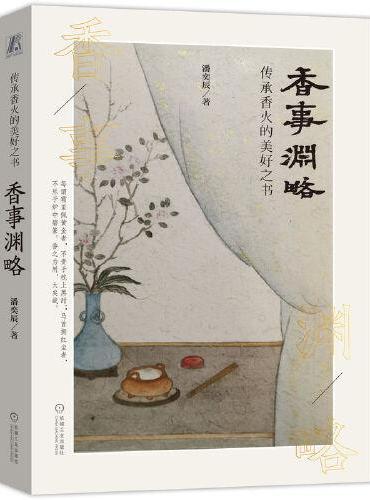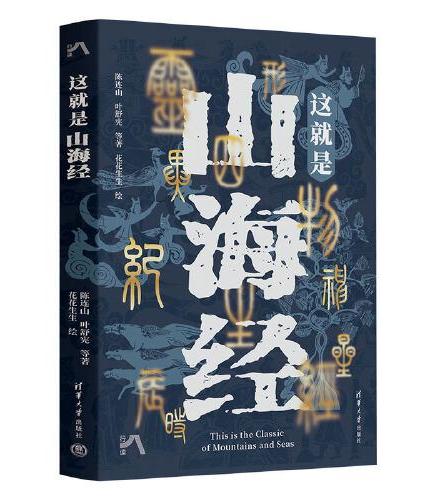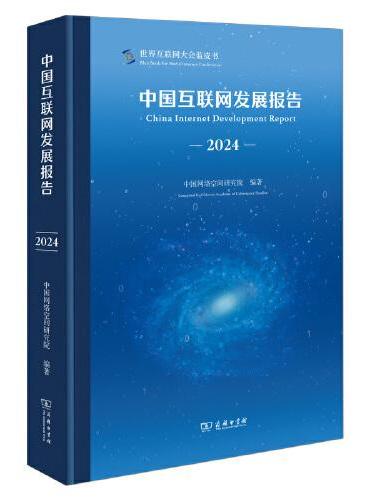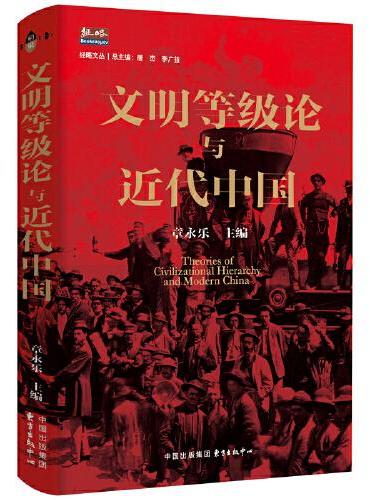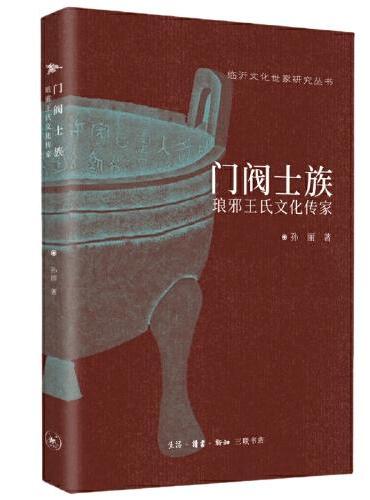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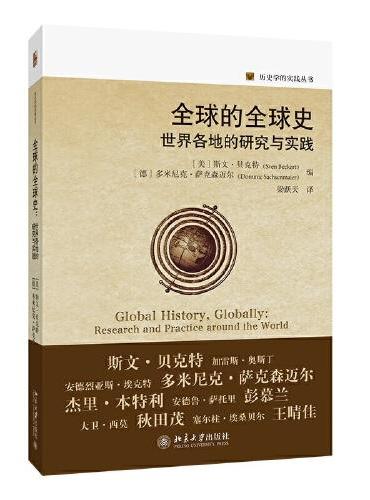
《
全球的全球史:世界各地的研究与实践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
售價:HK$
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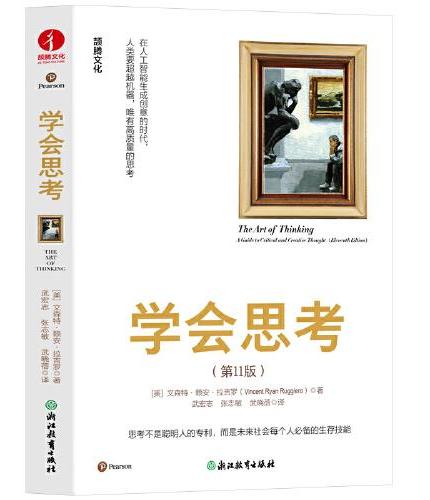
《
学会思考 批判性思维 思辨与立场 学会提问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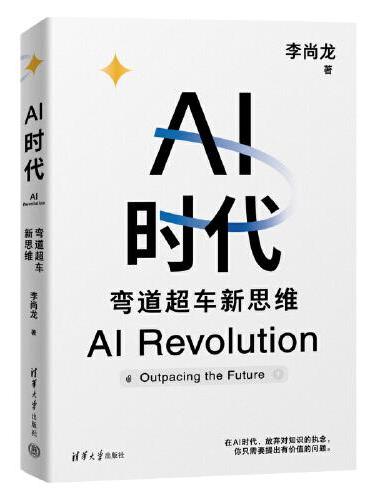
《
AI时代:弯道超车新思维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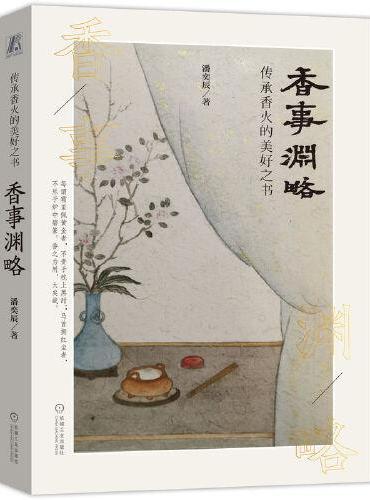
《
香事渊略
》
售價:HK$
1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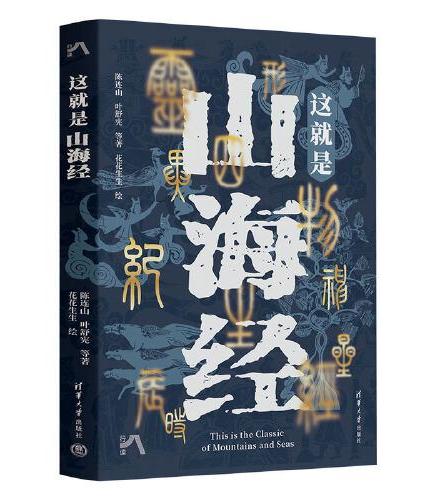
《
这就是山海经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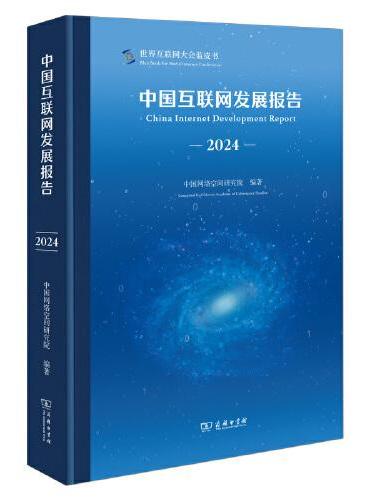
《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4)
》
售價:HK$
2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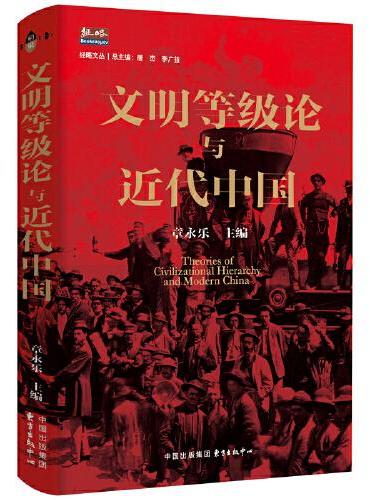
《
文明等级论与近代中国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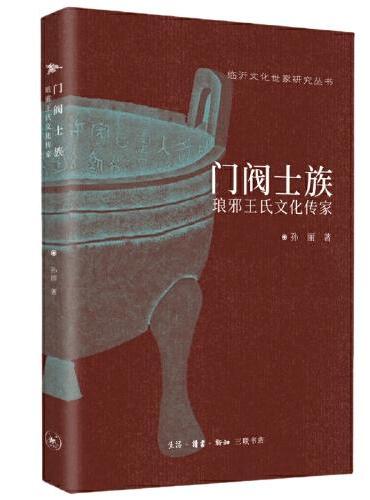
《
门阀士族:琅邪王氏文化传家
》
售價:HK$
86.9
|
| 編輯推薦: |
梁文道《开卷八分钟》盛赞的美食作家,称赞其温柔斯文尔雅。蔡澜、欧阳应霁、庄祖宜联袂推荐。
被公认为台湾*美食散文作家,曾获第二十届吴鲁芹散文奖、梁实秋散文奖、开卷好书奖、《联合报》读书人奖。
作品长期领衔各大吃货书单,其风格更深刻影响陈晓卿创作《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读者称美食类写作,除了蔡澜,我只服蔡珠儿。
用味觉书写文化的经典之作,把吃转化为清凉散文。字里行间尽是优雅与从容、诙谐与睿智。难得有人把做菜写得这么美,把尘世写得这么动人。 ?
邀请ONE一个当红插画师黄雷蕾手绘食物插画,清新温暖,引人垂涎。双封面雅致装帧,进口日本广告纸,仿古设计,使美食色香溢于纸上。
|
| 內容簡介: |
中国文化以饮食见长,山珍海错田蔬河鲜,煎炒煮炸蒸溜熬炝,食材与烹术洋洋大观,饮馔品目更是精细考究。
应季蔬果的时令感、月饼盒中的人情世故、满汉全席的华贵排场、鲍鱼宴的富丽张扬、大闸蟹的美味神话、炒饭的身世之谜、台式烧肉粽里的乡土情结
作者细数厨中食材的前世今生,以锅铲为笔墨,挥洒翻炒出饮食文化的幽微滋味,汇成这部饕餮之书,以飨读者。
|
| 關於作者: |
蔡珠儿
台湾南投人,先后就读于中国台湾大学中文系、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曾任台湾《中国时报》记者。著有散文集《彩食记》(原名《红焖厨娘》)《饕餮书》《种地书》《花丛腹语》《南方绛雪》《云吞城市》等,曾获第二十届吴鲁芹散文奖、梁实秋散文奖、开卷好书奖、《联合报》读书人奖。
|
| 目錄:
|
推荐序 香格里拉厨房
自 序 怪兽、老饕和馋猫
辑一 食物之春秋代序
粽子、傻子与魔镜
二十四张秘密菜单
忧郁的老火汤
切一片月亮尝尝
辑二 食物之身世查考
满汉全席清宫秀
鲍鱼的溏心术
大闸蟹的美味神话
炒饭的身世之谜
辑三 食物之香港氛围
茶餐厅地痞学
打一场Party的硬仗
煞食与口腔
私房菜社会学
没有鸡吃的日子
辑四 食物之小道可观
我爱你,就像鲜肉需要盐
米酒、伏特加与二锅头
我们的饕餮时代
薯片的时空版图
外卖年菜,解放内人
蒜烤古典与油煎阳光
|
| 內容試閱:
|
自序
怪兽、老饕和馋猫
饕餮是一种古代怪兽,在生物图鉴和动物园里找不到,它和蛟龙、凤凰、麒麟一样,都是虚构的动物,只生存在文化里,但却活灵活现,不只有鲜明的图样形象,还繁殖出丰富的语意象征。
龙凤麒麟是祥瑞的吉兽,所以人中之龙凤毛麟角都是好的;而饕餮则是贪食的恶兽,望文生义,字形狰狞,饕餮之徒当然不是善类。至于老饕,看来虽比较亲切温和,但也不像是好东西。
然而喜欢吃喝、讲究饮食之人,通常被人叫作老饕或美食家,有时还被当成尊称。我因为写过几篇谈吃食的小文,被朋友误以为会吃懂行,不由分说就被扣下这两顶帽子,吃饭总要我选馆子和点菜,这个没问题,但是帽子就让我很不自在,立刻想摘下来。我那点粗浅皮毛,离老饕和美食家的境界固然还远得很;而基于疑心和偏见,我对这两个名词都没好感,总觉得字里行间暗藏着讥刺贬抑,就像广东人说的有骨。
在我的想象中,老饕带有贪意,好像人生无所用心,整天都在找好吃的,一副需索不止、贪得无厌的模样;而美食家则带有刁意,让我联想到精乖刁钻、东挑西拣,充满嫌恶和势利的嘴脸。天啊,我虽没出息,但也不想落得那般下场。
但如果不用这两个字,又该怎么说呢?好吃、爱吃、馋人以及粤语的为食等字眼,非但粗疏浮泛,而且也有贬义(通常下面紧接着懒做、鬼、猫等字眼。会吃、善吃、知味或者粤语的食家,情况稍好,但档次好像又太高了,不适用于像我这样只是对吃喝煮食有兴趣的普通人。
中国文化以饮食见长,山珍海错田蔬河鲜,煎炒煮炸蒸溜熬炝,食材与烹术洋洋大观,饮馔品目更是精细考究,因而发展出精密发达的专门语汇,唯独对饮食者和饮食态度绝少着笔,即便偶尔提及,总带有浓厚的训诫意味。
老饕这个称呼,据说源于苏轼的《老饕赋》,濡染了东坡先生的丰神隽采,老饕本来是美名,然而千载以来,此字仅限于文人的风雅闲事,内涵并未创新升级,经历岁月的风化磨损后,语义逐渐松动掏空,开始带有市井气和轻贬之意。都怪那个饕字太丑怪,然而汉字有数万个,一千多年来,为什么没有出现更理想的称呼?为什么我们一直用那只不存在的怪兽,来指称这么具体切身的饮食行为?
我想,可能因为饮食深受伦理道德的规管,而道德对吃喝是很严厉的。在中文里,喜欢吃喝,要不等于贪嘴而馋又等于懒,懒又等于混,要不就是专精成家但不能经世致用,只是闲趣而非正事,不是低抑就是高举,落差太大,欠缺中间的层次等级。
因此,一个喜好吃喝与厨事的普通人,很难在中文里找到适切的形容称呼,勉为其难,我通常说自己是个食物爱好者,但这也有语病,一来带洋骚味,二来好像有食皆爱,来者不拒,兜了一大圈,又跌回饕餮的怀抱。
相形之下,英文就好多了,一句foodie言简意赅,说来心安理得。Foodie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口语,源自英美的媒体和城市中产,用以替代古板正经的gourmet和gourmand,用法较为轻松,含义更见宽广。Foodie除了指对食物有热烈或专精兴趣之人,也指热衷品尝试菜的内行食客以及喜好搜罗食材和钻研庖艺之人。此外,由于时尚杂志爱用此字,foodie也有赶时髦之意,指追随新潮食风之人。
关于老饕和美食家的用语,英文远多于中文,虽然那些字多数是从法国和希腊借来的。翻查《韦氏大词典》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常见的有gourmet精于辨赏的美食家,aristologist餐饮专家,gourmand 胃口好的美食家,epicureepicurean,会享福之人),gastrologer美食学家,gastronome对饮馔掌故有研究的美食家,亦作gastronomer或 gastronomist,或者从法文原封搬来的bon vivant讲究美食者和connoisseur 鉴赏家,包括饮食和艺术等等,令人眼花缭乱。
饮食之道在于分别心,分判鉴别,辨识品味材质的纤毫之异,修辞亦然。这些用语各有精微差异,例如gourmand暗示食欲好,不挑嘴;epicure强调官能感受,较为挑剔;gastronome偏重知识学养,而bon vivant和connoisseur虽说品位高尚雅致,却有些恃傲之意,近乎势利的food snob了。
而相对于中文,英文对贪嘴就比较宽容了,贪食(gluttony)虽是古代的七宗死罪之一,但现在已没有严厉的谴责之意,贪食者glutton指的是饮食过量,而非食欲馋念,其用法有时更是正面的,形容对事物的耽迷酷爱,如a glutton of books就是手不释卷的爱书人。
英文的贪吃与善吃之间,并无鲜明界限,只有模糊些微的差别,很容易就混淆相泯了,例如gourmand,以前指的是暴饮暴食的贪吃者,现在却指美食家,虽然还是大食多量,但已转为正面意义。这倒也符合进化逻辑,如果没经过贪吃的历练,怎能辨异识微,发展出善吃的品位?
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对饮食有迥异的价值观,就以贪食来说,在食物匮乏、严禁纵欲和浪费的文化里,这是不可饶恕的死罪。但在富裕的社会,贪食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反而成了可以夸示的行为,发展出庞大的相关产业。把食物放进嘴里,会有各种气味、质感和层次;放进社会和历史里,所透显的正负明暗和角度光影,就更加折射变幻,摇曳迷离了。
这本《饕餮书》,说的不是美食,也不是贪吃,而是食物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饮食也许真是一头怪兽,移形换影,光怪陆离,可怖可笑又可爱,而不管这头怪兽变成老饕、馋猫、foodie还是美食家,它始终不停在咀嚼时间,分泌意义。
二〇〇二年的秋天,杨照找我给《新新闻》写专栏,我向来文思驽钝,下笔磨蹭,那时又要笔耕一个方块,本来应该敬谢不敏,但是他出的题目实在太诱人了,这专栏叫食物与权力。我像个馋嘴的小孩见到一座冰淇淋做的雪山,虽然胃纳小食力弱,还是不顾一切栽进去,忘情狂吃。
写了一阵子,巴蛇吞象吃不消,我开始叫苦知惨,题目是不愁的,有关食物的话题和新闻太多了,每天层出不穷,但都是夹泥带沙、纷紊驳杂的粗原料,要从这里面提炼出现点,解读(或者编排?)出文化脉络,析滤出深藏不露而又狡谲飘忽的社会关系,可就戛戛其难了,那段日子,我好像老在赶稿,东翻西找,左思右想,好不容易熬夜交了稿,刚刚喘口气,新的一周又如狼似虎扑来,周刊真是恐怖读物。写了几个月,内外交煎,时间与心力皆有不逮,我只好向杨照告罪,休笔喊停。
收到这本书里的文字,主要就是食物与权力那段短暂专栏的结集,时间背景是二〇〇二年到二〇〇三年间,地理背景主要是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由于地利之便,有不少与香港有关。又因为是写给新闻周刊,我的记者旧癖复发,不免贪热好鲜,抓时效贴新闻,倾力描摹当下的现象事件。相隔数年时移事易,回头再看这些篇章,个中的论述与观点,便显得仓促单薄,不够深入周延,让我颇感虚怯汗颜,想要逐篇重写,无奈木已成舟,时间之河亦已滔滔东去,不复当初情境。
但又不忍一笔勾销,当成呆账处理,因为这里面有些东西,当初胆粗粗、懵查查写下来,虽然粗糙率意,却有一股热情冲劲,即粤语所谓的有火;现在也许比那时略识一二,但肯定写不出那种感觉了。凡存在的未必合理,但总是记录和备注,多少是现实的速写剪影,也是我个人的小型食物史。于是捡回来重新整治,补缮修葺循环再用,回锅翻热加料新炒,因成是书。
要感谢杨照以及《新新闻》当时的主编陶令瑜,我在香港深夜赶稿时,她在台北往往也正挑灯夜战,我们经常上网聊天,互相打气说笑,重振工作精神。要感谢杨泽、陈映霞、许悔之、黄芳田等友人,写作过程中,他们慷慨给予的鼓励、批评和意见,在书里和心中,我都深深铭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