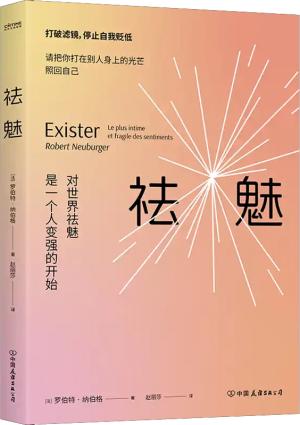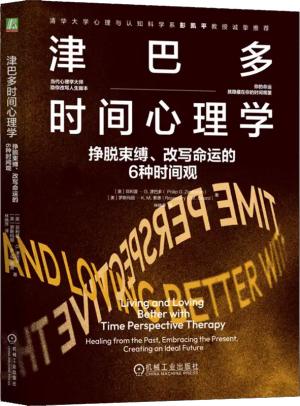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我们终将老去:认识生命的第二阶段
》
售價:HK$
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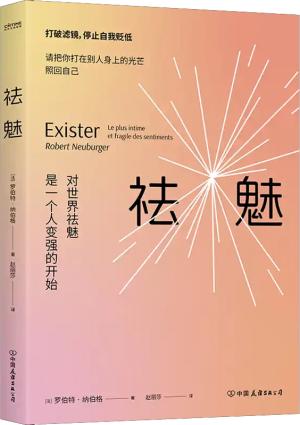
《
祛魅:对世界祛魅是一个人变强的开始
》
售價:HK$
62.7

《
家族财富传承
》
售價:HK$
154.6

《
谁是窃书之人 日本文坛新锐作家深绿野分著 无限流×悬疑×幻想小说
》
售價:HK$
55.8

《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第3版
》
售價:HK$
110.9

《
8秒按压告别疼痛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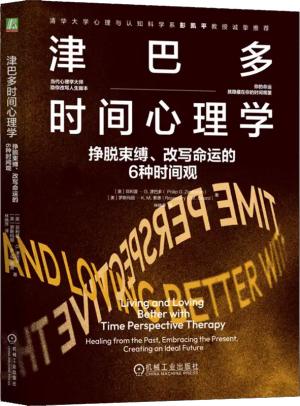
《
津巴多时间心理学:挣脱束缚、改写命运的6种时间观
》
售價:HK$
77.3

《
大英博物馆东南亚简史
》
售價:HK$
177.0
|
| 編輯推薦: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诗界莫扎特 辛波斯卡,传说中的首部诗集!
被时间隐没的传奇诗集,尘封七十余年,中文版首度面世,继《万物静默如谜》后又一经典诗集。
你用书本、昆虫和树叶,教我什么是生命的清晨。
辛波斯卡的早期诗作,风格沉静阴郁,充满意象。在看似平凡的生活细琐中,发掘其中浩瀚,将诗意提升到更深广的哲学意境,如战争、死亡、伤痛,向生命提问,悲悯动人。
波兰文直译,力求传达辛波斯卡作品原貌!
应波兰文学基金会要求,诗歌全部由波兰文直译。译者林蔚昀,二〇一三年获波得兰文化部颁发的波兰文化功勋奖章,也是波兰国宝级作家布鲁诺舒尔茨《鳄鱼街》的译者,其译本广受赞誉。
李健、幾米、陈绮贞、许晴等推荐。
李健曾朗诵辛波斯卡的名作《墓志铭》,许晴曾朗诵《种种可能》。
图书装帧 金衣奖设计师山川操刀,精装双封,印银烫白,随行小开本便于阅读。
|
| 內容簡介: |
《黑色的歌》是一本被时间隐没的传奇诗集这是辛波斯卡的首部诗集创作,却被尘封了七十余年。当年没有出版的原因众说纷纭:波兰历经二战的摧残,在种种动荡不安中,这本出道作品很难有机会出版问世。
直到二〇一二年诗人过世后,她生前信任的秘书和友人代为处理她的遗物。于是,收录了辛波斯卡大学时期(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八年)创作的《黑色的歌》,终于在世界读者的企盼下,于二〇一四年首度在波兰出版,其中还收录了辛波斯卡*初公开发表的诗作《我在寻找字》。
|
| 關於作者: |
维斯拉瓦辛波斯卡
当代至为迷人的诗人之一,享有诗界莫扎特的美誉。一九九六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史上第三位获奖的女诗人。
一九二三年生于波兰小镇布宁。她擅长以幽默、诗意的口吻描述严肃主题和日常事物,以诗歌回应生活。二〇一二年二月的一个晚上,辛波斯卡在住宅里安然去世。在她的葬礼上,波兰各地的人们纷纷赶来,向诗人告别。
代表作《万物静默如谜》《我曾这样寂寞生活》等。
|
| 目錄:
|
译序
为了更多的东西
儿童十字军
我在寻找字
和平
无题
音乐家扬柯
摘自一天的自传
关于九月的记忆
关于一月的记忆
无名士兵之吻
寄往西方的信
献给诗
生命线
诸灵节
高山
漫游
微笑的主题
关于追人的人与被追的人
遗憾的归来
运送犹太人
战争的孩子
玩笑的情色诗
马蹄铁
黑色的歌
今日的民谣
学校的星期天
|
| 內容試閱:
|
译序
我在寻找字谈翻译辛波斯卡《黑色的歌》
翻译《黑色的歌》,是诚惶诚恐的。
惶恐,因为《黑色的歌》(Czarna Piosenka)是一本传奇性的诗集。它收录了辛波斯卡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八年间的诗作,本来应该成为她的第一本诗集,但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内容敏感、无法通过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审查,或是遭到出版社拒绝,或是辛波斯卡自己决定不要出版)没有发表,直到辛波斯卡过世后才得以和读者见面。
创作者的作品重新出土,总是会引起好奇、期待、讨论和争议。有人会质疑这样做是否违背作者意愿,有人担心看到不成熟的少作会让自己想象中的作者形象破灭,也有人乐见创作者不同时期的风格,借此了解他们创作、成长的过程。
虽然辛波斯卡生前一直不太愿意回顾少作,但她也不是完全没有发表过这些早期作品。在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辛波斯卡诗选》中,就收录了五首未结集作品中的诗作(这五首都收录在《黑色的歌》之中)。据辛波斯卡生前秘书、现任辛波斯卡基金会执行长迈克尔鲁辛涅克(Michal Rusinek)的说法,辛波斯卡对自己过世后作品和遗产如何处理规划得很详细,也都经过了审慎考虑。因此,既然辛波斯卡把《黑色的歌》的打字稿留给了她的遗嘱执行人,这表示辛波斯卡默许了它的出版虽然辛波斯卡对这本诗集的样貌、书名、排版已无任何影响力。
双面辛波斯卡
《黑色的歌》会不会挑战、颠覆读者眼中的辛波斯卡,让原本的形象破灭?我想,挑战和颠覆是一定的。《黑色的歌》收录的多数诗作都青涩(但有些诗作则成熟得惊人!)、用字不是很精准、情感直接强烈,而且少数诗作具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宣导色彩,这和辛波斯卡中晚期诗作成熟、精练、对事物抱有冷静观察、从来不为任何主义服务的特色,形成有趣的对比。如果隐去作者姓名,搞不好读者会以为这是两个不同作者的作品就像辛波斯卡的《青少女》中所说的:我们真的差很多,想的和说的,完全是不同的事,她知道的很少但固执己见。我知道的比她多却充满犹疑。
《黑色的歌》和辛波斯卡中晚期的诗作真的这么不同吗?有没有一些主题是延续的,但是后来以变奏的形式出现?年轻的辛波斯卡和中老年的辛波斯卡可以对话吗?在读完《黑色的歌》和辛波斯卡的中晚期诗作(从一九五七年的《呼唤雪人》到二○一二年的《够了》,共十一本诗集)后,我的结论是:两者是有对话性的。《黑色的歌》中的《高山》,在《呼唤雪人》中变成了《未曾发生的喜马拉雅之旅》,但是重点已从登高的感动转化为对人性的思考。在战后不久发表的《运送犹太人》,后来化为《呼唤雪人》中的《尚且》,虽然后者没有直接指犹太人大屠杀,但是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找到线索。而且因为《尚且》脱离了原本的背景,我们也可以用它来理解所有类似并且不断重复发生的暴行。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不是那么明显的互文性,但也同样有趣。比如,辛波斯卡对战争、受害者、死亡、人类处境、世界的关注,在她早期作品中就可以看到。她的幽默感和深入浅出、掌握事物矛盾的天赋也很早就显露出来。她早期写爱情比较直接、天真,后期则多了犹疑、冷眼和世故。她早期喜欢在诗中大量运用叙事以及散文化的风格(所以有时候结构太散乱,文字也不精练),这在她中期的某些散文诗中还可以看到痕迹,而在晚期,这些叙事性已完全融入诗中,散文的部分只剩下文字较为口语化这个特色。
当然,有些年轻时期的特色在中晚期并没有保留下来,毕竟成长并不只是延续,也包括舍弃。辛波斯卡年轻时爱写组诗,这在她中期的作品中很少出现,晚期则完全没有。她年轻时喜欢用艰涩、不易懂、少见的字眼,这在中晚期几乎看不到或者说,辛波斯卡慢慢意识到,语言的实验与创意有很多种,不一定要用大家看不懂的方式来写。因此,她中晚期的诗依然充满令人眼睛一亮的语言巧思(双关、颠覆陈腔滥调的话语、自创新词),但逻辑清楚,令人可以理解,像是透明的琥珀,可以看透,却让人怎么都看不厌。
综合以上,《黑色的歌》是一本有趣的诗集。它让我们看到一位年轻诗人的肖像,一位年轻女士记录时代、和时代对话的企图。对欲了解辛波斯卡的人来说,《黑色的歌》是非常珍贵的素材,他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辛波斯卡后来创作的原型,也可以看到她的创作是如何随时间成熟、改变的。如果《呼唤雪人》开启了辛波斯卡诗歌创作的成熟期,那么《黑色的歌》就是童年和青春期。了解了这个时期,才有可能了解完整的辛波斯卡。不管这个时期的作品有多么不成熟、不完美,它们都有其美丽、动人、诚恳之处。这些不成熟、不完美正好符合诗人当时的心境、年纪与经历,而且正是因为有这些不成熟、青涩、冗赘、一头热,才会有后来的成熟、老道、精练和沉淀。
我不会将辛波斯卡的改变称为去芜存菁(实际上,辛波斯卡没有把芜去除,而是不断尝试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它),而会把它称为蜕变和成长。我所认知的成长并非放弃孩童或青少年时期的特质,而是把它们和大人时期的特质相结合。从这个角度看,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辛波斯卡的作品总是在成熟中有天真,在世故中有童趣。
与辛波斯卡的对话
不管再怎么努力让读者接近原作,翻译一定会失真、一定必须背叛,这是它无法避免的宿命。我在翻译《黑色的歌》时遇到一个很大的困扰:要如何面对辛波斯卡早期的青涩风格?是要保持那语言的青涩、模糊、缺乏逻辑、拙劣、创新实验性,还是要改成读者熟悉、看得懂、可以欣赏的语言?修饰可以让阅读的过程比较容易,但是这样会不会改变原作本质,削弱和中晚期诗作对照的张力?虽然那语言很青涩,但同时也质朴可爱啊。即使是造作、故作高尚、强说愁,也是造作得那么天真、可爱。这些特质不值得保留吗?读者的语言习惯、阅读习惯不能被挑战吗?
如果今天这本书不是译作,我对语言的精确性会比较宽容,因为那时候读者不只是用文字在阅读作者,也是用他和作者共享的对语言的知识、对社会文化背景的知识在读、在猜。翻译作品天生就缺乏这种猜的条件,文字是它唯一的沟通工具,所以必须追求精准、易读。于是,我必须牺牲一些比较有原创性、实验性的语言,比如在《诸灵节》中,辛波斯卡写道:我会让冷杉和紫菀做成的花圈拥抱丑陋的坟墓。这里的花圈原本应该是winieta,指的是欧洲古书上拿来装饰页面的花卉插画(放在书名页或章节的开头或结尾)。但对中文读者来说可能有点冷僻,所以改成易于理解的花圈。
不过,我并没有把每个有棱有角的地方都修平修整。比如辛波斯卡经常使用的双重否定句(如《摘自一天的自传》中的在云朵之后的夜晚并非没有星星),我就倾向于保留。虽然改成肯定句会比较通顺、比较像中文,意义也不会改变,但我觉得那和双重否定所要强调的事情有着细微的差异比起单纯的有星星的夜晚,并非没有星星的夜晚有一种啊,原来不是没有啊,还好还有一点星星的幸运幸存感。
寻找不可能的字
说了这么多关于翻译的眉角,也许读者会觉得:这么说来,这本诗集根本是无法翻译的嘛。翻译它有意义吗?确实,我经常听到这个可以翻吗?的质疑,尤其是诗,只要我告诉别人我在翻译诗,就会有人问:诗可以翻吗?或直接断定:诗是不能翻的。
如果我们把翻译当成制造复制人,每个细节都要百分之百一模一样,包括肉体和灵魂,那诗当然是不可以翻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翻译当成作者和读者共同生下的孩子(作者的基因占绝大多数),那翻译就是可能的。我们不必否认,翻译永远都会是不完全的东西。因为它不是原作(虽然以原文阅读原作,也是另一种翻译,读者永远无法完全了解作者)。但是,或许像村上春树所说,文字本来就是不完全的东西,能装载进去的东西也是不完全的思想和感情。这很符合现实的状态,多半时候,我们并无法完全理解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也无法完全抓住它们。
在《我在寻找字》这首诗中,辛波斯卡写下了找不到字来描写战争犯罪者恶行的挫折和无力:我们的话语是无力的,它的声音突然变得贫瘠。我努力地思索,寻找那个字但是我找不到它。我找不到。有趣的是,这段话也可以用来形容说话、写作本身。当一个人意识到沟通的局限,他可以选择沉默、拒绝沟通、改变沟通的方式或者继续寻找。辛波斯卡选择了继续寻找。
我之前写诗,现在写诗,之后也会写诗。辛波斯卡在一九五一年这么说。把这句话当成座右铭,我觉得我也可以继续翻译、寻找下去。
林蔚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