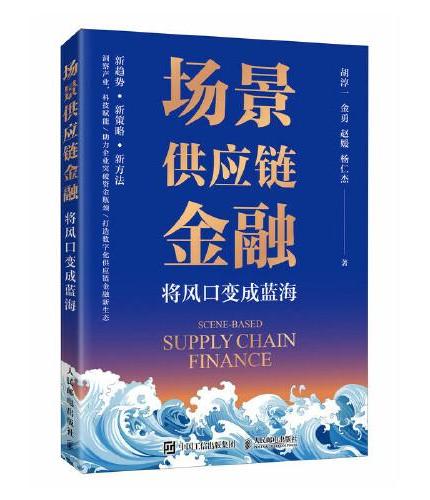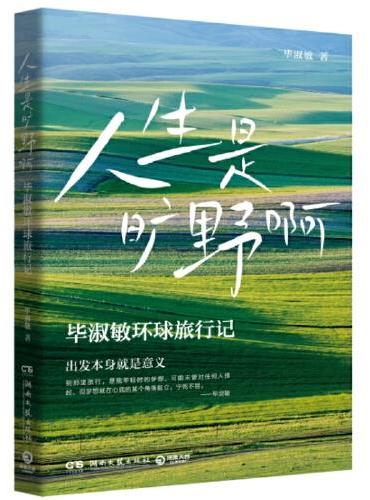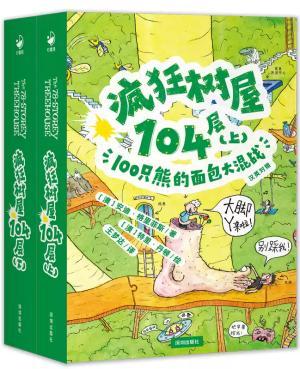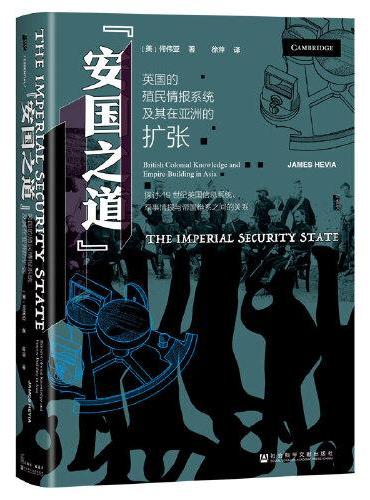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重返马赛渔场:社会规范与私人治理的局限
》
售價:HK$
69.4

《
日子慢慢向前,事事慢慢如愿
》
售價:HK$
5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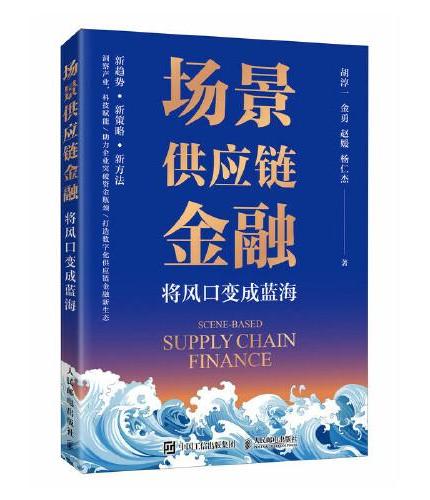
《
场景供应链金融:将风口变成蓝海
》
售價:HK$
111.8

《
汗青堂丛书146·布鲁克王朝:一个英国家族在东南亚的百年统治
》
售價:HK$
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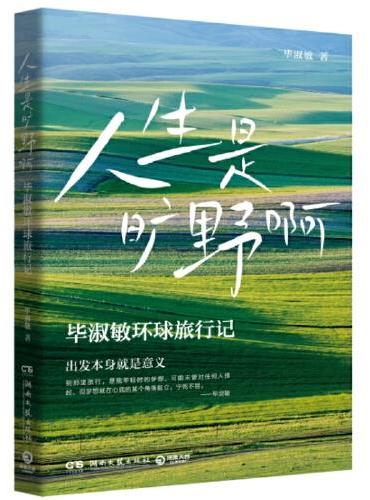
《
人生是旷野啊
》
售價:HK$
72.8

《
疯狂树屋第4辑91层上下全2册 漫画桥梁书The Treehouse中英文双语版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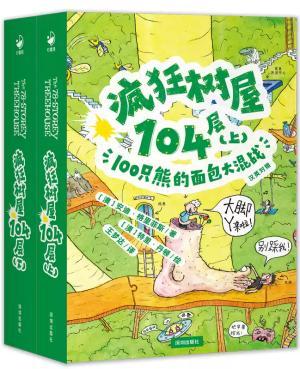
《
疯狂树屋第4辑104层上下全2册 漫画桥梁书The Treehouse中英文双语版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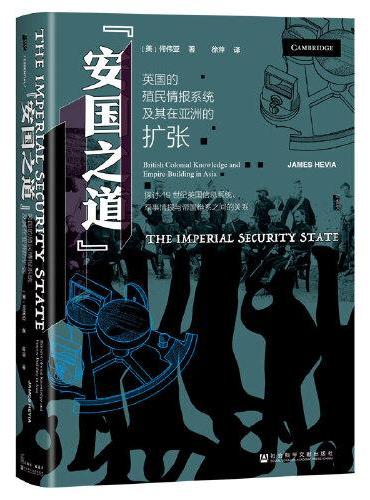
《
甲骨文丛书· “安国之道”:英国的殖民情报系统及其在亚洲的扩张
》
售價:HK$
88.5
|
| 編輯推薦: |
★《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首次标点整理,全书标点准确,校语简明。
★李怀民对中晚唐诗特别是寒士诗的评价,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底本选择精善,嘉庆刻本内容完整,楮墨精良,后来刻本多所沿袭。
|
| 內容簡介: |
《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二卷,补遗二卷,清李怀民撰。晚唐张为撰《诗人主客图》,取中晚唐诗人列为六主七十八客,试图从风格与继承关系角度梳理中晚唐诗史,但其书存非完本,说明文字与诗例残缺,致使后代难明意旨。李氏选王建、张籍、贾岛、姚合以下中晚唐诗人三十二人,别为清真雅正与清真僻苦二派,仿张为原图,列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前冠以主客图人物表,各以年代系之,注明科第;后附各家诗选,各作小传,附采诗集序跋、评论资料,于中晚唐五言近体,颇具提纲挈领之功。该书的问世,是清乾隆后宗唐诗派从学习盛唐转向中晚唐的标志,在当时影响很大。
该书未有整理本,此次据清嘉庆刊本标点排印,拟列入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
|
| 關於作者: |
李怀民1738-1793,名宪噩,号石桐、十桐,以字行。清乾隆间诸生,高密诗派的创始人,著有《石桐诗抄》、《十桐草堂集》等。
张耕,中华书局编审。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编辑、整理工作,责编书籍包括《白居易诗校注》、《白居易文校注》、《杨万里集笺校》、《刘克庄集笺校》、《辛弃疾集编年笺注》、《张孝祥集编年校注》、《王若虚集》等。
|
| 內容試閱:
|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説
李懷民
計敏夫《唐詩紀事》:張爲作《詩人主客圖》,序曰:若主人門下處其客者,以法度一則也。以白居易爲廣大教化主,上入室楊乘,入室張祜、羊士諤、元稹,升堂盧仝、顧況、沈亞之,及門費冠卿、皇甫松、殷堯藩、施肩吾、周元範、祝元膺、徐凝、朱可名、陳標、童翰卿;以孟雲卿爲高古奥逸主,上入室韋應物,入室李賀、杜牧、李餘、劉猛、李涉、胡幽貞,升堂李觀、賈馳、李宣古、曹鄴、劉駕、孟遲,及門陳潤、韋楚老;以李益爲清奇雅正主,上入室蘇郁,入室劉畋、僧清塞、盧休、于鵠、楊洵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升堂方干、馬戴、任翻、賈島、厲玄、項斯、薛壽,及門僧良乂、潘誠、于武陵、詹雄、衛準、僧志定、喻鳧、朱慶餘;以孟郊爲清奇僻苦主,上入室陳陶、周朴,及門劉得仁、李溟;以鮑溶爲博解宏拔主,上入室李群玉,入室司馬退之、張爲;以武元衡爲瓌奇美麗主,上入室劉禹錫,入室趙嘏、長孫佐輔、曹唐,升堂盧頻、陳羽、許渾、張蕭遠,及門張陵、章孝標、雍陶、周祚、袁不約。共六主七十八客。余嘗讀其詩,皆不類。所立名號,亦半强攝。即如元、白、張、劉,當時統謂元和體,爲乃獨以元稹屬白居易,而張籍、劉禹錫更分承之李益、武元衡,誠不知其何所見?以韋應物之沖淡,獨步三唐,宋人論者,惟柳宗元稍可並稱,而乃僅入孟雲卿之室,且與李賀、杜牧比肩,何其不倫耶?其他不可勝舉。至其所標目,適如司空表聖《二十四品》,但彼特明體之不同,非謂人專一體,且即六者,亦不能盡體矣。是蓋出奇以新耳目,未爲定論也。余讀貞元以後近體詩,稱量其體格,竊得兩派焉:一派張水部,天然明麗,不事雕鏤,而氣味近道,學之可以除躁妄、祛矯飾,出入風雅;一派賈長江,力求嶮奥,不吝心思,而氣骨凌霄,學之可以屏浮靡、卻熟俗,振興頑懦。二君之詩,各有廣大奥逸、宏拔美麗之妙,而自成一家。一緒所延,在當時或親承其旨,在後日則私淑其風,昭昭可考,非余一人私見。慨自明季歷下、竟陵諸公互主騷壇以來,各立門户,不本於古,使學者入於歷下則非竟陵,遁於竟陵則誚公安,迄無至是,豈知古人派别依然具在,特不肯降心一尋耳。予每欲聚集諸家,分承兩派,訂成一書,嫌於創始,或驚俗目,喜得張爲《主客圖》,本鍾氏孔門用詩之意而推廣之,雖所用不當,而取義良佳。謹依其制,尊水部、長江爲主,而入室、升堂、及門,以次及焉,庶學者一脈相尋,信所守之不謬,且由淺入深,自卑至高,可以循序漸進,不至躐等也。
今之選唐詩者,大概古今並收,以希各體俱備之目,且矜尚七言詩,利其句長調高,便於諷詠,不知七言律詩,唐人不輕作,嚴滄浪曰:七言難於五言。余嘗考唐詩,王、楊、盧、駱,絶無七言近體;燕、許稱大手筆,張止十二篇,蘇十三篇;沈、宋律體之始,沈七言十六首,宋止三首而已;崔司勳《黄鶴樓》千古絶唱,然此篇及《行經華陰》一首,合生平纔兩首耳;其他如王龍標亦止二首,李東川八首,高達夫七首,岑嘉州十一首。凡初、盛名家,俱各寥寥。杜工部、王右丞、劉長卿稱七律最多,然合五言對較,曾不能及其半。由此觀之,唐之不輕作七言明矣。元、白、劉夢得沿及北宋,其風少熾,然未有如後世之甚者也。今則匝街遍市,無非七律填滿,使世之爲七律者約其意、降其格而爲短章,則並不能成語矣。夫不學短律而爲長律,猶不學步而趨也。唐人之所以專攻五言者,唐以此制科取士,例用五言排律,其他朝廟樂歌,亦類用長排體,蓋取其體制宏整、法度嚴密,使長於才者不得濫其施,裕於學者可以勉而至,故唐二百八十年間,士子鏤心刻骨,研煉於五字之中,其理則本於經,其材則取於《選》,當時相矜相賞,總是此事。夫是以唐多詩人,詩盡能工,不然,何不謂吟成七個字,撚斷數莖鬚耶?今略五言而學其七言,是棄其長而用其短也。吾之訂唐詩而不及七言,誠欲力矯此弊,倘能由此而精之,因其體而充之,三唐七言具在,固自各能得所宗主矣。至若古體詩,或當别有支派,似非可專取於唐者,請異日細論之。
自故明以來,學者非盛唐不言詩,於是乎襲爲渾淪宏闊之貌,飾爲高華典册之詞,至前、後七子而其風益盛矣!余讀其詩,貌爲高華,内實鄙陋:其體不外七言律,其題半屬館閣應酬,更可笑者,大半仗中原紫氣黄金風塵等字希圖大聲,宜袁氏兄弟譏明三百年無詩,可存者《掛真兒》《銀柳絲》小令而已。此論誠過當,然盛唐實不易學,前輩謂學《選》體者讀初唐,學盛唐者看中、晚,學唐人者讀宋詩。蓋以初唐之與六朝,永貞、元和之與開、寶,北宋之與五代,時相近,人相接,其心法相授,屢降而不離其本,特氣運遞遷,高者漸低,深者或淺,幽隱者或顯露,渾淪者或説破矣!後學徒厭其淺卑顯露,而務爲高深渾淪,是未下學而驟欲上達也。吾謂淺卑者實與人以可近,顯露者正與人以可尋,升其堂不患不入其室,故宋人不可輕也。但宋自西崑混擾以後,詩體頗難辨,又多染五代之習,流爲尖酸粗鄙,學者未能得其骨格而襲其皮貌,則敗矣!學詩者誠莫如中、晚,中、晚人得盛唐之精髓,無宋人之流弊,又恐晚唐風趨日下,而取晚之近於中者,類爲一家,言雖稱兩派,其實一家耳,學者潛心究覽,久久自入於初、盛,譬由門户而造堂奥也。
予家藏書不多,耳目所接,積之既久,以私意潛究,有似淵源可尋,然尚不敢自信,後得龔半千《中晚唐詩紀》,間載原本傳序,據所稱張、賈弟子,頗與鄙見相合;又檢明楊升庵《詩話》,言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一派學賈島,詩皆五言律。鄙意竊喜:古人已有定論,用修諒非無據。但用修又云:其體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也。余嘗笑之,彼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今不讀古而徒事苦吟,撚斷筋骨亦何益哉?真處褌之蝨也。據用修此論,真是粗心浮氣耳。雖聞二派之名目,實未睹二派之實也。《三百篇》,民間士女不曾撚鬚作詩,亦曾切合平仄、較量聲律乎?且如文公多才,演成《雅》《頌》,其《國風》所陳,不盡出文人,凡變風淫辭,悉可尤而效之乎?杜工部詩苦致瘦,孟浩然眉毛盡脱,王右丞走入醋甕,是皆盛唐大家,用修所心慕者,且謂獨不撚鬚乎?至謂其起結平平,將何者方謂不平?渠自不平,用修未見耳。其云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此正中、晚善學初、盛處。初、盛人平舉板對而氣自流動,總提渾括而意無不包,降格而下,力量不及,則不敢妄襲其貌,於是化平板而爲流走,變深渾而爲淺顯,乍看似甚易能,細按始驚難到,要其體會物理,發揮人情,實能得初、盛人内裏至詣。最可怪者,中、晚人皆着意三四,至後聯往往帶過,雖琢對精工,意不在此,用修不暇致詳,而顛倒説來,真負古人苦心。至若詩之用事,審其可用則用之,非主於不用,亦非主於用。陸士衡云:徵實難工,翻空易巧。《詩品》云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此皆閲歷有得之言也。中、晚人惟知力量不逮初、盛,深恐用事則意爲所用,反成疵累,而或意之必須借事以發者,然後用之,用則其事不必從乎其舊,而翻新之;又或其事不必與吾詩相符,而巧合之,其中神妙,又自難言。若止如後人之用事,徒事誇多鬥靡,即極切合妥當,豈免爲點鬼簿哉?天地間文章祗在當前,搜得出便成至文,鍾記室曰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梅宛陵曰:發難顯之情於當前,留不盡之意於言外。二語實盡古今詩法。必如用修言,是驅天下人盡爲牛鬼蛇神而後快,恐詩道不如此也。且用修之詩務闊落而乏静細,矜才麗而欠真切,彼固詡詡以盛唐自命,豈知五霸三王之罪人也,究何曾細心味乎張、賈兩派之妙,徒見清真瘦削,非九天閶闔規模,便存一卑視之心,吾恐晚唐人筋骨不失仙人清羸,而用修實遭降肛之困也,自處於褌而不知,尚暇譏人爲蝨耶?
吾鄉阮亭先生,爲詩不能盡脱時蹊,其論俗字甚精,即如老杜詩中之聖,阮翁指稱其緑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等句爲俗;明高季迪《梅花詩》三百年無異辭,阮翁謂其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爲真俗,是真巨論也。按工部以垂字形容風竹,以綻字刻繪雨梅,時人所謂工於匠物也;季迪以高士方梅之品,以美人比梅之質,又時人所謂妙於品梅也,而阮翁總斷曰俗。彼豈好翻案哉?良謂詩之忌俗,猶詩之貴清,在神骨而不在皮膚。果其不俗,雖亂頭粗服,無礙其爲美女;而苟俗也,即荷衣蕙帶,終不得謂之仙人。世之論者不及見此,而誤以元輕白俗按四字東坡亦帶言甚輕,非如今人所論。之俗爲俗。樂天爲詩,八十老嫗亦解,彼固好以俗情入詩者,而曰:十首秦吟近正聲。是則大不俗矣;陶元亮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王摩詰曰:五帝與三王,古來稱天子。宛肖不讀書人口吻,是俱謂之俗乎?俗在骨不在貌,俗關性情,不關語句;王鳳洲謂擬《騷》賦不可使不讀書人一見便曉,此等見識,正萬俗之源也。後世人大半爲此等論所誤,故爲辨俗如此。
張、王固以樂府名,然惟後人祗知其樂府耳。當時謂之元和體,寧單指樂府哉?且水部自標律格,其近體固當與樂府並重,後人乃謂鴻鵠之腹毳,直目論耳!《紀事》稱賈島變格入僻,以矯艷於元、白,元、白誠無可矯,遂啓後人妄訾,乃謂元、白、郊、島總病一俗字,元、白譬若袒裼裸裎,郊、島等之囚首垢面,無論所譬不當,即如其言,亦非俗也,吾故云今人錯認俗字。但元、白、劉夢得,恐學者利其省事,流爲率易;貞曜無近體;吏部祗能古作,故皆不録。
鍾記室《詩品》詳推漢、魏、晉人之詩,而定其源所從出,别爲上、中、下三品,遂資後人口實。余按所品亦實有未允者,然記室亦特就詩論詩,明其體格相近,非真見其一脈相傳也。至所論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又曰孔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陳思入室,潘、陸諸子自可坐於廊廡間矣,此誠千古不刊之定論。即起諸賢而問之,亦應首肯,況余選《主客圖》,初非敢如記室之尚論其淵源所自俱有明徵,特效裒輯焉耳。至圖中所列及門,不無斷以己意,要皆會昌以後人;又據升庵晚唐兩派之説。即有不盡然者,或亦非古人所深罪也。耳目不廣,姑就所見引列,其有遺賢,後當補入。
自《記事》定爲初、盛、中、晚之目,學者遵之。劉隨州開元進士,而派入中唐;馬戴與賈長江、姚武功同時,而别爲晚唐,是蓋以詩爲升降也。然朱慶餘格律如水部,而不免爲晚唐,僧清塞僻澀如李洞,而無礙其爲中唐,亦似有不可盡憑者。余但因其體格之相近者,次爲先後,並時代亦不拘,實非敢妄爲等殺,觀者幸勿泥執。
宋儒之理誠不可爲詩,而詩人實不能離。其言書情,即正心之學也。發乎情,必止乎禮義。其言匠物,即格物之學也。故其詩曰:君吟三十載,辛苦必能官。特唐時儒教不純,或雜佛、老,然王仲初曰:君子抱仁義,不懼天地傾。固已知孔氏之教矣!李太白思復雅樂,杜工部自比稷、契,元、白、張、王、韓文公、孟夫子各出其讜言正論以維持世教,是知唐詩雖小道,實與《三百》之義相通,但其間遇有隆替,才有大小,其升之廟廊而恢其才,則爲樂府、爲雅頌;非然,即一室嘯呼而約其才,爲苦吟,爲孤索。要皆各得性情之正,而不流爲淫哇。唐之盛也,道德渾於意中,和樂浮於言外;及其衰也,氣節形於激烈,名義著爲辨説,而凡李義山、段成式、温飛卿、韓致光等淫詞艷語不足以淆之。故余定中、晚以後人物有似於孔門之狂狷:韓退之、盧仝、劉叉、白樂天,狂之流也;孟東野、賈島、李翱、張水部,狷之流也。後世人不識,或指其言爲俗劣,爲粗鄙,爲直率,爲妄誕。嗚呼,是皆浮沉世故、居心不正者徒以香情麗質爲雅耳!古人固已先知之,乃曰:今時出古言,在衆翻爲訛。又曰:所得非衆語,衆人那得知?彼固衆人,安得不以衆人之見爲見耶!吾定《主客圖》,竊見張、賈門下諸賢,微論其才識高遠,要之氣骨稜稜,俱有不可一世、壁立萬仞之概。夫是以與時鑿枘,坎坷多而遭遇難。然司空圖不事朱温,顧非熊高隱茅山,馬虞臣以正言被斥,劉得仁以違時不第,此皆孔氏之所收也。其餘諸子不能枚舉,間有行事無考者,其言存,可按而知之。願世之觀吾《主客圖》者,先求爲古之豪傑,舉凡世俗逢迎、諂佞、悭吝、鄙嗇、齷齪種種之見,一洗而空之,然後播爲風詩,以變澆風而振俗,或亦盛世之一助云。
乾隆甲午長夏高密李懷民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