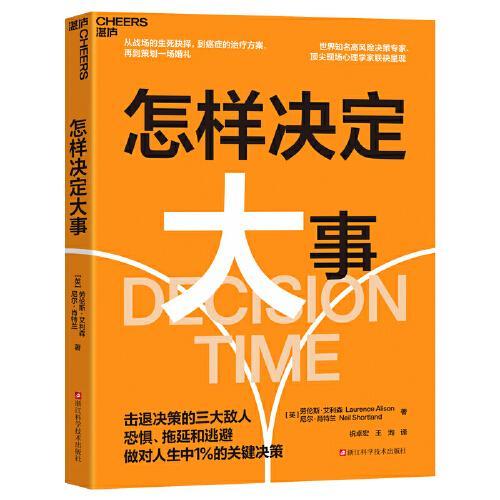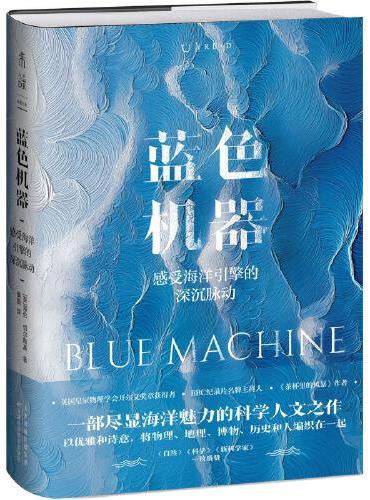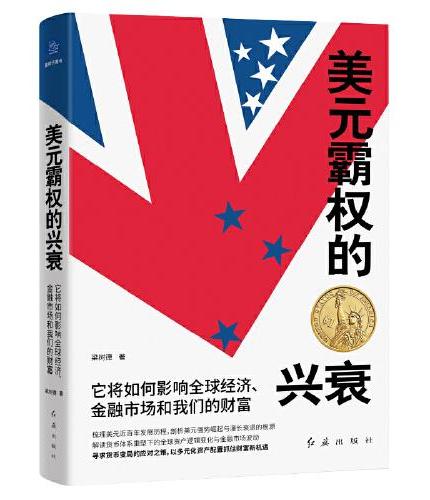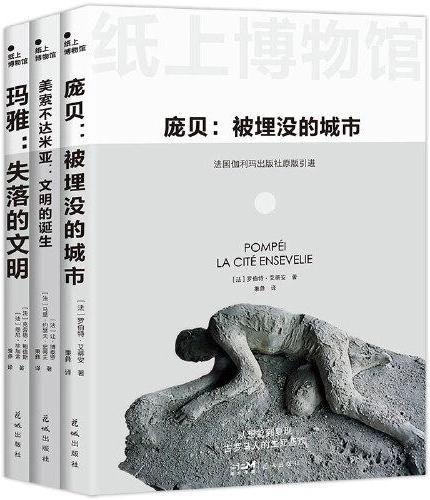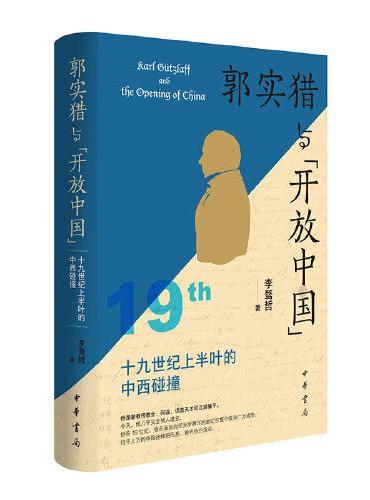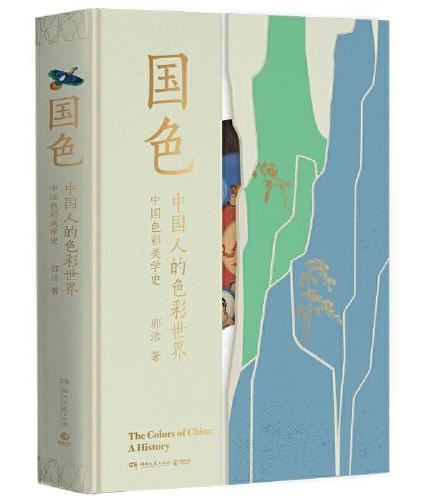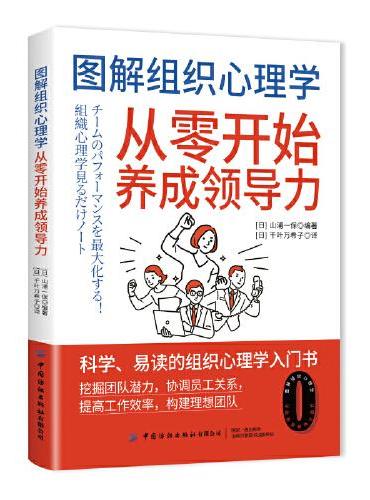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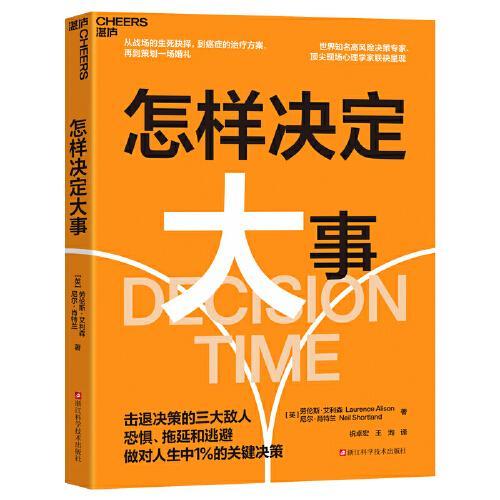
《
怎样决定大事
》
售價:HK$
10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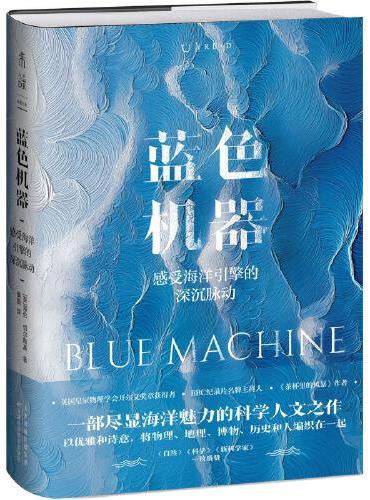
《
蓝色机器:感受海洋引擎的深沉脉动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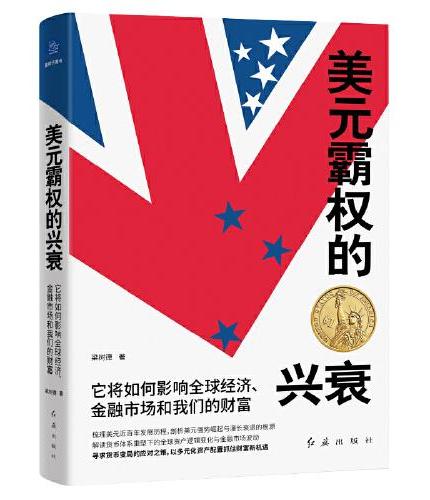
《
美元霸权的兴衰:它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和我们的财富(梳理美元发展历程,剖析崛起与衰退的根源)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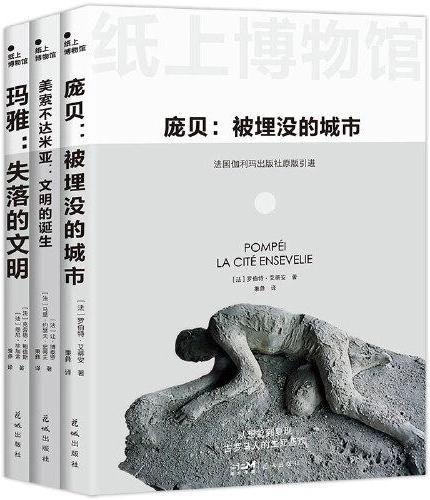
《
纸上博物馆·文明的崩溃:庞贝+玛雅+美索不达米亚(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450+资料图片,16开全彩印刷)
》
售價:HK$
2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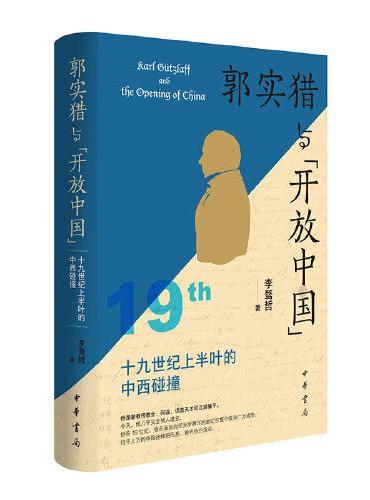
《
郭实猎与“开放中国”——19世纪上半叶的中西碰撞(精)
》
售價:HK$
74.8

《
海外中国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份制:良与贱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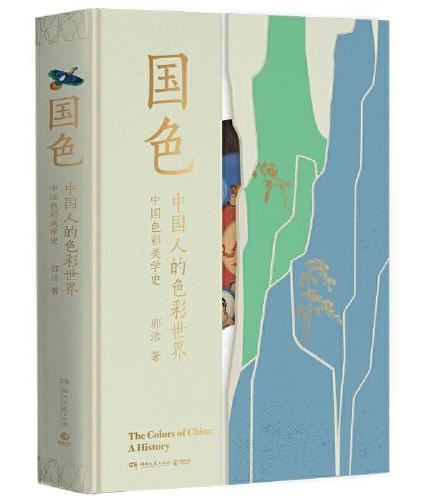
《
国色(《寻色中国》首席色彩顾问郭浩重磅力作,中国传统色丰碑之作《国色》,探寻中国人的色彩世界!)
》
售價:HK$
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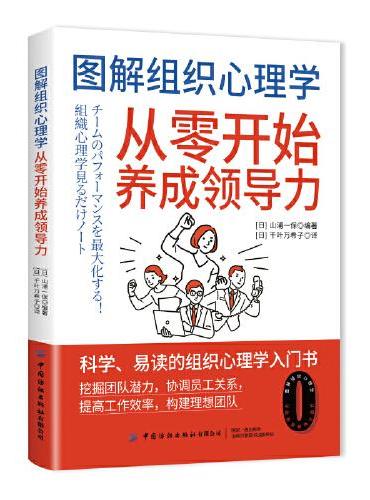
《
图解组织心理学:从零开始养成领导力
》
售價:HK$
74.8
|
| 編輯推薦: |
法国美第奇奖作家
哲学享乐主义代表
米歇尔翁弗雷
对食物、美食学以及饮食与身体关系的哲学思考
|
| 內容簡介: |
|
如果嗅觉和味觉不能抓住稳定的形式,消耗、摧毁所感知的对象,那么,美食学(gastronomie)如何能被承认为一种艺术?
|
| 關於作者: |
|
米歇尔翁弗雷(Michel Onfray,1959 ),法国哲学家、随笔作家。曾任高中毕业班哲学教师二十年,后辞去教职,创办卡昂民众大学。其思想汲取了尼采、伊壁鸠鲁及犬儒派哲学的精髓。主要著作有:《旅行理论》《无神论》《哲学家的肚子》《美食家的理性》《向森林求助》等,其中多部在三十多个国家翻译和出版。
|
| 目錄:
|
001序 言 食物的自传、续篇及待续
001第一章 气泡的微哲理悼唐培里侬修士
019第二章 美食的礼仪和美食舞台艺术悼格里莫德拉雷尼埃尔
069第三章 通向生殖器之路悼挪亚
097第四章 子宫、松露与哲学家悼布里亚萨瓦兰
141第五章 提神饮料神话简史悼神农氏和C
169第六章 烹饪符号帝国悼卡汉姆
217第七章 天使之享庆典悼圣帕特里克
249第八章 转瞬即逝之美悼菲利亚
294后 记 一种扩大到肉体的哲学
304致 谢
|
| 內容試閱:
|
序言:食物的自传、续篇及待续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星期天,天冷冷的,下着雨,大概在深秋季节,或是寒意凛凛、飘着绵绵细雨的初冬。父亲在地里忙着。父亲的老板让他开垦成一块菜地。原来的一畦荒地被吞噬,经过开垦形成了一幅广袤的土地,面积够得上领取国家津贴了:一切都消失了,被连根拔起、被掠夺、被摧毁,杂乱地掩埋在一地荒芜中。植物的根,还有一片片被秋天腐烂的落叶,一切回归到正在消解蔬果残渣的泥土里。腐殖土被挖开了一个个洞,种下的蔬菜根部垒着土堆,仿佛那块地开垦出来是用来做公墓的。还记得那天下着雨,一场永远都属于诺曼底,寒意沁入骨髓的雨。
父亲冒着密雨忙碌了一整天。他的蓝色人造革衣服被雨淋湿而变得沉甸甸。从上衣、肩膀和背上像水汽般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味道。中午,他回来吃饭,像往常一样沉默;而我,是一个喜欢说话、对任何细微征兆都会感到不安的孩子,在我眼中,他将沉默推至令人极其绝望的境界。喝完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他又踏上了那条路,走向坑坑洼洼的田地,整个下午他都在地里翻土。在那片用栅栏围起来,未来将变成菜圃的地里,他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我躲在土地旁的旧木屋后看着他弯着腰,坚定用力地用铲子翻土,一下一下富有规律。尽管那时我只是个孩子,但已经知道这种腐殖土和未来埋葬人们肉体的土壤是一样坚硬的。
他是否知道儿子正站在木棚屋的角落后,看着浑身淋湿的父亲弯腰专注于手中的工具,以自己的方式孤独、勤劳而勇敢地颂扬土地而心疼他呢?在后来的若干年里,我已经长成少年,甚至是青年,仍不止一次看见父亲,但我从来不打扰他。他在地里为老板播种、收割、翻耕,永远都在忙着极为普通、随着四季轮回而不断重复的工作。尽管父亲终日劳筋苦骨,胼手胝足,与终将埋骨的黄土亲密接触。而我却始终希望他能在这样的尘世间再活得久一些。
他的耕种使雏形渐显出来:这块土粒细碎的地,换作别人会用厚犁铧马虎地翻耕,但在他的手下变成了一个菜园。在附近所有的菜园里,我一直认为他的菜园是最美的:用栽植绳辟出,规整、笔直、干净。他把所有的菜畦都围上细绳,沿着绳子用手掌刃划出线,接着等距离地播下了种子。不久后,这些种子将萌出新芽,将菜园点缀得似一片星空或海域。
当天晚上,天空一如白天的阴沉,细雨绵绵。他给母亲看了一块犁地时找到的黄色小硬币。他用沾满泥土的粗大手指夹着这块硬币。硬币也和泥土粘在一起,亦如他的灵魂和肉体。硬币被投入水中,渐渐显露出它的秘密:这不是一块铜币,而是一枚金路易。父亲露出了微笑,这是他唯一一次流露出情绪的征兆。他告诉我们兄弟俩,他在读小学时就从一位他非常崇拜的老师那里学习了一首拉封丹的寓言《农夫和他的儿子们》,寓言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类似的故事。他回忆了一会儿,一字不差地背诵着这首寓言中的诗句,就像有时候在夜里,当一家四口睡在冰冷的房间里,他朗读着雨果《沉思集》中一首诗的开头。我并不满足于听他读诗。我想,即使到今天,听到这首诗仍会让我激动不已。
还是回到父亲的菜园。尽管那时父亲的工资非常微薄,靠着菜园的收获,我们还是得以从紧巴巴的日子中挺过来。糙皮的土豆、又甜又香的胡萝卜、绿油油的生菜上渗出的汁液一直流到了根部,四季豆长出了巴洛克风格的花苞,带刺的小黄瓜像一个凶神恶煞的史前怪物,芹菜破开泥土向上生长是为了让浓郁的香气飘散出来,布满弯弯绕绕纹路的卷心菜是我最早认识的分形物体,香喷喷的韭菜像一个调皮的闺蜜,轻轻地拂动长叶,纤弱的细葱在微风中慵懒无力,香芹层层叠叠,堆成一片幽绿,新鲜的百里香带有一种普罗旺斯风情的香味。还有新鲜的小洋葱头,以后会被挂在车库上晒干,像大蒜一样被编成一串串、悬在屋梁上。被鼻涕虫和蜗牛啃食的酸模能酸倒牙齿,圆嘟嘟的番茄肉质红嫩,散发着果香。另有一小块地和菜地分隔开来,种着美国石竹或者大丽菊,石竹是送给母亲的,一直以来它身上拥有一种能深深感动我的特质。地里还会种上草莓。
父亲,属于沉默和土地;母亲,是絮叨,也是厨房的化身。拣菜、冲洗、和面、切配、烤、煨、炖,她总是忙碌着。尽管伙食费拮据,她却能常常备上煎蛋卷,甚至有时在月头还能准备肉和鱼:烤肉在炉子里噼里啪啦地响着,每个周日都会有表皮松脆的烤鸡,奶酪培根焗牛肉、蔬菜牛肉汤、奶油煎鳕鱼、辣酱熏牛舌、马德拉葡萄酒烤火腿、水果蜜饯布丁、巧克力果酱吐司。还有给父亲准备的一锅一锅浓汤,每天一大早去干活前,他吃早饭时都要喝些。有土豆韭菜汤、洋葱汤、番茄汤,总之各种各样的浓汤。有时候搭配面包,有时候煮着细面条,或木薯粉。
我还记得厨房玻璃窗上凝结的水汽,外面寒意凛凛,还下着雪,饭菜还没出锅就已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我在土豆泥中挖出一个小洞,母亲可以往里倒入一两勺酱汁,而父亲往盘子上撒葱末时也会有些掉进去。肉是红彤彤的,烤炉里飘逸出的蒜香味弥漫了整个屋子。火苗窜动的炉灶成了厨房里的火盆.屋外寒冬肆虐,某种类似于幸福的感受在屋里氤氲开来。
然而一个九月的早晨,一切都消失了,十岁的那年一场可怕的家庭变故迫使我在外寄宿了七年。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想自己已经把一些让人幸福的最本质的东西扔进了火堆里。父亲的菜园,还有母亲的厨房,都成了久远的回忆。在随后许多年里,对我来说,稀薄的汤、潦草应付的准备工作、凝固在盘子里的酱汁、令人恶心的食物,这些就足够了。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二十年过后,距离夏特龙河岸不远的地方,我在一个晚上来到了波尔多。这个城市曾带给了我无穷的痛苦,一些从未开口提及的遭遇,还有一段段毫不光彩的经历留下的创伤。当晚入住诺曼底酒店后,我难以入眠,走到阳台上看着梅花广场、加龙河以及城里昏黄颤抖的灯光。我没穿衣服站在窗户边,寒风像鞭子一样抽在身上,过去从未在如此深沉的夜色下思索自己的人生,度量自己的空虚。恶心、厌倦、绵绵无尽的悲伤。波尔多曾把我推到了深渊的边缘,我发誓永远不再踏足这个城市。
然而因为《雕塑自我》(lasculpturedesoi)出版而安排的一系列报告会,我不得不又渡过了加龙河。我再次见到了这条肮脏奔涌的河流,火车从铁路桥上驶过发出轰隆隆巨响,到达了火车站。我下了火车,走进了一家有
名的鞑靼餐馆。
晚上的活动在莫拉书店举行。我知道店里书刊极为丰富,而且熟悉书架的布局,可以让我体验淘书的幸福。金色的护壁板,挂式吊灯,挑高的天花板,多得数不清的书籍,举行读者见面会的大厅与外部环境格格不入,让人产生轻微的幻觉。汽车、人影在外面经过,晃动的人影中有几个我还必须再碰面。我渴望尽快离开。德尼莫拉邀请我共进晚餐。我接受了。我们重回到音乐、文学、葡萄酒和旅游的话题上来。他发誓要成为最符合格里莫德拉雷尼耶尔定义的晚宴东道主。我们谈起了伊甘酒庄出产的甜白酒,可我从来没有品尝过:我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在垂涎生命中第一个女人的第一枚吻、第一次拥抱。一个略显笨拙的大男孩害羞腼腆,渴求得到一位绝色美女青睐却无法企及,谈到美女更是颇有研究又乐此不疲。我把德尼莫拉当作一位经验丰富的兄长,向他求教情感困惑、享乐和幸福。他和我聊起了吕萨吕斯伯爵、酒庄、酒窖以及他知道的
葡萄酒的许多好年份,问我如何评价米歇尔塞尔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著,也告诉了我他的想法。接着,话题又转到了巴洛克音乐和圣达梅隆产区葡萄酒、罗曼式风格和俄罗斯建筑之间的对应联系。佛泽堡1988和龙虾沙拉,香芹圣雅克贝和卡隆堡1985。红酒与海鲜的联姻促使我们展开了对葡萄酒品种的配合、相邻性及亲和力的研究。我们的眼睛闪耀着光芒,我被波尔多征服了。
于是两人聊起了亲和力:当蜂蜜冰淇淋和巧克力冰淇淋上桌时,德尼莫拉问我想品尝哪一瓶酒?我对巧克力有着对葡萄酒同样的狂热,并不希望将香槟或波尔图糟蹋了这两样。德尼莫拉让我相信他,跟随他追求一种独特的亲和力,他指着酒水单上的一瓶酒,向酒务总管询问它的最佳饮用温度和时间。过了一会儿,在餐厅的另一头,我认出了老板娘手里酒瓶上的标签,身体顿时变得僵直。我突然很想起身离开餐桌,去和人交涉一下,表达自己的反对或拒绝。那是一瓶伊甘堡出产的酒,年份当然是1979年。
时机到了吗?还有机会吗?我陷入一种焦虑,仿佛花很长时间为一次机遇做准备而机会却远没有到来。当我在谈论伊甘堡时,难道没有怂恿对方奢侈消费和不合时宜的大方吗?为了避免这种让人不安稳的状态,如何拖延、回避、追溯时光?为这个独特的日子,我已经想象了许许多多的机会,彼此之间都不尽相同,所有的机会都与一个独特而令人遐想,需要像建座教堂一样堆砌的事件相联系。我想过要庆祝一个重要事件。这个事件本身就成为了一个节日。
酒被打开了,放在我们眼前。接下来是长时间的静默,感觉就像宗教信徒在默祷。德尼莫拉是我的教义传授人,我觉得自己在一生中都应对他予以敷圣油的礼遇。有一天我认为自己成为了一名祭司,在向他人传授教义的同时接受他的传授,将他看做我的导师,如同吕西安杰法尼翁在道德领域是我的导师。保持一段安静的时光,将这段时间用于默祷来迎接这一事件真是必要的:我仍听到它无尽的喧嚷,回音缭绕直至今日。
一切都暂停了,中断了。餐厅的声响充斥在我的头脑里,我不敢对视同桌的目光。一股激动的情绪占据了我的肚子、肌肉、躯干和皮肤。一切都绷紧了,仿佛被安置在白色的区域。在这里我不知道从我们的嘴里出来的是一声尖叫、一声呜咽或是一个单词。终于我和德尼莫拉交换了眼神,这让我们内心达成了一种默契,我知道这是一种牢不可破的默契。
当然,人的经历超越了言语,也同样超越了书写。她栖息在言语之外,因为人的情感,无论它是哪种情感,它永远超越试图为其划定范围的词语。因为,毕竟,伊甘堡就如同从一片混沌中浮现的第一种形状,地球形成时一片喧扰后的第一个声响,第一个音符。我们像旅行者一样发现它的色泽,下定决心以宇航员辨认星空那样的热情去观察色调变化。闪耀的色彩仍在我的心里跳动:淡黄色、金黄色、杏色、蜜色、咖啡色、焦糖色、深栗色、铜褐色的热度、浅黄褐的甜味,金褐色的秋日微颤的枯叶。然而,眼前的美酒被轻轻晃动,酒体丰满,流动的液体线条优美而略显分量的质感,酒滴从玻璃瓶壁沿滑下。透过神秘的玻璃瓶,世界仿佛失真,在霍尔拜因的光线下,葡萄酒的金黄色构成了变形的图像。时光在流逝,悠长绵密,稀有又浓烈,我们在品尝
后来伊甘堡其他品种的酒也端上来了,但没有一瓶像第一瓶所具有的意义。接下来还品尝过其他酒庄的优质葡萄酒和名菜,谈起美好的回忆,情绪激动,还有丰富的菜肴,珍稀的美酒和优美的举止。为了在美味的回忆中来往,我必须依靠即兴发挥和偶尔的闲聊。有一天,遇到的一个问题启发了我真正的智慧:美食给你留下的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有选择性的问题。选择什么呢?在哪些剩下的菜肴当中呢?有点奇怪且造作的钻牛角尖
了。我必须找到是什么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最私密的痕迹。伊甘堡,还有吗?罗曼尼―康帝,柏图斯还是白马呢?奥信,拉图还是拉菲呢?罗林格餐厅、赛德伦斯餐厅还是罗比雄餐厅?是科唐坦半岛出产的鲍鱼,莫尔旺地区的带馅肉片卷还是里斯本佛手贝呢?
一个想法像一道闪电在我的脑中划过:在一片模糊中隐约呈现出儿时的记忆。美食给我留下的最美好的回忆是父亲菜园里的草莓。那时的夏天,天气很热。草莓被热气浸透了,连果实中央都是温热的。绿叶形成的阴影也不够为草莓遮挡。我摘了一枚果实。父亲让我用水冲洗一下,用他的话说,是为了洗干净并让它变得清凉。水龙头出来的水流很冰凉,那是菜园的地下水。我把草莓放进嘴里,感受到表面清凉和中间的温热,它的皮肤有点冷,柔软,果肉带点温度。在上颚的碾压下,草莓化成汁液,溢满了我的舌头、两腮,然后流入了我的喉咙。我闭上眼睛。父亲就在我的旁边,弯着腰在菜地里忙碌。在一瞬间.但确实一种永恒.我变成了这枚草莓,一种纯粹简单的味道存在宇宙中,弥漫在我儿时的身躯里。幸福用它的翅膀,轻轻拂过我,而后飞往了别处。从此,我一直在等候这位享乐天使再次降临,我是多么热爱它的羽毛和呼吸。可以肯定的是,我满怀热情地寻找它,但它在躲着我,当我没有等待时它现身了,当我不再抱有期待时它又突然出现了。对它而言,这本《美食家的理性》就是一座陵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