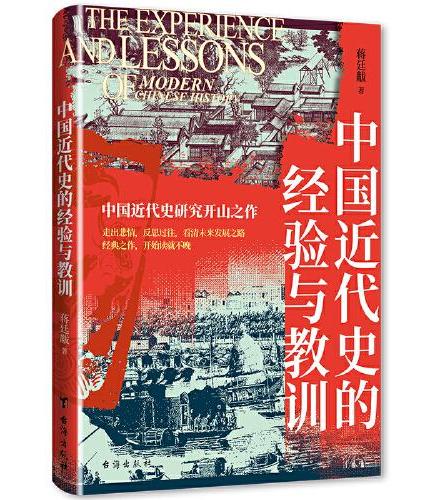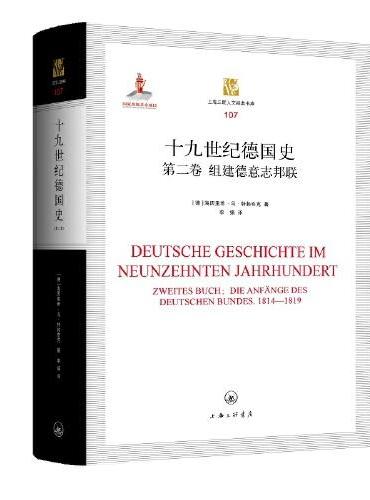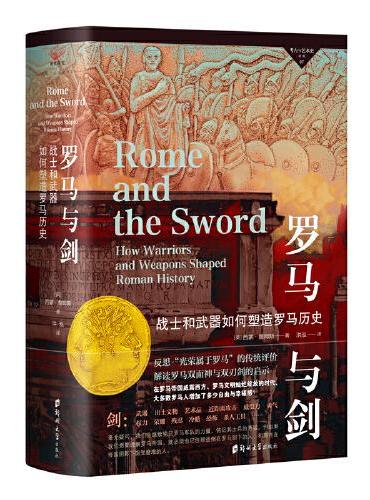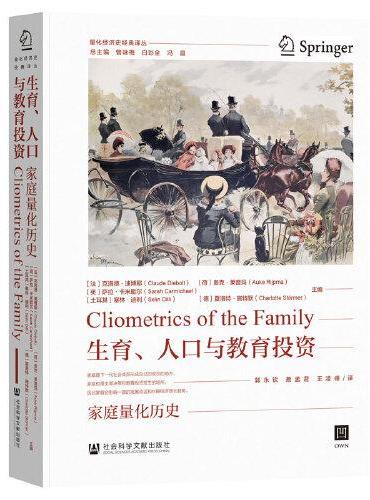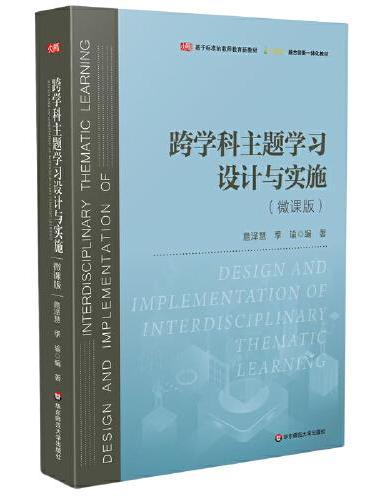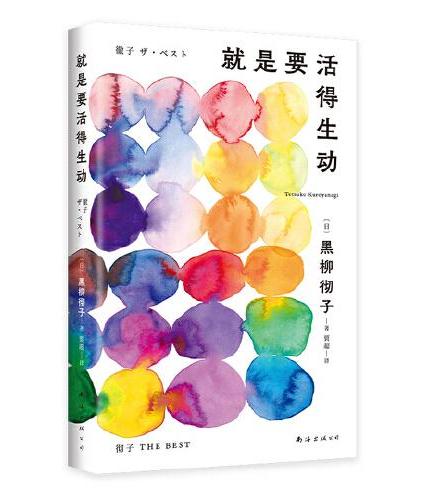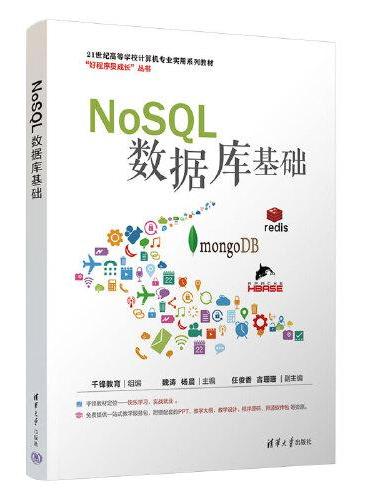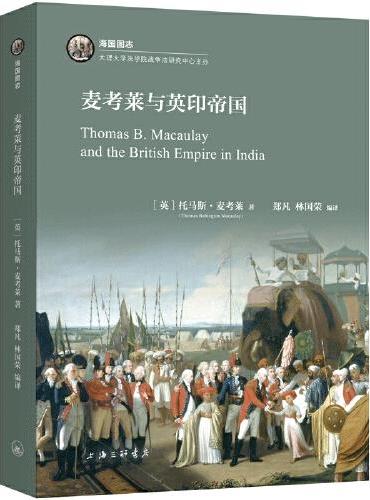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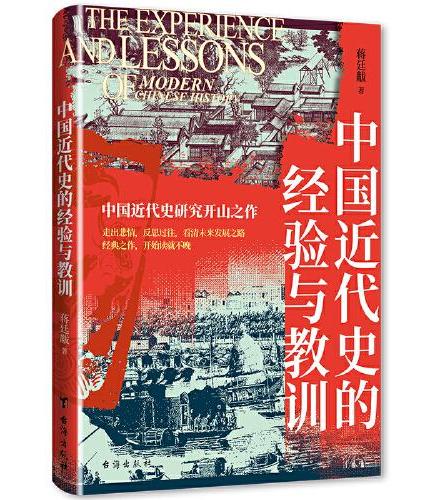
《
中国近代史的经验与教训——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山之作!走出悲情,反思过往,看清未来发展之路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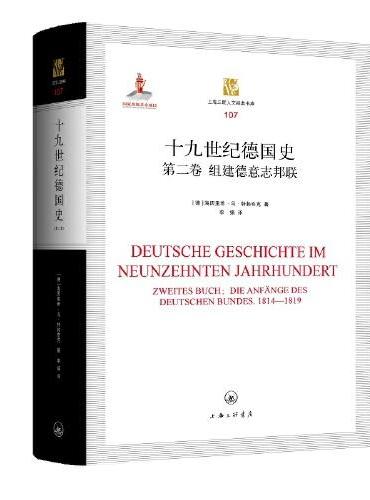
《
十九世纪德国史(第二卷):组建德意志邦联
》
售價:HK$
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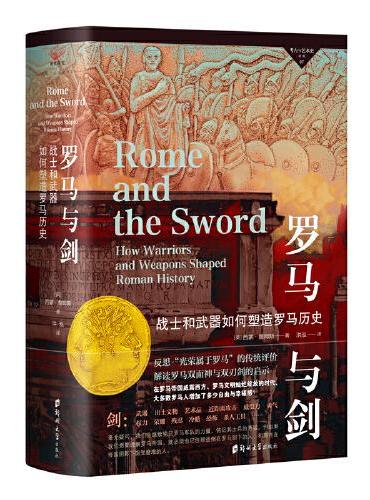
《
罗马与剑:战士和武器如何塑造罗马历史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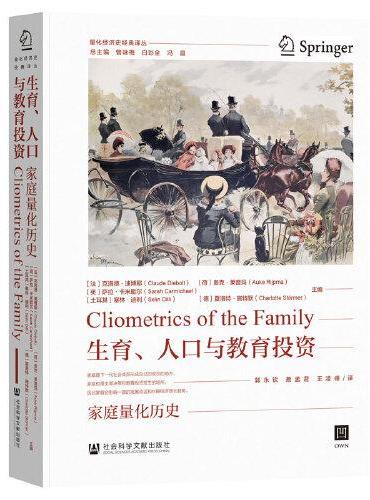
《
生育、人口与教育投资:家庭量化历史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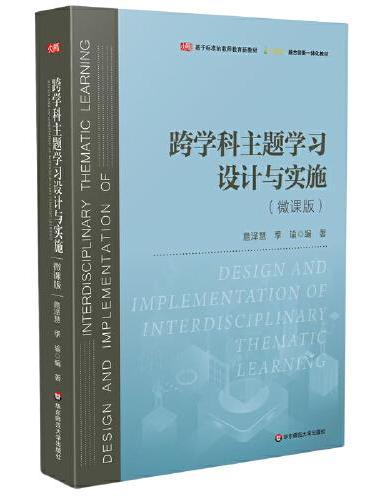
《
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与实施 微课版(基于标准的教师教育新教材)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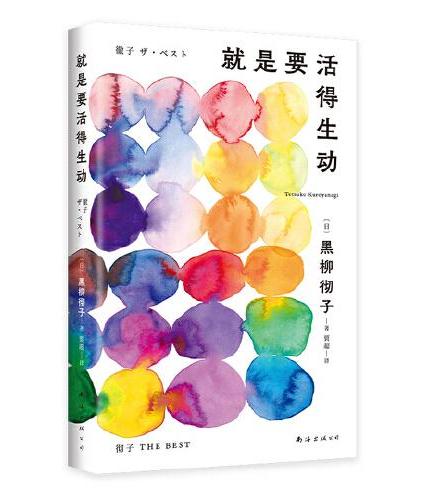
《
就是要活得生动(她,单身,90多岁,还在搞事业!日本电视女王黑柳彻子随笔集,从容幽默的老奶生活录)
》
售價:HK$
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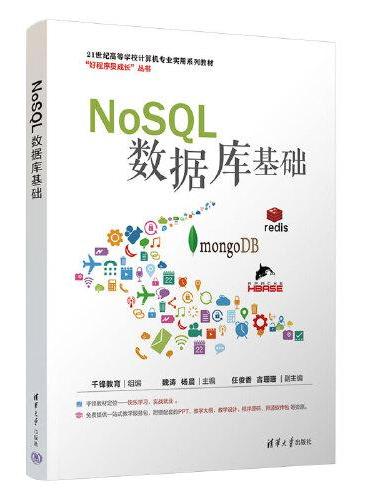
《
NoSQL数据库基础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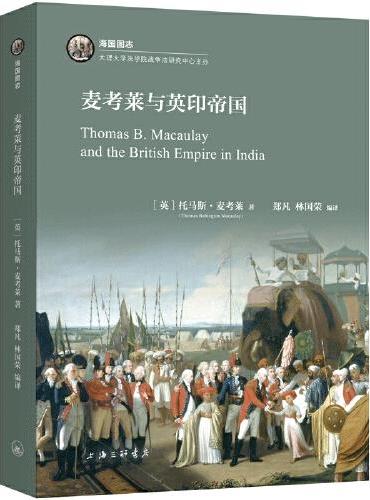
《
麦考莱与英印帝国
》
售價:HK$
96.8
|
| 編輯推薦: |
|
苔菲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幽默作家,更是是一位非常细腻、观察力非常强的的心理学家。她的语言简洁而有力量,书中充满她对人性的思考和对人类处境的忧惧,同时不失她特有的讽刺和幽默。但是这一次,她幽默的面具下紧裹的是恐惧。
|
| 內容簡介: |
苔菲自1920年起,定居法国,在巴黎俄罗斯侨民中享有极大的声誉。她的回忆录堪称是一部俄罗斯的精神苦旅,其背景是当时给俄罗斯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内战争。1914年欧战爆发以后,引发了俄罗斯国内的内战,导致俄罗斯各阶层大批人士的流亡和出走,苔菲毫无例外地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而这一次旅行中的所见所闻,被她以诙谐幽默的文笔记录下来,让今天的读者可以在轻松的阅读中,窥见当时社会急剧变化之下人们的精神和生活状态。
19世纪以降,俄罗斯诞生了一大批*的文学巨匠,如普希金、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这些金子般的名字迄今仍在向世人闪烁着独特的光芒。然而,作为一座富矿,俄罗斯文学在我国所显露的仅是冰山一角,大量的宝藏仍在我们有限的视阈之外。金色俄罗斯丛书进一步挖掘那些静卧在俄罗斯文化沃土中的金锭,向中国读者展示赫尔岑的人性,丘特切夫的智慧,费特的唯美,苔菲的幽默,什克洛夫斯基的精致,波普拉夫斯基的超现实,哈尔姆斯的怪诞可以这样说,俄罗斯文学史即一部绝妙的俄国思想史,它所关注的始终是民族、人类的命运和遭际,还有在动荡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理性的迷失。
苔菲自1920年起,定居法国,在巴黎俄罗斯侨民中享有极大的声誉。她的回忆录堪称是一部俄罗斯的精神苦旅,其背景是当时给俄罗斯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内战争。1914年欧战爆发以后,引发了俄罗斯国内的内战,导致俄罗斯各阶层大批人士的流亡和出走,苔菲毫无例外地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而这一次旅行中的所见所闻,被她以诙谐幽默的文笔记录下来,让今天的读者可以在轻松的阅读中,窥见当时社会急剧变化之下人们的精神和生活状态。
19世纪以降,俄罗斯诞生了一大批*的文学巨匠,如普希金、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这些金子般的名字迄今仍在向世人闪烁着独特的光芒。然而,作为一座富矿,俄罗斯文学在我国所显露的仅是冰山一角,大量的宝藏仍在我们有限的视阈之外。金色俄罗斯丛书进一步挖掘那些静卧在俄罗斯文化沃土中的金锭,向中国读者展示赫尔岑的人性,丘特切夫的智慧,费特的唯美,苔菲的幽默,什克洛夫斯基的精致,波普拉夫斯基的超现实,哈尔姆斯的怪诞可以这样说,俄罗斯文学史即一部绝妙的俄国思想史,它所关注的始终是民族、人类的命运和遭际,还有在动荡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理性的迷失。
金色俄罗斯丛书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诗人、翻译家汪剑钊主编,遴选普希金、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大师的经典作品,向中国读者呈现优美而深厚的俄罗斯文学。
|
| 關於作者: |
作者:
苔菲,俄国白银时代的幽默作家,以幽默短篇小说闻名。其作品以文风幽默、泼辣,文字洗练、清新著称。
译者:
李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著有《左琴科小说艺术研究》《伏特加里的红月亮》,译著《重病的俄罗斯》《涅瓦河畔》《萨哈林岛》等。
|
| 內容試閱:
|
译者序
作者苔菲冠名回忆录的这本书,讲的其实是她本人的一次旅行,若按传统的说法,应该叫旅行记比较得体。
不过,稍加浏览,旅行记几个字便套不上了。不错,苔菲此番旅行时间长,所到之处亦不少,只不过其中所录与我们今天熟悉,并且预期的装点此关山式的游记大相径庭。尽管作者开宗明义,说她在此书中不写英雄,不讲政治,记述的全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以及在那个年代见怪不怪的寻常事,但正是这些普通人寻常事,仍然让今天的读者如此地触目惊心,不忍卒读,不由得像作者一样连连惊叹,这简直就是部冒险小说!
经常出门的人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出门旅行最重要的是安全。有意思的是,苔菲此番始自莫斯科,终于叶卡捷琳诺达尔(今:克拉斯诺达尔),历时秋冬春夏的南北贯通四季之旅,却是为了安全所做的极不安全的选择。
1914年欧洲一战爆发,原本偏安东隅的俄国受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命参战,这使得原本就内忧外患、矛盾重重的俄帝国雪上加霜。天怒人怨,终于在1917年一年之内连续爆发两次革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尤其是后一次革命,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格局,在地球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人类社会新纪元。然而,俄国十月革命同样无法毕其功于一役,红色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遭到来自国内外数股反革命武装冲击,于是在1918-1922年长达四年期间,发生了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惨烈空前的国内战争。一时间,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幼,革命的反革命的彼此杀戮,不革命的人人自危,不是丧命就是丧家,真当是搅得周天寒彻。
像苔菲这种贵族出身,帝俄时期就已成名的文人,在时代风暴中,即使不反革命,亦属于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嘴里末日到了的资产阶级,所有只要不革命,日子照样难过。同时,虽然俄国当时城市化程度相当低,但倘若将资产阶级,譬如旧日沙皇政府的中小官吏、类似苔菲这样的大小文人、大小企业主金融家、财经人士、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城市市民这一干人等小范围地聚拢来,数目不可谓之小,如若再撒开每个人的社会关系网,上下一勾连,其总和同样可观。这些人不管是表面不革命心里反革命伺机而动,还是真心怕革命惶然无措,还是盲目无知起哄随大流,甚至是昧着良心发国难财,一旦浮动起来,带来的恐慌混乱,不稳定不确定则恰如苔菲旅行所遇所知。
是的,苔菲不了解布尔什维克。但苔菲了解沙皇俄国,了解专制制度下的社会现实,以及生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各色人等。作为一个喜剧作家,她自出道伊始,便遵从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创立的批判本质,笔锋所指,字字句句落在她所痛恨的制度弊端、社会弊病和人性的悖谬鄙陋上。其犀利不留情面,在回忆录里亦并不鲜见。譬如,对那个叫嚣永远不干活的贵族地主,发誓为兄弟报仇的沙皇官吏,在餐馆里叱骂侍者的贵族老爷,苔菲只寥寥数笔便将他们的丑嘴脸恶本性勾勒出来,这些沙皇专制制度的主人公,其现身说法,一如冷眼旁观的苔菲所直言,比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更能让人憎恨产生他们的社会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作品深得一贯坚守党性原则的列宁所喜爱的原因。甚至在她流亡国外,尚未公开发表反苏言论之前,列宁还曾建议盗版发表她1920年代描写灰暗的流亡生活的小说。
尽管立场坚定,苔菲的创作却明显不同于19世纪俄国文学中由果戈理确立的,以讽刺为主的喜剧传统,其艺术个性十分鲜明。话说及此,有必要对苔菲其人稍加了解。有时候,有才能不一定有地位,地位不一定有钱,有钱不一定有德,有德不一定有情趣,所幸的是,苔菲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样样都有的贵族家庭里。曾祖父是共济会会员,写过神秘主义诗歌;父亲是律师、刑侦学教授,出版过杂志《司法公报》;母亲有法国血统,通晓欧洲文学;姐姐米拉(玛丽亚)是女诗人,人称俄国的萨福,曾获普希金文学奖,先于苔菲成名。良好的教养,高雅的修养,使得苔菲随性而不任性,有时天真到弱智,有时又精明得通灵,接人待物往往不以世俗的尊卑贵贱论短长,在她眼里,哪怕是崖畔的野花,坚硬的宝石都是有感情有温度的。
所以呢,即便她将笔下卑劣、卑微人物身上的庸俗、粗鲁和丑陋放大一千倍,其夸张笔法饱蘸的却是宽厚的笔墨。同为看透,在喜剧大师果戈理的创作中,是无所假借的赤裸裸地撕破,不调和不姑息的讽刺;而在苔菲那里,则是含笑的批评,温婉的幽默。简略地说,从审丑的技术层面看,首先,幽默既不像讽刺那般锐利直接,也不同于滑稽丑怪在生活中的呈现,哪儿都有,看得见听得着。幽默是一场智力的游戏,它的起点固然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依据,但它一定是琢磨思索的结果,其自在自然,是绕出来的知其所以然,是智慧精进的演绎,否则即恐失之浅薄、堕于油滑。其次,同样是揭露贬斥丑恶鄙陋,讽刺和幽默这二者的审丑主体,对审丑对象的主观态度和立场其实是很有区别的。讽刺要的是瞄准丑恶一棍子打死的痛快淋漓,而幽默奉行的宗旨是温良恭俭让的警醒救治,同情就是它的核。说得美学一点,即黑格尔所言,与喜剧性不可分割的乃是一种无限的恳切和信任;说得玄学一点,那是神圣的微笑,一个伟大心灵的断念,从某种程度上看,竟是可遇不可求的了。再从审丑的社会层面看,幽默与否,并不单纯取决于喜剧艺术家的天性和修为,它还需要相对宽松良好的社会条件。所以,幽默才被置于喜剧艺术的最高范畴,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回顾自普希金19世纪初开创俄国文学的那百来年间,沙皇的专制制度确实无法给幽默艺术提供适宜的土壤,幽默在俄国自然愈加稀缺了。
就苔菲个人而言,她深知,在她的目光下无法隐遁的渺小、无益、可笑、荒唐、卑微,其实是源自人性的缺欠,可谓人人生而有之,她所打击的那些卑劣人物,正是那个丑恶的社会制度的普遍产物;他们的活动,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根源于那个社会制度。故此,苔菲从不把自己与人们分开,总是与他们站在同一行列里,她对笔下那些愚昧无知人怀抱着确定不移的温情。创作上如此,生活中亦如是。在这部非虚构的回忆录,让人印象最深的,非苔菲的经纪人古锡金莫属。从一开始游说苔菲加盟他的巡回演出,到行程过半不得不分手,不单苔菲,就连读者也看出来了,这个敖德萨小剧场老板身上的毛病远不止忽悠这一点,可苔菲容忍了,只念他的好。再说阿维尔琴科的那个奇葩经纪人,他的大力帮助,为苔菲与古锡金解除合约所出的妙招,居然是让苔菲给自己抹黑。还有那些之前拍着胸脯,发誓保护苔菲的朋友们,眼看敖德萨失守在即,一个个竟然招呼也不打,自顾自乘船逃亡,弃苔菲于危境而不顾。饶是如此,苔菲没怨天尤人,也不痛心疾首,在看似简单,不加雕饰的叙述中,一如既往地不诱惑人,不欺骗人,既不惧怕真理,又不破坏感情的分寸,让人在领略公正不阿、一针见血之余,更感受到悲天悯人的同情。这就使得她的幽默笔调中有某种颤栗的苦涩的笑,为人类而产生的痛苦。她那似乎是内省的、善良的幽默,在人的心灵上留下无法平复的划痕。难怪十月革命前,儿童爱读她的书,少年爱读她的书,自食其力的成年人爱读她的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爱读她的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人都醉心苔菲的小说,从邮局小伙计到沙皇尼古拉二世。人们将她奉为俄国幽默女王,在空前隆重的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庆典上,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邀请的作家仅苔菲一人而已。至于回忆录中所记诸如探望病人送菊花;帮忙搬家把没拧上盖子的墨水瓶混着衣服一道扔进纸板箱,拿走了零碎落下行李;见义勇为修钢琴拔出琴键却插不回去,林林总总类似的乌龙行为,每每看到,总让人忍俊不禁,一时忘怀。
然而,战争革命非儿戏,回忆录可不是小说,此间每一个逗笑桥段,细思量,实际上都不过是那场残酷战争的衍生品,只要你稍作移步转睛,便可直觉回忆录里每一个当事人亲临的逼人情境。苔菲说过,生活在笑话中非但不快乐,反而更悲剧。信哉,斯言。
不是吗。无论何时何地,避不开的是活人惨白的面孔,死人的残肢断臂,衣服上的血迹和脑门上的抢眼。眼见新朋老友消失,像苔菲的多年老友М.,新相识敖德萨首领格里申-阿尔马佐夫,他们原本只是普通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天翻地覆之际,被推上刀尖枪口,白白送死,一个个都成了被杀害的上帝的仆人,这让人情何以堪。
不是吗。战争革命之初,人们还会被吓得牙齿咯咯发抖,还会屏住呼吸细听搜查捕人的卡车是开过去了,还是在大门口停下来了,那时听到枪托砸门还会心跳恶心。可是久经红色白色恐怖,人们反倒习以为常了,恐惧到麻木,实叫人无语。
不是吗。虽说战争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红军杀白卫军,白卫军杀红军,杀人成了稀松平常之事,冤头债主死得其所,无辜百姓亦妄遭荼毒,但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为给家人报仇的白卫军Х.上校,竟将杀人当做了茶点。更有甚者,在这种新的日常生活条件下,人们对伤、亡这类字眼竟是如此习以为常,伤者与死者就是日常生活,它们已经惊扰不到任何人,也不会引起任何人多可怕!多伤心!的惊呼,反倒是那些小偷小摸,或什么毫不搭界的鸡毛蒜皮是小事,被人们讨论得津津有味。错乱至此,夫复何言。
不是吗。当苔菲在基辅一家糖果店门口看到一个佩戴肩章的帝俄军官在吃甜点心,这在过去再平常不过的一幕,却令她惊叹这一切多么奇怪!白天、太阳和周围的人群、军官手上的甜点心,曾经的日常生活成了传奇,即便不是梦,苔菲们也已经不习惯了,无法走进这样的生活了。其绝望谁又承受得起。
所以尽管苔菲不怕死,但是她怕那些怒气冲冲的面孔,怕人拿着手电筒直射她的脸,她怕那无法消除的、愚蠢的仇恨。怕寒冷、饥饿、黑暗,怕枪托砸地板声、喊叫声、哭声、枪声和别人的死。那一切令苔菲如此疲惫,她再也不想经历这些,再也不能经受这些。她走了。她逃了。
行路难啊。从莫斯科到叶卡捷琳诺达尔,奉承完红色政委再讨好白色军官,那晓得还有黑色的德国军官横生枝节,一路行来真可谓步步惊心。
行路难啊。躲过了人祸,逃不脱天灾。之前基辅有西班牙流感,其后叶卡捷琳诺达尔发斑疹伤寒,有大难不死的,譬如苔菲,有在劫难逃的,譬如奥列努什卡的小丈夫,在在都是命悬一线。
行路难啊。下了火车上马车,乘不到客车搭货车,苔菲跟旅伴们从北到南,在印着俄罗斯字样的绿色巨幅地图上一路下滑,不想不愿可是不由自主,一步一回头却又无可奈何,因为,不是俄国民谚说的舌头,也不像苔菲自嘲所谓的语言,书里书外的人都明白,是战火烽烟将这一干乱世的浮萍驱赶,一去难返。
或许从莫斯科出发时,苔菲并未意识到这将是一趟单程旅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点的变换,碰到形形色色人,遭遇千奇百怪事,她该清楚,此番行走,注定是她的一场人生苦旅。过后看,以及今天看,那也是她祖国的一段苦旅。
1928年,去国十年,回家无望,苔菲遂于异乡巴黎写下这部回忆录。只不过这一回,女作家的幽默外衣,被现实的血雨腥风撕扯得支离破碎,笑面具后面是恐怖。
李莉
2016年8月酷暑于杭州二不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