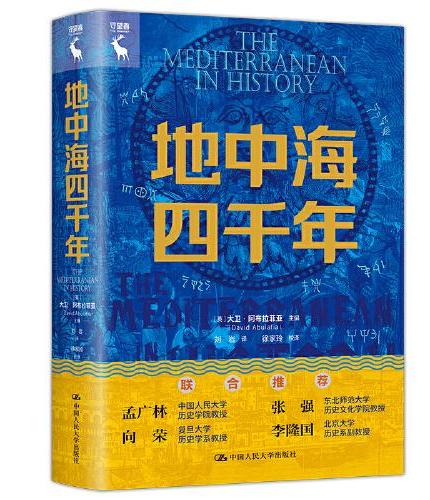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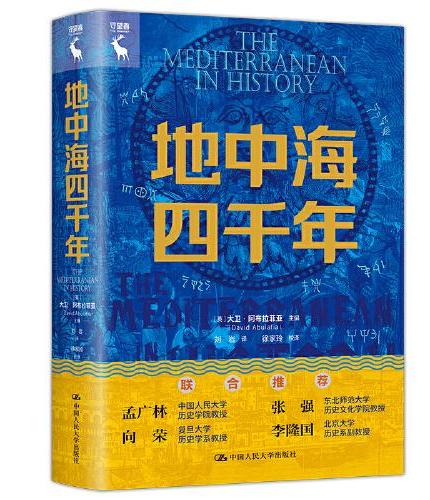
《
地中海四千年
》
售價:HK$
184.8

《
君子至交:丁聪、萧乾、茅盾等与荒芜通信札记
》
售價:HK$
68.2

《
日和·缝纫机与金鱼
》
售價:HK$
41.8

《
金手铐(讲述海外留学群体面临的困境与挣扎、收获与失去)
》
售價:HK$
74.8

《
五谷杂粮养全家 正版书籍养生配方大全饮食健康营养食品药膳食谱养生食疗杂粮搭配减糖饮食书百病食疗家庭中医养生药膳入门书籍
》
售價:HK$
54.8

《
七种模式成就卓越班组:升级版
》
售價:HK$
63.8

《
主动出击:20世纪早期英国的科学普及(看英国科普黄金时代的科学家如何担当科普主力,打造科学共识!)
》
售價:HK$
86.9

《
太极拳套路完全图解 陈氏56式 杨氏24式和普及48式 精编口袋版
》
售價:HK$
32.8
|
| 編輯推薦: |
|
《暗杀》是两届布克奖作家希拉里曼特尔的全新短篇小说集,其中*饱受守争议的一篇《刺杀撒切尔》入选了BBC短篇小说奖短名单对真实历史人物实施虚构暗杀,在英国引发了空前的热议。其他几则短篇故事也同样笔锋犀利,曼特尔对于英国的阶层鸿沟、社会矛盾、家庭黑洞等种种问题的剖析,都在《暗杀》中体现。
|
| 內容簡介: |
《暗杀》是希拉里曼特尔201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全书共收录了十一则短篇小说:
一场失败的族裔融合(《很抱歉打扰你》),一桩令人不寒而栗、故意杀人的交通事故(《寒假》),一个被社会潮流异化吞噬的家庭(《心跳骤停》),一位处于事业瓶颈、追问写作如何干预生活的女作家(《我该怎么认你》),再到饱受争议的主打短篇《刺杀撒切尔》,一场灵感来自真实场景和感受的虚构暗杀,真实与虚构在看不见的门里渐渐虚化
|
| 關於作者: |
希拉里曼特尔出生于英国格罗索普市,于伦敦经济学院和谢菲尔德大学攻读法律。2009年、2012年凭借历史小说《狼厅》和《提堂》两次摘得布克奖。目前,克伦威尔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镜与光》正在创作中。曼特尔是首位两次获得布克奖的女性作家,此前只有JM库切和彼得凯里两次获此殊荣。
1974年,希拉里曼特尔开始了创作生涯。第一部小说《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重现了法国大革命的恢弘场面,获1992年《周日快报》年度小说奖。1995年《爱情实验》获霍桑登奖。2005年《黑暗深处》入围英联邦作家奖和橘子奖短名单。2003年出版了以童年生活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学说话》。迄今为止,希拉里曼特尔已经出版十一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自传。最新出版的作品是2014年的短篇小说集《暗杀》。2006年希拉里曼特尔受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2014年受封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DBE)。
|
| 目錄:
|
很抱歉打扰你 ..........................001
逗号 ....................................027
长QT综合征 ..........................044
寒假 ....................................050
哈雷街 ................................ ..059
人身伤害 ............................ ....079
我该怎么认你? .......................093
心跳骤停 ................................ 120
终点站 ................................ .137
刺杀撒切尔 ..........................144
英文学校 ............................... .175
看不见的门(代译后记) ........210
|
| 內容試閱:
|
看不见的门(代译后记)
黄昱宁
哪怕单看标题,《刺杀撒切尔》也注定成为新闻焦点,更何
况开篇第一句就是:先想象一下她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条街。执笔为枪,瞄准离世不久、生前毁誉参半的政治风云人物,在虚构中让其偿还血债,这不是一般的小说家会干的事他们会觉得这样的表达方式不够含蓄不够微妙。然而,两届布克奖得主希拉里
曼特尔不属于一般的作家。对于这个极具挑衅性的题材,她毫不含糊地表示,这决不是什么一时冲动的游戏之作,虽然只是个短篇(译成中文不过一万三千余字),却已经在我心里酝酿了三十年。
曼特尔说的是一九八三年。与小说中描述的场景类似,时任
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在温莎的医院里刚做完眼科手术。仅就小说缘起的角度而言,故事中那个从卧室窗口能看到医院花园的女主人公,就是曼特尔本人她在温莎有一套小房子。仿佛是出于本能,当撒切尔夫人蹒跚着步入她的视野时,曼特尔立刻就目测了距离,她的拇指和食指比划成手枪,当时我就想,如果这里站的不是我,如果是别的什么人,那么她就死定了。
仇恨何以如此强烈?用曼特尔的说法,这是在为人民说话:
现在想到她时,我还能感觉到一种沸腾着的憎恶,她对英国造成了久远的伤害我从来没有投票支持过她。但我可以退后一步,把她作为一种现象来关注。作为一名公民,我因她而受罪,但作为一位作家,我因她而得益。至于撒切尔夫人团队刻意替她打造的励志故事和个人形象,曼特尔冷笑一声,毫无顾忌地展开人身攻击,本质上,她是反女权主义者,是心理层面上的异装癖。
曼特尔向来持坚定的左翼立场,她对以撒切尔夫人为领袖的
英国保守党在八〇年代对内对外的铁血政策深恶痛绝,也算意料之中事实上,对这个问题,大多数英国文化界人士都持类似看法,程度或多或少而已。不过,时隔三十年,这股怒火仍然在字里行间熊熊燃烧,这一点显然超过了某些人的承受范围。撒切尔的前公关顾问甚至呼吁警方对她开展调查,因为她公开承认了谋杀的动机和意愿。对此,曼特尔的回应简直一剑封喉:让警方来调查,哪怕让我自己做主,我也难以设计、不敢期盼这样的好事儿,因为真要来这一出,那大伙儿立马就能看出,他们有多么荒唐。
话说回来,这篇小说之所以闹出一段风波,除了因为英国
报章素来喜欢煽风点火,也确实与曼特尔本人的这种泼辣风格在英国文坛独树一帜有关。不绕着圈子说话,不低调行文,不屑在厚厚的泡沫塑料里藏软刀子就这点而言,曼特尔其实很不英国。
然而,与态度同样鲜明的,是技术,这是曼特尔之所以是曼
特尔的另一个要素而这一点,又恰恰很英国。在窗口目测距离之后,曼特尔迟至三十年后才动笔,不是为了等撒切尔夫人去世,而是要解决技术问题毕竟,虚构艺术不是靠一腔怒火就可以成立的。
尽管灵感来自真实的场景和感受,但曼特尔真正下笔,就必
须尽可能收起主观判断:我并不是这两个人物中的任何一个。杀手来自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冒用水暖工的身份闯进民宅寻找射击点,他包里的金属配件组装起来就是一把枪,枪的绰号叫寡妇制造者;而第一人称叙述的女房主所处的社会阶层、接受的教育程度显然高于前者,她起初还以为对方是个摄影记者,因为他们关心的都是抓到一个好角度。这一组人物存在怎样的差异、矛盾和共鸣,如何在短时间内在他们之间制造张力,这是作家真正关心的问题。一句双关语如何理解,一杯茶要不要放糖,一首歌的历史意味着怎样的民族认同,这些都是作者安排的关节藉此,在杀手等待动手之前,人物关系被一步步推向高潮。
整篇小说极大程度上是被对话而不是动作推动的因为最
重要的动作还来不及发生。对话始终像绷紧的弦,人物之间的对抗与同情随时转化。哪怕他们最后成了事实上的同谋,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彼此之间的鸿沟。杀手清醒地对女主人说,你以为是站在我这边的?你并不知道我是哪一边的。相信我,你根本不知道。而女主人同样不放弃以微妙的词语来羞辱对方的机会:资产阶级,这算哪门子工艺专科学校的词汇呀?她的几乎出于本能的还击充满着温莎式的优越感,因为工艺专科学校也算是个接受高等教育的地方,专收那些进不了大学的年轻人:他们聪明到会说亲缘关系,却只能穿廉价的尼龙外套。
对真实人物实施的虚构暗杀,最终将通往何处?彻底落实或
完全虚化都不是最佳选择。曼特尔把结局设置在开枪之前,悬念定格于半空,但同时又在此前突然荡开一笔,安排女主人领着杀手找到一扇通往隔壁大楼的门,开出一条虚拟的逃生通道。这实在是神奇的一笔,视角骤然从我身上抽离,拉到高处俯视众生。真实与虚构在这道看不见的门里共存,文本也因此跳脱表层情节,被赋予更为深刻的意义:
谁不曾见过墙上的门?那是残疾儿童的慰藉,是囚徒的最
后一线希望。它是濒死者最便捷的出口他的死,不会是被死神捏在手中,喘着粗气发出尖利的惨叫,而是在一声叹息中辞世,如一片坠落的羽毛。它是一扇特殊的门,不会遵守任何支配木材或者钢铁的法则。没有哪个锁匠能挫败它,没有哪个看守能踹开它;巡警会从门前绕过,因为这扇门虽然有形,却只有信徒才能看见它。一旦穿过了这扇门,你回来时就成了天使与空气,火花与火焰。刺客宛若一枚火星,这你知道。走出防火门他就熔化了,所以你永远不会在新闻里看到他。所以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面孔。所以,正如你所知,撒切尔夫人一直活到终老。然而,记住那扇门,记住那堵墙,记住那扇你从来看不到的墙上的门有多大的力量。记住你打开一条缝时从门里吹来的寒风。历史永远会有别的可能。因为有时间,有地点,有黑色的机遇:那一天,那一刻,灯光斜照,远处,靠近辅路,冰淇淋车叮当作响。
历史永远会有别的可能,这是历史小说家曼特尔的典型口
吻。事实上,短篇小说并不是曼特尔经常涉足的领域,只有在创作大部头历史小说的间隙,她才会应《卫报》或《伦敦书评》等报刊的邀约,写几个短篇。不过曼特尔出手往往不同凡响,常常入选各种年度最佳,质量确实远高于数量。这本主打《刺杀撒切尔》的短篇集,便是曼氏多年来十一篇作品的集合(应版权方要求,中译本比原版多收录了一篇《英文学校》)。
翻译这个短篇集的时间,几乎与我本人开始学习中短篇小说
写作的过程同步,这样的安排里当然藏着私心,希望多少能学到一点东西。交稿之后回想,当然不敢说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曼特尔的风格之独特,一定会在记忆里留下不易抹去的痕迹。纵观这十一个短篇,题材迥异,长短不同,但都跟《刺杀撒切尔》一样,属于态度和技术异常鲜明的作品。或许可以这样讲:如果说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以卡弗、门罗等为代表的简约、含蓄、冲淡是世界短篇小说的主流,那么曼特尔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潮流的。
说曼特尔态度鲜明,是因为她始终在不抹杀人性的多面和社
会关系复杂性的基础上,从不回避自己的立场。对于触目惊心的阶层鸿沟、社会矛盾和家庭黑洞,曼特尔不装糊涂,不和稀泥;对中产阶级的改良愿望的幻灭,对于他们的矛盾、纠结和虚弱,哪怕以第一人称叙述(作者本人显然就属于这个阶层),曼特尔也不会放过任何一道豁口,该撕碎的时候毫不留情;对于底层社会的艰辛和粗鄙,乃至其中仍然蕴含的潜能,曼特尔亦能真正做到贴身叙述她笔下的劳动阶层,较少带着知识分子刻意审视的痕迹。在她笔下,无论是一场失败的族裔融合(《很抱歉打扰你》),一桩令人不寒而栗、故意杀人的交通事故(《寒假》),一个被社会潮流异化吞噬的家庭(《心跳骤停》),还是一位处于事业瓶颈、追问写作如何干预生活的女作家(《我该怎么认你》),都很难归入既有的类型,也都逼真地展现了几十年来社会政治问题如何渗入英国的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透过这些文本,我们也可以看到曼特尔鲜明的
技术特点。在视角和意象的转换上,曼特尔总是能做到迅疾而奇特,善于在日常生活描写中突然绽放出超现实的火花。比方说,如果你熟悉曼特尔的历史小说,可能会在《英文学校》的一段视角转换中看到《提堂》开头采取老鹰视角的影子:一阵无聊过去,《旗帜晚报》也看完了,此时尿意袭来。她有一个塑料花瓶,装到半满时,她站到椅子上,小心翼翼地把瓶子摆稳,然后打开阁楼窗户。如果此时有人待在屋顶上,比方说,一只鸟或者一个正在修排水管道的男人,比方说,一只从遥远海面上飞来的海鸥;它会看见一只黄黄瘦瘦的手冒出来,沿着窗框摸索;它会看见有个瓶子在小心翼翼地倾斜,接着,一股细细的水流沿着石板淌下去。
曼特尔的小说,对话往往异常简洁却具有攻击性,下笔堪称
凶狠。她擅用词语双关来造成阶层之间的误会,抓住词语在英国人生活中定义各种微妙关系的特点,极具反讽意味,同时也给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此外,曼特尔在铺陈气氛和设计细节
上都是高手,喜欢在优美奇诡的描写中突然撕开伤口,暴露生活中最残忍的那一面;相应地,她也善于在阴郁、黑色、教人窒息的情节中悄然打开那扇看不见的门,门里汩汩涌出的优美而诗性的描写与前者形成惊人反差于是,光愈显明亮,暗愈显浓黑,作品愈显其异质的美感。
刺杀撒切尔:1983年8月6日
然而,1983年夏天,这个素来颇有教养、购物者和观光客都会绕道而行的角落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在20号和21号的花园后面坐落着一家私立医院,一栋优雅的灰白色建筑盘踞在街角。在首相遇刺的三天前,她到这家医院动个眼科小手术。从那以后,这块地方就乱成一团。陌生人推搡着常住客。新闻记者和电视摄制组堵住了马路,在车道上乱停车,拿不出停车证。你能看见他们在斯皮纳小道上步履蹒跚地走来走去,追着电线和灯光跑,眼睛贼溜溜地瞄着卡拉伦斯街上的医院大门,脖子上挂着照相机。每隔几分钟他们就会簇拥在一起,他们的战袍汇聚成一大团,好像在彼此安慰,什么事也没发生:不过总会出点什么事的,迟早。他们就这么等着,一边等一边咕嘟咕嘟地喝下纸盒装的橙汁和罐装拉格啤酒;他们吃东西,碎屑溅到前胸,污迹斑斑的纸袋子扔进花坛。圣李奥纳多街尽头的面包房上午十点就卖空了奶酪卷,一到正午,什么东西都没了。温莎人聚集在三一广场上,把手中的购物袋往矮墙上一搁。我们都在瞎猜,咱们凭什么这么荣幸啊,她几时才能走啊。
温莎跟你想象的不一样。这里有个知识分子阶层。你一旦沿着蜿蜒曲折的路从城堡上下来,一路走完皮斯考德街,就会发现,这些知识分子并不都是一脑子保皇思想的马屁精;等你穿过交叉路口拐到圣李奥纳多街,没准还能嗅出一点隐秘的共和派气息。当地社会党的投票点好歹能带来一丝聊胜于无的安慰,人们窃窃私语,说这一票投了也白投;他们只能在投票时耍耍心机来表明自己的感情有多么强烈,或者到艺术中心参加几场标新立异的活动来彰显自己的精神。艺术中心是最近刚从消防站改造翻新的,那些自费出版的诗人把此地视为交流平台,一箱箱发酸的白葡萄酒被四处分发;每逢周六上午,这里还开设关于励志、瑜伽和装裱图画的课程。
然而,撒切尔夫人一来,那些异见分子都上了街。
他们三三两两簇拥在一起,打量着记者团,冲着医院大门横眉冷对门口有一排珍贵的停车位,标明医生专用。
有个女人说,我有哲学博士学位
,老是忍不住想把车停在那里。时间尚早,她买的面包刚出炉,还热着;她紧紧抱着它,像抱着一只宠物。她说,各种狠话满天飞呢。
按我说就该来一把匕首,我说,直插她心脏。
你这情绪,她满怀赞赏地说,是我听过的最狠的话啦。 罢了,我得进去了,我说,我在等杜根先生上门修锅炉。
周六也能上门修?是杜根吗?那你真是太有面子了。最好赶快去。如果你让他白跑一趟,他会问你收钱的。他这个家伙是个骗子。可你能怎么办呢?
她从包底搜出一支钢笔。我给你留一个电话号码吧。我们俩都没纸,她就在我光溜溜的胳膊上写了一个。给我电话。你会去艺术中心吗?我们可以碰个头,喝一杯。
门铃响起时我正在把毕雷矿泉水放进冰箱里。我一边放一边想,眼下我们是浑然不觉,不过日后回想起撒切尔夫人在这里的日子,我们将不无快意:在街上交到新朋友,聊聊我们共用的水暖工。大门对讲机照例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就好像有人在线路上放了把火:上来吧,杜根先生,我说。对他还是恭敬一点为好。
我住四楼,楼梯挺陡,而杜根向来行动迟缓。所以,当我很快听到有人敲门时,吓了一跳。你好,我说,你的车停妥了吧?
在楼梯平台上更确切是在最上面一级的阶梯上(而我独自呆在原地)站着一个身穿廉价棉夹克的男人。当时我的想法很单纯,这是杜根的儿子。水暖工?我说。
没错,他说。
他费力地走进来,身上背着水暖工常用的那种包。在客厅的弹丸之地,我们的鼻尖都几乎要碰在一起。在英格兰的夏天,他这一身棉夹克委实太厚,把我们俩之间的空间都给占了。我往后挪了两步。出什么问题了?他说。
它要么哼哼唧唧,要么乒乒乓乓。我知道已经八月份了,可是
没事,你没错,你没错,你可没法指望天气靠谱。暖气片热吗?
有时热有时不热。
你的管道里有空气,他说,我一边等,一边把空气放掉。还是这样好。如果你有扳手的话。
疑虑就是在这一刻爬上心头的。等,他是这么说的。等什么?你是摄影师?
他没答腔。他正在身上摸索,搜遍每个口袋,同时皱起了眉头。
我在等一个水暖工。你不应该闯进来。
你自己把门打开的。
不是替你开的。不管怎么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费事。从这边你是看不到医院正门的。你得从这里出去,我直截了当地说,然后向左转。
他们说她会从后门出来。在这里抓个角度再好不过。
从我的卧室看医院花园,取景得天独厚;只要在我的住所附近走上两圈,就能猜到这一点。
你替谁工作?我说。
这你没必要知道。
也许是没必要,可是如果你告诉我,会显得礼貌一点。
我退回厨房,他跟在后面。房间里洒满阳光,现在我能看清他了:个子不高,结结实实,三十多岁,不修边幅,圆脸,面貌和善,头发乱糟糟。他猛地把包往桌上一扔,脱下棉夹克。他整个人的体积一下子就小了一半。这么说吧,我是自由职业者。
即便如此,我说,你用我的房子,就该付我钱。这才公平。
这事你不能开价,他说。
听口音他是利物浦人。跟杜根,或者杜根的儿子完全不相干。可是他直到进屋来站在门口时才开口,所以我刚才怎么能料到呢?
他完全可能是个水暖工的,我对自己说。我不是彻头彻尾的傻瓜;此时此刻,我惟一在意的就是自尊。先得验明正身人们一般是这么建议的再让陌生人进门。不过,想象一下,万一你把杜根的儿子晾在楼梯顶上,妨碍他及时奔赴名单上的下一户,减少他获取战利品的机会,那他会闹成什么样。
厨房的窗户俯瞰三一广场,此刻那里人声鼎沸。只要我伸长脖子就能看见左侧有个新来的警察,正从克拉伦斯月牙宅邸的私家花园一路小跑着出来。抽一根?客人找到了他的烟。
不抽。希望你也别抽。
合情合理。他把烟盒塞进口袋,掏出一块揉成球状的手帕。
他从落地窗前往后退两步才站定,用手帕抹了把脸;脸和手帕都搞得又皱又灰。显然,踏进别人的私宅也让他不太习惯。我其实对自己比对他更生气。他要谋生,既然有个蠢女人自己把门打开,那你也许就没法怪他闯进来
。我说,你打算呆多久?
预计她一小时以后出来。
这就对了。怪不得街上的嘈杂声越来越响。你怎么知道?
我们里面有人,一个姑娘。护士。
我递过去两张厨用卷筒纸。谢喽。他吸干额头上的汗水。她就要出来了,医生护士正在列队迎候,好让她一一致谢。她将沿着这列队伍走,嘴里念叨着谢谢你和再见,然后蹒跚着从边上绕过去,钻进一辆豪华轿车,扬长而去。嗯,大致如此。我不知道准确时间。所以我寻思,如果我能提前跑到到这里来,就能把准备工作做好,看看角度什么的。
你抓到个好角度能拿多少?
终身监禁,不可假释。他说。
我笑了。这又不是犯罪。
我就是这感觉。
这里有点远吧?我说。我是说,我知道你有特殊的镜头,这里也只有你一个人占着,可你就不想来个特写镜头?
喏,他说,只要我能看得清,距离根本不是问题。
他把卷筒纸揉成一团,四处寻找垃圾桶。我从他手里接过那张纸,他嘴里嘟囔了一声,然后就忙着解开他的包,那是一只帆布大包,依我看,无论对摄影师还是不管哪种生意人,这包都挺合适。可是,当他把包里的金属配件一样样拿出来时,即便像我这么无知的人,也看出这些玩意不该是摄影师用的。他开始组装这些配件;他的手指纤巧灵活。他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歌声几乎轻得像耳语,这首小曲是从足球场看台上流传开的:
你这个利物浦佬,肮脏的利物浦佬,
只有碰上银行转账日才会笑一笑。
你老爸是贼,你妈咪贩毒,
拜托别把咱们的车轮盖也卸掉。
三百万人失业,他说,他们大多跟我们过着一样的日子。这里没有这样的问题吧,是吗?
哦,没有。这里有的是纪念品商店,人人都有工作。你去过高街吗?
我想到游客们在人行道上推推搡搡,争抢那些虚头八脑的旅游纪念品和上了发条的皇家卫士模型。这简直像另一个国家。没有听到楼下的马路上有谁在说话。那位老兄还在哼着小曲,专心致志。我不知道他的歌有没有第二段。他每从包里拿出一个配件,就用一块比手帕更干净的布擦拭,动作轻柔,满怀虔敬,就像弥撒之前,祭台助手擦拭各种器皿。
配件组装完毕,他端起来给我细看。折叠式枪托,他说,她漂亮就漂亮在这里。能塞进装爆米花的袋子里。他们管她叫寡妇制造者不过这回就不是寡妇喽。可怜的该死的丹尼斯
,呃?从现在开始,他就要蛋疼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