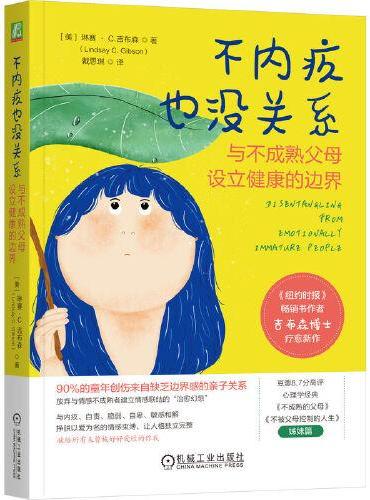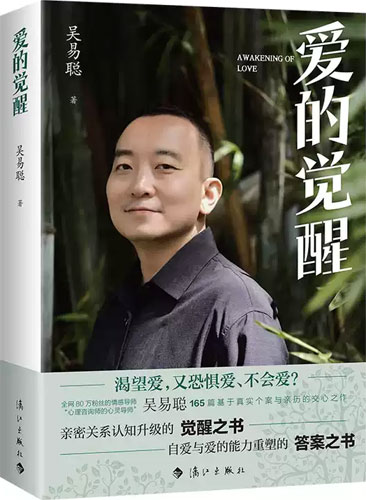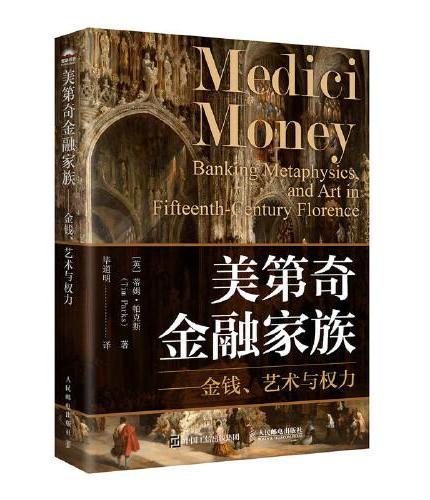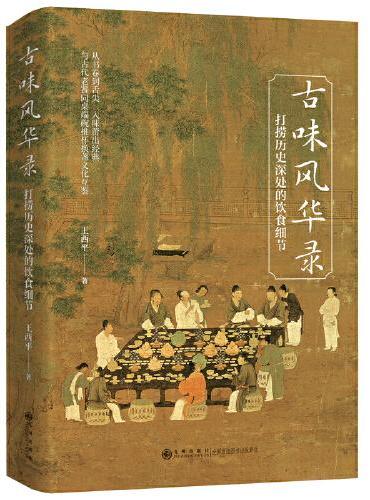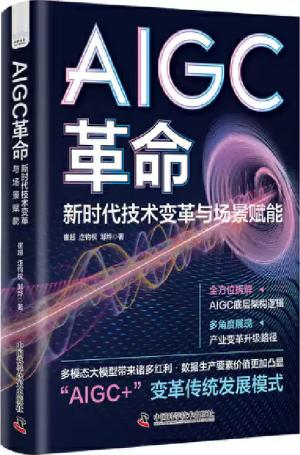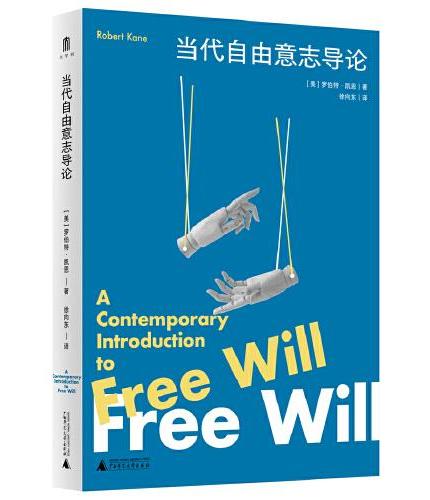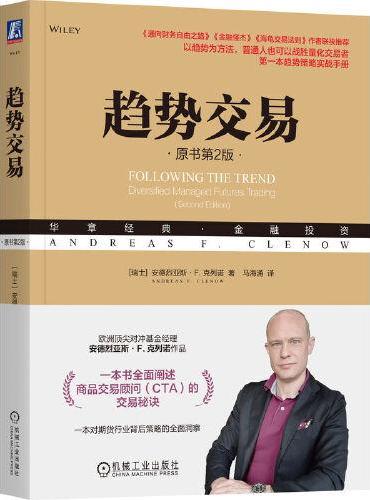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不内疚也没关系:与不成熟父母设立健康的边界
》 售價:HK$
75.9
《
爱的觉醒
》 售價:HK$
85.8
《
美第奇金融家族——金钱、艺术与权力
》 售價:HK$
65.8
《
古味风华录:打捞历史深处的饮食细节
》 售價:HK$
74.8
《
AIGC革命 :新时代技术变革与场景赋能
》 售價:HK$
75.9
《
大学问·当代自由意志导论(写给大众的通俗导读,一书读懂自由意志争论。知名学者徐向东精心翻译。)
》 售價:HK$
74.8
《
(格式塔治疗丛书)进出垃圾桶
》 售價:HK$
96.8
《
趋势交易(原书第2版)
》 售價:HK$
97.9
編輯推薦:
简明的哲学导论:写给没有哲学基础、想要思考大问题的读者,介绍了困扰无数伟大思想家的核心论题。
內容簡介:
某一个时刻,我们会自然地想到关于自我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我与世界关系的问题等,这时候,我们就天然地成了哲学家。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目錄
导论
內容試閱
多年来,我始终在摸索如何让人们对观念产生兴趣,其间碰到了很多困难,本书就是我努力克服困难的结果。在这样做时,我不仅将自己当作一位教师,也当作一位尝试向普通听众解说人文科学特别是哲学之价值的人。实际上,我首先受惠于时代氛围。当今时代的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价值持有一种怀疑态度,正是这种态度向我表明这项任务是多么紧迫。不过,认真一点说,我受惠于多年来教过的学生,正是他们的点头和皱眉让本书最终得以成形。我也感谢我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助教,在使用本书的早期版本来教学时,对于如何才能让学生积极投入,他们提供了第一手的经验。然而,要不是因为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凯瑟琳克拉克(Catherine Clarke)和安格斯菲利普斯(Ang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