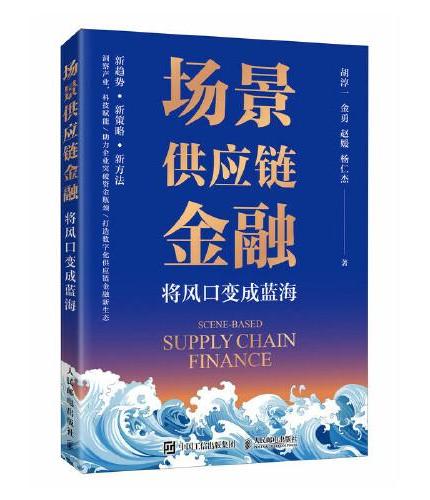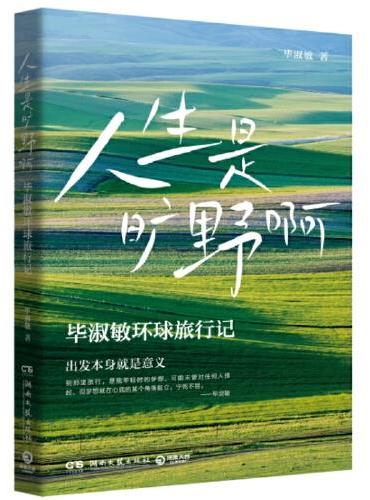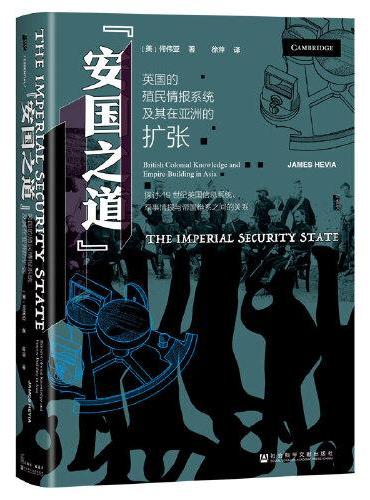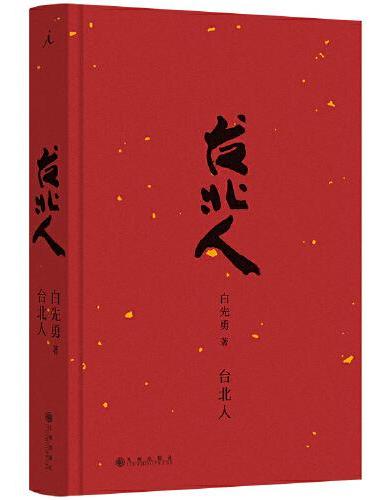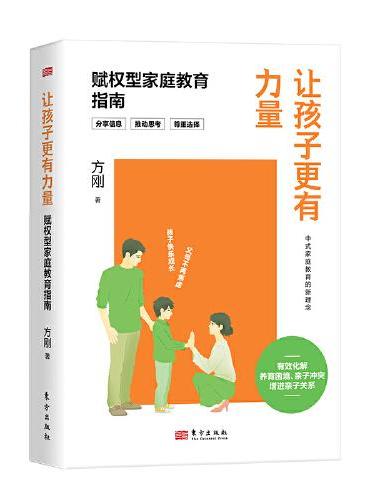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日子慢慢向前,事事慢慢如愿
》 售價:HK$
55.8
《
场景供应链金融:将风口变成蓝海
》 售價:HK$
111.8
《
汗青堂丛书146·布鲁克王朝:一个英国家族在东南亚的百年统治
》 售價:HK$
91.8
《
人生是旷野啊
》 售價:HK$
72.8
《
甲骨文丛书· “安国之道”:英国的殖民情报系统及其在亚洲的扩张
》 售價:HK$
88.5
《
台北人(2024版)
》 售價:HK$
87.4
《
万千心理·成人情绪障碍跨诊断治疗的统一方案:应用实例
》 售價:HK$
132.2
《
让孩子更有力量:赋权型家庭教育指南
》 售價:HK$
67.0
編輯推薦:
学好英语了解英语
內容簡介:
《英语的秘密家谱》带领读者由借字窥见英国的历史,及其他文化与之发生擦撞或者共生共荣的痕迹,探讨英语如何由罗马帝国边陲的番邦土语,演变成走向21世纪的世界语言。
關於作者:
作者亨利希金斯Henry Hitchings,英国人,是语言和文化历史评论家,著有《约翰逊的字典》、《真的不用读完一本书》,同时也是《卫报》《金融时报》《新政治家》等报章杂志的撰稿人
目錄
1. Ensemble 合奏
內容試閱
语言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