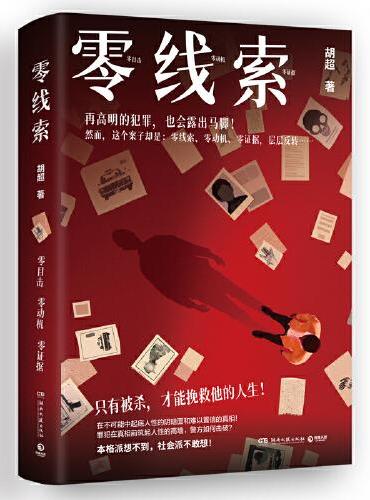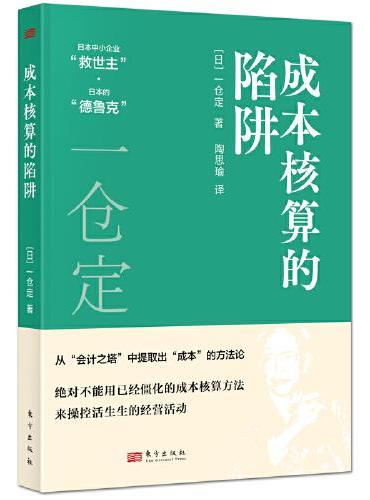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零线索(只有被杀,才能挽救他的人生!)
》 售價:HK$
65.8
《
成本核算的陷阱
》 售價:HK$
46.2
《
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万有引力书系)
》 售價:HK$
103.8
《
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
》 售價:HK$
113.3
《
活力物质:“物”的政治生态学
》 售價:HK$
93.2
《
哪吒传漫画(1-4册)
》 售價:HK$
85.0
《
我是时代的孩童:陀思妥耶夫斯基随笔选
》 售價:HK$
103.8
《
捡来的瓷器史(2024年“最美的书”,从偶然捡到的古瓷碎片中发现中国瓷史的重要瞬间)
》 售價:HK$
186.4
編輯推薦:
知识人的心灵礼物
內容簡介:
本书收录了国际知名学者汉娜阿伦特等人的16篇文章。书中内容涵盖面很广。在政治与社会方面:如以塞亚伯林的《爱因斯坦和以色列》,W.H.奥登的《偏头疼》,加布里埃尔安南的《马勒的重现》,以及汉娜阿伦特的《关于暴力的思考》。这本文选中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分别出自约瑟夫布罗茨基、布鲁斯查特温以及安德列萨哈罗夫。这些文章在知识界和思想界都曾引起了极大的影响;在文学与艺术方面收录了诸如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以及琼迪迪安的《在萨尔瓦多》。罗伯特洛威尔的《两个诗人》,斯特拉文斯基的《生命之泉》以及罗伯特休斯的《安迪沃荷的崛起》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關於作者:
■苏珊桑塔格■以塞亚伯林■罗伯特休斯■加布里埃尔安南■布鲁斯查特温■彼埃尔布莱兹■伊丽莎白哈德维克■琼迪迪安■W.H. 奥登■约瑟夫布罗茨基■罗伯特洛威尔■戈尔维达与大师一起分享思想的艺术和智慧的乐趣
目錄
目录
內容試閱
关于暴力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