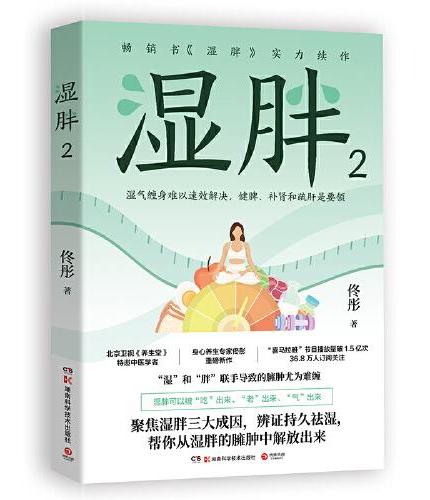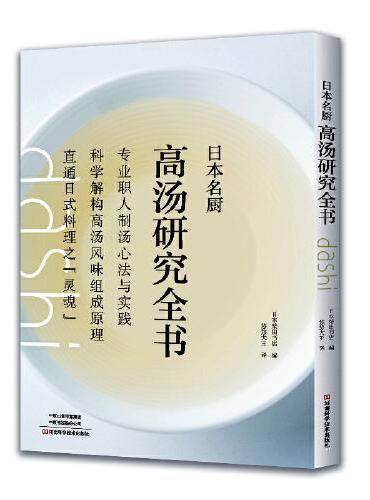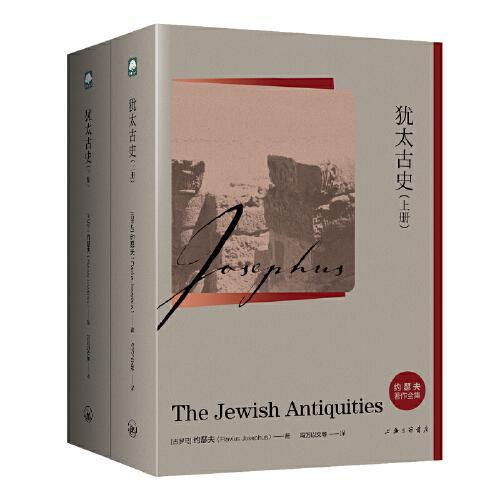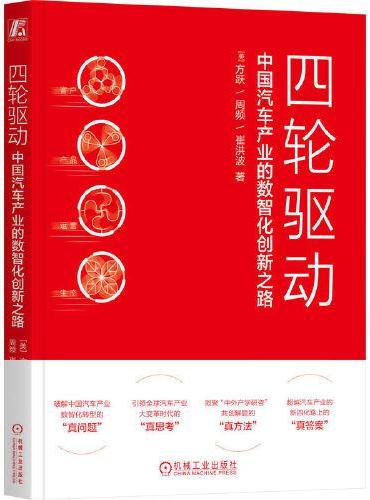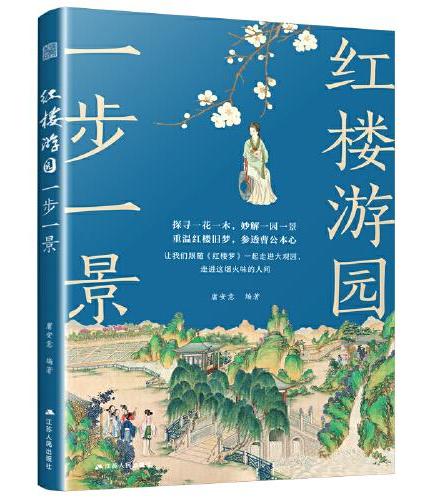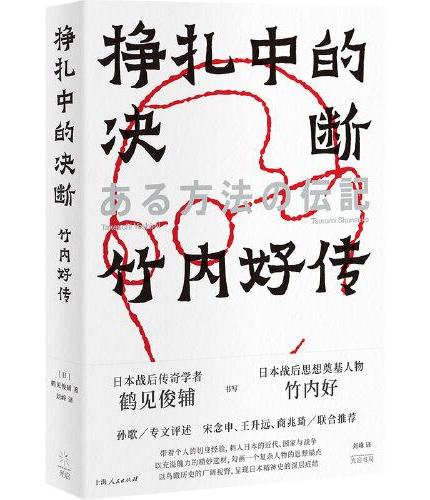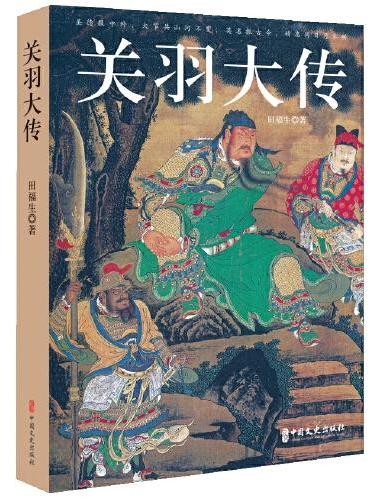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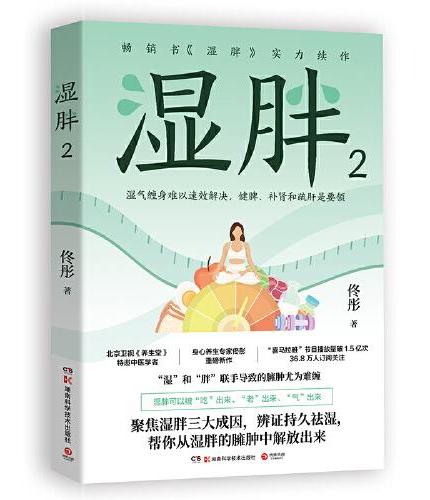
《
湿胖2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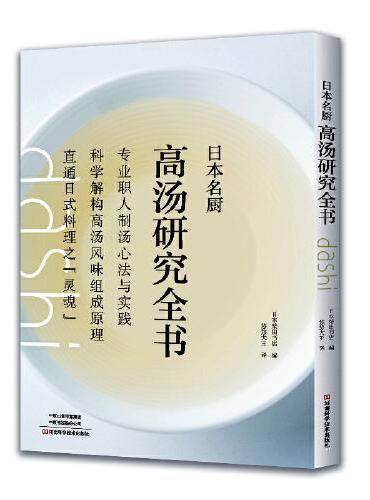
《
日本名厨高汤研究全书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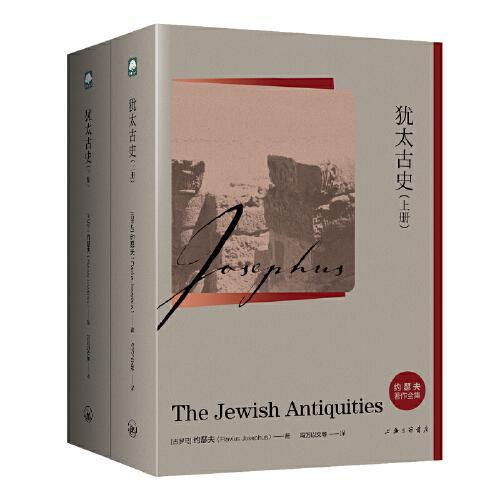
《
犹太古史
》
售價:HK$
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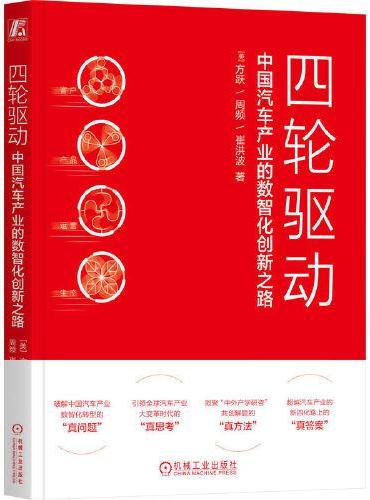
《
四轮驱动:中国汽车产业的数智化创新之路
》
售價:HK$
97.9

《
帮凶:全二册
》
售價:HK$
8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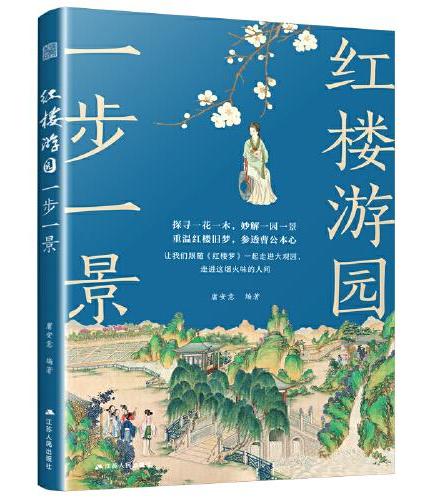
《
红楼游园一步一景:详解红楼梦中的园林和建筑 配有人物关系图 赠送大观园全景图 精美书签
》
售價:HK$
8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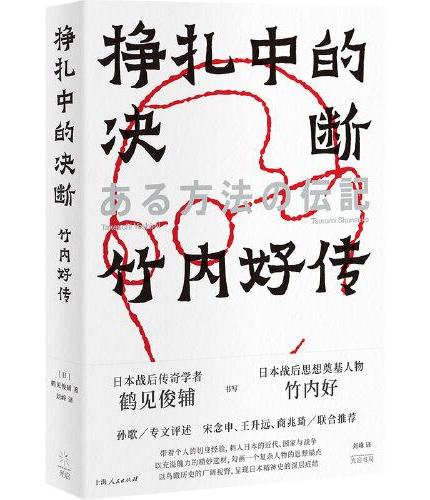
《
挣扎中的决断:竹内好传
》
售價:HK$
9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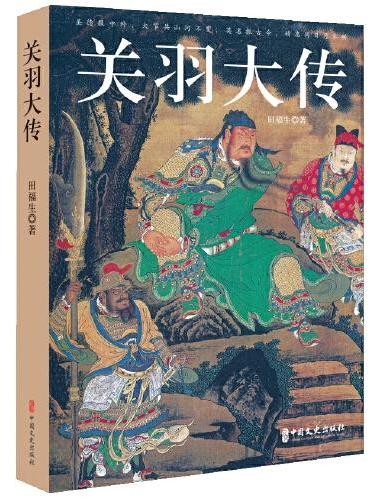
《
关羽大传
》
售價:HK$
96.8
|
| 編輯推薦: |
在随着大海晃荡的船上,我一封又一封地给海外画家们写着信。
日头无论是升是落,都会挂在水平线上,像个大红球。
我眼睛追着光,心想,在地球的背面,有人正陪着我做画家梦。
★ 著名摄影家阮义忠的青春记忆,探讨艺术又一力作
★ 为了那些没有完成的访问记,遗失的画作,未尽的画家梦
★ 来自七十年代的珍贵书信,尽述海外画家的异乡漂泊与追问
阮义忠作为著名摄影家、摄影评论家,对华人摄影界乃至艺术界影响深远,本书为其探讨艺术的又一力作,从绘画角度切入,为读者提供人文美学的全新思考。
访谈完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其中涉及的艺术主题,在当时属于前沿观念,而今仍不过时。同时收入海外重要画家的肖像、手迹及珍贵画作,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史料。书中受访者对往事的追怀叙述,十分生动可感,呈现出上世纪下半叶华人艺术家的生存状态,尤其是旅居海外后的文化冲突和身份思考。
本书探讨绘画而不限于绘画艺术,发问者精心筹划,受访者精辟作答,问与答相激相发,于会心处给人启发。读者不仅可借访谈一窥画家胸襟、素养和观点,更能从中读到他们风格化的印记,及观察和触摸外部世界的方式。本书适合所有艺术爱好者,尤其是那些想成为优秀画家
|
| 內容簡介: |
|
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学画青年的一腔热诚,访问丁雄泉、谢理法、庞曾瀛、廖修平、赵春翔、萧勤等八位旅居海外的重要画家,留下一系列珍贵书信。这组颇具个性的海外画家群像,勾勒出当年华人艺术界的探索与成就。每一篇访谈尽述一位艺术家的旅居见闻、岁月往事、成长轨迹、美学特色,讨论绘画而不仅限于绘画,跨越音乐、建筑、雕塑、摄影等众多领域,在对种种艺术形式的创作和解读中注入人文、生活美学的思考,甚至深入到画家创作理念和情感归宿层面,探寻艺术本质,对艺术往何处去进行追问。本书颇具人文情怀,亦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史料,收入海外重要画家的肖像、手迹及代表作品,为读者呈现真实可感的画家人生,并激励有志于学画的年轻人踏上寻梦之途。
|
| 關於作者: |
阮义忠
摄影家、摄影评论家,阮义忠摄影人文奖创始人。1950年生于台湾宜兰县。1972年于英文《汉声ECHO》杂志社工作,开始拍照。四十年来先后出版《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失落的优雅》《正方形的乡愁》等十本摄影集,并于世界多国个展。论著《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被视为华人世界摄影启蒙书。创办的《摄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杂志被誉为最具人文精神的摄影刊物之一。1988年开始于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任教,2014年以教授资格退休。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之后,成为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的志工。近年来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深圳商报》《生活月刊》等媒体撰写专栏,并在大陆各城市开设摄影工作坊。
|
| 目錄:
|
每画一张画,就像自杀过一次 ----丁雄泉访问记
虽然我来自东方,我已背叛东方 ----谢理法访问记
美术不要忘了做文化作用的事----庞曾瀛访问记
门里门外 ----廖修平访问记
墨韵与灵性的存在 ----赵春翔访问记
将视界放在广大的空间及深邃的时间里 ----萧勤访问记
我个人是没有重要性的 ----李明明访问记
两个故乡,台南和巴黎 ----陈锦芳访问记
附录:
中国的画家蒋彝
阮义忠的线画席德进
|
| 內容試閱:
|
每画一张画,就像自杀过一次
丁雄泉访问记
一度,丁雄泉可能在国际上与赵无极齐名,但是他作画速度太快、作品太多,尤其是水墨与版画,油画创作较少,以收藏家的角度来看,价值便比不上赵无极了。但丁雄泉的画作衍生品、卡片在欧美各国处处可见,甚至比一些西方大师还受欢迎。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他的地位相当高。
在我采访过的画家当中,近距离接触过的唯有丁雄泉。他首次来台时,我把他拉到《汉声》杂志办公室看陈耀圻导演、《汉声》制作的纪录片《七个节庆》。我和他、黄永松挤在小小的编辑部,把窗户用黑布遮起来,以十六毫米放映机投影在白墙上。看完后出门,他跟我讲了这么一句:安东尼奥尼拍的中国太冷,你们拍的这部台湾却太热!这就是丁雄泉,语不惊人死不休,句句正中要害。
他爱送人礼物,从纽约带来一瓶香水,说是要给我的女朋友。他还提议跟我互换手表,以资纪念。我可没答应,因为他戴的那只极其昂贵、号称世上最薄的机械手表,而我的芝柏表虽也算名牌,价格只及他的几分之几。
他是看中了我那只表的设计,根本不在乎价差。这就是他。只要是美的,从美食、美物到美女,他都要追求。跟他通信是件愉快的事儿,因为他总把心中话无拘无束地彻底表白。跟他在一起,大概所有人都会忘了矜持,禁不住放肆起来。也由于如此,他三次来台,身边的酒肉朋友愈来愈多,埋单的总是他。他数度邀我去夜店狂欢,我都兴趣缺缺,后来实话实说:我很喜欢你,但围绕在你身边的人实在不敢领教。他没生气,只是笑笑:你还太年轻了!
第一次处得很愉快,第二次很多场合我都没奉陪。第三次他来台开画展,我们应某杂志之邀对话。在展览现场见面时,他变得陌生,客气地对我说:真没想到,你放弃画画,现在竟然成了鼎鼎大名的摄影家!
丁雄泉很少跟人谈私事,对他的进一步了解,还是透过《生活》月刊的《家书》别册。在他于一九七〇年代给二哥月泉、三哥秋泉的信函中,吐露了深邃的眷恋。就是这些信让我明白,自号采花大盗的丁雄泉,在狂放不羁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纯真的心。
月泉、秋泉二位兄长:
来了,来了,终于来了,每次接得家信一则是忧,一则是喜,见到了仁泉大哥的来信,恍似一把火把我全身烧焦,眼泪隐隐地在眼中要想大哭,但小孩、老婆都望着我,我不能哭,一哭就无控制,或许会哭上三天。自从离开你们到现在还没哭过,心中积了无数的泪,遭遇过太多的伤心事,化愤怒为力量,化悲哀为爱情吧!
母亲一定是去了,好在她老人家也是好福气。杜甫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年纪老些的人对死看得淡一些。昨夜整夜失眠,我感觉到好像针刺,我尽量想法子使得自己平静,约朋友大吃一顿,想想快乐的事情。太悲把人刺激变成疯狂,当然我无法忘记母亲的一切,尤其在外,工作半夜回家,小孩老婆都已安睡,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黑暗中想想往事,想想上海你们。有时极想要坐在母亲身旁,坐上三日三夜(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于纽约)
在这里,也借《家书》的简介将他的生平略微呈现:
丁雄泉,画家,诗人,一九二八年生于江苏无锡,成长于上海。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有过短暂学习,但自认是一名自学的素人画家。一九五二年移居巴黎,结识了眼镜蛇画派(Cobra Group)成员,建立深厚的友谊。六年后移居纽约,与美国的波普画派及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家们颇有渊源,然从未认为自己属于任何艺术派别。移居美国后采用一些新媒材创作。作品典藏于许多世界知名美术馆与基金会。发表过十三本诗集与画册。于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七日逝世于纽约。
我访问丁雄泉时,用的不是邮简,而是信纸。他书写像画符,每个字都又大又潦草,一个问题可以回答好几张纸。也因为如此,所有来信被我集中保留,单独放在一个大信封袋里。牛皮纸上写着左营邮政789414号。就是这几个字让我想起,当时的我是个小水兵,只能趁船舰靠岸时,专程到左营邮局取信。
在随着大海晃荡的船上,我一封又一封地给海外画家们写着信。日头无论是升是落,都会挂在水平线上,像个大红球。我眼睛追着光,心想,在地球的背面,有人正陪着我做画家梦。
(丁雄泉访问记是我于一九七二年秋末开始与他接触,获得他的首肯后,于一九七三年四到七月的四个月期间,以密集航空邮件往来完成的。)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纽约城
义忠先生:
接来信,知道你正在为《幼狮文艺》介绍海外画家做访问工作,可惜我不同意。访问应该是真人面对面,像谈爱情一样方有味,相谈时有不断的趣味及智能产生。像你这样提议的访问工作,好像一把胡琴自拉自唱,令人坐井观天,读来也似老太婆念经或老头子拉屎。
好像已有数年了,有不少朋友要为我写介绍都被我婉拒,像刘国松、席德进、秦松、何政广等人。原因不多,第一,所有介绍文章都太公式化,读来乏味,而且又像是吹喇叭,肉麻当有趣。我在海外,看到不少介绍文章。而这些文人画家都是些走江湖,三脚猫。在读介绍文章时心中突然涌起荒凉之感。
何况我又不是耶稣,并不愿意及喜欢人人爱我的图画,我的画就是我的生活和精神。
希望你原谅,我喜真人真言,痛恨假惺惺,就连美丽大小姐也不要,若是她来一个假惺惺。
匆匆祝好
丁雄泉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纽约城
义忠先生:
又接来信,知道你也是画图的年轻人,很好,很好。
我说的三脚猫不是你,是余光中。他也写些艺术评论介绍之类,我看了心中觉得要吐三口痰。当然还有那些老太太型的画家与酱油味精大师傅,都令人倒退三步。我对于牛郎织女的爱情也是鼻子发霉三天。
明年夏天东南亚一行,来台湾七日。偷偷摸摸去绿灯户来一个十八摸,月亮弯弯照九州岛,几家欢乐几家愁
据说去中国大陆旅游,要来一遍最近十年来的自我介绍,这真是洋山芋搓皮,莲子掏心,也是叫人发冷三尺。
当然,我并不是胖女人装瘦,丑人作怪的骚腔。没有一个人能写介绍我的文章流畅似夏雨,轻得像天女散花,连接似七巧星。我自己也是写了许多诗,总觉得不容易写,读者看了还不是往垃圾箱一掷为快。
十五年来抽水马桶里洗笔,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大片爱情变成一片片花天酒地,自作自受好不快乐,他人事管他娘。
祝好
丁雄泉
一九七三年元月十日纽约城
义忠先生:
附上展览会目录一册,昨夜展览会开幕后和许多画家去中国城大吃一顿,令人痛快一次。
知道你大忙在和许多人接触及写访问,你所说的中国画家我都认识,只是点点头而已,从无谈心,高谈阔论。原因,我不喜欢他们的画,处女型、寡妇型、半吊子型、坐井观天之大情人,小裁缝的妹妹也来一笔。
你可告诉痖弦,将来我用丁雄泉的笔名写一篇采花大盗访问记。我觉得请人抓痒还不如自己来洗菜,自己的花还是开在自己的绿叶上,不是我拒绝你的提议,有许多微小又微妙的东西是不能和人说的,只能像小溪一样的慢慢地流出来写出来。
总而言之,你不能写我的访问,一写出来非得罪上上下下数十人之多,痖弦有没有这个胆量登出来?当然我也可以用不着辩论、不管他人事的方式写,像唐伯虎一样。
祝好
雄泉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日纽约城
义忠老弟:
刚从南美巴西归来,眼见老父仙游回去。我又是红眼、肺炎、牙痛、冷汗、噩梦,好像也要乘风归去的样子。奈何数位医生不断地救,又慢慢地好起来。还好,只是四十五岁,要是五十四岁也是一脚登天。
你有没有过替死人换衣服,把一个人放进棺材的经验?我从前写了很多关于死的诗,都是浪漫的。例如:
我死后放一把火
抛进抽水马桶
请拉一把
如今,吞了一座大火山,根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你来信上提出的问题很有趣,但还不够特出和稀奇古怪,也不大胆,更没有屈原的天问。你用不着把我当一个人,像一阵春风就可以了。若是问题提得多和好,我愿意接受你的访问,但不要提及当代活的中国画家,四海之内,皆醋瓶也。
五十个问题像一首诗,像一座原始森林,像五千里路上的白云,像五天的暴风雨。不论任何问题,都能答复。你到底有多少想象力?有没有连贯性?问题里当有大树根、绿叶、鲜花、蝴蝶、春天、轻风、太阳光,最后像一只苹果打在头上,得到最后的答复。
祝好
丁雄泉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三日纽约城
义忠老弟握手:
你最近两封信写得好极了,千帅、万鲜,又像初夏的阵雨把你自己年轻的青春不断地暴露出来,像不像野猫叫春?
我的第一本诗集(一九六一年)《我的粪及我的爱情》;
第二本(一九六四年)《一分钱的生活》(瑞士出版),共印两千一百本。内有六十一首诗,七十张石版画(十六个国家的名画家,共有二十八个画家的作品),其中有一百本是精装手工纸,每张石版画都有画家亲笔签名,现售价三千五百美金(美国国家科学院也买一本收藏);
第三本(一九六七年)《中国的月亮》;
第四本(一九六九年)《酸辣汤》;
第五本(一九七二年)《绿了芭蕉》;
第六本(一九七四年)《早晨》;
第七本(一九七四年)《游山玩水》;
第八本(一九七四年)《统统都在我的脑袋里》;
就要出版第九本(一九七四年)《红嘴》,在香港印,一首诗长六十页,加上五彩版有七十二张之多,完全仿照电影杂志,共计两百页(美女如云)。
附上犹太国特派专栏文学家兼诗人阿骂死的采访特稿,你看得懂犹太文?《纽约时报》有两次特访稿,也是全页。
现在根本不记得一切电话号码,昨天做的事情差不多都忘记,这样才能四大皆空。唯有这样,才能迎接万象更新不背臭包袱。唯有这样,才能不恨他人也不吃醋。唯有这样旦如朝云,才能暮如行雨。唯有这样浑浑噩噩,才能阳春白雪。唯有这样挥金如土,才能扬长而去。
好吧!把题目都踢过来,把吃过的空瓶隔海掷过来,把摸过的奶奶香气也推过来,垃圾马桶一切都要,我胃口甚好又大,想来必是春天了吧!
雄泉
阮义忠:打从您画画到今天,您是怎么画过来的?
丁雄泉:乘飞机飞过来。
阮义忠:您在您的画中画些什么东西进去?
丁雄泉:吃喝嫖赌、酒色财气,样样都来。
喜怒哀乐、甜酸苦辣,样样都去。
阮义忠:您愿不愿意向任何人或特别的人解释您自己和您的艺术?
丁雄泉:和一个陌生的妓女做爱,就是解释我自己的裸体和我爱情的艺术。
阮义忠:有没有因为一个女人和您的关系,而影响您的画风转变?
丁雄泉:绝对没有。我自己是一匹瀑布,女朋友、女姘头像蝴蝶、蜻蜓一样飞来飞去嘻嘻哈哈,我是一棵大树,开花春风得意笑口常开。女人就像小鸟,在我的肚皮上叽叽喳喳。
阮义忠:您会不会把爱情的感受拿来入画,或者把做爱的经验画出来?
丁雄泉:爱情不光是指男女之间的爱。我爱海洋,爱大蒜,爱春天,更爱美女,尤爱猪肚。酸辣汤加水饺是和三十岁妇女一样有劲。昨天看了一阵大雨,夜上又看大小姐出浴,今晨吃水饺,果然画出一张好画。走在马路上看见一些穿迷你裙的大小姐轻飘飘,我的马路就是一张画布,大小姐就是五颜六色的颜料飞来飞去。
阮义忠:从您开始画画已经画了多少画?卖了多少画?毁了多少画?留了多少画?有多少中国人买您的画?有没有得过什么奖?
丁雄泉:已画了两千多张,卖了三百多张,毁了一千多张。有两个中国人买过我的画。得过一个古根汉奖(一九七〇年,奖金一万美金《裸体美女画》)。
阮义忠:听说您还画裸体美女,又画中国画,也画抽象画,三种不同的主题不同形式的画,是不是真的,为什么?
丁雄泉:我的胃吃天上的鸽子,海中的黄鱼,地上的猪。
我的舌说法语、英语、国语。
我的身体和金发碧眼的女人、红发绿眼的女人、黑发黑眼的女人做爱。
你有没看见天上的虹也是红、黄、蓝。
阮义忠:您认为懂您的画的人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还是根本没人喜欢最好?
丁雄泉:当然是根本没人喜欢最好。等将来我有足够的钱供养我一生的时候,我一面画一面撕掉,根本就是逢场作戏。好与坏根本是无聊的。为什么世人还没有批评这些风吹得美,那些雨下得不够巧?
阮义忠:您希望自己的画根本没人喜欢最好,那干吗没事开个展览,没事出个画集,是不是想骗钱?
丁雄泉:我是一棵大树,一年四季不断地开花,心里并不希望每人来看我的花。我并不是耶稣和妓女,要人人都来爱我。我开我的花,我画我的画。你喜不喜欢是你自己的事。
阮义忠:以今天的艺术潮流来看您的作品,您的地位是处在潮流之前,还是潮流之后?
丁雄泉:这问题太小孩子气。
潮流这名词用在投机人的身上才妙。对我来说是:昙花一现的树倒猢狲散。
阮义忠:如果有人说您的画是抄袭某某人的,您会不会生气,有多少人的画和您一样过或很接近过?
丁雄泉:我认为我自己是一座火山,一匹瀑布,一阵狂风。总是不断地激动,不断生长。你不能说这块云抄那块云,天上的云都是抄来抄去的,你所说的抄袭都是理智的人做的,像我非常情感的人是不做的。
你有没有看见过一只豹在摹仿一只猪在马路上走路?
阮义忠:保罗詹金斯(Paul Jenkins)和莫里斯路易斯(Morris Louis)算不算您的同路人,山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是不是你们的带路人,把你们四个人合起来展的话,您以为如何?
丁雄泉:薄颈根(Paul Jenkins)的画太油腔滑调了,像一个流鼻涕的卖油郎,油腻得像小飞仔的飞机头上涂满生发油,把蟑螂、蚊子一齐跌落千丈。
马律师路( Morris Louis)的画是妙想天开,太阳光高照的时候,突然数道鲜艳彩虹异路同归,一大片天空任由您呼吸。他是美国开国以来第一大师。
三方雪(Sam Francis),他可以说是半个宋朝人,静似皓月当空,他的眼睛比天还蓝,他的画常使人恍然大悟。他是美国第二个大师,也是全世界的画家中第一个能表现出色即是空,空即色的人。
我的画像天女散花,性交后一刹那的星光灿烂。像裸体人轻飘飘,像春风轻轻吹。飞呀飞,没有上帝飞呀飞,没有政府飞呀飞,没有敌人飞呀飞,不欠钱呀飞呀飞,不用护照飞呀飞,不要付房钱飞呀飞,快活死了。
若要四个人合展,我一脚把薄颈根踢掉。三方雪不能算带路人,因为我们不是跟班。他是从马跌死(Matisse,通译马蒂斯)那边成长过来的,经过日本的绘画和中国哲学的影响,产生了中西合璧、由西到中。我也是中西合璧、由中到西,故我们的世界是十分相近的。假如我们四个人同乘一辆公共汽车,每人的呼吸是互相呼来吸去,所看见的风景也是大同小异。
真巧,现在正在美国作五大城市的博物馆巡回展览的新鲜空气画派,由毕次堡咖喱鸡博物馆通译匹兹堡卡内基博物馆主办,三个人每人十五张大画(三方雪,我,和一个美国女画家穷蜜姐儿Joan
Mitchell[通译琼米歇尔]),四十五张大画一路上开过去,像一大片树林跟着大山。春天的桃花,夏天的莲花,秋天的桂花,冬天的梅花,花天花地处处闻鸟叫,红黄蓝紫青,莺声燕语,大山中有飞瀑,飞瀑中有云雨。
此博物馆馆长主办的动机和你的意见十分相像,相隔一万里,是不是心心相印?
阮义忠:您的抽象画看起来像手淫射在墙上的精液,是不是打算一直这样画下去?
丁雄泉:手淫都是文人终身的玩意儿,冷冷的,静静的,理智的。我是一个强盗,自称采花大盗,热热的,动动的,情感的。画上的颜色多至数十种,完全像一个夏天的花园,红黄蓝白黑响遏行云。最近我的画都是轻飘飘在花丛里飞来飞去。
一个人的精液真是太少了,差不多和眼泪水一样少,手淫是一种温柔的技巧,我认为扬州八怪的画像手淫,像在人行道上看花园。想起了梅花画梅花;想起了坐在公共汽车上的小姐就手淫起来,与她在冰箱里蠢蠢欲动,飘飘欲仙,一切都是假的。
或许你说的是在这个射字上,我认为射字不够正确,我是喷。喷出万紫千红的花,我的胃是一个地下海,画图的时候总是跳进画里面,全身烫热,像一匹瀑布一气呵成,或像喷泉把甜酸苦辣(分了又合一起,合了后又分,像宇宙造星)一齐喷在蓝色天空。蓝色天空也、我的画布也、我的精神。
阮义忠:听说您心中越是不开心越是画好画,是不是真的?
丁雄泉:把心中的酸气、怒气、屁气像弹棉花一样弹出来,织成雨过天晴的世外桃源,怎么会不高兴?
阮义忠:您的画是不是一点也不受日新月异的美国社会干扰,纽约新鲜事天天有,对您是否都不管用?
丁雄泉:美国纽约的螳螂和老鼠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多得摇头像电风扇。纽约每星期都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展览,我认为一点也不新鲜,都是挖空心思的老处女,弄一些碎石、枯柳来一个迷魂阵,装腔作势地包包小脚,用一些颜色涂涂地板。
新鲜就像一棵大树,春天来了樱花满开,雨过天晴太阳光在碧蓝的天空直射下来,把一切照得红红绿绿。说得更露骨一点,新鲜一个生产后的母亲。
阮义忠:您画画前和画画后有什么不同?
丁雄泉:三十三次黑变白
我画画以前我是男人,我画画以后我是女人
我画画以前我是枕头,我画画以后我是孔雀开屏
我画画以前我是夏天,我画画以后我是春天
我画画以前我是老虎,我画画以后我是蝴蝶
我画画以前我是头发,我画画以后我是青草
我画画以前我是桃花,我画画以后我是花粉
我画画以前我热,我画画以后我昏倒
我画画以前我是夜晚,我画画以后我是白天
我画画以前我是地球,我画画以后我是太阳
我画画以前我是大山,我画画以后我是狂风
我画画以前我是冰箱,我画画以后我是火炉
我画画以前我是茶叶,我画画以后我是烫茶
我画画以前我是橘子,我画画以后我是橘子水
我画画以前我是钢,我画画以后我是桥
我画画以前我是木,我画画以后我是船
我画画以前我是酸,我画画以后我是甜
我画画以前我是树,我画画以后我是树林
我画画以前我是摩天大楼,我画画以后我是野花
我画画以前我是镜子,我画画以后我是天空
我画画以前我是冰,我画画以后我是雨
我画画以前我是冰淇淋,我画画以后我是云
我画画以前我是大海,我画画以后我是露水
我画画以前我是大火,我画画以后我是夕阳
我画画以前我是大河,我画画以后我是瀑布
我画画以前我是影子,我画画以后我是早晨
我画画以前我是牙齿,我画画以后我是蜜蜂
我画画以前我是烟囱,我画画以后我是浮烟
我画画以前我是火车头,我画画以后我是彩虹
我画画以前我是愤怒,我画画以后我是雷响
我画画以前我是蛋, 我画画以后我是鸡
我画画以前我是烤鸭,我画画以后我是饭店
我画画以前我一千岁,我画画以后我是婴孩
我画画以前我及时行乐,我画画以后我乘风而去。
阮义忠:您打算什么时候开个回顾展,要您选地方,您选哪里?
丁雄泉:一想起回顾展就脸红,我一直往前飞,你有没有看过一架飞机开倒车?
选地方,当然是坟墓。可是我死后也不愿有坟墓,早在十年前我写在一首诗里我死后一把火烧成灰,往抽水马桶一倒,一拉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有一个女朋友的母亲也是画家,读了我的诗她要她的女儿把她烧成灰,倒在她夏天常去的海滩上,结果她死了,她变成灰,我还和她的女儿一起去海边游水,我们裸体躺在白沙上,我还开玩笑说:想不到你妈妈的胸脯这么软。
阮义忠:能不能谈谈您的诗,通常什么情感刺激了您,才会动笔写诗?
丁雄泉:自己是一座火山满盖白雪,不知在什么时候会突然爆发,把白雪喷上天变成白云。
上大饭店大吃一顿,甜酸苦辣一齐倒进胃里,又去厕所大解放,肚子空空如也轻得可以飞了,这时只要大叫就是好诗。
阮义忠:说起吃,怎样才算大大有劲?
丁雄泉:先来一碗百步追魂(毒蛇)的血胆,加上金门大曲混合的开胃酒。
炒蛇舌加韭菜
炒蜻蜓尾加杨柳
炒猪犀子加向日葵
炒象鼻加桂花
炒金鱼颊加桃花
红烧马屁股加冰糖
红烧老鼠奶加白雪
红烧蚂蚁加青椒
红烧雌老虎加醋
水果,冰冻爱情豆腐
阮义忠:有一天您的画没人要了,您的诗没人看了,再也没有人提起您了,落魄,潦倒,您打算怎样?
丁雄泉:你指的这类人,乃电影明星、政客、天主教神父、和尚、生意人,都是自以为人中龙凤,挤眉弄眼,千娇百媚的大忘八蛋。
我的画根本不要人看,我的诗也不要人看,根本没有人知道真的我。我自己一直感到非常落魄,非常潦倒。因为落魄,孤注一掷。因为潦倒,四大皆空。我的心好比天上的白云,与那些走在马路上的家伙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阮义忠:一幅好画,一首好诗,有没个标准,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作品才算好?
丁雄泉:没有标准。
好的画好的诗不是用冷眼旁观可得,马路上拆字先生写不出好诗,马路上的画像师画不出好画。好也没有什么稀奇,作品到了一种境界无分好坏,喜爱不喜爱也是你自己的事。
我讲自己的心得:先把大衣、汗衫、臭袜子一件一件脱掉,在大海里泡上一泡,再在大太阳下烧上一烧,再把你眼睛张开来望望蓝天,当你看蓝天自己也变成蓝天,那时候的白云就在你肚皮上飞来飞去。当你看大山,你自己也变成大山,老虎和梅花鹿在你的腋下奔来奔去。当你看大海,你也变成大海,鲸鱼、老鼠斑鱼、黄鱼、金鱼在你的嘴里游来游去。当你看到一棵大树,你自己就是一棵大树,从地中跳出来,樱桃、梅子、荔枝从你的手臂滑下来。
怎样才能变:就像天上的云雨,分与合,分了又合,合了又分。分是表现,把自己展成千千万万,合是吸收,叠结成网。这样分了又合,合了又分,把你周围的一切都合了去,就是太阳、月亮。马路上的小草、露水,狗尿、桂花也成了天作之合,或许早已合成了,你根本没有看见,对你没有什么关系而已。
阮义忠:一张好画又到底有什么好法?
丁雄泉:像一个好朋友,当你心里不开心的时候,它静静地陪着你,把天上的白云拉下来给你,把雨倒在你的杯子里,把彩虹推到你的屁股上,这样你的心花就朵朵开了。
阮义忠:有没有令您佩服的当代中国画家?为什么?中国人当不成好画家吗?
丁雄泉:据说好酒是不酸,有才气的人是不争风吃醋,中国五千年以来小气的人太多了,不是做皇帝乱杀人,就是做奴才乱磕头,碰一碰破口大骂,摸一摸饱以老拳。一动不如一静、一静不如一睡,睡吧!我们的老狮子,睡了五千年再来一个五千年。
阮义忠:如果耶稣也是个画家,你会不会入教受洗信上帝去?
丁雄泉:耶稣我从未见过,只是见到一些图片或教堂里的雕刻而已,在我的感觉上耶稣只是一根棒冰。
阮义忠:如果有人要为您立铜像的话,您希望立在什么地方?
丁雄泉:乖乖,不得了。最适当的地方是公共厕所的门口,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最真实的地方,大家都来这里脱裤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阮义忠:以您今天的艺术成就,如果以军阶表之,应该是什么阶级?少将、中将,还是上将?
丁雄泉:当然是小兵了,当了七星大将不如去死了算了,假如一定要活的话,那真俗不可耐的烂,像毕加索真是烂得像一只鸡,连骨头都烂出来了,假如他早死四十年,还可以说是个大画家。最后四十年的作品,像生了杨梅疮的肥女,像一块猪油贴在这里,搭在那里,像一只蟑螂一样地奔来奔去。我看了常把刚吸进去的新鲜空气都呕了出来。多可怕呀!一个百孔千疮的美人向你做媚眼。
阮义忠:您说毕加索这么烂,那普天之下有没有比他更烂的人,当代有几位画家您觉得不烂?
丁雄泉:一只过了九十天的老苹果早已烂了,一头牛过了九岁也是上气不接下气,毕加索若是樱花一朵,那真太美了。自从一九四○年以来,他一年不如一年,最后什么也没有,满画都是垃圾和技巧,俗又熟,像一堆臭黑的骨头。巴黎每年的五月沙龙就可看到每年当代画家最大最好的出品。不要说第一流的年轻画家比他好,他的画连第二流也比不过。讲颜色没有,气韵没有,境界没有,热情没有,虹彩没有,新鲜空气没有。大家都同意一个十九岁的女人和一个九十岁的女人,哪一个美丽。
阮义忠:这样说来,毕加索、达利、夏加尔三人由您来打分数,您给他们几分?
丁雄泉:毕加索一分
达利半分
夏加尔零分
阮义忠:那由你看来,石涛、八大、李白、杜甫哪一个最该死?
丁雄泉:世界上的人的精神、学问、爱情、理想,每每不同而四通八达千变万化。有一些人老是坐在那里,有一些人一辈子都在走,有些人跳,有些人奔,更有些人飞。
李白一直都在飞(黄河之水天上来),杜甫一生都在走,走来走去走不出大门(朱门酒肉臭),杜甫像一棵树生不出香蕉和橘子,只开一些没有香味的白花。李白是一朵白云,杜甫是一杯苦茶,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天差地远根本不能相比。
八大一生下来就是飞的鹤,腾云驾雾的得意忘形。石涛像一棵不开花的野草,在风中装腔作势,僵硬思索,重重叠叠。石涛一开始作画就搞趣味,搞趣味恰似抓痒,抓了一生还是蓬头垢面。
现在全世界的画家在搞趣味的,不知千千万万喂!你这个屁股怎么画的?那座大山真是有趣得很。嗳!这种新花样还没人画过,快快画!快快开展览会,不要被人偷去了。一个伟大的诗人、画家、音乐家绝对不计较技巧,有比技巧更好的东西。当然还有些坐在家里描画的人,极像老太太打毛线。
我到现在一直还没看见过一张惊天动地的石涛,石涛的画张张假的,就是石涛自己画的真迹也像假的一样。假的画和假钞票一样,在有些国家里是要枪毙的。
阮义忠:您说伟大的诗人、画家、音乐家绝不讲技巧,有比技巧更好的东西,那这是什么?
丁雄泉:又要讲一座大山。
对诗人来说,一座大山常常下雨,但又岭上多白云,雨过天晴彩虹开。
对画家来说,一座大山满开红红红红红、黄黄黄黄黄、紫紫紫紫紫、青青青青青、白白白白白的花,蝴蝶千千万万。
对音乐家来说,一座大山瀑布千匹、莺声燕语,谑浪笑敖,一气呵成。
一座大山只有秃树枯草有什么用,不下雨,没有云。不开花,没有蝴蝶。没有瀑布,不洒脱。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诗人、画家、音乐家合在一起。
阮义忠:您有没有自己一套很特殊的技巧?
丁雄泉:吐痰。
阮义忠:您有没有伟大的理想,假如给您无比的权力,您怎样改造世界?
丁雄泉:第一步是把全世界的钞票烧光。
阮义忠:假如现在给您一百万人,您要他们去做什么?去爱人?去打仗?
丁雄泉:把万里长城拆掉。
阮义忠:您有没讨厌的事?
丁雄泉:常常有太多的压力,我十分希望有九个身体,一个身体随便怎样总是不够的。
一个身体在东方吸气
一个身体在西方吐气
一个身体整日微醉
一个身体在月光下的云上做爱
一个身体裸体雨中草上飞
一个身体去银行兑现千万美金支票
一个身体与侠客大吃大喝
一个身体和蝴蝶随风飘流
一个身体和小孩一起哭
阮义忠:还有没有更令您生厌的事?
丁雄泉:有。
热眼看世界一切太冷
我要把天空漆成黄色,树漆成粉红,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都漆成金色,共产主义国家的人都漆成红色,自由主义国家的人都漆成七色彩虹。把全世界的汽车都推到大海里,把全世界的冰箱都抛到大山顶上,让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吃到新鲜的水果。
阮义忠:你打算到几岁才不画画?
丁雄泉:我死了以后还是在画画,你信不信?
阮义忠:那你希望什么时候死?
丁雄泉:每次做完爱的一闪,总是希望马上死。
阮义忠:一定要您死,您选择哪一种死法?
丁雄泉: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阮义忠:让您再活一遍,你打算怎么活法?
丁雄泉:天从人愿变成一条大鲸鱼一生不穿衣服,大大圆圆,光光滑滑,闪闪湿湿,在大海底下飘飘欲仙。只是做爱、做爱、做爱。
阮义忠:要是您有一天不能做爱了怎么办?
丁雄泉:作一颗灰尘躲在花蕊里。
阮义忠:您失恋过没有,失恋过几次,每次都是甩了女人,还是女人甩了您?失恋时您如何打发自己?
丁雄泉:我自己就是一个玩具,玩女人时也被她人玩,玩腻了就甩,不管谁甩谁。失恋?那是处女的玩意儿。
阮义忠:何谓爱?
丁雄泉:一脚把自己踢进冰箱里去立立,
一拳把自己揍到白云上去坐坐。
阮义忠:性呢?几个太太对您最适合?
丁雄泉:性是一个大工厂,不断制造新的世界。几个太太?我看一万也不多。
阮义忠:您对哪一型的女人最感兴趣?您认为哪处最性感?
丁雄泉:我爱的女人像地球一样外冷内热,我爱大奶奶小屁股,雪白雪白的皮肤,墨黑墨黑的长头发,湿湿的眼睛,有意无意的雾中看花。滑滑的大腿像两棵香蕉树。软软的唇像蝴蝶。舌像鱼。
金发美女拍拍照片是不错的。
阮义忠:和一个女人在一块最雅的是什么时候?最俗的是什么时候?您的画是雅是俗?您愿意自己是雅人还是俗人?
丁雄泉:最雅是痴笑上马桶,一面梳头一面唱歌,最俗是照镜装腔作势,哭着要钱。我的画一定雅又妖。
我的人雅更野。
阮义忠:女人是穿衣服好看还是裸体好看?
丁雄泉:穿了衣服的人始终是愁眉不展。
阮义忠:您爱不爱哭,印象中最深的一次,是大哭还是闷在被子里偷偷地哭,为什么?在什么时候?
丁雄泉:不爱哭,有一次切了三斤洋葱,听天由命地哭了一场。
阮义忠:您有没有自杀过,想不想自杀?
丁雄泉:每次我画一张画像自杀过一次,画成后从鬼门关回来,像初生的婴孩一样,一面哭,一面笑,对世界上的一切,再感到新鲜可爱。
阮义忠:您死了,希望别人怎么处理您的画?
丁雄泉:像秋天的叶子
一阵风也好
一把火也好
阮义忠:丁雄泉啊!听说正果并不好修,有人吃斋,有人戒欲,有人隐居,有人避世,有人以撒手西归而去印证,不知您要如何去得道,能否告之,大愿洗耳恭听。
丁雄泉: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
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
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
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
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
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
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
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
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
(原文有714个忘,现略。)
阮义忠的线画:自我心灵的独白
席德进
最近一年来,在一些重要的文艺刊物和杂志中,我们常发现一些刊头和插画,出现了一种纯以线条结构组合,带有无限意象的黑白画,点缀在每篇文章的开端。它在那儿,像是一个生命的源体单独地存在着,同文章的本身毫无关联,但又觉得不可缺少它。因为在那一片密集的单调的方块字群的篇幅上,它像在缓缓呼吸着,微微震颤着,如一池静水偶然掀起的漪涟。
这些黑白线画的作者是谁?看签名,是QQ。一个新面孔。直到最近,痖弦把一位小个子的青年人介绍给我,说他对画极有兴趣。当他把手中一叠黑白线画展示给我看时,我才知道QQ就是他阮义忠。
一头自然卷曲的黑发,两眼深凹着,面部的轮廓显明。不太喜欢说话,要是开口了,那调子是急促的,一片段一片段的。人不到二十岁,却具有二十岁以上人的深沉。不见他发表意见但可以看得出他的意志坚决肯定,自有其主张。
阮义忠生长在台湾东部偏僻的小镇,兄弟姐妹共五人(阮义忠按:实为九人),他居其中。小时就爱乱画,此外就是看书。我不念大学。我讨厌学院派的画。在中学上课时就听不进课,只顾画满练习簿的线来表达心中的需要。虽然他没有进大学,但他那书架上所堆积的世界文学名著,已是非常壮观了。
音乐和诗的意味在他的线画中,明显看得出来。他常常在播放古典音乐的咖啡室泡上半天,手中也捧着一本诗集。可是他并没有写诗,却用了粗、细、直、曲、刚、柔的线转化成为他的形象的诗篇。这些形象带着律动和节奏,在线与线之间产生了一种音响感,这就是他对音乐的崇拜之后,自然而然的表露。
阮义忠没有向任何人请教过或学过画。他不需要如此。因为绘画对他来说,仅是一种自我心灵的独白。他唾弃色彩。线的无限的变化的字汇已足够满足他心灵的要求。他承认很喜欢凡高的画,但不是凡高画上那种骚动的狂热,而是那线条的律动感动了他。最近他把亨利摩尔的雕刻图片反复地用单线摹写着,他憧憬着那伟大的雕刻作品中隐藏着的一股与天地抗衡的自然伟力。
阮义忠的线画是抽象的。它不表现任何物体,线仅是他对美的表达方式。非常自由地运用着各种感情的线,来寻求它们自身的组合、结构,形成一个自我的世界。有时是几何的,但又不绝对几何。
有时像一片岩层、一个指纹,一束植物叶脉的组织,一块矿石的剖面,温和的,缓缓地流动着,凝固着,疏疏密密,虚虚实实,错错落落,自成天趣。
在文艺刊物上,从前也出现过一些有灵性的插画:龙思良的风格支配过一个时期,之后是高山岚,这两位青年画家,现在都已从插画的天地中隐退了。原因大概是这个职业,不能认真当作职业。目前的一些插画,多是东抄西拼,把嬉皮文化的调子引渡过来,而缺乏自我的创意。现在阮义忠的线画格渐渐兴起来。他最近为一本交响乐全集的书画了一百多幅线画,也有些丛书以他的线画作为封面。也许是因为他的画含有广泛的意义与感情,用在哪儿都很适合,总是给人清新之感。像一首散文诗,发散着清幽、超脱的逸趣。
阮义忠否认他的画是插图。为它不帮助文章去说明什么,也同文章内容没有任何关联。他的画是独立的,像一片浮雕,自我存在于那儿。唯一的效果是用来增加了一本书的视觉美,给呆板的文字面上嵌进一块有生命的个体。你说它是装饰也可以,因为一幅画本身挂在客厅里,不也是一件装饰品吗?
阮义忠还很年轻,他能在一开步就把握着自我,维护着自我,然后创造自我的天地,已远超过一些艺术学校的学生,他们缺乏主见,借老师的眼睛来作画,而把自己失落。一个人能发现他天生的本质,而继续不断地去培植它,已算尽到了一个人的天职。
我们相信阮义忠的画在不久的将来,经过他辛勤的淘炼、演变,会比现在更尖锐,更洗炼,更不同于前辈大师,而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形成一个线条的律动美的世界。
原载于一九七〇年十月,《大学》杂志第三十四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