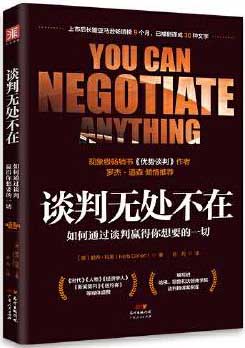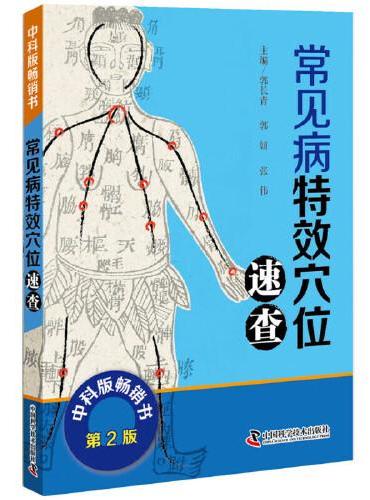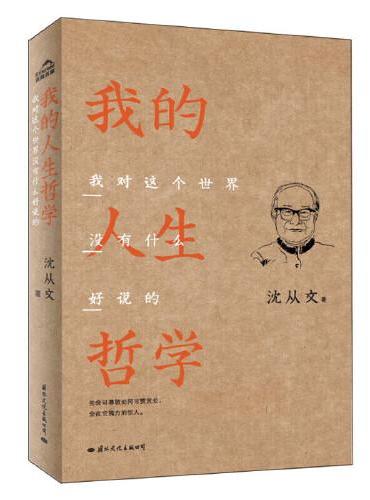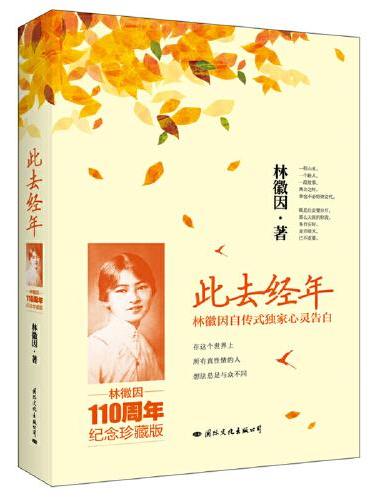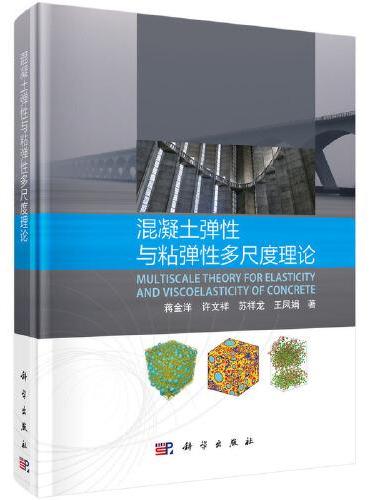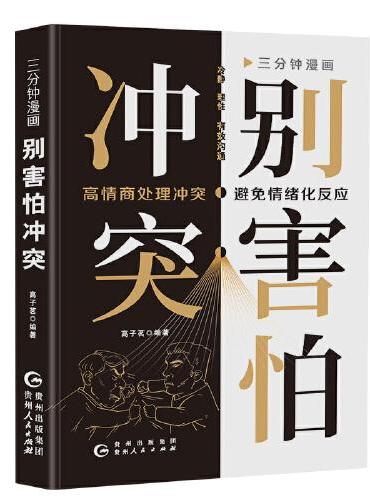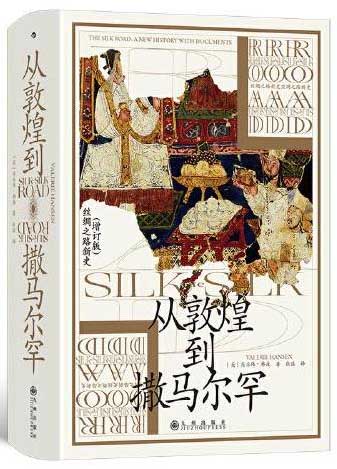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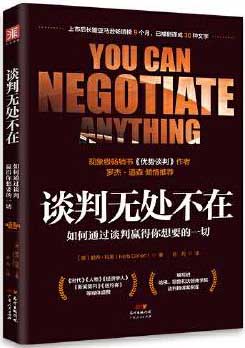
《
谈判力:谈判无处不在+谈判从说不开始(套装2册)
》
售價:HK$
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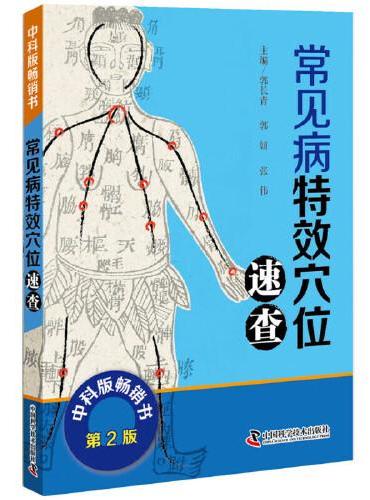
《
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
》
售價:HK$
3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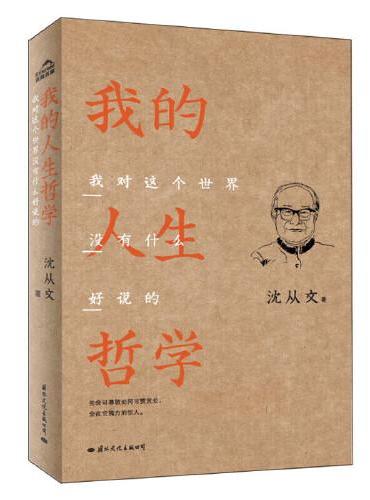
《
我的人生哲学: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
售價:HK$
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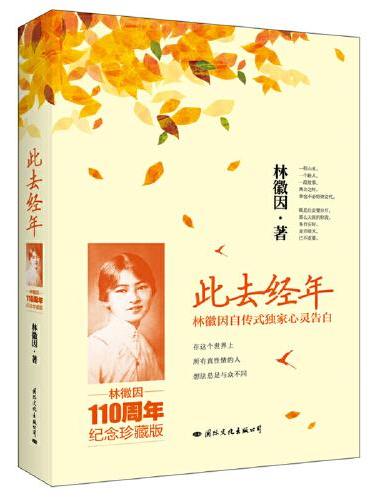
《
此去经年:林徽因自传式独家心灵告白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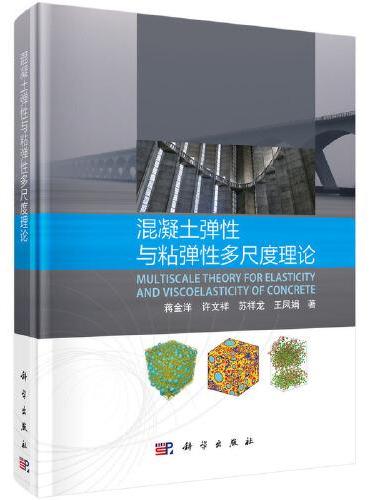
《
混凝土弹性与粘弹性多尺度理论
》
售價:HK$
18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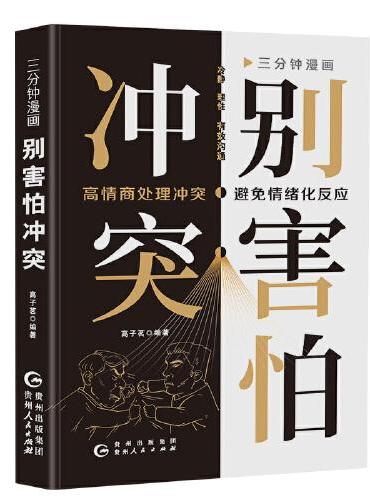
《
别害怕冲突 高情商处理冲突避免情绪化反应 揭秘冲突背后的复杂原因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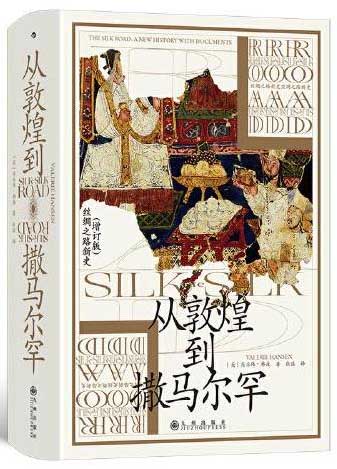
《
从敦煌到撒马尔罕 汗青堂丛书002
》
售價:HK$
118.8

《
梁衡给孩子的365堂作文课(孩子听得懂、学得进、用得上的大师级作文课)
》
售價:HK$
283.8
|
| 編輯推薦: |
|
豆瓣评分9.4在读者评论中,《绿色国王》是:我们的商科启蒙《货币战争》的海外版本一本奇特的科幻式金融作品……在我们眼中,“绿色国王”有:基督山伯爵式的复仇白手起家的智慧柔情似水的爱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
|
| 內容簡介: |
|
《绿色国王》讲述了一个纳粹德国集中营幸存者的故事。他从二战中成长起来,并通过自己的智慧和魅力创建起一个庞大的财富帝国,甚至试图缔造一个主权国家。主人公以奇特的方式为父报仇,在中东参加突击队,在北非参与走私,又浪迹印第安人的部落,之后来到美国,从身无分文变成拥有1600多家公司的亿万富翁。小说既描写了主人公曲折而惊险的传奇经历,又介绍了他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勇于开拓和精于企业经营的生动故事,使人们通过这一串生意经,可以看到西方社会的种种画面。绿色的意思有三层,一是钞票,二是和平,三是他创建的那片国土的色彩;而国王的称号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世俗的权力和名誉。这本书记录了一个有史以来个人所能达到的*高梦想,同时也是一部对人权和法统的反思录,值得反复阅读。
|
| 關於作者: |
|
保尔-卢•苏里策尔(Paul-Loup Sulitzer)是法国知名企业家、经济和金融专家。其父系罗马尼亚移民。苏里策尔幼年丧父,从十八岁起投身商界,白手起家,后又经营房地产,很快成为巨富,被誉为“法国*年轻的总经理”。苏里策尔从197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根据自己从事商业活动的经历写成《金钱》(1980)、《现金》(1981)、《财富》(1982)三部小说,出版后立即在14个国家畅销,被誉为“金融三部曲”。《绿色国王》是作者非常成功的一部代表作,于1983年12月在法国出版,初版即销售30万册,轰动整个法语世界。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部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风靡全世界,苏里策尔因此成为世界文坛上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
| 目錄:
|
|
目 录引 子 毛特豪森集中营001第一章 萨尔茨堡的摄影师006第一节 大难不死006第二节 雷伯的眼睛008第三节 对雷伯的审讯013第四节 重回家园021第五节 再访瓦格纳的书店026第六节 走访埃玛•多宁030第七节 哈尔特海姆城堡036第八节 雷伯•约尔•白尼适046第二章 波哥大的烛台054第一节 初建战功054第二节 雅古尔事件060第三节 法国之旅067第四节 走私烟卷075第五节 仇人行踪081第六节 处决前党卫军中校087第七节 处决埃立希•施泰尔098第三章 瓜阿里沃人113绿箍束发的白人113第四章 黑 犬129第一节 婚礼上的客人129第二节 收保护费的黑帮小混混131第三节 白手起家140第四节 放弃国籍161第五节 房产交易170第六节 华尔街行动182第七节 股票拍卖186第五章 卡拉卡拉伊瀑布194第一节 夏眠•佩吉194第二节 罗克鞋店交易206第三节 伦敦交易216第四节 油画——油船——小麦221第五节 雷伯的部下233第六节 游艇上的枪声247第七节 又回丛林259第八节 金 矿264第九节 四色卷宗270第十节 戴不锈钢边眼镜的年轻人276第十一节 让人不爽的弗格斯288第十二节 退隐归来297第十三节 十亿美元现金310第十四节 夏眠•佩吉之死326第十五节 响尾蛇334第十六节 南美的秘密行动345第六章 木腿海龟365第一节 丛林下的秘密365第二节 奇怪的地图377第三节 处决前奏384第四节 借刀杀人388第五节 1969年394第六节 王国概况(上)398第七节 王国概况(下)403第八节 雪莉死后408第九节 魏茨曼夫妇的担忧423第十节 裂痕433第十一节 “雷伯的告别巡回演出”439第十二节 开曼来客447第十三节 群英荟萃450第十四节 1980年5月5日459
|
| 內容試閱:
|
第二节
雷伯的眼睛
大卫塞梯尼亚兹带着布莱克斯托克、一位医生和两名步兵回来。布莱克斯托克拍下了他们发现这个墓坑时的情景,这些照片从未公开发表,甚至没有列入任何档案。但十三年以后,雷伯却从布莱克斯托克夫妇那里买下了它们。
布莱克斯托克认为,那个年轻人能够活下来,不仅仅是一连串令人头晕目眩的事态发展的结果。当雷伯被救出来的时候,他身体的姿势表明他被埋下去以后几秒钟,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他曾拼命努力想爬到坑面上来。雷伯已经从他的八个同伴的尸体中开出一条路,此举艰难异常,因为他是第一批被扔进坑里的,坑顶又被党卫军的靴子踩实,然后铺上生石灰,再盖上泥土。
坑里一共埋了九个人,都是男孩子,年龄在十二岁到十七岁之间。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的幸存者。
雷伯终于从坑里被救了出来,这时他又一次失去知觉。雷伯的身高和消瘦程度让塞梯尼亚兹吃了一惊:身高有六英尺,即一米八,体重却只有一百来磅。[1]
其实,关于他的两项估计全错了。在1945年5月5日那天,十六岁零八个月的雷伯克立姆罗德身高已达到一米八四,体重仅三十九公斤。
雷伯的后脑勺挨了一枪,部位在左耳后边。子弹轻轻地擦过耳垂,击碎了枕骨底部,划伤后颈上端的肌肉,椎骨只受了轻度损伤。这样一来,他身上其他伤口的情况更为严重,或许也更为疼痛。医生还为这个少年取出另外两颗子弹,一颗是在他的右股,另一颗是在他臀部的正上方。此外,他浑身上下受到生石灰腐蚀的地方不少于三十处。他的背部、腰部和小腹上保留着数以百计的鞭痕和被香烟头烫伤的痕迹,其中有些已是一年多以前留下的老疤。唯独他的面孔完好无损。
这张脸不仅使第一个看到他的塞梯尼亚兹激动不已,后来所有见过他的人也一样。倒不是因为这张脸可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俊美,事实上这张脸缺乏清晰的轮廓;而是它所表现出来的戏剧性的、异乎寻常的内在张力,同时却又缄默不语。这绝不是一个认命的人的脸,尽管在集中营的死亡和绝望中留下的烙印比比皆是。特别是这双有着淡绿色瞳孔的灰白眼睛,凝视人和物时深邃得让人难以忘怀。
接下来的几天内,雷伯几乎总是在睡觉。然而,一场小小的骚动却由他而起。一批以前的囚犯来找斯特罗恩,声称他们代表所有的难友提出抗议,他们拒绝与一个党卫军的男宠同住一处。实际上,他们用的字眼还要难听很多。但是那位来自新墨西哥州的红发矮个子少校没有理睬这一要求,他有别的问题需要操心毛特豪森集中营不断在死人,每天都要死好几百人。
关于那个少年的事,斯特罗恩对塞梯尼亚兹说:如果不是你救他,这孩子一定早就送命了。那么,就由你来照看他吧!
可是,我连他的名字也还不知道呢!
这是你的事情,斯特罗恩用他的高嗓门回答,从现在起,你自己想办法吧。
这次谈话发生在5月7日的上午。塞梯尼亚兹不得不把雷伯安置在集中营那些尚待决定命运的卡波[2]的棚子里,这让塞梯尼亚兹感到自责,对这个陌生的少年有某种罪行的念头本身都会使塞梯尼亚兹反感。他去探望过雷伯三次,只有一次发现他醒着。塞梯尼亚兹想问他一些问题,但得到的回答都是奇异的凝重而梦幻般的目光。
你认出我了吗?是我把你从埋葬坑里拉出来的
没有回答。
我想我至少应该知道你的姓名。
没有回答。
你对我说过你是奥地利人,你一定很想和家里人取得联系吧?
没有回答。
你是在什么地方学会法语的?
没有回答。
我只是想帮助你
雷伯闭上眼睛,转身面壁。
第二天,也就是5月8日,塔拉斯上尉从慕尼黑赶来,还带来了德国投降的消息。
乔治塔拉斯是格鲁吉亚人不是美国的佐治亚,而是苏联的格鲁吉亚[3]。在哈佛大学,塞梯尼亚兹就听说塔拉斯是俄国贵族出身,1918年全家移居美国,1945年,他四十四岁,显然已自许担负着一项使命,那就是说服我们这个星球上尽可能多的人不要过于高看自己。他痛恨感伤主义。面对人类种种愚蠢透顶的行为,塔拉斯持一种自然的无动于衷的态度(如果是装出来的,至少也装得很出色)。他随时准备讽刺挖苦。除了英语,还有十几种其他语言他都能说得很流利,其中包括德语、法语、波兰语、俄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塔拉斯到毛特豪森上任,所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布莱克斯托克在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里拍下的照片选一些最令人发指的贴在他办公室内的墙壁上。当我们审讯那些绅士们的时候,他们必然死不认账,我们至少可以让他们看看他们恶作剧的结果。
塔拉斯很快就把塞梯尼亚兹开始整理的几份卷宗处理完了,而且亲自主持讯问工作。
塞梯尼亚兹同学,这都是些小鱼小虾,还有别的吗?
塞梯尼亚兹向塔拉斯谈起那个被活埋的少年。
你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有关这个年轻人的材料少得可怜,德国人的任何名单中都没有他的名字。在1944年后半年和1945年的头几个月内,由于苏联红军日益推进,曾有几万名囚犯被运回德国和奥地利,但他也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批。一些证词断言,他来到毛特豪森集中营才三个月,至多四个月。听到这些,塔拉斯莞尔一笑。
在我看来,事情很简单。一些党卫军的高级军官撤回奥地利来,准备组织最后一次殊死抵抗。如果只有一个军官,不可能需要九个情人,除非他是超人。他们到达毛特豪森,自发地加强了驻防。当我们的第七军逼近时,他们又掉头就跑,这一回则是向着山区、向着叙利亚甚至向着热带而逃。而在逃跑之前,他们还是本着那个令人赞叹的民族一贯追求秩序井然的态度,先把那些如今已成为累赘的心肝宝贝干净利落地处理掉,还用生石灰和泥土盖起来。
在哈佛大学,一些果戈理的读者曾经不无道理地给塔拉斯取了一个雅号布尔巴[4]。塔拉斯非但不生气,还引以为荣,并且用来作为评论文章和在考卷上写评语的署名。现在,他透过金丝边眼镜把炯炯有神的目光转向墙壁上那些恐怖的照片。
当然,我的大卫老弟,我们可以把别的事情统统撇在一边不管,转而关心受到你保护的那个少年。总之,只有几十万名战犯在急切地等待我们对之表示关注。小事一桩。更不要说还有几百万已经死去、正在死去或者将要死去的男人、女人和儿童。
如此这般,塔拉斯爱作长篇大论,还喜欢用他的冷嘲热讽叫任何与他谈话的人下不了台,简直以此为乐。尽管如此,那个奥地利少年的故事想必还是引起了塔拉斯的兴趣。两天以后,即5月10日,他第一次去看那个少年。对那些在场的卡波,他说俄语、德语、波兰语和匈牙利语。对于陌生少年,他刻意地只给予迅速的一瞥。
这一瞥就够了。
他的反应和塞梯尼亚兹一样,但也有相当大的差别:那少年确实同样使他震惊,但他知道为什么。塔拉斯发现,这个幸存者的眼睛和另一个人的眼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塔拉斯在普林斯顿曾与后者交谈过几句,那是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家的午餐桌上,他是物理学家朱利叶斯罗伯特奥本海默。相同的淡淡的瞳孔,一样地深不可测,似乎在凝视着凡人永难进入的梦境。同样的神秘,同样的天资
唯一不同的是,眼前这个少年最多只有十八九岁。
接下来的几天,乔治塔拉斯和大卫塞梯尼亚兹都忙于他们来毛特豪森要办的公务,大部分时间花在根据揭发材料进行的调查工作上。他们力图把曾经以各种名义负责管理这个集中营的人列出一份名单。名单建立起来之后,附上证词,以备将来专门审理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所犯罪行的军事法庭上使用。当美国军队逼近时,原上奥地利州集中营的看守中有许多人就地躲了起来,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预防措施,用的还是本人的真姓名,祭出服从的美德Befehl ist Befehl(德语:命令就是命令)来自我开脱,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就足以解释一切。由于缺乏人力物力,塔拉斯起用了一批前囚犯,其中有一个犹太建筑师,名叫西蒙威森塔尔,是在好几个集中营里关过的幸存者。
过了一段时间,在塞梯尼亚兹的催促下(至少,这是塔拉斯向自己解释的理由),塔拉斯又想起那个曾被活埋的年轻人,他至今还不知道此人的名字。那一小群向斯特罗恩少校提过抗议的囚犯之后没有再来,而其中最起劲的三名法国犹太人已经离开集中营回法国去了;因此,这项指控实际上已经不了了之。不过既然已经立档,就得有个结论。
塔拉斯决定亲自主持讯问。多年之后,塔拉斯在截然不同的场合下面对雷伯克立姆罗德的炯炯目光时,将回忆起这第一次见面在他的脑海里留下的印象。
第三节
对雷伯的审讯
雷伯现在走路已经不再一瘸一拐了。虽然还谈不上胖了此等词语用在这类幸存者身上显得荒谬可笑但至少他的气色已经开始好转,看上去也不再那样骨瘦如柴了。塔拉斯估计他有一百来磅重。
我们可以用德语交谈。塔拉斯说。
淡淡的虹膜,明显更为深色而又发绿的瞳孔,灰色的眼睛深深地盯住塔拉斯的眼睛,然后故意缓缓地环顾这间屋子。
你的办公室?
他说的是德语。塔拉斯点点头。他产生一种异样的、近乎羞怯的感觉,这种新颖的感觉让他觉得挺好玩。
以前,少年说,这里是党卫军指挥官的办公室。
那时你常到这里来吗?
少年正在浏览墙壁上的照片,他走了几步,靠近那些照片。
除了在这里拍的,另外一些照片是在哪儿拍的?
达豪,塔拉斯说,那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地方。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这时那少年已绕到塔拉斯背后,继续仔细观看墙壁上的照片。塔拉斯凭直觉蓦地意识到,对方是有意这样做的,他不肯坐在我的对面,现在又想逼着我转过身去,以此向我表示他要掌握这次谈话的主动权。
那好吧,塔拉斯温和地说: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克立姆罗德。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
出生在奥地利?
在维也纳。
出生年月?
1928年9月18日。
据我所知,克立姆罗德不是犹太姓。
我母亲姓伊茨柯维奇。
这么说,你只是个Halbjude[5],塔拉斯说道,他已经注意到两个名字之间的关联。一个是天主教名字,而另一个雷伯,则是犹太家庭常用的名字,尤其在波兰。
沉默。少年又开始沿着墙根走动起来,走到塔拉斯背后,绕过他,出现在他的左边,再次进入到塔拉斯的视线里。他走得很慢,在每一张照片前面都驻足良久。
塔拉斯微微转过头去,看见雷伯的双腿在发抖,顿时他生出一股强烈的怜悯之心。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他从背后观察克立姆罗德,见他光脚穿着一双没有带子的皮靴,这双靴子他穿可能太小。同样,他的裤子和衬衫也都短得可怜,在他那骨瘦如柴的笨拙的身上直晃荡。这幅身躯被酷刑折磨得变了形,却纯粹靠着意志的力量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高度,一厘米也没有缩减。塔拉斯还注意到他的双手修长优美,但烟头烫的老伤疤犹在,又添了生石灰灼伤的新伤痕。这双手垂在身体两侧,丝毫没有紧张的抽搐。塔拉斯凭经验知道,这种虚假的淡定恰恰体现了一般成人也难以企及的自我控制能力,包括塔拉斯本人在内。
这一刹那间,塔拉斯心里更明白了,究竟是什么使塞梯尼亚兹如此震动。原来,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身上散发着一种不同寻常、无以名状的气质。
塔拉斯不敢多想,赶紧继续提问:
你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来到毛特豪森集中营的?
我是今年2月份到这儿的,具体日期我说不准,大概2月初吧。他话说得很慢,音调极为深沉。
是列车运来的吧?
不是列车。
那么谁和你一起呢?
和我一起被埋的那些男孩子。
总得有人把你们带到这儿。
党卫军的军官。
一共有多少军官?
十来个。
他们归谁指挥?
一名中校。
他叫什么名字?
此时,雷伯站在屋子的左角,与其脸孔齐高处是布莱克斯托克拍摄的一张放大的照片,画面上是一座焚尸炉敞开的炉门,半焦的尸体在闪光灯下一片惨白。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雷伯的声音十分平静。
他举起一只手,细长的手指触到了光滑的相纸,仿佛在抚摩那张照片。然后,他转过身来,靠在墙上。他面无表情,眼神空幻,不带任何色彩。他那重新开始长出来的头发是深栗色的。
你有什么权力向我提这些问题?就因为你是美国人,因为你们打赢了这场战争?
我的天哪!塔拉斯心想。他像挨了一闷棍似的,生平第一次语塞。
我并不觉得自己被美利坚合众国打败了。事实上,并没有被任何人打败的感觉声音依然遥远。
雷伯的目光落在一架玻璃柜上,柜子里堆着好些卷宗,塔拉斯在卷宗旁放了一些书籍,雷伯正在凝视这些书
2月初,我们到达此地,雷伯说,我们是从布痕瓦尔德来的。到布痕瓦尔德以前,我们一共有二十三个人,但是有五个男孩在那边给烧了,还有两个死在从布痕瓦尔德到毛特豪森的路上。那些把我们当女人使用的军官在卡车里杀死了那两个孩子,是我把他们埋葬的。他们走不动了,老是哭,他们的牙都掉光了,就显得不那么好看。这两个孩子一个才九岁,另一个稍微大一点,大概十一岁。军官们坐一辆轿车,我们坐的是一辆卡车,可是他们常常迫使我们下车步行,有时候用绳子套住我们的脖子,逼着我们跑步。他们就用这个办法消耗我们的体力,使我们逃不了,甚至不想逃。
雷伯用双手撑着墙壁把身体从那儿挪开。他几乎像处于被催眠状态那样目不转睛地瞧着柜里的书,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停止说话,塔拉斯觉得雷伯就像个教员一样,一面望着窗外的一只鸟,一面背诵着他的讲义,声音同样遥远而冷漠。
我们到达布痕瓦尔德的时候,刚过了圣诞节。在此之前,我们在克姆尼茨待了一段时间。到克姆尼茨之前,我们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到格罗斯罗森以前,我们在普拉绍夫集中营,那是在波兰境内,靠近克拉科夫,当时是夏天。
现在,雷伯完全离开了墙壁,开始慢慢地朝玻璃柜那边走过去。
不过我们在普拉绍夫集中营只待了三个月。有几个男孩在那儿死去了,主要原因是饥饿。一共死了六个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到达普拉绍夫以前,我们在森林里走了好长一段时间不,我们先到普热梅希尔但在这以前和以后,我们走了好长时间。我们是从雅诺夫斯卡集中营出发的。我曾经到过雅诺夫斯卡两次。一次是在去年5月,还有一次更早,是在1941年,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半。
雷伯叙述经历的方式很特别。他让自己的记忆从现在向过去倒退,就像电影放映机倒片似的。他朝前走了三步,站到柜子的紧跟前,和柜子里的书只隔着一层玻璃。
这些书是你的吗?
是的。塔拉斯说。
第二次去雅诺夫斯卡以前,我在贝乌泽茨。我的母亲汉娜伊茨柯维奇和我妹妹米娜于1942年7月17日死在贝乌泽茨,我亲眼看见她们被活活地烧死。请问,我可以打开柜子摸一下这些书吗?
可以。塔拉斯回答时委实局促不安。
我妹妹米娜当时才九岁,我绝对相信他们把她扔进焚尸炉时她还活着。我姐姐卡塔丽娜比我大两岁,她死在一节火车车厢里,本来我也被指定上那节车厢。她上了一节只能容纳三十六个人的车厢,他们却硬塞了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个人进去,最后塞进去的几个就躺在别人的头顶上。他们在地上撤了生石灰。我姐姐卡塔丽娜是最先一批进去的。到最后连一个小孩也塞不进去的时候,他们关上了车门,把车厢拉到侧线上,在太阳底下烤,一搁就是七天。
雷伯读出了书上作者的名字:沃尔特惠特曼。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美国人。塔拉斯回答。
他是诗人吗?
和魏尔伦一样。塔拉斯回答。
那双灰色的眼睛瞥了一下塔拉斯的脸,视线又回到《草叶集》上。塔拉斯提了一个问题,雷伯迟迟没有回答,塔拉斯以为还得再问一遍。但是雷伯摇了摇头。
我还没有掌握英语,只认得几个单词。不过我打算学英语,还有西班牙语。也许还要学其他语言,比如俄语。
塔拉斯垂下眼帘,然后又抬起头来,他感到茫然失措。自从雷伯进屋以后,塔拉斯坐在办公桌旁,除了信笔记下一些什么外,没有任何举动。他突然对雷伯说:
你可以把这本书拿去看。
我得花一段时间才能读完。
你需要多久就放在你那儿多久。
多谢。雷伯一面说一面又看了看这个美国军官,然后继续叙述。到贝乌泽茨以前,从1941年8月11日起,我们在雅诺夫斯卡。到雅诺夫斯卡以前,我们在利沃夫我母亲汉娜伊茨柯维奇的父母家里。我们是1941年7月5日星期六到利沃夫的。我母亲想去看我的外公外婆,她在维也纳领到了我们四个人的护照。我们是7月3日星期四离开维也纳的,因为当时利沃夫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了。我母亲十分相信护照,但是她想错了。
雷伯开始翻动《草叶集》的书页,但他的动作显得很机械。他侧下头以便看清别的书名。
蒙田[6]!这个作家我知道。
这本书你也可以拿去看。由于激动,塔拉斯的声音有些颤抖。
这二十本书他一直带在身边,聊以暂时忘却战争的恐怖。如果要他从中只挑一本的话,那么一定是蒙田的这一本。
至于我,雷伯说,我活了下来。
塔拉斯重新读了一遍手头的笔记,借以恢复常态。他按照时间顺序把雷伯提到的集中营的名单念了一遍:
雅诺夫斯卡,贝乌泽茨,又是雅诺夫斯卡,普拉绍夫,格罗斯罗森,布痕瓦尔德,毛特豪森他问道:你真的到过所有这些地方吗?
雷伯淡漠地点了点头。他关上了柜子的玻璃门,双手紧紧地把塔拉斯借给他的两本书抱在胸前。
你是什么时候成为那群男孩中的一员的?
雷伯离开玻璃柜,朝门口的方向走了两步。
1943年10月2日,党卫军中校在贝乌泽茨把我们集中了起来。
就是那个你不知道名字的中校?
就是他。雷伯一面说一面朝门口又走了一步。
他当然在撒谎,塔拉斯心想,同时越来越感到心神不安。假定他说的其余一切都是真的,塔拉斯相信是这样,那就无法想象,这个具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的少年,居然把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5月与他一起生活了二十个月的那个人的名字给忘了。他在撒谎,他也明白我知道他在撒谎,但他不在乎。他并不企图为自己辩解,也不想解释他是怎样活下来的。而且,他好像既没有羞耻感,也没有仇恨。也许他精神上受了刺激,尚未恢复
最后的解释在塔拉斯看来最缺乏说服力,他自己也不相信。确切地说,和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这次初会,时间最多不过二十分钟,塔拉斯却感到,这个骨瘦如柴、连站都站不稳的少年具有一种能控制任何局面的不可思议的本领。卓尔不群塔拉斯想到的就是这么个词儿。雷伯那双灰白色的、深邃的眼睛后面蕴藏着非凡的智力,塔拉斯十分具体地感觉到它的压倒一切的分量。
雷伯又朝门口走了一步,他的侧影构成一种冷酷的美。他已经准备离去,这时,塔拉斯又提了最后几个问题,主要是想延长这次会见。
他就是那个用鞭子抽你、用烟头烫你的人?
你这是明知故问。
同一个军官,在二十个月的时间里?
沉默。雷伯又朝门口走了一步。
你刚才对我说,那个党卫军中校在贝乌泽茨把你们集中在一起,时间是
1943年10月2日。
一共有多少孩子?
一百四十二个。
把你们集中在一起,目的是什么?
雷伯微微地摇摇头,表示他不知道。这一回他没有撒谎。塔拉斯对这一点如此有把握,这使他自己也感到惊奇,匆匆地又问了几个问题。
你们是怎样离开贝乌泽茨的?
坐卡车。
去雅诺夫斯卡?
只有三十个人去雅诺夫斯卡。
那么另外一百一十二个人呢?
他们去马伊达内克了。
塔拉斯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在波兰境内的又一个杀人集中营,可与贝乌泽茨、索比波尔、特雷布林卡、奥斯威辛和海乌姆诺并列。
是那个中校选择了三十个男孩吗?三十个全是男孩?
是的,你都说对了。
雷伯又朝门口迈了两步,这时他已经走到门口。他站在门槛上,塔拉斯可以看见他的背影。
我会还给你的,雷伯说着抚摩了一下惠特曼的《草叶集》和蒙田的《散文集》。这两本书我会还你的。他微微一笑。请别再问了。那个中校把我们带到雅诺夫斯卡,从那时开始,他就把我们当女人使。后来,由于俄国人不断推进,他和其他几个军官一起向德军谎称去执行一项特别使命,把我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就是他们不杀我们的原因,除非我们支持不住。
这些军官的名字你一个都不记得吗?
不记得。
他在撒谎。
有多少孩子和你一起到达毛特豪森?
十六个。
塞梯尼亚兹中尉在坑里发现你的时候,你们一共只有九个人。
我们到达毛特豪森以后,他们杀了我们中的七个。他们只留下他们的宠儿。
这番话是用一种从容而超然的语调说的。他跨过门槛,最后一次停止脚步。
你的姓名可以告诉我吗?
乔治塔拉斯。
T,a,r,r,a,s,对吗?
对。
沉默。
我会把书还给你的。
当时,奥地利分为四个军事占领区,毛特豪森在苏军占领区内。大批过去的囚犯被转送到利昂丁的一个临时收容难民的接待营,设于林茨附近美军辖区内一所中学的楼房里,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坐过这所学校的课椅,希特勒的双亲曾在学校对面的一所小房子里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乔治塔拉斯、大卫塞梯尼亚兹和他们那个调查战争罪行的单位在林茨安顿了下来。尽管这次迁移使他们忙上加忙,但他们并没有中断搜索隐藏在当地的前党卫军看守人员的工作。
因此,直到几天以后,他们才发觉年轻的雷伯失踪了。
约四十五公斤。 译者注
集中营中管理囚犯的囚犯。译者注
美国的佐治亚(州)和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在法语和英语中拼写相同。译者注
塔拉斯布尔巴是俄国作家果戈理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乌克兰哥萨克老英雄。译者注
纳粹用语:半个犹太人。
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思想家和散文作家,主要作品有《散文集》。译者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