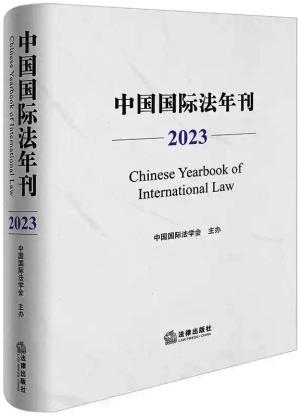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有兽焉.8
》
售價:HK$
68.8

《
大学问·明清经济史讲稿
》
售價:HK$
7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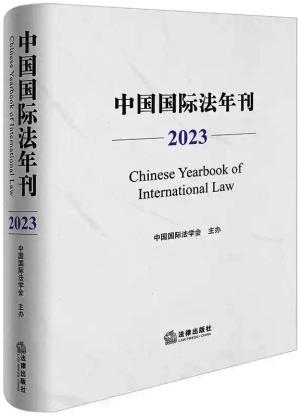
《
中国国际法年刊(2023)
》
售價:HK$
115.6

《
西班牙内战:秩序崩溃与激荡的世界格局:1936-1939
》
售價:HK$
217.8

《
基于鲲鹏的分布式图分析算法实战
》
售價:HK$
108.9

《
夺回大脑 如何靠自己走出强迫
》
售價:HK$
65.8

《
图解机械工程入门
》
售價:HK$
96.8

《
中文版SOLIDWORKS 2024机械设计从入门到精通(实战案例版)
》
售價:HK$
98.9
|
| 編輯推薦: |
《冬日笔记》是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对自己一生的剖白。他以一种近乎随意而散乱的逻辑,组织起六十多年的人生碎片,描述了从童年到晚年之间的身体意识、感受到的快乐和痛苦、他与父母的牵绊以及对父母的探索与迷思这是保罗奥斯特继《孤独及其所创造者》《红色笔记本》《穷途,墨路》后的第四本回忆录,是一本坦率、优美的深刻之作。
一部热情洋溢的回忆录充满沉思默想,哀婉动人一本优美的深刻之作。
《华盛顿邮报》
生动地记录下思考的瞬间,反省了青春期和渐渐逼近的老年所感受到的屈辱,每一次都描写得诚实坦率,又透着优雅。
《星期日独立报》
这是一本回忆录,但它并没有如一般回忆录那样复述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相反,在生命即将迈入六十四岁之际,奥斯特思考了身体上的痛苦与愉悦、时间的流逝以及记忆的重量。
《图书馆杂志》
|
| 內容簡介: |
《冬日笔记》
一扇门关上了。
另一扇门打开。
你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冬天。
2011年1月3日,大雪纷飞,保罗奥斯特坐在桌前,写下《冬日笔记》的第一行字,此时距离他六十四岁生日还有一个月,距离他第一部作品《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则已三十年。
这是保罗奥斯特对自己一生的剖白。他以第二人称的方式、从局外人的角度来审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进而审视自我、解剖自我;他以一种近乎随意而散乱的逻辑,组织起六十多年的人生碎片,描述了从童年到晚年之间的身体意识、感受到的快乐和痛苦、他与父母的牵绊以及对父母的探索与迷思,记录下从少年时代的性觉醒到中年深沉的婚姻之爱,以及他对食物、睡眠的思索和1987年他以作家身份开启的人生新旅程,而读者总能从字里行间找到他小说创作时的灵感来源以及原型。
|
| 關於作者: |
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
1947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集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译者、电影导演等多重身份于一身,被视为美国当代最勇于创新的小说家之一。
主要作品有小说《纽约三部曲》《幻影书》《在地图结束的地方》《密室中的旅行》《日落公园》以及回忆录《孤独及其所创造的》等。曾获法国美第奇文学奖、美国约翰克林顿文学杰出贡献奖、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作品被翻译成30种文字,他也是每年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人选之一。
编剧并导演的电影作品有《烟》《面有忧色》和《桥上的露露》,其中《烟》在1996年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和最佳编剧奖。
目前定居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区。
|
| 內容試閱:
|
你以为这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以为这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以为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会在你身上发生这种事的人,而随后,一件接着一件,它们都开始在你身上发生,与发生在其他每个人身上一样。
你爬下床走到窗前,赤脚站在冰冷的地板上。你六岁。外面,雪在下,后院的树枝正在变白。
现在说吧,趁还来得及,然后希望一直说下去,直到再也没有更多可说的。毕竟,时间快用完了。也许可不妨暂且把你的故事放在一边,试着检视从你记事第一天起到这一天,活在这个身体里有怎样的感觉。一系列感觉资料。人们可称之为呼吸现象学的东西。
你十岁,仲夏的空气是热的,热得压抑,那样潮湿、那样令人不适,甚至当你坐在后院树荫下,前额都聚满汗水。
无可争辩的是你不再年轻。一个月后的今天,你将满六十四岁,尽管那不算太老,不是那种人们会视作耄耋之年的岁数,但你仍然忍不住想起那些没能活到你这个年纪的人。这便是一例或可永不发生、但实际上已发生的事。
上周暴风雪时扑面而来的风。冷得刺骨,而你在外面空荡荡的街上,讶异于自己竟在这样猛烈的风暴里出门,然而,就当你努力保持着平衡时,有那种风带来的狂喜,有看见熟悉的街道变成一片模糊的纷飞白雪的喜悦。
身体的愉悦和身体的痛苦。最重要的是性快感,但也有口腹之愉,有裸身泡热水澡、挠痒、打喷嚏、放屁、赖床一小时及在晚春初夏的温煦午后面向阳光感受暖意在肌肤驻留的乐趣。不胜枚举,每一天都有某个或某些身体愉悦的时刻,但痛苦无疑更持久、更难对付,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几乎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曾受到攻击。眼和耳、头和颈、肩和背、臂和腿、喉与胃、踝与脚,更不用说有一次从臀部左侧长出的巨大脓肿,医生称之为毛鞘囊肿,在你听来像某种中世纪的痛苦,令你一星期无法坐在椅子上。
你小小的身体接近地面,这三四岁时属于你的身体,也就是说,脚与头之间的距离很短,而那些你不再注意的东西一度是你常见的、专注的:由爬行的蚂蚁和丢失的硬币、落下的枝条和压扁的瓶盖、蒲公英及三叶草组成的小世界。特别是蚂蚁。它们是你记得最牢的。成群结队的蚂蚁在它们的粉状山里进进出出。
你五岁,蹲着俯视后院一座蚂蚁山,专注地观察六脚小动物来来回回。不知不觉,三岁邻居潜行至你背后,用一把玩具耙打你的头。叉刺破了你的头皮,血流进头发,流向后颈,你尖叫着跑回家,在家里祖母为你处理伤口。
祖母对母亲说的话:你的父亲会是那样一个优秀的男人假如他变得不同的话。
这个早上,在又一个一月破晓时分的昏暗中醒来,一道柔和的浅灰色光渗进卧室,你妻子的脸转向你的脸,她的眼睛闭着,仍在熟睡,被单一直拉到颈部,头是唯一可见的部分,你惊叹她看起来多么美,多么年轻,即使是现在,你与她初次共眠三十年后,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同床共枕了三十年后依旧如此。
今天雪继续下,你下床走到窗前,后院的树枝变白了。你六十三岁。你想起少年时代至今的漫长旅程中几乎没有一刻不在恋爱。结婚三十年,对,但在此前的三十年里,有多少痴心与迷恋、激情与追逐、谵妄与疯狂燃起的欲望?从生命有意识之初起,你就一直甘愿作厄洛斯的奴隶。你男孩时爱的女孩,身为男人时爱的女人,每一个都与其他的不同,有些丰满、有些苗条,有些矮、有些高,有些书生气、有些爱运动,有些喜怒无常、有些开朗外向,有白人、黑人、亚洲人,表面上的一切你都不在乎,你只关心探测到的内心之光、个体的火花、展露出的自我火焰,而那道光会令你觉得她美,即使别人对你看见的那种美视而不见,随后,你会渴望与她在一起,靠近她,因为女性之美是你永远无法抗拒的东西。回到你上学的最初几天,在幼儿园班里,你爱上了那个金色马尾辫女孩,有多少次你和心仪的小女孩偷偷溜开、两人一起躲在角落恶作剧而被桑德奎斯特老师惩罚,但这些惩罚对你而言不算什么,因为你在恋爱,而那时你是个爱情傻瓜,正如你现在也是。
你存下的伤疤,尤其是脸上那几个,每天早上对着浴室镜子刮脸或梳头时都会看见。你很少想到它们,但无论何时一想起,你就会明白它们是生活的印记,那刻入脸庞的各种突起线条是来自秘密字母表的字母,它们道出了你是谁,因为每个伤疤都是伤口愈合的痕迹,每个伤口都是与世界意外撞击造成的也就是说,一场事故,或某件本不必发生的事,因为照定义来说,事故就是某件不必发生的事。与必然事实相对的偶然事实,这个早上你望向镜子,意识到整个人生都是偶然的,只有一项必然的事实除外:或早或晚,生命会告终。
你三岁半,你二十五岁怀孕的母亲带你去纽瓦克市中心的百货商店进行一场购物之旅。她由一位友人陪伴,也是一个三岁半男孩的母亲。一度,你和你的小伙伴逃脱了母亲们的控制,开始在店里奔跑。这是个巨大的开放空间,无疑是你曾涉足的最大的房间,而能够在这庞大的室内区域里野奔,有明显的兴奋感。最终,你和那男孩开始朝地板上俯冲,在光滑表面滑行,有点像不用雪橇滑雪,这游戏显得那样有趣,令人产生欣喜若狂的感觉,你们越来越不顾一切,愿意越来越大胆地尝试。你们到了一处店里正在施工维修的地方,没有注意到前面有什么障碍物,你又一次在地板上俯冲,顺着玻璃般的表面航行,直到你发现自己正一头冲向一个木制的木工长椅。你略微转动小小的身体,以为可以避免撞上扑面而来的桌腿,但在那你不得不改变路线的短暂一秒,你没有意识到有个钉子从桌腿上戳出来,一个长钉子,正好与你的脸一样低,而你还没来得及停下,左侧的脸颊便在飞身而过时被这钉子刺穿了。半个脸都破了。六十年后,你不再记得这事故。你记得那奔跑和俯冲,但一点不记得疼痛、流血及马上被送往医院的情形,或缝合你脸颊的那位医生。他干得很漂亮,你母亲总这么说,因为目睹第一个孩子半边脸被撕裂的创痛从未过去,她经常说起那精妙的双重缝合法,这方法使伤害降到最低限度,也令你没有终生破相。你本可能失去眼睛,她会对你说或者,更惊人地,你可能会死。无疑她是对的。多年过去,伤疤越长越淡,但每当你去找,它都依然在那儿,而你会带着那好运(眼睛没伤!没死!)的象征,直到去往坟墓。
眉部撞伤的疤痕,左一个,右一个,几乎完美对称,第一个是在小学体育课躲避球比赛上全速奔跑,撞上了一堵砖墙(后来那些天里巨肿的黑眼圈,令你想起拳击手吉恩富尔默的一张照片,差不多那时候,他在一场冠军赛中被休格雷鲁滨逊打败);第二个是二十出头时,在室外篮球赛上切入上篮,被身后犯规撞飞到篮架的金属柱上。另一个伤疤在下巴处,来源不明。很可能是童年早期摔倒所致,重重摔倒在人行道或石头上,令你肉体裂开,留下印记,每天早上刮胡子时仍可看见。没有故事伴随这伤疤,你母亲从来没有谈论过它(至少你不记得),假如不算彻底令人迷惑,你也觉得奇怪,这根永恒的线条被只可称作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东西镌刻在你下巴上,而你的身体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地,这些事件并没有被一笔勾销,从历史里消失。
1959年6月。你十二岁,一星期后你和那些六年级同学就要从这所语法学校毕业了,你从五岁起就开始上这学校。天气极好,是最明媚的晚春,阳光从无云的蓝天倾泻而下,暖得恰好,湿度小,柔风搅动空气,拂过你的脸庞、颈项及裸露的臂膀。一放学,你和一帮朋友就结伴去格罗夫公园打皮卡棒球。格罗夫公园与其说是个公园,不如说是片乡村绿地,一大片保养良好的长方形草地,四周都有房子,一个舒适之处,新泽西小城里最赞的公共空间之一,你和朋友们经常放学后去那儿打棒球,因为棒球是你们所有人的最爱,连着打好几个小时也不厌倦。没有大人在。你们建立自己的基本规则,自己解决争端通常用言语,有时也用拳头。五十多年后,对于那天下午打的那场比赛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你真正记得的惟有这个:比赛结束后,你独自一人站在内野中央,自己玩接球,也就是,把球高高掷向空中,追随它的起落,直到它落进手套,这时你立即又一次把球掷向空中,每一次掷球,都比前一次飞得更高,而掷了几次后,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在球会腾空好几秒,白色的球升向明净的蓝天,白色的球落进手套,而你整个人都专注于这项不动脑筋的活动,你全神贯注,除了球、天空及手套外什么都不存在,这意味着你的脸是朝天的,你追随球的轨迹时是抬着头的,因此你不再注意到地上正在发生的事,而当你抬头望向天空时,地上发生的事是:某样东西或某个人不期然朝你冲来,这碰撞如此突然、猛烈、充满力量,你立刻就倒在了地上,感觉仿佛被一辆坦克击倒。最糟糕的一击在头部,尤其是前额,但身体也受到撞击,当你躺倒在地、气喘吁吁时,你看见血从前额流出,不,不是流出,是涌出,于是你脱掉白色T恤,把它压在血涌之处,仅仅几秒后,白色T恤就全部变红了。其他孩子们惊呆了。他们朝你冲来,尽其所能帮助你,直到那时你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似乎是你们那帮人中的一个,一个叫作B.T.的(你记得他的名字,但不想在此透露,因为你不想让他难堪假设他依旧活着)高瘦笨拙和蔼的白痴对你那高耸的、摩天大楼般的投掷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他渐渐也想加入进来,他没有告诉你,他也想试着接一次你的投掷,便开始朝球下落的方向跑去,当然,头仰着,用他那呆呆的方式张着嘴(谁跑步的时候张着嘴啊?),而一瞬间后,他在全速奔跑中撞到了你,张开的嘴里突出的牙齿直接撞向你的头。因此现在血从你身体里涌出,因此你左眼上方的皮肤划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幸运的是,家庭医生的办公室正好就在附近,在格罗夫公园周边那排房子的某一栋里。男孩们决定立刻带你去那儿,于是在朋友的陪伴下,你拿血淋淋的T恤捂着头穿过公园,也许有四个朋友,也许六个,你不记得了,你们集体冲进了科恩医生的办公室。(你没有忘记他的名字,就像你没有忘记幼儿园老师的名字,桑德奎斯特老师,或者那些你少年时期其他老师的名字。)前台告诉你和你的朋友,科恩医生正给一位病人看病,她还没来得及从椅子上起身通知医生有紧急状况需要处理,你和朋友们就门也不敲地冲进诊疗室内。你看见科恩医生正在和一位丰满的中年妇女讲话,她坐在检查台上,只穿着胸罩和衬裙。那女人发出一声惊叫,但科恩医生一看见你前额涌出的血,就要求那女人穿好衣服离开,并要你的朋友们回避,然后匆忙开始缝合你的伤口。这是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来不及麻醉,但你在他穿过皮肤缝针时尽量不发出嚎叫声。他的活干得或许不能与1950年缝合你下巴的那位医生媲美,但好歹很有效,你没有流血至死,头上也不再有个洞。几天后,你和六年级同学们参加了语法学校的毕业典礼。你被选为旗手,这意味着你要举着美国国旗顺着礼堂走道,把它插进台上的旗座。你头上包裹着白色纱布绷带,由于血仍不时从缝合处渗出,白色纱布上有一大块红色印迹。典礼后,母亲说当你举着旗帜行走在走道时,你令她想起一幅独立战争受伤英雄画。你知道,她说,就像《76年精神》一样。
持续猛烈攻击你的,一直持续猛烈攻击你的是:外部,意思是空气或更准确的说,你的身体在周围的空气里。你的脚底锚住地面,但你的剩余部分暴露在空气里,而那便是故事开始的地方,在你的身体里,而一切也会在身体里结束。现在,你正思考着风。稍后,若时间允许,你会思考冷与热,无数种雨,如同盲人蹒跚穿过的雾,癫狂的、机枪似的砸在瓦尔省屋顶瓦片上的冰雹。但此刻,是风抓住了你的注意力,因为空气很少静止不动,在几乎不可见的、呼吸包裹着你的虚无之外,有微风和飘香的轻风,突如其来的阵风和飑风,在那栋瓦顶屋子里经历的长达三天的西北强风,横扫大西洋海岸的润湿的东北风,还有大风、飓风和旋风。而你在那儿,二十一年前,你走在阿姆斯特丹街头,去往一场已取消但未告知你的活动,试图尽责地恪守许下的承诺,你在那场后来被称作世纪风暴的飓风中,一场超级强烈的飓风,就在你固执而不明智地决定冒险外出后一小时内,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大树将被连根拔起,烟囱将栽倒在地,停泊的车辆将被举起、在空中航行。你迎风而行,试图沿着人行道前进,但尽管你努力地想到达目的地,你无法挪动。风吹进你的身体里,在接下去的一分半钟里,你困住了。
十三年前的一月,你在都柏林半分桥上,在又一个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飓风过后的晚上,过去两个月来你一直在导演的那部电影拍摄的最后一晚,最后一场戏,最后一个镜头,只是要把摄像机固定在女主角戴着手套的手上,然后她转身,放开一块小石头,让它落入利菲河的水中。非常简单,全片最不费力、最无需创造性的镜头,但你在那强风之夜的湿冷及黑暗中,在九周充满数不清问题(预算问题、工会问题、选景问题、天气问题)的艰苦卓绝的拍摄工作后你筋疲力尽,你比开拍时轻了十五磅,在桥上与剧组成员一起站了好几个小时后,爱尔兰那潮湿、寒冷的空气已渗入你的骨头,就在最后一个镜头快要开始前一刻,你意识到手已被冻住,手指无法动弹,你的手变成了两块冰。为什么没有戴手套呢?你问自己,但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离开宾馆去桥边时根本没有想过戴手套。你又拍了一次最后那个镜头,随后你和制片人、女主角、女主角的男朋友和几位剧组成员,去临近的酒吧解冻并庆贺电影完成。这地方很拥挤,挤得满满的,密闭的房间里满是大声说话的、闹哄哄的人们,他们窜来窜去,带着末世般的欢乐,但有一张桌子是为你和朋友们保留的,于是你在桌前坐下,就在身体与椅子接触的那一刻,你明白你已经精疲力竭了,所有的身体能量、所有的感情能量都流失了,以一种你从未想象到的方式消耗殆尽,那样崩溃,以至于你觉得随时可能流下眼泪。你点了一杯威士忌,而当你握住酒杯,将之举到唇边时,你高兴地发现手指又能动了。你点了第二杯威士忌,然后第三杯,然后第四杯,突然之间你睡着了。尽管周围狂乱嘈杂,你却成功地一直睡着,直到那个好人、你的制片人把你拉起,半拖半拽地把你弄回宾馆。
是的,你酒喝得太多,烟抽得太多,掉了牙齿也懒得去补,你的膳食不符合当代营养理念,如果说你不吃大部分蔬菜,那只是因为你不喜欢,你发现就算不是不可能,你也很难去吃不喜欢的东西。你知道妻子担心你,尤其担心你的烟酒习惯,但幸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X光显示你的肺有任何损害,没有血液测试显示你的肝有任何问题,于是你继续带着恶习前进,深知它们最终会带给你严重伤害,但你越是年长,就越是觉得不可能有意愿或勇气放弃那可爱的小雪茄和时不时的几杯酒,它们在这些年里带给你如此多的愉悦,而你有时想,如果要这么迟将它们从你的生活中去除,你的身体会垮,系统会停止工作。无疑你是一个有缺点、受过伤的人,从一开始就带着伤口的人(要不是这样,你为什么要花整段成年时光令词语流到纸页上?),而你从烟酒之中得来的好处就像枴杖,撑起你残破的自我,令你在世上前行。自我疗药,你的妻子这么称呼它。与你母亲的母亲不同,她不希望你与众不同。你的妻子容忍你的缺点,不粗言不责骂,如果她担心,那只是因为她希望你永远活下去。你计算着那么多年来你一直拥她在旁的理由,这一定是其中之一,在广袤的恒久之爱的星座里最亮的一颗星。
更何况,你咳嗽,尤其在夜里,当身体处于水平状时,在那些气管严重阻塞的夜晚,你爬下床,进入另一间房,发疯般不断咳嗽,直到把所有那些粘滞的东西都咳出来。照你的朋友斯皮格曼(你认识的烟瘾最重的人)的说法,每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抽烟时,他都必答:因为我喜欢咳嗽。
你在人生旅途中曾无数次陷入困境,比如,那些你感到有种紧急的、压倒性的需求要清空膀胱、但身边没有厕所的绝望时刻,那些碰上交通堵塞的时候,或坐在一辆停在两站之间的地铁上,强迫自己要忍住的纯粹焦虑。这是一个无人谈论的世界性难题,但每个人都有过那样一个时刻,每个人都渡过了难关,在人类苦难中没有一例比肿胀的膀胱更喜感,因此你往往不去嘲笑这些事件,直到你成功地释放了自己有哪个三岁以上的人会愿意在公共场合尿裤子呢?因此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话,这些话是你朋友父亲的临终遗言:要记住啊,查理,他说,永远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小便的机会。就这样,长者的智慧代代相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