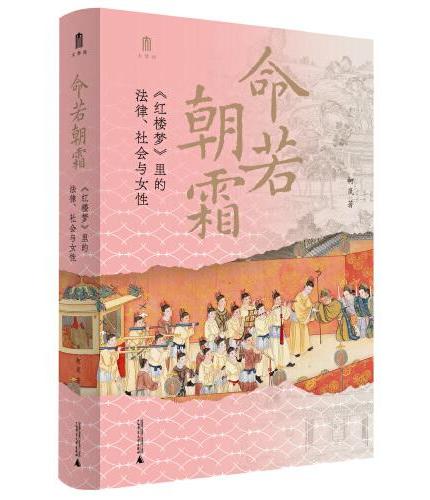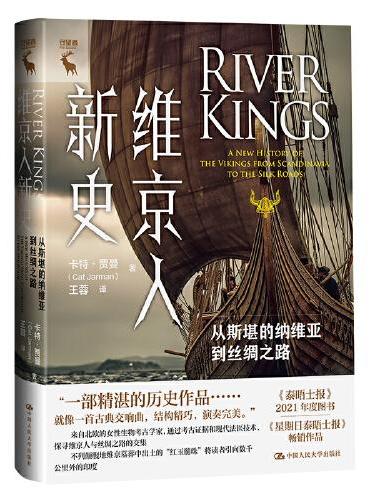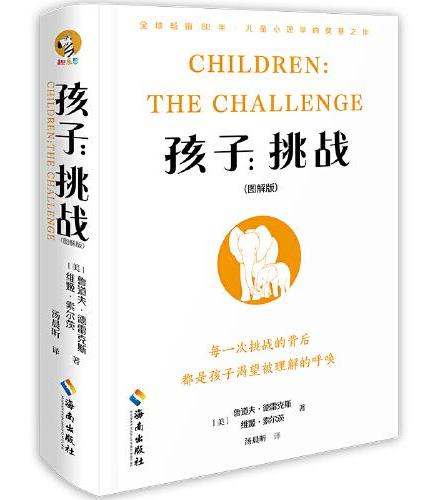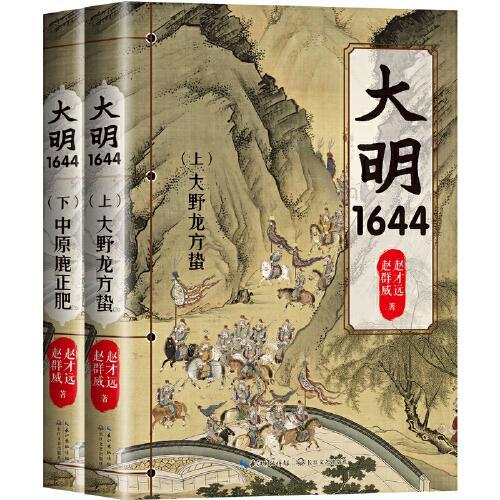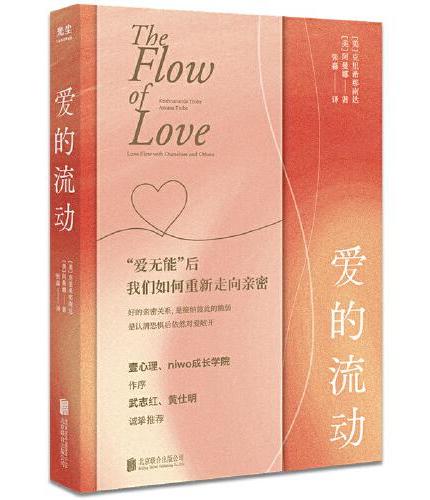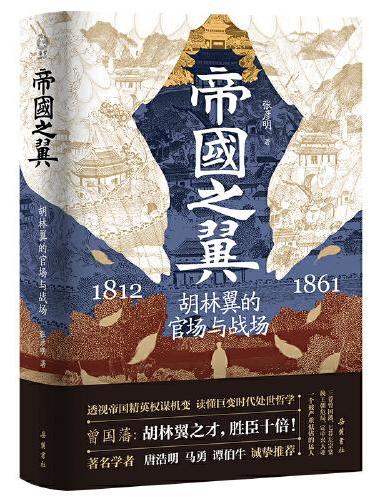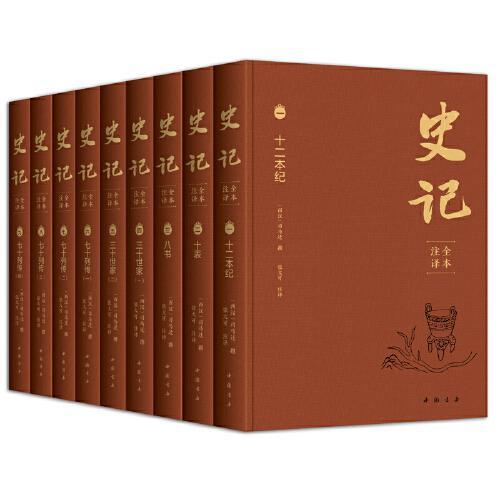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空气炸锅懒人食谱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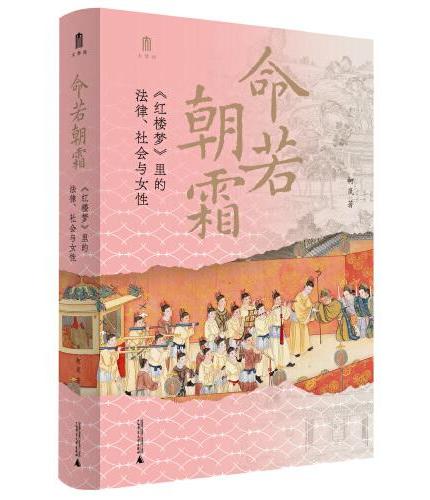
《
大学问·命若朝霜:《红楼梦》里的法律、社会与女性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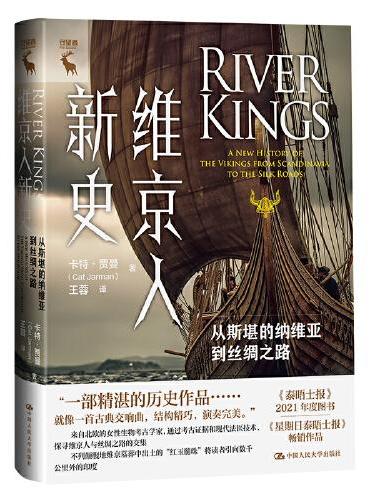
《
维京人新史:从斯堪的纳维亚到丝绸之路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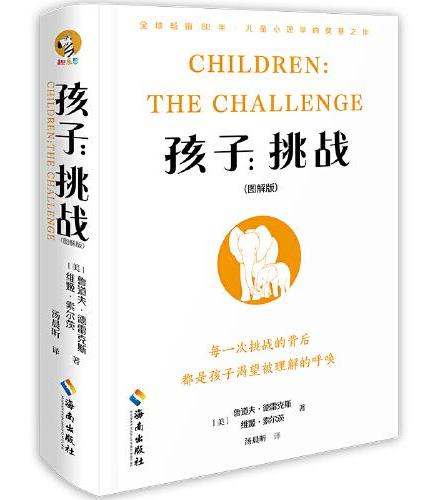
《
孩子·挑战(全新图解版)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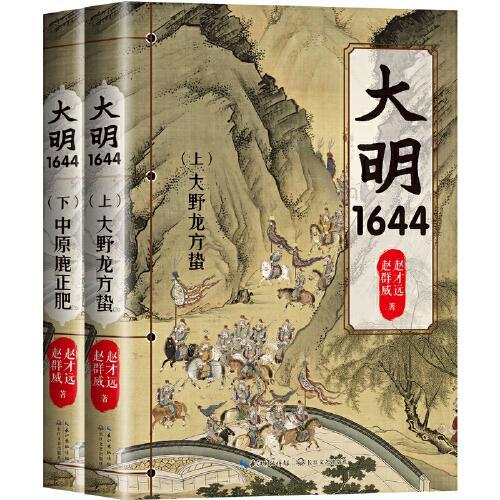
《
大明1644(全二册)
》
售價:HK$
1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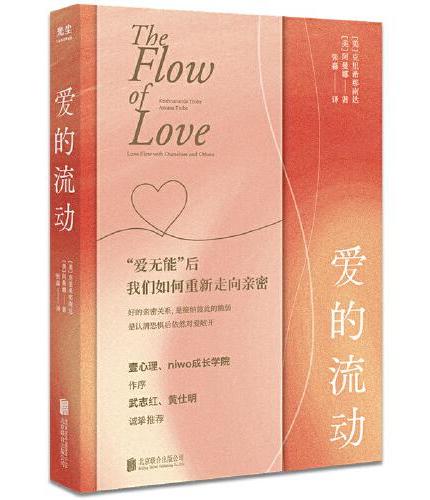
《
爱的流动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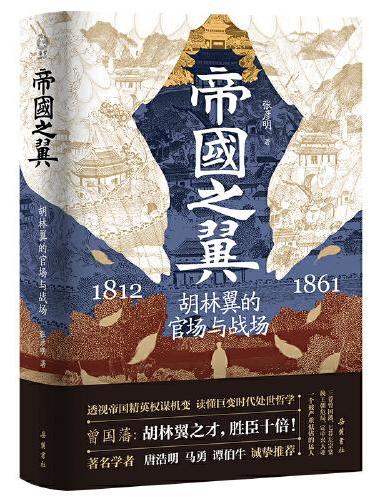
《
帝国之翼:胡林翼的官场与战场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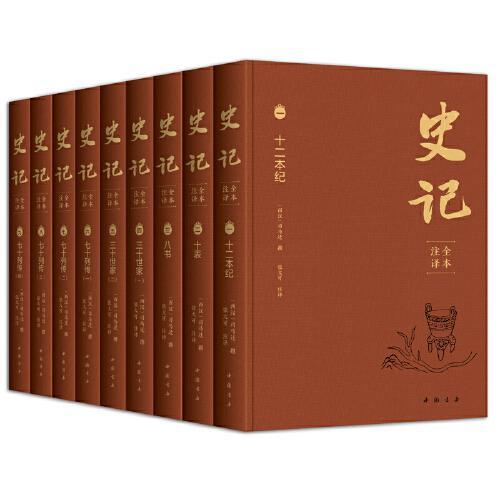
《
史记全本注译(布面精装,全套9册) 附赠“朕来也”文创扑克牌1副!
》
售價:HK$
715.0
|
| 編輯推薦: |
1.新概念作文系列图书历来受读者欢迎;
2.书内作品质朴清婉、笔触细腻;
3.本书精选新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最具实力作者的代表作;、
主营销语:
1.继郭敬明、韩寒、七堇年之后,第十八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新一代文学饕餮盛宴
2.高分作文权威指南,语文精英领航追梦。
3.温情而精致的装帧设计,优质的阅读体验。
|
| 內容簡介: |
|
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是由清华、北大等十四所高校联合举办的全国性文学比赛,继郭敬明、韩寒、张悦然、七堇年之后,新一届新概念获作文大赛新生代潜力股写手最新力作。其中,有一代青少年自我与梦想的呐喊,有校园生活、青春情愫的细细诉说,有故土之思、人生感悟,有对现实的关照、对人性的思索,还有各种新鲜的文体实验。
|
| 關於作者: |
涂山乔
青年作家、图书编辑
第十三届、第十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花火第一届超级明星文学新人选拔赛全国28强之一,曾任《拉萨晚报》记者,《风华新概念作文获奖者范文》系列图书主编。
|
| 目錄:
|
PART1她是黯淡星
时光积匣王书娅
好久不见李乃琛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何晓宁
年轻的蝴蝶兰杨一欣
就像璀璨星光王书娅
演员王若兰
PART2在岛屿之间
怪
兽何晓宁
逃
离冯瀚乐
七零八落沈思岚
请 假胡啸天
我的玛茉莉张心怡
无爱者自拥王若兰
PART3流年花事了
第十三级阶梯王书娅
绿 洲沈思岚
写给弟弟们叶烘楠
起风了苗杰
我会大张旗鼓地回归这里冯浩华
百可王译彬
PART4第十三个星座
青城山下白素贞滕卢涛
人脑电波垃圾站沈思岚
水生胡星海
中毒两个三
晚歌舒阳
雪葬吴百川
陈楚九王若兰
PART5双马镇来客
没有风筝的春天何晓宁
珀舅舅崔健
临夜吴百川
昨夜星辰王书娅
改变的,没变的李乃琛
高考之外余姗姗
|
| 內容試閱:
|
绿 洲
她从杂志中抬起头,十指交叠捧起水壶。西去的长途汽车自进入沙漠以来,窗外就是一成不变的薄沙丘和杂树。她欣赏着缓缓后退的景致,不时偷瞥一眼邻座的男人。
车上的乘客大多拉上了窗帘打盹儿,昏暗中手机翻开又盖上的亮光倏忽即逝。
水汽热腾腾地熏蒸着她的脸,眼镜没一会儿就蒙上了迷离的水雾。她心不在焉地摘下眼镜擦拭,盘算着如何跟他搭话,最终还是用了最快捷的办法共同话题。
嗯,您也看《绿洲》?她扬了扬膝上的杂志。
四目相对一秒有余。
这本书叫《绿洲》?他掀起封面瞟了一眼,我不知道,这是同事送的。
客车缓缓驶入沙漠腹地,顺着公路的静脉流入沙漠的心脏。
逼仄的小书店内冷冷清清,没几个顾客。光线偏黄,有如暮色将近。几步之遥的大街上,阳光普照。日光过于明亮,给人一种做什么都光明正大的感觉。此时的她缩在书店一隅翻找杂志的样子,乍看来真有些偷偷摸摸。
从一摞杂志中准确地抽出《绿洲》,她起身熟练穿梭在狭窄的通道间,硕大的书包没有蹭掉一本书。
《绿洲》这本杂志她每期必买。镇上唯一的书店老板是个很懂经营的人,向来不多不少只进两本,两本都卖掉后才继续进货。不过,《绿洲》每月只有一本,老板说另一本有人订阅了。她不订阅是因为想享受这份提心吊胆的期盼害怕哪个人心血来潮就把唯一的《绿洲》买走了。尽管小镇人口稀少。
老板面前有个男生俯身写着什么,她在一旁等候。只见老板拿出新的《绿洲》给他。那个男生把书塞进包里匆匆离去,单肩包滑下肩头露出跟她一样的校徽。
她瞥了一眼登记簿最末的名字,管仲宁。暗自腹诽,管仲和管宁居然合体了
一阵颠簸后她从车上醒来,邻座的男人还在看那本卷边的旧杂志。
她打了个呵欠懒懒地说:您这本书是前年的吧。男人好像看入迷了,被打断后迷茫地嘟囔:是吗?不知道。
她尴尬地一笑:抱歉,我是《绿洲》的编辑,在沙漠里遇见读者觉得挺有缘的。
学校的图书室像魔法变出的秘境,每天傍晚准时开启结界的大门。她掐点赶来,还是有人捷足先登,一个熟悉的名字占据了首位。管仲宁背对书架坐在大厅中,她则绕过大厅来到她的御座书架尽头孤零零的一张桌子。她拂去桌上的灰尘,坐下看书。没一会儿图书室里三三两两聚集了几对刚填饱肚子的学生,在大厅里小声说话,大声笑。
才看了两章内容,她发现图书室异常安静。人走光了,那个管仲宁还在。突然萌生出好奇,他在看什么书?她把好奇心强压下去继续看了一章,直到图书室阿姨拉长嗓门喊:收馆!她贪婪摄取了最后几行字才合上书。
阿姨可能心情不大好,大嚷着叫他们关灯。管仲宁似乎不常来,对这道命令一头雾水。
你不用管,我去关。她觉得自己把手一挥,十分潇洒。
走出门时,管仲宁正在黑漆漆的走廊上站着,很容易被误会成在等她。她看了眼表上闪烁的荧光字,随即脸色一变,飞奔出图书室朝教室跑去。管仲宁好像愣了一下,不过最后还是跟着她奔到了教室。直到跑到已经开始晚自习的教室外,看见管仲宁的身影闪进了自己身后那扇门,她才大悟,原来姓管的一直在邻班啊
是吗男人说,幸会幸会。我同事啊,是你们的忠实读者呢。
那真难得,我们的受众是青少年啊。
嗬,那家伙心里还是个少年呢。男人打趣道。
汽车在一处站牌前停下。天色近晚,暮色四合,沙丘背后冒出缕缕炊烟。每一个绿洲就是一处站点。
乘客们走下车去舒展筋骨。她独坐出神,咂摸着男人的话。
心里是个少年吗?
文学社第一次活动居然选在放学后的黄昏,还是顶无聊的读书会。她兴趣寥寥,卷着本《绿洲》就去了。在社长发表长篇大论时,她注意到管仲宁也在,就坐在唯一的破窗户底下。昏黄的暮光倾洒在他身上,映得校服扣子明晃晃的。
多年后,她回想起那一天,总觉得那场景不太真实。他整个人掉在光芒里,像一幅浓艳的油彩混在素描画当中。她不禁幻想,那个时候上帝安排他突兀地出现,就是为了拯救她的。
自由读书时间,管仲宁带着一本《绿洲》坐到她面前,心无城府地笑着。这时她注意到他的面相,新疆人,可能是少数民族,五官的轮廓很深,眼窝微微凹陷,眼神显得深邃。一头乱发像野马的鬃毛一般,颇有喜感。
呃,你也看《绿洲》?那匹野马说,在她眼中是边打着响鼻,边喷吐热气。于是她扑哧笑出声来,管仲宁抓着自来卷的头发如坠五里雾。
读书会寡淡如水,只有她跟管仲宁聊得很是投机,倾盖如故。
他们有这么多的共同点,比如都崇拜鲁迅。不知是不是带了同一本《绿洲》的缘故,他们变熟络的速度快得惊人,只几句话的工夫,她把埋在心底多年的秘密都脱口而出了关于她想要成为《绿洲》编辑的梦想。同时她也知道了管仲宁是四段围棋手的事。
那你为什么不加入围棋社?
围棋社的事太多,哪儿还有看书的时间。管仲宁笑答。她则专注于捕获他的每一个表情,如同热衷于收集标本的博物学家。
那天之后,没人发现她上课时不怎么抬头了,而是猫在桌斗前钻研一本叫作《围棋入门》的书。
有时候一见钟情可能无关色相,只因为那个人恰好契合自己卑微的梦想。
车继续向前开,夜幕降临了。
坐了一整天,男人没话找话地问:您来沙漠做什么?旅游还是采风?
来找个人。她欲言又止。
男人正想问下去,后排突然有个人吐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那边,她则转头看向漆黑的窗外。
曾经,高中生活是一片寂寞的沙漠,眼前所见的总是一成不变的沙丘。自管仲宁出现的那一天开始,她的世界里猛然间掀起了一场沙暴,一时之间,满眼兵荒马乱,飞沙走石。
然而现实中的自己所迎来的货真价实的改变,也只是多了个书友而已。说起来,跟别人一块儿看什么青春杂志,感觉怪怪的。
文学社活动还是照常在黄昏进行。她望着窗外一轮红日沉入天边,时间也像沙漏游移一般,不留痕迹地流走。直到她缓过神来,才发觉管仲宁已经停在某一页上等了她许久,才忙不迭地翻页。
一页又一页,真快。感觉自己还没看出些什么呢,高一就这么翻过去了。这一年,她最好的朋友是管仲宁。
那个年代,校园里还没有什么男闺密
蓝颜之类的词汇,男女间稍显亲密,就会惹来流言满天飞,自然包括她与管仲宁。她倒不在乎唾沫星子里的飞短流长她是喜欢管仲宁的,但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庸俗的恋情。如果她刚上高中时就学过哲学的话,一定能将这种感情准确地定义出来。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那是一种感激感激他
将自己从日复一日的沙漠中拯救出来了。
麻木不堪的生活,如同一片乏味的沙漠。
她在日记本上写下这句话时,阳光正好,桌上的橙汁被晒得热乎乎的。管仲宁坐在一边写作业,神情安适仿佛在默诵一首诗。这时她便会想到那个会作诗的文学社社长郝梅,总是在活动课上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她们班那个众星捧月的骄傲女生尧曼,干什么事都要独占风头还有那个宣传部部长胡袖,永远瞪着一双三白眼,说话的嗓门尖得像是要大吵一架她那个患有重度洁癖症的舍友,在旋着圈儿擦拭过自己的杯沿后,还是用狐疑的目光扫遍她的全身
如果生活真是片沙漠,每一颗沙砾都是一个无趣的人。
她曾跟管仲宁倾吐过无数次交际上的烦恼,一遍遍说,一遍遍说:我真的跟谁都处不来,我讨厌所有的人。这时管仲宁就会皱着两条粗眉劝慰她:你别把人家都想得那么坏。
哎,你,没法带我走出沙漠去,只是给我提供暂时的休息,像绿洲一样。
沙漠的夜晚冷得像山尖上积聚的一泓雪水。几乎睡了一天的乘客们此时照样睡得很沉,车内回荡着有轻有重的呼吸声和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她在心里默数着白天经过的几个绿洲四年来,那些地方都被她一一踏遍。
邻座的男人还没有睡,正在吃力地发短信。她得以看清收件人的名字真的撞上了,十年没有见过的人的名字,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出现在邻座男人的手机屏幕上。
她很惊讶自己的镇定。四下沉静的车厢里,她仿若自言自语般地嘟囔:明天就到最后一个绿洲了。
短暂的期末,匆忙的文理分科,青春离去得既荒唐又绵长,像疾速行驶的列车一样匆匆迎面而来又疾驰着与我们擦肩而过。
她得知管仲宁留在理科班是一个日头特别大的燥热的中午。她用凉水揩了好几把脸以保持清醒,然后立在宿舍的公用电话前,深吸了一口气。
管仲宁,是我。
哦什么事?
你不是说要学文吗?
这个,是前几天刚决定的。你也知道啊,我毕业要回阿克苏老家的,学理比较方便,这是真的。
这样啊,那你好好努力吧,再见。
再见。
她搁下话筒,脑袋被风扇吹得一阵眩晕。忍不住埋怨自己最后一句话为什么要说再见呢?该死!真俗气!
果真,那是她跟管仲宁说的最后一句话。文科部和理科部是相背而立的,高中最后两年他们就这样成了近在咫尺的陌生人。她忘记了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没有朋友,没有可以倾诉可以互相鼓劲的人,简直像一具行尸走肉,瞎掉了双眼茫然地徘徊在沙漠中心。
日复一日高强度的学习中,她想起管仲宁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临近高考前,几乎把他忘了。直到发榜那天,她才如梦方醒。她不知道,自己一直都把对他的记忆放在心底,到了某一个结点就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
四处打听管仲宁的成绩,得到的却只是含糊的回答他?好像考得不太好可是也没听说他复读呀不知道要去哪儿上学
失望与隐忧啃噬她的心。此时她惊恐地发觉,行走沙漠的这两年,她已经不知不觉失去了与管仲宁的联系。这下子,天涯海角,人海茫茫,再无寻回他的可能。高考后的暑假,她调动自己那可怜巴巴的人脉,打听管仲宁的下落。还是,没有一点儿消息。
这个人,仿佛藏进沙漠的某处了。
北疆的天空逐渐揭去了拒人千里的黑纱,睁开迷蒙的双目,望着滚滚红尘中慢吞吞移动的客车。天刚蒙蒙亮,旅客们纷纷准备早饭,在饭菜的香气中,她和邻座男人同时开始收拾行李。
两天的旅程,他们已经彼此熟悉。她会心一笑,便问:您也在最后一站下吗?
是啊。男人答,我同事来接我。方便的话和我们一起?我们帮您找人!
那倒不麻烦了。她摆摆手,不过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气象观测站上班的。男人笑起来,其实主业是帮政府种树。她赔着笑了几声,想起男人的行李中那一顶草绿色的鸭舌帽。
密密麻麻的电子稿件铺满整个电脑屏幕,如同无数个针尖戳进她的眼睛。编辑部里开着幽蓝的冷光灯,岑寂。隔壁明亮的休息室里其他编辑说笑的声音清晰可闻。她摘下眼镜,揉着发酸的鼻梁,疲惫地眨了眨眼睛。然后关了电脑,又关掉灯,独自坐在黑暗里。
大学毕业后来到《绿洲》编辑部工作,梦想实现得如此轻而易举。起初她觉得欣喜,不过工作两年多以后欣喜早已被磨平了,她又开始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梦想的生活。
一定是因为人际交往障碍吧,不管在什么环境里,我都像拼图里一个没有凹凸接口的方块那样格格不入。
毕竟过惯了独来独往的生活,她放弃抱怨把工作干下去,告诉自己,因为你在旅途的路上,所以你活该孤独也许只有竹官的信寄来的时候,她的心才会猛地跳动一下。
竹官是一个古怪的作者。在回车键一敲便能群发稿件的年代,他却固执地千里迢迢寄来文稿。尽管如此,竹官的来稿四年间从未间断过,时不时混在全国各地的信件中,特大号的手工信封格外扎眼。
编辑瞥到那个大信封,顺手丢在一旁不是稿件质量太差,只是这个竹官,投稿连地址都不写。而且文章根本不符合稿约,写的永远是沙漠里的生活见闻,新鲜是新鲜,可寄错地儿了。
竹官的第一封信出现在编辑部那晚,她彻夜难眠,脑海里翻腾着过去的事。怎么看都感觉是那个人,竹官,和那个姓管的这么多年了,他还在看《绿洲》啊难道他知道我在这里吗?那为什么不写地址呢?带着胡思乱想,那年春天她回了新疆,去了很多地方,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就是没见到那个过去的人。再后来,她每年都会去新疆,坐着长途汽车在沙漠线上转一圈。来年依旧如此。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不死心,或许再一个十年,或许明天就不行了。而竹官的来信雷打不动,如同眼前的海市蜃楼,或者一片虚幻缥缈的绿洲。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一个月前。新年即将到来,竹官的稿件也破天荒地是一篇校园小说。她展开毛糙的信纸,读着那些熟悉的字,那内容与她的青春如出一辙。
看到文章结尾的话,她在小隔间的塑料桌板上哽咽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她径直走到主编的电脑前,告诉他这篇稿子一定要用,并且她会把稿费送到不知名的作者手里。主编吃惊地看了她好一会儿,大概在想一个不爱说话的小姑娘怎么突然强硬起来。
众编辑也处在云里雾里之时,她毅然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带上新印出的油墨芬芳的《绿洲》,又一次踏上了进疆的旅程。
这一次,仿佛真的有天意,她一上车,就发现邻座上有一个拿着《绿洲》在看的人。
即将到达终点站,车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乘客。沙漠的黄昏,落日熔金,沙砾光辉灿灿。新疆的日光那样强烈。她在心里算了算,刚刚好,十年了。
邻座的男人用她听不懂的语言讲着电话,她把头靠在座椅上,一呼,一吸,堵在身体里的郁结随着这一深呼吸而彻底舒散。
她想象着这些年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自己只是在书店里找《绿洲》,耽搁了些时间而已。
客车抵达最后一个绿洲,缓缓停靠。远处的沙丘背后闪出了一辆破吉普车。随着邻座男人的招手呼喊,车窗里伸出了一个脑袋。戴着草绿色的鸭舌帽。满头的自来卷,迎着风沙乱飞,像野马的鬃毛似的。
快步走过去,生怕慢一点儿他就会被淹没在岁月的尘埃里。
她淡淡看了一眼,然后平静地摘下眼镜,闭眼默数一、二、三。
睁开眼的一刻,她明白,绿洲到了,雨季也来临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