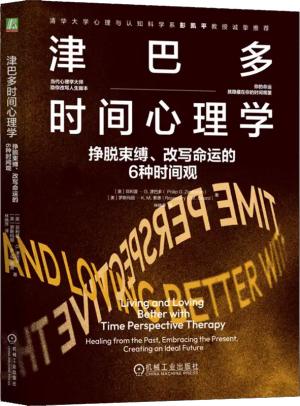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在线百科”
》
售價:HK$
99.7

《
我读巴芒:永恒的价值
》
售價:HK$
132.2

《
你漏财了:9种逆向思维算清人生这本账
》
售價:HK$
55.8

《
我们终将老去:认识生命的第二阶段(比利时的“理查德·道金斯”,一位行为生物学家的老年有用论
》
售價:HK$
91.8

《
谁是窃书之人 日本文坛新锐作家深绿野分著 无限流×悬疑×幻想小说
》
售價:HK$
55.8

《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第3版
》
售價:HK$
110.9

《
8秒按压告别疼痛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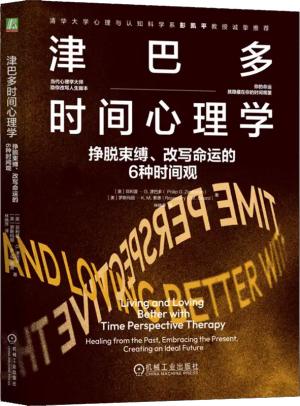
《
津巴多时间心理学:挣脱束缚、改写命运的6种时间观
》
售價:HK$
77.3
|
| 編輯推薦: |
|
正装,皮鞋,汗水, 平庸又局促的我们,拼命扮成憧憬中的Someone。 履历表上短短一两百字的自我介绍能代表什么?社交网络上看似温馨的留言不就只为相互取暖?都快大学毕业了,周遭的同学怎么还在搞那些有的没的?以上,有此心态者,是不屑的曲高和寡?是耍酷的孤高品味?是文青的愤世嫉俗?还是对未来焦虑、不安、逃避的反射?或许各种纠结的心情都有吧,但更重要的是该如何诚实面对自己?逊毙了又如何?我能够承认自己逊毙了,这会是优点,这就是本书作者朝井辽给年轻人的处方。
|
| 內容簡介: |
|
即将面临毕业求职季的大学生拓人,跟几位好友一同讨论求职的策略。但拓人逐渐被更多的困惑与迷茫所束缚:简历上短短一两百字的自我介绍能代表什么?社交网络上看似温馨的留言只为相互取暖?都快大学毕业了,周遭的同学怎么还在搞那些有的没的?拓人并不知道答案,只发现昔日无话不谈的同窗好友,都走上了彼此渐行渐远的道路。而他也越来越迷茫,简历上华丽的辞藻拼凑出的那个人,是谁?
|
| 關於作者: |
|
朝井辽,1989年出生,50年来最年轻的直木奖得主,日本当代青春文学的代言人。 2009年以《听说桐岛要退部》获得新人奖出道,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获得第三十六届日本电影金像奖、第三十四届横滨电影节等多项大奖。 随着朝井辽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在2012年推出以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求职为背景的《何者》,对大学生求职季期间暗自相互嫉妒与日本社会现状的描写精准而深刻。该作品一举获得第148回直木奖。 主要作品:《听说桐岛要退部》《何者》《拉拉队男子!!》《星之窗的声音》《重生》《少女不毕业》《可改写的世界地图》
|
| 內容試閱:
|
|
你是拓人的朋友吗? 嗯!瑞月兴冲冲地点头。 谢谢你来看这场戏。 熟悉的高个男生脸上满是微笑。 祝你今天看得尽兴。 就在那出戏的尾声里,银次宣布了退学。 我在舞台上和银次面对面。经过无数次反复排练,已经在脑海里刻下烙印的台词回荡在整个狭小的演厅里。 (这这是哪儿?我们到这儿多久了?) 最后一次和他面对面是公演四天前的深夜,当时我们都在阿泽学长的公寓里。我当时还抽了烟。 (我也不知道,但我敢肯定这儿不是地球天上,没有太阳,地上,也没有影子。) 那天我们本来是去讨论剧本的大结局,却在最后关头陷入僵持,并产生了很大的争执。那是我第一次因为最后一幕应该表达出何等内容这种问题和他正面冲突。也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在哪儿相互妥协,所以一直以试探的语气争吵。 (但是这儿有光。有光,却没有影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开吵之后,阿泽学长叼着烟卷去了阳台。后来我问他,他说我们刚开始争执的时候其实他感到了些许安心。一切都彻底无法挽回了,他才轻声说:以前你们俩一起搞了那么多创作,却始终没有过争执,这才真让人恶心。 (也不知道。怎么也不会痛、不会饿、不会困。地球上的常识,在这里都无法通用。) 在这场戏里倾注了很大心血的我最后甚至开始越过戏本身,对银次本人展开了人身攻击。 (我们,还活着吧?) 互相压在心里的旧怨一旦爆发,就会超乎想象地无可抑制。话语超越了情绪,像滚开的油锅一样飞溅,我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怨恨的话像连珠炮一样,再也找不回平衡。 (就连这,也不能确定。但既然心脏还在跳动,血脉还在奔腾,我敢说,我们还活着。) 我一直想说的,银次,你少没做明白就乱自我展示我做得很努力了好吗?像埋头写本,不知不觉写了一天什么的,这种话难道不应该等到演出结束之后再说吗?还有那些你跟这个那个会面商讨之类的话,等到公演结束了你再说这次演出还要感谢某某们给我提供了宝贵建议不也行吗?我说真的,你少搞这些利用别人来给自己贴金的把戏了。再说了,什么我这几天看了几本书看了多少场戏都特别没劲你懂吗?跟数量有关系吗?还有,你总说什么在演艺界拓宽人脉,确实你没少往各种剧团庆功宴跑,那你当初勾搭的那几个人现在还有联系吗?你现在给人家打电话,人家搭理你吗?你忙活这些,算什么人脉啊!看你一眼都嫌恶心,真的。 (喂??!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啊?) 正因为总和他在一起,我才会把这些鸡毛蒜皮的毛病都记在眼里。越指责他,我越感觉对每一件事儿都怀恨在心的我器量太小,越为自己感到可耻。即便如此,我也无法停止。 (不要声张!我听到声音了。) 我和银次从大一就意气相投,一起缔造了许多次演出,还说过总有一天,要一块儿建立起一个剧团。我在最靠近他的地方说着这样的话,心里某处却在客观观察我们俩。 (我听到了,你仔细听,就是那边。) 根本不可能。我在心里某处冷眼看待我们俩。 (声音?) 我们浑身是病态,我已经再也看不下去了。 (听啊,它在说话!看啊!它在挥手!来啊,来啊这不是在呼唤着我们吗?) 大概那个时候我是着了魔了。我在想,为什么只有我自己感受到了弥漫在我们身上的,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气息呢? (等等!) 会面、研讨会、演艺圈的人脉。你光用这些假模假式的词儿,成不了什么人物。只要你还想着要把自己晒给谁看,你就绝对绝对成不了什么人物。 不管是什么想法,只要还装在脑子里,不论何时你都会觉得它是杰作。你会永远陷在里面,再也不能自拔。 (刚才听到的声音,难道是) 我本来没想说这么多。但当时我一心只想把这些东西推到他眼前。这些一直以来在他身边却始终藏在我心里,决心总有一天要给他看的东西。这些深藏已久,极其残酷,本以为已经在我内心最深处生根发芽了的东西,一口气从浅得超乎想象的地方喷涌而出。 (这不是我们的声音吗?) 银次却说。 (怎么回事?) 我本来就在考虑这件事。现在我决定了。这次公演结束后,我要退出行星剧团,还要退学。 我决心,要靠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找工作,我要过艺术人生。 (我们,在向自己挥手?) 我猜,银次肯定也像我想把这些东西全倒出来一样,一直都想把自己的决心甩到我眼前给我看。我们互相亮出了底牌,再也无话可说。 (什么?你在说什么?) 剧场很小,所以我一眼就看到瑞月直勾勾地望着台上的我们。她的眼神和她在班级聚餐上说佩服那个自告奋勇收钱的姑娘所表现出称赞时的眼神一模一样;和她听到我说自己是写舞台剧脚本的,说佩服我所表现出尊敬的眼神一模一样。现在这道眼神还在直视着我。 (那边的我们,并不是在呼唤着我们。) 别看了。我当时想道。 (他们是、他们是在和我们,挥手告别。) 舞台转暗。 我和银次退下舞台,各自准备下一幕。你是拓人的朋友吗? 嗯!瑞月兴冲冲地点头。 谢谢你来看这场戏。 熟悉的高个男生脸上满是微笑。 祝你今天看得尽兴。 就在那出戏的尾声里,银次宣布了退学。 我在舞台上和银次面对面。经过无数次反复排练,已经在脑海里刻下烙印的台词回荡在整个狭小的演厅里。 (这这是哪儿?我们到这儿多久了?) 最后一次和他面对面是公演四天前的深夜,当时我们都在阿泽学长的公寓里。我当时还抽了烟。 (我也不知道,但我敢肯定这儿不是地球天上,没有太阳,地上,也没有影子。) 那天我们本来是去讨论剧本的大结局,却在最后关头陷入僵持,并产生了很大的争执。那是我第一次因为最后一幕应该表达出何等内容这种问题和他正面冲突。也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在哪儿相互妥协,所以一直以试探的语气争吵。 (但是这儿有光。有光,却没有影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开吵之后,阿泽学长叼着烟卷去了阳台。后来我问他,他说我们刚开始争执的时候其实他感到了些许安心。一切都彻底无法挽回了,他才轻声说:以前你们俩一起搞了那么多创作,却始终没有过争执,这才真让人恶心。 (也不知道。怎么也不会痛、不会饿、不会困。地球上的常识,在这里都无法通用。) 在这场戏里倾注了很大心血的我最后甚至开始越过戏本身,对银次本人展开了人身攻击。 (我们,还活着吧?) 互相压在心里的旧怨一旦爆发,就会超乎想象地无可抑制。话语超越了情绪,像滚开的油锅一样飞溅,我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怨恨的话像连珠炮一样,再也找不回平衡。 (就连这,也不能确定。但既然心脏还在跳动,血脉还在奔腾,我敢说,我们还活着。) 我一直想说的,银次,你少没做明白就乱自我展示我做得很努力了好吗?像埋头写本,不知不觉写了一天什么的,这种话难道不应该等到演出结束之后再说吗?还有那些你跟这个那个会面商讨之类的话,等到公演结束了你再说这次演出还要感谢某某们给我提供了宝贵建议不也行吗?我说真的,你少搞这些利用别人来给自己贴金的把戏了。再说了,什么我这几天看了几本书看了多少场戏都特别没劲你懂吗?跟数量有关系吗?还有,你总说什么在演艺界拓宽人脉,确实你没少往各种剧团庆功宴跑,那你当初勾搭的那几个人现在还有联系吗?你现在给人家打电话,人家搭理你吗?你忙活这些,算什么人脉啊!看你一眼都嫌恶心,真的。 (喂??!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啊?) 正因为总和他在一起,我才会把这些鸡毛蒜皮的毛病都记在眼里。越指责他,我越感觉对每一件事儿都怀恨在心的我器量太小,越为自己感到可耻。即便如此,我也无法停止。 (不要声张!我听到声音了。) 我和银次从大一就意气相投,一起缔造了许多次演出,还说过总有一天,要一块儿建立起一个剧团。我在最靠近他的地方说着这样的话,心里某处却在客观观察我们俩。 (我听到了,你仔细听,就是那边。) 根本不可能。我在心里某处冷眼看待我们俩。 (声音?) 我们浑身是病态,我已经再也看不下去了。 (听啊,它在说话!看啊!它在挥手!来啊,来啊这不是在呼唤着我们吗?) 大概那个时候我是着了魔了。我在想,为什么只有我自己感受到了弥漫在我们身上的,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气息呢? (等等!) 会面、研讨会、演艺圈的人脉。你光用这些假模假式的词儿,成不了什么人物。只要你还想着要把自己晒给谁看,你就绝对绝对成不了什么人物。 不管是什么想法,只要还装在脑子里,不论何时你都会觉得它是杰作。你会永远陷在里面,再也不能自拔。 (刚才听到的声音,难道是) 我本来没想说这么多。但当时我一心只想把这些东西推到他眼前。这些一直以来在他身边却始终藏在我心里,决心总有一天要给他看的东西。这些深藏已久,极其残酷,本以为已经在我内心最深处生根发芽了的东西,一口气从浅得超乎想象的地方喷涌而出。 (这不是我们的声音吗?) 银次却说。 (怎么回事?) 我本来就在考虑这件事。现在我决定了。这次公演结束后,我要退出行星剧团,还要退学。 我决心,要靠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找工作,我要过艺术人生。 (我们,在向自己挥手?) 我猜,银次肯定也像我想把这些东西全倒出来一样,一直都想把自己的决心甩到我眼前给我看。我们互相亮出了底牌,再也无话可说。 (什么?你在说什么?) 剧场很小,所以我一眼就看到瑞月直勾勾地望着台上的我们。她的眼神和她在班级聚餐上说佩服那个自告奋勇收钱的姑娘所表现出称赞时的眼神一模一样;和她听到我说自己是写舞台剧脚本的,说佩服我所表现出尊敬的眼神一模一样。现在这道眼神还在直视着我。 (那边的我们,并不是在呼唤着我们。) 别看了。我当时想道。 (他们是、他们是在和我们,挥手告别。) 舞台转暗。 我和银次退下舞台,各自准备下一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