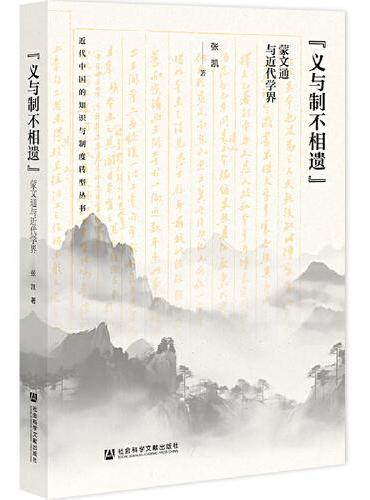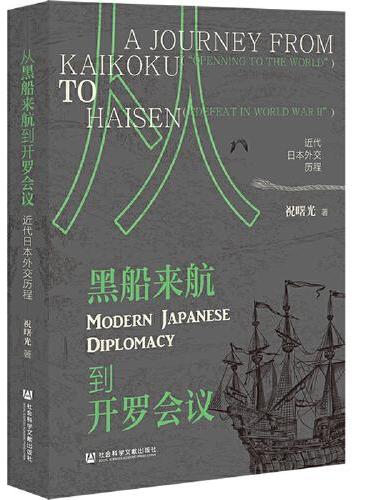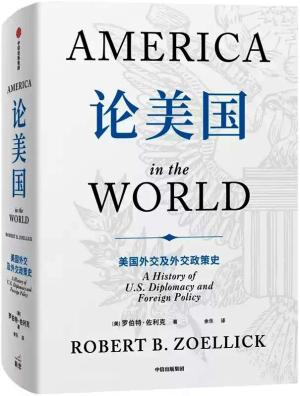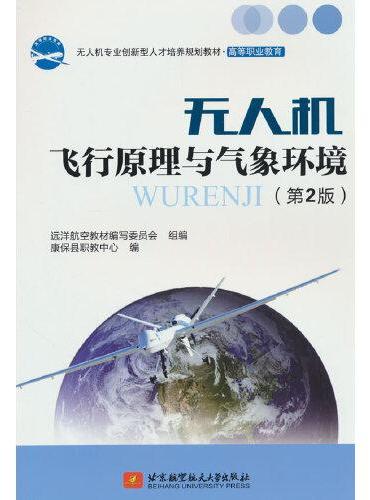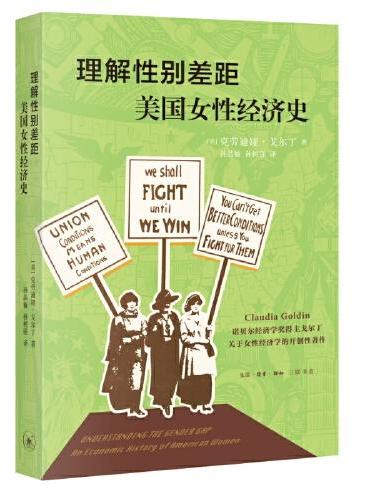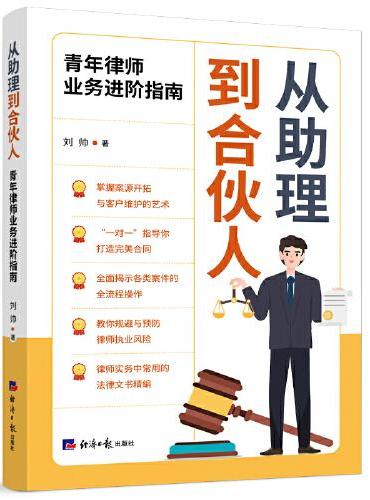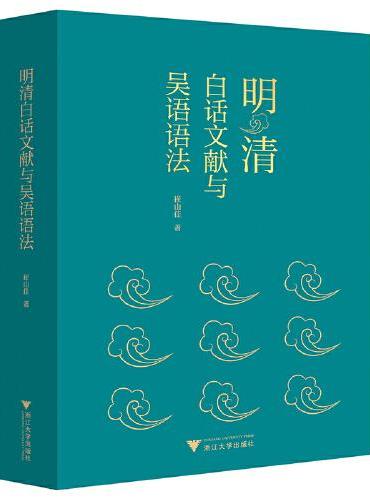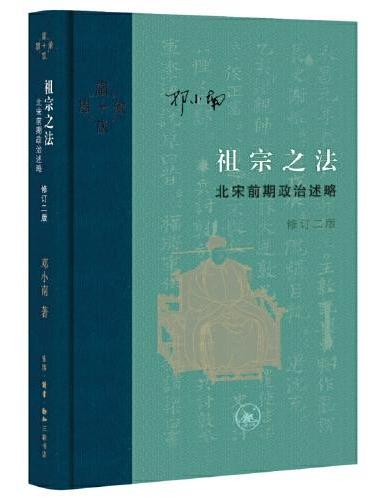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义与制不相遗”:蒙文通与近代学界
》 售價:HK$
107.8
《
从黑船来航到开罗会议:近代日本外交历程
》 售價:HK$
140.8
《
论美国(附赠解读手册)
》 售價:HK$
140.8
《
无人机飞行原理与气象环境(第2版)
》 售價:HK$
31.9
《
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
》 售價:HK$
90.2
《
从助理到合伙人-青年律师业务进阶指南
》 售價:HK$
74.8
《
明清白话文献与吴语语法
》 售價:HK$
217.8
《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二版)
》 售價:HK$
107.8
編輯推薦:
《非凡的时光: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与波斯纳、阿克曼等法学大家对坐,闲聊学术与人生、光荣与梦想,一起重返美国法学的辉煌时代。作者选取了当今最为知名的十位法学大家,与之对谈,这些法学家代表了当代最重要的十个法学流派(法律经济学、自由主义理论、批判法学等)。阅读本书,可以初步了解法学理论的整体脉络。本书采用对谈录的形式,用浅白的口头语讲述法学理论,深入浅出,好看易懂。除了最前沿的法学思想,本书更多展现的是这些法学大家的成长历程,他们的人生与梦想,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以及让人忍俊不禁的八卦。
內容簡介:
《非凡的时光: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是哈克尼教授与当今美国最为知名的十位法学家的对谈录,与谈者包括享誉世界的波斯纳、肯尼迪、阿克曼等法学大家,他们是当代各大法学流派批判法学、法律经济学、法律与社会、自由主义法学等的代表人物。 本书带您深入十位法学大家的理论世界和心路历程,重返美国法学史上那个大师辈出、流派纷呈的巅峰时代。
關於作者:
詹姆斯哈克尼,美国东北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1986年本科毕业于南加州大学,主修经济学;198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获法律博士学位,读书期间曾担任《耶鲁法学杂志》编辑。著有《非凡的时光:重返美国法学的巅峰时代》《披着科学的外衣》等。
目錄
导言
內容試閱
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