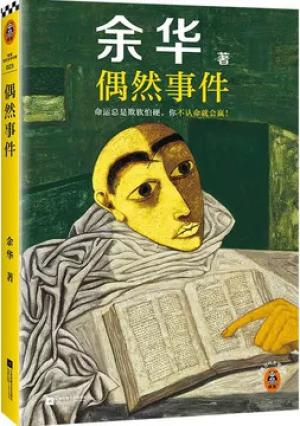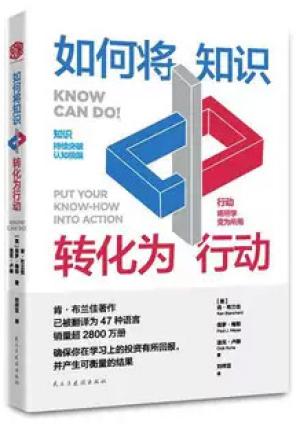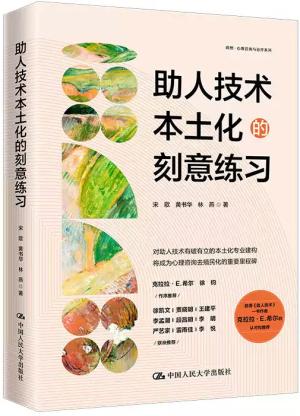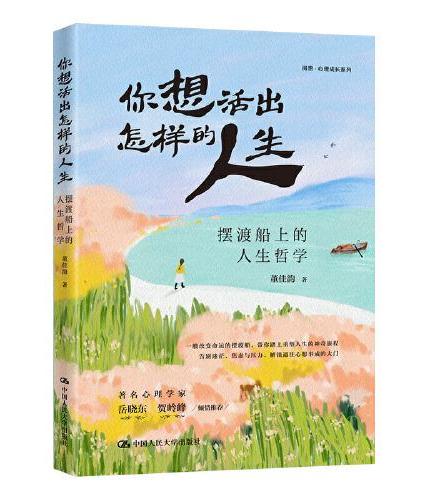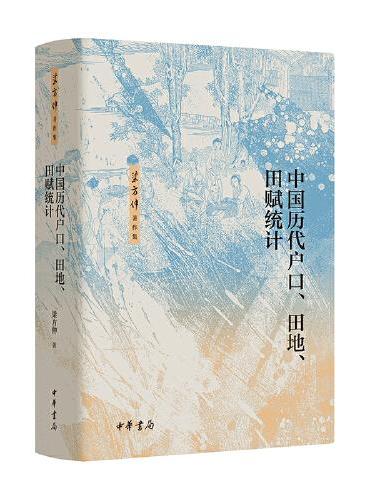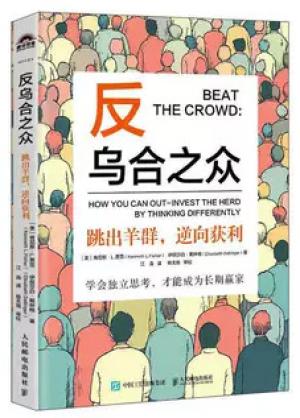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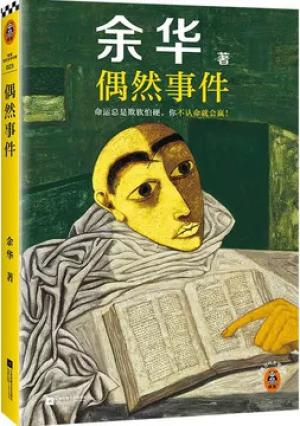
《
偶然事件(命运总是欺软怕硬,你不认命就会赢!)
》
售價:HK$
54.9

《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2025)
》
售價:HK$
2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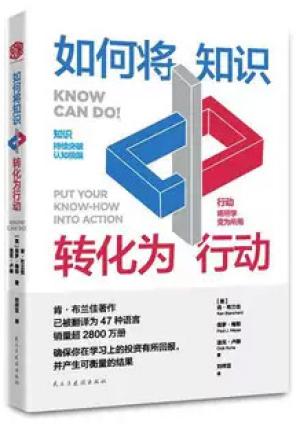
《
如何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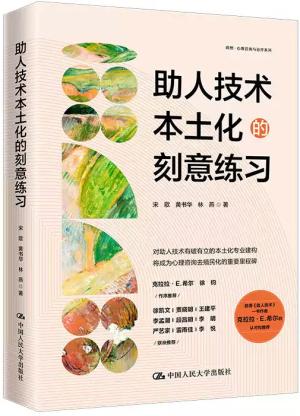
《
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
售價:HK$
87.9

《
中国城市科创金融指数·2024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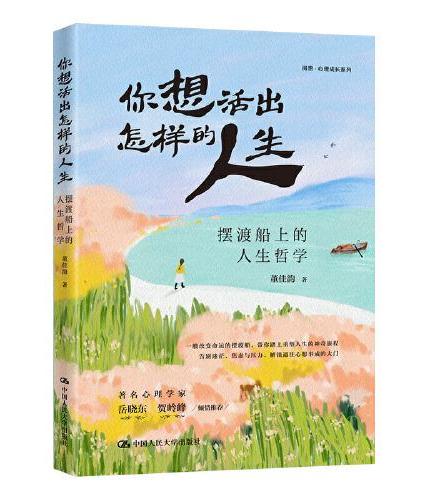
《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摆渡船上的人生哲学
》
售價:HK$
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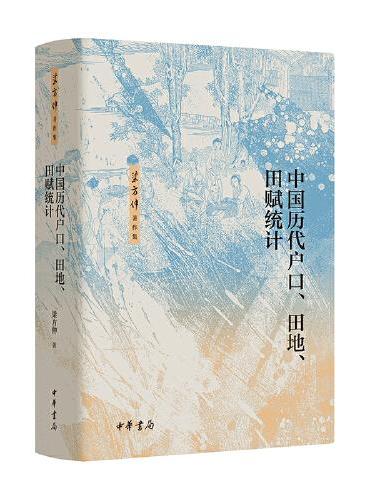
《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HK$
14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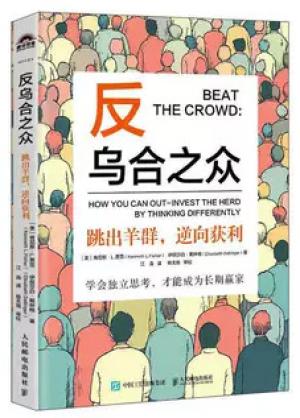
《
反乌合之众——跳出羊群,逆向获利
》
售價:HK$
76.8
|
| 編輯推薦: |
★ 无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立场的政治思想者
★ 都难以摆脱他那充满悖论与危险的思想幽灵
★ 20世纪极具争议政治思想家、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成名之作
★ 开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之先河
|
| 內容簡介: |
一切浪漫现象都是受非浪漫力量的控制。
昂首超然于各种限制与决断之上的人,变成了异己势力和异己决断的臣仆。
——卡尔·施米特
浪漫主义是19世纪西方的主导精神,对于思想史研究而言,政治的浪漫派问题不可小视。《政治的浪漫派》是施米特的代表作之一,初版于1919年,1925年再版并增加长篇序言,关注的是作为政治哲学的浪漫主义,看似思想史论著,其实针对的是现实政治问题,其用意在于表明浪漫派的“永恒交谈”与自由主义议会民主制的公开辩论基于相同的形而上学真理论。本书开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之先河,晚期的浪漫主义哲学研究(如伯林)尚不及其所达到的思想深度。施米特从德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出发,讨论浪漫派在思想史上的位置,阐明了浪漫派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基本看法,并表明了它的本质是一种关于政治的趣味。本书着力在思想史的脉络里整理弥漫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精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思想史力作。
|
| 關於作者: |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年7月11日-1985年4月7日)
20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最后一位欧洲公法学家
施米特的写作生涯长达60余年,在20世纪诸多重大政治思想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20世纪的霍布斯”之称,其思想对20世纪政治哲学、神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决断论为著;并提出了许多公法学上的重要概念,例如制度性保障、实质法治国,及法律与主权的关系等。
施米特出生在德国西部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个小镇普勒腾贝格的天主教家庭,从小喜好文学、艺术、音乐、哲学、神学,曾就读于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与斯特拉斯堡大学。1910年完成博士论文《论罪责与罪责模式》,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施米特一边研究新康德主义法理学,一边写论瓦格纳的华彩文章。1916年以《国家的价值与个人的意义》(一文取得教授资格,并发表了一部从政治哲学角度论诗人多伯勒的长诗《北极光》的专著,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思想生涯。同年,与塞尔维亚女子帕芙拉·多萝蒂克结婚。
1933年,施米特担任柏林大学教授,同年,出于诸多策略性的考量,加入纳粹党。“二战”后,施米特曾被冠以“第三帝国桂冠法学家”的称号。1933—1936年,施米特担任普鲁士政府成员,享有众多学术职位,包括著名的《德意志法学家报》主编。1936年后,施米特因其在纳粹执政前后态度之转变,及其入党甚晚的事实而渐受部份党政高层质疑,且受到党卫军机关报《黑衣军团》的攻击。战后被盟军逮捕并移送至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应讯,却未被起诉而获开释。施米特后因拒绝与西德政府“去纳粹化”政策妥协而被剥夺正式任教之权利。纵然如此,施米特仍持续著书立说,对西德公众舆论以及欧洲左、右翼知识精英发挥其影响力。施米特以96岁高龄逝世于慕尼黑,葬于故乡普勒腾贝格,墓碑上铭刻着施米特对自己的盖棺论定:“他通晓律法。”
施米特与马克斯·韦伯曾有所来往,且深受其影响,部分地继承了韦伯对现代性批判的论题,其中一个明确的倾向就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但称施米特为“反自由主义者”,则失之草率,有学者认为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来自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批判。
译者
冯克利 1955年生,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内公认一流水准的翻译家,自1990年代以来对于学术思想的传播有突破性的杰出贡献,在公共思想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思想史。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译著包括勒旁《乌合之众》,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经济、科学与政治》《自由主义》《科学的反革命》《哈耶克文选》,考德威尔《哈耶克评传》,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伯林《反潮流》,霍布斯《论公民》,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德沃金《至上的美德》,牛津大学《英美哲学概论》,布坎南《立宪经济学》,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等。
刘 锋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并担任《国外文学》编辑工作。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以及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思想文化的研究。著有《的文学性诠释与希伯来精神的探求》等,并曾发表文学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十几篇,学术译著包括《基础神学》《宪法学说》等多部。
|
| 目錄:
|
编者说明(刘小枫)
再版前言[1924]
导论
一、表面状况
二、浪漫精神的结构
1.寻求实在
2.浪漫派的机缘论结构
三、政治的浪漫派
结语:政治浪漫派作为政治过程的伴生性情绪反应
人名译名对照表
|
| 內容試閱:
|
一切被浪漫化了的对象的机缘性质
浪漫派的感受借以塑造自身的知识素材,相对于布景而言是无关紧要的,这一点对于政治浪漫派尤其重要。并非对政治领域的一切感受都需要落实为政治结社。从诺瓦利斯那儿,我们看到了如下事实最简单明了的事例:对政治对象的机缘性印象,被转化为诗与自然哲学之间的彷徨,非政治的印象反映在政治结合之中。政治在比喻中被诗化了,例如:军事伪装是鬼火;士兵身着色彩鲜艳的制服,因为他们乃国家的花粉;金银是国家的血液;国王是太阳系中的太阳。来自自然哲学、神学或其他“更高”科学中的许多类比的运用,情况也是如此。在这里,把对象提升到诗的境界这一目的才是关键所在。类比的目的不是概念的澄清,或是为了建立学说和方法论,这是真正的自然哲学家—他们不是浪漫派—的事情,即使他们犯下了最粗暴地滥用类比的过失。“君主制是真正的制度,因为它同一个绝对中心联系在一起”这类证明,也出现在博纳德的著作里,它们反映着一种经院哲学式的、理论上对统一性的偏好。在德· 迈斯特那儿,它们是对一种合乎法统的、极不浪漫的最高权威之需要的结果。而在诺瓦利斯那儿它们受审美的左右,它们是诗的具象。这清楚地表现在下面这些话里:等级制是“国家的对称的根系,是作为政治自我之理性认知的国家组织的原则”。在这里,来自自然哲学、费希特、美学和政治学的各种联想,被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变成了一堆紧凑但本质上毫无价值的比喻泡沫。
浪漫派这种对待事物的方式,是建立在不断从一个领域逃向另一个领域,逃向另一“更高的”第三种因素,以及把不同领域的观念搅在一起的习惯上。佐尔格指出,缪勒的著作中全是“假冒伪劣的货色”;威廉· 格瑞姆尖锐地说道,他觉得缪勒著作中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借来的”。他们指出了第二条原则:这种大杂烩是在利用别人的思想,它除了导致似是而非的颠倒的文学夸张外,没有任何能动性。不过给人以虚假印象的还有第三种因素,它来自浪漫化的精神特点:浪漫派的形式游戏的场所永远是机缘的。因此浪漫派的虚假论证能够为任何状态辩护。今天,集权制的警察国家是没有生命的人造机器,不应当为它而牺牲等级制特权的活力。明天这些特权成了一个巨大活体必须加以保留的强健肌肉。分权制能表示对整个有机体的人为破坏。明天它又能表示存在于整个自然界的反题,即在互动中—因为战争是万物之母—诞生的作为更高统一体的有机体之反题的活力表现。人为的“制造”是最不自然的和令人厌恶的。但普鲁士民族的伟大却在于它自觉创造了被自然所否定的东西。今天,法国大革命是伯克所认为的反常的偶像崇拜和没有意义的罪行。明天,它又可以成为“自然的力量,受压迫受奴役的生命的亲和性选择”,它打破了道德顾虑和形式的束缚,如此等等。
扼要说明政治浪漫派与浪漫派政治的区别:对后者来说,结果而非原因是机缘性的
在面对每一种新印象时缺少连贯性和道德上无所依傍,其根源在于浪漫派以审美为本质的创造力。就像伦理或逻辑一样,政治与他是格格不入的。不过,或许应当把政治浪漫派跟浪漫主义的政治家区别开来。本质上不是浪漫派的人,也可以受到浪漫主义观念的激励,他能让自己的源于其他因素的活力受这种观念的支配。为了避免讨论这里所涉及的复杂政治活动,我只想说说大学生卡尔· 路德维希· 桑德(Karl Ludwig Sand )对科策布的刺杀(1819 年3 月20 日),作为这种浪漫主义政治的典范。
桑德的成长过程很符合18 世纪教育年轻人的严格道德标准。他在童年和青年时代刻苦磨练意志,强迫自己不屈从于软弱的欲望和嗜好。在法国,罗伯斯庇尔堪称恪守道德的著名典范,这被说成是“古典精神”(esprit classique )严格传统的后果。在德国这个概念却会引起误解,因为德国的古典主义受人道主义和卢梭思想的影响,其早期的严厉已有所松弛。但是它仍然存在于德国,它在桑德身上造成的结果是,他保留着心理内省和果断行事这种非浪漫的能力:一般意义上而非“更高”意义上的行动能力。作为一名大学生,他加入了当时流行的已经有抒情牧歌意味的浪漫主义。他热衷于古老的民谣,他赞美中世纪的纯真。他坚信自己对自由和没有任何浪漫主义痕迹的国家的理想。在这个可敬的人看来,科策布—这个贪婪而又恶毒的俄国老走狗—是敌人。以厌恶沙皇作为其表现的原始的大学生政治,并没有特别浪漫的东西。德国人爱国热情的方向,是自觉地只反对一切法国的东西:反对高卢主义,它是受到排斥的敌人,它的外来统治削弱了民族意识。作为“高卢人”的科策布是“道德的”,但这仅限于指他性情温和。大体上,学生们把他视为“叛徒”和为一种要让德国的大学生组织失去道德精神的政治势力效力的奸细。然而,不能说桑德有着针对某个敌人的明确的政治和民族感情,他的决定是这种情感的结果。这一行动的动机肯定来自政治观念。但是选定科策布也许只能这样来解释:在桑德看来,那个“恶棍”已经变成了卑鄙无耻的象征。他成了浪漫主义的虚构之物。即使桑德的行动仅以爱国动机为基础,仍然改变不了科策布在政治上显然无足轻重这个事实。这一事件具有浪漫主义的结构,是因为一个纯粹偶然的对象,成了一种严肃而重要的政治意图的牺牲品。因此这种结构也是机缘性的,因为政治着力点是以机缘方式选定的。只有它的方向是由外部决定并且是反政治浪漫主义的。因此结果,即后果,是机缘性质的;呈现的不是原因,而是机缘性结果。强大的政治能量没有能力找到自己的目标,它把巨大的力量用在了机缘性的时刻。
这种以浪漫方式设想机会的政治,其不朽的典型是堂· 吉诃德,他是个浪漫主义的政治形象,但不是一个政治浪漫派。他不去理解更高的和谐,而是能够分清对错,作出在他看来有利于正义的决定。这种能力为浪漫派所无,因此,甚至施莱格尔和缪勒的浪漫主义法统论也只能被解释成他们不关心正义的结果。对自己骑士理想的热情和对假想的不义的愤慨,驱使这位可怜的骑士不自觉地对外部现实视而不见,他也不以审美的态度撤退到自己的主体性中去,构想批判现状的怨言。他真诚的热情使他陷入了浪漫主义的优越感变为不可能的境地。他的战斗荒唐可笑。然而这仍是战斗,他把自己置身于危险而不是更高级的战斗之中,譬如亚当· 缪勒所说的那种艺术家与材料的战斗,或鞋匠跟皮革的战斗。他有着一名骑士对自己身份的真诚热情,而不是市民阶级对贵族的印象的热情。在19 世纪,贵族的浪漫派和贵族本身,如阿尔尼姆和艾兴多夫(后者正好也认同于堂· 吉诃德)绝对没有能力表现出像市民阶级作家施莱格尔和缪勒那样的政治浪漫派风格。然而,即使在堂· 吉诃德身上,本体论成为新问题的新时代迹象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个西班牙贵族常常接近于一种主观的机缘主义。他宣称自己对杜尔西妮娅(Dulcinea )的思念比杜尔西妮娅的真实面貌更重要。这是因为杜尔西妮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依然是理想奉献的对象,这鼓舞着他做出伟大的举动。
向着更高的、主观的创造性的机缘转移,可把一切反题消解于和谐的统一体之中。如果不存在这种转移,也就不存在浪漫主义。这就是把古代或中世纪历史人物描述为浪漫派—基于其个性方面尤其是心理病理学方面的相似性—的无数历史类比,为何经常把这个词只作为政治空谈的象征,作为“暧昧”、“古怪”的同义词,作为一种亢奋的心理状态或空想主义的原因。在这里,这种描述的模糊性与历史类比的普遍不确定性有关。凡是拿一个罗马皇帝与一个19 世纪的统治者作比较的人,会把双方改造成某种形象,其特点更多地是由坚持考虑双方的相似性而不是由踏实的研究所决定的,而那种相似性是有待证实的。因此浪漫派的特点也能被赋予那个皇帝,并不考虑浪漫派在多大程度上只是现代特有的现象。例如,当苏亚雷斯(André Suarès )把尼禄(Nero )皇帝—他通过出色的心理观察,把尼禄描述成一个残暴、任性而又矫揉造作的小丑—打扮成一副现代模样时,这就是浪漫派的一种人为产物。这种历史对照和类比是文学创作的来源。它们喜欢把已经变成了神话或传奇的公式、被蒙上一层感情迷雾的历史名人和事件,当作有价值的动机。浪漫派如缪勒和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根据拿破仑来塑造阿提拉(Attila)或成吉思汗,他们利用这些形象,与诺瓦利斯利用圣母玛利亚的方式如出一辙。这种浪漫主义不涉及任何政治活动。与它的内在前提和方法相一致,它旨在产生审美效果。但是它也能被有意或无意地用于政治煽动,它能产生超出浪漫主义的政治效果—换言之,一种政治激情的产物,就像奥柏的《波蒂奇的哑女》(La Meutte de Portici )变成了一种政治行动,或奥柏变成了政治家一样,因为在1830 年的比利时革命中,这部歌剧激起了革命者的热情。出于政治兴趣并被当作政治工具的历史类比,则与此有所不同。一个浪漫派塑造政治典型的努力之最著名的历史类比之一—大卫· 费里德利希· 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的《叛教者尤利安—王座上的浪漫派》(Julian den Abtrünnigen, den “Romantiker auf dem Throne der C.saren”, Mannheim, 1847),就是建立在这种典型的政治考虑上。它对“政治浪漫主义”的概念内涵特别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