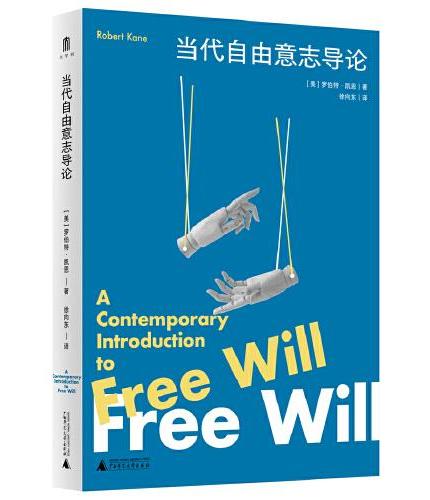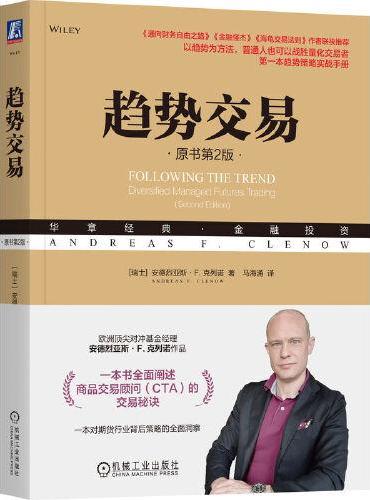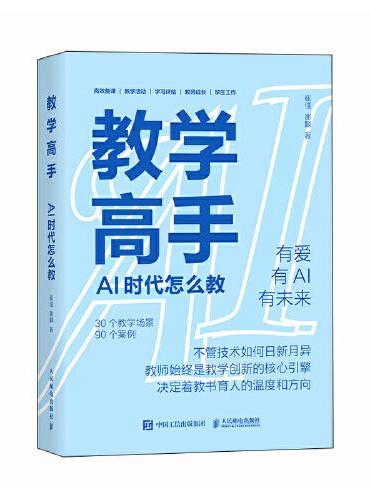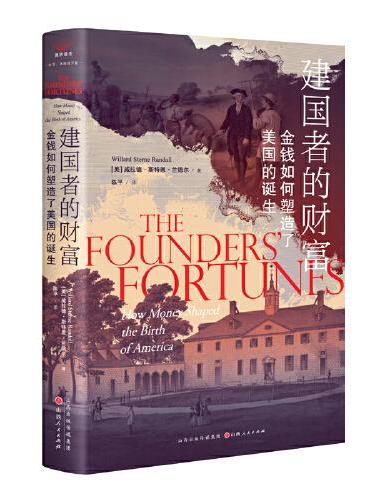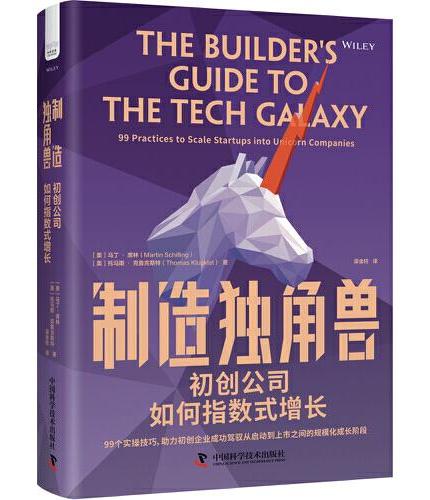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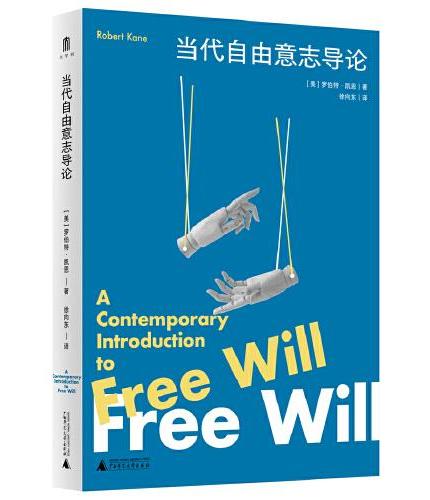
《
大学问·当代自由意志导论(写给大众的通俗导读,一书读懂自由意志争论。知名学者徐向东精心翻译。)
》
售價:HK$
74.8

《
(格式塔治疗丛书)进出垃圾桶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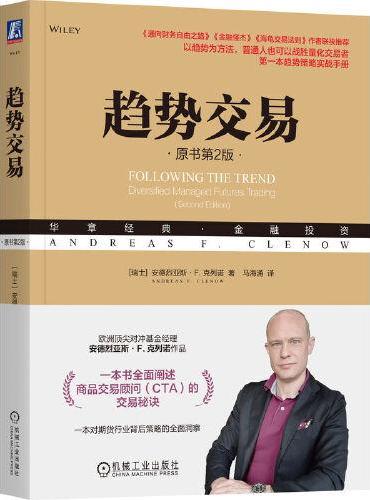
《
趋势交易(原书第2版)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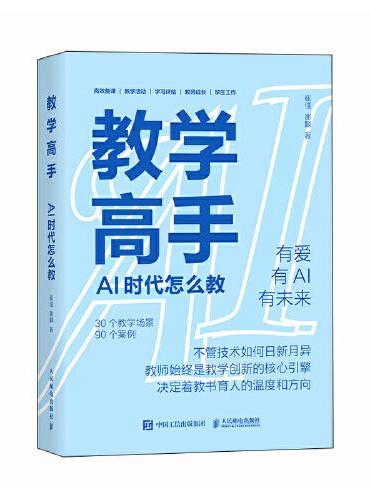
《
教学高手:AI 时代怎么教
》
售價:HK$
65.8

《
中国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报告2025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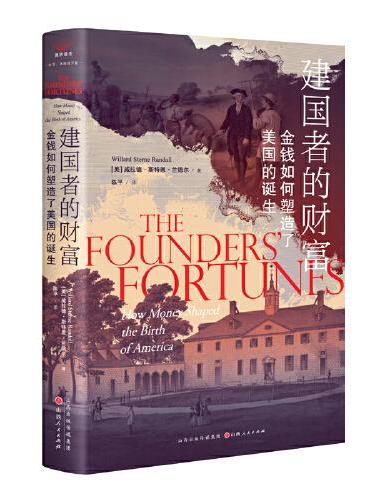
《
建国者的财富:金钱如何塑造了美国的诞生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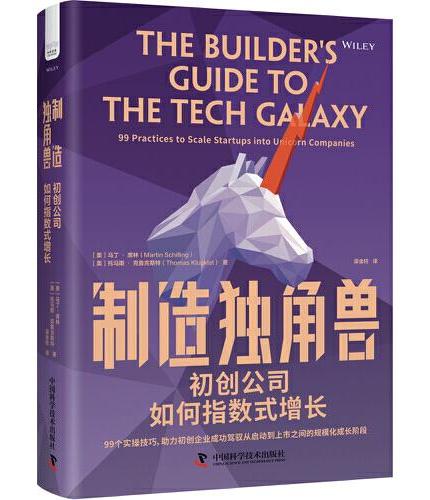
《
制造独角兽:初创公司如何指数式增长
》
售價:HK$
86.9

《
绿色黄金 : 茶叶、帝国与工业化
》
售價:HK$
75.9
|
| 編輯推薦: |
|
温暖甜宠派古言大神看泉听风继《九重韶华》之后**古言《玉堂金阙》,看泉听风的小说不但对历史的考据比较严谨,写法上也很有中国古代刻画人物的特点,就是通过细节语言刻画人物。晋江点击上千万、积分上亿的**力作!
|
| 內容簡介: |
《玉堂金阙》讲述了吴郡陆氏的嫡长女陆希,原想低调平静的过完这一生,却不想三岁那年,因继母陷害,被高严救起后,她就注定了卷入了皇朝翻云覆雨的争斗。
高严,出身就带着逼死生母的原罪,父亲厌弃,众人嫌恶,对他来说,生命之中,**的一线阳光就是陆希,他对陆希的感情纯粹明净,却因家族深陷皇位之争,而让陆希举棋不定。
直到陆希父亲陆琉的猝死,皇家的逼迫,让陆希在一夜之间被迫成熟坚强,她抓紧了高严伸出的手,两人从年少之时的相知相许,到后来的相濡以沫,两双手始终没有分开过。
从宋朝的两次废立太子,高家从一人之上的权臣,一度低至谷底;到高家举事造反;从高严之父高裕登上皇位,到父子、兄弟相残,高严一路走来,披荆斩棘,可他从来没有回头,也没有动摇,因为知道他身后总有一人会永远陪伴着自己……
|
| 關於作者: |
|
看泉听风,晋江文学城超级积分榜作家,温柔甜宠派古风代表作者,擅长写温暖甜宠文,文笔细腻、轻快,善于从细节描绘人物个性、驾驭故事场景。
|
| 目錄:
|
上
楔子 1
**章 14
第二章 40
第三章 57
第四章 93
第五章 124
第六章 147
第七章 171
第八章 192
第九章 223
第十章 249
下
第十一章 1
第十二章 15
第十三章 63
第十四章 92
第十五章 127
第十六章 156
第十七章 185
第十八章 206
第十九章 227
第二十章 243
后 记 256
|
| 內容試閱:
|
上 册
楔子
建始五年冬,天色阴沉沉的。
“呸!这鬼天气!冻死人了!”建康城郊一处简陋的农庄里,一名穿着薄皮袄、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从外面冲了进来,身上、头上还带着积雪。
屋内一名老妪正蹲在炭盆旁烤火,一见大汉回来了,忙起身给大汉拍着身上的雪:“回来了,快进来暖暖。”
“阿娘有东西吃吗?饿死了。”大汉从怀里解下一个钱袋递给老妪。
“有麦饭,你在炭盆上热热就能吃了。”老妪解开钱袋数着里面的铜板,“这次比前几次多了些?”
“天气冷,也没人能打到野味,野味的价钱涨了不少。”大汉回头见里屋黑乎乎的没点灯,“二少君又出门了?”
“又出去抓野兔子了吧。”老妪叹气,“八九岁的孩子哪里能不馋肉?”
“阿娘你没给二少君吃肉吧?”大汉警觉地问。
“没有,你都说了那么多次了,我哪敢给。”老妪说。
大汉松了一口气:“将军是再三说了不能给二少君吃肉的,说少君火气大,要吃点素压性子。”不过他也不忍心让一个八岁的孩子天天吃素,所以对二少君自己出去打猎找肉吃睁只眼闭只眼,横竖不是他们给的就好了。
“哪有一压就是三年的。”老妪嘟哝,“真是同人不同命,都是一个娘生的,大少君听说上个月立了功,还得了皇帝的夸奖。我还听人说,将军在大少君五岁时就给他请先生教他读书认字习武了,可二少君这都八岁了,大字还不认识几个。难得来看二少君一次,还把二少君丢河里去了,大冬天的将军怎么狠得下这个心!”一样都是嫡子,将军的心真是偏得没边了,就算是夫人为了生二少君难产死了,也不能这么对自己的孩子啊,要是夫人在天有灵,还不知道有多伤心。
“阿娘,你少说几句,将军的决定我们不可以讨论的,”大汉劝着自己阿娘,“我们做下人的只要照顾好二少君就够了。”大汉不好说她照顾的这个孩子五岁就把自己继母的兄弟给杀了,这件事是高家的秘密,知道的人不多。
这家农庄的主人是当今中护军高威,高威有嫡出子女三人,长女高丽华为当今太子妃,长子高囧、次子高严,这两个孩子待遇可谓天差地别,高囧是备受高威喜爱的嫡长子,而高严因其出生导致母亲难产而亡备受高威冷落。
老妪叹气:“我不也就跟你说几句嘛,说起来也多亏了二少君,不然我们家日子就难过了,我也没儿媳孙子了。”
“可不是。”大汉咧嘴一笑,他不是军户但在大宋跟魏国开战之时他应召入伍,打了五年仗,好歹保住了一条命下来,但是腿瘸了,还是将军心善收留了他,后来又把二少君交给他照顾,家里托着二少君的福才渐渐宽裕了起来。
“呼——”紧闭的大门再次被推开,西北风呼啸而入,好不容易才暖和起来的两人不由都打了一个寒噤:“二少君你回来了。”老妪起身絮絮叨叨地说,“这几天天冷,你别天天往外跑了。”
进来的男孩子看起来不过七八岁,一张脸仿佛美玉琢成,若不是他一身劲皮装,神色冷漠地一手握着一张弓,一手提着一只血淋淋的剥皮兔子,真会让人觉得是个小女娃。对于老妪的唠叨,男孩恍若未闻。
“笃、笃、笃……”细细的敲门声响起。
老妪和大汉困惑地对视,这时辰怎么还有人来?
冷——陆希现在只有这么一个感觉,她的四肢已经僵硬了,意识也开始迷糊了,她举起手送到嘴里狠狠地一咬,刺痛让她清醒了下,她再次奋力在雪地里爬走着,不能停下,停下就死了……她不停地告诉自己,她上辈子死得迷迷糊糊的,连自己为什么会穿越都不知道,这辈子她不能再这样了……
她不认为自己再有一次好运。但是三岁幼儿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尤其是她已经连续在雪地里走了小半天了,陆希感觉自己身体已经接近极限了,“啊!”她低低地叫了一声,脚一软,整个人就跌坐在雪地上,冻得坚硬的泥土没有划伤她,但是把她摔得半天都爬不起来。
寒风一下下地刮在她身上,陆希缓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一步步地继续往前走,她不能死!她不要冻死!她脑海里只有这么一个念头,陆希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突然她看到了一户人家,她精神一振,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居然快步冲到了那户人家家门口,抬起手拍着,但是那声音连她自己几乎都听不见。陆希四处望了望,捡起了一块小石头,举着石头一下下地敲着那扇大门。
高严听到敲门声,心中微动,难道是阿姊来了?他转身去开门,但大门口空无一人,高严垂目,也是,阿姊都成太子妃了,怎么能随便出宫。咦?这是什么东西?高严低头看到一团黑黑白白的东西,他再定睛一看,居然是个小娃娃,白的是衣服、黑的是头发,手里还拿着一块石头。
“救我——”陆希丢开了砖头,吃力地伸手搭在了高严的脚上,人再也撑不住地失去了意识。
高严黑黝黝的凤眸盯着小娃娃冻得已经发白的小脸一会,弯腰抱起了她。
“二少君,是谁?”老妪在里面等了半天没听见什么动静,不放心地跟儿子一起出来看二少君。
大汉错愕地看着高严手中的一团:“这是什么?”
“哎呀,是个孩子呢!”老妪倒是一眼就认出高严手里抱了一个孩子,看着这孩子穿得单薄,不由心疼地说:“谁家这么狠心,居然让孩子穿这么少。”说着她连忙将孩子抱了过来,捞起一旁的棉被紧紧地裹住,连忙喊媳妇烧水。
“二少君,这孩子你从哪里弄来的?”大汉困惑地问。
“门口捡来的。”高严道,阴沉沉的样子一点都不像是个孩子。
大汉无语地望着高严,他还挺能体谅将军的,二少君这脾气一般大人都不会太喜欢,阴沉得实在不像孩子。
老妪忙喊来了媳妇给孩子泡了热水,洗干净了孩子后,两人惊呼道:“好漂亮的孩子啊!”两人还是**次见比高严更漂亮的孩子呢。
老妪注意到怀里的小女娃浑身雪白粉嫩,除了脚上、胳膊上有几处瘀青外身上连个小红疙瘩都没有,不由奇怪道:“这孩子瞧着也不像是附近农户的孩子,难道是哪家富户走失的小娘子?”
“富户会走失小娘子?”媳妇问,“莫不是被拐子拐出来的吧?”
“那些该死的杀千刀的!”老妪恨恨道,“这么漂亮的小娘子,家里也不知道有多喜欢呢,要是走丢了人家该有多伤心?”
媳妇暗忖,孩子漂亮就能受宠?那二少君怎么说?莫说大少君了,就是大娘子都没二少君漂亮,也不见将军有多喜欢二少君。
高严自把孩子交给老妪后,也没多上心,他平时基本一年到头都泡在山上,老鲁一家只负责他每天三顿吃喝,他既没有功课也没有人陪他,救那个小孩子只不过是他一时兴起,他压根没有想过这个孩子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少惊天动地的变化……
“走开!”高严警戒地瞪着又朝自己靠过来的小玉娃娃。
小玉娃娃果然听话地停住脚步,但是乌黑的大眼立刻浮起一层水光,嫩嫩的小嘴瘪着,要哭不哭地望着他。
一瞬间高严几乎以为自己做了何等十恶不赦之事,他脚步顿了顿,懊恼地看着这丫头,“过来我就杀了你!”说着晃了晃手中的木匕首,恶狠狠地瞪着小娃娃。
陆希眨了眨眼睛,伸出小手字正腔圆地吐出了一个字,“抱——”
“……”高严瞪着小娃娃抬起的两条手臂。
陆希仰着小脑袋,小手坚持不懈地张着:“抱——”
高严不动。
陆希吸了吸鼻子,语气里带上了哭音:“阿兄,抱——”
高严下意识地伸手,等他回过神的时候,小丫头已经被他抱在怀里了,高严脸黑了。
“阿兄吃肉肉——”陆希从怀里掏出一个包得严密的油纸包,她打开油纸包,里面是一只鸡腿,她把鸡腿送到了高严的嘴边。
高严看着这只鸡腿,再看小玉娃娃,小娃娃大眼一眨不眨地看着他:“我克死我阿娘。”高严说。
“我还杀过人。”高严继续说,双目专注地看着怀里的小娃娃。小丫头对他笑得一脸灿烂,露出了一口整齐的小米牙。
“你不怕我?”高严问。
陆希握着鸡腿的手坚定不移地放在高严嘴边:“阿兄吃!”
高严看着那鸡腿,张嘴咬了一口,鸡腿已经凉了,味道并不好,但却是高严三年来吃过的**吃的肉了,平时他抓了猎物后不过只是放在火上烤得半生不熟罢了,高严咬了一口后,要再喂给小丫头。
陆希脸埋在了他怀里:“阿兄,皎皎困困。”
“好。”高严抱起小丫头往房里走去,很慷慨地奉献了自己的床。高严是主,鲁家人是仆,高威再不喜欢次子,高严能享受的待遇也比下人好多了,陆希满足地蹭了蹭温软的被褥合眼就睡了,这些天她睡眠严重不足。
高严梳洗后,将小丫头往里移了移躺下,他轻轻地摸了摸她嫩嫩的双颊,低声道:“要是你真回不去了,就留下陪我吧。”长这么大除了老鲁一家子外,**次有人能陪自己这么久。
原本高严还以为这小丫头是附近的某户农家生的女儿,养不起丢在雪地里,可阿巩说这丫头外面是穿着粗布衣物,但身上尽是被这些粗衣磨出来的新伤痕,皮肤嫩得就跟豆腐似的,贴身穿的小衣,阿巩琢磨了半天,也分辨不出是什么料子,这样的娇娃娃别说是附近的农家了,就是寻常的富户都养不出。也正是如此,高严不敢让人大张旗鼓去打听,这样的孩子只身出现在荒郊野外,绝非家人粗心地走失。他让老鲁出去打听了好几天都没收获,或许她的父母不要她了?那她就留下陪自己吧。
“高—严—”高严坐在床上,一字一顿地说道。
陆希坐在高严对面,身上穿着高严改小的衣服,整个人窝在被子里,只露出一个小脑袋,“高—严—”一字一顿地重复,这个游戏她常陪耶耶、祖母玩,不过耶耶、祖母经常教着教着就对着她发呆,让陆希很无奈,想学说话都没人教。
高严凤眸漾出了浅浅的笑纹:“皎—皎—”
“皎—皎—”陆希指了指自己。
高严满意地端起一碗奶粥:“粥—”高严**次发现,他居然还能为人师表。
小丫头舒服地靠在高严腿上,嘴张着理所当然地享受着高严的伺候,等喂完饭她晃着脚要下床。
“怎么了?”高严问。
“散步消食。”陆希说。
高严见粉嘟嘟的小娃娃一脸正经地告诉自己饭后散步消食,嘴角忍不住往上扬,弯腰给她穿上厚厚的小皮袄后,牵着她的手在农庄里走:“皎皎,想不想抓雀儿玩?”
“雀儿?”陆希重复一遍发音。
“雀儿。”高严用树枝在雪地上画了一个简洁的小鸟图案:“雀儿。”
陆希恍然,再次重复了一遍。
高严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皎皎不是不会说话而是没人教,有人教她就学得很快,高严纳闷,皎皎看起来就是富户家养出来的小孩子,怎么没人教说话呢?“等天气暖和些,我们就能上山了,山上有很多好玩的小动物,你喜欢我们都可以抓。”高严一边拿出一把米撒在地上,一面给陆希说着怎么抓雀儿。
陆希兴致勃勃地看着高严设置各种机关,还不时地发出几个单音节字附和着,她从小就听人说过冬天抓鸟,但从来没见识过怎样抓鸟。
老鲁一家子不可置信地看着高严牵着陆希的手在农庄里遛弯,无论遇到什么东西,高严都会指着那东西说出它的名字,再让陆希重复。
“真是见鬼了。”大鲁喃喃道,照顾了二少君三年**次见他居然连续五天都待在家里,还有耐心陪一个小娃娃玩,他长这么大说过的话都没有今天一天多吧?大鲁的儿子跟高严差不多年纪,鲁家也比较同情二少君,但还是从小教导孩子离高严远一点,二少君脾气真不好。
“那小丫头的家人你找到没有?”老鲁吸着旱烟问儿子。
“二少君就让我出去打听了一次就不让我再打听了。”大鲁说。
老鲁敲了敲烟头,若有所思地看着那小小的身影,他总觉得那丫头来历太古怪了些,收留下这孩子的当天,他就跟儿子一起出门查看了一番,顺着那孩子留下的痕迹两人走了快大半个时辰,才看到一行车印,因天色已经晚了,两人也不便再追过去,但是他们两个成人要走大半个时辰的路,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要走多久?而且还是在这大雪天,难道是有人特地把孩子放在他们门前,但是路上只有孩子移动的痕迹,真让人想不通。
“笃笃——”敲门声再次响起,大鲁起身去开门,一开门就见大队人马站在农庄门口,他忙上前行礼:“太子妃。”
“阿严呢?”高严的长姐太子妃高丽华从马车里探出身体问,“又去山上了?”
“回太子妃,二少君在院子里。”大鲁说。
“这些天天气冷了,阿严还是不要天天往山上跑了。”高丽华浅浅地一笑。
大鲁让自己媳妇陪在高丽华身边,自己则进去通报高严,与此同时随从的宫侍们也在这陋室里铺上华贵的地毯,有人去整理高严的卧室,以便太子妃入内稍稍歇息,高严房间是这个农庄**的地方。
“阿弟在做什么?”高丽华问。
“回太子妃,二少君跟小娘子在抓小雀。”大鲁的媳妇说。
“小娘子?什么小娘子?”高丽华问。
“是二少君*近救的一位小娘子。”
这时高严听了通报,抱着陆希去见高丽华:“阿姊。”
“这是你救下的孩子?”高丽华看着站在高严身边的小女娃惊讶地问。
“是的,她叫皎皎。”高严说,“皎皎,这是阿姊。”
皎皎?这名字怎么好像在哪里听过?高丽华的念头一闪而过,就被眼前这个漂亮的小女孩子给迷住了,“真是漂亮的孩子,阿严她长得比你还漂亮。”高丽华刚成亲,少女心性未脱,见这小丫头生得漂亮,不由爱怜地伸手摸了摸她的小胖手、小胖脚丫,果然软软嫩嫩的,高丽华一脸满足,她有两个弟弟,可她已经记不起两个弟弟有过这么可爱的时候。
高严没说话,也懒得辩驳他是男人,男人是不能说漂亮的。
“太子妃,房里已经收拾好了,您跟二少君先进屋吧,外头太凉。”一名宫侍恭敬地说。
“太子妃?”陆希困惑地仰头看着高丽华,再看看高严,阿兄是太子妃的弟弟?怎么可能!她一直以为高严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个稍稍有点小钱的人而已。不然怎么会把儿子关在这么贫瘠的农庄?
太子原配早逝,今年五月的时候续娶太子妃,陆希不知道新任太子妃的家世,想也不是普通人家,那么阿兄作为太子妃的弟弟怎么可能会住在这么破烂的屋子里?
小丫头一脸困惑的小模样,惹笑了高丽华,等到了内房,高丽华先让内侍将自己带来的东西都放下,又关切地问了弟弟几句近况后,接过内侍带来的精致的拨浪鼓,晃动着逗着这个玉琢似的胖娃娃,这是高丽华原本给大鲁的女儿准备的,现在看着这粉嘟嘟的小胖丫头,高丽华让人先拿出来了,反正给大鲁女儿的礼物还有很多。
陆希见她笑得一脸灿烂,伸出粉嘟嘟的小手,要抓她手中的拨浪鼓,陪她玩好了,陆希无奈,反正耶耶也常对自己做这种事。
“皎皎乖,叫阿姊——”高丽华趁着娃娃抓住拨浪鼓的瞬间,樱唇微嘟,要亲那看起来非常可爱的小嘴。
“她不喜欢这种东西。”一双手伸来,高丽华快入口的嫩豆腐一下子被抱走了。
高丽华瞪大了凤眸:“你怎么知道她不喜欢?”
“皎皎,要吃吗?”高严没回答高丽华的话,反而拈起一根樱珠梗,将一颗紫红晶莹的樱珠凑到娃娃的嘴边,娃娃嘴一张,就将樱珠咬住,小脑袋往后一仰,高严手中就只剩一根樱珠梗了。这是高丽华给阿弟带来的,高威只是不许儿子吃肉,对旁人送蔬果倒是不反对,可惜高严*讨厌的就是吃蔬果。
高丽华呆呆地望着这一幕,半晌惊道:“你怎么连核都不去掉就给她吃了?万一她咽下去怎么——”高丽华的话还没说话,就见高严拿着一只小碟子放到娃娃面前,娃娃嘴一张,一颗樱珠核就吐了出来。
高严嘴角微挑:“她只是不怎么说话,又不是笨蛋,怎么不知道吐核呢?”说着他又喂了娃娃两颗樱珠,等喂到第四颗的时候,陆希小脸一撇,表示不要吃了,又扯了扯高严的衣角。
“她要什么?”高丽华困惑地问。
“漱口。”高严让内侍端来一盏温陈茶来给她漱口,一系列的动作如行云流水。胖娃娃扭过身体拉着厚被子,显然是准备睡觉了。高严拿出一个铜香炉:“阿巩,给皎皎换块新炭来,她要睡了。”
“二郎,被褥里还暖和呢!房里还烧了三个炭盆,一会你也睡上去了,就更热了。孩子挨冻不好,太暖和了也不好,会上火的。”阿巩就是老妪,她先伸手摸了摸被褥,再摸摸娃娃的小脸、小手,确定她并没有着凉,就没让高严再添炭盆,太暖和对身体也不好。
“你和她一起睡?”高丽华见阿弟这么熟练地照顾这孩子有些发怔,现在一听他和仆妇的对话就更吃惊了。
“不然呢?”高严反问。这个偏院原本就只是他和老鲁一家子,平时大宅送来的分例不会克扣,也不会多上一厘,炭火也恰好够他们用,能住人的房间也就这么几间,皎皎不睡在下人房,当然只能和他睡了。
高丽华讪讪一笑:“也是,反正你们都还小。”她想自己每次过来找弟弟,都是前呼后拥地带上一堆仆役,连睡觉的被褥都带来了。只是阿父又不许任何人提及阿弟,她劝过父亲很多次,但是父亲始终不肯松口,高丽华也曾偷偷给阿弟送过肉食,但是被父亲发现后,他不仅把那些肉食没收,还狠狠打了阿弟一顿,高丽华再也不敢给阿弟偷偷送东西了,更别说她现在已经嫁入皇家身不由己。
“阿巩,你说皎皎三岁了,三岁的孩子不是说话都挺顺溜了吗?为什么皎皎会说的话不多?我看她挺聪明的。”高丽华转移了话题。
“太子妃,您看小娘子,一身皮儿多白多嫩,身上半个疙瘩都不见,还有这贴身的小衣服多软,老奴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柔嫩的料子呢!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养出来的,下人伺候得好,要什么不用她说,就送到手了,不怎么会说话也是常事。”阿巩见皎皎小手扯着自己的衣服,笑着抱起了娃娃疼爱地说:“小娘子,阿巩给你脱衣服。”
“阿巩,吃。”娃娃仰头对阿巩甜甜地笑,小手里握着一颗大大的樱珠,往阿巩嘴里塞。
“哎哎!皎皎小娘子真好!”阿巩受宠若惊地收下娃娃手里的樱珠,樱珠便是在时季也是珍贵稀罕的果子,更别说在这种数九寒冬了,要不是大娘来看二郎,二郎也不可能吃到这种果子,阿巩哪里敢吃。
“皎皎给你的,你就吃吧。”高严说,除了肉他对任何蔬果都不感兴趣。
“老奴谢二少君赏。”阿巩连声谢赏。
“这料子——”高丽华若有所思地摸了摸。
“怎么了?”高严问。
“这不是从崖州进贡的吉贝布吗?太后前段时间赏了我一匹,说这料子轻软,又比软绸还透气,***冬天做寝衣。”高丽华正色问:“阿严你老实告诉我,这孩子你从哪儿找来的?”
这孩子身上穿的料子分明和太后赏她的那匹吉贝布一模一样,吉贝布在上贡之物中也属于罕见,这种**的布匹一年也就进贡那么二十来匹,宫里的贵人都不够分,高家也算是生活豪奢的豪门显贵了,也不会拿这种布给小娃娃做小衣,小娃娃一天一个样,新做好的衣服别说来年了,就是几个月后就不能穿了。这个孩子的身世绝不简单,可高丽华又不曾听说这几日有哪家丢了孩子。
“门口捡来的。”高严说。
“你当我傻子吗?”高丽华没好气道,要是在门口都能随便捡个奶娃娃,他这里早人满为患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她真是我在门口捡到的,她就趴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块小石头,在不停地敲门。”
“打听到是哪家的孩子了吗?”高丽华问。
“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叫皎皎,家里有父亲、姑姑还有祖母。”高严说,“我这几天让老鲁去外面暗地里打听了,问问有没有大户人家走失了孩子。”高严没说这个举动他只让人做了一次就没再做了,他打定主意了要养皎皎一辈子。
高严让娃娃躺平睡好后,唤阿巩给自己打水:“时辰不早了,阿姊你不回宫吗?”
“我今天回行宫。太后老寒腿又犯病了,半个月前就去汤泉行宫养病了,今天是她让我先来看你的,我马上要走了。”高丽华也在行宫陪了太后半个月,太后不知道接到了什么消息急着回去,高丽华作为新妇也不敢随意打探宫廷消息,只隐约知道此事跟她小姑子有关,据说连皇帝和太子都惊动了。
“嗯。”高严应了一声。
“你这里不方便,让我把皎皎带走吧。”高丽华说,“你一个男孩子,怎么会照顾人呢?”她是私心想玩玩这娃娃,她长这么大**次看到这么漂亮乖巧的小娃娃。
“她这几天都是我照顾的,怎么不能照顾她呢?她晚上还要起来喝水,你会喂她吗?天这么冷,还要小心不能让她着凉,你要是说交给下人照顾就算了,皎皎晚上看到陌生人会哭的。”皎皎晚上睡着后都是一觉睡到天亮的,根本没有那么多事,高严为了让姐姐打消主意,故意说得麻烦。
“好吧。”高丽华看出了弟弟压根不想让自己带走娃娃,“她要是找不到亲人,你想领养她的话,等过了元旦带她回建康,我让人给她办户籍。”高丽华也心疼弟弟一个人在农庄没人陪,要是这孩子真找不到亲人让她陪阿严也好。
“好。”
“等过段时间,我和耶耶说说,让他把你接回家里去,你也八岁了,该进学堂了。”高丽华低声对阿弟道,一面是自己亲爹,一面是自己弟弟,她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尽量让两人矛盾缓和。宫侍们又催促着自己要出发了,她安慰了弟弟几句后,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她入宫后要不是还有太后照顾,根本不可能出宫看阿弟。
高严沉默地看着阿姊离开,目光落在已经睡着的陆希身上,没关系他也有皎皎陪了,但是此时的高严没有想到,在阿姊走后不久,皎皎的家人就找来了。
当晚一更刚过四点,建康城宵禁的暮鼓已敲响,各坊市的大门紧闭,街上空荡荡的,间或有更夫瑟缩着提着灯笼、敲着梆子报更的身影,更夫有气无力的报更声,显得建康城越发的寂静。巡街的兵丁们顶着寒风在建康城巡逻。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众人大惊,连忙侧身回避。
“这么晚还能出门,他们是哪家的?连着好几天了,怎么都没人管?”一名巡街的兵丁惊讶地问。
“谁敢管?”小头目斜了下属们一眼,“这么晚还能得了圣上的手谕骑马出城,我们大宋朝能有几家?”他下巴微微一抬,指着不远处一户大门正对大街,其偏门、侧门已经打开,不断有人进出的豪宅道:“看到门口的双戟没?”
“难怪!原来是陆家!”众人看到门口插着双戟顿时恍然,原来是陆家弄出来的动静,那就不奇怪了。吴郡陆氏是本朝的**世家,自先汉起就是累世官宦的江南大族,承传千年、历经数朝不倒,历代高官名士辈出,素以“经史之学与诗文风流兼美”著称,陆家历任当家人无一例外地都是文坛领袖。如今的陆氏家主陆琉为高邑公主的驸马,高邑公主是太子郑启同母的胞妹,下降陆家时皇帝要求女儿“妇事舅姑如父母”,有了公主府就不能天天晨昏定省了,故只在陆府门前列了双戟,也示陆家尚主。
“这陆家是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么晚还出动这么多人?”另一名兵丁问,“这几天白天也是,整天有人在各坊间找人,连禁军都出动了。”在建康城里找人哪有这么容易,禁卫军都出动了两万了,还是一无所获,若不是这些天陛下跟太子好好的,大家都要怀疑宫里出了什么大事。
“管这么多干什么?这大户人家的事多着呢!”小头目打了一个喷嚏,还是早点巡视完,回去喝壶热酒。
“也是。”这些兵丁几乎都是目不识丁之人,可在京城巡街的,哪个不是人精。看这架势也知道是出大事了。
而城门口守城的军士,一早接到了宫中急令,一骨碌地从城墙旁的小屋滚出来冒着寒风,将城门飞快地放下,重重的城门才落地,一队骑士就疾驰而过,军士等骑士离开后再次关上城门。
“你说闹了这么多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等回到生着火盆的小屋后,两个关城门的小兵一边热着酒,一边闲聊道。
“是陆家丢了孩子吧。”一人拣了几颗花生吃。
“哪个孩子?”另一人下意识地问。
“还能是哪个孩子?如果是小的那位,现在建康城早翻天了!”那人丢了一颗花生入嘴。
“是萧家那位生的?”另一个人轻声地问。
那人点头。
另一人叹气,“可怜那——”萧家的子孙去年都死绝了,今年轮到外孙女了。
这事说来还有一段公案,陆家的家主陆琉先后两位妻子,原配嫡妻为前梁汝南长公主萧令仪,后娶的继妻为本朝高邑公主郑宝明,两位妻子各给他生了一女,长女陆希为前朝皇室后裔,次女陆言则是当今皇帝的亲外孙女。萧家的皇位是灭在郑家手里的,萧家的子孙基本都被当今圣上杀光了,现在轮到这个外孙女出事也不稀奇。
“算了吧。”那人嗤笑一声,“这种世家小娘子一出生就是金尊玉贵,人家身上一件衣服说不定就抵得上我们几年的用度了,可怜?人家哪里需要我们来可怜?外面那些被饿死的孩子都可怜不过来。”
另一人点头:“这倒是,我们算什么?那些金枝玉叶哪里需要我们来可怜。”人家生下来就享他们一辈子都享不到的福气,他打了一个哈欠,“还有半个时辰就该换班了,回去好好睡一觉。”
“是啊。”
冬季的夜里格外的寒冷,也格外容易让人熟睡,尤其是在偏僻的院乡下。高严送走了阿姐又打了一套拳法,用冷水冲洗了下身体后就休息了。这套拳法还是他没被高威赶来农庄前跟着高威的侍卫学的,要不是他天天练习,他也不能上山打猎。高严回到了自己房里,陆希已经睡着了,高严也没吵醒她,轻手轻脚地掀开自己的被子躺下,刚合上眼睛。
“咚咚——咚咚——”敲门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的响亮。
“谁啊?”老鲁不情愿地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裹着厚衣去开门,一开门他原本已经有些浑浊的眼神一下子亮了:“你们是谁?”门口站满了骑着骏马的武士,武士手中握着的火把将漆黑的夜空都映亮了。老鲁眼睛眯了眯,大宋马匹属于官家财产,可不是光有钱就能买到的,更别说这些骑士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强兵悍将,放眼整个大宋,家里能拉出这么一队骑士的寥寥无几。
骑士策马移动了下,一名穿着貂裘斗篷的男子从马上翻身而下朝他走来:“敢问这位老翁,贵府五日之前是否收留了一名三岁的女童?”男子的斗篷还连着帽子,过分宽大的帽子将男子的脸遮住了大半,仅露出半个形状完美的下颌,声音清雅中带着焦急,看起来同那些骑士格格不入。
“你们——”老鲁有些惊疑不定地打量着那名男子。
那男子将斗篷帽子拨下,露出了让老鲁感觉有些眼熟的俊美容貌,他对着老鲁温和地问道:“老翁,你们收留的孩子有可能是某的女儿。”说话间陆琉脸上焦急的神色已经止不住了,这些天城里城外他已经找了无数家了,但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五天了……已经五天了,陆琉眼底忍不住露出了绝望,皎皎你到底在哪里?
老鲁这才恍然,难怪他觉得这位郎君容貌有些眼熟,皎皎小娘子长得不是有点像他吗?“你是皎皎小娘子的父亲?”这郎君长得可真出色,就是看起来似乎脸色不太好,眼底发青、嘴唇都爆皮了。
“皎皎?”陆琉浑身一震,上前抓住了老鲁,“皎皎?你们真的收留皎皎了?”陆琉激动得眼睛都红了,找了五天,几乎所有人都劝自己放弃,说皎皎找不到了,可陆琉还是提着一口气坚持着,他一定要找到皎皎,不然他怎么对得起阿仪?怎么对得起姑姑、姑父?
“敢问这位郎君贵姓?”老鲁问着陆琉,“我家少主人是中护军高大人之子。”
“高威的孩子?”陆琉一怔,他听说了城外有人来打听女孩子走失的事,就入宫请了圣旨急急赶来了,却没想是高威的儿子救了皎皎。
老鲁见来人居然若无其事地直呼自家郎君之名,大吃一惊,这位郎君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比起自家郎君小太多了,可他还能直呼其名,显然身份在郎君之上,他猜到皎皎小娘子身世不凡,却不想她的家世居然如此显赫。
陆琉正想入内找女儿,又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陆琉和老鲁循声望去,又见一队骑兵出现,为首一玄衣人马尚未完全停下就翻身下马:“乞奴。”
老鲁看到那玄衣人腿一软,就跪在了地上:“太子殿下。”郑启是高家的女婿,老鲁借着高严的光见过郑启一次,郑启本身又是出众之人,让人一眼就记住了。
郑启是接到下人回报后赶来的,乞奴已经五天没有好好休息了,一直在外面奔波,郑启知道他现在根本不想见自己,可还是放心不下他。郑启想到自己妹妹做出的蠢事,就忍不住想把她关在屋里一辈子别出门。看到老鲁,郑启眉头一皱,“多奴呢?”多奴是高严的小名,这个小名很明确表示了高威对儿子的看法,所以高丽华很少叫高严小名。
陆琉直接大步往农庄内走去:“皎皎?皎皎你在哪里?耶耶来了!”
陆希睡眠一向很好,睡着后很少能被惊醒,而高严在陆琉敲门的那一刻就惊醒了,再听到陆琉叫女儿的时候,他警醒地翻身**反应是要把皎皎藏起来,但是还没有等他有什么动作,睡得很香的陆希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醒来,含糊地叫道:“耶耶?”她好像听到耶耶的声音了,是做梦吗?
高严听着陆希嘴里叫父亲,身体一下子僵直了,想要抱陆希的手也停顿在了半空中,果然她也是不得已才陪着他的吗?
农庄里根本没有几间房屋,陆琉很快就锁定了高严的房屋,他也顾不上礼貌推门而入,陆家的家丁急急地跟在陆琉身后。高严的房里黑漆漆一片,但是借着家丁手中的火把,陆琉**眼就见到了那个慢吞吞地从床上竖起来、揉着眼睛的小身影,“皎皎——”陆琉跌跌撞撞地上前,将失而复得的珍宝紧紧地搂在怀里,头埋在女儿的发间,泪水不自觉地流出,“皎皎——”
“耶耶?”陆希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耶耶!”她小手把住了陆琉的腰:“皎皎好想你!”
“皎皎——对不起!都是耶耶不好!”陆琉手颤抖地抚摸着女儿暖乎乎的小脸,“好囡囡,耶耶的皎皎——”
郑启看到找到了小丫头,心里彻底松了一口气,幸好没事,不然乞奴也不知道会怎么伤心。见这对父女抱着一起哭,他上前道:“乞奴,先带皎皎回去吧,袁夫人还在府里等着。”
陆琉这才发现女儿还穿着单衣,而卧房的大门敞开,他慌忙脱下斗篷把宝贝裹住:“皎皎,我们回家看大母。”说着就要抱女儿。
但是陆希小身子一扭,一把抓住了一直沉默不语的高严:“阿兄,皎皎要阿兄!”
“阿兄?”陆琉这才注意到女儿身边有个漂亮的小男娃。“皎皎这是谁?”他错愕地问。
“阿兄!”陆希坚定地揪着高严的衣服寸步不离,这些天她算是看清了高严在高家的地位,太子妃的嫡亲弟弟就住这个鬼地方?别说高严这些天对自己这么好,就光是凭借他救了自己,她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这么虐待!
高严原本僵直的身体渐渐地放松了下来,他不由紧紧地搂住了怀里的小娃娃,皎皎没有不要他,他不会跟皎皎分开的,除了皎皎他谁都不要!高严心里想到。
**章
永初三年年末,建康城一连下了好几天大雪,到了二十日白天,雪虽然停了,可天气依然阴霾霾的,不见一丝阳光。
城头除了少数几名在角楼上巡逻的士兵外,大部分守门的兵丁都躲在了城墙下的休息间里烤火取暖,城门口排了长长的等候进城的队伍,厚重的城门已经半关。在离城墙几里地外,无数从各地逃来的流民、还有建康城的乞丐,聚成一团,靠仅有的几个火堆取暖。建康城里的灾民和乞丐本来就多,前段时间北方接连不断的水灾、旱灾,使江南一带又多了不少饥民。
因临近元旦,又恰逢二十八日是崔太后五十寿诞,建康的官员们为了讨太后、陛下欢心,将流民和乞丐都赶出了建康城,灾民们无处可去,只能待在没有任何遮掩物的城外,为了避免冻死,一个个哆嗦着依偎着在一起。建康城各处虽都建了粥棚,但对越来越多的饥民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突地,一阵寒风夹杂着雪片吹来,原本就不是很旺的火势,一下子又弱了许多,火光若隐若现,似欲熄灭,雪片更如刀子般割在身上,灾民中隐隐传出了孩子的哭闹声和妇人的安抚声。当卫府派出甲士走入营地的时候,母亲们都紧紧捂住了哭泣孩子的嘴,灾民连呼吸声都压低了,不敢发出丝毫声响。不少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或许明天早上从这里拉出去的尸体中就有他们了。
“咦?”浓浓的粥香味弥漫在空气中,饥民原本无神麻木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不少人兴奋地跳了起来。
“唰!”整齐的拔刀声,一柄柄尖刀在夜色中寒光凛冽,一名全副盔甲看起来是小首领的甲士大声喝道,“一个个地来领粥,不会少你们一份!但谁敢趁机作乱杀无赦!”杀无赦三个字,被那甲士说得杀气腾腾,饥民一个个畏缩着跪在地上。很多人听到了晚上还能喝到热粥,眼泪一下子滑过已冻僵的脸,今晚好歹能保住命了。
“嗒!嗒!嗒!”一阵阵闷雷般的响声传来,地上隐隐震动起来,众人茫茫然地抬头,只见远处烟尘滚滚、惊雪四溅,众人面露惊容,几名反应快的人赶紧拉着自己的行李,远远地离开城门口。
马蹄声渐近,一长队昂然跨坐于骏马之上的骑士出现在众人面前,有眼尖的已经看到为首一人斗篷下那若隐若现的绯袍,“是大官人啊——”低低的惊呼声此起彼伏,不少人已经畏缩地跪地。寻常百姓一辈子连**的绿衣小官都不一定能见到,何曾见过这么大的官。
“咴——”怒马长嘶,蹴踏之声入耳,一名黑衣骑士跳下马后,将一卷公文展现给守城的军士看,军士看了公文的内容以及黑衣骑士取来的印信后,忙朝那绯袍行礼:“大人,请!”
“吱嘎噶——”厚重的城门缓缓地打开,待城门完全打开,那些骑士再次绝尘而去,城外的雪道上仅留下一串长长杂乱的马蹄印。
“此时骑马入城,莫非又发生了什么大事?”在离城门口不远处,停了一辆犊车,车内两人透过挽起车帘的车窗望着这一幕,车中一名头戴二梁冠、身披鹤氅裘的俊美男子说道,说完后又见天上大雪飘飘扬扬,他长叹一声,“雪越下越大了。”
“等回去后,我就派人去打听。”男子身边的青衫文士说,劝男子道:“郎君,天色已经晚了,雪又这么大,我们还是先回去吧。你身子刚好,莫再着凉了。”
“哪这么娇贵。”男子嘴上说着,可还是放下车帘。
文士吩咐车夫驾车离去,车帘落下前,映入两人眼中的是饥民们几乎虔诚地捧着粗瓦碗一点点地舔着稀粥的样子,刚刚马队入城那么大的动静,他们似乎丝毫未觉。两人心里百味杂陈,沉默一会男子道:“季慎,以后每天粥棚都施粥两次吧。”
“已吩咐下去了,从前天开始就一天两次了。”施温道,他迟疑了下又道,“郎君,只是长此下去,以我们一家之力,怕是撑不了多久。”即使建康官办的粥棚,一天也就施一次粥而已,数万名灾民,陆家再豪富,也无法长久地供应。
“能供多久就多久吧,天又这么冷,晚上不施粥,死的人更多。”他如何不知这并非长久之计,可如果他现在不这么做,别说以后了,就是今天也肯定会死不少人,有能力就继续帮下去,没有能力就停下,自己所求不过是“问心无愧”四字罢了。
“郎君是一心为公,就怕——”施温暗叹一声,郎君这番举动怕是会碍了不少人的眼吧?这么多灾民,撇开那些老弱病残的不提,剩下那些身强力壮的流民,哪家不眼馋?
“旁人之议,与我何干?”陆琉淡声反驳。
犊车缓缓驶入城内,相比城外饥民的惨状,建康城内却是一派花团锦簇,街道两旁的树上、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挂上了彩灯,灯光从各色灯纱中散射而出,晕出一片朦胧多彩的烟霭。雪越下越急,不一会屋宇、地上就覆上了一片白色,朦胧多彩的灯光映着这整整的一片白色,煞是好看。
陆琉望着这片雪景不作声。施温知道陆琉今早刚为崔陵赶流民出城的事,同崔陵大吵了一顿,现在心情正不好,也不去触他霉头。
“郎君,到了。”犊车轻微地震动了下,便停下了,施温掀起车帘,仆佣们提灯而上,伺候陆琉下车。
“这是什么?”陆琉刚下车,目光随意地扫过园里的时候,眉头一皱问。
陆琉突如其来的问话,让下人们怔了怔,顺着陆琉的目光望去,只见原本冷冷清清,只有松柏、冬青这些四季常青作物点缀的花园里,居然一派花团锦簇,各色牡丹、海棠、芍药等鲜花一应俱全,浓香扑鼻,可细细一闻,这香味又不是花香,再定睛一看,这些鲜花居然是各色绫罗绸缎扎成,若不细看,几可乱真,那香气自然也不可能是天然的花香,而是后熏上的。
众人面面相觑,管家上前回道:“回郎君,这些缎花是中午公主派人来挂上的,说冬天花园里太冷清,放些缎花也能热闹些。”
陆琉听罢,嘴角一哂,也不说什么,疾步往书房走去。
施温也不急着跟随,而是招过几名小厮,吩咐了好些话后,才不紧不慢地往陆琉的书房踱去。
书房四角摆放了炭盆,屋内温暖如春,儿臂粗的蜜烛将书房照得亮如白昼,烛影摇动中淡淡的暖香在书房中弥漫,灯光透过窗纱,将屋外台阶上玉堂富贵的石雕都照得清清楚楚。
陆琉除了鹤氅,头上梁冠也取下了,手中拿了一卷画册翻看着,甚是怡然,见施温进来,示意他坐下。
施温坐于陆琉下方,见陆琉手中的画册,是一册十二幅花卉虫草图,每幅画卷用的素绢皆用赭石、淡墨染成古色后方才在上作画。所画之花卉柔丽雅致,似芳香可闻,草虫须爪毕现,若振翅欲飞。连印章的印泥都舍了厚重沉稳的朱砂色,改用清丽的朱缥色,使画作愈发古雅精丽。
“郎君,这是大娘的画作?”施温略为惊异地问,他知道大娘从小就在观主、郎君的教导下习字作画,却不知大娘书画已如此之好。施温口中的大娘,是陆琉的长女陆希,而观主则是陆琉的嫡亲胞姐陆止,陆止一心向道,立誓终身不嫁,前梁景帝赐她道号“清微”,还给她盖了一个清微冠,陆止从此便让家人称其为清微,不再提俗世之名。
“是。”陆琉脸上带了淡淡的笑意,皎皎的画技越发精进了。他示意丫鬟给磨墨,他之前答应过女儿,待她这卷画册画完,便在上题词作诗。只是自己*近为了崔陵驱逐城中饥民之事,同崔陵争辩多次,一直静不下心来给女儿画册作诗,就先题几个字吧。
施温见陆琉心情好转,见机将一叠厚厚的功课奉上:“郎君,这是大郎*近的功课,公主刚让人送来。”
陆琉眉头都不抬下,继续翻着长女的画作:“放着吧。”
施温不解,大郎的功课,不是郎君特地吩咐送来的吗?怎么郎君不看呢?陆琉道:“我答应了皎皎,给她画作题字的,趁着现在心情还好,先题完再说,等看了那点功课就没心情了。”
施温啼笑皆非:“郎君说笑了。”
陆琉认真地给女儿题了字,亲自匀了印泥在女儿的画作上印上了自己的私章后,才让施温把儿子的功课奉上。只消一眼就见那练习纸上的每个字高矮胖瘦皆不同,他挑了挑眉头,随手抽了一张功课,丢到了书案前对施温冷笑道:“王右军当年挥毫一气呵成了《禊帖》,写了二十个不同的‘之’字,乃千古绝唱,我这儿子倒比王右军更出挑,每个字都是不同的。”
施温低着头一声不吭,陆琉继续看着儿子的作业,和看女儿画作那一幅幅细细品鉴不同,陆琉唰唰两下就把那叠厚厚的功课翻完了,翻完后随手往书案上一丢,接过丫鬟递来的茶盏一仰而尽:“把他给我叫来。”
施温见陆琉如此做派,就知他心中不爽,吩咐僮儿去叫大郎过来,施温又亲自给陆琉重上了一盏清茶:“郎君,我听说大娘前段时间还遣人去安邑,吩咐安邑县的长吏将赋税又降了三成。”
陆希出生之时便被先朝武帝册封为县主,封地安邑。陆希不能主管安邑政事,但收取赋税一事她是能做主的。今年一年大宋各地,水灾、旱灾不断,圣上下令降了三成的赋税,陆希又把属于自己的那块赋税降了三成,至少安邑那块不会出现流民了。
陆琉自坐垫上起身,离了书案,掀衣往软榻上一靠叠了腿,取过云展把玩,似笑非笑地斜睨着施温:“皎皎乖巧,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不用变着法子给他求情。”
施温被识破了心思,也不羞窘,只劝道:“郎君,大郎还小,慢慢教着便是。”
陆琉“哼哼”笑了几声,也不接施温的话。
陆琉有两女一子,长女陆希为原配前梁汝南长公主所生、次女陆言为继妻常山长公主所出,两女无论容貌还是品性才华皆无可挑剔,**的独子是府中姬妾所生,因陆琉尚未给他取名,家中人皆称大郎。
他也是陆琉目前**的儿子,今年才五岁,极得嫡母常山公主的喜爱,带在身边亲自抚养,饮食起居无一不妥帖周到。主母如此看重,家中下人自然也捧着他、宠着他。一般来说,只要父亲不查他功课,陆大郎小日子是非常滋润的。
这日天气寒冷,他刚在乳母的伺候下,钻进烘得暖暖的被窝,却被陆琉一声令下,惊得连滚带爬地从被窝中钻了出来,匆匆穿上衣服往书房赶去。因是去外院,陆大郎的乳母向氏也不好跟随,只吩咐了小厮们好好伺候着。当陆大郎赶至书房的时候,他的六个伴读也来了,七人战战兢兢地站在门口,等着下人通传。
“还不进来,还要我出去请你不成。”书房里传出了温和清越的话语声,陆大郎粉嫩的小脸一苦,两条小腿有点打颤了。他闭了闭眼睛、咬了咬牙,颤巍巍进了书房,就见父亲斜躺在软榻上,吓得脚一软,差点跪倒:“父亲——”他犹豫地望着书案旁的坐垫,要不要把那坐垫移过来给父亲磕头?
“我还没死呢,不用你给我整天磕头。”陆琉一见儿子畏缩的样子,就心火大盛,不耐烦地用云展敲着扶手:“过来点,我还能吃了你不成?”
书房里的丫鬟忙摆了一个坐垫在陆琉软榻下方,陆大郎想了想,还是恭敬地朝陆琉磕头请安后,才端正地跪坐于陆琉下方。
陆琉见他那副酸腐样,嘴角一哂,卷起云展,一下下地轻拍着自己的手心,问儿子道:“说说,这些天都学了什么?”
陆大郎眼珠子随着云展一上一下,听到陆琉的问话,不敢怠慢,朝父亲磕了头才道:“先生刚教了我《论语》,还让我描红。”
“既然已开始描红了,可会写字了?”陆琉问,神情喜怒难辨。
“会一些。”陆大郎犹豫地说。
“写几个字给我看看。”陆琉道,书房伺候的丫鬟忙将书案和笔墨奉上。
陆大郎握着笔:“父亲让我写何字?”
“一至十。”陆琉悠悠然道。
“嗄?”陆大郎困惑地眨了眨眼睛,心头莫名一颤。
“不会?”陆琉长眉一挑,单手撑于扶手上,似笑非笑地斜睨着儿子。
“会!”陆大郎连忙在纸上画了一横,太紧张了,连先生教过的笔法都忘了,就直直地画了一条横线。
陆琉讥道:“你是写字还是画木棍?”
陆大郎手一抖,照着先生教过的笔法,一丝不苟地重新画了一条,只可惜画得歪歪斜斜的。
陆琉嗤了一声:“这条蚯蚓画得倒是传神。”
陆大郎忙用毛笔舔墨,想要再写一笔,陆琉不耐道:“你准备写几个一?继续写下去。”
大郎唯唯诺诺地应下,屏息写了二字,这次两横稍微直了些,他自觉写得不错,心定了定,可耳边却听父亲轻轻的一声冷哼,他手一软,一笔又写歪了。
施温在一旁看着,心中暗暗叹息,平心而论,大郎的字虽然下笔无力,但字形隽秀,对一个五岁的孩子说,这手字已经很不错了,可惜还是不能和当年的大娘比,大娘五岁的时候,那手字已经颇有风韵了,甚至二娘五岁的时候,写的字也比他好上很多。更让施温叹惜的是大郎稍嫌怯懦的心性,他忍不住暗忖,若是大娘是郎君的长子而不是长女,该有多好,或者二娘是男孩也是极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