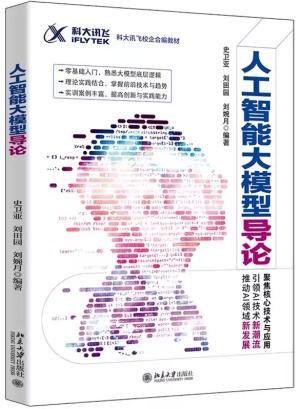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想通了:清醒的人先享受自由
》
售價:HK$
60.5

《
功能训练处方:肌骨损伤与疼痛的全周期管理
》
售價:HK$
140.8

《
软体机器人技术
》
售價:HK$
97.9

《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
售價:HK$
74.8

《
奴隶船:海上奴隶贸易400年
》
售價:HK$
75.9

《
纸上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破译古老文明的密码,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150+资料图片)
》
售價:HK$
85.8

《
米塞斯的经济学课:讲座与演讲精选集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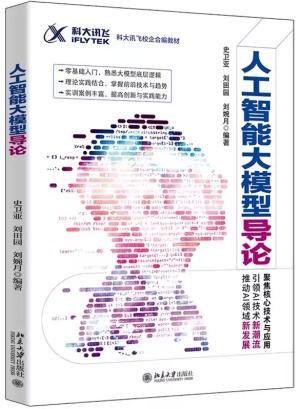
《
人工智能大模型导论 科大讯飞校企合编教材
》
售價:HK$
75.9
|
| 編輯推薦: |
粗粝浑浊的西北气质
沉郁深广的智性思考
人民文学新世纪散文家奖获得者
朝阳以文为刀解构城乡中国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朝阳的非虚构散文集,他从乡村进入城市,以乡野的眼光观察城市,又以城市的头脑思考乡村,站在城乡之间,他扼腕沉思,行文粗粝而沉郁,消解了田园牧歌,也解构了城市文明,他反思,他质疑,以男性气质的硬性思考,捕捉日常生活的戏剧性悖论,剖露出浑浊杂乱的生活真相,他的文字是有小说质感的散文。
|
| 關於作者: |
|
朝阳,原名王朝阳,现居西安,当代散文家,曾获得人民文学新世纪散文家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出版过《野地》《演出》等著作,现为华商传媒集团副总裁。
|
| 目錄:
|
序言:怎么说话,何以沉默
丧乱
父父子子
死亡四种
新闻
公司
中巴
小姐
一桩命案的若干线索
无法抗拒的传说
在乡下
在城里
后记:文学的梦
|
| 內容試閱:
|
丧乱
一、
没有人相信我所说的一切,包括睡在我身旁的妻子。
我从睡梦中醒来,我听到了窗外鸟叫的声音,这是传说中的那只鸟,它只叫了两声,然后消失了。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希望能再听到这种声音,我希望再次证实这种声音。但是没有。
那种声音无法描述。
它在深夜的时候来到我的窗前,它是不详之鸟。
我已经知道,在这个夜晚,我的祖母去世了。
这是2002年农历9月7日夜晚,一只迷信中传说的不详之鸟,飞临我的窗外。我祖母在这个夜晚告别人世。就在这个夜晚,同样的鸟叫声在我老家的窗外啼叫。我姑母听到了这种叫声。她后来说,在听到鸟叫之后,她知道我祖母的魂灵已经走了,那只鸟是来召唤我祖母的魂灵的。她赶紧给我祖母穿上老衣。两个小时之后,我祖母离开了人世。
我无法说服谁,因为我首先无法说服自己的妻子。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的祖母去世了。
二、
我开始准备行囊。
我们家族之树中最老的一枚叶子凋落了,她行世86年。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包括我父亲。在我祖母去世之后,我祖母的名字永远成了一个秘密。
我开始准备行囊,还有在情感上的关于我祖母的所有的积蓄。很少。我发现我远没有我母亲去世时那么难过。我们是隔世的感情。
不,不仅如此。还因为,我祖母是作为我母亲的对立面出现的。她一直站在我母亲的对面。她是一个标准的婆婆,她永远都认定,自己才是儿子最值得信赖的人,是媳妇篡改了自己的儿子。她不可爱。一直到晚年,一直到她再也没有力气和我母亲争斗,一直到我母亲去世,她才容纳了我母亲。我母亲也是在一个深夜离开人世的,当我和我父亲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时,她把头埋在被子里。我三十年里第一次看她落泪。我祖母说:
我儿子怎么这么命苦呢?
过了片刻,她又说了一句话:
老天爷还让我活在人世干什么呢?
这一年我母亲53岁,我祖母83岁。
三、
村子里的人们说,我叔父是个具体的人。在我们村子里,具体的人还有村子东头的宝羊哥,村子西头的骡子叔。
给我叔父介绍对象的时候,对方问,人怎么样?媒人就说,人本分着呢,具体人么。对方就没有再问。
那是一个冬天,我和我叔父去临村买粮去。我祖母肿胀着脸坐在炕上。她叮嘱我叔父:叫你叔把秤秤好。我们就踏着月光上路了。是个冷清的夜晚,天空像一碗稀汤寡水的饭。我和叔父走在无人的路上,我不知道和叔父说话。我叔父走一段路说一句话。他说:狗。前边蹲着一只狗。他说:快收玉米了。玉米在我们身旁。又走了一段路,他唱了一句戏。我没有听明白词,那像一种自言自语。他哼了一种腔调,然后就没有了声音。我们从后门进入了一户人家,他们的前门关着。整个村子似乎都睡了。我们用很短的语言做完了交易。要扎口袋的时候,那个人又从自家的囤子里抓了一把玉米。我们不知道感谢,抬了粮食朝外走。身后是那家关门的声音,艰涩的无法比喻的声音。快要出村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香气,是醋溜白菜的香气。我一下子就闻出来了。我叔父说:醋溜白菜,谁家在炒醋溜白菜。我能听到他喉结转动的声音。我们低着头,抬着玉米回家。我祖母从炕上下来,她手里端着油灯。她解开袋子,抓起一把玉米,放了两颗到嘴里。我们听到清脆的玉米被咬碎的声音,那是包谷晒干水分以后发出的声音。我叔父说:人家给多抓了一把。
四、
这个夜晚像一副着色过重的铅笔画,永远留在我心里。我祖母的身影似乎一直在油灯前晃动。对黑暗的惧怕和对饥饿的恐惧糅合在一起,从未分离。
现在,我站在了我祖母的灵柩前。我祖母躺在这里,我叔父跪在他的身旁。这是许多年以前那个夜晚的三个当事人。我祖母的嘴唇上放着一粒包谷,这是人世最后的一颗粮食,放在她的嘴边,由她带进坟墓,帮她驱赶另外一个世界的饥饿。我摸着我祖母的手。这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手了吗?饥饿已经远离这个老人了吗?饥饿曾经多么严重地袭击了我们,饥饿至今还留在我的身体里。饥饿使我变得肥胖,饥饿使我在吃饭时丧失理智。我始终无法拒绝食物的诱惑,我面对食物时总是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冲动。我吃得很快。我讨厌我妻子贵族化的细嚼慢咽,她对待食物的态度更像一个厌食症患者。我的胃有强大的消化功能。我总是把他们撑得很饱。吃饭对我来说就是必须把胃撑饱,让自己的胃变成一个马力强大的容器。当然,几乎所有的中国餐馆都在以自己的喧闹、丰盛、人满为患,来证明一个备受贫穷、饥饿困扰的国度,来证明一群人备受饥饿迫害的童年,我从来没有认为那是一群美食家。
我祖母躺在这里,躺在她满是灰尘的家里。人们来来往往,从她的身旁走过。柜子上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上歇着一层灰尘,留着一些已经无法辨认的指纹。它几乎就是一个摆设。对我祖母来说,电视展示的外部世界毫无意义,电视只是对现在生活的一种干扰,电视只是虚拟了一个幸福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它改变不了什么。她不允许家里人看电视,她觉得任何娱乐都是毫无必要的。她容忍不了家里的任何闲人,她具体地、分门别类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没有尽头的生活像没有尽头的路,她只是不停地走,从来不看远方。她没有任何爱好,她没有任何信仰。你甚至看不出她哪怕是对生活的一点热情。她只靠本能生活,她只是在日子中一天一天熬过。她要看着种子下地,她要看粮食收回来,她驱赶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她要把他们赶到地里去。她让人难以忍受。她让人觉得,如果生活就是这样,生活就是一场徒劳,她让人觉得,生命如果是这样,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但是,她不接受任何指责,她不指望任何人理解自己。这一切只是因为,她对人世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她把希望给过丈夫,丈夫撇下了她,她把希望给了儿女,儿女们带给她更大的不幸。她四十岁时丧失了丈夫,她的女儿在五十岁时丧失了丈夫,她的儿子,我的父亲,在五十岁时丧失了妻子,他们先她而去,集体腰斩了她对人生的希望,她生活在没有希望的深渊里。无常的灾难让一个缺少文化的农村妇女不敢再对生活抱有任何幻想,生活对她来说就是受难,以自己的生命抵抗无法预知的命运。没有人知道她怎样在漫长的岁月中杀掉自己的所有爱好和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八十多岁让人无法理解的老人。到最后,她似乎连疼痛感也丧失了,她在八十多岁时摔断了胳膊,自己躺了几天,又起来了。
她躺在这里,我不知道她在死亡降临的那一刻想些什么。她感到恐惧吗?她对她生活的这个世界留恋吗?她能回忆起自己早逝的丈夫吗?她曾经快乐过吗?从来都没有人真正走进过她的内心,从来都没有人理解她的人生。现在,一个孤独的老人上路了。她从来没有相信过存在另外一个世界,她就这样完了吗?
在她告别人世的最后一晚,她已经四天没有吃喝,输液的针头无法插进她的血管。她最后的一个动作是,把身边的电灯拉着,拉灭,再拉着,再拉灭。她不断重复这个动作,似乎在考验自己还有没有力气生活在这个世界。那是一只15瓦的电灯,她认为15瓦的电灯已经足够照亮整个夜晚。在凌晨五点的时候,她停止了这个动作。她放弃了。
我祖母的一生结束了。
她姓何,86岁。是我们家族的源头。我的追溯到此为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