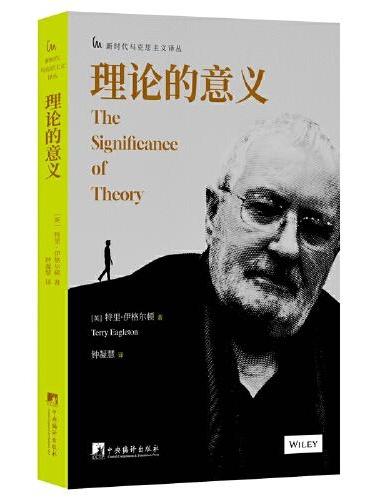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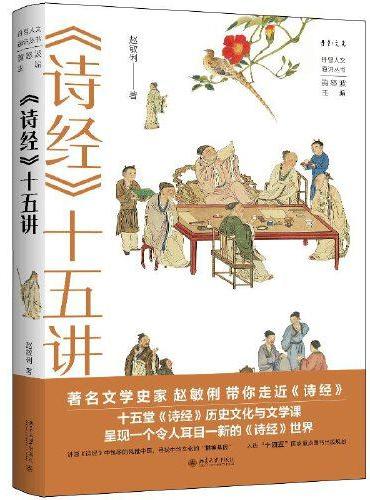
《
《诗经》十五讲 十五堂《诗经》历史文化与文学课 丹曾人文通识丛书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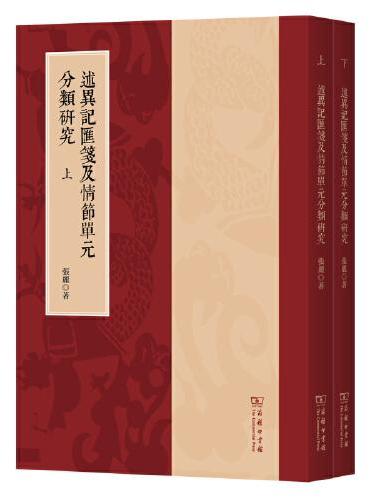
《
述异记汇笺及情节单元分类研究(上下册)
》
售價:HK$
1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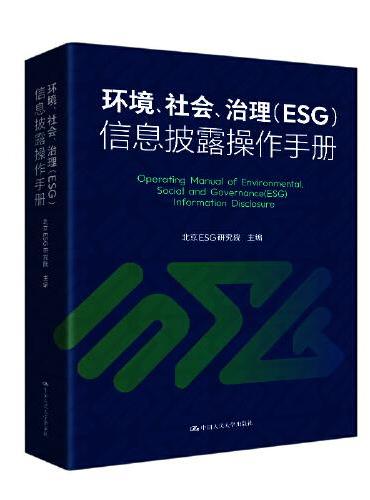
《
环境、社会、治理(ESG)信息披露操作手册
》
售價:HK$
261.8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2928.jpg)
《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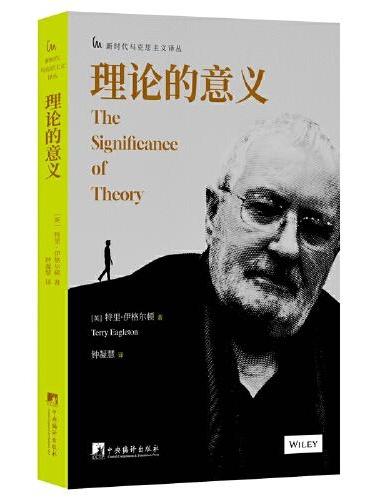
《
理论的意义
》
售價:HK$
74.8

《
悬壶杂记:医林旧事
》
售價:HK$
52.8

《
谁之罪?(汉译世界文学5)
》
售價:HK$
52.8

《
民国词社沤社研究
》
售價:HK$
140.8
|
| 編輯推薦: |
每个人身边,都有那些所谓的朋友,以关心的名义,绑架你的幸福。
当幻想的美好遭遇现实的残酷,未来该何去何从?
费米娜文学奖获奖小说,法国销量超过150000册。
1999年在英国出版英文版,书评出现在各大报刊。
|
| 內容簡介: |
感情破碎、郁郁寡欢的单身妈妈奴珂与她年幼的儿子欧仁尼奥一起生活在巴黎的一个小公寓里。为了全身心地抚养儿子,她执意放弃了自己短暂的艺术事业,找了一份稳定但无聊至极的工作,并试图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儿子身上……
距离圣诞节只有两天了,奴珂牵着儿子的手走在下雪的街头,一路上,他们经历了一件又一件疯狂、搞笑却又让人心碎的故事。他们遇到了亚当和夏娃、出租车司机、花匠安东……母子两人的关系频频受到外界的威胁。他们能够克服道路中的重重阻碍还有那些试图决定他们幸福的所谓善意,顺利度过这个圣诞节吗?
|
| 關於作者: |
|
热娜维芙·布丽扎克(Geneviève Brisac,1951— ),法国著名作家、文学编辑、文学批评家,出生于巴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授文学,并开始文学创作。曾在法国著名的珈利玛出版社担任文学编辑,并为法国《世界报》等报刊撰写文学评论。1996年,她的小说《单身妈妈的周末》荣获“费米娜文学奖”,并于1999年在英国出版英文版。2011年,更加具有自传性质的故事《与父亲共处的一年》获得“出版人奖”。除了在成人文学领域的成就,她还著有二十余本儿童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小丫头奥尔加》系列。2009年,她还与法国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奥诺雷共同创作了《不,我的女儿,你不能去跳舞!》的电影剧本。其作品不仅在法国备受赞誉,而且已经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深受各国读者喜爱。
|
| 內容試閱:
|
“你*喜欢什么动物?”我们走在夜色里,欧仁尼奥问。离圣诞节还有两天。
我说:“考拉、松鼠和水獭。喜欢考拉,因为它的爪子抓在桉树干上的姿势,还因为它和袋鼠是邻居。喜欢松鼠,因为榛子。就像我常说的,它捧着榛子的画面多美好啊。喜欢水獭,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它的名字读起来既难听又动人。因为水。” 我撒谎了。更确切地说,他的问题令我想到的是一只犰狳似的动物。
我的身体和胳膊形成一个无形的把手,欧仁尼奥已经把他的胳膊塞了进去。他神色忧郁。
“你觉得伊丽莎白女王幸福吗?”他喃喃道。
谁跟你提起这个戴帽子的老古董了?又是你爸爸吗?气量狭隘的驳斥险些脱口而出。然而我还是克制住了,说:“我觉得,够幸福的吧,但她的孩子们令她失望。” 把“失望”和“孩子”两个词并置,是一种毫无缘由的恶毒,欧仁尼奥蔫了。
我感到惭愧。
“我们得赶快,”欧仁尼奥说,“迟到了,妈妈,紧着!” “紧着”这个说法真低俗,伊丽莎白女王绝不会说出这种词!”我答道。
伊丽莎白女王是我们的偶像、我们嘲弄的对象、我们的斯芬克斯、我们的替罪羊。
“她生活得不幸福,”我*终这样说,“因为她并不非常希望活得幸福。” 他困惑不解。我想到另一位女王,由于短裤的松紧带断了而冻死雪中,她拒绝从石椅上起身,那里掩藏着她遭受威胁的自尊。我给儿子讲了这个故事。在冰冷的石凳上冻死,是自尊的**,我指出这一点,并突然对自己借机教育儿子的做法感到骄傲。可欧仁尼奥却讥笑道:“浪漫主义又蒙蔽了你,妈妈。故事根本不是这样的。女王大发脾气,咆哮,暴跳,从王国里*强壮的男人中挑了十个,叫他们把石凳挖出来,抬回了王宫,累得他们个个流着大汗,喘着粗气。
谁也不得私下议论女王丢了短裤。你看,这才是自尊的**。” 欧仁尼奥比我更接近王室心理。我取出钥匙和玛姬·辛普森①钥匙夹。玛姬·辛普森,永远的蓝色发髻,那么温柔贤惠。在大楼门厅里,我们听到了鸟叫,颤巍巍的叫声。
它们住在楼梯下通常用来停放儿童推车的地方,因而整个楼梯井里都回荡着它们的练歌声。那是一只巨大的鸟笼,阿拉伯式的花纹缭乱繁复,每当从笼前经过,我都禁不住会说:“欧仁尼奥,你听见天使的音乐了吗?”而他轻微的厌烦,则使我恢复到常态的生活。就像每天早上我送他上学时一样,我对他说: “看,这座房子是巴黎*美的。它很白,很光洁,侧面有花园,铺着砾石,浓密的绿栅栏掩映着小丛的玫瑰,窗户很高,整座房子像一张脸,宽宽的额头,长方形的眼睛。” 欧仁尼奥回答:“你总是说这话:看,听,看,听。饶了我的眼睛,饶了我的耳朵吧。”他的态度很认真。
我们登上楼梯,我在前,他抓着我的后衣襟。我很怀念那段尚在眼前的时光,那时我无视一切劝告,出于对全体医务人员的挑衅,也出于纯粹的愚蠢,把他抱了起来。我想起他刚才对我说的话:“快点,妈妈,我们迟到了。” “迟到,我们约了谁吗?”我怀疑地问。他笑起来。
“只是想个办法让你往前走,”他有些被自己的放肆吓到了,小声说,“你总说只有榜样才能教育。
我们迟到了,这是你*常说的话。”他模仿着我的样子,抻着脖子、噘着嘴、担心地皱着眉:“我们迟到了,快点,亲爱的!” “可我假期里不这样!” “我假期里这样!”欧仁尼奥回答,“马上就是圣诞节了,妈妈。我们得快点。我们去哪过节,不会待在这里你烦我、我烦你吧?人家都有喜欢的家人,我们呢,我们怎么办?” “先说要紧的,我们吃什么?”我说。
长沙发里一个清晰的声音提议:“麦当劳?” “我给你买回来,还是我俩结伴去,像情侣似的?”云霄里的王者①迟疑了,对如此的温柔感到有些吃惊。
“你去买回来。”一番深思之后,他得出结论。
我感到伤心。“好的,亲爱的。你要什么?” 下楼前,我拉上了窗帘,我*终还是把它安在了我们共用的房间里,血红色的窗帘,沉重而庄严,令我想起在剧院工作的时光,它在这里就是为此,为了令我想起我的辞职。看着我们居住的这条狭窄的街,我想,每扇窗后,都有不同的冬夜。在我和欧仁尼奥生活了两年的这套一居室里,有两扇窗。窗外,我们对面墙上,有一小幅画,我以前从没有注意到,那是一幅绿色的画,被一盏小射灯照耀着。它展现的好像是一处风光,大概是一座山崖和一片湖水。看不清,只能看见银色的反光,让人想到那百年一次浮出水面的城。
街上的麦当劳餐厅食客寥寥。进门左手边,坐着紫罗兰。这是我给她起的名字,因为她是个安静的女人。紫罗兰时常会给我讲些什么,这就是她来此的目的,聊一聊。她带着那只不透明的塑料盒,盒子里是一摊烂泥似的东西,竖满了小尖刺。我从不问她吃什么,我们只谈孩子和生活。今晚,她吃完饭,收拾干净,嘟囔着,捡了二十多根吸管塞进她的大包,包里还有塑料勺,随着她的步履颠簸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吸管们将在包里和那些塑料勺子们会合。紫罗兰的存在,没有令我难过,反而给了我安慰。因为她优雅的举止,因为她从不忧伤,尽管她老、穷而且孤独。
我向稍远些的地方望去,橘红色的餐厅里,中央立柱后面,半掩着一张沉思的、愉快的脸,是那个整天在距离麦当劳几米处乞讨的流浪汉。他完完全全生活在这里,在这里睡觉,在这里一天吃两餐,同样的时间、同一张桌子,就像个寄膳寄宿于此的客人。他正把餐巾纸往脖子上围。
我要了大份薯条、中式酱料和一根吸管,我把给儿子的麦当劳拿上楼。
“放在我脚下,奴隶。”他说。
我还没有脱掉大衣。我不想提那时蜇着眼眶的泪水,也不想提落在他头上的巴掌,不光彩,可我那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薯条打着旋飞了出去。
“你总是捣蛋!”我嚷道。
“只是个玩笑,妈妈,”他结结巴巴地说,“你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你只想着你自己,却假装想着所有人,这样不行,就是因为这个你才一个人的,我们俩就像两只死老鼠。” 我想靠近些,摸摸他的胳膊。我想到那些被孩子打、遭众人议的母亲: “她们活该。太宠孩子,把孩子变成恶魔。” “不宠孩子,把孩子变成残废。”另一个声音高叫。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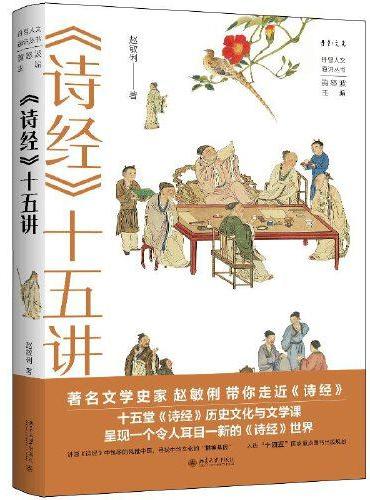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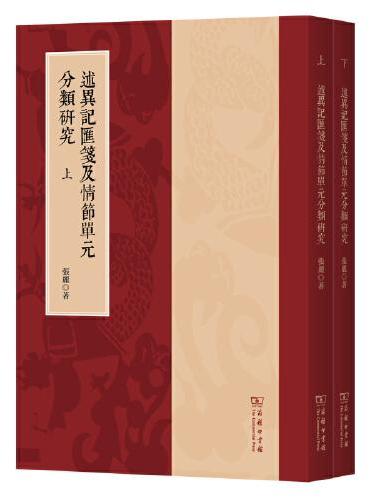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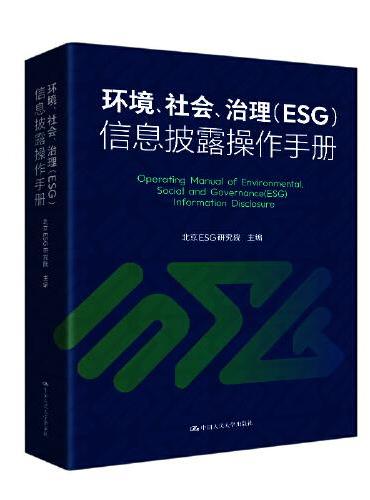
![桑德拉销售原则 伍杰 [美]大卫·马特森](http://103.6.6.66/upload/mall/productImages/24/46/97871117629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