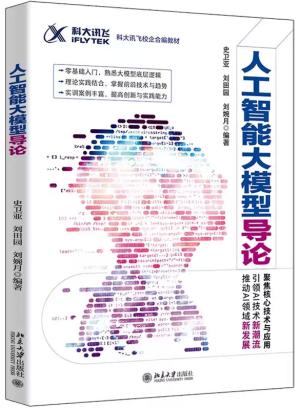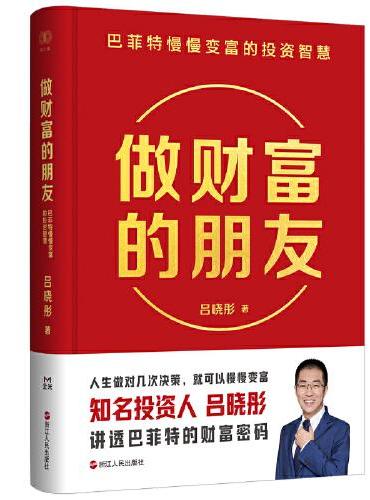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软体机器人技术
》
售價:HK$
97.9

《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
售價:HK$
74.8

《
奴隶船:海上奴隶贸易400年
》
售價:HK$
75.9

《
纸上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破译古老文明的密码,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150+资料图片)
》
售價:HK$
85.8

《
米塞斯的经济学课:讲座与演讲精选集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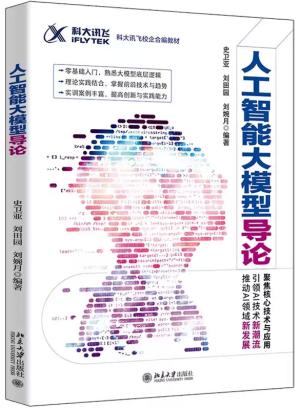
《
人工智能大模型导论 科大讯飞校企合编教材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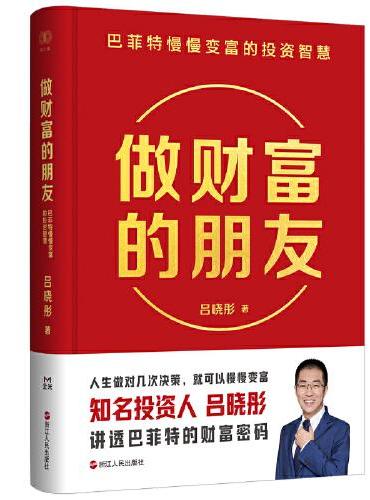
《
做财富的朋友:巴菲特慢慢变富的投资智慧
》
售價:HK$
82.5

《
一群数学家分蛋糕:提升逻辑力的100道谜题
》
售價:HK$
60.5
|
| 編輯推薦: |
|
《老北大的故事(修订版)》:用心感知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作者以学术史的视野,借阐释“故事”展现历史图景。
|
| 內容簡介: |
《老北大的故事(修订版)》为陈平原“大学五书”丛书中的一本。
作者将众多零散的关于老北大的私人记忆集合起来,作为一种“大学叙事”,加以辨析、阐释与发挥。借助若干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来呈现 “北大传统”和“北大精神”。
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考察,将关于校庆的诸多“好话”与“老话”作为解读对象, 试图在纵横交错的“历史地图”上,寻找真正的“北大之精神”。除了凸显史家的眼光,更希望引导读者走向历史深处,思考若干重大问题。
除了侦探校史上扑朔迷离的“故事”,更是认真剖析建构光荣传统的“神话”。
|
| 關於作者: |
|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当代中国人文观察》等。
|
| 目錄:
|
目 录
“大学五书”小引 001
小引 003
**辑 北大旧事
校园里的真精神 011
哥大与北大 049
北大传统之建构 086
老北大的自画像 107
──“校庆感言”解读
作为话题的北京大学 124
──历年“纪念册”述评
第二辑 校史杂说
北京大学:从何说起? 151
北大校庆:为何改期? 167
北大校名:如何英译? 184
北大校史:怎样溯源? 192
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 205
──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
不被承认的校长 218
──丁韪良与京师大学堂
迟到了十四年的任命 241
──严复与北京大学
第三辑 百年庆典
北大的“光荣”与“梦想” 273
作为一种文化景观的百年校庆 279
有容乃大 283
——答《人民日报》记者问
大学有什么用 290
——答《南方周末》记者问
北大:一个话题 297
——答《新快报》记者问
“半真半假”说北大 303
——答《新周刊》记者问
辞“校史专家”说 308
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 313
——兼答《北京大学校史》编者
再说“北大生日” 317
第四辑 大学书影
大学百年 323
──从《东京大学百年》说起
“书信作家”胡适之 328
──关于《胡适书信集》
人文景观与大学精神 333
──读《剑桥与海德堡》《哈佛琐记》等
读《(民国二十三年度)国立北京大学一览》有感 343
关于建立“胡适文库”的设想 353
“为了蔡先生的嘱托” 359
——《蔡元培年谱长编》读后
“触摸历史”之后 365
《北大精神及其他》后记 372
附录:《北大精神及其他》序(夏晓虹) 379
修订版后记 384
附识 386
|
| 內容試閱:
|
校园里的真精神
永恒的风景
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构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可以言之凿凿的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科研成果、名师高徒外,还有必须心领神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介于两者之间, 兼及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是众多精彩的传说。
比如,当老同学绘声绘色地讲述某位名人在这棵树下悟道、某回学潮在这个角落起步、某项发明在这间实验室诞生、某对情侣在这条小路上**次携手时,你感觉如何? 是不是觉得太生动、太戏剧化了?没关系,“无巧不成书” 嘛。再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信不信由你。只要不对这所学校失去信心,慢慢地,你也会加入传播并重建“校园风景线”的行列。
比起校史上极具说服力的统计数字,这些蕴涵着温情与想象的“传说”,未免显得虚无缥缈;因而,也就不大可能进入史家的视野。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的场所。漫步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或者“远眺”窃窃私语的湖边小路上的恋人,只要有“心”,你总能感知到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
如此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叙述,实在难以实证。但对于曾经生活或向往生活于其间的人来说,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却极有魅力。世人之对“红楼内外”感兴趣,有各种各样的机缘。我的*初动因,竟是闲聊时的“争强斗胜”。
比起“全北大”(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科、硕士、博士的全部课程)来,我只能算是“半路出家”。正因为有在别的大学就读的经验,我对北大人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开口闭口“我们北大”,不只表明身份,更希望提供评判标准——既充满敬意,又有点不以为然。试着虚心请教:让你们如此心迷神醉的“我们北大”,到底该如何描述?有眉飞色舞、抛出无数隽语逸事、令人既惊且喜的;也有引经据典,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从蔡元培到毛泽东,让我重新回到现代史课堂的。后者可以帮助确定北大在百年中国政治史上的位置,只是叙述姿态过于僵硬;前者补阙拾遗,而且引人遐想,可惜传说多有失实。
希望能够兼及“宏伟叙事”与“小品笔调”,我选择了“回到现场”的研究策略。比如,同样谈论北大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五四”,我会对游行路线怎样设计、集会演讲为什么选择天安门、火烧赵家楼又是如何被叙述等等感兴趣。至于史学家不大关注的北河沿的垂柳、东斋西斋学风的区别、红楼的建筑费用、牌匾与校徽的象征意味、北大周围的小饭馆味道怎样、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褂魅力何在等,也都让我入迷。
于是,我进入了“历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广泛搜集并认真鉴赏起“老北大的故事”来。杂感、素描、随笔、小品、回忆录,以及新闻报道、档案材料等,有带露折花的,也有朝花夕拾的,将其参照阅读,十分有趣。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当年的“素描”与几十年后的“追忆”, 竟无多大出入。考虑到关于老北大的旧文散落各报刊,寻找不易,不可能是众多八旬老人转相抄袭。**的解释是, 老北大确有其鲜明的性格与独特的魅力,因而追忆者“英雄所见略同”。借用钱穆《师友杂忆》中的妙语:“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一个人如此,一所大学也不例外:能被无数学子追忆不已的,方才是此大学“生命之真”。此等“生命之真”,不因时间流逝而磨灭,也不因政见不同而扭曲。
其实,“老北大”之成为众口传诵的“故事”,很大程度得益于时光的流逝。绝大部分关于北大的回忆文章,都是作者离开母校之后才写的。而抗战爆发北大南迁,更是个绝好的机缘。正因远离红楼,方才意识到其巨大的感召力,也才有心思仔细勾勒其日益清晰的面孔。1940 年代出现一批相当优秀的回忆文章,大多有此心理背景。柳存仁的系列文章《北大和北大人》中,有这么一段话:
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旧游星散,否则如果我在今天还有机会住在东斋西斋矮小卑湿的宿舍里, 我决不会,也不能写出这样一篇一定会被我的师友同学讥笑做低能的文章。……我不愿意忘记,也猜想其他的师友同学们也永远没有忘记那霉湿满墙, 青苔铺阶的北大二院宴会厅,更决不会忘记那光线黑暗的宴会厅里,东边墙上悬挂的一幅蔡孑民先生全身的油画,和他在画中的道貌盎然和蔼可亲的笑容。这幅像,这个古老的厅堂,也许就足以代表北大和北大人而有余。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踏进那青苔铺阶的古老厅堂,更何况那厅堂已经失落在敌人手中,难怪远游的学子频频回首, 并将其相思之情诉诸笔墨。
抗战胜利了,北大人终于重返红楼。可几年后,又因院校调整而迁至西郊燕大旧址,从此永远告别了令人神往的沙滩马神庙。对一所大学来说,校址的迁移,并非无关紧要,往往成了撰写校史时划分阶段的依据。抗战南迁, 对于北大日后的演变与发展,实在太重要了。因而,将“老北大”封闭在1898—1937 的设想,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对于习惯新旧对举、时时准备破旧立新的人来说,只要与“今日北大”不符者,皆可称为“老北大”。这种漫无边际的概念,为本文所不取。为了叙说方便,本文将“老字号” 献给南迁前的北京大学包括其前身京师大学堂。
从1918 年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起,“老北大”的形象逐渐浮现。有趣的是,历年北大出版的纪念册中,多有批评与质疑;而发表在其他报刊的回忆文章, 则大都是褒奖与怀念。对于母校之思念,使得无数昔日才情横溢尖酸刻薄的学子,如今也都变得“柔情似水”。曾经沧海的长者,提及充满朝气与幻想的大学生涯,之所以回味无穷,赞不绝口,大半为了青春,小半属于母校。明白这一点,对于老学生怀旧文章之偏于理想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文所引述的“老北大的故事”,似乎也未能免俗, 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尽管我已经剔除了若干过于离奇的传说。至于或记忆失误,或角度偏差,或立意不同,而使得同一事件的叙述出现众多版本,这不但不可惜,反而正是老北大之精魄所在: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因而也就不会有完全统一的形象。
前面提及“英雄所见略同”,这里又说是形象塑造无法统一,二者岂不互相矛盾?不妨套用“求同存异”的治世格言:对“老北大”精神的理解,各家没有根本的区别, 差距在于具体事件的叙述与评判。
“北大老”与“老北大”
“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此乃二三十年代流传在北平学界的口头禅。就从这句“读法不一”的口头禅说起吧。
首先是叙事人无法确定,有说是择校的先生,也有说是择婿的小姐。择校与择婿,相差何止千里!与叙事人的不确定相适应,北大之“老”也难以界说。有说是北大人老气横秋,办事慢条斯理的;也有说是校园里多老房子、老工友,连蔡元培校长的汽车也老得走不动的;还有说是历史悠久、胜迹甚多的。第三说*有诗意,容易得到北大人的认可。朱海涛撰写于1940 年代的《北大与北大人· “北大老”》,正是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
摩挲着刻了“译学馆”三个大字的石碑,我们缅怀当年住在这里面的人,每月领四两学银的日子。在三院大礼堂前散步,我们追念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时,多少青年人被拘禁在这里面。徘徊于三一八殉难同学纪念碑前,我们想起这国家的大难就有待于青年的献身。这一串古老的历史的累积,处处给后来者以无形的陶冶。
说“陶冶”没错,说“古老”则有点言过其实。比起巴黎、牛津、剑桥等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名校,北大无论如何是“小弟弟”。在《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上,有两则在校生写的短文,也叫《北大老》,极力论证刚过“而立”之年的北大,不该“倚老卖老”,更不该“老气横秋”,因为有牛津大学等在前头。
到了1948 年,校长胡适为“纪念特刊”撰写《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仍是强调“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可笔锋一转,擅长考据的适之先生,谈论起另一种计算年龄的办法: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 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一二四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
有趣的是,北大校方向来不希望卖弄高寿,更不自承太学传统,就连有直接渊源的同文馆(创立于1862 年,1902 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也都无法使其拉长历史。每当重要的周年纪念,校方都要强调,戊戌年“大学堂”的创立, 方才是北大历史的开端。胡适称此举证明北大“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这与当事人对大学体制以及西方文化的体认有关,更牵涉其自我形象塑造与历史地位建构。说白了,北大的“谦虚”,蕴涵着一种相当成熟的“野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如此说来,比起北大校史若不从汉朝算起,便同文明古国“很不相称”的说法(参见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历任校长之自我约束,不希望北大往前溯源,其实是大有深意在。从北大的立场考虑,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当然,校史的建构,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需求或个人的良好愿望。我想说的是,相对于千方百计拉长大学历史的“常规”,历来激进的北大,之所以“谨守上谕”,不敢越雷池半步,并不完全是因为“学风严谨”。
翻翻光绪二十四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光绪二十八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两种重要文献所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包括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员聘请、学生守则等,都与传统书院大相径庭。至于随处可见的“欧美日本”字样,更是提醒读者,此章程与“白鹿洞书院教条”了无干系。当然,有章可以不依,有规可以不循,制定了新的章程,不等于建立了新的大学。幸亏有了**届毕业生邹树文、王画初、俞同奎等人的回忆文章,我们才敢断言,京师大学堂确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得到普遍承认,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历史,便逐渐被世人所遗忘。选择若干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大学草创期的艰难与曲折,比如孙家鼐的规划、许景澄的殉难、张百熙的实干、严复的苦撑,等等。至于进入新式学堂后,学生如何习得“文明生活”,也是我所深感兴趣的。光绪二十五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禁约》,有些条款现在看来“纯属多余”。比如用相当长的篇幅强调课堂上必须依次问答、不可抢前乱说、声音高下须有节制等。*有趣的,还是以下这条禁令:
戒咳唾便溺不择地而施。屋宇地面皆宜洁净,痰唾任意,*足生厌。厅堂斋舍多备痰盂。便溺污秽, 尤非所宜。是宜切记,违者记过。
想象当年的大少爷们,如何“忍气吞声”,逐渐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实在是很好玩的事情。今日中国任何一所大学, 都不会将此等琐事写进规章。可在“西学东渐”史上,“不随地吐痰”,也算是颇有光彩的一页。
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没有毕业生,学校因战乱停办两年。壬寅(1902)入学的,方是**批得到“举人学位” 的大学生(时在1907 年)。邹树文《北京大学*早期的回忆》中,述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之礼贤下士,为学校网罗人才,在遭时忌、多掣肘的环境下恢复京师大学堂,功不可没:“我们现在人知道蔡孑民先生,而忘记了张冶秋先生任管学大臣时代创办之艰苦,实在比蔡先生的处境难得许多呢!”此说不无道理。1905 年,大学堂的管理人由“管学大臣”降为“监督”。出任**任监督的张亨嘉,以其精彩的就职演说,被学生不断追忆。这里选择邹树文颇为戏剧化的描述:
监督与学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学生向监督三个大揖,行谒见礼。礼毕,张监督说:“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 努力自爱。”于是乎全部仪式完了。这总共十四个字, 可说是一篇*短的演说。读者诸君,还听见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说没有?
此种逸闻,很合北大人的口味,因而谁都乐于传诵。至于当初张监督为何如此“言简意赅”,是否别有苦衷,也就无暇计较了。
大学初创阶段,弊病甚多,此在意料之中。大部分学生承袭科举陋习,以读书为做官的阶梯,仕学馆录取的又是在京官吏,大学于是乎与官场没有多大差别。学生可能地位显赫,因迎銮接驾而挂牌请假;运动场上教官小心翼翼地喊口令:“大人向左转!”“老爷开步走!”这些逸闻,全都查有实据。可笑谈终归是笑谈,实际上,大部分毕业生并没得到朝廷的恩惠,所谓“奖励举人”,与“升官发财” 根本不是一回事(参见王道元《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另一个更加严重的指责,便是学生无心向学,沉缅于花街柳巷。陶希圣撰《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其中有一节题为“二院一堂是八大胡同重要的顾客”,写尽民初国会参众两院及京师大学堂的丑态。可据千家驹回忆,1930 年代的北大学生,也颇有经常逛窑子的(《我在北大》)。学风之好坏,只能相对而言。想象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师生,都是“官迷心窍”,或者整天在八大胡同冶游,起码不太符合实际。
不说京师大学堂的教员,以及培养出来的学生,颇多正人君子;就说新文化的输入与大学的改革,也并非始于1917 年蔡氏之莅校。不妨先读读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其中述及北大的整顿与革新:
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民初北大“启革新的端绪”者,多为章门弟子。从学术思想到具体人事,太炎先生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密切的关系。除上述沈兼士、钱玄同、周氏兄弟外,进入北大的章门弟子还有朱希祖、马裕藻、黄侃等。据误被作为太炎门徒引进的沈尹默称,章门弟子虽分三派,“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和北大》)。这种纠合着人事与思想的新旧之争,在蔡氏长校以前便已展开,只不过不像以后那样旗帜鲜明目标明确而已。读读林纾、陈衍、马其昶、姚永朴等人有关文章,可以明白北大校园里的改朝换代,如何牵涉政治潮流、学术思想、教育体制,以及同门同乡等具体的人事关系,远非“新旧” 二字所能涵盖。
京师大学堂尚有独立的面貌,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1912—1916),则基本上隐入历史深处。除了以上所说的“革新的端绪”外,还有几件小事不能不提。一是民国初建,教育部以经费短缺管理不善为由,准备停办北大, 校长严复上《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一是袁世凯称帝,北大教授马叙伦挂冠而去,学界传为美谈;再就是1916 年9 月,校方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20 万,筹建后来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
紧挨着皇宫的大学
北大之所以名扬四海,很大程度得益于1919 年的五四运动。西学的引进与新文化的产生,既有密切的联系, 也有不小的区别。谈“西学东渐”,上海更适合于作为题目; 至于“新文化运动”,则是发生在古都北京,而且由当年的**学府北京大学挑头。就因为,后者包含着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涉及士大夫政治的转型,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尊。不满足于寻求新知,更愿意关心天下兴亡,这一自我定位,使得“闹学潮”成为北大的一大景观。很难想象,没有学潮的北大,能否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作为一所大学,北大固然以培养了大批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而骄傲;可北大影响之所以超越教育界,则在于其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在某个特定时期,“闹学潮”几乎成为“争民主”的同义词。
北大之闹学潮,可谓渊源有自。1935 年12 月30 日, 刚刚结束一二· 九运动的北大学生,出版了《北大周刊》**期(一二· 一六示威特刊)。其中有赵九成所撰题为《我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的文章,意在正本清源:
我们的学生运动,不是从现在起的,也不是从五四时代起的,推溯其源,当导源于东汉。……在中国,*先发生的便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
三万太学生讥议时政,裁量公卿,成为强大的舆论力量, 制约着朝廷的决策。于是,天子震怒,大捕党人,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对于“党锢之祸”,史家评价不一,但将其作为统治者镇压学生运动的开端,则不会有异议。此等“清议”之风,为自视甚高的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生徒所继承,因而成为皇上的心腹之患。不过,历代虽有严禁学生干政的禁令,太学生的政治激情却从来没有熄灭,这与其一身系天下兴亡的自我定位有关。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取代国子监而成为全国**学府和教育行政机关;即便改为“国立大学”,学生们仍自认作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反差:校方溯源时,不愿从东汉太学讲起;学生闹学潮,反而攀上了“党锢之祸”。
北大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与古老的“太学”传统,确实不无联系。所谓“京师大学堂”, 在晚清,往往省略“京师”二字,径呼“大学堂”(有“大学堂”牌匾为证)。近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史料》,将京师大学堂直译为Capital College,远不及以前的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 准确传神。“皇家大学”,这才是当年创办者的真正意图。将一所大学建在皇宫旁边,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上有一张北大全景照片,显然是在景山上俯拍的。当年的摄影师,只要稍微调整一下镜头,紫禁城便进入视野。只不过大学堂开办不久,帝制便已覆灭,民国子民不再仰慕皇宫。
与近年各种真真假假的皇家服饰、皇家菜系、皇家建筑大行其时截然相反,二三十年代的读书人,更愿意强调其平民意识。诸多关于北大周围环境的描述,偏偏不提近在咫尺的皇宫。张孟休的《北京大学素描》,已经讲到了景山公园的“高岗眺望”,皇宫依然不入高人眼。刘半农欣赏三院前面的无名小河,理由是“带有民间色彩”和“江南风趣”,远非“围绕皇城的那条河”可比(《北大河》)。1940 年代中期,朱海涛撰写《北大与北大人》系列文章, 其中《沙滩》一则,终于从汉花园、大红楼、松公府、四公主府转到了远眺“玲珑剔透的紫禁城角楼”:
向西望去,护城河的荷花顺着紫禁城根直开入望不清的金黄红碧丛中,那是神武门的石桥,牌坊,那是景山前的朝房,宫殿。我尤爱在烟雨迷蒙中在这里徘徊,我亲眼看到了古人所描写的“云里帝城双凤阙, 雨中烟树万人家”。文章对日本侵略军将北大人引以为荣的红楼作为兵营大发感慨,可想而知,谈论紫禁城,也是个相当沉重的话题。不管是故国相思,还是观光游览,紫禁城的帝王之气,并不为浮尘所完全掩盖。因而,朱文的*后一句,“北大人是在这种环境中陶冶出来的”,值得仔细琢磨。
在望得见皇城的地方念书,形成何种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制已经取消,高高耸立的皇宫,依然是某种文化符号。每天阅读此符号,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或者欣赏,或者厌恶,但有一点,皇宫所包含的“政治”“权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阅读者。北大师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无这种心理积淀。每回学生示威游行,都要在天安门前演讲,当然不只是因那里地方宽敞。进入民国以后,“天安门”作为政治符号,取代了“紫禁城” 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种开放性,兼有“公共空间”与“权力象征”的双重意义,成为政府与民间共同注目的焦点。从北大民主广场到天安门城楼,这距离未免太近了。当初清政府筹建京师大学堂时,若把校址设在山清水秀、远离权力中心的郊区,学生们的政治意识是否会有所减弱,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北大学生自认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种信念之确立,早在五四运动以前。1903 年的拒俄运动中,北大学生集会抗议,慷慨激昂,表示“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在这“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幕” 中(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虽有“伏阙上书”的动议,但其读禁书,喜演讲,发通电,以及事后有人走向社会,组织武装等,均非汉宋太学生所能想象。而五四以后的学生运动,往往有政党的直接领导,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所谓太学传统,主要取其政治意识;至于实际运作,早已斗换星移。
将学校作为党争的基地,其间利弊得失,黄宗羲、章太炎的意见截然相反,值得三思。这里不想详细讨论学潮的功过,而是借政府对待学潮的态度,窥探现代中国政治的演进。借用谢兴尧的话来说,便是“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红楼一角》)。
在“**幕”中,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争到了马上选派出国留学的权利。此后,读书人地位急剧下降,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1919 年的五四运动,只是以火烧赵家楼的罪名,把若干学生抓起来,可见政府对舆论尚有忌讳。到了1926 年的三一八惨案,那可就是公开的屠杀了。周作人将后两个事件,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的象征:五四代表知识阶级的崛起,三一八象征政府的反攻。“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与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此后可就大不一样了,以北大教授李守常、高仁山惨遭杀害为标志,政府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以**手段解决学潮(《红楼内外》)。
对于20 世纪上半叶由北大及其他高校发起的学潮, 我赞同目前大陆学界的主流意见,即大多数参与者是出于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崇高目标。**需要补充的是,学校当局的苦衷,同样值得理解与同情。除了校园内部的风波, 校长必须承当主要责任,绝大部分针对政府的示威游行, 学校当局是无能为力的。学潮一旦发生,教授可以参与, 也可以不参与;校长则夹在政府与学生中间,处境相当尴尬。历任北大校长,从张百熙到胡适之,大都采取保护学生、化解矛盾的策略。可几十年间,党派在学潮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大,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北大校长实在不好当。办教育者的心情不难理解:在“理”与“势”间保持某种平衡,以求得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蔡元培以其地位与个人魅力,可以用不断地辞职作为武器,这一点,并非每个校长都能够并愿意做到的。
在每所大学中,作为主体的校长、教授、学生,三者各有其位置及利益,奋斗的目标自然不会一致。而在北大这样极为敏感的地方,如何处理源源不断的学潮,对校长来说,无疑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众多回忆录中,蔡元培成了**支持学潮的大学校长。这种描述,与蔡氏本人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有较大的出入。作为北大校长, 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但反对学生示威游行。可以将蔡氏自述,与蒋梦麟的回忆相参照。《西潮》第十五章述及五四后蔡元培的辞职南下:
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
指责北大学生沉醉于权力、不断的学潮扰乱了正常教学秩序,此乃校长的立场。至于大学生眼中的校长,则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读读当年学潮积极分子的回忆文章,其中多有校长、院长的“漫画像”。
蔡元培长校十年,一半时间在外,与学生直接冲突较少,可也仍有金刚怒目的时候。据说,曾有学生几百人集合示威,拒交讲义费,请看蔡校长如何处理:“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我给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为国家大事而抗议,与争取个人福利,二者不好相提并论。可是,“校园政治”的微妙之处正在这里:你很难分辨主事及参与者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谋求私利。学潮一旦爆发,必然鱼龙混杂,而且很容易“转化”。有感于此前之谈论学潮,多从学生角度立论,方才强调引进校长的视角,以供参照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