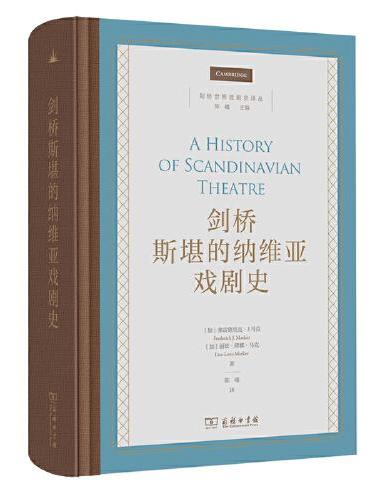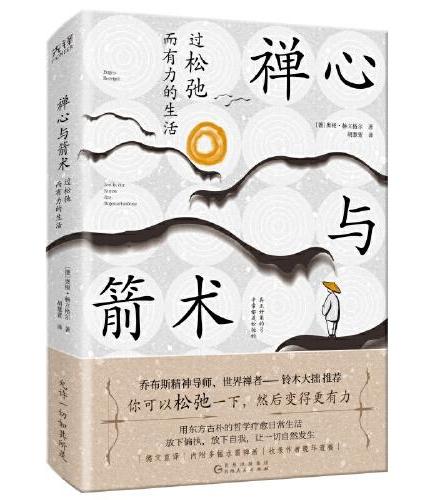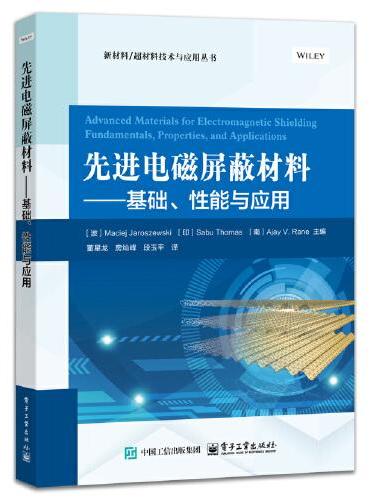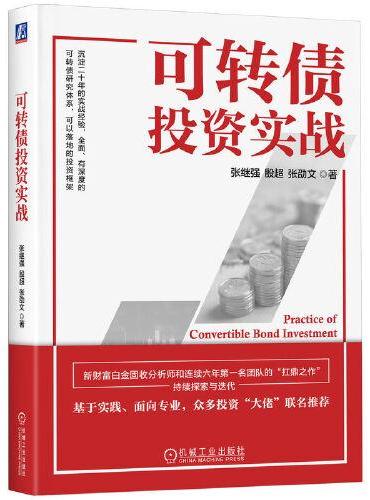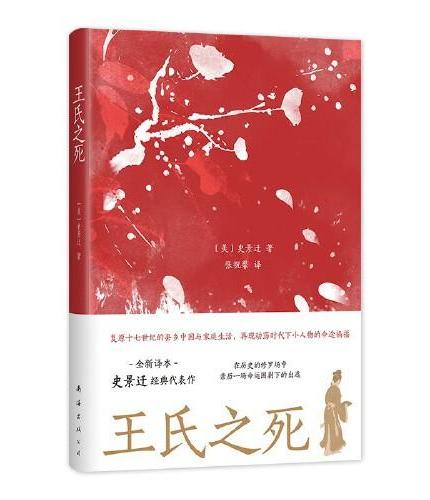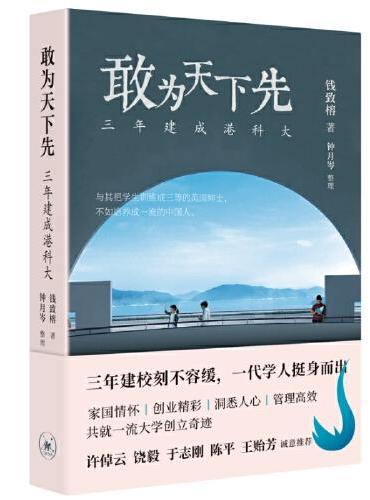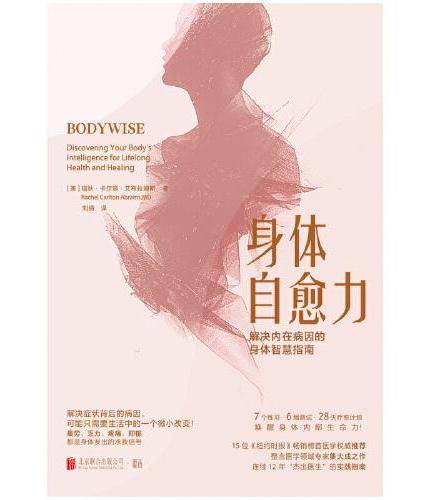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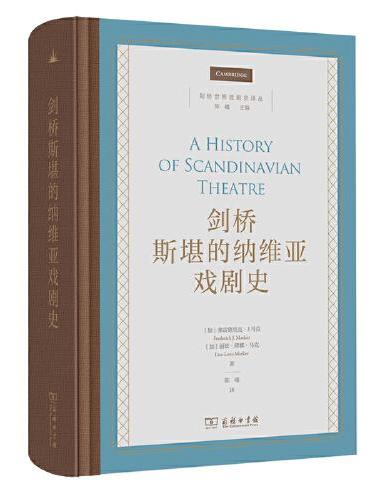
《
剑桥斯堪的纳维亚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HK$
15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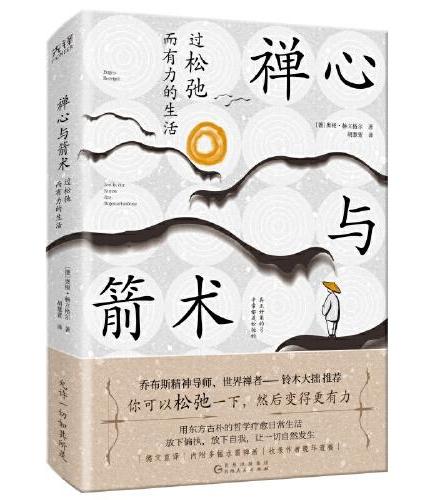
《
禅心与箭术:过松弛而有力的生活(乔布斯精神导师、世界禅者——铃木大拙荐)
》
售價:HK$
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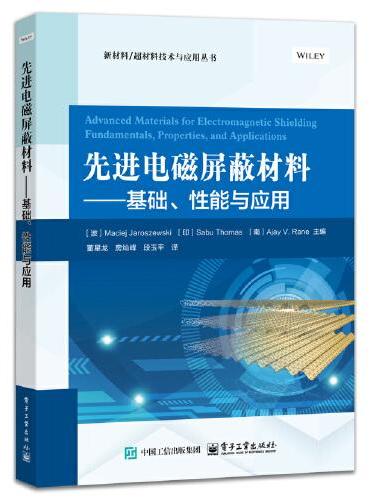
《
先进电磁屏蔽材料——基础、性能与应用
》
售價:HK$
2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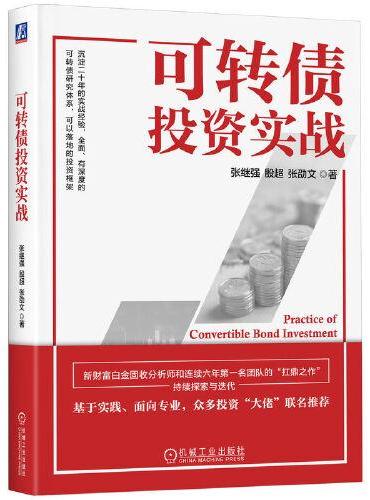
《
可转债投资实战
》
售價:HK$
1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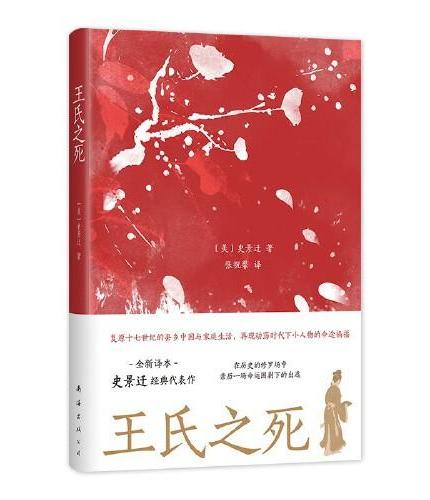
《
王氏之死(新版,史景迁成名作)
》
售價:HK$
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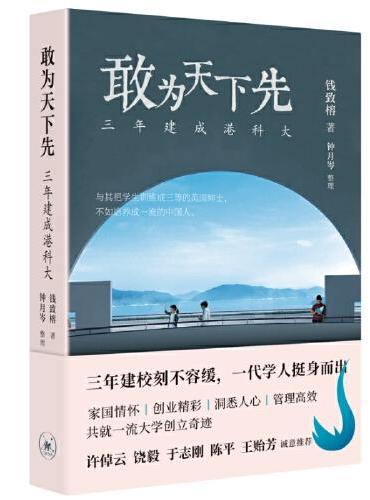
《
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
》
售價:HK$
79.4

《
长高食谱 让孩子长高个的饮食方案 0-15周岁儿童调理脾胃食谱书籍宝宝辅食书 让孩子爱吃饭 6-9-12岁儿童营养健康食谱书大全 助力孩子身体棒胃口好长得高
》
售價:HK$
4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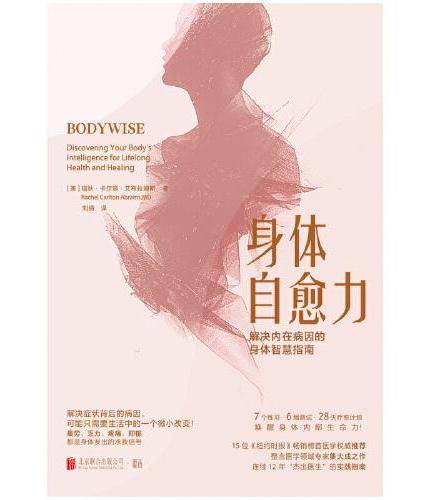
《
身体自愈力:解决内在病因的身体智慧指南
》
售價:HK$
101.2
|
| 編輯推薦: |
我愿意相信,在平行宇宙的那边,一定有另一个他们。
就让他留在那个不常开启的房间;就让她保持昨日清澈的容颜。
就让我们老去的老去,他们年轻的,永远年轻。
1.《不曾爱过,怎会懂得》是著名作家沈熹微十年后首次发表的短篇小说集。
这本书告诉我们:离开永远比相遇更容易,因为相遇是几亿人中一次的缘分,而离开只是两个人的结局。相遇难,分手易,但世人看不到有缘无份的熙攘,总以为机会无限,所以不珍惜眼前人。我们总是这样,悲伤时要一个肩膀,而开心时拥抱全世界。时光偷走的,永远是你眼皮底下看不见的珍贵。
十年过去,她的状态和心境都发生了变化,她说:“分散很好,寂静很好,我喜欢道别。郑重其事地道别,使我们知道自己如何相聚过。 情怀不再,这样的小说不会再写了,这是*后的告别。因这直抵尽头的意义,我又变得有点珍惜。我曾经非常年轻,曾经一无所有但饱含激情,曾经不怕丢脸地写字。 ”
2.新书《不曾爱过,怎会懂得》讲述了15个爱憎会、怨别离的故事,这世间的相遇离别,男女痴缠,而结局往往是绚烂之后,归于寂静和平淡。
对爱情小说来说,很多仍在相信童话的人往往设计结婚做为完美结局,但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童
|
| 內容簡介: |
关于生活:原来一切并非我以为的样子,现实的开始就是想象死亡的开始。想象的样子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我甚少对生活有所想象,我只是像坐在车上的人,接受生活迎面而来,速度令人猝不及防,像是要将人一拳打倒,随即又消失,快得根本抓不住。
关于孤独:我涉足他的世界,重新布置他的房间,整理他的衣物,将他阳台上枯萎的植物拔除,全部换上我爱的品种,我以为他是因为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才默默地放任纵容。这一刻,我才忽然明白过来,这只是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我来不来,走不走,对他来说都是可有可无的,我不是他心里的那个人。
关于失去:在晚风里看着他将车开走,她缓缓走上楼梯,没有踏响感应灯。黑暗中,许多往事如鬼魅般从眼前一一飘过,又匆匆远去,将她一人留在这里。所幸,要说的话都说了,放得下的,放不下的,都要道别。
关于青春:年轻的生命就像海绵,努力吸收着外来的一切。那时候,世界贴得那么近而未揭开朦胧的面纱,爱情仅限于天真的想象,但那天真里有种笃信,笃信快乐和伤害是爱的组成部分,就像日子是由晴天和雨天组成,生活是由高潮和低谷组成,这种完整的本身就是美的。
爱过,离散,生活继续。这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只要舍得放下身段,谁都可以谋得一席之地。
没有人的离开是永远的消失,每一段经历都会给生命留下痕迹,给自己的身心留下或深或浅的烙印,使我们成为*终的自己。
15个故事,15个相逢与别离,沉默或欣喜。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堂的模样,有创伤,有缺陷,有遗憾,独独没有完美。
得不到的与已失去,都是我们所拥有的,不曾爱过,怎会懂得,懂了之后,庆幸还有余生可追忆。
|
| 關於作者: |
|
沈熹微,著名作家,安妮宝贝后**被人称道的心灵故事写作者,“新小资文学”代表人物,发表文字上百万。出版小说集《浮夸》。得益于幽居病中的十年,文风沉静,有与年龄不符的成熟豁达。她的文字如工笔画细细描摹所见所感,但在优美、细腻和聪明、敏感之外,你可以发现她的故事中有属于她自己的坚硬内核,对于时间、人生、爱情的反省,宛如一个人独自穿越黑暗悠长的隧道,这条路没有尽头。
|
| 目錄:
|
目录
1.夜盲症
2.白月光
3.往事如风
4.明日天涯
5.茵茵
6.沸点
7.流沙
8.在水一方
9.微澜
10.失焦
11.太迟
12.暗河
13.爱后余生
14.多雨的夏天
15.祝你幸福
永结无情游(跋)
|
| 內容試閱:
|
我总这样对别人说——阮茵茵是我见过的*好的女孩。
我一眼便认出了阮茵茵。
她瘦高个子,单薄的身材,穿着短款的米白色布旗袍、和横绊扣同一色系的粗跟皮鞋,独自撑着太阳伞等在公司楼下的篮球场边,两条腿白得近乎透明。六月灼热的日光在她身后投下一条深深的阴影,乍看过去,那影比人实在,而人,在周身素淡的颜色中反倒像是要化开。
“茵茵。”Cindy叫她。
女孩回过身冲我们挥手微笑,唇角扬起,露出一线洁白的牙。她的发际用细小的夹子别住,露出宽阔光洁的额头,发梢垂下来,蓬松地落至两肩,旗袍是朴素的款式,整个人看上去好似一张干净柔和的旧手绢,看不出年纪,却感觉极舒适。
我愣了愣。
Cindy指着我对阮茵茵说:“这就是我们部新来的尹长萍,暂时要先跟你同住一阵。”
茵茵点头,特别对我笑了笑。仿佛怕自己表示欢迎却不得其法,她很主动地去帮我拎手边那只简陋的行李箱。箱子本来就旧了,清晨来时又被路边的公车溅了半身的泥水,我连说不用,阮茵茵却已将拉杆利落地拔出来。她的手臂瓷白细长,腕处有一只淡绿色的玉镯顺着清瘦的小臂上下滑动,哐的一声,我来不及提醒,那镯子便已弹碎在行李箱早坏掉的拉杆上。
碎裂的玉石纷纷跌落在水泥地上,瞬间失了颜色,阮茵茵的手有些发红。我万分尴尬,离开B城时那只箱子的拉杆也曾这样突然弹出来打到我,为什么当时不觉得痛?
Cindy一手掌着我们一人的肩道:“没事没事,我那里有只差不多的镯子,茵茵你也见过的,明天给你带来,就算替长萍赔啦。当然,月底可是要从她薪水里扣除的。”Cindy脸上是精明的笑意,我辨不清她是玩笑还是当真,倒是阮茵茵嗤了她一句:“谁要你的?”转头安慰我,“别听她瞎说,赔什么赔,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我仍是不安,担心她是出于礼貌,讷讷地说:“要赔要赔。”阮茵茵说:“哎,真的不用了!不重要的,长萍,别放在心上。”茵茵的声音不像作假,我认真地看了她一眼,舒展的脸上笑容淡淡的,眼睛里也没有责怪的意思,手里那把碎花阳伞还不计前嫌地朝我这边倾斜了一些,于是我亦做出放宽心的样子——再计较倒显得我小气。
我喜欢茵茵叫我长萍时的调子,像两滴浓稠的墨汁从笔尖滴落,绵软而坚定。
茵茵有许多书,亦舒的居多,整整齐齐地码在简易的木质书架上,不上班的时候,她就坐在地上的抱枕上阅读。我加班归来,见着她塞了耳机缩在灯下读书的样子,是很恬静的一道风景。见我进门,茵茵起身赤脚往厨房走去,原来是给我留了傍晚自己做的樱花寿司。那寿司形状可爱,口感软糯,茵茵在旁边微笑地看我,一脸孩子气的满足,让人没有办法不喜欢。
我和茵茵不在同部门,午间在办公室休憩时,她是我们部的话题之一。办公室的女孩子们似乎都对茵茵的私生活有兴趣,在众人眼中,她是极善解人意的女子,气质温婉美好,值得被人好好珍惜,但茵茵似乎并没有男伴。开始我意外,后来又想通了,虽然她总能给人以爱情的感觉,但那感觉始终很淡,是有点过于寂静的美好,就像她衣橱里的那些款式怀旧的衣裙,美丽而不合时宜。我想不出什么样的男子可以与茵茵匹配,直觉告诉我,她有喜欢的人,因为她看上去很寂寞,一个女子寂寞的原因常常都是因为心里住着一个人。
我们从未对彼此提及感情,大概是觉得唐突,或者根本无济于事。
只这样和阮茵茵住在一起便觉得好,好像因此可以和葛栖迟稍微接近,而这幻觉时常让我感到羞耻。
离开B城时,葛栖迟并没有挽留我。
早在见面之前,葛栖迟就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他是个标准的“三不”男人: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我在电话里打哈哈,恬不知耻地说:“没关系,反正我是不要皮、不要脸、不要命地赖上你”。他不置可否地笑,又危险又魅惑。
在电话线里爱上一个男人,听起来不像25岁的女人做的事情,但我自己也说不清楚,那种没有来由的爱情的感觉,听到电话响都会引发小腿痉挛,悸动如初恋少女。
我认识葛栖迟是因为工作上有往来,我俩各自所在的公司之间是供销关系,许多业务需要保持联络。同部门的A少妇要陪幼子上钢琴课,B小姐约会太多,C先生则根本神龙见首不见尾,于是我时常独自加班至深夜才将数据整理出来。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葛栖迟总是低低地说“你稍等”,接着传来的就是走路时发出的衣角摩擦声,或嘈杂或慵懒的音乐像海潮起起落落。又过了片刻,传来打火机嗒嗒的声音,他告诉我:“可以了,嘶——这门口的风真大。”然后朗声笑起来。
那一刻,我环顾着只有一盏灯亮起的办公室,窗外是沉寂于暗中的高楼,好像在深海航行时才能看见的岸边的灯火,心里如灌满了风,动荡的都是倦倦的温柔。
渐渐地,我和葛栖迟说得越来越多。他白天是部门主管,夜里常在酒吧流连,过着都市白领*惯常的生活。有时他凌晨拨电话过来,却喊着别的女人的名字;有时他压抑得说不出话;有时他发信息过来:“长萍,我和几个朋友在天桥上唱歌,张国荣的《取暖》,忘词了,你发给我吧。”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不直接上网搜索,但只是怀着一些温柔,慢慢地将整首歌词用短信一条一条发过去。
“我们拥抱着就能取暖,我们依偎着就能生存……”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爱上了一个诗意、莽撞的少年,一个会在午夜的天桥上唱歌的男子,满怀湿漉漉的柔情。
那天是我先哭了——工作不顺。我是闷头做事的人,按功行赏时没有我,出了漏子却在会上被点名批评,被罚光所有的奖金。其实不是多大的事,只是听到葛栖迟的声音,我莫名地备觉委屈,还没开口就呜咽了。他笑说:“你怎么像个孩子?干脆来B城吧,哥们儿罩着你。”我哪里听得这样的话,很快开始收拾行装,辞职时赚到了许多不舍,平常偷懒耍滑要我做事的人倒真真假假地替我打抱不平起来,然而我去意已决。
也许葛栖迟那一句只是安慰的玩笑话,却碰上我这个“三不要”的死心眼。
我带着我的旧箱子去了B城。葛栖迟没有来机场接我,打电话说还在应酬,走不开。他身边是模糊而熟悉的嘈杂,应该是在饭局上。我打车在陌生的城市寻找葛栖迟的门牌,因为知道是他的地方,被放鸽子时心情竟然也毫不低落,像所有一心投奔爱情的女人那样盲目地快乐。后来我想起自己的卑微,原来许多“幸福感”都来自这样的自我催眠。
等至凌晨,电梯门轻轻地叮一声将我从打盹中惊醒,一个穿黑衬衣的平头男人向我走过来,我认出了他。我说:“你让我等这么久。”他扁了扁嘴,将我整个拉入他带着酒气的怀里,那怀抱让疲惫瞬间涌上。
我在葛栖迟家里住下,他没有固定的女伴,也不似自己说的那么不羁,我为此安心。
进入葛栖迟的生活并不困难,也许是因为他性情随和,也许是因为我们真正相处的时间并不很多,大部分被用来吃饭,说话,像朋友一样聚头。扔掉碗以后,他在客厅看电视,我在厨房洗碗,切换频道的间隙里他偶尔的一声咳嗽都让我有烟火男女的幸福感,碗槽里的油渍都变得亲切起来。葛栖迟的房间里开始有了我的物件:用掉一半的护肤品,西柚味道的洗手液,菜谱,甚至针线筐。空气里有我们共同酝酿出来的味道,也隐隐浮荡着别的陈迹,我不动声色地搜寻着,像急于占领一片土地的士兵那样,在葛栖迟家里发现了一些被圈定的角落,那是属于别个女人的深重痕迹。
葛栖迟并不爱我,这很显然。只是我从来不清楚自己可以这么细腻敏感,很多个深夜在他身边醒来,借着微光看他有些疏离的睡姿——两条手臂圈出小小的领地,并不真正让我靠近,我想,我须得承认我们彼此间始终不够了解,而他不让我了解。我只是怨恨自己,不知为何无法做到过去的粗心大意,为什么明知生活经不起推敲,还是要苦苦较真。
我对葛栖迟说打算去找份工作的时候,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是否打算长住B城,就像问过路人。
我的脸红了,讪讪地说:“当然,B城很好,何况有你。”
“我对你又不好。”葛栖迟吃着我做的糖醋鱼,皱着眉头抿着一根刺,语气轻描淡写。他没有一点点歉疚,我自然找不到责怪的理由,连发作的可能性都没有,只能感觉到周遭的空气都慢慢稀散,那些从他薄薄的唇间努出的鱼刺像是一根根扎进心里,痛得我倒吸凉气。
爱人原来只是徒劳。这个叫葛栖迟的男人,我涉足他的世界,重新布置他的房间,整理他的衣物,将他阳台上枯萎的植物拔除,全部换上我爱的品种,我以为他是因为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才默默地放任纵容。这一刻,我才忽然明白过来,这只是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我来不来,走不走,对他来说都是可有可无的,我不是他心里的那个人。
“说说而已,我打算走了。”我听到自己淡淡的语气,不知有没有强作镇定的痕迹。
“哦。”葛栖迟点点头。
很快就是冬天。在没有爱情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亦觉得自己特别有耐力,有时希望一头淹死在大堆做不完的文件里,再也不用考虑眼角又添多一条细纹此类琐事。倒是有几次从公司出来,我看见茵茵独自走过路口转角——应该是去约会——仔细打扮过的身影在路灯下被拉长得格外旖旎。我有点怅然,因为葛栖迟。
B城应该已经下雪了,他有没有夜夜喝酒取暖,心会不会冷?
新公司的年会在一间温馨而精致的会所举办,Cindy在薄薄的皮草大衣里面穿了一件胸口缀水钻的黑色吊带裙,耳朵上挂着某品牌的新款吊坠,大概是黑水晶,在暖暖的灯光下十分低调地华丽着。据说她家世甚好,表现出来的品位常常超越了行政经理这个职务,尤其站在妆容内敛的总监身边,有种喧宾夺主的气势。
女孩子们都穿得很美,乍一看满室衣香鬓影,营销部的莫娜甚至另带了两套衣服,分别在餐前和餐后穿。我照例在办公室做文件到*后时限,赶过去的时候还穿着平常的工装裤和毛衣。我眼花缭乱地寻找茵茵的影子,她果然坐在角落,一件白色披肩式的短大衣,下面是素色的锦缎旗袍、靴子,打扮十分优雅,手边端着瓷杯,照旧美得像一幅画。
“长萍,过来坐。”茵茵向我招手,我目不斜视地向她走去,因为住在一起,理所当然地比其他同事更加亲近几分。因为走得太快,我猛地撞上一个人,一个很高的陌生男人,穿着高领毛衣、牛仔裤。他扶住我,回头对茵茵笑:“你怎么能让女人都这么心急?”
茵茵朝他微一跺脚,脸就红了,有点嗔怒的表情,于是我看出一些端倪。
男人叫诸晨,公司高管,以行事不羁、作风散漫出名,但业绩甚好,据说曾在欧洲留学多年,现在常常满世界飞。我来公司几个月未见其真身,原来他也才30岁的样子,模样还挺过得去,有点像佟大为,浪子版的。诸晨难得来参加一次公司活动,在女职员的仰望中好像皇帝微服出巡。我有些刻薄地想,难怪每个人都极尽风骚之能事,恐怕都是在等着被临幸。我不愿意也如是想茵茵,却分明觉得她今日有点不同。
晚餐是自助式,诸晨不拿托盘,只在女人间穿梭,四处嬉笑讨食,占尽口舌便宜,一副浪荡子模样。这场景让我想起葛栖迟来,他们是不同类型的男人:葛栖迟外表冷淡,绝不肯温软讨好,不开心则立即表露出来,即便是在床上,也有着惊人的自控力;诸晨明显油滑许多,他对每个人都笑容可掬,即便是对初次见面的我,也赞了句“真是自然随性”,不管是不是真心,听起来**不讨厌,甚至会觉得有点荣幸。是的,这个男人极易让人产生被欣赏的错觉。
我想念葛栖迟,冷漠的葛栖迟,不肯爱我的葛栖迟,他不肯费一点心机维持和平。
诸晨和Cindy跳舞,和莫娜对唱,和姿姿拼酒,茵茵一直坐在角落里。从吃饭的地方到唱歌的豪华包厢,她不刻意地看他,而是微笑地和旁边的人说话,或定定地望着屏幕上不停切换的MV画面,喝果茶,吃零食,发信息,看上去没有任何不妥。我坐在另一边抽烟,远远地看着阮茵茵,我疑心她此刻是寂寞的,当然,也许这怀疑根本是出自于我自己的寂寞。
那夜我喝得有些醉,在回去的车上语无伦次地和茵茵说起葛栖迟,我问:“如果你是我,你会怎样,是会坚持争取,还是决然放弃,或者根本一开始就不给自己失足的机会?”记忆中她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握住我的手,一下又一下温柔地拍着,示意我镇静。
我将年会时的照片放在博客上,好几张都是茵茵,微笑的、白衣不染风尘的样子。
葛栖迟打电话来,声音冷冷的:“有意思吗,尹长萍?”
很久没有听到葛栖迟喊我的名字,虽然我们仍有些联系往来,但不过是询问对方近况,我刻意说得模糊,他并未仔细追问,我想我过得好不好,他大概都是不在乎的。他这样直接地发问,我忽地有些失措,不知道如何对他解释我来此地的初衷,更不知如何说我已经改变了初衷——我对茵茵,已经放下了任何预谋,我甚至不愿意去窥探打听她小心掩饰着的爱情脉络。
阮茵茵是葛栖迟深爱的女人,我知道这件事还是和葛栖迟见面之前。也许是因为没有预计到后来的发展,他对我说起过许多。他大学三年级时认识了低他一级的阮茵茵,他对她一见钟情,并展开了笃定而热烈的追求,然后顺理成章地在一起。阮茵茵始终表现得很恬淡,态度淡到有些漠然。他有些不甘,开始和另一个学妹走得很近,想以此刺激阮茵茵得到更多回应,没想到她尽管低落,却毫不争取,反而很快置身事外,大方地祝福他们。至此,葛栖迟回不了头,只得撒手走远,却从未真正地忘记过阮茵茵。
很多个电话里,葛栖迟醉时喊的都是阮茵茵的名字,直到现在,她的一帧旧照仍被他放在钱夹的*里层。在那个隐秘空间,葛栖迟觉得自己仍可以像大学时候那样和她心心相印,而后来的他,真是那样将他们的过去关在了一个小小的相框里,也将自己的心关了起来,从此再也没有住进过任何人。
离开B城,前来接近阮茵茵的生活,一开始我只是想看看她是个怎样的女人,竟能让葛栖迟在五年以后依然心怀挂念,难以忘却。后来我渐渐感觉出,阮茵茵的存在,怕是天生就要作为一种深刻的记忆在所有靠近过她的人心里变成永恒,就如她当初的软弱和退让对葛栖迟来说,是一根鲠在咽喉的软刺,偶尔触及都会疼。
“葛栖迟,我对茵茵没有恶意,我和她做了朋友,这事和你不相干。”
“是吗?”葛栖迟的反问透着浓浓的怀疑。
我发现自己非常失败,给所爱的人留下了恶俗的印象——他以为我会神经质地寻根到他的旧日恋人头上进行一番报复,但他忘了他们早已没有任何关系,我再不甘心都不至于迁怒于阮茵茵。
“恐怕我们现在要比你们亲近得多,我一针见血。”
“咳,因为都过去了,我不想她被打扰,也不想让她知道我仍旧……”葛栖迟没有说完,他的语气缓和下来,同样相当直接。
我们对所爱的人有多温柔,对不爱的人就有多残忍。他没有说完的内容清晰分明地钻进我耳朵里,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不会的,你放心。”我刻意冷淡了声音,不想被他听出软弱委屈,然后挂断线,捂着胸口长出一口气,抬头就看见茵茵从隔壁的洗手间走出来。她静静地看着我,眼里满是宽容和体谅,然后走过来轻轻将我拢住,我才发觉自己脸上都是泪。
阮茵茵自然是知道的,年会那天的晚上,我刻意将事情都说给她听了。没有别的企图,仅仅是想直面自己的悲哀,我只是想告诉她,我在爱着一个人,苦苦地爱,卑微地爱,却还是求不得,而这个人恰恰是她轻易就能够放掉的,不留恋的,甚至已经忘却的。那一刻,我很想走进茵茵的内心,看她是不是也怀着一样的无奈,一样有求不得的人,一样有欲说难言的痛,我知道一定有,比如诸晨。
我毫无根据地笃信着自己的直觉,诸晨不像茵茵会爱的人,但他肯定就是她爱的人。我没有问过茵茵,就在她轻抚我手的那一刻,在她安静而温和地看着我的那一刻,我想我们之间已经有了许多了然于心的默契。
年后公司有个会议,地点在附近的休闲山庄,类似农家乐的地方,藏在山里面,风景优美,据说娱乐设施也相当齐全。大家都乐得前往,假公济私的目的显而易见。
一群人开着车,潇潇洒洒地往山里驶去,打头的是诸晨的丰田越野,坐在他身边的是Cindy,后排放着大家的小行李,并没有其他人。他们一向走得很近,有点暧昧,但谁都没有真实的证据,只靠无谓的捕风捉影来增添许多谈资。
我和茵茵坐在后面的商务小面里,听着女孩子们议论Cindy和诸晨,语气中有莫明的打抱不平,大概是为了诸晨。她们在背后将Cindy称为肥婆,因为大多在工作上受到她的强势管制,甚至连她原本姣好的容貌和丰满的身材也否定掉,像是Cindy占了诸晨多大的便宜,其实说来说去,不过是嫉妒。
茵茵向来不加入这样的谈话,她看着窗外,我则看着她。
车子在山里开了两个多小时,曲曲折折,满目的绿色像是永远都不会结束,山路被刻意维护过,两边时不时会冒出精致的木刻路标,倒真的风景清雅,丝毫没有冬末的料峭。
车窗上很快结了雾,我几次睡着,醒来都发现自己靠在茵茵的肩膀上,她小心地倾斜着角度适应我,想来支撑得非常疲惫,走路都有些缓慢。
Cindy在前面招手,腕间露出一只淡绿的玉镯,果然和茵茵摔碎的那只一模一样。
不知是谁走在她旁边夸张地赞道:“呀,这个镯子真好看!”
她嫣然一笑,说:“是诸晨在泰国买的。”
我回头看看茵茵,她神色如常,淡得不着痕迹。应该是一起收到的礼物吧,我并未见别人有,茵茵又是平常职位,想来诸晨对她多少有些特别。但除却这个,如果一定要想出什么别的蛛丝马迹,恐怕是他们特别疏远,诸晨甚至不怎么和茵茵说话,玩笑亦有分寸,不像他和Cindy,简直如搭台演出,嬉笑怒骂,生怕周围嘘声不够热烈。像Cindy这样的女人,自身已经是活色生香的一台戏,图的不过是台上台下的热闹劲,要说她真正对诸晨有什么,那倒也不见得。
我们本就是黄昏才出发,吃罢晚饭已接近午夜,Cindy风风火火地号召大家上山露营看日出,有几个人响应,却没有看到诸晨。众人散去了,我和茵茵在小径上散步,我说:“Cindy真是精力旺盛,要搁战争年代,肯定是个女战士。”
茵茵笑:“她真是很能干,也很辛苦,自己还带着两岁的儿子。”
“噢?”我很意外,Cindy虽然年岁不小,但真看不出来有孩子。
“她先生不在了,是车祸。当时孩子还在她肚子里,她不顾家人反对生下来,为此还跟父母决裂了好一阵子。Cindy是太要强了,其实她的家境根本无须她再出来奔波,唉,若是换成别人……反正我是做不到这样的。”茵茵的语气像条丝绒带子在夜色里飘浮,她并未与我挽手,只是抱着自己的双臂,黑夜里渐渐腾起冷雾,寒冷使人怅惘。
我们一路走到山庄的地下酒吧。
说是酒吧,其实更像90年代末小城里的卡拉OK,放着很旧的酒廊舞曲,地上铺着一层彩色玻璃,下面的灯光打上来,照在天花板上吊着的塑料藤蔓上,将整个空间渲染得极不真实。幸好人不是很多,我和茵茵坐在吧台的高脚凳上,点了两瓶科罗娜。粉红艳俗的灯光照着茵茵雪白的脸,有种说不出的美丽。她真的是美女,美得没有一点侵略性。
吧台的服务生向茵茵搭讪,我百无聊赖地看着她身后。朦胧的光影处,诸晨和另外一个男人有说有笑地走过来,那个男人穿着白衬衣和黑色的羽绒外套,领带松开,发式是极短的平头,我们同时看到彼此。
是葛栖迟。
葛栖迟告诉我,在山庄见到阮茵茵时,他很想给诸晨一个耳光。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了,像所有的平淡夫妻那样,是一种更类似于好朋友的和谐关系。我没有奢求他有多爱我,但至少我爱过,争取过,这大概已经是我所能获得的*好结果。见过阮茵茵之后,葛栖迟似乎终于放下心结,不再耽于过往,而是任生命的河流顺势流淌,有缓有急,有起有伏,但总归向前奔流。
茵茵却像是独立在时光之外,她停住了。
诸晨是葛栖迟的同学,也是阮茵茵的学长,这是我之前全然没有想到的。原来当年他们同时在大学舞会上注意到瓷器般静美的阮茵茵,诸晨先去请她跳舞,待到她羞怯而肯定地将手交于他的掌心时,他却恶作剧地将手伸向她身后的女孩,可能是因为一贯乖张的作风,或者故作个性的姿态,总之诸晨将阮茵茵独自留在那里,幸好有个葛栖迟适时地出来为她解围。
从一开始,阮茵茵爱的就是诸晨,葛栖迟对她来说,不过是尴尬时借以下场的台阶。她与他舞着,却认真地为自己的轻率后悔,如果矜持一点,淡漠一点,诸晨是否就会对自己珍惜一些?
事后诸晨向阮茵茵道歉,说过分的行径是为了引她注意。她保持着优雅的风度,不声不响地和葛栖迟走在一起。之后诸晨出国,阮茵茵和葛栖迟分手,再之后她毕业,去了诸晨所在的公司就职,种种因缘辗转,不知可否用巧合一言蔽之。
阮茵茵仍爱诸晨,像我所感觉到的那样,却再未有过一丝积极。在这个凡事靠拼、靠抢、靠彼此厮杀直到头破血流的世界,她的种种矜持就成了无能。在爱人这件事情上,她多番痛恨过自己的软弱,却同时也珍存着它,就像她写得极好的那手楷书——无论书写着怎样疼痛的内容,远远看过去总是挺拔的,有种遗世独立的姿态。
姿态是很重要的,她不愿意为爱情厮杀拼抢令身段尽失,那样的爱来得太痛苦,并非出于本心。可是她也会想,不去争斗,难道他真的懂自己默默的坚守吗?也不见得。我猜茵茵常常都要设想一番,为每种假设找一个结果,和自己认真地计较着,末了想到因为没有放肆去爱一场,还是有点后悔,有点不甘,到底意难平。
那一晚我们四人在山庄的地下酒吧碰面,大概是诸晨的有意安排。然而,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甚清楚:让阮茵茵知道我和葛栖迟的关系?或者让葛栖迟了解,无论何时,阮茵茵仍在他的世界里?诸晨像个好胜心强的大孩子,因为被宠坏了,所以即便是对喜欢的女人,也无法坦坦荡荡地说:来,我们相爱。
恋爱像共舞,须得你进我退,或你退我进才有情有趣。
像诸晨的花招百出和阮茵茵的孤绝静立,终于只落得一个对峙的局面。
后来我敲开葛栖迟虚掩的房门时,他正凭窗站着,念及往事,背影越发孤单得有些苍老。我走过去轻轻拥住他。他知道是我,不会是别的谁,默默地按住我的手,长长地叹息一声。那隐忍而无奈的一声,让我们同时懂得了彼此的悲哀,亦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亲密默契。
不久之后,我和葛栖迟结婚,在B城,只宴请了双方父母和几个当地的朋友,茵茵和诸晨都有寄礼物来,却再没有更多消息。第二年年底,诸晨也结婚了,和Cindy。我有点愕然,但转念一想,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这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只要舍得放下身段,谁都可以谋得一席之地。
至于茵茵,我猜她还是那样美丽,像所有真正美好的女子那样不惧苍老地优雅着。
只是,青春却过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