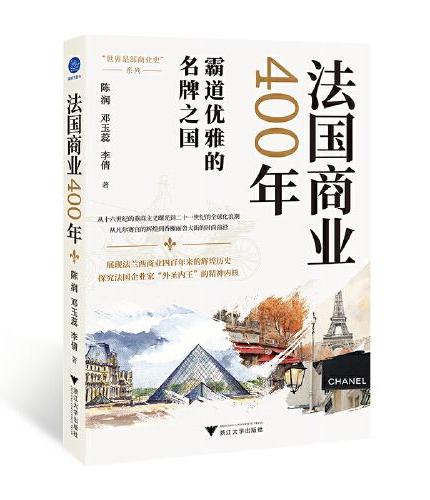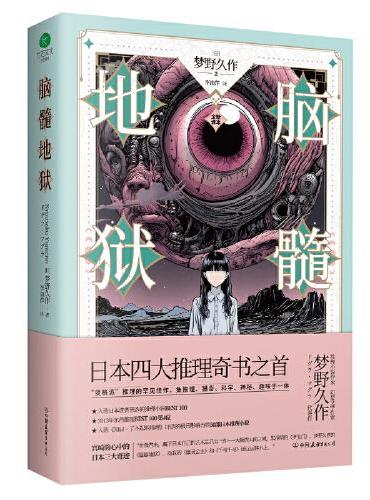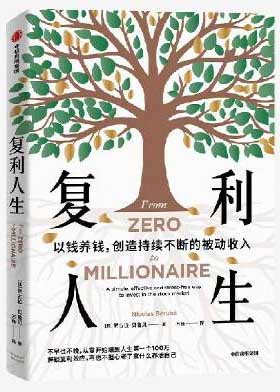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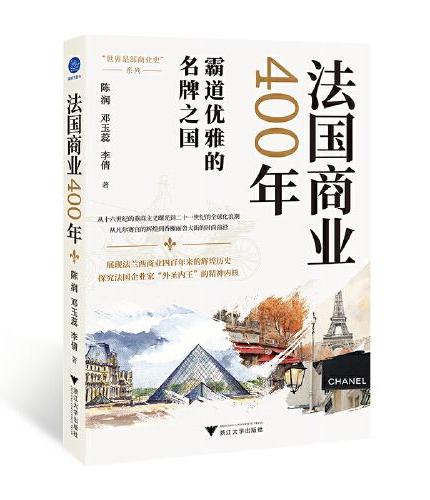
《
法国商业400年(展现法兰西商业四百年来的辉煌变迁,探究法国企业家“外圣内王”的精神内核)
》
售價:HK$
74.8

《
机器人之梦:智能机器时代的人类未来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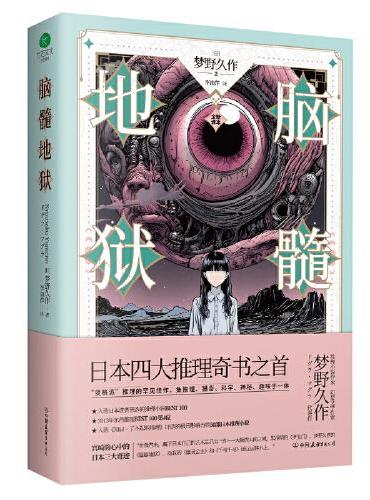
《
脑髓地狱(裸脊锁线版,全新译本)日本推理小说四大奇书之首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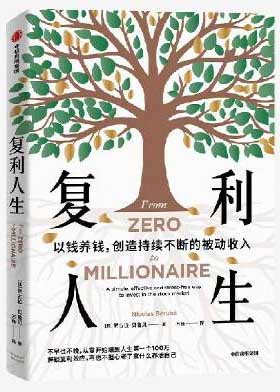
《
复利人生
》
售價:HK$
75.9

《
想通了:清醒的人先享受自由
》
售價:HK$
60.5

《
功能训练处方:肌骨损伤与疼痛的全周期管理
》
售價:HK$
140.8

《
软体机器人技术
》
售價:HK$
97.9

《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
售價:HK$
74.8
|
| 編輯推薦: |
本文作者是实力派作家、编剧卢岚岚。著名作家刘震云盛赞“卢岚岚的小说好看”,说“卢岚岚的小说好看。掩卷,又让人沉思。因为作者懂人物关系,懂不同的人物关系的结构。懂,是好的开始。就好像她说,写作是从**个字开始。”她擅长以绵密真实的文字直击人心,直击生活,征服读者。《每一个成年人都是劫后余生》作为作者全新力作,无愧于名家赞誉。
卢岚岚也是中国一流文学期刊热爱的作者之一,一有新作即被疯抢:《人民文学》《当代》《收获》《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均曾重磅刊登她的作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人民文学》副主编宁小龄也极力推荐《每一个成年人都是劫后余生》。
在《每一个成年人都是劫后余生》中,作者讲述了9个真实到冷酷,却在绝望里透出温暖的故事,这也是9篇写给这残酷世界的柔软战书。每一个看似平凡的人,每一种看似平淡的人生背后,都隐藏着本质上惊心动魄的故事。世界残酷,而活着的我们却竭尽全力,想在冷酷中触摸美好。这本书,帮你看清人生中的种种不堪,再给你勇气,扶你上马,再走上漫长的一程。
人生的残酷不在于戏剧化的大起大落,而在于不动声色的消磨与龃龉。《每一个成年人都是劫后余生》以绵密细致的文笔,
|
| 內容簡介: |
真实的人生就是不断犯错,不断碰壁,不断仓惶,不断执着;就是一次又一次面对绝境,却从绝望中抬起头来,再次抓住那一丝丝温暖与美好。
9个真实到冷酷,却在绝望里透出温暖的故事,几乎涵盖了文学与生活的所有重要主题:生存、苦恋、相守、恐惧、情欲、欺骗……有人想要给爱人一个灿烂前途,却赔上了自己又葬送了爱情;有人想要拯救可能破碎的家庭,却一步踏进了此生最大的阴影;有人原已泥足深陷,却又因一个丢失的钱包挖出了内心深藏的温暖和良善;有人早就对生活麻木,却为了一段旧回忆再度找回了温柔和希望……
每一个成年人都是劫后余生。这9封写给残酷世界的柔软战书,让你历历看清人生中那微妙的尴尬、蚀心的痛苦、明亮的希望、宝贵的柔情,给你勇气,扶你上马,再走上漫长的一程。
|
| 目錄:
|
仓皇的青春与爱情
不信时间能治愈
公开课
断指
草莓
荒漠甘泉
暑热的身体
飞翔的阻力
偷爱
|
| 內容試閱:
|
不信时间能治愈
四月里的一个星期三,我不是特意请的假,我是正好轮休。丈夫上班,儿子
上学,我就一个人了。
今天是母亲的忌日。
我没有告诉小学三年级的儿子;丈夫也不该记得这个日子。这么多年了,何
况偶尔跟他说起时,我只说母亲是那天走的,最粗略地带过原因。这种事,他不好深问下去。
吃了早饭背上包,丈夫带着儿子出了门,我在门口跟他们说再见;等他们进了电梯,我就跑去阳台等。一会儿,一大一小两个背影走出了楼门,走上小区甬道。两个人的手牵得好好的,高矮差好远,可是步态那么相像,我不禁要微笑。两人拐弯了,往学校方向拐去,我看不到了。不过我趴在栏杆上好久,转不过身来。我好像看到了二十六年前的我。瘦小,穿浅蓝罩衣深蓝裤子,梳两条辫子,虽然在读小学六年级,跟现在的孩子比,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智,大概都类似小学二三年级吧。假如二十六年前,我能陪着她走那条漫长的凄凉的路,静静的,牵着她的手,给她一点温度和力量,那该多好啊!她就不会孤孤单单,不会有那样的命运吧?
母亲的忌日其实不是我走那条路的那天,但我的记忆像一张洇湿的水彩画,那上边的颜料已渐渐溶成一团,分不清边界了。如今我时常以为,我从那条路上走回家,母亲死了。要使劲想,才能说服自己,这两件事其实中间隔了一天。
那条路,叫松木场路,现在一定不存在了。拓宽了,整治了,或许都在上面盖起了高楼,而且必定已经属于市区了。那一年那一天我独自走在那儿,它有多荒凉!两旁全是农田,或者树,或者孤零零的厂房。路面是碎石和粗砂混合,走在上面嚓啦嚓啦响;路基边一丛一丛野草,也是跟今天一样的风,风过来,野草就哗哗地倒伏、直起、倒伏、直起,我一路走去,遇见极少的人。几乎都是骑着加重自行车从旁掠过的农民。其中的一个骑车人,我是不会忘的。
今天是母亲的忌日。据我妹妹说,我父亲还好好地活着呢,还一人住在老家那个老旧的居民区里。我离开他已二十年,我不跟他说话已二十六年。我也从不主动向妹妹打听他的消息,她愿意说一点儿,随她,我听了不回应。她能告诉我的也不多,因为她定居上海。有丈夫有女儿的,只是周末打电话问一下他。问一下。我不愿意用“问候”这个词,这个词太温情,没必要。
丈夫怎么看这件事?我是一个没有了母亲、也像是同时没有了父亲的人。结婚前后,他试图跟我父亲见面,翁婿之间做热烈的沟通,彼此亲如父子,我想了几日,对他说:父亲再婚了,他和那个女人想过自己的日子,不想跟我们往来,双方都有子女,关系难处。——
一劳永逸的说辞。我再不必为此烦恼。
我离开阳台,走到卧室。床头柜靠墙边立着母亲的黑白照。年轻时候的照片,二十多岁吧。她走的时候也很年轻啊,比现在的我还小两岁。明亮的眼睛,温婉的笑容。我母亲很美,如果说我有美的地方,那全来自母亲。她在市图书馆上班,新书来了,要登记造册,还要在每本的书脊上贴一张红框的小纸片,她不做别的,她专写那些卡片、标签、编码,每一个数字都一样大小,每一个汉字都像是印刷体。不知道是工作让我母亲一丝不苟一尘不染还是由于母亲的性情才让她承担了这个工作,总之,我的母亲是又干净又整洁的,从里到外,像一本精致美好的图书。
我父亲,在一个大单位工作,他具体工作的科室可能比今天的总裁办公室还让人敬畏,让人臣服。他是房管科的科长,在那个房子由单位分配的年代,他见到的所有职工都是对他堆着笑脸的。每当面临分房,哪怕只是为了重新分配某个调走的职工的一个单间,我们家也跟过年一样。有许多人,当然都是分头前来,但都在夜黑时分,拎着水果,或者用报纸包了一条烟,或者是两瓶用结结实实的棕色包装纸绳绑住瓶颈的老酒。他们分别但都是同样的过程:放下礼物,然后坐下,母亲为他们泡一杯茶,他们顾不上喝茶,先说自家恶劣的住房条件,然后请父亲在分房工作会议上为自己说句话,父亲“嗯嗯”地点头应承着,来人放下心来,笑着赞美我和我妹妹,有时伸手抚摸我们的头顶,他们多半不敢久留,是否是怕父亲的应承会消失?急急要走,然后父亲起身送客,母亲跟在后边。客人说不完的“谢谢”和“再会”。
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房要分的日子。冬天刚过去,空气还很冷冽。天黑了,我和妹妹坐进被窝里。并排,靠着墙,穿着小棉袄。她翻连环画,我看《金陵春梦》。一本很艰深的跟“春梦”无关的大书,一套有好多册,我那时候虽然懵懂未开智的样子,却是个文学少年,看的尽是些大人都不看的生僻书。《金陵春梦》我当然也是看不懂的,看这种书可能跟母亲在图书馆工作有关吧。那天母亲不在,我想不起来她为什么不在家。也许是去看生病的同事,或者去给妹妹开家长会,也或者她自己身体不适,去医院挂个急诊拿点药。总之那晚母亲不在家,甚至那晚她回来了没有、她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再无印象。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占据了那块记忆的空间。
田阿姨来了。父亲把她迎进来。我们的老房子很奇特的,木结构木地板,两层楼,环成一大圈,于是有宽宽的回廊,中央是个花园。我家就是二层的其中两间。奇特是在于家家都没有厕所,去大马路上的公共厕所或者用箍了铜条的马桶,而我家却有个厕所!在三层!三层唯有那一间突兀出来的用作厕所的小板房,我不知道这是否与我父亲的职位有关。田阿姨进来了,我和妹妹喊她“田阿姨!”,她走到我们床边,摸摸我们的脸,手凉凉的。然后从提包里往外掏,掏出十几个橘子,搁在我们的被子上,让我们吃。我挺喜欢这个田阿姨,因为她气质高雅,皮肤很白,头发蓬松微卷,个子高,身段苗条。虽然她结婚了,有两个女儿,但我觉得她跟其他已婚妇女不一样,很脱俗,让人喜欢看。我以前去父亲的单位,见过她,她与许多人在一间极大的办公室里,每人一张桌子,堆满各种文件资料,好像做什么统计。
我和妹妹的床在外间,里间是父母的卧室。田阿姨就在里间卧室跟父亲说话。她家住得太遥远,远到公共汽车都不通,她又不会骑自行车,每天要先由老公骑车把她驮到公交车站,再搭两趟车,才能到单位。因为远,两个女儿都寄放在爷爷奶奶家,方便上学,周末接回家。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三年多了,当然以前连房子都没有。现在全厂职工都知道有五套房子可分配,田阿姨觉得应该来努努力,通过父亲这儿,“让领导充分了解我家住房条件需要改善的迫切性”。
类似田阿姨这样的话,有许多叔叔阿姨来我家讲过。所以我听到了,很可怜她们家,但是也没有觉得必须首先解决田阿姨家的问题。谁家都很迫切,谁家都是因为难处跑来我家的。
田阿姨说要回去了。她家很远嘛。经过我们的外间,跟我和妹妹打招呼道别,笑笑的,提醒我们:“吃橘子啊!”父亲这个时候在旁对她提议:“要不要上个厕所?我们楼上有。”
这个提议很正常,田阿姨一路回去,一两个小时里都没法上厕所的。她想了想,点头说:“好。”于是父亲走在前边带路,田阿姨也忘了跟我们做最后的道别,跟着出去。我们的门就开着。
然后我感到事情的怪异。从我们的房间出去,是公用的回廊,拐个弯,是那道极陡极窄的木楼梯。楼梯下方贴墙有根灯绳。父亲没有拉那根灯绳,他们是摸着黑上楼的。我没有如往常那样看到拐弯处射来的光,这使我感到怪。第二个怪是当他们上楼后,非常安静,时间好长。上个厕所该有的声音没有,却有不该有的时长。最后的怪异是当他们下来时,不是摸索的小心翼翼的脚步声,而是噼噼啪啪,凌乱不齐,听起来,像是一个逃一个捉。脚步立定后,静了一刻,父亲朝我们这边叫一声:“阿瑾,阿灵,田阿姨要走了。”父亲的意思是让我和妹妹再打声招呼。于是我和妹妹参差喊出:“田阿姨再会”、“田阿姨再会”,田阿姨却没有跟我们说“再会”,那儿没有再传来什么声音,除了她往外走的脚步声。那天晚上我感到的就是这些怪异,但我什么都不说。即使妹妹跟我同龄,我都不会跟她讨论的。我现在发现,小孩子都有一个充满疑惑和秘密的阶段,一个得不到答案的阶段,同时也是不想去寻求答案的阶段。
放下母亲的照片,我觉得不需长久地沉溺在过去。今天虽是个特殊的日子,但是日常的事情需要按部就班地做。我首先得把卫生间清理干净,床铺还乱着,丈夫和儿子匆忙吞咽下的早点还有残渣在盘中,我一点一点收拾,心里渐渐舒展开来。卫生间里儿子的小牙刷上残留着一团牙膏,不知他的牙是怎么刷的;叠他们两人的被子,发现一个好玩的共同点:睡前竖铺的被子这会儿都横过来了,可见夜晚他们都不安生睡;而早晨的煎鸡蛋,儿子爱吃蛋黄,父亲爱吃蛋白,所以我能凑成个完整的煎蛋替他们吃完。做这些事让我高兴,让我非常高兴。我碰到的所有东西都有他们的体温,都有他们的气息,让我安心。跟二十六年前的那一个星期比,现在我每一天都生活在安心中,生活在温暖中。
田阿姨来过的第二天,生活还是原来的样子,第三天,就变脸了。
晚上,吃了夜饭,母亲在一个拐角的公用厨房洗碗,我和妹妹写作业,父亲轻轻走过来,用手搭了搭我的肩,我回头看他,他还是轻轻地说:“你来一下。”
我起身。父亲走在前边,我跟着。父亲走去那道通往厕所的楼梯,手在墙边停了半秒,拉亮了灯,往上走,还回头看我跟上了没有。我们没说话,我好像知道这会儿该沉默,而不是连声问“怎么了?怎么了?”我们一齐走上三楼。
三楼有点儿像如今的露台,一半是露天的水泥地,一半是红砖和木板搭就的小厕所,蹲式的白瓷坑嵌在砌高的水泥台子中央。父亲在露天的暗地里站定,没让我等多久,开口问:“田阿姨来的那天,你记得吧?”
“嗯。”我点头。
“我对她做不好的事情了吗?”
什么意思?什么叫“不好的事情”?你对她做的又怎么来问我?我根本听不懂这个问题,于是我沉默不答,但我隐隐觉得大事发生了,而且这桩大事是一桩坏事。
父亲其实也不期待我的回答,他自顾自跟我讲述:
“我没有对她做什么过分的事嘛!楼梯黑,那天我没拉到灯绳,我怕她摔跤,我就好心扶她上来,她上厕所时,我就站在这个地方等,我没进去,怎么可能进去嘛!我晓得分寸的。是因为她上好了,你看,厕所不是高一块吗?我怕她地方不熟,要踩空,所以就马上过去搭把手,把她扶下来。就是这两个动作嘛!两个再小不过的动作。完全是客气嘛!”
他边说边做着手势,随着他的讲述指点我看楼梯啊、水泥台子啊,好像我是刚来此地的陌生人,不知周围环境。
“爸,你说这个做什么?跟我?”我语气平静地问,但我已经开始恼怒了。我听出了他的不端的举动,这让我觉得羞耻。一个女人上厕所,你本来都不该跟上来的,你还要伸手扶人家,扶两回!你真不要脸!还硬要说是好心,客气!
父亲听了我的疑问,刚才的争辩语气一下子跌落下来,变成了可怜兮兮:“她老公今天来单位找到我,说这个女人家回去以后就说我调戏她,扑上去,动手动脚,解她裤带,要强——”
我大喊一声:“爸!”我不想听见这么脏的用词。我从未听到过这种东西,比我亲眼看见还恶心!这么难听的词这么难看的事竟然来自父亲,我无法接受。
父亲收起话头。他往楼梯下方张望一眼,可能是怕我的这声大喊把母亲招来。我们静了几秒。楼上楼下都很安静,然后他叹了长长一口气。
他接着讲下去,更加的慌张,声音发着抖,像是在央求我,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他对他的这个卑怯可怜不加掩饰:“她老公说,只要房子分给他们,这件事就算了,亲啊摸啊随便它,房子不到手,大家都有的好看,弄到我们单位都晓得,弄得你姆妈单位都晓得,叫我们做不成人。”
夜空下这么两个人。做了丑事的父亲和唯一可用来倾诉的女儿。我觉得这两个人都可怜。几乎要被扒光了皮的父亲不可怜吗?有这么一个父亲的女孩不可怜吗?
我根本没想去问他一句:你到底对那个女人家做没做不好的事?这种问题我问不出来,也无需问。我已经确认父亲做下了肮脏事。谢谢你在女儿面前还要点儿脸面,没把话说透说清楚!不去拉灯绳,扶她上楼,站在一旁听女人小便,你已经足够肮脏了!你不需要更多的行为,我不需要更多的理由。我于是不追问他是否被冤枉,不追问他怎么找清白。他脸都不要了来告诉我是有原因的,我偏偏咬紧牙关不给他路走。
我们在夜空下对峙。
父亲败下阵来,肯定是他败,因为母亲的碗不会无休止地洗下去的。父亲开口:“你去找找那个姓田的,叫她不要把事情做绝。房子我尽量争取,但是,争取不到也有可能的。分房委员会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书记,厂长,副厂长,八九个人!”
“要找你自己去找。”我回答。
父亲叹息:“我要自己能去找,这件事情还告诉你啊?她老公今天差点要打人。我要去说房子没把握,他马上把事情闹开!你是小伢儿,你哭哭啼啼去求他们,他们应该会心软一软吧?”
我全身被痛心和愤怒填满。父亲一夜之间沦落到如同蝼蚁般由人捏咕,而这都是咎由自取,现在要让我也低声下气地去求人!我继续沉默。他沉默地等待。母亲的脚步声响起来了,我趁着这声音下楼梯。
p style="t
|
|